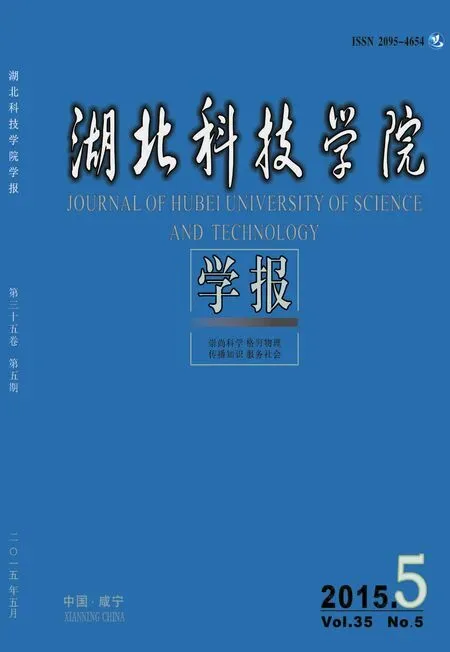小说名著翻译中的文体风格对等探研
——以引语翻译为例
程丽群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
小说名著翻译中的文体风格对等探研
——以引语翻译为例
程丽群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
以文学文体学为理论依据,以小说名著《傲慢与偏见》和《红楼梦》的源语文本为对象,选择它们在句法层面上典型的引语译例,分析、比较原文与译文的文体风格对等问题,避免假象等值,提高翻译质量。
小说名著翻译;文学文体学;文体风格;对等;引语
一、风格对等的理论依据和研究范围
小说名著的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翻译,译者需很好把握原著的艺术魅力,充分认识到语言形式与主题意义和审美价值之间的深层关系,将原文蕴涵的美学功能与风格对等呈现于译文中,这可从文学文体学中找到理论依据。
文学文体学特指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审美价值为目的的文体学派。它是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注重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申丹,2002)。通俗而言,文学文体学是一门研究语言在文学中的运用情况的学科,反对只凭主观判断,主张从语音、词汇、语法及篇章结构入手细读原文,挖掘作者的语用意图和语用效果,重点分析文学语篇的语言风格特征,从而获得审美享受和精神体验。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与成熟,文学文体学越来越多地用于指导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尤其是指导译者在小说翻译过程中,对原著文本进行细致的文体风格分析,发掘小说语篇的美学意义。总之,文学文体学的应用是寻求翻译中达到最大风格对等的有效途径,也是译文读者理解和欣赏小说语言艺术的关键。
不同的文学作品文体风格迥异,各具特色。风格问题是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译出风格是文学翻译的全部指归(周仪、罗平,1999)。小说的文体风格具体反映在它的艺术风格、思想风格和语言风格之中。既然文学文体学研究的焦点是作品语言的运用,那么语言风格的对等翻译应该是提升翻译实效最重要的途径。语言风格是人们在书面或口头语篇中运用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它是作者用语言表达手段所形成的各种特点的综合表现(孙燕,2002)。《傲慢与偏见》和《红楼梦》都是经典的现实主义语言盛典,作品中超强的艺术表现力和非凡的语言风格魅力是其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利奇和肖特将那些可能产生风格的语言特征称为风格标记(Leech、Short,2001),笔者在此选择两部名著中的一些句法层面上的引语标记翻译,探讨译本与原著的文体风格对等问题。
二、引语风格标记
两部小说名著中引语的妙用的确令人叹为观止。作者精心设计了一系列鲜活生动和意韵深长的引语来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表达情感冲突、塑造人物形象和性格,从而突出作品的主题意义。
1.《傲慢与偏见》的引语分析
Page认为《傲慢与偏见》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风格的成功(Page,1972)。而该小说一个重要的句法风格标记之一是使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叙事,以揭示话语的微妙内涵、展示人物性格和冲突、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作品尤其不惜笔墨,通过创设大量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里很自然的夫妻对话,实现了贝内特先生与贝内特太太两个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原著一开始,奥斯汀就根据话题、夫妻情绪和叙事节奏的变化,巧妙选用不同类型的引语和转述动词展示话题冲突,向读者推出了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妻子饶有兴趣、情绪高涨,丈夫反应“迟钝”、冷淡低调。孙译在表达上与原片段风格相当,并同样忠实地使用直接引语描述妻子的唠叨,用间接引语、简短陈述句和自由直接引语点明丈夫在三个话轮中的“漠不关心”。这样的译文契合原文的语言形式,较好地保留了原语语言表达简炼、情节的冲突性增强的美学效果,实现了文体风格等效。
小说原文第一段里贝内特先生与太太的对白,生动的以直接引语呈现的对白表面上看平淡无奇,实际上言语中充满了步步为营的嘲弄意味,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奥斯汀选用一连串明快、简练的直接引语的目的是让贝内特太太的亢奋与兴致和贝内特先生的故意不合作与装愣形成鲜明的对比,营造一个戏剧性的冲突开端,为进一步展现丈夫寡言、狡黠和妻子无知、势利的鲜明个性做铺垫。孙致礼的译文虽然言简意赅,但笔者认为有两处翻译欠佳。一处是“思谋”二字笔墨过重,不足以传递原文诙谐挖苦的语言风格,因为奥斯汀笔下的贝内特太太是一个外露愚蠢,遇事欠分析欠考虑的人,还不如改为“盘算”或一个简单的“想”字。另一处译文“跟女儿们有什么关系”不能充分显现贝内特先生对妻子唠叨和无知的厌烦感。如果试译为“关我们女儿们什么事?”则能更好地暗示丈夫的自认高明和对妻子的愚逗。
2.《红楼梦》的引语分析
《红楼梦》第32回中有这样一出场景:
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惊又喜,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的知己,自然我也可为你的知己,既你我为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呢?既有“金玉”之论,也该你我有之,又何必来一宝钗?…(曹雪芹,1979)
此情景讲述的是黛玉走进屋,听到宝玉评论自己时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内心真实的情感活动,其语言形式用第三人称述评和故事内人物的自由直接引语描述。
杨宪义夫妇将其英译为:
This surprised and delighted Tai-yu but also distressed and grieved her. She was delighted to know she had not misjudged him, for he had now proved just as understanding as she has always thought. Surprised that he had been so indiscreet as to acknowledge his preference for her openly. Distressed because their mutual understanding ought to preclude all talk about gold matching jade, or she instead of Pao-chai should have the gold locket to match his jade amulet…
霍克斯的英译如下:
Mingled emotions of happiness, alarm, sorrow and regret assailed her.
Happiness:
Because after all (she thought) I wasn’t mistaken in my judgement of you. I always, thought of you as a true friend, and I was right.
Alarm:
Because if you praise me so unreservedly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your warmth and affection are sure, sooner or later, to excite suspicion and be misunderstood.
Regret:
Because if you are my true friend, then I am yours and the two of us are a perfect match. But in that case why did there have to be all this talk of“the gold and the jade”Alternatively, if there had to be all this talk of gold and jade, why weren’t we the two to have them? Why did there have to be a Bao-chai with her golden locket…
小说翻译中很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假象等值”,即为了追求译语与原文内容对等,很多译者不自觉地忽略原作语言形式所蕴含的深层文学主题意义,不大注意原作的语言形式美,随意改变原作的句法结构,使得译文读者无法欣赏到原作真正的文体价值和风格神韵。
表面看来,杨宪义夫妇的译文意顺晓畅,与原文内容大体相同。但仔细研读发现杨译与原文形合神不合,文体风格不对等。从文学文体学的视角分析,首先,原文中场外人物客观述评与场内人物主观思衬并存的语言形式生动地揭示了黛玉复杂的内心想法。“喜”、“惊”、“叹”之后的自由直接引语非常适合表达黛玉的主观心理活动,也对塑造黛玉特有的性格很有帮助。而杨译采用的平行陈述句式将黛玉对宝玉的主观想法变成了客观事实,也就是说黛玉“从想法的产生者变成了事实的接受者(申丹,1998)”,这明显与黛玉原本敏感多情、疑惑不安的性格不相吻合,削弱了原作要表达的黛玉对宝玉的痴情色彩。其次,自由直接引语的连续使用形象地展现了人物丰富的情感变化,特别是黛玉对宝玉的称呼由“他”向“你”情不自禁的转变缩短了情感距离,这对暗示原作中黛玉至爱宝玉而又疑虑重重的主题意义有着积极的作用。毋庸置疑,杨译客观化的陈述无法还原黛玉对宝玉的亲切指称,这就意味着原文通过自由直接引语和人称变化所创建的美学功能和文体风格在杨译中荡然无存。所以,杨译与原文风格是假象等值。
相比而言,霍克斯的翻译在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方面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它较好地再现了原文中黛玉主观心理活动和情感变化所蕴含的文体价值。由于汉英语言结构的差异,霍译灵活运用“She thought”和“Because”来实现英文形合语言的连贯性和逻辑性,并降低了三个平行的场外叙述语向场内人物主观想法突转而带来的非协调感。但是,霍译坚持用第二人称指称宝玉的做法,不及原文中“他”称转向“你”称引发的情感效果强烈。换言之,霍克斯对人称转换背后隐藏的人物情感与小说主题之间的紧密联系认识不足,自然也有点不忠实原文的风格之嫌。再来比较黛玉初遇宝玉那一幕的两个译例:
原文: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到:“好牛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
杨译: His appearance took Daiyu by surprise. "How verystrange!”she thought.“It's as if I'd seen him somewhere before.He looks so familiar.”
霍译: Dai-yu looked at him with astonishment. How strange! How very strange!It was though she had seen him somewhere before,he was so extraordinarily familiar.
原文生动表达了黛玉第一次见到宝玉时那种似曾相识的诧异和震撼,曹雪芹善于使用自由直接引语丰富人物的情感联想,反映人物的主观思想。对两种译文进行细致的文体分析就不难发现,杨宪义的翻译比较忠实原文,也契合原文用第一人称表达内心想法的语言形式,即与原文风格基本对等。霍克斯的译文虽然表面上忠实、顺达,却不符合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第三人称叙述重客观、第一人称叙述重主观的文体特点。这种以间接引语代替直接引语的翻译方法,无形中将人物自然流露的主观想法和情愫演变成了客观认定的,平淡无奇的事实,大大降低了黛玉那油然而生的震惊感,削弱了小说名著的文学美感,更重要的是违背了小说表达的黛玉与宝玉“木石前盟”的主旨意义。因此,霍译与原文在文体风格上有较大相差。
三、结语
小说中引语的妙用能够反映鲜明的人物性格特征和复杂的心理情感活动,有效推动故事情节向高潮发展。由以上分析可知,《傲慢与偏见》和《红楼梦》中创作精巧的引语产生了良好的文体效果和文学审美情趣,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小说翻译尤其是名著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进行细致的文体分析,保留原文蕴意无穷、妙趣横生的引语表达形式是保证原文与译文文体风格对等的一种有效途径。实践证明,译者只有关注原文语言形式与主题意义和文体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译文中的再现,才会避免原文与译文在风格上的“假象等值”,提高翻译质量。
[1]Page Norman.The language of Jane Austen[M].Ox ford:Basil Blackwell,1972.9.
[2]曹雪芹.红楼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重印).
[3]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220.
[4]刘霞敏.《傲慢与偏见》对话描写艺术的文体分析[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4).
[5]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申丹.略论西方现代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中的作用[J].外语与翻译,1998,(4).
[7]申丹.论文学文体学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J].中国翻译,2002,(1):11~15.
[8]孙燕.文学风格及其翻译[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S3):334~347.
[9][英]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M].孙致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8.3.
[10]许钧.风格与翻译 —— 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风格的传达[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174.
2095-4654(2015)05-0063-03
2015-03-02
H05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