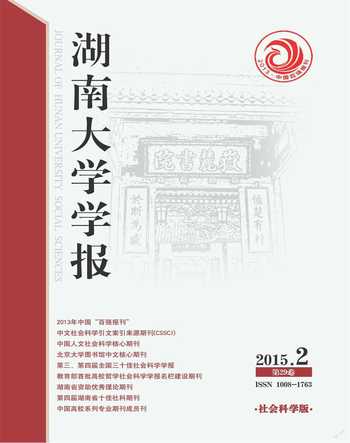抗战时期张舜徽先生在湖南的学术成就*
周国林,孙建伟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蓝田国师,创建于1938年,是设立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的简称。校舍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李燮和老家修建的府第,即李园。蓝田国师环境优美,“院舍在蓝田镇北里许之光明山,冈峦起伏中,横宇林立,前后古木参天,境极清旷。”[1](P4)虽处抗战期间,仍有不少著名学者来这里任教。钱基博是该校招牌性的学者,学校大门和大礼堂的对联、院歌都出自他的手笔。除钱基博外,第一批来该校的教师,还有汪德耀、任诚、钟泰、袁哲、罗睿[2](P114-115)等著名学者。钱钟书也曾来该校任教,《围城》中的“三闾大学”即以蓝田国师为原型。
张先生于1942年9月17日由杨家滩至蓝田国师,开始了其人生至为重要的一站。张先生来该校任教与钱基博、马宗霍二位前辈学者有密切的关系:“无锡钱子泉、衡阳马宗霍两先生主讲国立师范学院,过采虚声,谬加招揽,书问稠叠,令人感奋,适骆绍宾先生亦自辰溪来蓝田,相与怂惥,其议乃定。余自惟拙劣,岂敢抗颜为大学师。既辞不获已,乃强起应之。”[1]P3在蓝田国师期间,张先生居第一院李园东楼,“松竹四合,苍翠异常,”非常怡人。与张先生“洽比而居”的除钱基博先生外,还有阮乐真、曾金佛、吴忠匡等。张先生《八十自叙》中所述的“年过三十,始都讲上庠”[3]P108即指蓝田国师任教之始。蓝田国师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和学术氛围,为张先生潜心学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一 友朋切磋,壮议振俗,立论学之伟愿
张先生任教蓝田之始,即树立了论学之伟愿,从其新用斋号“壮议轩”可知。1942年11月3日日记:
朝食后,收到徐绍周丈寄来所书“壮议轩”额横幅,书法甚健,当付装池,悬之壁间。余生于辛亥七月,去秋三十已满,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如斯,因取《大戴记》之语,名所居曰壮议轩,以期昕夕省惕,庶几免于无业之讥,非敢高论以忤俗也,实欲诵先正之法言,无违于正,以免俗耳。昔阎潜邱晚而笃学不衰,自扁其居曰老教堂,盖亦有取于《大戴》之义。吾于潜邱,无间然也。今之采于斯以自勖,亦以慕大贤云。[1](P97-98)
张先生所云《大戴礼记》之语,出自《曾子·立事》:“三十四十之间而无艺,即无艺矣;五十而不以善闻矣,七十而无德,虽有微过,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讽诵,其壮不论议,其老不教诲,亦可谓无业之人矣。”[4]P75这段话的意思为,人生分为“讽诵”、“论议”以及“教诲”等三个阶段,三十至四十岁之间正值人生之壮年,应该有所“论议”,努力成为“有业之人”。张先生认为自己已过而立之年,应该在壮年有所论议,在学术上有所作为。任教蓝田是张先生在学术生涯上由“少”而“壮”,由“讽诵”而“论议”的重要转折时期。张先生在蓝田国师时期“壮议”学术,大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友朋之间,切磋学问。张先生同前辈学人讨论学术相当频繁,其日记中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如1942年10月29日,张先生午后到骆绍宾先生家,论议清代经师之利弊,及近人治学之风气,并对其师黄君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认为黄君有为人所仰慕者三事,可以矫厉末俗者三事:
盛推其师蕲春黄君高绝不可攀望。综其学诣,为人仰慕者三事。读《说文》、《广韵》烂熟,于均学尤为专门,一也;思理缜密,读书无一字跳脱,二也;文辞雅艳,三也。黄君学术精密,诚如绍宾先生所言,不为溢美。余尝从武昌徐氏假观黄所批校群书,及其往还书札甚多……则其专力致精,常通夜不眠,宜非它人所能及。然余以为此犹黄君之小者,未足以尽之。吾独得其学行之大,可以矫厉末俗者,有三焉:天性醇厚,事嫡母至孝,一也;绝顶聪明,而治学以愚自守,二也;不附和时下风气,卓然有以自立,三也。[1](P88-89)
在蓝田国师期间,张先生同钱基博先生“朝夕相见,谈论欢洽”。张先生在纪念钱基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所作的题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崇高典范》的讲话中忆起其与钱基博先生的交往情况:
记得和钱子泉先生第一次通信的时候,是在一九四一年的春天,那时我刚三十岁,而他已五十多岁了。我在署名的上面自称“后学”,这是应该的。但先生在回信中却说:“后学撝谦,非所克当,获廁友朋,为幸多矣。”我于是发现这位老学者是一个很谦和的人,容易接近。不久,我应国立师范学院之聘,到蓝田任教,与先生朝夕相见,谈论欢洽。时间虽只两年,往还却很稠密。[3](P360)
张先生日记中有多处关于与钱基博先生讲论学术的记载。如在1942年9月25日的日记中,有与钱基博先生讨论“北岳之学”的记载:
钱翁以为北岳之学,由义理以贯典制,推典制以归义理,经经纬史,颇似南宋之永嘉金华学派……与余所见略同。钱翁撰《近代文学史》,未及录北岳。自去岁余赠以《北岳遗书》,读而好之,故能窥其微处。余谈次,又力劝其补入《文学史》,以表章之也。[1](P6-7)
又如在1943年5月3日的日记中,有与钱基博先生讲论《百年来湖南之学风》一书的记载。张先生认为该书“属意可谓盛矣,”同时也从书名和著述义例两个方面,对该书所拟录入人物之去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知其近欲撰《百年来湖南之学风》一书,就湘贤事迹叙述之,藉以作厉士气。所采自罗、曾、左、郭、江、刘、王、李诸公外,益以汤海秋、魏默深、王壬秋、阎季蓉及今人章行严共十五人,但从诸人困心衡虑时论议行事加以阐扬,以为后人处贫贱患难者之鉴。其属意可谓盛矣。惟余以为,既以“学风”名书,则王壮武特于治戎为长,不合入录,与不得已,附之罗山传末可也。章行严至今犹存,以著述义例言,不录见存之人,避标榜也。余举此二者告之,不知其果能听取否也。[1](P421-P422)
除钱基博先生外,张先生同钟泰、马宗霍二位学者论学亦多。在同辈学人中,张先生与董世昌、张汝舟、阮乐真、曾金佛等人亦时常讲论学问。
二是品评时贤,激扬学风。对于当时人的著作,张先生亦能秉持公心,予以评述。如对于梁启超、钱穆二家考论清代三百年学术源流之书,张先生认为梁氏书但叙清初大儒,而未及乾嘉以后;钱书晚出,较为翔实,而漏略亦甚。1942年9月27日,张先生在研读钱穆之书后,对该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取材广博,采择精当,持论平实,能见其大,指出该书成就远在时下一般著述之上。但同时亦指出该书“可补者实多”:
自余观之,可补者实多。梨洲之下,宜附以邵念鲁,以其为章实斋史学所自出,不可忽也。颜、李之下,宜附以刘继庄、王昆绳,以其羽翼习斋,同归致用,兼举并列,相得益彰。戴东原宜有惠定宇,以其开吴学之先河,足以匹敌东原,不当在东原下……章实斋之前,宜有翁覃溪,救敝之言如合符契,岂容偏废?曾涤生之下,宜取刘霞仙与罗罗山并举,义理之言刘氏所发尤多,实为湘学后劲,自船山以来未之有也。此特就其显见者言之,至其它必待充实者尤多。[1](P12-13)
张先生不苟时俗,不附会时议,对于其时已经形成风气的学术观点,亦敢于大胆发表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在1943年4月13日日记中,张先生指出孔氏有维系人心、济补刑政之功用,对废孔之说加以驳斥:
夫孔子生于周末,去今二千四百余年,其所论说容有宜于古而不适于今者,且人事日新,文明日进,而谓吾华立国之道求之孔氏而足,是固拘虚之见也。虽然,立国于大地,必有其所以维系人心于不敝者。孔氏于既往二千年中为天下纲纪,足以济刑政之所不及者实大且多。今欲有所革易,自必先立一新伦理之中心思想,而后可譬诸窭人之子。今渐富矣,恶夫茅茨采椽之陋,必别营峻宇彫墙而后可徙也……故言废孔可也,废孔而不别图树立伦理之中心思想不可也。[1](P370-371)
紧接着,他又指出“孝”为先民教民之本,与华夏之存亡息息相关,并以邓禹之举为例,对非孝之说予以驳斥:
若夫善事父母之为孝,先民以为教民之本。吾华夏历数千年而见灭于异族者,亦赖有此耳。其与乎邦族存亡之故盖有二焉:一曰人才之消长系于此也……二曰国民忠愤之思必基于此也……昔余读《后汉书》,深服邓禹初入长安,遽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诣洛阳,其智虑为不可及。有此一举而天下归仁,胜于临之以兵,施之以政万万也。呜呼,此岂敢为异论高言之书生所能梦见哉
对非孝废孔之说的驳斥,体现了张先生的真知灼见,及独立、冷静地思考学术、学风的理性态度。
二 遍览群籍,如克名城,成学术之宏基
蓝田国师“略无尘俗之扰”的环境给张先生潜心读书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张先生在教学工作之余,遍览群籍,为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张先生的读书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敢于读大部头的书,制定计划,日有定程。张先生恪守“攻书如克名城”的古训,对于经史要籍,立志要遍搜尽读。张先生读书有自己的计划,计划一旦制定,就会严格执行。以其在蓝田国师时读《宋史》和宋人、清人文集为例:
其一,以一年之力,尽心以治《宋史》。1942年10月6日日记:
今税驾此邦,略无尘俗之扰,爱日以学,期竟前功。所宜汲汲从事者,其《宋史》乎?余近来思研寻宋学精蕴,尤非通知其史事不可,期以一年之力,尽心以治之。[1](P39)
次日,张先生即往图书馆借阅宋代史书。1942年10月21日,张先生发愤以归熙甫之言自厉,定读《宋史》以为日课:
自明日起,定读《宋史》为日课,虽百忙亦不可间断。昔归熙甫深于此书,钻研不替,集中有《宋史论赞》一卷,每言“人患《宋史》多,我正患其少”,此通人之言也。余治此书,当昕夕奉斯言以自厉。[1](P61)
据张先生晚年“至一九四四年,当吾三十三岁时,全史校毕”[16]之语,可见宋史以下诸史,正是张先生任教蓝田国师时校读完毕的,张先生严格地执行了自己的读书日程。
其二,以十年涉猎,遍读宋人、清人文集。1942年9月29日日记:
暇思清代学术,其耑悉自宋人开之……由此言之,有清一代之学莫不渊源于宋。今欲穷清儒之根株,必先明宋学之流别。余自今以往,当取宋清两代之书纵心力读之。期以十年涉猎,庶几免于一孔之讥矣。计余此时已读清名家集,不过三十余家;宋名家集,不过十数家……弇陋已甚,安可不自勉耶?”[1](P20-21)
1942年10月28日日记中亦有“宋元两代博通之人极多,余必求其文集而遍读之”之语。《清人文集别录》的结撰,正是其纵心力以读文集的最好证明。
二是善于将读书、思考和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张先生的日记中,有大量的阅读文集后所作的要点摘录及评说的记载。如1942年11月25日日记中摘录了魏了翁文集中的论“文”之语,并指出其“议论通达,实获我心”:
魏鹤山论文之言曰:“仰观俯察,而日月之代明,星辰之罗布,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凡物之相错而粲然不可紊者,皆文也。近取诸身,而君臣之仁敬、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夫妇之好合、朋友之信睦,凡天理之自然而非人所得为者,皆文也……”议论通达,实获我心。吾平昔持此论久矣,而古人已先言之。士生今日,阅览不可不博也。[1](P162-164)
1942年10月23日的日记中,张先生在读完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外集》之后,对陆陇其之学进行了评价:
陆清献之学,专宗朱子,排斥陆、王甚力。论学大旨,具于《学术辨》三篇(《文集》卷二)。它若《答嘉善李子乔书》、《上汤潜庵先生书》、《答同年臧介子书》、《答秦定叟书》(《文集》卷五)诸篇,亦大有关系。观其论阳明处,未免过苛。然俌弱扶微之思,固足尚也。《四库提要》称其学问深醇,操履纯正,此八字盖足以尽之……吾观清献论太极理气,虑犹涉乎超玄,未足以喻诸中下之资。其教诲学子,平易正直,而可循者则有在矣。[1](P66-68)
张先生日记中所作的摘录和评说,既是材料的积累,也是其学术观点的总结。张先生很多重要的学术著作都能从日记中找到材料或思想渊源。如《清人文集别录》中关于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外集》的观点与日记中所述非常相近:
为学专宗朱子,排斥陆王甚力。论学大旨,具见是集卷二《学术辨》三篇。其次若卷五《答嘉善李子乔书》、《上汤潜庵先生书》、《答同年臧介子书》、《答秦定叟书》诸篇亦大有关系……由其论学定于一尊,自不免举一而废百。言论所至,又不第诋斥陆王而已。[6](P54-55)
三是乐于读书,以读书为人生最大的乐事。张先生读书非常勤勉,“每日凌晨三时辄醒,醒则披衣即起,不稍沾恋。行之毕生,受益至大。起床后,整顿衣被几案,迨盥漱毕,而后伏案观书。”[7](P216)几十年如一日,寝馈于群籍之中,人不胜其苦,张先生但觉其乐。1943年1月12日日记中有关“劳”、“愚”的一段话颇能道出张先生读书所达到的境界:
近来读书甚勤,不觉疲惫,而领悟亦日进。从知以劳自养,则精神愈用愈出;以愚自处,则聪明愈用愈灵。能守此劳愚二字以终吾身,必无不成之事。勉之而已。[1](P288)
在张先生的日记中,常能体会到其读书时得意忘言的愉悦心情。1942年11月3日日记:
如言鹿有粗义,鹿裘乃裘之粗者,非以鹿皮为裘也。鹿车乃车之粗者,非以鹿驾车也。《吕氏春秋·贵生篇》颜阖鹿布之衣,犹言粗布之衣也。此解真谛,得未曾有。一语道破,积惑顿消,快慰之至。”[1](P98)
1943年3月16日的日记中有“得此一言,冰解的破,欢欣鼓舞,得未曾有”[1](P331)之语;1943年3月18日的日记中有“偶悟及此,无任豫悦”[1](P335)之语;1942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有梦见关中大儒李颙的记载,梦境与读书相连,与所景慕之先贤“精诚与通,亦可喜也。”[1](P87)此中真趣,实难与外人道。
三 结撰名作,广植根基,开一代之学派
在蓝田国师任教时期,张先生伏案著述,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完成了校雠名作《广校雠略》的写作。《广校雠略》是一部推衍郑樵《校雠略》思想的著作。从其日记推测,《广校雠略》的撰写应始于1943年上半年,完稿当为年底。张先生在《三十五年来我是怎样把教学和科研结合在一起的》一文中对《广校雠略》有详细的介绍:
当我在三十二岁(一九四三年)的时候,便开始《广校雠略》的撰述,首先谈到“校雠学”名义及封域,然后因论立题,分为古代著述体例、标题、作者姓字标题、补题作者姓字、援引古书标题、序书体例、注书流别、书籍传布、书籍散亡、簿录体例、部类分合诸论。这是有关介绍古书情况的部分。继之以书籍必须校勘、校书非易事、校书方法、清代校勘家得失诸论。这是有关阐述怎样校书的部分。再继之以审定伪书、搜辑佚书诸论,而以汉、唐、宋、清学术论结尾,共一百篇。这是我讲授校雠学的最早著作。[3](P583)
《广校雠略》是张先生在蓝田国师任教期间,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是张先生的开山之作。该书是他三十岁之前的治学小结,也是他一生著述的起点。1958年,他提起此书时,指出书中的某些内容,“仍不失为愚者千虑之一得”:
十五年前,我写过一部《广校雠略》(有壮议轩自刊本),是推广郑樵《通志·校雠略》的体例而写作的。主要谈到了学术流别、著述体例、以及目录、校勘、辨伪、辑佚等多方面的问题。当时是用文言文写的,因论立题,各相统摄,共一百篇。现在看起来,其中有些内容,仍不失为愚者千虑之一得。[8](P210)
可见张先生对《广校雠略》一书亦是颇为重视和满意的。作为《广校雠略》的附录,《毛诗故训传释例》亦完成于该时期。
二是完成了《清儒粹语》等资料长编的纂辑工作。张先生在撰写学术著作之前,很注重资料的收集和纂辑,以为其学术立论提供材料支持。如张先生欲撰《清儒通义》,并不急于动手,而是先进行材料的“博求”和“周采”工作,完成了《清儒粹语》、《清儒识大编》的编纂,并计划另纂《清儒著述叙录》,以为《清儒通义》的撰写做准备。1942年12月31日日记:
余年来搜辑清儒论学之文,分令及门手录者积百数十篇,今日付书肆,分装成三厚册,命之曰《清儒识大编》,此后犹当博求而周采之,以充斯篇帙也。自去秋发愿欲撰《清儒通义》,自惧才力不足以任此,姑先为长编,以俟异日写定可也。凡吾所录《清儒粹语》及此《识大编》,皆《通义》之底本。此外犹思纂《清儒著述叙录》,以甄录有清一代之书,苟能成此三种以当长编,庶几《通义》可涉笔矣。[1](P249)
三是完成了《郑雅》的纂辑以及《两戴礼记札疏》、《逸周书》校释等著述。张先生旧有写定“九雅”的计划,《郑雅》为其中的一种。所谓《郑雅》,即“纂郑氏《礼注》、《诗笺》及佚注之辑存者”[31]而成之书。张先生在六七年前已开始了《郑雅》的编纂,并已完成部分工作,但一直因“分心它业”而迁延未成。1942年10月30日日记:
余尝持论以为,考辨群经名物,必以郑氏为宗,而取贾、孔之说疏明之,浩然欲撰《郑雅》一书。《礼注》、《诗笺》综录略定,既已写为《三礼郑注义类》、《诗笺义类》二种,臧之箧衍六七年矣。惟诸经佚注未及排比。频岁奔走四方,恒以郑氏佚书自随,思乘暇隙竟此全功,率以分心它业,不克专意于斯,坐视无成,良足叹息。[1](P90)
1943年3月17日日记中说:“余尝发愿欲篹《郑雅》,久而无成,近乃矢志为之。”[1](P331)这大致上是张先生集中精力纂辑《郑雅》之始,整个《郑雅》的定稿工作,用了约四个月的时间。《郑雅》经过了张先生细致的剪裁,已非一般的资料汇编可比。《郑雅》一书,后来成为张先生《郑学丛著》中的一种,是他最为珍视的一部分。
1942年12月7日日记中有“自今日起,校《逸周书》”[1](P185)之语;1942年12月30日有“《逸周书》初校毕”[1](P247)之语。从该日日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先生为校释《逸周书》所费功夫之大:“此书旧多脱误,不可卒读。自卢文弨、丁宗洛、王念孙、洪颐煊、庄葆琛、朱右曾、何秋涛、徐时栋、陈逢衡、朱骏声、俞樾诸家相继考校,残书阙简渐复可观。”[1](P247)其校释成果在四年后又重加整理,写成《周书小笺》,于40年后,编入《旧学辑存》。收入《旧学辑存》中的《两戴礼记札疏》亦完稿于该时期。
张先生的治学范围非常广阔,著述颇丰。张先生后期的一些重要著作,如《清人文集别录》、《中华人民通史》、《说文解字约注》、《清儒学记》以及《经传诸子语选》、《周秦诸子政论类要》等,皆能从蓝田时期找到其渊源。在蓝田国师任教期间,张先生壮议学术,遍览群籍,著书立说,并制定规划,积累材料,为以后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钱基博先生曾预言张先生“异日必享盛名,足以自开学派。”[1](P729)张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上的开创性贡献,与他任教蓝田时期的治学经历密不可分。
[1] 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2] 李洪岩.钱钟书与近代学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3] 张舜徽.讱庵学术讲论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清)王聘珍撰.王文锦 点校.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张舜徽.旧学辑存·叙目[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8]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序言[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以《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