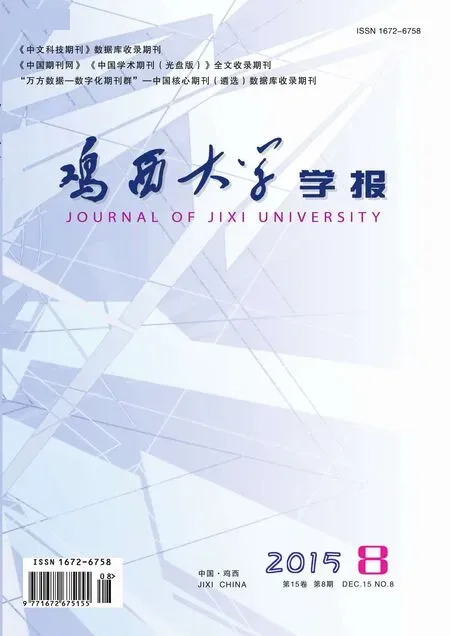论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
陶沙,夏伟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论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
陶沙,夏伟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实行过限的认定与责任归属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实行过限是行为在主客观层面均予以过限,即主观层面超越共谋范围,客观层面超过共同行为。就过限责任的归属而言,应当联系共同犯罪的结构性特征,按照过限犯罪与共谋犯罪之间的关系分为构成要件重合、交叉以及排斥三种情形,并个别化的予以考察。
实行过限;主客观共同过限;归责原理
对于任何犯罪而言——不论采取何种主客观立场,行为人都只在其主客观相对应的范围内承担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由于各行为人都是独立的意思主体,因此部分行为人超越“共同意思”而实施过限行为实属不可避免的状况。但此时,应当如何认定实行过限以及如何分配各行为人的责任,刑法理论上仍然纠缠不清。此外,鉴于共同犯罪实行过限涉及到责任轻重的问题,进而对量刑产生实质的影响,因此,研究此问题亦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一 问题的由来
认定共同犯罪实行过限的核心在于确定各个行为人的归责问题,即当部分实行行为超越“共同谋议”范围时,责任应当如何分配。任何定罪模式,都需要对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进行综合考察,在主客观相对应的范围内认定犯罪的成立。这种对应性的规则同样适用于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即原则上只能追究对客观过限行为存在主观罪过的行为人的责任。然而,由于共同犯罪本应当作为一个犯罪整体来考量,而且各个行为的因果效力往往贯彻共同犯罪的始终,非过限实行人的相关行为通常对过限行为的实施提供事实上的便利,此时如何从这一整体中分离出“个人责任”则是此问题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我国现行刑法理论上对此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研究的重点停留在实行过限的认定上,且往往混淆实行过限的认定与实行过限的责任归属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方面,现有研究文献的研究集中在对实行过限的认定上,并时常为了“创新”需要对实行过限作出不符合规范的限定。如有的学者认为,实行过限只能是一种“故意犯罪”,亦即在“共同故意之外实施的故意犯罪行为”,而不能是过失形态。[1]尽管刑事立法将共同犯罪的罪责形态限定为故意形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行过限也要受到此种约束;况且,为了全面地贯彻法益保护主义的思想,理论上也不得不承认过失共同犯罪的形态。因此,过失实行过限在规范上和理论上均不存在障碍,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将其排除出实行过限的概念范围。另一方面,受到“先入为主”观念的影响,容易将实行过限的认定与责任归属这两个原本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等量齐观。如有的学者认为“实行过限的判定标准”是该问题的“核心”,决定着“行为人责任的承担”,[2]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在实行过限认定标准之外再确立一个归责的依据。诚然,对于绝大部分情形而言,实行过限的认定基本上可以确定对某一犯罪的归责走向。但是,共同犯罪的特殊性表明仅仅认定实行过限还远远不能够解决过限部分的责任归属问题,例如,在结果加重犯型共同犯罪实行过限场合,基本犯的各行为人共同具备着防止加重结果发生的注意义务,在这种情况下,非实行过限人往往也要对过限结果承担责任。由此可见,实行过限的认定只能很偶然地解决在通常情况下个人责任的承担问题,完全贯彻这种逻辑思维在某些情况下会消解共同犯罪的“共同性”特征。
二 实行过限的本质:主客观共同过限论之确立
1.当前学说及评述。
何种行为偏离了共同犯罪的实行路径,进而可以成立刑法意义上的实行过限,刑法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归结起来有主要有以下三种。
(1)超越共同意思说。该说认为,实行过限是部分行为人超越共同的实行意思的情况,即该部分是行人偏离了按照共同的犯罪意思所要求的“举止行为”。[3]按照此说的观点,在共同正犯的情况下,部分行为人的过限行为只能
个别地加以归责,而不能共同负担。例如,A、B、C三人共谋入室盗窃,其中A负责望风,B、C负责实行,其中C在A、B不知情的情况下单独完成了抢劫,此时就抢劫责任而言只能归属于实行人C。在狭义共犯的情况下,在正犯实行超越共同意思的情况下,就超越的部分单独对行为人进行归责;在正犯行为不足——即尽管已经着手实行但是没有实现构成要件结果——的情况下,依照共犯从属性理论,限缩共犯的责任范围。“超越共同意思说”强调实行过限的主观面,即共同意思的范围决定着实行过限与否,对于责任主义的维护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共同犯罪的结构特性表明,对于实行过限的处理必须全面考虑各个行为人之间的关系,否则必然会造成处罚的不当。在结果加重犯型共同正犯的场合,各行为人的共同注意义务会对责任的归属产生实质的影响
(2)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论。该说为日本通说,认为,共犯的实行过限实际上是“共犯所认识到的犯罪事实与正犯所事实的犯罪事实之间的不一致”的共犯错误的一部分,属于共犯的抽象事实认识错误。[4]于是,实行过限中各个行为人的责任就转化为抽象事实认识错误下行为人的责任问题,此时,根据日本判例、通说之构成要件符合说[5]应作出如下处理:对于过限实行人而言承担过限责任,对此不存在疑问。对于非过限实行人而言,如果过限之罪与非过限之罪存在构成要件上存在包含关系,则在罪名、科刑上取较轻之罪,如在基本盗窃罪与过限抢劫罪之间,非实行过限人仅对被包含的盗窃罪承担刑事责任;如果过限构成要件之间不存在这种包含关系,则构成共谋事实未遂犯与实现事实过失犯的想象竞合,从一重处断。该说通过将实行过限转化为抽象的构成要件错误的问题,进一步解决非过限行为人的责任分配问题,其一劳永逸的优点是显而易见。但是,(1)从事实层面看,实行过限人作为独立的意思主体,能够独立的支配其自身的行为,其意思并不能时刻的反映给共同犯罪中的非实行过限人。(2)从理论层面看,错误理论仅仅适用于解决故意责任问题,对于过失过限[6]情况下的归责问题,由于缺乏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基础,错误理论并不能提供解释方案。
(3)超出预见范围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应当根据行为人对过限行为有无预见来确定是否成立实行过限。[7]也就是说,在共同犯罪中,只有当非过限实行人对于过限行为没有预见,才能够免除其过限部分的责任;相应地,即使该结果超出了行为人“共谋”范围,只要非实行人对于该过限结果有预见,就要对该结果承担责任。然而,“预见”这一概念具有价值相对性的特点,难以确立具体的标准。实际上,“预见”也好,“没有预见”也罢,都是从行为人的角度来确定过限责任的归属的。可是,如果从行为人角度看待这一概念,其总是主张对过限结果没有预见,因为该结果超出了“共谋”范围;但从司法机关的角度来看,由于造成了过限的结果,往往更倾向于推定行为人对于结果有预见,并对该过限结果对其归责。可见,对预见的有无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标准,站在不同的角度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难以与客观主义刑法立场向协调。
2.真正的实行过限:主客观共同过限。
如前所述,主流学说事实上均没有为实行过限的判断确定一个合理的标准。从主客观层面考察客观过限行为与主观共谋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种形态,即客观过限、主观过限和主客观共同过限。下面,笔者将就这三种情况分别予以检讨。
客观过限的情形下,非实行过限人对于过限结果没有认识、预见或者即使有认识但是依照当时的情形无法对非实行过限人进行责任归属。前者如多人共谋伤害,其中一人无罪过地导致他人死亡的场合,则对于该过限部分无论如何也不能对行为人进行归责的。因为,尽管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过限结果,但是由于缺乏主观上的罪责基础,无法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对于非实行过限人而言,不论其主观上对客观有没有预见、认识,也不应当要求其承担客观上不属于其所造成的结果。
主观过限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意欲超越共同范围而实施某种犯罪行为,但是客观上没有着手实行。主观过限中,过限部分仅仅停留于思想层面,属于思想犯范畴,不具有刑事意义上的可罚性。例如,共谋伤害的数人中,有人意欲实施杀害行为,但是出于恐惧没有实施。不过,由于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的特殊性,在很多情况下共同犯罪本身就为过限行为的事实奠定了基础,可以归属于过限之罪的预备行为,此时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具备相应的犯意,是否能够肯定其可罚性则有待商榷。不过,从限缩处罚范围的角度考虑,对主观过限情形不归责是比较合理的做法。
实行过限的本质是客观共同过限,这是由认定实行过限的目的所决定的。刑法理论之所以研究实行过限的认定,是因为实行过限的认定必然涉及到责任的由谁(不论是实行人还是非实行人)承担的问题,不涉及任何责任承担的情形,在刑法理论研究上没有意义或者意义微小,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实行过限。笔者认为,实行过限的认定只涉及认定本身的问题,只解决在什么范围内过限责任应当被承担的问题;而责任归属解决的是责任应当如何承担、由谁来承担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因此,二者不能等同视之。既如此,实行过限的责任首先要由过限实行人承担,其次才能进一步讨论非实行过人的责任问题,也就是说实行过限的认定必定要使得实行过限人承担过限责任,此时根据犯罪成立判断“无时无刻不遵循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8]也必然要求过限行为人主观上超越了犯罪的共同意思,客观上超越了共同行为,从而使得二者在主客观层面得以统一。
三 实行过限的责任归属:以客观构成要件为中心
认定实行过限的本质,认为只有在“主客观共同过限”的场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行过限,然而,紧接着必须要回答的是:对于实行过限应当如何责任归属?为解决此问题,
应当对“主客观共同过限”的情形进行类型化区分。根据过限之罪与共谋之罪在客观构成要件层面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情形,即构成要件重合、交叉以及排斥,对于这三种情形下的责任归属问题,应当在坚持责任主义(主要是自己责任)原则的基础上,考虑共犯之间的特殊关系进行个别的判断。
1.构成要件重合的过限。
构成要件重合的过限,是指除却过限行为之外,各行为人的行为在构成要件内是重合的。在此情况下,根据罪名之间是否存在结果加重犯关系,可以区分为结果加重型实行过限与非结果加重型实行过限。
结果加重型实行过限发生在后罪与前罪具备包含关系的场合,如故意伤害罪与故意伤害致死、一般抢劫罪与抢劫致死等。对此种情形下实行过限的责任分配问题,刑法理论上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基本行为上存在共犯关系,所以各行为人对于加重结果的发生具有共同的注意义务,对于加重结果也成立共同正犯。[9]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对于结果加重型实行过限,“其他之人应否同负加重结果之全部刑责,端视其就此加重结果之发生,于客观情形能否预见”。[10]笔者支持第二种观点,因为,一方面结果加重犯=故意的基本犯+过失的加重结果,而按照过过失犯的基本构造,行为人对于客观结果之发生至少具有预见可能性才能承担过失责任。另一方面共同犯罪的特殊结构表明,各行为人对于防止加重结果的发生有着共同的注意义务,即防止在客观上发生加重结果。
对非结果加重型实行过限的责任问题,由于过限部分往往单独构成其他犯罪,此时需要回归到犯罪的本质进行个别化的考察。例如,甲与乙共谋入户盗窃,乙看到熟睡的女主人丙遂生邪念实施强奸行为。此时,原则上由行为人乙单独承担责任,即使甲对于乙的强奸行为有预见或者知悉也不例外。这是因为,甲参与盗窃的行为与丙被强奸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并且甲也没有对丙事实救助的法律义务。
2.构成要件交叉的过限。
构成要件交叉的过限,是指行为人所共谋的犯罪与过限实行人所实行的犯罪不一致,且两罪在构成要件层面存在一定交叉。如前所述,日本刑法理论对于此种情形是按照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来处理的,就结论而言,非实行过限人成立的是前罪故意的未遂犯和过失的后罪的想象竞合犯。然而,从基本常识上看,并没有过失教唆这种情形,想象竞合犯的成立前提根本不存在,换言之,该说最大的缺点在于其机械的逻辑演绎过程可能得出与生活常识相悖的结论。
事实上,对于上述教唆犯的情形,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已经给出了合理的结论,只要依照罪刑相适应原则即可与之匹配。我国刑法第29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受“理论现行”——即为了在我国贯彻共犯从属性与共犯独立性之争——的因素的影响,刑法理论上对该条的理解局限于“教唆之罪与被教唆之罪相同且未达到既遂”的情形。然而,刑法解释得以展开的首要依据是具体的条文,其次才能选择合适的理论。而从文意上看,本文所讨论的“构成要件交叉情形下的实行过限”正位于“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文义范围,且此情形在实质上与该款所规定的从轻或者减轻情节相匹配。
3.构成要件排斥的过限。
在共同正犯场合,由于过限之罪完全超出了共谋之罪的范围,过限行为在客观层面与共谋行为划清了界限,根据责任主义原则,由过限行为人个人承担责任。但应注意,如果非实行过限人如果通过自己的意思或者行为扩张了犯罪计划的范围,则仍然需要承担责任,不过此时已经不属于实行过限的范畴。在狭义共犯场合,由于共谋之罪与过限之罪在客观层面不存在任何关系,即狭义共犯行为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因此,按照因果共犯论,狭义共犯人的客观责任也被否定,换言之,此种情况下狭义共犯人也不应当承担责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狭义共犯行为对于过限行为没有任何作用,而是没有犯罪构成要件意义上的客观作用。例如,A教唆B盗窃,B接受教唆却实施强奸的情形下,虽然两罪在客观层面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就主观上引起犯意而言,教唆行为仍然可能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只不过,由于客观层面的事实不存在,无法奠定值得刑法处罚行为的客观基础,因而根据主客观共同符合的原则也不能追究狭义共犯人过限部分的责任。
[1]冯英菊.共同犯罪中实行过限的判断——色诱抢劫案中女性帮助犯的定性[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02): 105.
[2]叶良芳.实行过限之构成及其判定标准[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8(01):89-90.
[3]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总论(卷二)——犯罪行为的特别表现形式[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25.
[4][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M].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21.
[5][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M].刘明祥,王昭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203-208.
[6]肖本山.共同犯罪的过失过限[J].法治论丛(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9(01):42.
[7]王昭武.实行过限新论——以共谋射程理论为依据[J].法商研究,2013(03):102.
[8]刘艳红.实质犯罪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0-21.
[9][日]山口厚.刑法总论[M].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48.
[10][台]林钰雄.新刑法总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42.
[11][日]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M].钱叶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Study of Surplus Behavior in Complicity
Tao Sha,Xia Wei
(Law Schoo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1189,China)
The determination and imputation of surplus behavior are two different things.In essence,surplus behavior is that the behavior exceeds connection of“common intent”in the subjective aspect,and oversteps common behavior in the objective aspect.As for imputation of the surplus responsibility,it is linked with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 of complicity,the surplus behavior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kinds of situations:constitution overlap,cross and rejection,and each situation should be observed individually.
surplus behavior;exceed in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spects;imputation principle
D924.11
A
1672-6758(2015)08-0069-4
(责任编辑:蔡雪岚)
陶沙,在读硕士,东南大学。研究方向:刑法学。
夏伟,在读硕士,东南大学。研究方向:刑法学。
Class No.:D924.11 Document Mar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