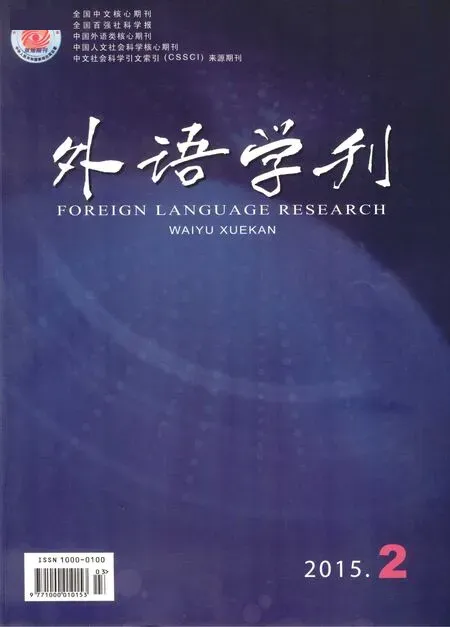美国黑人女作家的白人女性书写*
曾竹青
(中南大学,长沙 410083)
美国黑人女作家的白人女性书写*
曾竹青
(中南大学,长沙 410083)
托妮·莫里森、艾丽丝·沃克以及雪莉·安·威廉姆斯小说中的白人女性既是白人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她们将白人女性塑造成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形象实际上是在影射美国妇女运动中迫使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走向分裂的种族主义问题。在书写白人女性与黑人女性的分离与和解中,莫里森等向我们指出超越种族主义藩篱、实现所有女性解放和平等的途径——推翻白人男性权力的统治。
黑人女作家;白人女性;白人男权;受害者;加害者
1993年,记者比尔·莫耶斯在采访托妮·莫里森时这样问她:“你打算何时写白人?”实际上,早在1981年的《柏油娃》中,莫里森就已经开始书写白人人物了,更不用说以一个白人女性视角叙述的《宣叙》(1983)了。除了莫里森,与她同时代的艾丽丝·沃克、雪莉·安·威廉姆斯等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中同样也有白人人物出现。在这些黑人女作家对白人的书写中,白人女性形象尤其引人瞩目,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既是白人父权社会的被压迫者,又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这些白人女性的双重身份实际上折射出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中存在的种族主义问题。在莫里森等人创作的年代,种族主义造成了美国女权运动内部的分崩离析,不管是黑人女性还是白人女性都急需找到一条超越种族隔离、实现所有女性解放的途径,而莫里森等人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了这一探寻的过程。
1 白人男权社会的受害者
沃克、莫里森和威廉姆斯小说中的白人女性多来自于中上阶层。在她们笔下,这些中上层阶级的女儿和妻子们尽管从表面上看一个个锦衣玉食,但实际上,她们都是父权社会的被压迫者。当她们是父亲的女儿时,她们是婚姻市场待价而沽的商品,等待她们的只有一种命运:体面的婚姻,为家族带来利益。在雪莉·安·威廉姆斯所著的《德沙·罗斯》中,鲁斯是富有的棉花厂主的女儿,在父亲和叔父的眼中,她的人生目标就是找个富裕家庭的儿子做丈夫,既能让她今后的生活有保障,又能促进家族的生意。在婚姻市场上,美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托妮·莫里森《柏油娃》中的马格丽特,她的“令人惊奇的美”使她从寒门女一跃而为豪门妻。而对于在家人眼中相貌平平的鲁斯而言,要想俘获多金郎,只能靠衣装了。因此,为了吸引更多的追求者,鲁斯要盛装参加每一次的社交舞会,这就使得她整个少女时代都是在怎样将自己装扮得更美中度过的。法国的丝绸、来自巴黎的时装、蕾丝花边……怎样穿戴才能打败谁谁家的女儿等是她每天与人讨论的话题。在男权中心主义主导的社会中,美丽的衣裙和精巧的装饰物是男性规约女性的工具以及男性欲望的投射物,舞会上包裹在这些云裳羽衣中的鲁斯如同市场上陈列的商品,承受着男性欲望目光的注视,成为出价最高的男子的战利品。
而当这些战利品被优胜男带回家后,等待她们的是压制自我成为丈夫眼中的贤妻良母的规训。在这样的规训中,丈夫们扮演着威严的引导者的角色,如《柏油娃》中马格丽特的丈夫瓦莱里斯特里特先生,在马格丽特眼中,他就是上帝, “她从未想过他会犯错”(Morrison 1981:59)。而在丈夫的眼中,妻子都是些需要被引导的头脑简单、任性的孩子。婚前吸引瓦莱里的马格丽特的“惊人的美丽”到了婚后却变成了幼稚、无知的代名词,她的高中学历被无限放大,在丈夫及丈夫周围的人蔑视的眼光中,她就如同琼·芳登在电影《蝴蝶梦》中扮演的角色,在丈夫的豪宅中手足无措。当然,这些丈夫们从来不在物质上对妻子们吝啬,他们满足她们这方面所有的欲望,但一旦她们要求自主和独立时,他们不是嘲弄就是打压。艾丽丝·沃克《紫色》中的市长在市长太太的几次要求下给她买了辆车,但从不教她驾驶。每天市长回家都要看一看妻子,再看一看停在院子里的汽车,用嘲弄的语气问道:“米莉小姐,你觉得那辆车怎样?”(Walker 1982:107)。在美国,车是自由独立的象征,而市长的嘲弄和不愿意教开车表明他既不相信也不愿意妻子有独立意识的能力。同样,玛格丽特在物质上要什么,她的丈夫都满足她,但当她执意要带黑人女仆去看电影时,她的丈夫以他特有的平静,却不失威严的,同时还带着点嘲弄的语气阻止她这样做。当未达到目的后,他干脆将她抛入冷战中,让她恐慌,不知所措,只有屈服。最后,在丈夫无时不在的严厉的目光的监督下,马格丽特终于如丈夫所愿记住了豪宅中那些奢华精美物什的名字,记住了叉匙正确的摆放位置,明了了她与黑人家仆之间的界限,成为了与豪宅匹配的举止优雅得体的贵妇人;也如他所愿为他诞下家族产业继承人,保住了她在豪宅中的一席之地。
这些丧失了自我的女子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独立意识。鲁斯在她丈夫抛弃她后,完全没有经营农庄的经验,只有依赖她的黑人保姆多卡斯和逃到她的种植园的黑人打理,依照其中一位逃奴阿达的说法:“要不是我们,她早就饿死了”(Williams 1999:174)。当《紫色》中市长的女儿发现丈夫不再爱她而向索菲亚哭诉时,索菲亚建议她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她却装作没听见这个建议,因为在父权社会规约下长大的她从来就没有独立养活自己的意识。而马格丽特宁愿在肉体上折磨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来舒缓被压抑的痛苦也不愿独立。按照黑人女仆的说法,她将自己唯一的儿子分裂成两部分。对于属于她那部分的儿子,她宠爱他,感觉只有在他面前她才觉得自己是个有独立人格的人。而对于属于丈夫那部分的儿子,她用针扎他,用火烧他,报复丈夫对她的蔑视和压制。
不管是将女性物化为商品也好,还是对她们进行压制自我的贤妻良母的规训也好,这些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男性的厌女情结。自中世纪以来,基督教文化对女性持两极化的认识,一面是“怪罪夏娃的肉体罪恶论”,一面是“推崇崇拜圣母的贞洁观”(卢丽安 2013:73)。由这两极化认识所形成的厌女情结和厌性思想看似矛盾,实则互为因果,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男性控制女性的权力。在原罪论话语中,女性历来被形容为邪恶的色欲引诱者,是她们将罪恶带到这个世界上,而男性是她们放荡的肉体的受害者。为了摆脱被女性放荡肉体俘虏的命运,男性自命为上帝的代理人和裁决女性德行的法官与监督者,以圣母贞洁的身体为典范,编造出纯洁高尚的处女玛丽这样的神话来祛除女性所谓的与生俱来的罪恶(Hooks 1982:29-31),将她们规训为服从于父权和夫权的良家女子。
而当厌女情结与种族主义联手时,这些白人女性的身体还背负了另一项罪恶,即背叛白人种族,玷污白人种族的纯洁性。黑人学者路易斯·戈登曾这样描述白色种族主义社会中白人女性的处境:在反黑人种族主义者的眼中,白人女性不是纯洁无瑕的珍珠。“因为隐藏在她的白色之中的……是反黑人种族主义者所怀疑的黑色……每一个白人都会对她身体白色的纯洁性打个问号。不像黑人女性只能生出黑色小孩,白人女性既可以生出白色小孩也可以生出黑色小孩,正因为如此……白人女性被视为既吸引人又让人厌恶的可怕的东西。”(Gordon 1998:305) 对黑白种族混交的恐惧使得白人种族主义者都患上黑人男子要强奸白人女性的妄想症,在维护白人女性贞洁和白人种族纯洁性的旗号下,白人种族主义者疯狂地对黑人男子处以残酷的私刑。埃米埃特·提尔事件就是典型的案例。这个住在芝加哥的14岁黑人少年就因为到南方探访亲戚时朝白人女子吹了下口哨,当晚就被白人男子秘密地处死。就这样,在弥漫着厌女情结的白色种族主义社会中,白人女性身体被迫承受着种族权力、仇恨与恐惧的重负,被塑造成“象征白人男性权力”的符号(Hall 1983:334)。 在艾丽斯·沃克的《梅里迪恩》中,林恩的遭遇充分说明这一点。
林恩以她的白人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与她断绝关系的代价追随民权运动分子黑人青年特鲁曼,但却发现她在黑人中的处境十分尴尬与艰难。在黑人与白人之间不允许通婚的年代,她和特鲁曼不能同时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更为令人沮丧的是在黑人眼里她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在民权运动中心工作的黑人男性都害怕她:“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只有他们才不把她当女人看待。对他们而言,她就是通向死亡之路。他们从骨子里感觉到了她身上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力”(Walker 2003:146)。也正是白色种族主义附加在她身上的这种权力成为了托米·奥德强奸她的借口。托米·奥德有意识地将他对林恩的侵犯当作是一场反对压迫的“白色”起义,后来他鼓动另外3名黑人去强奸林恩的说辞也是“白人强奸了你们的祖母、母亲和姐妹,现在该轮到你们上场了”(Walker 2003:175)。在这种情形下,林恩不能将她的受害经历告诉任何人。如果告诉黑人,没人会相信她、同情她;如果告诉白人,只会又掀起一股迫害黑人的浪潮。在屈辱的沉默中,林恩成了种族仇恨的替罪羊。
2 白人种族主义的加害者
尽管这些小说中的白人女性在白人男权社会中是被害者,但她们同时也是白人种族主义加害者。《德沙·罗斯》中德沙的女主人得知她最能干的园丁凯恩被她丈夫打死后,她将怒火发泄到德沙身上,认为是德沙的放荡导致了她丈夫和凯恩之间的争风吃醋,让她失去了最好的园丁。为了以儆效尤,她将德沙的衣服剥光,在炎炎烈日下指使人鞭打德沙直至德沙昏死过去。而阿达的女主人对丈夫强奸黑人女奴的暴行不闻不问,表明她认为丈夫针对黑人女奴这样的行为是理所当然,不值得她大惊小怪。威廉姆斯在小说中塑造的这些白人女主人形象可以说是对历史的真实写照。在蓄奴制时期,黑人女性不仅要遭受黑人男性所遭受的劳役之苦,还要时时面临白人奴隶主性侵犯性剥削的威胁。她们当然不能指望同为奴隶的黑人男性的庇护,在绝望中,她们往往求助于女主人,希望她们能出面干涉,但都以失败告终。绝大多数女主人会变本加厉地迫害遭到男主人强奸的黑人女性,因为深受女人是与生俱来的色欲引诱者之说洗脑的女主人认定是黑人女性犯下了引诱罪,而她们的丈夫只是个无辜的受害者。(Hooks 1982:37) 有的女主人就像阿达的女主人一样,竟然怂恿这种对黑人女性性剥削的行为,因为黑人女性代替她们满足丈夫的性需求,让她们自己得到解脱。(Hooks 1982:36)
即使在蓄奴制废除后,白人女性对黑人女性的压迫还在继续。在《紫色》中,生活在20世纪初期的市长太太在将胆敢对她说“不”的索菲亚关进牢房几年后,终于如愿以偿地迫使索菲亚做了她的仆人。她将索菲亚安置在楼梯间狭小的储物室,要索菲亚每天24小时随时听候一家大小的使唤,1年365天都不准索菲亚与家人见面,而且时时都在提醒索菲亚身为黑人的卑贱地位。最典型的是市长太太要索菲亚坐到车后厢去那一幕,想要秀一下自己车技的市长太太突然提出要开车送索菲亚回家过圣诞节。出发时,当索菲亚像往常教市长太太开车那样要坐到副驾驶座位上时,市长太太则站在她那边的车门外,清了清喉咙,意味深长地对索菲亚说,“这是在南方”。当索菲亚回答她知道这是南方后,市长太太又清了清喉咙,故意问索菲亚,“瞧,你正要坐到哪里去?”,索菲亚回答说她要坐到平常教开车时坐的那个位置,市长太太更明确地提醒她,当不是在教人学开车时,“你见过白人和黑人并排坐在一辆车里吗?”(Walker 1982:109)。就在这一问一答中,市长太太给索菲亚上了一堂生动的种族等级制度下的南方伦理课。这位经常被丈夫嘲笑、凡事只能顺从丈夫意志的市长太太却对黑人应该坐在何处毫不含糊。
此外,沃克、莫里森和威廉姆斯在她们的小说中还都塑造了帮助过黑人的白人女性,那么,她们骨子里是否也有这样的种族优越意识呢?
在《德沙·罗斯》中,鲁斯的原型是1830年一位收容逃跑奴隶的白人女种植园主。在表现这个做着废奴主义者同样事情的白人女性时,威廉姆斯并没有把她塑造成一个多么高尚和无私的人。对黑人她持有她那个时代白人所有的偏见。当她听说阿达是为了躲避男主人对她及她的女儿的强奸才逃跑时,她当即就向她的保姆多卡斯表示阿达是在撒谎,“没有哪位白人男子会干出那样的事”(Williams 1999:91),而且她实在看不出骨架粗壮、皮肤棕色的阿达和她那位半痴呆的女儿有什么吸引人之处,“大家都知道男人只喜欢半白的或更白的女人”(Williams 1999:92)。在她看来,即便阿达讲的是事实,那也是阿达犯下了引诱男主人的罪行,更何况她一点也不迷人,因此她最后认定“一定是因为诽谤男主人才被女主人赶走的”(Williams 1999:93)。当她听说德沙是被她残酷的主人卖掉时,她马上想到一定是德沙做了什么下贱的事情才被主人卖掉,这下贱的事一定与德沙刚生下来的孩子有关,那孩子身上一定有一半男主人的骨血。尽管她允许逃跑的黑奴住在她的种植园里,为他们提供安身之所,但她也把他们当作免费的劳力使用,使她获利不少。实际上,在丈夫抛弃她后,她已处在种植园破产、身无分文的境地,是这些逃奴的劳作在养活她和她的孩子们。最后,她能离开破败的种植园开始新生活也得益于这些逃奴精心策划的逃跑方案:先由她将他们卖掉,他们再从买主那里逃出来,用得来的钱各奔前程。
在《梅里迪恩》中,林恩的白人种族优越感表现为另一种形式。与白人往往将黑人妖魔化和野蛮化不同,这个投身于黑人民权运动的白人女子来到南方后,她将生活在贫穷中的南方黑人浪漫化。在她眼里,那个胖胖的穿着破烂黄裙子的黑女人所哼唱的歌曲有一种让人流泪的魔力。她将这魔力视为艺术,“对她而言,南方,以及生活在这里的黑人,是艺术”(Walker 2003:136)。她将黑人视为美学对象表明她在心理上与黑人有距离(Barnett 2001:69), 而且这种距离还包含一种观看与被观看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即她作为观看的主体有把握和控制被观看客体(黑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实际上就是身为白人的优越感,这使她对黑人的真正问题视而不见,只凭自己的主观意向去美化黑人形象。
3 超越种族主义藩篱的途径
莫里森、沃克和威廉姆斯小说中白人女性的双重身份折射出美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中存在的种族主义问题。历史上,美国早期的妇女权利运动与废奴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妇女权利倡导者往往将她们所遭受的性别主义压迫比作蓄奴制对黑人奴隶的压迫,视黑人为她们天然的盟友,因而纷纷投入到废奴运动中。这就使得美国主流历史一直认为,美国妇女运动从一开始就在为黑人的自由摇旗呐喊。但是,当蓄奴制废除后,白人男性在历史上第一次想给予黑人男性投票权却把白人女性排除在外时,这些曾经参与了废奴运动的女性权利倡导者却露出了白人种族主义的面目。她们不是联合起来要求所有男性与所有女性享有投票权,而是愤怒地指责白人男性在政治领域更愿意巩固性别等级,而不是维护种族等级。在她们看来,低劣的“黑鬼”竟然有了投票权,而高贵“优越”的白人女性却被剥夺了这一权利,这是白人男性对她们的羞辱。(Hooks 1982:127) 可见,这些白人女性权利倡导者并不想看到黑人最终享有与白人平等的社会权利,她们参加废奴运动是想借此为政治舞台推广她们的政治主张,显示她们正在成长的力量。
妇女权利运动中的种族主义不只表现在反对黑人男性拥有投票权上,它还以或明或暗地排斥黑人女性的方式体现在之后各时期的女权运动中,使本应追求全体女性自由平等的运动变成专属于白人中上阶层女性的活动。(Hooks 1982:128-148) 同是白人男权社会的受害者,白人女性与黑人女性是天然的同盟者,但广泛存在于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白人种族主义意识最终迫使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主导的女权运动分离,这种因种族因素造成的分离同样也出现在本文所分析的小说中。在《梅里迪恩》中,梅里迪恩克服了重重厌恶白人的心理与林恩结成了牢固的友谊,但当林恩告诉她强奸的事之后,连接她和林恩的那根纽带立刻断裂了。对于梅里迪恩,任何有关黑人强奸白人女性的事都让她本能地想起历史上白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残害黑人男性的私刑,这是白人种族主义带给所有黑人的永不能消除的创伤。在《紫色》中,市长一家人自私傲慢,对索非亚尤其刻薄,只有他们的女儿伊莲诺·简妮小姐除外,她处处为索菲亚辩护,索菲亚也以善良友爱回报她,使得从小被父母忽视的她感受到了父母般的关爱。不过,她们之间的情谊只维持到伊莲诺·简妮把她的未婚夫斯丹利介绍给索菲亚的那一天。当伊莲诺·简妮对她未婚夫说是索菲亚将她抚养大时,她的未婚夫搭腔说,“是啊,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由黑人带大的,这就是我们为何如此好的原因”(Walker 1982:269)。很显然,斯丹利在这里将索菲亚比作“黑人妈咪”。“黑人妈咪”是白人制造出来的黑人女奴的典范,她不顾自己的孩子,全心全意抚养主人的孩子,是白人的忠实奴仆。(朱梅 2007:56) 而在黑人眼中,这一形象代表着奴性,是对黑人女性的贬低和否定,这无疑激怒了索菲亚。
这样的分离是痛苦的。索菲亚用激烈的言辞赶跑了伊莲诺·简妮后,“她很不好受,眼里闪着一点泪花”(Walker 1982:274)。正如贝尔胡克斯指出的,黑人女性与女权运动的分离损害的是女性争取解放与平等的事业。一些黑人女性组建与白人女权主义者相对立的“黑人女权”组织,但实际上却落入了种族主义窠臼,走上了与反对种族主义相反的道路。她们排斥白人女性,渲染对白人女性的种族主义成见(Hooks 1982:150-151),像梅里迪恩的祖母和母亲一样,将白人女性看成一群“轻浮的、无可救药的东西,她们又懒又不机灵”(Walker 2003:109),“除了像生育机器一样,生出一个又一个白人孩子长大后来压迫黑人女性之外没有任何用处”(Walker 2003:110)。那么,怎样才能超越种族主义的藩篱,实现所有女性的解放呢?在《柏油娃》中,莫里森用马格丽特与昂蒂妮最后的和解回答了这个问题。
马格丽特刚结婚后,处处受到丈夫瓦莱里的挑剔和蔑视。在丈夫的豪宅中,她感到空前的孤立,唯一的安慰是与黑人女仆昂蒂妮的友谊。但当她丈夫瓦莱里警告她不要与黑仆人搅在一起时,害怕被丈夫抛弃的她只好断绝了与昂蒂妮这段姐妹般的情谊,与昂蒂妮在同一屋檐下冷眼相对。再也没有了倾诉对象的马格丽特只有拿自己的孩子出气,以发泄内心的苦闷,而昂蒂妮则因她的这一行径而将她视为恶魔,两人的积怨也越来越深。最后,在圣诞大餐聚会上,昂蒂妮奋起抗议瓦莱里不经她同意就擅自解雇了她的助手,在激愤中她向大家揭发马格丽特用针扎和用火烧年幼儿子的事实。不过,在这场圣诞大餐后,瓦莱里却被马格丽特美迪亚式的报复击垮,他变得迷茫,混沌不清。而马格丽特却变得强大起来,就像瓦莱里以前对待她那样,她也将他当成孩子或病人对待,主宰着他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源于昂蒂妮在圣诞大餐上对瓦莱里的抗议和对马格丽特秘密的揭发,没有她,就没有象征白人男性权力的瓦莱里的崩溃,也没有马格丽特的新生。再也不受丈夫控制的马格丽特主动向昂蒂妮道歉,而平静下来的昂蒂妮也认识到是瓦莱里将她“视为笨蛋,让她无所事事”,由此她才干出魔鬼般的事情。最后,她们俩人相约都成为“了不起的老太太”,消除了彼此的种族隔阂,达成了和解。可见,对于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她们共同的敌人是白人男性权力。它不仅压迫她们,还导致她们之间的分裂,只有像昂蒂妮和马格丽特击垮瓦莱里那样推倒白人男性权力的权威,才能让所有的女性获得解放。
卢丽安. 《哈姆莱特》的历史问题:《哈姆莱特》与现代早期英格兰的政治性别关联[J]. 外国文学评论, 2013(3).
朱 梅. 托妮·莫里森笔下的微笑意象[J].外国文学评论, 2007(2).
Barnett, P.E. ‘Miscegenation’, Rape, and ‘Race’ in Alice Walker’s Meridian[J].SouthernQuarterly, 2001(3).
Gordon, L. Bad Faith and Antiblack Racism[A]. In: Roediger, D.R.(Ed.),BlackonWhite[C].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98.
Hall, J.D. ‘The Mind That Burns in Each Body’: Women, Rape and Racial Violence[A]. In: Stansell, C., Snitow, A., Thompson, S.(Eds.),PowersofDesire:ThePoliticsofSexuality[C].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Hooks, B.Ain’tIaWoman:BlackWomenandFeminism[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2.
Morrison, T.TarBaby[M]. New York: Plume, 1981.
Roediger, D.R.BlackonWhite[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98.
Walker, A.TheColorPurple[M].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82.
Walker, A.Meridian[M]. New York: Harcourt, 2003.
Williams, S.A.DessaRose[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1999.
【责任编辑陈庆斌】
TheWhiteFemalesinAfricanAmericanFemaleWriters’Writings
Zeng Zhu-q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Toni Morrison, Alice Walker and Sherley Ann Williams create whit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ir novels. In their works, the white female characters are portrayed as the victims of the white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the white supremacists as well. Characteri-zing the white females in this way actually reflects the white racism which separates black women from white women in the American women’s movements. In writing the separ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of the white women and black women, Morrison, Walker and Williams point out that to overthrow the rule of white male power is a way to realize liberation and equality for all the women in America.
African American writer;white female;white male power;victim;victimizer
I106.4
A
1000-0100(2015)02-0141-5
10.16263/j.cnki.23-1071/h.2015.02.027
2014-05-24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百人工程”课题“英美文学经典的文化研究”(05BR3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