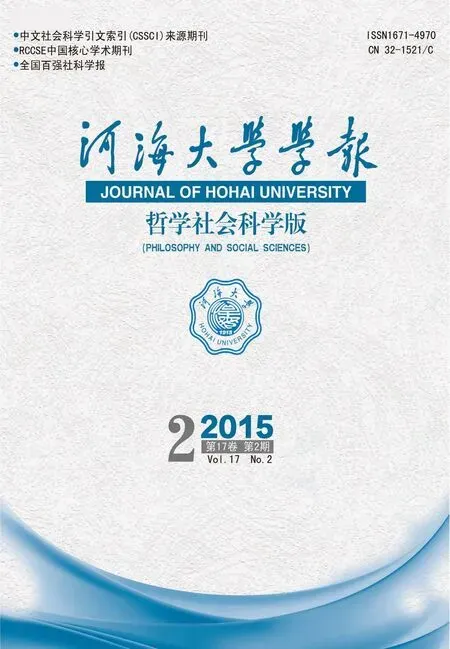国家公祭:社会记忆与国家认同
叶 欣
(1.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8;2.河海大学军事教研室,江苏南京210098)
伴随冷战时代的终结,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褪去的同时,民族主义正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运动,成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在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多民族国家,面对国家内部社会结构剧烈动荡的巨大威胁,国家认同和社会秩序遭受严重挑战。国家认同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举足轻重,本文从“国家公祭”这一社会事实出发,剖析凝结国家认同的社会逻辑,探讨国家公祭作为载体如何经由社会记忆制造国家认同。
一、国家认同:国家公祭和社会记忆的归依
1. 本质上的集体观念
国家认同本质上属集体观念的范畴。从原初概念看来,《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将其界定为“国民认同”。随后,有学者提出“国家认同”的基本内涵,认为它不是简单的“国民认同”,而是建立在自我意识和他者意识形式上的具体、持续的动态之旅,是一种关系的客观映像。英国社会学学者Andreas Pollmann将“国家认同”界定为4个维度:公民国家身份、民族国家身份、民族自豪感、国家归属感[1]。
伴随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细化国家认同的具体表现。有学者提出,现代国家既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也是“政治共同体”,国家认同既包括“历史文化的认同,也包括政治的认同”[2]。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于1995年对23个国家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琼斯和史密斯采用因子分析法区分了国家认同的先赋性维度和自愿选择性维度,得出“前者偏重文化属性,后者表征政治属性”的分析结果,从实证角度佐证国家认同的“文化维度”和“政治维度”。文化认同作为国家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的动力源,它“是国家认同最深厚的基础”[3]。是社会成员分享共同的历史传统、习俗规范和社会的记忆,从而产生较强凝聚力的国家观念、集体情感和国民意识。因此,它作为价值认同的过程是让社会成员接受某种价值范式,将特定价值理念、社会规范内化为价值取向,外化为行为习惯,构建价值的“共同体”。此外,政治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构成核心和关键,“政治合法性来源于政治权力客体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对政治系统的评价,不从社会文化视野出发是不能找到政治系统真正的合法性基础的”[4],政体想要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需要各部分(各阶级)的人们积极参加而且能够怀抱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5]。这一意愿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对所属国家的政治体制、制度、领导和意识形态等达成政治共识、心理认同和情感归属。
2. 国家认同的客观性
国家认同源于被个体感知的社会活动,是被建构的过程。国家认同的客观性有其发展过程,原始的宗教活动演变为赋予规训和秩序的仪式,形成和提升了人们“认同”的价值内涵,在社会范围内产生效应、构成集体记忆,在不断体化实践中强化认同,形成习惯。这种根植于个人体内的价值观和道德感即是国家认同的客观性内核。
涂尔干认为,在祭拜和信仰的起源上,来自“集体的欢腾”,即原始的宗教活动。随着文明的行进,原始宗教逐步发展为赋予规训和秩序的仪式活动,社会成员的精神价值和道德活动成为国家认同的根源。道德力量转达“集体意识作用于个体意识”的方式,“由一个道德存在(即群体)对另一个道德存在(即群体的个体成员)”施加影响而形成[6]。虽然社会活动利于道德力量的构成和集体意识的凝结,但需要借助社会记忆朝向国家认同。涂尔干借助两条路径进一步阐释社会活动的暂时性如何转化为具有持续凝聚力的国家认同:首先,确保活动的周期性;其次,在活动中使用符号表征加以传承,延续影响。这两条路径均在社会活动间歇时段内维持与活动相关的记忆,也就是社会记忆。
“社会记忆”一词演变自涂尔干学派二代成员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1989年,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出版了《社会如何记忆》,随后,诸多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日益重视社会记忆。康纳顿强调个人记忆的社会性,即社会记忆如何产生并传递,系统阐述社会作为整体怎样实现记忆,记忆以何种形态存在,又如何从个体向群体转变等核心问题。他认为通过纪念仪式和身体操演可以实现社会记忆的传播,并称其为“体化实践”[7]。体化实践并非要追溯历史来源,它主要通过人们的行为举止“体化”历史在场。它不着痕迹地为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记忆系统,记忆文化的特有姿势,这种姿势操演为身体提供助记方法。反复的体化实践养成“习惯”,它既是符号,也是知识,是手与身体的记忆;在“习惯”养成时,通过我们的身体来“理解”[8]117。因此,透过社会记忆,国家认同体现了客观性效应。
3. 国家公祭的国家认同价值
康纳顿认为,社会想要生存,需要反复地重复行动和交流思想。国家公祭通过纪念时间和空间的相对固定,不断反复、强化人们体验创伤情感的过程,勾连社会记忆。
国家公祭对国家认同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客观性存在,即物质文化。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丛葬地、英雄纪念碑等,它们作为特殊历史的存在物,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存了尽可能真实的历史现场。历史的重构“从社会群体的记忆获得指导性动力,也显著地塑造记忆。”[8]10符号或话语标识引发人们的创伤记忆和集体情感。二是本质上的集体观念,即通过公祭仪式、纪念空间等方式唤醒社会记忆,这主要由非物质文化唤起。非物质文化作为“文化活化石”被看作“中华民族的情感基因”。非物质文化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各类形态的传统文化表达,如南京大屠杀文献,相关音乐作品、摄影作品、视频资料、幸存者口述档案等;第二种是文化空间,即按照传统习惯的约定时间和场所举行的传统民众民间文化综合纪念活动。
国家公祭构建历史与现实、时间和空间、身心俱融的文化场域,满足社会成员创伤情感的体验需求,让人们在社会记忆中憩息游荡的灵魂,寻求情感归属,有效消解现代性生存境遇中社会成员的生命和作为人的本质被割裂的倾向,激活世人情感的生动性和丰富性,通过客观性效应的映射和集体观念的本质体现凝聚国家认同。
由此,国家公祭的国家认同价值衍生出关联交织的系列问题,国家公祭作为仪式化的社会活动,究竟通过何种方式凝结社会记忆、推进国家认同?而社会记忆在国家公祭中又有怎样的具体作用和表现?在基于史实的前提下,社会记忆如何重现历史在场,制造新的记忆并赋予其意义?国家公祭的现实观照和历史责任怎样体现?对以上问题的追思,不仅能够深挖国家公祭作为载体如何勾连社会记忆和国家认同,而且也对国家公祭的认同价值有更为客观理性的解释。
二、从国家公祭看社会记忆的书写
国家公祭作为凝结国家认同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国家创伤的集体唤醒、历史在场的符号表征和对当下现实感和合法性的强化来书写社会记忆,有效推进国家认同。
1. 国家创伤的集体唤醒
追溯每个国家的历史,不同的时期均有过遭受外来暴力“侵袭、压迫与支配”的可能,从而导致创伤记忆的形成。国家创伤可以唤起社会记忆,建构国家认同。1994年以来,每年12月13日10时,南京城上空都会传来低沉、凄凉的鸣笛,现代化的南京都市被整体拉回到1937年南京城破家亡的黑色记忆。南京大屠杀作为国家创伤的社会记忆被唤醒。
“南京大屠杀”、“犹太集中营”、苏联“卫国战争”以及“珍珠港事件”等都属于创伤记忆。“受难经验成为凝聚族群认同的工具,仪式化的定期纪念此经验,得以强化与维持族群边界”[9]。而由于受难经验发生时间的久远和不在场,使得社会记忆的传承和意义制造在传递的过程中容易被区隔,国家的创伤记忆在年轻一代中存有不同程度的丧失,记忆的阻隔让代际交流变得不易。因此,国家公祭铭记并镌刻过往的历史和事件,追述社会记忆与集体创伤的历史记叙,成为国家弥合集体创伤纬度、宣示其主体性并重新叙述社会记忆的一种手法。
2. 历史在场的符号表征
符号的产生和使用让人们“不再生活在单纯的物理宇宙当中,而是生活在符号宇宙当中。”[10]国家公祭中较为明显也极易辨识的是历史在场的符号表征,它所突显的文化符号,也成为社会记忆的鲜亮符号。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七次会议决定,“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家每年举行公祭活动。在首个国家公祭仪式的前夕,社会各界围绕国家公祭举办悼念活动,搜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有关符号表征,构建历史在场的社会记忆。比如,学生、记者、民众和社会人士寻找位于南京的23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丛葬地,了解历史、勾连记忆。其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清凉山丛葬地坐落河海大学清凉山校区内距东校门不远的一片丛林中,碑体采用水磨石打造,三面棱柱形造型,碑身三面为3个“人字形”,象征30万中华儿女屹立大地,共同托起一个三足鼎,正面刻写“居安思危”,碑座采用三层圆形的红色台阶,象征30万同胞血洒江山。纪念碑身三面书写碑文,正面中文书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清凉山遇难同胞纪念碑”字样并附有中文碑文,侧面、背面分别使用日文、英文的碑文,三种文字一起镌刻那段惨痛历史,警示世人悲剧不能重演。
南京大屠杀的惨痛随时间的流逝渐行渐淡,丛葬地借助建筑、雕塑、碑、柱等元素来限定空间和塑造形象。在纪念碑的设计过程中,应用各类环境手段引导人们思考,启发其想象力,继而表达空间的纪念性[11]。从而见证一段屈辱的社会记忆。幸存者和见证者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活化石”,他们与悼念者和国家公祭连接,形成扬·阿斯曼所说的“文化记忆”,也就是达成一种沟通记忆,使事件体验者的个体记忆变成集体记忆。这一历史在场的符号表征让社会记忆深刻,激励国人自省和奋进,丛葬地作为国家公祭的仪式符号,见证跨历史和超地域的社会记忆,象征国家的团结和基本认同。
3. 强化现实感和合法性
假如国家公祭呈现出历史在场的符号表征体现旧有的集体记忆,那么,它还可能通过现实感和合法性的强化来制造新的社会记忆。国家公祭之所以能够制造新的社会记忆,主要来自两大要素:一是国家公祭能够模拟现实社会;二是国家公祭能够解释社会现实。对现实社会的模拟,可以借助言语来表达,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首个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铿锵有力,语言的力量直击人们内心,这不仅因为语言本身,也由于语言的蕴意,它是人们正在使用并富有生命力的内涵。再如国家公祭的纪念空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丛葬地、爱国人士故居,无疑是现代空间中纪念物的集体展示。此外,网络纪念空间也成为人们通过现代化平台寄托哀思、悼念亡魂的重要空间,2014年7月6日,“国家公祭网”上线,在次日下午的6点,该网站的海内外页面浏览量超过2200万,参与网上祭奠的人群超过60万人次,而到当晚的24时左右,共有950898人次进行线上祭奠,快速增长的数字说明人们对国家公祭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可以说,国家公祭让历史照进现实、勾连现实生活,它通过仪式或符号语言来描绘现实世界,让参与者在形式化和艺术化的社会活动中感受现实社会。
另一方面,国家公祭中的历史回溯,并非只为说明历史在场和其延续性,也是为了解释社会现实,其核心点在于对现实的历史定位和合法性赋予。国家公祭用符号表征历史在场,其背后蕴含着合法性赋予。康纳顿认为,“控制社会的记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权力的等级。”[8]序言1他指出,“社会记忆”支持现存的社会合法化,其体现为现存秩序的权力关系。福柯、布迪厄、德里达等当代社会理论家们也基本支持“权力在本质上操纵记忆”的观点。可见,国家公祭中的国家权力赋予现实社会高度的合法性。
综上所述,国家公祭展现社会记忆的功能本身就是书写社会记忆,它不仅通过国家创伤的集体维度和历史在场的符号表征来体现既有的社会记忆,还借助现实感的强化和合法性的赋予制造新的社会记忆。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公祭能制造出的新的社会记忆,它既建立于社会现实,也建立在与特定历史的联结上。它通过提供与社会现实有关的历史线索,定位和解释现实,也使其富含历史线索,被赋予真正社会记忆的功能。
三、从社会记忆到国家认同的凝聚
一般来说,社会记忆的本质内涵是“对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的凝结、积淀和破译、复活的双向过程。”[12]而国家认同的关键在于个体怎样关注自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运用何种语言表达符号。无疑,二者是契合的,即社会记忆能够制造最普遍的国家认同。而国家公祭因为国家行动而拥有普遍的关注度,被广泛成员共识和记忆,祭典仪式展演、符号语言表达强化着主流话语的叙述和力量的辐射。
1. 制造社会共识
国家公祭活动刻意营造社会最广泛的共识。这一共识从两个层面体现,宏观层面看,国家公祭活动让社会成员高度关注,有效增强集体意识。在媒体平台多样化和传播技术智能化的当下,这一活动有效实现“集体关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相关活动就是例证,它拥有社会关注度,公众有参与热情,事实上,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其中,一系列纪念活动在首个国家公祭日前夕先后举行。江苏省组织开展21项悼念和文化教育活动,全国各地10余家省市党报联合推出关于公祭的系列报道,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媒体参访团齐聚南京与史学专家座谈等,形式不同但背后机理一致,以国家的行为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意义重大。这一重大意义体现了国家认同的凝聚和集体意识的凝结。微观层面看,国家公祭作为国家行为,被社会成员普遍拥有和记忆,参与公祭活动、观看祭典仪式作为社会活动而存在。是否参加国家公祭?与谁参加国家公祭?通过什么方式参加国家公祭?是组织行为还是个体行为?在什么地方参与或观看国家公祭,在纪念空间、公共空间,还是在家中?参与或观看时关注的重点是什么?是仪式本身、仪式过程、仪式语言还是祭典音乐、祭典画面?参与个体作何感受?是悲悯、愤恨、心灵震撼还是默默反思?这些与国家公祭相关的行为和仪式,不会随活动的结束而消亡,它成为最广泛的公众议题,不断地被检识和讨论,继而形成新的社会记忆保留并继承。
国家公祭能够制造普遍共识,对现代社会有重大意义。不论是国家或国民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对某种精神偶像或价值符号的沟通与接受,同时也赋予该偶像或符号以新时代的神圣化需求。”[13]
2. 祭典仪式展演
在梁启超眼中,国家公祭对国民“精神教育”和“历史思想”的现实意义重大。埃德蒙·利奇把仪式看成“带有程序的信息”,一个仪式序列不断重复自身以“充分”实施,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把相同信息通过不同渠道和不同形式“多次重复地发出”,从而减少多传递信息的模糊成分。反复进行的仪式实际上是为了清楚地呈现仪式的内涵及其意义。2014年首个国家公祭日,中国国家领导人和1万多名国内外社会各界人士于当日上午10时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进行国家公祭仪式,仪式过程为:奏唱国歌——肃立、默哀(警报1分钟)——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敬献花圈——南京77位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习近平与幸存者、少先队员代表为国家公祭鼎揭幕——习近平作重要讲话——工、农、兵、科、学、企届代表撞响和平大钟3次、放飞3 000羽和平鸽——仪式结束、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史实展。国家公祭的仪式和它所包含的符号至关重要,因为“个人成其为个人、社会成其为社会、国家成其为国家并非自然形成”,它借助认同来实现,“这种认同经由符号和仪式的运作而造就。”
国家公祭仪式何以构成社会记忆?其根本原因在于该仪式不仅是表达性的,形式化的且受到场合限制的“象征表现类型”,更重要的是“操演种类”,渗透国家文化。国家公祭仪式通过“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加强社会记忆,以仪式展演为载体,体化和刻写社会记忆的核心内容,于象征性的场景中传承和延续。“在习惯的记忆里,过去似乎沉淀在身体中”。如水的平静岁月里,记忆沿袭潜移默化的习惯,饱含累积的社会经验,积淀于身体,流动于社会,行动于国家。诚如高丙中所言:“个人、社会和国家是共生的,个人在社会中,在国家中;社会在个人中,在国家中;国家在个人中,在社会中。”[14]
3. 话语力量辐射
国家公祭蕴含难以觉察的话语影响力,就凝聚国家认同而言,它的记忆功能能够形成辐射公众的话语力量。一方面,国家公祭的话语蕴含特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国家公祭的话语对主题有解释性功能。对比日常交流的语言,国家公祭的话语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不附着日常语言交流结构的松散弊病。首先,国家公祭话语表达明晰、准确;其次,国家公祭话语简洁且易于记忆;第三,国家公祭话语指涉国家“共同体”,包容国家所有成员,让人们容易产生共鸣。
国家公祭作为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它的话语表达克服了日常用语的随意和局限。有关国家公祭活动中,话语的力量让社会成员深刻记忆并震彻心灵,除具有感召力之外,国家公祭话语还拥有解释性功能,它既能诠释国家公祭的本身意义,也能够诠释其背后的社会期待。试想一下,缺乏活力话语表达的国家公祭是怎样?无从知晓国家公祭的事实用意,也全然不知其想要表达什么。诚然,国家公祭的构成较为复杂,这也揭示它需要借助话语解释,成为意义对象被认同和记忆。纪念仪式中,究竟是什么在被记忆?部分答案在于“一个社群被提请注意其由支配话语表现并在其中讲述的认同特征。”[8]81这一“支配性话语”是“对崇拜对象的扮演。”国家公祭在扮演崇拜对象的过程中表现其深刻的话语含义,它在解释公祭意义的同时诉说国家期待。例如,2014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现场悬挂仪式标语,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持枪伫立。参加首个国家公祭日祭典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讲话的最后强调:“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愿同各国人民真诚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携手努力。”[15]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的纪念仪式讲话的最后也强调:“战争的教训提醒人们,纵容暴力、冷漠和观望必然导致可怕的世界性悲剧。”[16]这些有力的话语,直指国家公祭背后的社会期待,这种期待迅即传递给人们,并辐射开来。
总之,国家公祭中话语力量的感召力不止于国家公祭的实时效能,它的影响在公祭结束后持续存在,如吉登斯所言,“书写文字拓展了时空伸延的范围,产生出一种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思维模式。”[17]它割裂了时间与空间,这在发明了书写文字以后成为可能。社会成员在不同的时空书写文字表达国家公祭的力量话语,继而“书写”和“体化”社会记忆,凝聚国家认同。
四、理性反思作为国家认同载体的国家公祭
“以史为鉴,珍视和平”,彰显中国反对“一切反人类罪行”的立场。有关“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国家公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社会记忆,也是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记忆[18]。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教训,而非简单的民族复仇记忆,它是对生命的尊重、对和平现实的珍视和对历史责任的反思。
1. 历史照进现实
国家公祭作为仪式的展演,通过重拾旧有的社会记忆和制造新的社会记忆来部分关照社会现实。国家公祭作为考察国家认同客观性的现实依据,与国家认同勾连,但是,国家公祭的现实性和国家认同的客观性指涉不同问题。国家公祭的现实性指向反映社会现实的手段,以及对社会事实的再现程度;而国家认同的客观性指向国家认同的集体观念,这不是抽象或泛化的知识体现,它具有经验领域的可考察性。有学者认为,“公祭上升到国家层面反映出我们在不断深化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19]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和认识从原本的地方记忆上升为普遍的社会记忆、从国家记忆向世界记忆发展的历程。国家公祭借助仪式和符号语言来“书写”和“体化”社会记忆,有人为的特征,是一种主观的灵活调控。比如说,设立国家公祭日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是对南京大屠杀中死难同胞的告慰和尊重,对否认南京大屠杀右翼复辟势力的警告和法律压制。人们在唤醒人类成长中苦难经历与付出沉重代价的社会记忆同时,会加强思考无数生命的付出和苦难换来的和平现实。
国家公祭作为社会活动是国家认同的事实表现,现代社会呈多元分化,可能源于代际更替,也可能由于职业区隔;但无论何种分化,终究使得社会成员的归属逐级分层。如果再考虑社会分工和组织架构,社会呈现碎片化景观。虽然制度框架和文化积累与社会团结关联,但毕竟抽象而庞杂,如何运用极简方式构建国家认同的“共同体”值得注目。国家公祭,给制度框架和文化张力搭建可行动的平台,在“国家”平台发声,让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上升到生命、人类与世界高度,从人性的角度关注和研究惨案中的死难者、幸存者饱受的身心创伤,引发更多关注和思考[20]。在行动的过程中,朝向集体意识和社会记忆,转化为国家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以价值共识导引人们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国家认同。
2. 从记忆的责任到历史的责任
国家公祭强调具有历史经验的创伤、记忆、崇高等概念在理解世界历史问题上的作用和责任。“记忆的责任”最早出现在1955年,法国出版了题为《记忆的责任》的谈话记录集,谈话者之一普里莫·莱维从集中营走出,在集中营解放五十周年的语境下,该书的出版使得“记忆的责任”广泛流传,见证历史真实的记忆责任朝着记忆、朝向意义,而非朝着历史的真实,尽管它建立于历史的自我理解。过去蕴含伦理和争执价值,昭示着研究者有必要将“记忆的工作”转移至“记忆的责任”。“记忆的责任”与历史勾连,如维达尔—纳盖所说“我相信历史的责任,只有它才能培育出真正的记忆。”这与社会记忆不谋而合,依照需求来界定记忆的真实性。
历史并非服务于记忆,但透过时间的视角窥视记忆的责任,联结当下和未来,我们不自觉地成为将来的“我”的历史主角,“记忆的责任”与“历史的责任”瞬间弥合。因而,扎戈林在教育和社会领域界定历史的责任为“给每一代活着的人关于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文明的过去的知识”,这些知识也务必是“最广泛和最可能好的知识”。他的话语映射出历史的责任与表象真实的密切关联,展现反复切换的真实以何种姿态发展至今。
国家公祭从记忆的责任走向历史的责任。朝向意义、勾连认同的记忆的责任与视真实性为北极星的历史的责任紧密关联,在现实世界中演绎认同。历史真相并非干瘪无力的陈述和白描,它可以演绎“再制”为理解当代社会的方式,作为一种行为、操演而存在。国家公祭透过历史真相借助仪式活动强化社会记忆,在社会记忆中寻找实现国家认同的合理路径。
五、结 语
经上述可知国家公祭与社会记忆和国家认同的关联:国家公祭书写社会记忆,社会记忆凝结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客观性和必要性让国家公祭更为合法。由此,凝练出3个理念——保存和创新社会记忆,重视和凝结国家认同,支持和慎对国家公祭。
有学者将国家公祭视为国家权威“整合传统信仰”、“征用社会认同”、“建构象征权力”的方法,是试图对中国信仰的“反复重构”。国家将南京大屠杀死难日确立为国家公祭日,通过权力赋予其合法性,是对人民的尊重、对历史的正视和对和平的现实解读。南京大屠杀是历史的记忆,更是人们求解那段不堪回首的耻辱史的创伤反思,它从现实出发观照历史,透过历史映射现实。
在现代国家面临“多重逻辑共同作用的状态”,全球化、后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等逻辑交织、叠压和互动,客观上消解了前现代性和现代性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固定东西,甚至“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21]西方不同思潮的冲击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某些核心价值观正逐步消退”[22],国家公祭对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意义重大,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进程的物质世界中不断异化,国家记忆弱化、社会记忆断裂甚至人性本质出现撕裂,精神底线亮红,难以勾连自我、社会和国家。人们试图苦苦追寻社会文化、国家价值的核心所在,但价值的多样性致使诸多社会成员难解甚至无解。“意识形态不该也不可能终结,是业已达成的基本价值共识。”[23]它是“经过同意而来的社会和文化的统一”所达成的“集体性同意”[24]。国家公祭通过洞察南京大屠杀集体创伤的维度捡拾那段历史记忆并制造新的社会记忆,从国家层面认识和把握社会的内在客观逻辑,有效凝结国家认同。
[1]杜兰晓.大学生国家认同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4:21.
[2]肖滨.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76-83.
[3]门洪华.两个大局视角下的中国国家认同的变迁1982—2012[J].中国社会科学,2013(9):54-66.
[4]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4.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社,1981:188.
[6]涂而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05.
[7]赵静蓉.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浪漫主义[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137-142.
[8]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5.
[10]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33.
[11]陈蕴茜.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J].学术月刊,2012(7):134-137.
[12]孙德忠.重视开展社会记忆问题研究[J].哲学动态,2003(3):17-21.
[13]李向平.中国信仰的现代性问题:以国家公祭圣祖先贤为例[J].河南社会科学,2009(2):1-5.
[14]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42-50.
[15]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2-14(1).
[16]王文忠.普京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发表讲话[EB/OL].[2005-05-09].http://news.sina.com.cn/w/2005-05-09/16426591129.shtml.
[1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3.
[18]程兆奇.东京审判再检讨:2013年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J].军事历史研究,2014(4):161-169.
[19]王光禄,耿雪,吴楠.敲响历史警钟 共创世界和平[N/OL].[2014-12-12].http://ex.cssn.cn/index/index-focus/201412/t20141212-1439635.shtm l.
[20]刘忠良.日本海军舰队与南京大屠杀[J].军事历史研究,2015(2):20-29.
[21]金太军,姚虎.国家认同:全球化视野下的结构性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4(6):4-23.
[22]杨玉凤,陈绍西.软实力视角下中国政治价值观的历史溯源与现实审视[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62-68.
[23]樊浩.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意识形态期待[J].中国社会科学,2014(7):4-25.
[24]罗明星.共识的道德与道德的共识[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6(3):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