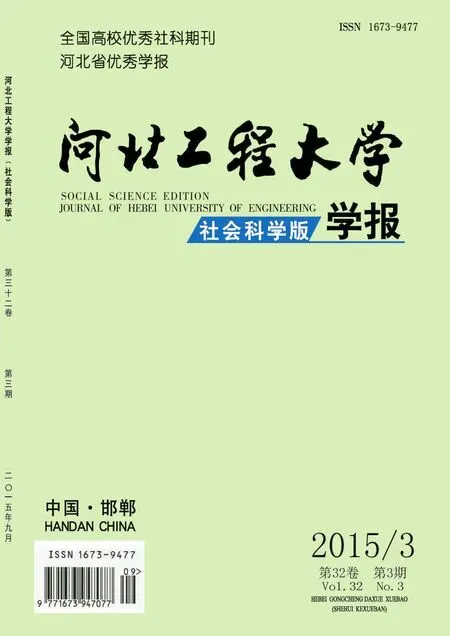译者人生哲学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研究——以夏济安对《美国名家散文选》的编选翻译为例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15.03.0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5)03-075-04
[投稿日期]2015-05-09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项目(编号:SCWY14-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张静(1971-),女,四川成都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一、引言
2013年12月,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美国纽约去世。在哀悼夏先生之时,不禁会联想到他的兄长,文学理论家和翻译家夏济安先生(1916-1965),夏氏昆仲在中国文学史和翻译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夏济安虽英年早逝,但他的翻译作品至今仍广为流传。董桥(1991,80)称赞夏济安的译作“惊为翻译秘笈”,甚至评价“论文采,五四以来用白话文写批评和翻译的,没有多少人能赶上他”(陈子善,1999,19-20),夏济安的译本以优美流畅见长,特点是“尽力让中文跟着英文走而不流失中文的韵致”(董桥,1991)。既能忠实于源语文本,又能在译本中保持目标语的韵致,充分体现出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主体地位也由此得以凸显。
近年,关于译者的主体性以及如何发挥其作用的问题,国内外研究者多有论述(曹明伦,2008,46-48;许钧,2003,10-13)。译者主体性在理论上可以区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王晓龙,2013),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作为个体的译者既会对译本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又会因个人原因对译本有所制约,如同一个“矛盾统一体”(阮玉慧,2009,85-89),那么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因素有哪些呢?“才俊、气足、学深、习雅”(曹明轮,2008)无疑是影响译者主体性的要素,而杨武能(2003,10-12)所提“译家的从业道德、工作心理、社会人格”等也是影响译者主体性的要素。笔者认为,除以上的语言能力、学识修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因影响译者的主体性,即译者的人生哲学。不同的人生体验影响着个人对生死、情感、价值、宗教等人生课题的看法和态度,不仅能导致其人生哲学的差异,也会对其实践活动产生影响,具体到翻译实践活动中,译者的人生哲学显然也会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发挥。
以夏济安编选翻译《美国名家散文选》为例,该书是他在台大期间编选并翻译的散文集,称得上夏译之精粹。他在序言中提到编选该书时特别注意作家研究和文章的选择,可见对入选作家和作品的取舍是有倾向性的,这反映了身为编者和译者的夏济安的审美观、价值观,以及对文学、人生的态度,是译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具体体现。本文从该书入手,结合夏济安人生经历和性格分析,从译者与原文语篇及译文语篇的关系来考察译者的人生哲学在文本选择和翻译中的重要作用,探究译者的人生哲学是如何影响译者主体性的。
二、夏济安的宗教情缘
夏济安和林语堂、冰心等有相似经历,都曾在教会学校接受长期的西方式教育。夏济安早年就读于苏州著名的教会学校桃坞中学,与钱钟书是校友,学校实行全英文教育,所以他的英文功底非常扎实(沈慧瑛,2010,45-47),也因此从小受基督教思想熏陶。夏济安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临睡前做祷告以及到教堂做礼拜的情形,在恋爱受挫时,他多次祈祷,认为上帝“是我顶好的指导”,是“全知全能”的,甚至“崇拜上帝甚于爱情”(夏济安,2011,57),可见基督教的教义已经深入到他的生活中。
基督教精神不仅融进了夏济安的人格,影响着他的人生观,还浸润着他的学术研究,影响着他的文学翻译实践。从《美国名家散文选》的选材上就能看出夏济安强烈的宗教气质,散文选中多为十八、十九世纪美国名家之作,这个阶段也是美国文学从深受清教思想影响到浪漫主义、超验主义兴起的时代,是美国“文艺复兴”的时代。夏济安所选的作者及作品多处体现出他的宗教观。清教徒是开垦美洲的首批移民,“节制、公正、和虔敬”是他们的美德,也是美国精神的根源,夏济安认为宗教文学所代表的清教徒的生活“有许多值得爱慕之处”(爱默生,2000,515),故他首选的作者即为美国宗教文学的代表人物──乔纳森.爱德华兹,是“美国宗教文学的最后一个杰出作家”,其人“律己甚严,志行高洁,温顺善忍,刻苦勤奋”(爱默生,2000,351),夏济安选择了爱德华兹12岁时所写的短文《飞蜘蛛》,这篇短小的文章彰显了作者的写作天赋,不过,夏济安选择此文更重要的目的是向作者本人致敬。夏济安说“我们选他,一则是因为我们尊重清教徒在美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再则是因为:清教徒严肃的态度无形中仍旧是美国民族性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爱默生,515)。实际上,清教徒严肃克己的生活态度早已照进了夏济安的生活,他一生中善于自我剖析反省,常常在日记中反思忏悔自己的疏失,说自己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你(基督教)的教条”(夏济安,2011,61),这些是与爱德华兹宣扬的清教徒精神极为契合。
《美国名家散文选》中还有一位出生牧师家庭、颇具清教徒精神的作家——爱默生,爱默生从牧师成长为超验主义的代表,他的思想也反映了美国文学的演进史,他在文集《论自然》中阐释了自己独特的自然观,包括了自然与人、神的关系,包含建立在自然之上的真、善、美的价值维度,夏济安从中选取《论美》一文放入散文选,其中有“God is the all-fair.Truth, and goodness, and beauty, are but different faces of the same All.”一句,是爱默生对上帝和真善美之间关系的诠释。其中All一词和different faces的翻译,如果不是基督徒或不了解基督教教义的译者会感到棘手,而在虔诚的夏济安笔下,这句话译为:“上帝是至美,而真善美三者,只是一个本体的三个方面的表现而已。”(爱默生,177)对比另一版本的译文“上帝是最公正无私的。真、善、美都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侧面”(吉欧.波尔泰,1993,),夏济安的翻译无疑是正解,因为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是创造了世界的永恒圣父,解救了世界的圣子,以及帮助了人类的圣灵(圣神),是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并不意味着三个不同的神,而是将圣父、圣子、圣灵视为同一本体(All),所以夏济安并未将“different faces”译做“不同侧面”,而是补充为“一个本体的三个方面”。夏济安把自己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基督教精神结合到一起,在翻译实践中付诸于笔端,成为他人生哲学的一个部分。
夏济安的宗教思想也是多元化的,夏志清说“济安对各种宗教(释、道、基督教)都感到浓重的兴趣”(夏志清,2001,216)。佛教对夏济安的影响不浅,佛经教义繁复深奥,可以归结为苦、集、灭、道四谛,世间有情皆为苦,夏济安一生受尽恋爱相思之苦,对于佛教的苦谛深有体会。他在日记中比较Kierkegaard的思想时(夏济安,2011,177),曾说“我顶强的倾向是ethical,我的宗教方面是佛教”,后来又再次重申,如果恋爱不成,“我殆必走入宗教一路去矣。我的宗教将是佛教——从根本上解除无明。”在《散文选》的翻译中,不难看到多处反映夏济安佛教修为的语句,如:出世(229),皮相(167),三界六合(151),寂灭(153),这些词用于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文集中竟然显得十分妥帖,没有违和感,再次证明了译者深谙东西方宗教文化,善于驾驭两种文字的高明之处。
不过,夏济安在宗教信仰上追求的更多的是精神的契合,而不单纯受教条拘泥,他也有独立思辨能力,对基督教思想有辩证反思,表现出其理性的一面,其中一个例证便是散文选中选择了奥利佛·温德·霍姆斯的一篇《爱德华兹论》,这篇长文对爱德华兹所代表的加尔文教派进行了抨击。可以想见,夏济安在选择和翻译霍姆斯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必定也如霍姆斯所说,用到了理性主义者的眼光,由此可见夏济安作为学者的严谨理智的治学态度和人生态度。
三、追求美的悲观主义者
单恋中的夏济安在日记中曾自认“我为人悲观倾向太强,好向根本虚空处着想......”(夏济安,2011,179)虽然他后来又称自己“因为对悲观哲学的严肃,才不敢轻易接受悲观”(184),不过,他又说“悲观人绝不可与世界妥协,只有出家和自杀,才是悲观人的出路”(183),而他在饱受相思之苦的时候,的确多次流露出打算脱离尘世甚至自杀的念头。夏志清对于兄长的性格有深刻的分析:“他的浪漫主义里包含了一种强烈的宗教感:济安不仅把爱情看得非常神圣,他的处世态度和哲学也都带有一种宗教信仰的悲观”(夏济安,2011,17)。
夏济安推崇王国维,认为自己和他心灵相通(夏志清,2001,216),而王国维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影响非常深。夏济安曾研究过哲学,从日记中不难看出叔本华似的悲观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叔本华的哲学宗旨是探索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问题,认为“生活之欲”是人生痛苦的根源。夏济安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对爱情和婚姻的欲望,对金钱的欲望,甚至开玩笑说“我现在顶大的欲望是要发财......先求尽量的享受,日后的结果不必考虑”(夏济安,2011,224),只可惜他的欲望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还成为了他悲观主义的源头。
悲观主义的印记也烙在了夏济安所翻译的名家散文中,以《西敏大寺》一文为例,华盛顿.欧文到西敏寺游览,写下此文来凭吊悲今古,全文弥漫着阴郁悲哀的情绪,夏济安在翻译此文时能“移情”作者,达到和作者感同身受的地步,从文章的开篇便可一见,而这段译文也是为业界所折服称道的:
“时方晚秋,气象肃穆,略带忧郁,早晨的阴影和黄昏的阴影,几乎连接在一起,不可分别,岁云将暮,终日昏暗......古寺巍巍,森森然似有鬼气,和阴沉沉的季候正好相符;我跨进大门,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置身远古世界,忘形于昔日的憧憧鬼影之中了。”
寥寥数语,便使原文的意象重现,更烘托出阴沉昏暗的气氛,将读者引入了西敏寺古老阴郁的建筑中,比较另一译本:
“正值深秋时节,这种天气让人感觉庄重而抑郁,早晨的阴影几乎和傍晚的相互连接,给这岁末的幽情更加笼罩了一层灰蒙蒙的色彩......在这古老的建筑群中,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刚好与这个季节的色调相吻合;我跨进门槛,似乎一脚迈进了古老的年代,将自己融入到那些前人的阴影当中了(徐翰林,2011,136)。”
后者显然缺乏夏译中的气场和情感,不能充分体现原文的风格,归根结底是译者和作者缺少感情上的共鸣,这是译者气质的区别造成的。读过原文和译文的读者都有类似感受,夏济安的译文甚至可以说胜过了欧文的原作,若非夏济安这般既浪漫又悲观的译者,是难以译出这样的文字的。正如林以亮(2000,3)评价夏译说“我们如果拿原文和译文再多读几遍,就会觉得译者和原作者达到了一种心灵上的契合,这种契合超越了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打破了种族上和文化上的藩篱”。
尽管夏济安对世界和人生有悲剧意识,却并不妨碍他追求生活中的情趣和美。他爱看外国电影,也欣赏京剧和西洋音乐,对电影和通俗文学亦小有研究。他在凡俗的物质生活获得的情趣得以升华为对美的体验,这种体验正如爱默生在《论美》一文中所述,美可以由最初级、最直观的万物形体之美到高贵的精神之美,最后到用理智来研究自然之美进而用艺术来创造美的境界,文中有一段:
The dawn is my Assyria; the sunset and moon-rise my Paphos, and unimaginable realms of faerie; broad noon shall be my England of the senses and the understanding; the night shall be my Germany of mystic philosophy and dreams.
夏济安译为:
“朝霞灿烂如锦,那就是我的亚述帝国;夕阳西落,明月东升,那就是我的帕福斯和不可思议的仙子之乡;昊昊阳午,那就是我的英国——常识和理智的故乡;黑夜就是我的德国——神秘哲学和梦想的国土。”
这段译文不仅在文字上契合了爱默生对美的追求,在精神上也契合了他的思想,将Paphos这个被爱默生视为神秘浪漫的爱与美的结合地补充出“仙子之乡”,而且整段文字对仗工整,朝霞、夕阳、阳午和黑夜勾勒出一幅动人的大自然图画,也准确地挖掘出爱默生原文中隐含之意,这其中不仅是出自夏济安的翻译功底,更包含了夏济安对美和浪漫的理解。
夏济安推崇的英国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认为,文化的最高理想是追求完美,这种完美是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完美。爱默生则是阿诺德喜爱的作家,夏济安在《美国名家散文选》的序和作者简介中都提到了阿诺德对爱默生的评价“在十九世纪,没有任何散文比爱默生的影响更大”(爱默生,2000,516),夏济安也认为爱默生的作品“已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溶入了我们不能自觉的思想背景中”(159)。夏济安选择并翻译爱默生的《论美》可以看做是隔着遥远的时空对两位前辈的致敬,惺惺相惜的三人之间的共性便是对美和世界的认识,以及对美的热爱和创造。
四、结语
翻译是译者进行的创造性实践活动,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既要受译本这一客体的制约,也会受到译者自身条件的限制,译者自己对生命和生活的认识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附加在新生成的翻译文本上,成为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作为一个率真、克己、唯美的翻译家,夏济安将自己的人生态度融入了《美国名家散文选》,这本书不仅最能表露他的译才,同时也是他人生哲学的反射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