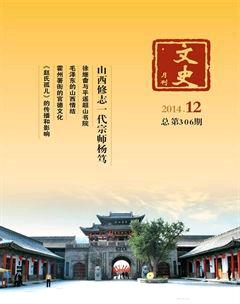《文学改良刍议》诞生记
张文禄
一百年前,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一群英姿勃发、胸怀寰宇,立志改革中国文学的青年,在中国文学这片广袤而浩瀚的海洋上,扬起了他们远行的帆。他们不畏航行的艰险,冲破重重惊涛骇浪,让那面“文学革命”的旗帜在这片波涛汹涌的海洋上飘扬着。而胡适,作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他对文学革命的贡献不能、也不会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正如欧阳哲生所说:“胡适的‘暴得大名是建立在他的早期新文化成就的基础之上的。”1917年1月,被陈独秀称为“今日中国之雷音”的《文学改良刍议》使胡适真正成了中国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但《文学改良刍议》绝非胡适一夜之作,而是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长期酝酿。
对文言文的“留念”
胡适曾说其文学革命的思想“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此话一点不假。第一个促使胡适思考文学革命问题的是清华学生监督处的书记官钟文鳌,他在每月定期邮寄各地留学生银票的时候,随信会寄一些诸如“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取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的宣传单。对于“废除汉字,取用字母”运动,实际上早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一些忧国忧民的留日学生通过对日本小学教育的思考就已经提了出来,后来还得到了袁世凯、吴汝纶等政客文人的支持。然而“音标文字只可以用来写老百姓的活语言,而不能用来写士大夫的死文字。换句话说,拼音文字必须用‘白话做底子,拼音文学运动必须同时是白话文学运动。”因而这个运动直到民国最初几年都只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这对于思想并不激进的胡适来讲,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直到有一天,胡适厌烦了钟文鳌这样的小传单,写了一封批判他不懂中国汉字历史的回信后,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胡适才觉得有必要弄清这个别人没有弄清的东西。
1915年8月,作为中国留美学生会“文学科学研究部”文学股委员的胡适,在部分留美学生“极力诋毁汉文,主张采用字母,以为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字母不可”的倡议声中,性情温和、处事中庸的他提出“此问题至重大,不当以意气从事,当从容细心研究之”。在如何对待汉文问题上,胡适找到了其好友赵元任,决定对该问题进行探讨。胡适所说的赵元任是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之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1910年8月赴美国,入康内尔大学学习数学,选修物理、音乐。赵元任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但他主要以著名的语言学家蜚声于世。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胡适谈赵元任写关于中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以及如何做的问题时说:“赵君后来觉得一篇不够,连做了几篇长文,说吾国文字可以采用音标拼音,并且详述赞成与反对的理由。”但这件事在当时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因为在《赵元任生活自传》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胡适主要做“如何可使我国文言易于教授”的研究。在胡适看来,中国文字虽然是“半死文字”,但它是中国教育的媒介,因而“文言终不可废置”。改变这种现状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文言文的教授方法,“使我感觉字母的文字不是容易实行的,而我那时还没有想到白话可以完全替代文言,所以我那时想要改良文言的教授方法,使汉文容易教授。”同时,胡适根据自己学习、运用文言文的经验,提出了包括给文言文加标点符号在内的四点教授意见。
从中国文字到中国文学
真正促使胡适思考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是1915年夏天到1916年8月与一帮朋友的探讨。1915年“任叔永(鸿隽),梅觐庄(光迪),杨杏佛(铨),唐擘黄(钺)都在绮色佳过夏,我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从中国文字问题转到中国文学问题。”梅光迪( 1890—1945) ,字迪生,又字觐庄,安徽宣城人。1909年胡适与梅觐庄相识。梅于1911 年考取庚款留美资格,属第三届庚款官费生( 胡适是第二届)。梅光迪赴美后,先是在威斯康辛大学,1913 年转入芝加哥西北大学文理学院,1915 年毕业。同年秋往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欧文·白璧德,1919 年获硕士学位回国。任叔永和杨杏佛是胡适中国公学时的校友。1915年8月20日在得知胡适决定去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后,任叔永作了一首诗《送胡适之往哥伦比亚大学》,诗中说:“我昔识适之,海上之公学。同班多英俊,君独露头角。”唐擘黄是福建闽侯人,1914 年留美,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后改学心理学,是胡适的美国校友。
1915年,胡适和他的这些朋友在风景宜人的绮色佳畅谈人生理想。这群学富五车的青年自然不会避开文学这个话题。在谈到中国文学时就不免会提到中国文字。“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但对于胡适提出的“中国文字是半死文字”这一观点任叔永和梅觐庄却持反对意见。胡适与任、梅二人是如何辩论的,在三人遗留的文献中没有详细的记载。胡适只是说:“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胡适的激烈就是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1915年9月17日,胡适为即将到哈佛大学深造的梅觐庄写了一首《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的白话诗,诗中写道:“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这是胡适首次提到“文学革命”。 1915 年9月20 日胡适也要离开绮色佳去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任叔永借用胡适送梅觐庄诗句中的外国字,作了一首戏赠诗给胡适,诗中有“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之句,胡适认为这是任叔永对他的嘲笑。曲高和寡的胡适在朋友的冷嘲热讽之下,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反而更加执着。21日,在去哥伦比亚大学的路上,胡适写了一首《依韵和叔永戏赠诗》,在诗中胡适写道:“诗国革命何自始? 要须作诗如作文。”在这句诗中,胡适实际上提出了他实施文学革命的具体方案,即“作诗如作文”。
面对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提法,1916年2月,梅觐庄提出了更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就已经分道扬镳了,还认为胡适提出的用白话文作诗并不能算是“诗界革命”。从2月到7月,胡适与他的朋友们就白话文入诗问题断断续续地进行了讨论。在此期间,胡适也更深入地思考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问题,并于4月完成了《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5月做了《谈活文学》、6月做了《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等文章。1916年6月16日,胡适返回猗色佳,在此居住了八天,并将《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交给任叔永并得到了任叔永的认可。7月8日,在他离开绮色佳不久,任叔永同陈衡哲、梅觐庄、杨杏佛、唐擘黄等在凯约嘉湖上乘船游玩,由于天气突变,暴雨如注,在返回岸边时船又翻了,所幸没有人受伤。为此任叔永作了一首四言的“泛湖即事”给胡适,诗中出现了“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的文言句式,而胡适又在1916年2月做过一篇《<诗经>言字解》的文章,因而对这首诗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任叔永也基本接受了胡适的建议并对全诗进行修改。但梅觐庄得知此事后不以为然,开始更加凌厉地攻击胡适的新文学理论。本来早在1916年3月间,梅觐庄已经认可了俗语白话文可以用在文学上,但经历这件事后,他写信给胡适推翻了自己说的话,“总之,吾辈言文学革命,须谨慎出之。尤须先精究吾国文字,始敢言改革。欲加用新字,须先用美术以锻炼之。非仅以俗语白话代之即可了事者也。”任叔永自然也站在了梅觐庄的一边,认为胡适“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胡适却不服气,他致函任叔永说:“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而在吾辈实地试验。”而此时胡适也已经更加坚定了白话文学的信心,也不打算在与朋友们争论下去,因为他们都认识到中国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但他们赞成的文学革命,只是一种空荡荡的目的,没有具体的计划,也没有下手的途径。这个途径需要胡适自己去找,要集中精力去做,因此,他再也不想与任、梅二人打笔墨官司。胡适在8月4日写信给任叔永,“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习一国语言,又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 结伴同行”。 胡适还声明:“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 事实上也是这样,从当年8月起,胡适中断了与梅光迪等人之间的争论,正式开始白话诗的写作。到8月23日,胡适就写下了著名的白话诗《蝴蝶》。endprint
《文学改良刍议》诞生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期如期发行。在这一期中有胡适的一篇名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文中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个方面: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胡适所提的这八条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与朋友们的争论中逐步形成的。在1916年2月3日,胡适通过与梅觐庄争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认为当今文学“徒有文而无质”,要想创造有质量的文学就要:“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避之”。在这里,胡适提出了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八条意见中的三条。1916年4月13日,胡适做了一首词《沁园春》,胡适对这首词进行了四次修改,在4月16日第三次修改后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4月17日,胡适又写下了我国文学的三大弊病:“一曰无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至此,胡适文学改良的八点意见中的五点已经提出。此后,胡适在与陈独秀、钱玄同、任叔永、朱经农等人的书信往来中逐渐形成了另外的三条。1916年8月胡适在给好友朱经农的信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这八条。
朱经农(1887—1951),生于浙江浦江,与胡适、任鸿隽、杨杏佛同为中国公学的校友,与后三人相比,朱经农的年龄虽不是最大,但资格最老。1916 年,朱经农赴美。胡适在6月9 日的日记中记载:“朱经农新自国中来,居美京,为教育部学生监督处书记,将以馀力肄业于华盛顿大学。经农为中国公学之秀,与余甚相得……今闻其来,喜何可言? 惜不能即相见耳。”尽管朱经农对胡适的白话诗并不看好,但他支持胡适的“文学革命”。在胡适受到好朋友任叔永、梅觐庄等人的非难时,“不但不反对白话,且竟作白话之诗”的朱经农就成了胡适难觅的知音,所以胡适将他的文学改良的全盘思路告知了朱经农。在当年的10月,胡适又写信给陈独秀,告知陈独秀中国文学改良的全盘思路。在陈独秀要求更详细叙述的请求下,历经一个月,胡适写成了文学改良刍议全文。但这篇文章最初的名字叫《文学改良私议》。不论是“私议”还是“刍议”,与此前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相比,都大大推后了一步。胡适思想上为何有这样的变化,按照胡适自己的说法是“可是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