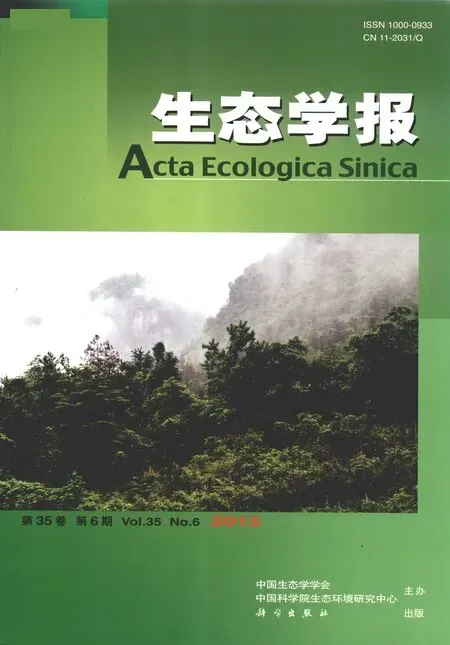南方丘陵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及其驱动因子
——以衡阳盆地为例
周松秀,田亚平,刘兰芳
衡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系, 衡阳 421002
南方丘陵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及其驱动因子
——以衡阳盆地为例
周松秀*,田亚平,刘兰芳
衡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系, 衡阳 421002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适应性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南方丘陵区是典型的水稻农业区,研究其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尤为重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衡阳盆地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进行了定量研究,分析不同适应能力区的适应性主要驱动因子。结果表明:适应能力的分布规律为衡阳市区最高,各县域适应能力呈现出盆地中部低、四周高的分布规律。不同适应能力区适应性驱动因子各异,高适应能力区主要驱动因子是经济条件,水热配合条件和灌溉设施是较高适应能力区的主要驱动因子,低适应能力区的主要驱动因子是人口规模和水土保持,热量和地形条件是极低适应能力区的主要驱动因子。高适应能力区因以农药和化肥的施用量为主要驱动因子具有短暂性,较高适应能力区以良好的水热配合条件和灌溉设施作为驱动因子具有可持续性,因而较高适应能力区的发展潜力超过高适应能力区。
农业生态系统; 适应能力; 驱动因子; 主成分分析; 衡阳盆地
适应性研究是全球变化背景下现代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1],并逐渐成为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研究的焦点[2]。地理学界认为适应性是为响应某种压力或驱动作用而采取或经历的一种偏离原来状态的行为[3-4],是人们努力减少全球变化的不利影响,同时合理利用现存环境的调整过程[5],适应能力是适应性研究的重点[6],即社会-生态系统对敏感和风险的消化程度和对既定的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馈赠能力。尽管生态系统过程遵循Tilman的资源竞争平衡理论,但是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因区域尺度不同适应性方式和机制各异[7]。不同地域的较小尺度区域典型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研究成果是客观表达较大尺度区域适应性的实践和基础。目前对中小区域尺度的适应性案例分析已逐渐引起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王龙昌等[8]根据调查资料和田间试验结果,系统地分析了旱地不同作物生长发育与降水分布的时序关系、旱地作物水分潜在利用率和旱地主要作物水分供需平衡与错位特征,并利用水分生态适应性数学模型,对宁南黄土丘陵区主要作物的水分生态适应性进行了定量评价。陈凤臻[9]等建立了适合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特点的区域适应能力评价模型,并对模型的构建思想、参数意义和评价指标的具体计算进行了探讨。何云玲等[10]构建了纵向岭谷区生态环境对气候变化适应性的综合评价模型,并根据评价结果对纵向岭谷区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空间分布特点进行了综合分析。仇方道[11]对东北地区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进行了研究。这些典型的中小区域尺度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研究成果是该领域研究的典范。概括来看,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环境耦合系统的适应性研究个案和研究成果尚少,所涉及的地域有限。区域生态系统适应能力研究是区域研究的新课题。
南方丘陵区是我国典型的稻作农业区和重要的粮食产区,也是我国脆弱生态环境区之一,属于中度脆弱区。目前南方丘陵区的生态环境脆弱性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12-13],脆弱性评价能较好地显示区域所面临的敏感和风险程度,亦即人类调整社会经济行为的迫切程度。但是如何调整社会经济行为,提升适应能力,必须进行适应性研究。结合国家的生态保护、恢复和生态建设与科技发展方向,全球变化的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和适应机制是我国生态系统研究中的重大科学问题[14]。笔者尝试以衡阳盆地为例,对南方丘陵区农业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进行定量评价,并分析适应性驱动因子,进而揭示全球变化的区域生态响应与适应过程和驱动机制,以便为区域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衡阳盆地位于南方丘陵区的江南丘陵,是典型的红色丘陵盆地。本文选择衡阳盆地为例研究南方丘陵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具有代表性[2,13]。衡阳盆地位于北纬26°07′05″—27°28′24″,东经111°32′16″—113°16′32″之间,总面积为15310 km2。其范围包括衡阳市、衡阳县、衡南县、衡东县、衡山县、祁东县、耒阳市和常宁市。地貌类型以岗地、丘陵为主,气候为大陆性特征较为明显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2,13],水域总面积为6.49 万hm2,湘江及其支流为各县市提供较充沛的淡水资源。耕地面积为30.15 万hm2,占境内土地面积的19.7%。衡阳盆地作为“鱼米之乡”,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农业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9.7%(衡阳统计年鉴2010),以水稻种植为主,辅以小麦、玉米、高粱和豆类等粮食作物及花生、油菜等经济作物。由于研究区水旱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不高。
2 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内涵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给出的适应性的定义和地理学界对适应性的理解,笔者认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可表述为因全球变化导致水热状况、水土保持等农业生态环境发生改变,农业生产在经历这些改变时所体现的保持农产品产量、质量及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的性能。其内涵包括以下三方面:(1)当全球变化引起的水热状况和土被覆盖等农业生态环境表现为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时,农作物利用这些优越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提高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或者当大气组成成分和气候水热状况的不利变化在作物生长能调节的阈值范围内时,作物通过调节叶片气孔导度、抗旱应急蛋白、土壤灌木菌根体和保护性酶的活性等[15]方式进行自适应调节,使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能健康持续发展,并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这两种情况属于农业生态系统的自发适应。(2)当全球变化引起水旱灾害频发、水土流失加剧和病虫害蔓延等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并超过农作物的自适应调节阈值时,为了不丧失生存空间和生存能力而进行社会经济行为的调整,农业活动采取一系列调控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农业生态系统的人为适应。(3)农业生态系统的自发适应和人为适应均为动态的相对适应,常用适应能力进行度量。影响适应能力的因素包括自发适应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因素和人为适应需具备的社会经济因素。
2.2 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评价指标的选取
全球变化背景下,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和弹性是农业生态学研究面临的重要挑战。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是自发适应能力和人为适应能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表现出的维持系统稳定和弹性的能力,自发适应能力主要由农作物的种类和农业自然环境状况决定,人为适应能力则主要因社会经济因素而异。当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发展时,农业生态系统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较强的恢复力,适应能力较强;反之,适应能力较弱。实际上,农业生态系统的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经济指标匹配情况比较复杂,对于某个区域尺度的某个时段,某些因子的量的增加会使系统具有较好的适应性,本文称这类指标为正向指标;另一部分因子则使系统的适应能力降低,本文则称之为负向指标。对于农业生态系统而言,农业基础设施、人均耕地面积,排涝能力,灌溉条件、森林面积比例,人均水资源等,都是最重要的指标。因此,本文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并将其归纳为自然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三个大类,以客观表达农业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
2.2.1 自然环境因素
衡阳盆地农业生态系统的自然环境因素包括气候、地形地貌、土地覆被、土壤等方面。对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影响较大的首先是气候因素。研究区属于典型的稻作农业区,其水热状况总体较丰富,年降水量丰富,气候温暖,热量充足,有利于稻作区的农业发展。但水稻种植业不仅要求水热丰富,更需要雨热同期。实际上,衡阳盆地水旱灾害频繁,春季阴冷易烂种,4—6月降水集中多暴雨易涝,7—9月受伏旱天气影响常有季节性干旱,寒露风易造成空壳、瘪粒导致晚稻减产等,都会降低农业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因此,本文在评价指标的选择时必需考虑区域背景下的影响适应能力的宏观指标,如平均降水量、平均气温、∑T≥10 ℃积温等,均属于正向指标,作为气候因素的宏观指标,以客观表达其适应性的本底条件和潜在能力。另外,评价指标还应考虑研究区典型的个性化指标,以识别各评价单位对各类暴露和敏感的响应程度,表达各评价单元的适应能力的区分度,因此选择暴雨日数、4—6月降水比重、7—9月干旱指数等区域个性化指标,且均属负向指标,作为适应能力评价的另一部分气候方面指标。地形地貌及土地覆被也是影响其适应能力的重要因素,本文选择坡度>15°面积占总面积比重作为地形地貌的评价指标,因为坡度>15°的土地不利于发展种植业,属于负向指标。土地覆被方面选择森林覆盖率作为评价指标,因为森林能够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属于正向指标。土壤是影响适应能力的又一重要自然环境因素。研究区的地带性土壤红壤和黄壤等适合稻作农业的发展,非地带性土壤的紫色土不易绿化、容易造成水土流失,是造成研究区水土流失严重和强烈影响农业生态环境的因素,对适应能力具有较强的制约作用,因此本文选择紫色土面积作为评价指标。
2.2.2 社会因素
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的社会因素包括水利设施、耕作制度和耕种方式等方面,且均对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影响较大。水利设施选择水库水塘密度作为评价指标,因为这是能否满足灌溉需要和蓄洪济旱的标志,且水稻种植业对灌溉水源的依耐性大。耕作制度和耕种方式是影响适应能力的主要社会因素,体现对现有气候资源、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利用程度和趋利避害状况。衡阳盆地土壤侵蚀严重,因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较少,耕地压力大,目前缓解压力的主要措施是开垦坡耕地,坡耕地农业生产稳定性差,保肥保水性能差,常以施用大量的化肥补充肥力,农业生态系统风险大。人均耕地相对较多的区域所面临的此类风险较小。因而把人均耕地面积作为正向指标。衡阳盆地属于大陆性特征较显著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河谷平原、丘陵盆地交错。受地形地貌与传统的农耕习惯的影响,且水田比旱地的比较效益高,因此坡耕地也常以水田的梯田形式存在,水田的面积占比大。本区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水热总量丰富,且水热总量足够让水田农业生态系统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但是其气候的大陆性特征导致水旱灾害频发,4—6月降水量大且多暴雨,梯田的水土流失严重;7—10月为衡阳盆地的旱灾高发期,夏秋干旱对以水稻种植为主的水田农业生态系统的风险大。因此本文把水田占耕地面积比重视为负向指标。由于农业的比较收益较低导致本该一年两熟或三熟的稻田仅种植一季水稻呈半撂荒状态。因此本文以15—25°的坡耕地面积、水田占耕地面积比重、人口密度等负向指标,以及人均耕地面积、晚稻播种面积占稻谷播种面积比重等正向指标作为社会因素的评价指标。
2.2.3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既是适应能力的驱动因素,也是适应能力的结果表征指标。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农民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和生产资料的投入等。农村的生活水平越高,农民越富裕,农业生产的投入越合理,农业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越高。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中如过量施用农药化肥等,短暂的经济效益会有所提高,但是土壤肥力退化、水资源恶化、农业病虫害蔓延等导致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减弱。稻谷单产指标既是适应能力的驱动因素,也是结果表征指标。稻谷单产受品种、耕作栽培和排灌等农业科技的影响,农业科技投入越多,排灌设施越健全,稻谷单产越高,农业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越强。另一方面,稻谷单产又是农业科技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光、温、水、气、肥)等综合影响的结果体现,故可视为结果表征指标,具有驱动和结果表征的双重作用。因此,作者选择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纯收入、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稻谷单产[16]等正向指标,以及农民恩格尔系数、农用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等负向指标作为经济因素方面的评价指标。本文构建的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3 评价单元的选择
本研究以衡阳盆地的衡阳市区及衡阳市辖的7个县域为评价对象,衡阳市区(市郊区)的农业生态系统与各县域类型和性质有较大差异,但是为了研究区域的完整性,衡阳市区也列为研究单元之一。县域是我国具备地域性、综合性和行政独立性的最基本区域单元[17],也是我国目前统计资料中经常采用的单元[13]。并且每个县域具有较一致的农业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及农耕文化背景。譬如衡南县位于盆地中部,耕地中水田占九成以上,化肥施用量大,晚稻播种率高,农业旱灾严重;常宁市位于盆地南缘,坡耕地面积小,晚稻播种率低,农业旱灾较轻。

表1 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Table 1 Twenty-two evaluation indexes of agricultural ecosystem adaptability
* 衡阳市农业区划报告数据集,衡阳市农业局,1986; 衡阳市统计年鉴数据资料查找方式为直接读取或通过简单计算获得,均为2000—2009年的统计年鉴平均值; 表中第6列权重值由文中第3部分的计算获得
3 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定量评价
农业生态系统是社会-生态复合系统,其自发适应能力和人为适应能力互相渗透、互相影响,通过耦合形成农业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而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因此,文章不分别计算其自发适应能力和人为适应能力,而是综合考虑各因素对适应能力的贡献和影响,建立适应能力评价模型。
3.1 数据标准化
在这22项指标中,X1、X5、X6、X9、X12、X13、X15、X16、X17、X20和X22等11项为正向指标,其数值越大,适应能力越高;其余11项为逆向指标,其数值越小,适应能力越高。数据处理时,先计算逆向指标的倒数,将其正向化[13],使所有数值方向一致。由于各评价指标数据的属性和量纲各异,需进行数据同趋化处理和无量纲化处理。本研究针对同一时间不同评价单元进行比较,由于多数自然环境指标数据只存在一个适宜范围,因而采用标准差标准化对数据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13]:
(1)

3.2 指标权重的确定
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因子信息存在一些相关性,为了消除信息叠加的影响,本文选择主成分分析法进行评价。主成分分析能够客观地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从而避免主观随意性。计算步骤如下:(1)利用Matlab7.0先把样本数据标准化,然后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特征根、主成分贡献率、累计贡献率[13]及主成分载荷矩阵(表2—3)。(2)主成分解释。根据主成分提取原则(即特征根大于1,累计贡献率大于85%)[18],确定主成分个数为4个,用Z1、Z2、Z3和Z4表示。分析每个主成分占累计贡献率的比重,即得出各主成分的权重。(3)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在计算各主成分权重的基础上,根据主成分载荷矩阵中每个评价指标的载荷值,计算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表1)。具体计算步骤见参考文献[13]。

表2 特征根及主成分贡献率Table 2 The eigenvalues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principal component

表3 主成分载荷值Table 3 Loadings matrix in principal component
3.3 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指数计算
适应能力大小用适应能力指数ACI表示,计算公式为[10]:
(2)

在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指数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参照文献[19]的划分原则,将衡阳盆地农业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划分为4类:即0.30≤ACI<0.50为高适应能力区,0.10≤ACI<0.30为较高适应能力区,-0.10≤ACI<0.10为低适应能力区,-0.30≤ACI<-0.10为极低适应能力区,计算结果和分类情况见表4。

表4 各区域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指数及级别Table 4 Adaptability degree of the eight evaluated areas
表4中的衡阳县、衡南县和祁东县的适应能力指数为负数,表示相对于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平均状况而言,其适应能力偏低[20]。适应能力指数越大,表示适应性越强。从表4可知,衡阳盆地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衡阳市区最高,其值为0.4584;衡南县最低,为-0.2982。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图1)。(1)衡阳盆地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整体状况较高,以适应能力指数大于0的区域为主体。(2)盆地中衡阳市区适应能力最高,为高适应能力区;南部的常宁市和耒阳市适应能力次之,为较高适应能力区;东北部的衡山县和衡东县为低适应能力区,但其适应能力指数仍都大于0。(3)盆地中部(除衡阳市区外)和西部为极低适应能力区,中部的衡南县最低。(4)衡阳盆地适应能力分布规律为衡阳市区适应能力最高,各县域的适应能力表现为盆地南部县域适应能力较高,东北部次之,中部和西部最低。

图1 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分布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ecosystem adaptability
4 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驱动因子分析
主成分载荷系数绝对值大小代表变量载荷信息的大小,正号表示变量与主成分作用方向一致,负号表示变量与主成分作用方向相反。因此,可以用载荷系数绝对值相对较大的指标代表该主成分。通过分析主成分载荷矩阵(表3),找出影响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主要因子,识别出各主成分的综合意义,分析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主要驱动因子。
4.1 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四大驱动力
衡阳盆地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驱动力主要有4个方面:(1)农业投入和增长方式是衡阳盆地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首要驱动力。第1主成分Z1在X13、X14、X15、X19、X21和X22等6个指标上载荷值较大,这4个指标分别表示人均耕地面积、人口密度、晚稻播种面积占稻谷播种面积比重、农用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和稻谷单产,可解释为农业投入和增长方式。Z1的特征值为10.3734,贡献率为47.15%,居4个主成分之首,是首要驱动力。(2)第2主成分Z2与X2、X4、X6和X9的相关程度较高,这4个指标分别表示暴雨日数、7—9月干旱指数、∑T≥10 ℃积温和森林覆盖率。第2主成分可解释为水热配合状况及水土保持条件,因而水热配合状况及水土保持条件是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第2驱动力。(3)平均降水量、4—6月降水比重和水库水塘密度等3个指标共同构成第3主成分Z3,第3主成分可解释为水资源条件,即水资源条件是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第3驱动力。(4)第4主成分Z4在坡度>15°面积占总面积比重这个指标上有较大的载荷,地形条件是第4大驱动力。
4.2 高适应能力区,经济条件是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主要驱动因子
主成分数值空间化到每个研究区域[9],计算区域驱动力得分值(表5),从而确定区域适应性的主要驱动力因子。
高适应能力区主要包括衡阳市区,适应能力指数为0.4584,为研究区最大值。从表5可知,第1驱动力D1中的农用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和稻谷单产的驱动力得分值分别为0.190329、0.19806和0.199682,远大于衡阳盆地中的其他各个县域,是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主要驱动因子。第2驱动力D2中的∑T≥10 ℃积温的驱动力得分值为0.0648117,第4驱动力中的坡度>15°面积占总面积比重的驱动力得分值为0.06742792,均为研究区的最大值,是该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次要驱动因子。衡阳市属于省辖市,是研究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社会经济发达。2009年,衡阳市辖区农民人均纯收入6937 元,高于各县域平均水平(6321.7 元),为衡阳盆地最高值;市辖区农民恩格尔系数为39.5%,为研究区的最低值,各县域平均为50.62%,根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市辖区已达到相对富裕水平,而各县域处于温饱状态。市辖区稻谷单产达9633kg/hm2,其他各县域稻谷单产均在6300kg/hm2以下*数据来源于衡阳市2010年统计年鉴。此外,衡阳市区位于盆地中部,地形较平坦,盆地的“聚热效应”使种植业所需的热量条件和地形条件较优越。可见,发达的经济条件是本区的主要驱动因子,优越的热量和地形条件是其次要驱动因子。

表5 主成分驱动力及其主要驱动因子得分值Table 5 The driving score of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以农用化肥施用量和农药施用量作为主要驱动因子的衡阳市区,尽管目前的适应能力为本区最高,但农药化肥在提高单产的同时,环境污染不容忽视,不仅会在土壤中残留,而且通过农业水利设施和地表径流造成水体污染,对环境造成危害,属于不可持续农业发展方式。另外衡阳市区(市郊区)跟其他各县域的农业生态系统有着本质区别,是以生产蔬菜和副食品为主的农业,而各县域农业则属于典型的稻作农业。但是本研究为了研究区域的完整性把衡阳市区纳入其中。衡阳市区的郊区农业今后应增加科技投入,控制污染,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4.3 较高适应能力区,水热配合条件和灌溉设施是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主要驱动因子
较高适应能力区包括常宁市和耒阳市等2个县级市,适应能力指数分别为0.1539和0.1340。从表5可知,常宁市和耒阳市的第2驱动力D2中的7—9月干旱指数得分值分别为0.0935001和0.0227717,居研究区第1位和第2位;第3驱动力D3中的4—6月降水比重的得分值和水库水塘密度的驱动力得分值也均为研究区的前2位。可见水热配合条件和灌溉设施是其主要驱动因子。常宁市和耒阳市位于衡阳盆地南部,水热条件配合良好,常宁市农业干旱频率为研究区最小(为55%),农业洪涝以耒阳市频率最低[19],农业生态系统的自发适应能力高,稳定性和恢复力较好。据常宁市和耒阳市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常宁市共投入水利建设资金3028 万元,对梅埠桥、野马、五龙山等13座水库进行除险加固,整修山塘386处,完成渠道清淤1361 km,全市粮食总产量 41.16 万吨,同比增长6.4%。耒阳市2009年开工各类水利工程283处,投入资金5294 万元,完成土石方38.71 万m3;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28座;新增农田有效灌溉面积3487 hm2。随着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农业生态系统的人为适应能力将会进一步高,常宁市和耒阳市农业生产能力提升前景良好。由于本区适应性主要驱动因子是良好的水热配合条件和灌溉设施,可持续发展潜力大。按照目前趋势,本区的适应性呈良好发展,其适应性将超过衡阳市区的市郊农业水平。
4.4 低适应能力区,人口规模和水土保持是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主要驱动因子
低适应能力区包括衡山县和衡东县,适应能力指数分别为0.0778和0.0178。第1驱动力D1中的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口密度的驱动力得分值,均以衡东县最大,衡山县次之;第2驱动力D2中的森林覆盖率的驱动力得分值,衡山县最大,衡东县次之。可以认为适度的人口规模和良好的水土保持条件是该区适应性的主要驱动因子,人为适应驱动因子为首要驱动因子,自发适应驱动因子居于第2位。该区紫色土分布较少,森林覆盖率较高,涵养水土的自然条件较优越,且水土保持工作较重视。例如,衡东县对湘江一级支流洣水两岸的水土保持十分重视,通过坡改梯、水保林建设和小型水利水保工程建设, 2009年对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21.14 km2的面积进行了治理,效果显著。并于2011年作为全国第1批水土保持监督执法能力建设试点县已经通过国家验收。衡山被列入了全国第2批水土保持监督执法能力建设试点县。本区农业增长较稳定,例如在“十一五”时期,2006年到2010年,衡山县农业总产值由16.08 亿元增长到24.09 亿元,增长49.8%;农业增加值由10.12亿元增长到16.45 亿元,增长62.5%;农民人均纯收入由4351 元增长到7322 元,增长68.3%。
4.5 极低适应能力区,社会经济因子的驱动作用较小,热量和地形条件是主要驱动因子
极低适应能力区包括衡南县、衡阳县和祁东县,适应能力指数分别为-0.2982、-0.1148和-0.1211,为研究区的最低值区。衡南县、衡阳县和祁东县的第2驱动力D2中的∑T≥10 ℃积温和第4驱动力中的坡度>15°面积占总面积比重的驱动力得分值均较高,仅次于高适应能力区衡阳市区。本区缺乏第一位的驱动因子,主要的社会经济因子的驱动作用较小,热量和地形条件是其主要驱动因子。本区是衡阳盆地农业生态环境的脆弱中心[17],脆弱的农业生态环境导致该区的农业敏感性和易损性较强。极低适应能力区位于衡阳盆地中部(衡阳市辖区除外)和西部,一方面盆地中、西部地形较平坦,盆地的“聚热效应”使种植业所需的热量条件和地形条件较优越。另一方面盆地的“聚热效应”导致蒸发旺盛,蒸发量一般为降水量的2—3倍[13],成为衡阳盆地旱灾最严重的区域,衡阳盆地农业干旱衡南县频率最高,达90%[20],衡阳县以85%的频率而位居第二。就洪涝灾害而言,盆地中部及其河谷的汇流作用加剧了洪涝灾害的发生,衡阳县和祁东县的湘江河谷洪涝发生频率较大[21]。可见,本区是旱涝灾害易发区和重灾区。旱涝灾害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造成严重危害,并导致土地退化、生产力下降和病虫害频发[22],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使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下降,造成农业生产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衡阳市统计年鉴2010的数据显示,衡阳县的晚稻播种面积占稻谷播种面积的比重为衡阳盆地的最低值,为48.6%,频发的水旱灾害已经制约了衡阳县的晚稻生产。衡南县的水田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最大,达90.7%,水田生态系统的主要作物水稻在分蘖和抽穗期对水分有强烈依赖性,晚稻恰遇夏秋频发的干旱期,表现出强烈的脆弱性,农业效益低,恩格尔系数为研究区的最大值,为56.2%。衡阳盆地中部县域因其农业效益低,致使农户的兼业和非农活动普遍,农业的生产性投资少,农业生产粗放,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农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低。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本文以衡阳盆地为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南方丘陵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适应能力以衡阳市区最高,适应能力指数为0.4584;南部的常宁市和耒阳市适应能力较高;中部的衡南县、衡阳县和西部的祁东县为研究区的极低适应能力区。研究区适应能力的分布规律:衡阳市区的适应能力最高,各县域的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基本呈现出盆地中部低、四周高,南部高于北部,东部高于西部的分布规律。衡阳市区(市郊农业)的高适应能力源于主要驱动因子农药和化肥施用量,其高适应能力具有不可持续性。今后衡阳市郊农业应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逐渐变农药化肥的环境恶化型石油农业为科技和固定资产投入型的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市郊农业。而研究区南部的常宁市和耒阳市尽管属于较高适应能力区,因其良好的水热配合条件和灌溉设施,其适应能力的提升潜力较大,属于可持续发展方式。按照目前趋势,其适应能力将超过衡阳市区(市郊农业)。常宁市和耒阳市今后应以其良好的水热条件和灌溉设施为契机,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
(2)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有4大驱动力,农业投入和增长方式是衡阳盆地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首要驱动力,水热配合状况及水土保持条件是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第2驱动力,水资源条件是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第3驱动力,地形条件是第4驱动力。不同适应能力区驱动因子各异,高适应能力区,经济条件是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主要驱动因子,其中的化肥农药施用量作为主要驱动因子,带来的高适应能力是短暂的,具有不可持续性。水热配合条件和灌溉设施是较高适应能力区的主要驱动因子。人口规模和水土保持是低适应能力区的主要驱动因子。低适应能力区的衡山县应大力发展优质生态有机稻和席草等特色农业生产,衡东县应积极采用良种等农业科技,做大做强国家级商品粮基地,改善农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极低适应能力区缺乏第一位的驱动因子,主要的社会经济因子的驱动作用较小,热量和地形条件是极低适应能力区的主要驱动因子。极低适应能力区的祁东县今后应充分利用优越的热量条件大力发展和扶持黄花、香芋等特色优势农业,提高农户的农业收入;衡阳县作为全国的粮食生产和油料生产大县,应多渠道进行水利设施建设和加大固定资产投入,提高社会经济因子的驱动作用;衡南县应发扬水田连片优势,建设排灌渠系和机耕道,发展优质稻的规模化生产和机械化耕作,提高农业生产率,降低水旱灾害风险,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
(3)从驱动力和适应性类型来看,首要驱动力主要体现为社会经济因子的驱动作用,贡献率达47.15%,第2和第4驱动力主要表现为自然环境因子的作用,第3驱动力则是社会因子和自然环境因子的综合作用。总体来看,社会经济条件是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主要驱动力。从不同的适应能力区来看,经济条件是高适应能力区的主要驱动因子;较高适应能力区和低适应能力区的主要驱动因子既有社会因子,也有自然环境因子;极低适应能力区的主要驱动因子主要表现为自然环境因子。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性驱动因子以社会经济因素为主。
5.2 讨论
(1)南方丘陵区的生态脆弱性研究成果较多,但适应性的研究尚少。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所得的结论较客观,适应能力评价结果和适应性驱动因子分析的结论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今后应从不同的研究视角、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区的适应性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2)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的首要驱动力和高适应能力区(衡阳市区的市郊农业)的主要驱动因子都包含农用化肥施用量和农药施用量,以这些因子作为适应性驱动因子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其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今后应该增加科技投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今后的研究中要加强适应性评价模型的研究,加强适应性驱动力的综合效果分析,科学辨析各驱动因子对不同区域适应性的驱动程度和驱动潜力,加强适应性管理模式和适应性策略的研究。
致谢:感谢衡阳师范学院谭家杰博士和2009级GIS专业覃俊同学对本文的数据和图像处理给予的指导。
[1] 温腾, 徐德琳, 徐驰, 赵德华, 冷欣, 耿其芳, 安树青.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现代生态学——第六届现代生态学讲座纪要. 生态学报, 2012, 32(11): 3606-3612.
[2] 周松秀. 基于生态脆弱性视角的南方丘陵区农业适应性对策研究——以衡阳盆地为例. 农业现代化究, 2012, 33(3): 327-330.
[3] Burton I, Kates R W, White G F. The Environment as Haza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4] Smit B, Wandel J. Adaptation, adaptive capacity and vulnerability.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 16(3): 282-292.
[5]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2001: the Science of Climate Ch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6] 徐广才, 康慕谊, 贺丽娜, 李亚飞, 陈雅如. 生态脆弱性及其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 2009, 29(5): 2578-2588.
[7] 傅伯杰, 赵文武, 陈利顶. 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地理学报, 2006, 61(11): 1123-1131.
[8] 王龙昌, 谢小玉, 王立祥, 卞新民. 黄土丘陵区旱地作物水分生态适应性系统评价. 应用生态学报, 2004, 15(5): 758-762.
[9] 陈凤臻, 姜琦刚, 于显双, 崔瀚文. 全球变化下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区域适应能力评价模型研究. 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 2010, 32(3): 292-296.
[10] 何云玲, 张一平. 纵向岭谷区生态环境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评价. 山地学报, 2009, 27(3): 300-305.
[11] 仇方道, 佟连军, 姜萌. 东北地区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评价. 地理研究, 2011, 30(2): 243-255.
[12] 田亚平, 刘沛林, 郑文武. 南方丘陵区的生态脆弱度评估-以衡阳盆地为例. 地理研究, 2005, 24(6): 843-852.
[13] 周松秀, 田亚平, 刘兰芳. 南方丘陵区农业生态环境脆弱性的驱动力分析——以衡阳盆地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11, 30(7): 938-944.
[14] 傅伯杰. 我国生态系统研究的发展趋势与优先领域. 地理研究, 2010, 29(3): 383-396.
[15] 周广胜, 许振柱, 王玉辉. 全球变化的生态系统适应性. 地球科学进展, 2004, 19(4): 642-649.
[16] 陈萍, 陈晓玲.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系统的干旱脆弱性评价. 农业工程学报, 2011, 27(8): 8-13.
[17] 王瑞燕, 赵庚星, 周伟, 姜曙千, 秦元伟. 县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及其动态分析——以黄河三角洲垦利县为例. 生态学报, 2009, 29(7): 3790-3799.
[18] 刘庆, 陈利根. 长株潭地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及空间分区. 农业工程学报, 2013, 29(6): 245-253.
[19] 赵跃龙, 张玲娟. 脆弱生态环境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 地理科学, 1998, 17(l): 67-72.
[20] 王宏伟, 张鑫, 邱俊楠. 榆林市脆弱生态空间分异特征及脆弱度分析. 水土保持研究, 2010, 17(3): 184-188.
[21] 刘兰芳, 肖志成, 谭青山. 衡阳市农业旱涝灾害发生规律及大灾预测. 中国农业气象, 2009, 30(1): 118-120.
[22] 李克让, 曹明奎, 於莉, 吴绍洪. 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评估. 地理研究, 2005, 24(5): 653-663.
Adaptability of agricultural ecosystems in the hilly areas in Southern China:a case study in Hengyang Basin
ZHOU Songxiu*, TIAN Yaping, LIU Lanfang
DepartmentofResourceEnvironmentandTourismManagement,HengyangNormalUniversity,Hengyang421002,China
Adaptability is the response to external pressures or actions that people make efforts to reduce the adverse effects caused by global change with the aim of harmoniously inhabiting the environment. In studies focused on global change, adaptability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on the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of plants under global change. The model of water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of upland crops has been discussed, and the eco-environment adaptability under changing climates in the past decade has been investigated.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agricultural ecosystem adaptability (AEA). Agricultural ecosystem adaptability is affected b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by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Different factors have different driving or restraining effects on AEA values. The rice farming regions of the hilly area in the Hengyang basin in southern China is the basis for our AEA study. Our study on AEA values is quantitative and applie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affecting adaptability in the different regions of our study area.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size of the driving force and AEA values, we analyzed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different regions. The AEA concept helps mainta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more likely to recover quickly from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such as floods or droughts) or economic (i.e. poor, lack of food, fluctuations in commodity prices) crises. Based on nat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we establish the AEA indexes for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Hengyang Basin. Our findings show that AEA is highest in Hengyang. In the other regions, the central parts of the basin have low adaptability and the surrounding regions have high adaptability. Good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of a high AEA, and good hydrothermal and irrigation systems induce high adaptability. Hengyang is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enter of the Hengyang Basin. The per-capita net income of farmers in Hengyang is the highest in region, and the farmers′ Engel coefficient is the lowest. Nevertheless, the use of pesticides and chemical fertilizers are still prevalent in Hengyang. Changning and Leiyang have good hydrothermal and irrigation systems.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seldom occur in these cities and this contributes to a high adaptability. Population size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soil and water are the primary driving factors in low adaptability areas. Extreme heat and harsh terrain conditions lead to the lowest agricultural ecosystem adaptability. The application of pesticides and chemical fertilizers result in a temporary high AEA, which cannot be sustained. High AEAs resulting from good hydrothermal and irrigation systems are sustainable.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a region with high AEA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regions with low AEAs. The low adaptability areas can improve their AEA ratings by not only us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a sustainable way, but also improving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creasing the production of good crop strains, improving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conditions and developing advantageous agricultural policies are very effective ways of enhancing adaptability.
agricultural ecosystems; adaptability; driving factor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Hengyang Basin
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B47);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2C05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71075); 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建设学科人文地理资助项目
2013-05-24;
日期:2014-04-25
10.5846/stxb201305241168
*通讯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 zhousongxiu@163.com
周松秀,田亚平,刘兰芳.南方丘陵区农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及其驱动因子——以衡阳盆地为例.生态学报,2015,35(6):1991-2002.
Zhou S X, Tian Y P, Liu L F.Adaptability of agricultural ecosystems in the hilly areas in Southern China: a case study in Hengyang Basin.Acta Ecologica Sinica,2015,35(6):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