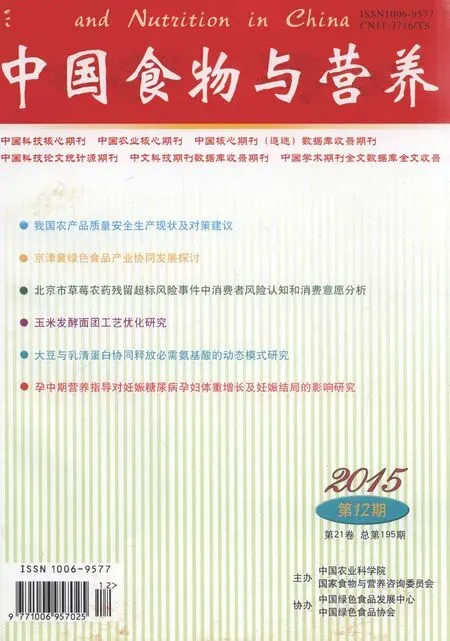我国粮食生产阶段中农业科技生产效率问题研究
周向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农业部农业信息服务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1)
民以食为天,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要任务。我国政府一直把发展粮食生产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粮食总产量从1949 年的1.13 亿t 提高到2014 年的6.07 亿t,增加了4.37 倍;粮食单产从1949 年的1 020kg/hm2提高到2014 年的5 385kg/hm2,增加了4.28 倍。与此同时,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大幅提高,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显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持续增加。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我国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最为关键的因素。
为了进一步揭示科学技术在促进粮食生产中的显著作用,本文首先以每增加1 亿t 粮食为标准,将1949 年至2013 年划分为五个粮食生产阶段;其次,描述了每个阶段我国粮食生产的特征1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同时回顾了同时期农业科技事业发展情况;最后,以1989—2013 年为样本区间(1949—1988 年的数据缺失),采用数据包络方法(DEA)测算了这段时期的农业科学技术生产率,定量分析了这段时期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1 我国粮食生产和农业科技事业发展情况
从1949—2014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总体呈增长态势(图1)。从具体时间来看,我国粮食产量在1949 年、1966 年、1978 年、1984 年、1996 年和2013 年分别达到了1.13 亿t、2.14 亿t、3.05 亿t、4.07 亿t、5.05 亿t和6.02 亿t,并首次突破1 亿t、2 亿t、3 亿t、4 亿t、5 亿t 和6 亿t。以每增加1 亿t 为分类标准,我国粮食生产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同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科技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发展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在时间上同粮食生产阶段高度吻合(表1)。

图1 1949—2014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

表1 我国五个粮食生产阶段和农业科技事业发展阶段对照表
1.1 粮食生产第一个阶段以及农业科技事业发展情况
1949—1966 年是我国粮食生产的第一个阶段,粮食产量从11 318.4 万t 提高到21 400.9 万t,增长89.08%。我国经历了17 年的时间,完成了粮食产量增加1 亿t,年均增长率为3.82%。1949—1966 年,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从109 958.7 千hm2增加到120 988千hm2,增加了10.03%,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1 029.33 kg/hm2提高到1 768.84kg/hm2,大幅度提高了71.84%。
与此同时,我国农业科技事业也进入了全面起步阶段[3]。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在留用民国时期科研机构人员和接管重组原有农业科研机构的基础上,按照计划体制的集中模式组建了新的农业科研机构。经过17年的时间,我国逐渐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三级管理的、学科齐全的农业科技体系。在这段时期,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初步发展,并取得不少科技成果,有力地促进了粮食生产。
1.2 粮食生产第二个阶段以及农业科技事业发展情况
1966—1978 年是我国粮食生产的第二个阶段,粮食产量从21 400.9 万t 提高到30 476.5 万t,增长42.41%。我国又经历12 年的时间,粮食产量突破了3亿t,但年均增长率从第一个阶段的3.82%降至2.99%。1966—1978 年,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从120 988千hm2下降到120 587.2 千hm2,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了0.33%,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1 768.84kg/hm2提高到2 527.3kg/hm2,大幅度提高了42.88%。
这一阶段正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前的“两年徘徊”时期,我国农业科技事业也处于曲折发展阶段。十年“文化大革命”对农业科技事业造成空前危害,农业科研机构纷纷被撤销,大批农业科研人员被下放,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被迫停止科研工作,新中国整体农业科研事业受到严重冲击。在这段历史时期,虽然经历不少曲折,但是由于坚持了一些正确的农业科技发展政策,实施了一批农业科技发展规划,我国农业科技事业仍然获得了一些发展。
1.3 粮食生产第三个阶段以及农业科技事业发展情况
1978—1984 年是我国粮食生产的第三个阶段,粮食产量从30 476.5 万t 提高到40 730.5 万t,增长了33.65%。我国经历了短短6 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粮食增产1 亿t,年均增长率高达为4.95%。1978—1984 年,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从120 587.2 千hm2下降到112 883.93千hm2,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了6.39%,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2 527.3kg/hm2提高到3 608.18 kg/hm2,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了42.77%。
这一阶段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我国农业科技事业也进入了恢复与调整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业科技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农业科技事业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这段时期,中央制定了正确的农业科技发展政策和切实可行的科技发展规划,各种奖励政策的出台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我国农业科技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4 粮食生产第四个阶段以及农业科技事业发展情况
1984—1996 年是我国粮食生产的第四个阶段,粮食产量从40 730.50 万t 提高到50 453.50 万t,增长了23.87%。我国经历了12 年的时间,粮食产量迈上了5亿t 的台阶,年均增长率为1.80%。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从112883.93 千hm2下降到112 547.92 千hm2,减少了0.30%,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3 608.18kg/hm2提高到4 482.85kg/hm2,提高了24.24%。
与此同时,我国农业科技事业进入了改革探索阶段[5]。1985 年3 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进入了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新时期。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启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科技体制开始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体制转变,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得到新发展。
1.5 粮食生产第五个阶段以及农业科技事业发展情况
1996—2013 年是我国粮食生产的第五个阶段,粮食产量从50 453.50 万t 提高到60 193.84 万t,增长了19.31%。我国经历了17 年的时间,粮食产量又迈上了6 亿t 的台阶,年均增长率为1.04%。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从112 547.92 千hm2下降到111 955.56 千hm2,减少了0.53%,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4 482.85kg/hm2提高到5 376.58kg/hm2,提高了19.94%。
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科技事业进入了改革深化阶段,开始了农业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并着力加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这一阶段的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了分工明确、良性互动的新型农业科研体制的形成,显著提升了我国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段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科技事业发展最好、农业科技成果最多、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最高的时期[6]。
1.6 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发展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并在时间上同五个粮食生产阶段高度契合。60 多年来,我国农业科技机构和科研人员数量从少到多,农业科研能力从弱到强,农业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表2)。
从表2 可以看出,除了粮食生产第一阶段外,其余四个阶段粮食单产年均增长率都要高于粮食总产年均增长率。这表明我国粮食产量的增加越来越得益于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而农业科技在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发展粮食生产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发展的五个阶段中,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科研队伍不断调整和优化;农业论文数量显著增加,从第一阶段的34 851 篇增加到从第五阶段的434 659 篇,增加了11.47倍;农业类重大科技成果大幅提高,从第三阶段的16 497项提高到从第五阶段的83 313 项,增加了4.05倍4暂缺1949—1978 年的农业类重大科技成果数量。;农业类国家级科技奖励从第一阶段的2 项增加到第五阶段的761 项,其中包括2 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表2 新中国农业科技事业发展成就
2 我国粮食生产中的农业科学技术生产率测算
本文以1989—2013 年为样本区间(1949—1988 年的数据缺失),采用数据包络方法(DEA)中的BCC 模型,测算了1989—2013 年的农业科学技术综合生产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2.1 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方法(DEA)由Charnes 等于1978 年提出,是评价相对效率的一种非参数方法,原理是将每一个评价单位视为一个相同类型“投入”和“产出”构成的决策单元,通过计算各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的权重进而确定整个评价单元的生产前沿面,之后根据各决策单元与生产前沿面的距离来测定DEA 的有效性。该模型包括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两类,其中投入导向型DEA 是产出水平一定的条件下使投入最小化,产出导向型DEA 是投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使产出最大化,二者从不同角度解决同一问题,本质上一致。上述作者最早提出的是CCR 模型,但是由于CCR 模型在判断某些决策单元时,不能回答非DEA 有效的决策单元究竟是由技术无效引起还是由于自身规模引起等问题,所以本文选取投入导向型的BCC 模型进行分析。BCC 模型可以测量综合技术效率,由Banker、Charnes 和Cooper 建立,简称为BCC 模型,其与CCR 模型的主要区别是在CCR模型的约束条件中加入了凸性假设(eTλ=1)。
BCC 模型可以表达为(1)式:

(1)式中,θ 为评价单元DMU0的有效值,X=(x1,x2…,xn),Y=(y1,y2…,yn)为输入和输出矩阵,s-和s+为松弛变量,分别为m 维、s 维的列向量,λ为权重系数,e 是分量为1 的向量,ε 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
BCC 模型有效性的判断如下:
(1)当θ <1 时,则决策单元DMU0有效;(2)当θ=1,且s-≠0 或s +≠0 时,则决策单元DMU0为弱DEA 有效;(3)当θ=1,且s-≠0 和s+≠0 时,则称决策单元DMU0为DEA 有效。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测算农业科学技术投入产出效率具体用到的数据包括农业科学技术的产出、农业科技劳动投入和农业科技资本投入。
(1)农业科学技术的产出。本研究选择了中文科技期刊刊登农林牧渔类科技论文篇数、农业类国家级科技奖励和农业类重大科技成果项目数作为产出[7,8]。
(2)农业科技劳动投入。农业科技的劳动投入时应综合考虑劳动者人数、劳动时间和劳动质量等方面,但是由于所收集的数据中在近年才开始统计职工的受教育程度、职业资格水平以及年龄结构情况,统计数据期间较短,如果对该数据进行分析无疑能够更全面地反应劳动力的异质性对于农业科技效率产生的不同影响,但是这将损失大量的样本,在农业科技劳动力投入方面包括了从业人员、科技活动人员、科学家工程师、课题投入人员,为了反应动态的变化和突出科技人员的作用,本研究选择1989—2013 年为样本区间,农业科技活动人员作为代理变量,而农业科学家工程师只有1990—2008 年的数据,暂不予考虑。
(3)农业科技资本投入。固定资产投资的计算主要是采用国际通行的永续盘存法进行估计,公式为(2)式:

(2)式中,Kt 是第t 年的资本存量;It 是在t 年的不变价投资额;βt 是固定资产折旧率。折旧率βt 一直没有统一标准,Hu 和Khan (1997)将中国官方折旧率取为3.6%,Maddison (1998)取17%,Wu (2003)取7%,由于统计匮乏无法取得相应的数据,本研究最终还是使用农业科研机构经费内部支出作为资本存量的计算基础。样本中的所有名义变量都是以2000 为基期的实际值。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采用的是1989—2013 年的农业科技投入和产出数据,可以发现这期间涵盖了粮食产量增长的第四个阶段(1984—1996 年)、第五个阶段(1996—2013 年)。
2.3 1989—2013 年农业科学技术生产率测算结果
本文利用数据包络方法(DEA)中的BCC 模型对1989—2013 年的农业科学技术综合生产率进行测算,并从时间方面将综合生产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其中,农业科学技术综合生产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农业科学技术综合生产率反映农业科学技术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反映农业科学技术本身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集中体现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带来的生产效率改善;规模效率反映农业科技规模化发展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集中体现农业技术推广带来的生产效率改善。表3 展示了利用数据包络方法(DEA)中的BCC 模型对1989—2013 年农业科学技术综合生产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测算结果。
3 结果与分析
从表3 可以看出,在粮食生产第四阶段和第五阶段,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生产率是比较高的。粮食生产第四个阶段的农业科技综合生产率平均值为99.7%,意味着我国将农业科技劳动投入和农业科技资本投入转化为科技论文、科技奖励、重大科技成果等农业科学技术产出的效率很高。我国农业科研资源利用的已经非常充分,距离前沿生产面仅需要再提高0.3%的生产率,其中1990—1996 年农业科技综合生产率高于第四个阶段的平均值。
第五个阶段全国农业科技综合生产率平均值为95.9%,低于第四个阶段的综合生产率,但是依然非常高,距离前沿生产面仅需要再提高4.1%的生产率,其中1997—2001 年、2008—2013 年的农业科技综合生产率高于平均值,其余年份则低与平均值,最低的是2007年,生产率仅为76.9%,效率值比平均值19%,意味着2007 年我国将农业科技劳动投入和农业科技资本投入转化为科技论文、科技奖励、重大科技成果等农业科学技术产出的效率相对较低。

表3 1989—2013 年农业科学技术生产率测算结果
我们进一步将农业科学技术综合生产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可以发现,除了1989 年、2006 年、2007 年规模效率要高于纯技术效率外,其余年份的纯技术效率都要高于规模效率,而且两个阶段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也高于规模效率平均值,说明1989—2013 年我国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效率更多的是依靠提高纯技术效率。这段时期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对于农业整体科学技术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更大。从时间上来看,1990—1996 年纯技术效率从基本上不变,均为100%,说明纯技术效率改善是农业科技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而规模效率则呈现出下降趋势。1997—2013 年,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变化波动都较大。
对比第四和第五个阶段,我们发现第四个阶段的综合生产率、纯技术生产率和规模效率均要高于第五个阶段。如果仅仅从表3 中的数据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随着粮食产量的增长,农业科技生产率呈现出降低趋势,然而,这个结论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支持。例如:近年来,随着农业对外合作水平逐渐提高,农业国际交流活动不断丰富,我国农业科研人员与国外科研人员合作日益密切。我国大量的农业科技劳动和农业科技劳资本投入到国际合作研究中,然而很多国际合作研究取得的科技成果(发表论文、奖励等)却无法统计在国内农业科学技术产出范围之内,这会直接导致国内农业科学技术产出的统计数据偏低,从而造成粮食生产第五个阶段的农业科学技术综合生产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明显低于实际值。
[1]许世卫,李哲敏,李干琼,吴建寨.基于农户的区域食物安全冲击影响模拟模型构建及应用分析[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4,20(3):10-13.
[2]钟永玲,曹慧,张玉梅.中国小麦中长期供需趋势分析及建议[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4,20(9):51-55.
[3]司智陟.国外确保粮食安全政策分析[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3,19(12):5-6.
[4]陈永红,刘宏.中国粮食中长期需求总量与结构分析预测[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3,19(1):32-36.
[5]翟虎渠.中国粮食安全国家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6]翟虎渠,刘旭,等.中国粮食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科技支撑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7]朱世桂.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2.
[8]路明.中国农业科学技术50 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9]申茂向.中国农村科技50 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10]沈镇昭,隋斌,等.中国农业科技十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11]牛盾,信乃诠,等.国家奖励农业科技成果汇编.1978-2003 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12]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国家奖励农业科技成果汇编.2000-2010 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