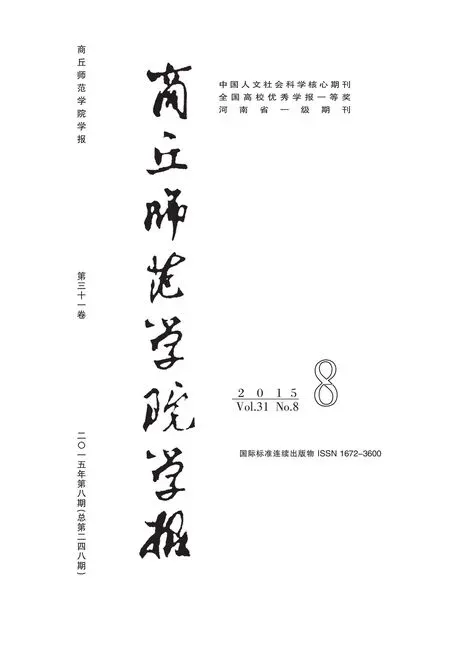性朴论:《荀子》与《庄子》之比较
周 炽 成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国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1)
[庄子·道家·道教研究]
性朴论:《荀子》与《庄子》之比较
周 炽 成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国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1)
《庄子》不全部出自庄子之手,《荀子》也同样不全部由荀子所写。《荀子》中的《性恶》应该是荀子后学的作品。在《荀子》最早的版本也就是刘向编辑的版本中,《性恶》夹在《子道》和《法行》之间,而这两篇已被公认为荀子后学作品。荀子本人持性朴论,其典型论述是《礼论》的“性者,本始材朴”。《荀子》中的《劝学》《荣辱》《儒效》等,都显示人性朴。《庄子》也主张性朴论,《马蹄》明确说:“素朴而民性得矣。”在反对性恶论这一点上,《荀子》的性朴论和《庄子》的性朴论是一致的。不过,《庄子》认为朴之天性绝对完美,故其性朴论实际上是一种性善论,而《荀子》认为朴之性有善的潜质,但还不够完美,需要人为的努力来完善。
性朴论; 《庄子》; 《荀子》 ;王充
今天能读到的对先秦人性论之争的最经典的概括,是由王充作出的,他说:“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孟子作《性善》之篇,以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之乱也……告子与孟子同时,其论性无善恶之分,譬之湍水,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夫水无分于东西,犹人性无分于善恶也……孙卿反孟子,作《性恶》之篇,以为人性恶,其善者伪也。”(《论衡·本性》)根据王充的概括,先秦有四种人性论:性有善有恶论、性善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恶论。论者们对此都很熟悉。不过,很多人都未注意到,在王充的概括中,性有善有恶论是最早出现的,也是被最多的人赞成的。今天有些论者想当然地以为先有性善论,后有性恶论,最后才有性有善有恶论和性无善无恶论。这种想法肯定不符合历史的实情。
王充的概括似乎是历史的定论。但也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以为《荀子》书中所有篇(当然包括《性恶》篇)都是荀子写的,没有把荀子本人和《荀子》这部书适当分开。第二,没有注意到《荀子》之《礼论》《劝学》等关于性朴论的说法。第三,没有看到道家尤其是《庄子》关于性朴论的说法。
本文试图以《庄子》与《荀子》为中心,阐发被很多人遗忘了的性朴论。
一、《性恶》是荀子后学所作
以荀子为性恶论者的基本依据,无疑是《荀子》一书中的《性恶》篇。但是,在先秦子书中,以某子命名的书,并不一定全为某子所写。冯友兰说过:“从古代流传下来,号称为先秦的著作,其中有很多诚然是伪作,例如《鬼谷子》、《鹖冠子》之类。但是有些篇章,如《庄子》、《荀子》中有些篇章,说它们是真固然不对,但说它们是伪也不适当。像《庄子》、《荀子》这一类的书名,在先秦本来是没有的,所有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篇章,如《逍遥游》、《天论》之类。汉朝及以后的人,整理先秦学术,把这些零散的篇章,按其学术派别,编辑起来成为一部一部的整书。其属于庄子一派的,就题名为《庄子》,其属于荀子一派的,就题名为《荀子》。他们本来没有说《庄子》这部书,是庄子亲笔写的,《荀子》这部书,是荀子亲笔写的。本来他们也没有意思这样说。后来的人,不知道这种情况,就在《庄子》这个题名下,加上庄周撰,在《荀子》这部书的题名下,加上荀况撰。再后来的人,就信以为真。”[1]321冯先生之说很有道理。《庄子》是庄子学派的代表作,而《荀子》是荀子学派的代表作。绝大多数论者早已赞成:《庄子》一书的《内篇》是庄子本人写的,而《外篇》《杂篇》是庄子后学写的。但是,现代论者大多不关注《荀子》一书中哪些是荀子本人作的,哪些是其后学作的。本文对其极为关注,尤其强烈关注被后人看得很重要的《性恶》的作者究竟是他本人还是其后学。
唐代学者杨倞在给《荀子》作注时,早就认为该书并非全部都是由荀子所写。他把《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这几篇放在书的最后,认为它们是荀子弟子所作。杨倞在注《大略》时指出:“此篇盖弟子杂录荀卿之语,皆略举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总谓之《大略》也。”[2]485他在注《宥坐》时又说:“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用记传杂事,故总推之于末。”[2]520杨倞的看法已得到大家的公认,因为只要一读《大略》《宥坐》等几篇,就会明显感觉到,它们在写作风格、表达方式、思想内容等方面都确实不同于该书的其他篇。汉代的刘向在编《荀子》时,也是把这些篇放在后面的,他应该也意识到了它们的特殊性。不过,有很重要的一篇即《性恶》,在刘向的编辑中排得比较后,而杨倞却把它提前了。这一很重要的细节几乎没有被现代学者所注意。
在刘向的编辑中,排在最后的9篇是:《宥坐》《子道》《性恶》《法行》《哀公》《大略》《尧问》《君子》《赋》。《性恶》是第26篇,排在《宥坐》(第24篇)《子道》(第25篇)之后,而在《法行》(第27篇)之前。显然,这三篇都是对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的记载(《宥坐》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论,《子道》主要记载孔子与弟子的对话,《法行》主要记载曾子、子贡、孔子的言论),而不是荀子自己的论说,与第23篇《礼论》及之前的论说文明显不同。刘向把在后人看来如此重要的《性恶》夹在不很重要的《子道》和《法行》之间,难道是随意为之的吗?刘向这样编排《性恶》,是否意味着他已意识到《性恶》跟《宥坐》《子道》《法行》等一样不出自荀子之手?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不妨把杨倞的编排与刘向的编排作一比较。看王先谦的《荀子集解》,可以很容易发现两者的不同。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也对两者作了对照。杨倞把刘向所编《荀子》之篇目的先后顺序作了一些调整。杨的编排与刘的编排之最突出的不同是:杨把《性恶》排序提前,从第26篇升至第23篇。杨倞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解释:“旧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议论之语,故亦升在上。”[2]434杨倞的话可以反推:刘向应该是把《性恶》看作非“荀卿议论之语”。也就是说,从这种编排的变动可见,杨倞肯定《性恶》是荀子自己写的,而刘向则认为它出自荀子后学之手。
在刘向放置于最后的9篇之中,《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大略》《尧问》6篇不是荀子所作,早已获得公认,人们对此不会有疑问。关于《赋》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但更多的论者认为它是集体的作品,不是出自荀子一人之手(荀子可能也写了其中一些,但还有其他人写的)。这类似《诗经》的情况。至于《君子》(杨倞认为,当为《天子》,后世传写误为《君子》),其中的尊君、赏罚得当等思想,与韩非子一脉的思想一致,故很可能是出自这一脉的荀子后学之手。《君子》中的话:“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古者刑不过罪,爵不逾德。故杀其父而臣其子,杀其兄而臣其弟,刑罚不怒罪,爵赏不逾德,分然各以其诚通。”显示了鲜明的韩非子之学的精神。不过,韩非子赞成连坐,而《君子》反对连坐。这表明了韩非子一脉内部的分歧。总之,刘向把这9篇放在《荀子》一书的最后,显然与他对它们的作者的看法有关。
从形式上看,在刘向所编的《荀子》一书的最后9篇之中,《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5篇是对话体,《大略》是语录体,《赋》是诗赋体,只有《性恶》和《君子》是论说体。对话体占了多数,而语录体和诗赋体是很特殊的。另一方面,这9篇之外的23篇,多是论说体(只有《成相》除外)。如果刘向认为《性恶》和《君子》这两篇论说文是荀子作的,他应该会把它们放到前面。大量的论说文都编在前面,而唯独这两篇编在后面。如果不把这两篇看作荀子后学的作品,怎么解释这一独特现象呢?
从总体上看,刘向的编排比杨倞的编排更合理。在刘向的编排中,如果把最后9篇排除,那么,荀子本人的作品就是从《劝学》始至《礼论》终,共23篇。首尾两篇都很重要,首篇为纲要,终篇为总结,很好地突出了荀子之重学与重礼,这两者是荀学最有特色的议题。这23篇的顺序大体上是:从个人(《修身》《不苟》《荣辱》等)到国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等),到天地万物(《天论》),附之以思维方法(《解蔽》《正名》等)。这个思路很顺,很清楚,也很有系统。如果刘向真的把《性恶》看作荀子本人的作品,那么,他将其编排在最后九篇之中实在难以理解。
相比之下,杨倞的重新编排则似乎失去了刘向编排的优点。在杨的心目中, 如果他也像刘一样认为首尾两篇都很重要,首篇为纲要,终篇为总结,那么,他当然很看重《性恶》。在现代人看来,《性恶》当然太重要了。但是,荀子真的把它看得那么重要吗?如果它真的那么重要,为什么在其他篇中从未说过人性恶或暗示人性恶呢?重礼的思想在《礼论》之外的很多篇中都有显示,重学的思想在《劝学》以外的很多篇中也同样都有显示。如果《性恶》真的是荀子本人写的而且真的那么重要,为什么在他那么多文章中单独只在一篇显示人性恶呢?如果把《性恶》看做不是荀子本人的作品而是其后学的作品,则可以合理地排除这些疑问。
从刘向所处的汉代到杨倞所处的唐代,经历了八九百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荀子作为性恶论的代表,逐渐得到了公认,而荀子后学作《性恶》的事实则被遮蔽了。那时的人不用标点,作为书的《荀子》和作为人的荀子,都是同样的写法。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把《荀子》中所有看法(包括《性恶》的看法)都作为荀子的看法,就这一点也不奇怪了。杨倞是专家,与一般人不同,他看到了《荀子》中部分篇不是荀子写的,但是,他也跟一般人一样接受了作为性恶论代表的荀子。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这种说法很精要、很对称,而如果说孟子主性善,荀子后学主性恶,这就不精要,也不对称了。显然,精要、对称的看法比不精要、不对称的看法更容易流传开来。不过,在这里应该看到,不精要、不对称的看法才符合历史的实情。
二、荀子本人持性朴论
荀子本人对人性的看法最典型的表述是《荀子·礼论》中的一段话:“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①这些话经常被人引用,但是,几乎所有的引用者都未注意到它与《性恶》对人性的看法的不一致。其实,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精神上,这段论述都不能与性恶论相容。“性者,本始材朴”是对性朴论的最明显不过的表述。朴之性不能说是善的,也不能说是恶的,而是中性的。朴之性不够完美,但如果以“恶”概括之,那就言过其实;朴之性可能隐含着向善发展的潜质,但如果以“善”名之,那也名实不符。显然,性朴论既不同于性善论,也不同于性恶论。它也异于世硕等人的性有善有恶论。虽然关于性有善有恶论的更详细的资料未留下来,但是,根据本文开头所引王充的话大体上可以推定:这种人性论认为有现成的善和恶这两面包含在人性之中,而性朴论却不这样认为。性朴论暗示人性中包括着向善或恶发展的潜质,但不主张人性中有现成的善或恶。另外,性朴论与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有接近的地方,因为两者都以比较灵活的态度看待人性,都承认人性中或善或恶的不固定性。不过,性朴论承认人性有不完美的地方,需要“伪”来完善之,而性无善无恶论则不然。性朴论并未对人性采取纯自然主义的放任态度,而性无善无恶论则有这种态度。
值得指出的是,像荀子这样的性朴论者并未自觉地以性善恶的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他不是以性朴论来回应孟子的性善论的。我还不敢肯定,当荀子说“性者,本始材朴也……”的时候,他是否已经读过孟子对性善的论述。就算假定他读过,他也不打算与孟子展开论战。荀子对人性的态度很像主张“性相近,习相远”的孔子。先秦很多讨论人性的人并不以性善恶的问题作为中心问题。虽然主张人性朴的荀子并未自觉地以性善恶的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但是,这种主张为后世关注这个问题的人提供了难得的资源。
可惜的是,论者们在讨论《荀子》一书的人性论时,大都把《性恶》的论述和《礼论》的论述混在一起,而看不到它们的分歧或者故意否定之。他们可能因一开始就接触荀子是性恶论的代表的传统说法而无法正视与之相反的论述。习惯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以荀子为性恶论者已有两千多年的传统。当人们习惯了这种传统之后,对他的性朴的论述可能就会视而不见或者见而不受。有人会故意强调性恶的论述和性朴的论述“实质上”没有区别。例如,有论者说:“所谓‘性朴’、‘性恶’,在荀子那里,含义是完全一致的。”[3]还有人认为,《性恶》中所说的人性恶,不是指自然情欲本身恶,而是指不受节制的自然情欲必然导致恶,而自然情欲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例如,路德斌说:“在荀子,其所谓‘性恶’,既不是说人的自然情欲本身是恶,更不是说‘人之所以为人者’是恶。其真正的含义是:人的自然情欲本身无所谓善恶,但不受节制的自然情欲必然导致恶。”[4]这似乎是以《礼论》中的性朴论来解释《性恶》对人性的看法。其实,《性恶》的作者是要用自然欲望不加控制地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之恶来论证自然欲望本身之恶。如果他主张自然情欲(性)本身无所谓善恶,这就不能成其为性善论者的对立面了。众所周知,《性恶》是针对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的。孟子显然认为,性本身就是善的。如果《性恶》作者以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他跟孟子论战还有什么意义呢?

性朴论的思想贯穿于整篇《劝学》之中,它没有留下任何性恶论的痕迹。但是,有论者坚持,该篇有性恶的思想。例如,王博在《论〈劝学〉在〈荀子〉及儒学中的意义》一文中指出:“对学的强调, 从逻辑上来说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 即人是非自足的或者有缺陷的存在, 所以需要通过后天的工夫来塑造和弥补。至于这种缺陷是什么, 以及到什么程度, 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荀子那里, 当然是其性恶的主张。性恶代表着人的生命中存在着根本上的缺陷, 因此需要转化。而在化恶为善的过程中, 学就构成了重要的枢纽。”[6]在王博看来,荀子之所以在《劝学》中强调学的重要性,是因为他看到人性中的根本缺陷,即人性恶。人之持续不断地学,就是为了转化人性中的恶。王博以《性恶》解读《劝学》,对之作了很大的误读。认真通读全篇《劝学》,能找到对人性恶的明述或暗示吗?能发现荀子肯定人性有根本的缺陷吗?假如人们撇开荀子是性恶论者的先入之见,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与其像王博那样无根据地强调《性恶》与《劝学》的一致性,倒不如换一种思路:两篇文章非常地不一致,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写的。
《荀子》中的《荣辱》和《儒效》也同样体现了性朴论的思想。《荣辱》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 人的习惯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后天带来的;千差万别的各种人不是本性使然,而是注错习俗使然。《儒效》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人性的可变性和后天作为、环境的重要性,反衬了天性之朴,天性之不恶。
性恶论对人性的看法是很悲观的,但性朴论却不如此。根据《性恶》,人生来就恶。性是与生俱来的、非人为的东西,因而性恶的判定显然意味着恶的先天性。但是,在《劝学》《礼论》《荣辱》《儒效》等,都看不到恶是天生的说法;相反,恶被认为是后天的作为和环境带来的。“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荀子·劝学》)兰槐之根,本来不臭,但如果浸于臭水中,它就会发臭,这表明了环境会改变本性。如果以兰槐之根比喻人性,那么,人性本不恶,而恶的产生完全是环境作用的结果。在《荀子》一书中,只有《性恶》篇主张恶来自天性,而其他篇都未有此主张。
假如承认《礼论》《劝学》《荣辱》《儒效》等出自荀子之手,假如再承认这些文章主张性朴论而不是性恶论,那么,说《荀子》中引人注目的《性恶》也出自他之手,这就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合理的说法应该是:《性恶》不是荀子所作,而是其后学所为②。
三、美朴与简朴
性朴论,不仅为儒家所持,而且也为道家所持。事实上,道家比儒家更为关注“朴”,以致于在汉代之后,它几乎成了道家和道教的专用概念。在老子、庄子等道家代表看来,朴之天性是绝对完美的原初状态。对这种状态的赞美、向往,成为道家的一个主调。《庄子·马蹄》云: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樽!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能至盗者,伯乐之罪也。
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正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上引之言应该是庄子后学所说,但也反映庄子本人的看法。庄子后学一开始说马之真性(朴性),当然实际上是以之比喻人之真性(朴性)。与人们赞美伯乐相反,这里严厉地批评了伯乐,因为,伯乐破坏了马之真性。本然状态的马(野马、朴马)是完美的,而被人驯服的马则惨不忍睹。在批评了伯乐之后,又接着批评陶者与匠人:陶者破坏了粘土(埴)之真性,匠人破坏了木材之真性。当然,对伯乐、陶者、匠人的批评,实际上只是为批评圣人作铺垫。庄子后学认为,圣人用仁义礼乐等破坏了人之朴性,实在是罪大恶极!“素朴而民性得矣”,残害朴素则民性失矣。在庄子后学眼里,所谓人类的文明状态,恰恰只是人类的灾难状态。人类最原始的状态,亦即最朴的状态,才是人类最完美的状态。
与道家之绝对赞美朴性不同,荀派人士比较中性地看待朴性。美朴与简朴两词,精要地反映了两家对朴的态度之异,亦即两种性朴论之异。荀学之性朴论不是性善论,也不是性恶论,而上述道家的人性论事实上是一种性善论。孟子的性善论美仁义礼智,道家的性善论美自然状态。虽然两种人性论所说的性的内容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在极力赞美人的本性方面是相同的。而且,道家实际上对性善的程度的认定比孟子的还要高。而荀子一系的性朴论则不从赞美的态度看人性。在他们看来,朴之性有善的潜质,但还不够完美,需要人为的努力来完善。美朴与简朴之异还带来其他之异:
第一,对仁义礼乐等的看法之异。从仁义礼乐等破坏朴性的立场出发,道家对它们作了非常负面的评价。但是,荀派人士则认为,“本始材朴”的人性需要仁义礼乐等来“隆盛”。它们不是毁坏人性的东西,恰恰相反,它们是完善人性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从荀子的性伪合到董仲舒的质朴与王教之合,都表明仁义礼乐等与朴性的一致性,而不是对抗性。
第二,对人为的看法之异。道家将所有人为都看成是与朴性相反的力量,对人为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上述庄子后学对陶者与匠人的评价,体现了道家对人为的激进否定。《庄子》中有名的关于混沌死的故事,也体现了同样的倾向。混沌是朴的象征,而凿窍是人为的象征。“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庄子·应帝王》)这种悲惨的结局表明了人为之可怕。很多道家人士都遵循天善人恶的逻辑。有道家倾向的《淮南子》的作者说:“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皓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所谓人者,偶嗟智故,曲巧诈伪,所以俯仰于世人而与俗交者也。”(《淮南子·原道训》)与道家相比,荀派人士则充分肯定了人为。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同样,主张性朴论的董仲舒说:“天之所为,止于茧麻与禾,以麻为布,以茧为丝,以米为饭,以性为善,此皆圣人所继天而进也,非情性质朴之能至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人为是“继天而进”的力量,而不是与天相敌对的力量。人为的作用,正如仁义礼乐的作用一样,可以使朴性更完美。
第三,对圣人的看法之异。在上引文字中,庄子后学因圣人设立仁义礼乐等伤害了质朴的人性而对之采取了猛烈的批评态度。他们甚至还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胠箧》)与激进道家的这种态度相反,荀派人士颂扬圣人(圣王)。荀子说:“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礼论》)“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春秋繁露·实性》)圣人的作用得到了荀学的充分肯定。
四、返朴与文朴
从上一部分的论述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道家性朴论倡导返朴,而荀学性朴论主张文朴。在道家看来,既然人类文明使朴的天性受到污染,返朴就是必然的选择。而荀子一派则选择“文朴”,这是笔者据荀子的“礼者,文理隆盛”而造出来的一个词,其意思是让一些东西作用于朴之性,使之更完美。道家返朴回到初生之性,而荀学文朴则让性朝前走。
老子早就提出“复归于朴”(《老子》第28章)。《庄子》也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山木》)“无为复朴,体性抱神。”(《庄子·天地》)作为性善论者,道家与孟子的思路是一致的,即设法回到最早的、最原本的善。老子用赤子来象征这种情形。因为赤子是最朴的,所以老子用“复归于婴儿”(《老子》第28章)来形象地描述返朴。老子在赤子身上寄托了太多的美德,如天纯无邪、洁正无伪、自足无贪、自然无忧、恬静无躁、平和无霸……这些美德都意味着朴,也意味着真。晚明李贽说的童心与老子说的赤子之心很接近: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抵;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盖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有言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似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再。
——《焚书》卷3《童心说》
这些说法体现的是道家的立场。在道家看来,从婴儿到少年、青年、壮年的过程,就是见闻日多、“道理”日广、不断做加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越来越远离朴、远离真,越来越假。道家的性朴论强烈地求真避伪。他们批评人类文明使人变伪,认为最朴的赤子是伪的对立面。很显然,返朴归真确实是道家的基本看法。
道家返朴归真的一种基本方法是做减法。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第48章)把身上已有的东西不断打掉,负担就越来越轻,伪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离赤子之真朴就会越来越近。道家推崇为道而反对为学。为学做加法显然与为道做减法相反。
另一方面,荀派人士的文朴就是老子所说的为学,就是做加法。“本始材朴”的性需要用礼来“隆盛”。荀子以重学而闻名,也以重积而闻名。两者都意味着对简朴之性的作用的增加。显然,文朴的过程,就是仁义礼乐、王教等在人身作用的增加的过程。道家的性朴论喜欢做减法,而荀派的性朴论喜欢做加法。《荀子·劝学》的名言大家都很熟悉:“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在这简短的话里,“积”就出现了5次。《荀子·儒效》又有类似的话:“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谓之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斲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在这一段话里,“积”出现了10次。这些话最能体现荀学的风格。越积越多,意味着文朴的作用越强。
之所以需要文朴,是因为性简朴、朴之性的不完备。如果荀派人士也像道家那样主张初生之朴性已经绝对完善,那么,文朴就是多余的。很明显,两家对朴的评价是不同的。荀子说:“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董仲舒说:“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这些话都表明了文朴的必要性。董仲舒还说:“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与性则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无贤圣……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董仲舒充分肯定了性中有善质,但也仅仅是善的潜质而已,不能说性中有现成的、完备的善。
用通俗的语言来说,返朴的道家担心人太虚胖,而文朴的荀学人士担心人太瘦弱。前者让人减肥,后者让人增加营养。两家性朴论指明了相反的方向。后人也许可以从两种相反的说法中都能获得教益。
五、不同意人性恶
虽然荀派人士的性朴论与道家的性朴论有以上所说的那些差异,但是,两者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不同意人性恶。也就是说,两家都会反对性恶论。
性恶论者不承认人性朴,而认为与生俱来的人性是恶的,善完全是人为的结果: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埶,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
——《荀子·性恶》
上引这些话,坚持性朴论的荀派人士不会接受,坚持性朴论的道家人士更不会接受。在反对性恶论方面,两家可以结成联盟。按照性恶论的逻辑,为了让人变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性,打破人性。从恶转到善的轨迹,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主张人的天性绝对完美的道家肯定不能认同这种说法。道家之天性善、人为恶的立场与性恶论者的天性恶、人为善的立场水火不容。当然,荀派性朴论者也不认可人性恶。董仲舒明确地指出性中有善的潜质,而荀子也蕴含这种思想。朴之性只是不够完美而已,决不能说是恶的。性朴和性恶的差别,一眼就看得出来。
荀派性朴论者不打破朴性,而是养护朴性、陶冶朴性。他们对性的肯定与性恶论者对它的否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说得严重一点,性恶论者的化性,实际上就是破性。这是性朴论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在性朴论者董仲舒看来,善来自性,正如米来自禾、丝来自茧、小鸡来自卵等一样。与小鸡从鸡蛋中孕育出来相似,善从性中发展而来。从善的潜质(朴)变为善,需要人为的作用,但也离不开自然的作用。在荀派性朴论者看来,这两种作用完全是融合在一起的。人为是“继天而进”的力量,而不是“逆天而生”的力量。性恶论者之破性,就是完全否定了自然的作用,从而使人为的作用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虽然我们反复说过荀派性朴论者总体上把朴看作是中性的,但是,有时候他们也会带着褒义来说它。在这些时候,他们与道家性朴论者就更接近了。例如,荀子指出:“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荀子·强国》)在这里,“朴”有明显的褒义。它与老子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57章)中的“朴”非常一致,都是指淳朴、敦厚。这表明:荀派人士与道家对朴的看法有一致的地方。
注 释:
①“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的另一个版本是:“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
②详见周炽成:《性朴论与儒家教化政治研究》,《广西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周炽成:《荀韩人性论与社会历史哲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4页;周炽成:《荀子非性恶论者辩》,《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冯友兰.三松堂自叙[M].北京:三联书店,1984.
[2]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张峰屹.也谈荀子的人性论[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7(9).
[4]路德斌.荀子“性恶”论原义[J].东岳论丛,2004(1).
[5]梁启雄.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王博.论《劝学》在《荀子》及儒学中的意义[J].哲学研究,2008(5).
【责任编辑:高建立】
2015-04-26
周炽成(1961—),男,广东郁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安继民乙未芒种于家乡
B222.6; B223.5
A
1672-3600(2015)08-0001-07
[主持人按语]
秋播一粒种,夏收万石粮。在夏收的丰收喜悦之中,我在家乡浩瀚宁静的夜空下欣赏学习着本期作者的劳动心血,却读出了自己的感受。和诸君相左之意,敬祈来日。
人性论是个古老而又常谈常新的话题,当且仅当在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互补结构中,人性善恶论作为社会善恶守恒律才与个体人性自由论构成争持中的真问题。周炽成先生所论之荀子与庄子的性朴论是以人的个体性为基础的人性的两个最简关系项,颇有见地。王传林所论庄子的“吾丧我”如果不首先抽象转换为一个时空性的动静结构,便既没有认识论问题,也没有境界论问题。高深讨论庄子逍遥游中的“待”字二义:依赖与等待,也是一个时空结构的相互转化问题。我所谓中西方哲学的一元对二元、自因对他因、时间对空间特征,于此获得一次次的证明。尽管这仍可能是仁智自见之论。
美国教授罗尼·李特约翰对东西方古代圣人的考察,迫使人对理性本身进行理性的反思。如果理性无法解决人类心灵的基本问题,理性对感性、科学对神学便应该有所谦卑。理性自负的结果是武断,理性武断与感性温情相比,究竟哪个更好一些,是一个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转换因而需要具体分析的问题。韩坤对峨嵋山早期道教的考察,有类似的心灵指向。同时我想,道释二教在西部的精神拓荒与生命探险,与儒法五岳文化是否构成人文地理上的秩序/自由关系?
儒道两家从魏晋到两宋的哲理升华所彰显的正是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在现实生活中的逻辑两难和功能互补的历史展开。刘世明对山涛的研究和李智福对郭象注《庄》的研究,分别从人生实践到哲学解释学展开,颇有情趣,究其底里,皆为人性的二重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