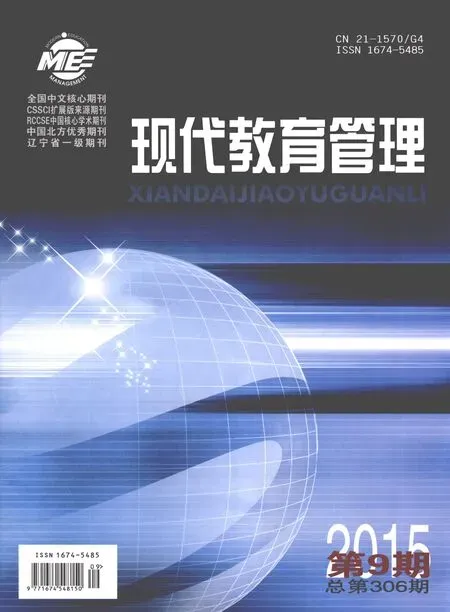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与大学的发展①
——模式1与模式2知识生产的联合
安超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与大学的发展①
——模式1与模式2知识生产的联合
安超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随着全球化、电子信息化带来的知识形态的转变,科学知识的生产已经产生了模式2生产模式,即应用导向、跨学科导向、异质性互动导向、实践性反思导向以及多维评价导向的生产模式,这势必给高等教育科学知识的生产带来新的挑战。大学的发展需要模式1和模式2两种生产模式的强强联合,要“学科语境”与“跨学科语境”并重,处理好专精与通博的关系;要“学术语境”与“应用语境”并重,处理好“象牙塔”与“服务站”的关系;要“学术使命”与“社会责任”并重,处理好“教学”与“研究”的关系。
知识生产方式;模式1和模式2知识生产;学科语境
英国学者吉本斯在《知识的新生产》一书中提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网络技术的普及,知识形态已经发生了转变,迄今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已显得“力不从心”,新的时代需要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出现,模式2知识生产方式应运而生。不过,吉本斯也指出:“模式2并不是要代替模式1,而是对其补充,事实上,它是模式1的一种发展。”[1]笔者认为,当今科学知识生产方式需要模式1和模式2的并重,二者的联合是新的知识生产大趋势,也就是当代知识生产的新特征,这对当下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当代知识生产的新特征
当今时代称之为“知识经济时代”或“信息爆炸时代”,意指知识的种类多样化、数量飞速增长、更新速度加快等。事实上,这些只是知识“爆炸”的表象,其内核是知识的形态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知识更为复杂而且细分程度更高,分支学科越来越庞大且学科交叉现象越来越普遍,并产生了新的研究领域;二是知识的定义发生了扩展和变化,技术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反思性知识等都被纳入知识体系,理性主义知识观、实用主义知识观等各种知识观都有拥趸者,传统的学术观点和尊严受到了挑战,新学科和新知识克服了障碍,登堂入室进入大学课堂;三是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破碎性、多元化、非一致性等特征慢慢进入主流话语,甚至成为知识分子的行话。吉本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并在《知识的新生产》指出,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1是一种理念、方法、价值及规范的综合体——是基于牛顿所确立的经典式科学研究,以单一学科研究为主,并有一套学术规范用来确保其学术权威性。与模式1不同,知识生产模式2越来越重视“应用型语境”,重视“跨学科及超学科研究”,重视形式的“敏捷多样”及知识的“社会作用”。
首先,模式2知识产生于实际应用的语境中,牵涉着所有参与者的利益包括知识的生产、流通、消费、应用各个环节,因此需要更多地专业协商,而在模式1中,问题的设定和解决通常由特定共同体的学术兴趣所主导,以学术旨趣为取向。
其次,模式2具有跨学科性、超学科性。跨学科并非简单的学科之间的叠加和整合,而是从组织的方式、生产的规模、生产者的遴选、产品质量的控制以及同行及跨行评议的选择等一系列环节改变,因此,模式2的知识是在更广阔、复杂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中产生。
第三,模式2具有结构的异质性和组织的多样性。模式2是非等级化的异质性,其结构是复杂多变的,典型的表现是,大学不再是知识生产的核心来源,越来越多的企业、科研机构甚至是民间机构都可以生产知识。而模式1的结构往往是层级制的,而且倾向于维持这一形式,因此官僚化程度更为严重。
第四,模式2生产方式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且更具反思性。许多参与者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相互影响和协商,研究者要对自己的研究保持敏感性,因为研究动机不再囿于科学与技术的范围,也不再是一人之事、凭一己之力可以完成,因而,知识生产也具有高度的自我反思性。模式1知识生产的场所较为集中且高度封闭,知识生产只是少数人或者说精英的权力,其知识的反思性远不如模式2。
第五,在质量控制上,模式2具有评价的多维标准。除了同行评议外,市场竞争力、社会效益及公众接受度等在评判模式2知识产品的质量中起到重要作用,而模式1主要是通过同行评议来评价和控制质量,因此容易造成学术垄断,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和游戏。
知识形态和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古代,由于传播技术的局限,大多数人缺乏手段去接近知识源,学问变成特权阶级的事,学术上的“贵族”守护着真理的宝库,只在极有限的条件下才对老百姓有所施舍。但工业革命尤其是电子革命后,书籍报刊越来越普及,知识传播广泛,迁徙自由,思想交流也变得便利,知识不再凝固不变,而是变动不居,知识的革命必然发生,尽管研究仍然是一门专门化的职业,但特殊的学者垄断阶级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成为历史。
虽然模式1生产方式较为传统,但其经典性、成熟性不容否定。模式1乃模式2的“深井”——为模式2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吉本斯也认为,模式2是从模式1的学科矩阵中演进而来,但他预测模式1与模式2会合并,并成为科学知识生产新格局中的重要方面。笔者认同这种看法,但这并非一种简单中庸的“折中论”,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合并”,而是发展的必需。模式2的发展和成熟,同时促进和加强了模式1的发展,故两者呈现出并重的状态,倾向于任何一端都会带来相应的问题,科学知识的生产有赖于两者之间的“制衡”。
二、知识生产新模式下大学的发展趋势
知识生产方式经历了从“哲学思辨式”到“经验试错式”,再到近代的“科学实验式”的历史。在“哲学思辨式”阶段,知识生产的学术与实用目标分离,学术研究由好奇心驱动,目的主要是认识和解释世界;在“经验试错式”阶段,知识生产的目的主要服务于实践,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科学观,目的主要是改造世界。在“科学实验式”阶段,知识生产成为具有自身独特价值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劳动方式,并逐渐被纳入到整个社会生产的分工体系中。李正风认为,当代知识生产需要“学术语境”与“应用语境”并重,“学科研究”与“超学科研究”并重,“同质性互动”与“异质性互动”并重,“学术使命”与“社会责任”并重,“稳定单一”与“敏捷多样”并重。[2]新时代的知识生产需要模式1和模式2的强强联合。
社会生活经历着彻底的、根本的变化,知识生产模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知识的刺激通过不同的渠道源源不断向人们涌现,民众对知识的态度已经变化,教育尤其是作为知识生产重镇的高等学校,也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彻底的变革。现在大学的很多课程以及方法仍热沿袭旧时代的思想,仍热被旧时代的学术观念、学术范式所支配。每个学校都是雏形的社会,反映大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学应该改变学校的道德风尚、师生关系、引进更生动的、广博的、自由的教育文化,并处理好“专精”与“通博”,“象牙塔”与“服务站”,教学与研究的关系。
(一)“学科研究”与“超学科研究”并重,处理好“专精”与“通博”的关系
跨学科和超学科的研究首先要建立在学科发展成熟的基础上,跨学科程度越高,对学科的成熟程度要求越高,否则将学科知识做简单的加法而非有效糅合是无法促进知识生产和创新的。从这一点上考虑,大学不但要保留,还要加强原有的“专精式”的学科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通博式”的通识教育。
自古以来,大学莫不在专精与通博上求平衡,然而鱼和熊掌无法一时兼得。首先,专业人士仍然有赖于高等教育的人才输出,大学的培养质量决定着专业人员的研究素质。罗素在《教育与美好生活》中提到:“现在英国各个大学正在复归类似于它们在中世纪所占据的地位和传统,它们正逐渐成为专业工作者的训练学院……专业人员的需求量在不断增长,而这些人才主要由大学提供。”[3]怀海德曾说:“我确信在教育中,你排除专精,则你摧毁了生命。”[4]学术有专攻,这是无可置疑的,社会职业结构需要专门知识,学生专修一系一科是必要的,知识上的许多突破仍需倚赖专业化,但大学教育毕竟不只是训练一技一能之士,通博因此也不可获缺。然而,中国的大学在专精与通博的路上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方面,学术专门化越来越厉害,越来越精细,不仅发生了两个文化之对垒问题,而且是“多种文化之相隔”,不仅发生“隔行如隔山”之现象,即使同行学者亦无法沟通其所见所学,学科壁垒越来越难以打破。“道术分裂”至于此,遑论知识掌握之整合性。另一方面,将通博的“理想”简单化为国际化,贪求“高大全”。为了达到与西方世界接轨,大学在全面引进西方大学课程设置和选择模式时,丢失了通博的内核。大学课程之开设花样翻新,泛滥无归,缺少重心,缺少结构性。许多学校的课程都是杂凑式的,没有内在的整体性,连贯性。在课程开设之后,大学没有配套的有效监督措施对课程教学效果进行评估。为了实现通博,实现“培养综合素质人才”的需要,很多大学走向了盲目合并的误区,认为专精就等于丢了学生的综合素质,然则,臃肿而没有质量的教学体制是大学发展的硬伤,会拖大学发展和学生发展的后腿。一个专业并非齐全的大学未必培养不出具有综合素质的学生,这主要靠办学理念、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发展取向,而与大学机构设置的求全求大无关。我们必须认识到通博的精神乃是自由、宽容精神的增长、对人性更为深刻的认识、对社会现象判断的敏锐性,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等,只有这样,学校才会变成一种生动的社会生活的真正场域,而不仅仅是学习功课的地方。
大学的通博,并不是指专业和发展上的贪大求全,这应该是一种理念,指的是对人类知识和文化有相当程度的整体性理解,对自由、不拘一格之学风的创建,对真善美等各种价值形态执着的追求,对学科综合问题的重视(比如人文学科与科学的整合),对民主平等之多元化价值观念的选择等,而非一种物质形态表现,比如,多设专业,设所有的专业,让大学的面积越来越大,专业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臃肿,科目越来越纷繁复杂……正如罗素所说的,“我们不如痛下决心,保住那些我们能够附着到新的更有效力的观念中去的东西;若恪守传统不放,不啻是在为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拼杀”[5]。
(二)“学术语境”与“应用语境”,处理好“象牙塔”与“服务站”的关系
“为科学而科学”,由单纯的好奇心所驱动的学术研究并不会过时。纯粹的学术旨趣有文化追求和政治策略双重意义。从文化追求层面看,无功利主义的纯粹学术理想使人类保持超越世俗和物欲的热忱;从政治策略层面看,在一定条件下是一种维系发展空间和能力的自我保护措施,即通过目的之纯真以求避免其他冲突的、强势的社会力量对科学的威胁、压制和摧残。[6]以应用尤其是市场为取向的知识生产的效果虽然能在短期内立竿见影,过分强调反而会损害科学知识生产的长足发展。所以后者需要前者的存在作为平衡,知识生产要以市场为“参照”而非以市场“马首是瞻”。
大学曾被称为象牙塔,指的是大学只为知识而知识,而对大学外面的民生社会问题漠然处之。现代教育在民主化、平民化、社会化的潮流冲击下,“象牙塔”已经成为被讥讽、贬低的名词,大学也被迫或者主动为社会提供实用的知识,从“象牙塔”变成“服务站”: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被社会化、政治化、市场化了,大学不再是象牙塔,从上至学校高层下至高校教师和大学生对社会的关注以及为了自身利益不断攫取社会资源的积极程度可见一斑。
罗素认为要使学术仍为大学的目标之一,就必须使之与全体社会生活发生关系,而不是仅仅与少数悠哉游哉的绅士的高雅乐趣发生关系。我们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当然不能萧然物外,一心只读圣贤书,对社会冷淡、对生命漠然。我们说大学不能只是“象牙塔”,要“学以致用”,但并非就要一味迎合市场,放弃了大学作为学习和创建知识的神圣场地。大学应该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应该是指南针,有所坚守,有所执着,才带动社会发展。
此外,人们一直担忧过于以应用语境为主的知识生产会使科学失去自由,学术研究失去独立性,使大学的理想发生异化。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的永恒话题,也是学术创新的保障,尤其是现代社会大学被“权力”、“金钱”、“政治”越来越多地绑架之时。中古以来,大学向教会争自由,向皇室争自由,向当权者争自由,向一切世俗的权势争自由,大学的发展史,可谓争取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历史。大学要发展,要成为学术的殿堂,摘取科学的最高桂冠,要高扬科学、人文、民主的大旗,要引领社会的发展,就必须重新获得学术自由权——一种真正有尊严的自由,而不是一种媚俗的无耻的“自由”。西方大学也有一些将二者成功结合的案例,可以作为我国大学发展的参照,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成功,尤其是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以其卓越的教育与科研功能为依托的。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认为,硅谷之所以成为大学科技园的成功范例,“答案并不在于斯坦福大学发现了什么‘秘诀’,而在于斯坦福大学严格贯彻一所‘研究密集型’大学具有的基本的普遍的目标与特性”。这些特性包括:始终承诺建造研究与教学的“卓越性尖端”;始终把教学与研究的结合看作主要任务;始终拥有设置学术方向的自由;把工业和社会上的伙伴关系作为研究的强化剂而非干扰剂;保持边界上的多渠道交流,对研究中的各种机遇保持开放[7]。
从现状看来,社会需要“象牙塔”式的和“服务站”式的大学并存,大学应该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定位,在政策扶持和社会需要下逐渐分化。分化并不等于分三六九等,而是各有所攻。少数大学作为研究性大学存在,部分大学成为“服务站”。在德国,大学和职业学院是并存的,而且不存在歧视问题,对此我们有必要向德国学习。
另外,两种模式能否在某种程度上“和平共处”,还涉及到分工,也即互动类型的问题。模式2所适合的扁平化组织,本意是为了减少沟通成本,但达到某个限度,生产效率反而会降低。因为扁平化的组织通常对应网络化的组织模式,而电子信息时代知识生产网络中节点增多、知识流转路径加长、流转路径受到阻滞、知识的衰减率增大等现象,都可使生产效率降低,从而出现熵增趋势,导致知识生产结构膨胀、老化[8]。如果说模式1的层级制组织存在纵向节点多的弊病,那么模式2的扁平化阻组织由于跨学科、参与者多样化等特征,便会存在横向节点多的弊病。因此,传统的直线型组织和矩阵组织的互动模式仍有存在的价值,需要与扁平化组织相结合,共同承担知识生产的工作。
(三)“学术使命”与“社会责任”并重,处理好教学与研究的关系
司训练在《知识生产网络的进化研究》中指出,的集群式知识生产的动力是知识源取向:就是接近知识源,获取种子知识(元知识或基因知识),产生新知识发酵并获取掌握知识发展的重要方向。[9]基于这一点来考虑,高校如果应对得当,即使无法处于垄断仍然可以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马克卢普认为知识传播也是知识生产的一个环节。知识传播不但需要凭借一定的技术方法和途径,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方式和途径,其中,教育方式和途径是最重要的一种[10]。学术期刊是高校及社会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此高校要改革学术期刊制度,拓宽论文发表渠道,加强论文发表质量,利用网络等先进通讯技术提高知识传播速度,使自己成为知识生产机构中的“知识源”。由于其他进行知识生产的机构如企业等不会将期刊的举办作为重头戏,虽然大学可能不再是知识的唯一生产者,但它仍然是重要的证书授予者和重要的文化资本的仲裁者。因此,高校可利用原有的优势,抓住机遇,避免在集群式生产中被边缘化,
当然,大学不可能再在知识生产中处于垄断地位,但高校因其特有的功能仍然是科学知识生产中的重要场所。这主要是因为知识生产需要投入资金、人才、设备和时间等生产要素。这其中,人才是知识生产和创新的核心和关键要素。[11]对于高技术人力资源的竞争是知识企业优化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因此,高校作为培养高质量人力资源的聚集地,要继续加强自己教学的功能,通过输出“知识生产”的人,使自身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主体。
大学要“传道、授业、解惑”,也有“发展知识”的使命。罗素注意到注重教学的人和注重研究的人往往存在某种对立情绪。但教学与研究是否不能兼得呢?罗素说:“当我们考虑大学在人类生活的作用时,就会发现,研究至少和教育同等重要。”[12]而美国大学的先驱者佛兰斯纳耶肯定教学之于研究的重要性,“成功的研究中心都不能代替大学”。笔者认为,研究与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教师只有通过研究才可以使其教学内容更为充实,更有创造性之发挥;同时,也只有通过教学才能使其研究更有生命,更有心灵上之冲击。若只重教学,则大学和中小学无异,若只重研究,大学就成为纯粹的研究中心。罗素在此问题上提倡不应期望教师长时间忙于教学,也应让他们拥有充分的空闲从事研究。罗素没有详述教学与研究的关系,但他批评了很多教师教学方法和内容的呆板陈旧,并倡导教师用研究的方式增加自己的新知识,为教学创新提供机会。
综上所述,模式1和模式2知识生产的并重是当今知识生产所必需,在这种形势下,大学要强化教学和科研的双重功能。德国哲人耶士培指出:真正的大学必须有三个组成:一是学术性之教学,二是科学与学术性的研究,三是创造性之文化生活。钱穆先生也曾指出中国学问传统向来有三统——人统、事统、学统,“人统”指一切学问在于学习如何做人;“事统”指学以致用;“学统”指为学问而学问。大学能否实现“三统”的并行不悖,答案就在于能否植根于创造性的文化生活,大学应该营造尚知尚师尚德的欣欣向荣的文化氛围,保证教学与研究的蓬勃发展。
[1]Michael Gibbons.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4:14.
[2][6][7]李正风.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9):157-292、69、287.
[3][5][12][英]罗素.教育与美好生活[M].杨汉麟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50、101、68.
[4]A.N.Whitehead.The Aims of Education[M].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7:100.
[8][9]司训练.知识生产网络的进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85、67.
[10]李伯聪.透视知识:知识的“散点透视”与知识社会[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188.
[11]夏先良.知识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104.
(责任编辑:李作章;责任校对:于翔)
The Chang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and the University Development
AN Cha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With the change of globalization and knowledge forms,the mod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has generated the Mode 2 kind of production which orients to practice,trans-discipline,heterogeneity interaction,reflection in action and multiple evaluation that challenge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universities.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needs alliance of Mode 1 and Mode 2 which attaches equal stress on expertise and erudition,academic and social service,teaching and research.
chang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Mode 1 and Mode 2 knowledge production;expertise
G640
A
1674-5485(2015)09-0046-05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重点课题“中国社会-文化视域下的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AIA11155)。
安超(1985-),女,山东泰安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