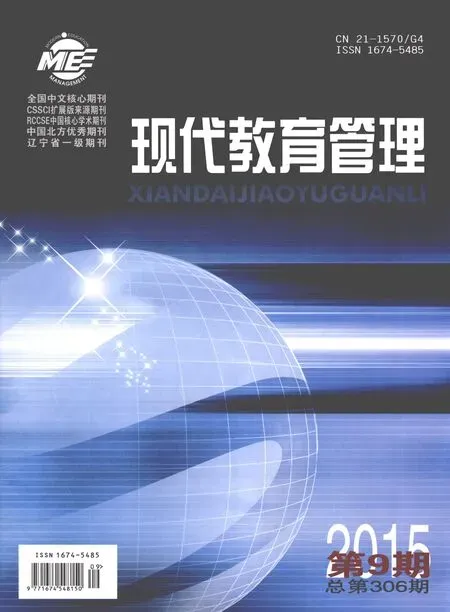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路径优化:基于供需适配性理论的思考①
何锋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路径优化:基于供需适配性理论的思考①
何锋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制度供给不足。教育补偿则是一种制度性补偿。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应关注补偿什么、怎么补偿及补偿效果等问题,即关涉教育补偿是否契合并有效满足补偿对象的需求。根据“供需适配性理论”及其四项标准,应提升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的相关性、可及性、质量性以及相适性,促进教育资源的高效配置,提高教育补偿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切实保障受教育者的教育权利,推进学前教育公平。
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供需适配性;教育公平
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永恒主题,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的工具”。当前,“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的最突出矛盾就是城乡教育差距的问题。农村教育资源、教育效果长期落后于城市已是不争的事实”[1]。教育补偿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主要是由政府为保障弱势群体(处境不利群体)的基本教育权利而设计的教育补救制度和采取的各种教育补偿和救助行为。“虽然绝对的教育公平难以实现,但积极对弱势群体采取补救措施能够消减经济和社会等外部性因素对学前教育公平的影响。”[2]因此,有必要充分了解补偿对象的需求,反思既有的教育补偿供给内容和方式,弥合供需之间的鸿沟,提高教育补偿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一、增强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的相关性
“相关性”关注的是提供给补偿对象的产品和服务是否顾及并符合他们的实际和迫切需求,是否针对亟待解决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特别应注意避免补偿主体提供的公共服务与补偿对象表达出来或尚未表达出(潜在的、可能的、发展性)的需求之间缺乏一定的联系,即出现服务供给与需求不对称的问题。“相关性”这一标准最为核心的要素是需求,即聚焦最需要补偿服务的目标人群的需求。因此,关注目标人群的需求至关重要,一方面,“政府要提供和传递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了解公众的需求及期望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3]。就经济学意义而论,需求蕴含两层含义:一是消费主体有需要;二是消费主体有支付能力。这两层含义暗合了“供需适配性理论”中的“相关性”和“可及性”两个标准。如果消费主体有很强的支付能力,但是主体自身没有需要,那么这种“需求”就会蜕变为“虚求”。如果需要超出了消费主体的支付能力,那么这种“需求”也只能沦为欲望。
(一)正视三种类型的群体需求状态
其一,“无意识型”需求虚无。补偿对象自己不知道有何种需求,难以表达抑或不愿意表达合理的教育需求。一般都认为“觉得都挺好的,没有什么要求”,这看似是对教育现状的“满足”,实际上这种“需求虚无”或“需求隐匿”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正如英国约克大学社会行政学教授布拉德肖所担心的,“问题是人们是否会说出感觉到的需求或者去追求这种需求的满足”。这种“需求无意识”和“需求隐匿”一定程度上表明补偿对象无力或无心关注幼儿是否接受学前教育以及接受何种质量的学前教育。
其二,“低层次型”需求满足。补偿对象的需求停留在较低层次上,甚至有悖于学前教育的基本规律,集中表现为“有的玩、有人看、教认字、会计算、能讲故事就行了”等成人化、小学化的观念和行为。
其三,“高质量型”需求期待。补偿对象有以“质量”为核心的需求期待与强烈诉求。有些地方“高标准”新建了不少村办园,但却出现了“楼美人缺”和“人去楼空”的现象,导致这类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调查发现,对于是否应开设村办园(班、点)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没有必要开设村办园。“家长不愿意在村办班就读,除非村办班比中心园办得好,家长才会考虑。而且现在的村和社区相对分散,即使办了村办班,也不能照顾到更多的幼儿,只能辐射到周边的一两个村,家长情愿多走一段路到中心园就读。”二是认为有必要开设村办园。“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村和村之间的路程比较远,应该就近入园。家长长途接送和乘车都给孩子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路途的安全问题伤不起,特别是村办班的办班质量应该得到保障,否则家长宁愿舍近求远。”
“高质量型”需求期待表达上虽有差异,但焦点均指向质量。而“无意识型”需求虚无和“低层次型”需求满足两种类型的需求则反映了一部分群体的学前教育意识和观念。“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二元教育结构已内化成城乡人口不同的教育意识与教育观念,这种意识与观念的不同又会反作用于城乡教育差别的存在。”[4]特定的历史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补偿对象的教育意识和观念,这种意识和观念又会对其教育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可见,观念的启蒙与变革是非常重要的。“无心”意味着教育补偿不仅要提供“有形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还要注重解决“无形的”观念羁绊。故而,正视观念的懵懂、散去观念迷雾,启蒙理念,使这一群体了解学前教育的基本规律以及对于儿童发展的价值是针对这两类目标人群不可忽视的重点补偿内容。比如,当前围绕学习和宣传《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而开展的“学前教育宣传月”就是旨在通过社会宣传,让科学育儿观念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因而,忽视补偿对象的实际需求、可能需求以及发展性需求的教育补偿往往会低效甚至无效,极易造成有限教育资源的显性和隐性浪费,最终会制约补偿对象享有平等的学前教育的机会与权利,难以真正促进教育公平。基于此,在教育补偿过程中需要在教育补偿对象的实际需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及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特点三者之间寻求臻于合理的平衡点,进而有针对性的逐步发展。
(二)完善需求表达与利益诉求机制
无论是个体需求还是群体需求都存在层次性、差异性及多样性。因此,应充分了解补偿对象的需求,构建并完善教育补偿对象的需求表达和利益诉求机制,这也有助于提升教育补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英国学者布拉德肖基于社会福利服务这一视角,认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感觉出来的需求、表达出来的需求、规范性需求和比较性需求。感觉出来的需求是指能直接反映一个社会成员当前所需要的东西。常常在社会调查报告以及媒体中出现。表达出来的需求是指社会成员把自身感觉性需求用实际行动来表现,它实际上是感觉性需求在行动中的进一步演变与发展。若果当某一类会群体的感觉性需求得到了政府和学者的重视、认可,那么该社会群体就极有可能成为政策的主要关注对象和最大受益者,他们的需求就成为一种表达性需求。规范性需求是指由行政管理者、学者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专业人员根据特定的实际情景,对需求进行严格定义,对需求内容进行具体规定。.比较性需求是指倘若某种公共服务得以标准化,则接受服务的对象就必然有一定的“社会性特征”,根据公共服务的标准或者服务对象所体现出来的特定的社会性特征,公共服务供给方就可以在一定的区域中较为清晰地分辨出潜在的具有这种需要的服务对象。
如何帮助教育弱势群体进行需求表达和利益诉求?一方面要以社会志愿者服务团队为依托,建立合理、顺畅的教育弱势群体的利益组织与表达渠道。在此基础上,构建教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借助于一定的组织形式(政府的或社会性的),拓宽教育弱势群体的利益联合通道。如此,各级政府就可以更便于及时了解教育弱势群体的教育利益需求并做出反应和回馈。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尚在完善过程中,大众传媒在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就是通过大众传媒表达的。因此,在现阶段应特别注重以大众传媒为中介,建立教育弱势群体的公共舆论表达渠道。
二、加强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的可及性
所谓“可及性”是指补偿对象获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具体而言,是指旨在帮助补偿对象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否具有物理性的和经济性的可获得性。也就是说,教育补偿这一公共服务常常会受地理位置(幼儿园与家庭距离远)和经济障碍(入园费用高)等限制,导致补偿对象的公共服务可获得性降低。就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而言,在提供公共服务时要关注补偿对象消费补偿服务的能力及所需付出的消费成本。比如,在村办园布局方面,应尽力避免出现“入园远”和“入园贵”等现象,以使这部分目标人群具备消费有质量的乃至优质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能力。特里·L·库珀就明确提出了消费公共服务的成本这一问题,“在现代工业社会,全面实现公民权利应当包括具有消费公共服务的能力。如果服务是以一种高成本的方式提供,使得公民无法消费得起的话,那么完整的公民权就被剥夺了”[5]。
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的目的在于使补偿对象能有效地“消费”政策,普惠受益。补偿对象为此付出合理的消费成本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倘若补偿对象所付出的消费成本偏高甚至高于其受益,就会丧失消费能力,结果可能就是“政策失真”,甚至是政策失败。因此,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要规避单向度的思维,不能过于用心精打细算“生产”成本,而疏于关注补偿对象的消费能力及可能付出的消费成本。否则,一个初衷很好的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起到副作用,与政策目标不兼容,甚至产生冲突,增加补偿对象的消费成本,比如家长、幼儿园乃至相关职能部门巨大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精神成本等。譬如,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入园远”问题,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幼儿和家长的时间、精力、安全等成本。
三、提升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的质量性
“质量性”标准是四项标准的关键所在。“质量性”强调提供给补偿对象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而不可使补偿对象只能得到劣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一)质量是教育补偿的核心要义
1.教育补偿:从机会公平转向质量公平
当前,“质量”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特别是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学前教育而言,更显紧迫和弥足宝贵。质量是教育补偿的核心要义,失去质量的教育补偿是没有含金量的“得不偿失”。当前,众多的研究有力地表明早期教育与保育对于个体及社会确实具有一系列的重要价值。然而,正如《强势开端Ⅲ:早期教育与保育的质量工具箱》研究报告开篇所提出的,这些的价值的实现都来自“质量”,若仅仅是扩大早期教育与保育的服务范围和资源总量而不关注质量,就极有可能不会对儿童或社会产生良好的益处。只有建立在有质量保障基础上的教育补偿,才可能实现约翰·罗尔斯所提出的“不仅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而且保障并实现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教育补偿不仅要给予农村学前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提供有质量的学习机会,实现机会公平向质量公平转向。
2.教师是关键:从重“技术装备”转向关注师资建设
没有质量或低质量的教育,是愧对儿童、家长和政府的。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重在提高质量,而教育质量的提升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其最为关键的支撑因素是教师。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要正确看待并处理好形式与内容、效率与质量的关系,教育补偿不能仅停留在盖房添设备之类的显性工作之上,而要转向正视并改善以师资建设为核心的隐性内容上。我们看到,有不少的“提优工程”、“扶持计划”等大都止步于技术装备,而师资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诚然,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从物质环境改变开始一步一步慢慢来,但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保障农村学前教育质量扎扎实实提升,真真切切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师资,“相对于数量而言教育效率的本质是教育质量。只有高质量的教育,才有对个人发展、国家发展的高贡献”[6]。哥伦比亚大学的C.Howes和S.L.Helburn提出了学前教育质量的三个组成要素:过程质量、条件质量和劳动环境质量。过程质量包括师幼之间相互作用、活动的组织实施等;条件质量包括是师幼比、师资学历、培训与研修等;劳动环境质量则包括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和职业满意度等。可见,师资及其素质是这三个组成要素的交集。
但整体来看,当前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师资较薄弱。从幼师比来看,2010年农村幼儿园幼师比高达36.42∶1,约为城市的三倍。再就教师学历来看,专科及以上学历,城市为71.50%,县镇为60.13%,农村仅为41.76%,城市比农村高出30个百分点。[7]因此,教育补偿要从技术装备取向转向师资建设取向,一方面要增加师资数量,另一方面则需要提高师资整体素质。
(二)厘清教育补偿中的两对关系
充分认识和理解教育补偿的质量要义,必须厘清“额外补偿”与“优先发展”及“坚守底线”与“维持低标准”这两对关系。
1.“额外补偿”与“优先发展”:“补偿性”和“发展性”兼具
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滞后,主要是由于制度供给不足,教育资源配置失衡造成的。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存在平等取向、强势倾斜取向、弱势倾斜取向和弱势补偿取向四种取向。在弱势补偿取向下教育资源配置是以反思历史为前提,对社会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利益受损群体进行补偿,优先保障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它是一种差异补偿,不仅需要额外补偿,更需优先发展。众所周知,多年来我国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以社会中的优势地区、优势群体为重点对象,优先满足条件和基础好的地区和幼儿园。为缩小差距,推进公平,如果再采取平等原则,城乡一视同仁,或仅是弱势倾斜,那么资源配置失衡将进一步恶化,教育公平离我们将愈加遥远。
有鉴于此,我国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需要从弱势倾斜走向弱势补偿,不仅要体现“同等待遇”,更要提供“优先待遇”,以实现农村学前教育的“积极发展”。
2.“坚守底线”与“维持低标准”:坚持有质量的底线要求
底线标准必须是建立在质量保障基础之上。若在观念上将底线理解为低水平或者低质量,在实践中仅仅是维持低质量、低标准的“底线”,则必然与教育补偿的要义背道而驰。此外,需要强调的是,教育补偿必须正视农村学前教育薄弱与落后的历史与现实,“没有照顾到农村教育发展的‘畸形’历程与缺损现状的‘保障底线’的思维和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作用”[8]。公平、普及、与高质量是当前国际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战略,在理念上它们并不是简单的递进关系,而必须同时予以关注。只有高质量的普及才能实现公平,正如《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2009)所指出的:“公平与学习质量永远是一个紧密的结合体”。
底线是用质量绘就的。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需要坚守有质量的底线,而不能仅维持低水平、低标准的“底线”。事实上,在学前教育体系供应面扩大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质量下降是每一个快速扩张学前教育服务体系的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这既涉及到资源的可获得性,又关涉质量监控体系的完善性。基于此,为确保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的质量,有两项当务之急:
第一,建立并完善农村学前教育质量标准。不可否认,我们还处在一个质量标准相对匮乏的阶段,农村学前教育质量标准建设尤为重要。特别是,有质量绝不等同于有现代化的技术装备。“物质条件在我国各地学前教育质量标准中所占权重高,学前教育机构的质量评价主要是评价学前教育机构的场地园舍、设施配置、教玩具设备等的数量和种类。”[9]现有的“质量标准”大多偏倾于设施设备配备标准、技术装备标准等,尚缺少针对性的师资配备、教育过程评估等标准。因此,亟需改变当前重设备配备标准,轻人力资源建设标准的现象。需要在尊重农村学前教育实际的基础上,制定一个与经济、师资水平等相适应,适合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水平的农村学前教育质量体系。
第二,探索建立“问责型”质量监管评估机制。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在实际运行中体现为若干政策和具体项目,这些政策和项目实际效果如何?这既需要过程性监管,也需要对其进行效果评估。通过评估有助于推广有效项目并对其增加投入,调整或撤销低效或无效项目,减少对项目质量进行稀释而浪费公共资源的现象。国际上不少国家非常重视对项目实施过程及其质量、效果进行严格的管理与评估。比如,美国历史上就有由于缺少及时的有效的项目评估,造成了经费大量浪费的惨重教训。有评估报告指出,美国联邦政府于1965年立法颁布启动的第一条款(Title I)项目,“数十年过去了,在我们花费了大约2000亿美元后,专家们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颇为惨淡的图景——项目收效甚微,不堪一击,效果不佳,甚至在他们自己看来,这些项目就是彻底失败的项目”[10]。有鉴于此,美国联邦政府随后启动了一项名为项目等级评定工具的审查制度,通过评估促进项目提高有效性。自2004年该工具使用以来,共有56个学前教育保教项目接受了这项等级评定,其中仅有2个项目被评定为“有效”,14个“一般有效”,5个“无效”,35个则为“不能判断结果”。苏珊·纽曼总结了有效的教育项目(政策)必须具备的七个基本原则,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坚持对项目的成效以及项目对儿童学业成就的贡献进行问责”。
四、关怀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的相适性
“相适性”主要是指提供和递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干预和机制应考虑服务对象的活动和在时间或劳动使用等方面的约束。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应关注当地经济、文化、生活等特点,提供与补偿对象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与生活能力相契合的公共服务。随着城镇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有两个鲜明的变化: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型村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大规模的村落群,“村”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都扩大了。特别是由于21世纪初大面积的“撤点并校”,农村幼儿园和学前班急剧减少,不少地方只保留一所乡镇中心幼儿园,农村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远”问题突显;二是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人口年龄结构日趋老龄化,留守老人和留守幼儿数量不断增加。据调查,“学龄前儿童在农村留守儿童中所占比例为27.05%,其规模达到1585.2万人”[11]。繁重的农耕事务和幼儿养育大多由祖辈所承担,“隔代教育”引发的问题也渐趋增多。为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教育补偿的“相适性”,笔者从幼儿园布局规划、幼儿园课程与教学两个方面进行考量。
(一)布局规划:因地制宜,形式多样
当前农村学前教育布局规划主要存在两个制约因素:一是不少农村地区经济状况不佳,没有充足的财政投入建设足量的幼儿园,导致资源严重不足;二是在有些地方,政府担心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农村地区的新建幼儿园将来会出现空置现象,频现超大规模幼儿园。因此,布局规划不能仅以当下形势为依据,而要根据人口、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当地农村发展趋向进行长远规划与超前布局。既要考虑目前农村学前儿童入园的紧迫需要,缓解资源紧缺,又要考虑农村未来人口的变化因素,避免资源浪费。值得一提的是,在主要关注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人口因素影响的同时还应考虑到补偿对象对于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消费能力和可获得能力。从实际情况出发,把“方便”、“就近”等“群众需求”作为幼儿园布局的基本要求。根据当地实际,办园(班、点)形式可以多样化、多层次化。比如,在偏远农村地区可多办学前班、村办点等形式(当然,公共财政特别是县级财政应着力保障学前班、村办班点的正常运行)。此外,“在部分比较偏远、贫困、适龄幼儿较少的乡村,应结合新农村建设,在村公共场所设立幼儿及其家长的活动室,由乡(镇)中心幼儿园组织教师或志愿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巡回开展灵活多样的教育活动,同时对家长进行家教指导”[12]。
(二)课程与教学:立足本土,超越本土
一方面,课程与教学应立足于本土。所谓“好的学前教育”绝对不是以城市为基准的。虽然城乡一体化,但城乡物质和文化环境存在差异,并不意味着城乡教育要同一化。在课程建设上应充分利用符合当地实际情境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农村新建园而言,应避免机械地以城市幼儿园为标准,进行环境创设和课程建设;避免盲目地追求环境的奢华,环境创设要体现“低成本且有质量”。比如,普遍盛行的大面积的塑胶场地可能并不一定适合农村幼儿园有效实施课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前农村学前教育师资力量严重匮乏,专业能力亟待提高,农村学前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相对较低,如果简单地模仿城市幼儿园的课程内容和实施形式,农村教师往往会难以驾驭,导致保教质量低下。因此,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要注重考虑到农村学前教育的师资状况,将高结构化课程与低结构化课程有机结合,既发挥农村学前教育的地域和文化优势,又能使农村幼儿获得相应的发展。
另一方面,课程与教学又要“超越本土”。所谓“超越本土”,就是在课程设计与教育教学中要减少“单一维度”经验的过度重复。我们给予幼儿的经验应该是多元的、整体的、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的。譬如,有的地方充分运用当地资源进行民间传统工艺游戏,为幼儿提供了经历和经验传统文化的机会,但是要避免活动类型、活动材料的长期重复。因为,从幼儿长远发展来看,长期进行低水平或者高水平经验的重复活动是不利于幼儿获得变化的、多元的丰富经验。
[1]龙安邦,范蔚.我国教育公平研究的现状及特点[J].现代教育管理,2013,(1):16-21.
[2]杨海瑶.学前教育的公平理念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学前教育法的思考[J].现代教育管理,2012,(3):40-44.
[3]孙选中.服务型政府及其服务行政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110.
[4]张乐天.城乡教育差别的制度归因与缩小差别的政策建议[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71-75.
[5][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2-53.
[6]褚宏启.关于教育公平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中国教育学刊,2006,(12):1-4.
[7]刘占兰,等.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报告201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103.
[8]许丽英.论教育补偿机制的构建——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实现路径探讨[J].教育发展研究,2010,(19):31-35.
[9]刘霞,戴双翔.我国幼儿园教育质量标准研究[J].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10,(1):144-158.
[10][美]苏珊·纽曼.学前教育改革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美国的经验[M].李敏谊,霍力岩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34.
[11]段成荣,杨舸.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008,(3):15-25.
[12]罗英智,李卓.当前农村学前教育发展问题及其应对策略[J].学前教育研究,2010,(10):9-12.
(责任编辑:李作章;责任校对:于翔)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ompensation 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Rethink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Adapt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HE Feng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of Science,Nanjing Jiangsu 210013)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backward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is the lack of system supply.Educational compensation is a kind of system compensation.We must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ontent,methods and effect of compensation.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he adapt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we should improve the correlation,accessibility,quality and adaptability of educational compensation,for promoting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improving the educational compensation accuracy and validity,and also earnestly promoting educational fairnes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educational compensation;the adapt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education equity
G610
A
1674-5485(2015)09-0029-06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10年度招标课题“学前教育体制和机制改革研究”(10JZD0035);教育部重点课题“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研究”(DHA110229)。
何锋(1981-),男,江苏如东人,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学前教育政策、学前教育课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