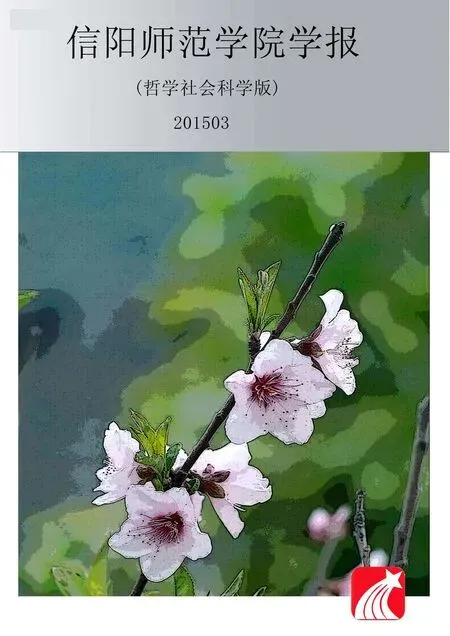“向上的台阶”上的“个人悲伤”——周大新和方方的两部中篇小说对读
吕东亮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在文学研究中,比较并不是一个新异的研究方法,甚至也不是一个逻辑自洽、具有内在合理性的研究方法。不过,比较性的研究如果有一个合适的基点的话,其有效性还是毋庸置疑的。本文选取周大新的中篇小说《向上的台阶》和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进行对照性阅读,主要是基于两部名作在社会阶层流动问题书写上的不同凡俗的表现。
一、为什么要对读
周大新的中篇小说《向上的台阶》,最初发表在《十月》1994年第1期,随后获得《十月》优秀作品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第六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入选多种文学选本,也被作家自己视为重要代表作之一。可以说,《向上的台阶》是周大新作品中经典化程度较高的一部。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发表在《十月》2013年第2期,随即引起热议,一个月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十月》杂志也很快组织了作品讨论会并在2013年第5期刊发讨论会记录稿《“问题”还是“主义”》,这对于著名资深文学期刊《十月》来说是不寻常的举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也斩获了《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老舍文学奖提名奖等奖项,并位居2013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第3名,其在文学史上的留痕是可以确定的。
《向上的台阶》讲的是贫寒人家出身的廖怀宝在新中国成立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历史时段中逐渐成为地厅级领导干部的故事。廖怀宝的父亲廖老七承继祖业,在镇上以代人写柬帖状纸为业,勉强维持生计。廖怀宝自幼聪慧,稍长便很快练得一笔好字,掌握了祖传的本领,随父亲一道谋生。他原打算继承父亲的生计,不料随着全国解放的进程,共产党委派的工作队接管了柳林镇的政权。工作队的队长戴化章看中了廖怀宝的一手好字,便劝导廖怀宝参与柳林镇新政权的筹建。在父亲廖老七“只要是官我们都当”[1]106的教谕下,廖怀宝进入官场。从镇文书做起,开始其“向上的台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为地区常务副专员。小说情节主要围绕着廖怀宝的每一次升迁展开,叙述的推动力也来自廖怀宝在升迁之际面对两难情境的抉择。虽然小说塑造的廖怀宝只是个案,但人物身上的典型性是存在的,因而可以说《向上的台阶》讲的是一个关于阶层流动的故事,这从小说题目也可以看出来,尽管小说的作者或许对此书写的宏观意义尚缺乏自觉。《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讲的则是新世纪(至少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底层青年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但最终归于失败的故事。偏远山村的农家少年涂自强通过刻苦学习考上了武汉的一所大学,为了凑够学费,涂自强提前启程,一路打工来到自己的大学。在大学期间,涂自强利用学校和同学们提供的帮助,维持了自己的生活并圆满完成了学业。毕业之后留在城市打拼的涂自强,顽强工作、努力向上,耗尽自己的能量,仍然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当意外的疾病袭来,涂自强的命运只有毁灭。《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发表后,很快被读者视为反映底层群体上升通道受阻等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虽然把《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视为“问题小说”,有些忽略小说的复杂内涵和艺术品位,但相对于流行作家包括方方自己的其他优秀作品来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在社会现实的呈现方面无疑是具有突破性的。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发表后,很多评论者都将其与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联系起来讨论,涂自强也被视为新世纪的“高加林”。就农村青年个人奋斗、农民进城等文学主题来说,二者也可以说存在着互文性的关系。不过,高加林和涂自强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分享的却是“文化大革命”后开启的同一个历史进程,而《向上的台阶》的故事却结束于这一历史进程的开始。因而,如果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观察社会阶层流动问题的话,《向上的台阶》或许更适合被我们拿来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进行文本的对话。
二、“向上的台阶”何以可能
《向上的台阶》中的廖怀宝,原本是一个小镇贫民的孩子,尽管跟从父亲学习而识字,却只能在维持生计的意义上发挥作用,廖家也没有能力供其读书考学,因而“学而优则仕”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向上的台阶”之所以在廖怀宝面前持续不断地展开,主要缘于社会历史的重大变革。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了,以裴仲公为代表的地主阶层被打倒了,作为一介贫民的廖怀宝才有了进入官场的历史前提。廖怀宝做了镇文书进入官场之后的每一次升迁,都离不开社会政治的变动。主动参与土改,弃取裴仲公的女儿,廖怀宝成为副镇长、镇长;迎合上意,率先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廖怀宝被提拔为副县长;积极实施“大跃进”,虚报粮食产量,又被提拔为县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之后佯病不出,避免被伤害,随后在解放干部的潮流中出任干校副校长,暗中保护被下放干校劳动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复出的老干部推举廖怀宝出任地区常务副专员。在小说的叙述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一次政治变动都针对性地为廖怀宝提供了升迁的机遇,廖怀宝的“向上的台阶”建基于政治变动所衍生的权力空间中。小说的描述是符合历史情势的。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政治运动频繁,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会导致社会阶层的变动,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社会阶层的流动就成为一种常态。这种政治动力主导下的社会阶层流动,很难说是一种良性的、合理的阶层流动。它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它给个体带来的屈辱和伤害是严重的,这些都显而易见且被历史所证实。根据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社会流动是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社会流动,既得利益阶层固化,公平正义就无从谈起,社会也将没有活力而面临危局。廖怀宝的“向上的台阶”,就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形象描述。廖怀宝一步一个台阶的历史时段,频繁的政治运动造就了太多的不公平和非正义,但宏观地来看,政治运动在客观上瓦解了固化的社会阶层,加速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底层的上升通道从总体上看是敞开的。如果我们暂时搁置对于小说人物的道德评价,便会发现廖怀宝这一类人的成长就是证明。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涂自强,其“向上的台阶”始于考上大学。考学自古以来就是社会流动的主渠道之一,《人生》中的高加林之所以深感压抑,就是高考落榜封闭了其向上的通道,而涂自强却获得了合法的、体面的通道,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和高加林深刻区分开来了。涂自强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家人欣喜异常,族人扬眉吐气,村人为之骄傲,离开村庄的时候,全村人送行,用送他的拖拉机手同学的话说就是“都拿你当英雄哩,指望你学完回来拯救村庄似的”[2]14。在现代化进程中陷落的、因而需要拯救的村庄,才是涂自强的起点,这起点和台阶是无缘的。考上大学,在村人的想象中,是“去县衙当官”,享受荣华富贵。岂不知涂自强所面临的大学时代,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不仅不能保障进入体制内当官,连工作也不好找。考上大学为涂自强提供的台阶,只是成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台阶。涂自强的大学生活相比于其同学来说,过得窘迫清苦,但相比于农村老家来说,已是天上人间,令涂自强感到满足。大学毕业,涂自强又一次需要寻找“向上的台阶”。他在赵同学的帮助下,分析了就业形势和自身优长,决定考研。涂自强对考研的准备是异常充分的,几乎投入了所有的精力,以至赵同学惊呼:“人类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涂自强前进的步伐了。”[2]72但意外还是出现,就在考试之前的晚上,涂自强接到父亲病死的消息,回家奔丧因而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机会。涂自强在埋葬父亲之后依然振作精神,投入职场,开始打拼。涂自强尽心尽力地干过许多辛苦的工作,对自己的生活又俭省至极,即便如此,生存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如同小说中叙述人所说的“他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2]170。被超负荷的工作所消耗的身体,却没有时间和条件得到补养,涂自强的灾难很快来临了。当他得知自己“肺癌晚期”的病情之后,把母亲安置在莲溪寺里(这里宗教似乎成为救赎的唯一途径),平静地接受了命运。“向上的台阶”上再也不可能有涂自强的闷头努力的身影。和廖怀宝相比,涂自强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政治波澜不惊的时代,是一个以社会公平正义的承诺为起点的新时代。但我们会惊诧涂自强的命运何以如此不堪。小说的叙述告诉我们,考研失败似乎是涂自强命运的转折点,意外的来临使这个机会迅速逝去。但我们可以追问,涂自强为什么不能再来一次,是什么使他不具备失败一次的权利呢?在涂自强的职场生涯中,我们会发现影响其安心工作、顺利发展的因素多是母亲带来的家累,但我们也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涂自强的母亲是家累,而有的人的父亲母亲却是关系、是背景、是成功的要素呢?涂自强的失败似乎源于突发的疾病,但小说如此处理并无任何牵强之处,因为每个人都会有风险,但为什么是涂自强没有社会医疗保障,没有定时体检等福利待遇,没有任何抵御风险的能力?只要我们对小说稍加梳理,就会发现,在当下看似公平竞争的体制中隐藏了太多的不公平,这才是涂自强从“图自强”到“徒自强”的根本原因。
关于社会阶层流动及其障碍,中国的学者十分认同英国社会学家帕金的“社会屏蔽”理论,即“各种社会集团都会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3]7。对于传统中国来说,“社会屏蔽”理论其实就是官本位体制的另一种名称而已。但在传统中国的开明时世,官本位还是有其正当性,而且“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是流动的,科举制的发明就是为阶层流动提供通道。《向上的台阶》中的廖老七之所以迷恋权力,训导儿子攀登仕途,就是因为阅世甚深,尤其是吃了官司和领略了大地主裴仲公家的繁华之后,体验到了官本位或者说是“社会屏蔽”的秘密,虽然这也算不得什么秘密。悖论的是,廖怀宝之所以走上仕途、不断上升,所凭借的不再是传统社会的科举考试的渠道,恰恰是革命及随后以革命名义进行的政治运动对官本位体制的冲击。尽管革命本身也是一个屏蔽社会,但因为不断地反省自身,不断地反对官僚体制,社会屏蔽所造成的不公平就成为显性存在,为革命提供了对象和动力,而革命的动力就转化为社会流动的动力。这是廖怀宝不断获得升职机会的重要原因。在小说的叙述中,廖怀宝在各种政治变动面前左右逢源,不断拥有上升空间,成为政治幸运儿,不免让人感到有些机遇是上天垂青,但除了小说塑造的个案之外,大量的廖怀宝们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向上的台阶”的。涂自强所处的社会似乎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开放社会,似乎摆脱了以往政治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屏蔽”个人发展困扰。但小说叙述的事实告诉我们,涂自强们所面临的“社会屏蔽”却愈加坚固,有如无物之阵,看起来并不存在,却隐性地发挥覆盖性的作用,留给涂自强的突破口越来越小。涂自强临近毕业时,赵同学对他发展的建议其实指出了涂自强所面临的台阶的有限性:“我觉得攻学位就是你最好的出路。你既没背景,又没财力,你有的只是个人奋斗的动力。但是,现在的社会,没有人际关系,个人奋斗到死,也没什么用。比较起来,还只有考学位相对公平点。你仔细想想看我的话有没道理。另外,我定要给你一个忠告:千万别回老家。下面的事,全无章法,哪天你死了都不晓得是怎么死的。”[2]70而且涂自强后退之路也被堵死了,赵同学的忠告很能说明基层中国的社会屏蔽更加严重无理,这从涂自强父亲的抑郁而死等情节也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涂自强们面临的困境,没有政治动荡的中国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发展的机会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均等、不公正现象,社会阶层不断固化,“富二代”“官二代”们身上不断聚集优质资源,发展空间日益广阔,而涂自强们这一无机会群体的个人奋斗却被屏蔽在发展空间之外,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三、“悲伤”为何是“个人的”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个人悲伤”一语出自于小说中涂自强女同学采药在高考落榜后写给涂自强的一首诗:“不同的路/是给不同的脚走的/不同的脚/走的是不同的人生/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2]2采药高考失败,涂自强高考成功,有人上榜,有人落榜,似乎是自然不过的事,也似乎是个人化的事,因而悲伤也只能是“个人悲伤”。涂自强找工作受挫之时,想到自己因为不是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名校学生而失去竞争力,就归之为还是自己努力不够没考上名校,此时的悲伤也只能被理解为“个人悲伤”。涂自强不会想到并追问,自己所上的乡村高中优质教学资源何等匮乏,升学率是何等之低,自己为什么不找一个大学生家教帮助自己补习功课,尤其是补习自己考研时感觉蹩脚的英语听力呢?涂自强不可能清楚地意识到他生于偏远山区农村家庭这一事实就造成他处在不公平的起点上,而社会资源配置的持续不公平所导致的“贫困因素的综合深化并在代际之间连续形成”[4]这一状态,正在他自己身上有力显现并发挥作用。涂自强只能从自身找原因,找不到也只能自我伤感一小会儿。涂自强离开农村之后,遇到了很多好人,得到了许多帮助,即便是那些辞退他的老板们,其行为也不缺乏正当性。唯一欠薪逃匿的学长老板使涂自强半年心血付诸东流,但这种意外风险对于职场打拼的涂自强来说实属正常,也不算是灾难性的。对此,小说给予了充分的叙述,小说用涂自强的口吻总结道:“他很明白,除了这个逃掉的学长,这世界并没有谁亏欠于他,这世间的人也并没有谁恶待过他。相反,那些来自无数人们的温暖,就像是许多的手一直在安抚他。而他享受了这种抚摸之后,面对的仍然是阵阵痛感。这世界于自己是哪里不对呢?是哪里拗着了呢?”[2]112涂自强寻找不到也无力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只能暂时处理为“个人悲伤”。尽管,他所看到的是,赵同学并没有经过顽强拼搏就想去美国去美国,想回来就回来,回来就进银行,一个月薪水就超过了涂自强半年。涂自强没有牢骚,没有抱怨,个人的悲伤激发了个人的奋斗意志。但当疾病袭来,没有医疗保障的涂自强再次意识到个人奋斗的限度,身体不是可以用来无限制地消耗的,“个人悲伤”的沉重性显现出来了。
《向上的台阶》中的廖怀宝,尽管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官场中身不由己,但还是具有选择的权利。他在当镇政府文书时,和自己一向爱慕的裴仲公的女儿姁姁发生实质性恋情,即将谈婚论嫁。当镇长戴化章警告他如要在政治上进步,娶一个地主的女儿是不宜的,他就痛苦地选择了抛弃姁姁。当农业合作化的苗头刚刚出现,作为镇长的廖怀宝就率先不顾实际地跟风而行,在“大跃进”中廖怀宝也同样违心地浮夸虚报粮食产量以获得提拔,此时他也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至少可以表现得被动一点。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追究领导责任事件中,他又昧着良知把责任推卸给自己的好朋友兼工作助手双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听从父亲和右派分子沈鉴的计谋,以自己脊梁被打断为由,不仅不出席母亲的葬礼,而且将妻子女儿推到造反派的虎口魔爪中去,灵魂彻底被权力欲望扭曲。尽管世事险恶,但廖怀宝不能说完全没有能力选择承担政治责任和家庭责任。小说为了揭示这一点,特意塑造了双耿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作为廖怀宝的一个镜像存在。双耿对政治权力就没有过分的欲望,他在廖怀宝抛弃姁姁之后接纳了姁姁,并无怨无艾地接受了并不应该由自己承当的政治责任,平静地和姁姁过着虽然身份卑微却拥有道德尊严的生活。双耿所能做到的,廖怀宝完全可以做到。廖怀宝虽然处于晴雨不定的政治氛围中,成为一个标准的政治动物,但总的来说则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即便是峥嵘岁月中的政治人,也会有一定的政治空间。因而,廖怀宝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充满了痛苦和悲伤,这悲伤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选择导致的真正的“个人悲伤”。
《向上的台阶》所讲述的故事,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政治中,大多被叙述为不正常的社会政治戕害了个人的灵魂,个人则常常以被动的受害者的形象在许多文化表述中出现。那时的文化意识形态认为,只有结束不正常的政治体制,大写的人、完全个人化的主体才会出现,才会避免灵魂锈损的悲剧。但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偏偏反其意而写之,他让我们看到在政治化的社会,个人绝不是完全被动无力,政治的变动恰恰为个人提供了变动自我身份的机会,社会流动的空间在不断产生。在如此形势中,个人的品质及其抉择就会成为个人命运的主要因素。《向上的台阶》至少告诉我们,把历史责任完全推给社会政治体制是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廖怀宝的出处进退也启示我们关注个人在历史中的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向上的台阶》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政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所讲述的故事的年代,是一个充分个人化的年代。新时期以来以“解放”“开放”为主导的主体化的文化政治赋予了个体化以合法性,承诺了开放社会的公平公正,也提供了个人奋斗的激情,同时也明确了责任的个体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命运的个体化。而这正是塑造涂自强们成长的意识形态。因而采药在高考落榜之后,只能归咎于个人,写出“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的诗句来。同样,涂自强在频频受挫之后,也只能用命运来解释自我的遭遇,在覆盖性的强调个人奋斗、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文化意识形态中,涂自强只能把耗尽能量却一无所有的悲伤归结为个人悲伤,面对合理得似乎无懈可击的社会体制,涂自强只能“失语”。方方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讲述是逼近真实的,她有意识地采用简练精到、节制情感的笔墨来描述事实、呈现事实,并不去诱导既定的结论。但愈是这样,提问就愈加有力:“果然就只是你的个人悲伤吗?”[2]170很明显,方方的叙述拆解了个人化意识形态的神话,尽管她没有在叙述中给出具体的原因分析,但结果的荒谬是最有力的质疑。当个人的努力达到极限仍然遭遇失败时,体制的不合理性就会呈现,这是任何文化意识形态的伪饰都难以掩盖的。
四、余论:文学如何对现实发言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对于方方的创作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作品。对于当今的文化场域来说,则具有空谷足音般的意义。在目下铺天盖地的流行文化中,正面主导青年思想的文化是励志型文化。以“奋斗”为主题的小说和影视作品风行一时,“我能”的广告成为青年流行语,马云、王石等新世纪创造白手起家神话的“李嘉诚们”成为一代有志青年的偶像。在这样的文化意识形态中,全社会包括青年自身日益将自我的进退成败归结为个人责任,也就是说奋斗中的青年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结构性的、总体性的,而是选择性的、个体性的。但越来越多的个案告诉我们,如此的文化叙述是有问题的,当我们进入具体的社会存在后,会发现青年自由选择、公平竞争、奋斗成功这一神话的虚假性,正如美国社会学者关于中国青年发展问题的调查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很多可选之项。”[5]66涂自强没有也不可能自外于这种文化叙述,他也感染了此种叙述的魅力,他面对自己的学长老板,也曾自信地说:“给我十年时间,我也会成你今天这样。”[2]91但现实很轻易地击碎了他的梦想。
涂自强在这种强大的文化意识形态面前招架无力,有时也痛苦地归因于自己的素质和个人魅力,比如形象气质不好,不体面,不讲卫生,缺少幽默感,缺乏高级生活常识,读书少以及人文素养差,等等。这些确实在今天的励志文化中被叙述为决定成败的细节因素,但在小说的叙述中,涂自强的这些缺点何其无辜。但流行文化不会考虑个体无辜的具体情况,它是均等的叙述,覆盖的却是严重不均等的个体,而不符合这种叙述,便被视为不上进、不道德的个体,这便是流行文化的悖谬之处。这种悖谬,正像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言:“这种无法尽消费者义务的不作为,转变成为被抛弃、被剥夺权利以及被降格、被阻隔或者被驱逐出其他人得以享用的社会盛宴的痛苦。”[6]85-86在此,文学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优长,方方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以不动声色的叙述,瓦解了流行文化建构的神话壁垒,击中了社会体制的痛处,堪称绝大手笔、弥足珍贵。小说叙述了许多涂自强得到帮助的故事,也叙述了涂自强令人感慨不已的努力,正是这种叙述使我们无法把涂自强的溃败归咎于偶然性因素以及个体努力不够,而只能直面社会阶层固化日益加深并且日益合理化这一惨淡的体制现实。文学就是这样在对现实的正面强攻中显示了非凡的力量。
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中的故事,今天看来或许有些司空见惯。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文化氛围中,却是独异不凡、难能可贵的。当时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的文化叙述,其主导形态是强调社会体制的压抑和非合法性,在此基础上解释个人的无辜,个体承担历史责任的不可能性。但周大新却独辟蹊径,捕捉到了看似压抑的社会政治体制在变动中所提供的政治空间,以及这种政治空间所可能推动的社会流动。不仅如此,他还满怀忧患地发现这种政治空间在很多时候恰恰给品质不良的人或者说具有强烈权力欲望又深谙传统阴暗政治文化的人,提供了“向上的台阶”。《向上的台阶》看似讲了一个老套的政治权力在阴暗中摆渡、道德缺失者成为权力掌控者的故事,其实却富有现实批判性或者说文化攻击性。因为当时有太多的人欣喜地认同新时期以来个人在无理性历史中无辜受难的英雄故事,进而掩饰事实上大量存在的自我违背道义的个人抉择;他们愿意重复讲述类似的故事,以摆脱个人的心灵重负和道德瑕疵,进而在历史所开启的新一轮人生竞争中赢得先机。吊诡的是,历史转换太过迅速,周大新所批判的把一切归咎于社会体制进而解脱个人责任的政治文化,很快转换为个人为一切负责的流行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不合理在励志文化的粉饰中被视而不见了,所有的事物连同悲伤都被书写成个人化的了。
作品风靡世界的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如果一部小说未能发现任何迄今未知的有关生存的点滴,它就缺乏道义。认识(或者说发现)是小说的唯一的道义。”[7]4这位迷恋存在的不确定性的小说家试图以极端的措辞来表述他对既有叙述的不信任,他致力于勘探存在的可能性,因而视发现未知为小说家的唯一使命,倡导小说“发现那些只能为小说所发现的东西”[7]4。米兰·昆德拉的话或许有些夸张,但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学却不无启示意义。当流行的文化叙述甚嚣尘上之时,穿越主导的文化意识形态的羁绊,打破合理化的幻象,发现被覆盖的生存真相就成为文学所必须承担的使命。这样的使命要求作家有批判的态度和怀疑的眼光,要求作家有处理自我之外的经验的能力,因为“自我”本身就是主导的文化政治所建构出来的一个幻象。周大新和方方都是当代文坛的成熟作家,也都具有走出狭隘自我主体的自觉意识,因而《向上的台阶》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可以视为他们对于时代的“发现”,也因此表现了文学对现实发言的力量。
[1]周大新.平安世界[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2.
[2]方 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3]李 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4]周仲高,柏 萍.社会贫困趋势与反贫困战略走向[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81-84.
[5][挪威]贺美德,鲁 纳.“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M].许烨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6][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7][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