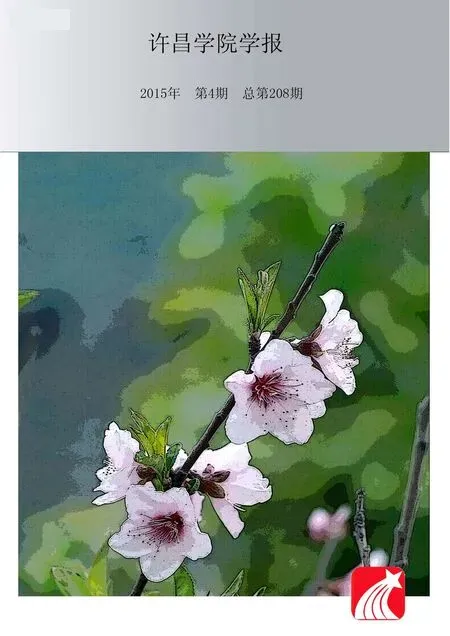徐幹“齐气”新解
——以徐幹与荀学的关系为中心视角
胡 清 清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徐幹“齐气”新解
——以徐幹与荀学的关系为中心视角
胡 清 清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曹丕颇以徐幹之“齐气”为嫌,应是由于徐幹所秉持的一份儒士气导致其在个性气质以及文学创作方面有诸多规范和节制,这和曹丕本人以及时代风气颇不相宜。而在如何搭建“齐气”与“儒士气”的关系问题上,荀学则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荀子为齐国儒生之首,徐幹对其借鉴甚多,故不妨将“齐气”视为“荀子之气”。
齐气;儒家;荀子
“齐气”一词由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批评徐幹之时提出,然而究竟何指,至今仍破费思量。目前学界的研究思路大抵沿着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地域角度出发,学者们往往先指出齐地、齐人有何特征,而徐幹是齐人,故理应也有这些特征。如最早李善在《文选》注中提出“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到后来郭绍虞援引各家之说论证齐风舒缓,再到后来谭家健指出“齐人的气质特点乃是舒缓。徐幹的‘齐气’,看来是指其气质而言”。[1]二是从文字学层面考察“齐”的义指,得出“齐”字的涵义。如志洋的“庄肃之气”,[2]黄晓令的“齐一之气、平平之气、乃至俗气”,[3]124吴孟夏的释“齐”为“中”,认为徐幹个性“通脱不够”,[4]216还有项念东的“齐平之气、端直之气”。[5]55考察徐幹为人为文,可知其与时代风气颇多扞格之处,故而引起曹丕微辞。究其缘由,则当归结于其所秉持的一份儒士之气。然而“儒士气”与“齐气”有何关联?在此一点上,笔者认为“荀学”搭建了两者之间的关联。荀子为战国末期大儒,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实为齐国儒生之首,而徐幹对荀子借鉴甚多,故不妨可将徐幹之“齐气”视为“荀子之气”。
一、徐幹儒学学养及其与荀学的关系
何为儒者?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显然徐幹与儒者的身份定位是十分相符的。作为建安文人集团的成员之一,徐幹较其他成员更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也就是他的这一份儒家君子人格。无论是从个性气质还是从价值追求上来说,徐幹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故后世亦多视之以醇儒形象,如北宋曾巩在《中论序》中说:“幹独能考六艺,推仲尼、孟轲之旨,述而论之。”又如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也称:“盖是时惟伟长著书,无忝儒者本色。”而最能体现徐幹学术思想的即《中论》一书,历代著录除《宋史》卷二百五《艺文志》列为杂家外均将其列入儒家。[6]400-403《中论》一书作为徐幹的寄意之作,我们可从中探究其儒家学养。
孔子殁后,儒家以孟、荀为最醇,[7]15而孟荀的很多思路并不一样,他们分别继承孔子思想而又有所发展。徐幹儒家学养的主要来源就是孔孟荀先秦儒家思想,而尤其对于荀子,徐幹的借鉴和吸收颇多。这一点,徐湘霖在《中论校注》一书中已有指出。以下从具体的思想主张出发探讨徐幹儒学学养与荀学的关系。
(一)关于社会秩序的建立
社会秩序问题是一个国家最根本也是儒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关于建立社会秩序,儒家向来主张“礼治”。而在此基础上,孔子找到了“仁”这一心理本原,来作为实现“克己复礼”的途径。孟子则进一步继承孔子的精神,提出了“性善说”和“仁政”。孔孟的思路大体一致,即建立社会秩序不是依靠外在的法律约束而是依靠人内在的道德自律意识和外在的礼仪象征形式维持。[8]151然而荀子的思路却与此不同。相比孔孟的理想主义,荀子对现实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他倡言性恶,虽一方面重视礼乐的垂戒示警意义和理性的道德调节,然另一方面也重视现世治理中的实用功利。[8]152故荀子提出“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的政治见解,形成兼涉“内圣”、侧重“外王”的治世理论。[9]5《王制》篇说:“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渐赏庆以先之,严刑罚以防之”。“刑”和“赏”是法家思想里两个重要的范畴,由此可以看出荀子的思路不再仅仅是儒者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儒者执着于理想而不切实用,但荀子的思路中蕴涵了十分实用的,既可以用之于道德自律,又可以推之于法律管束的意识形态意味。[8]154显然,徐幹关于建立社会秩序的理论深受荀学思想影响。作为儒者,徐幹既强调修养一己之道德,又十分称善礼乐的教化作用。然而徐幹也深刻认识到外在刑罚存在的必要,《赏罚》篇言“天生烝民,其性一也。刻肌亏体,所同恶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 徐幹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而这也就道明了赏罚得以实行的依据。故他在此一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政治大纲有二,二者何也。赏罚之谓也。人君明乎赏罚之道,则治不难矣。”又在《遣交》篇称“昔圣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职,纠之以八刑,导之以五礼,训之以六乐,敎之以三物,习之以六容”。由此可以看出徐幹的治国治民之方承继荀子“礼法并用”的思想。
(二)对于人性的判断
对于人性的基本估计,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孟子所持的“性善说”,另一种则是荀子倡言的“性恶说”,荀子在《性恶》一篇,开头就给予说明——“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有疾恶、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如果顺从之,则会导致争夺、乱理乃至归于暴的结果。因此荀子一方面特别强调教育和学习,依靠后天的熏染、修养来使人们养成遵守规则、服从秩序的习惯,[8]153另一方面则特别注意“礼”对人的规范和节制。通观《中论》一书,徐幹在人性问题上并未作出明确判断,然而基于对人性的看法而引申的主张,徐幹则大多沿着荀子的思路。在《治学》篇中,徐幹指出“民之初载,其蒙未知”,但他对人性当中的“瑕疵”与“恶”却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在《修本》篇中,徐幹说“夫珠之含砾,瑾之挟瑕,斯其性与?良工为之以纯其性,若夫素然。故观二物之旣纯,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徐幹认为珠玉之性是有瑕疵的,然良工可以纯其性,人之性也是有瑕疵的,而通过修身则可以使仁德纯粹。在《虚道》篇中他又说“夫恶犹疾也,攻之则益悛,不攻则日甚。故君子之兴善也,将以攻恶也。恶不废则善不兴,自然之道也”。徐幹认为人性当中的善与恶起着阴长阳消的变化,所以他也十分注重后天的学习和修养,认为君子之所以能够成德立行,都是“学”的缘故。[10]1与此同时,和荀子一样,徐幹也特别注重“礼”对人的规范和节制。这一点将在下文详加分析。
(三)对待“礼”的态度
荀子对于“礼”是十分重视的,荀子之学可谓就是“隆礼”之学。他在《修身》篇中说“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小到言语举动,大到治国安邦,作为言行道德规范的最高标准乃至修身治国的根本,“礼”在荀子的思想中几乎无处不在。而徐幹对于“礼”的重视也并不亚于荀子。在《法象》篇中,徐幹说:“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轨,折旋中矩;视不离乎结绘之间,言不越乎表着之位;声气可范,精神可爱,俯仰可宗,揖让可贵,述作有方,动静有常,帅礼不荒,故为万夫之望也。”由此可知,徐幹亦将“礼”视为言行动作之则,时刻不敢媟慢。又说“夫礼也者,人之急也,可终身蹈,而不可须臾离也。须臾离则慆慢之行臻焉,须臾忘则慆慢之心生焉,况无礼而可以终始乎!”这和《论语·里仁》篇所说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以及《中庸》里说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者也”的句式相同,然而不可须臾离的对象却由“仁”、“道”换成了“礼”,可见徐幹的思想中对于“礼”的重视是和荀子一致的。
(四)对待“名”的态度
“名”的实际内涵其实是一套语言系统,现象世界无一不是由语言指称的,[8]183所以“名”有着指称世界的意义。荀子说“名定而实辨”,[11]414也就是说名称一旦确定,那么实际事物就能分辨了。然而一旦名称的管理松懈,名与实的指称发生混乱,就会导致民众产生疑惑,而社会秩序也会因此混乱。所以荀子非常痛恨乱名的行为,在《正名》篇中,他指出乱名的罪行:“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在对待“辩说”这一问题的态度上荀子向来是谨慎的,然而当“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的时候,辩说也就成了必要,所谓“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徐幹在“辩说”和“乱名”的问题上承袭了荀子的态度。在《核辩》篇中,徐幹批判了只为“屈人之口”的辩说,指明辩的意义在于“为言别”,即“为其善分别事类而明处之也”。这便与荀子弄清名物事理的正名思想相一致。而对于“乱名”的行为,徐幹的态度更是毫不留情,在《核辩》一篇中他明言“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乱名改作者,杀之;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者,亦杀之”。
此外,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徐幹也承继了荀学一路的思想。如对于“学”的强调,对于“智”、“权衡”的看重以及对于尚贤使能的重视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徐幹的儒家学养与荀学一路的关系。
二、徐幹儒学学养对其文风的渗透与影响
把儒家君子人格作为理想与追求的徐干对于儒家思想是不遗余力去奉行的,故其儒家学养必也渗透影响到其文学创作。鉴于此,孙宝先生在《徐幹儒学文艺观与创作关系述论》一文中,根据徐幹在《中论》一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文艺思想,提炼归纳出了他的儒学文艺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注重个人创造的艺德观;其次,以言为贵、言为徳藻的重言观;再次,以立志为先、博达中正的才学观。可以看到因受其所秉持的儒家学养的影响,徐幹虽也重视“艺”、“言”、“才”,但对待它们的态度却始终以儒学价值观念为指导。在《艺纪》一篇中,徐幹指出“艺者所以旌智、饰能、统事、御群也”,“艺者以事成德者也”,徳是人的根干,而艺则是徳的枝叶,习艺是为了成德。这就赋予了“艺”以儒家所强调的价值功能,与孔子在评价《诗》时所提出的“兴观群怨”说是一致的。此外,《艺纪》篇又说:“故恭恪廉让,艺之情也;中和平直,艺之实也;齐敏不匮,艺之华也;威仪孔时,艺之饰也。”这些都是出于儒家思想而对“艺”所作的限定,与“温柔敦厚”的诗教也是相一致的。对于“言”,徐幹也十分谨慎,《法象》篇称“君子口无戏谑之言,言必有防”、“虽妻妾不可得而黩也,虽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核辩》篇又指出“苟美其声气、繁其辞令,如激风之至,如暴雨之集”的论辩只是屈人口舌而已。徐幹的才学观,亦是突出以儒学为核心的知识论和价值论。总之,徐幹的文艺观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学识为基础,以儒学价值观构建的德性为旨归,[12]115倘若与儒家价值无涉,徐幹的态度就会是像无名氏在《中论序》所说的“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了。
徐幹的儒学文艺思想是从《中论》一书中提炼出的,因而也在《中论》的创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当然这种影响也会扩展至其诗赋创作。下面就分别从这两个方面阐述徐幹儒学文艺观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
首先,《中论》一书在文风上体现出宗摹荀子的特色。《中论》一书承继《孟子》、《荀子》的子书撰制传统,[12]115而无论是在篇目安排、遣词造句以及辞采意气方面,《中论》都对《荀子》借鉴颇多。首先在篇目安排上,《荀子》和《中论》都以修身为要,而《中论》开篇便言《治学》,显然承自《荀子·劝学》。在用词方面,《中论》中的很多名物语词都来自《荀子》,如《法象》篇的“行必由检”的“检”字作为“法式、法度”的意义就来自于《荀子·儒效》篇“礼者,人主之所以为人臣寸、尺、寻、丈检式也”的“检”字;又如《修本》篇中的“虑人而不自虑者谓之瞀”的“瞀”字也是来自于《荀子·非十二子》一篇中的“瞀儒”一词。故孙启治在给《中论》作注解之时,就经常引用杨倞给《荀子》作的注。在句法方面,直接引用《荀子》的例子有《考伪》篇的“盗名不如盗货”、《贵言》篇的“礼恭,然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然后可与言道之理”。而如《艺纪》篇“故宝玉之山土木必润”一句则化用了《荀子·劝学》篇中的“玉在山而草木润”;《爵禄》篇中的“夫登高而建旌,则其所视者广矣;顺风而振铎,则其所闻者远矣。非旌色之益明,非铎声之益远也,所托者然也”一句化用了《荀子·劝学》篇中的“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等句。在辞采意气方面,《中论》一书颇有荀子之气,近人徐仁甫在《读<中论>札 》一书中就直接指出:“伟长法荀卿为文,缛而不繁,徐而不迫,雍容静穆,蔼然儒者之度。盖入而能出者,故虽有模拟,不可得而寻其迹,斯善撷属文采者矣。”[13]327
其次,在诗赋创作方面,因受儒学文艺观的影响,徐幹在内容、情感以及文采辞藻方面都有所节制。在创作内容上,与建安七子其他成员相比,徐幹较少游宴、奉命之作。偶尔有如《车渠碗赋》这样的同题奉命之作,徐幹亦是寥寥数语作结,不作夸饰奉承之语,显示了其一份不同流俗的儒家君子人格。在情感表达上,徐幹因受到“礼”的节制而不够激越,始终以“中和”为持守,保持着一份儒者应有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气度,此点对比徐幹与刘祯的赠答诗即可体察。刘祯为人慷慨任气,在《赠徐幹》一诗中将自己对“拘禁”甚严的不满以及对友人的思念之情都充分地表达出来。相较之下,徐幹在《答刘祯诗》中虽也说“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然其诗风高简浑朴,情感亦较含蓄收敛。在文采辞藻方面,徐幹主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并不喜辞人美丽之文,因而他的的作品大多语词质实。钟嵘在《诗品》中评徐幹曰:“伟长与公干往复,虽曰以莛扣钟,亦能间雅矣。”钟嵘在文学批评上比较注重情采,“以莛扣钟”大略即指情感表达与辞采方面而言。
三、曹丕“齐气”论与建安、黄初文气转换
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十分重视文学的政教功能,因而有诸多束缚,然至建安、黄初时期则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这首先得益于儒学的衰弱。汉末的乱世对于抱守儒家治世理想的文人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儒学价值体系的崩颓,使他们失去了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人生信仰也随之坍塌,所以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精神依托。而就是在这样的当口,人们的眼光开始转向自身的人生价值,这种转向开拓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是而人的觉醒以及文学的自觉也就成为了历史必然。鲁迅认为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儒家思想对文人头脑的束缚松弛了,文学不再仅仅只是政教的工具和附庸。随着文章日益为人所重视,它本身的审美作用也得到了充分肯定。对于作者来说,它不再需要弘扬大义,也可以仅仅作为一种宣泄情志、自我娱乐的方式。而在情感与辞采方面,也大大摆脱了先前儒家思想的限制。建安时代的作者,由于感念世乱,渴望建功立业,故其作品激情回荡,大多慷慨任气,劲健有力。[14]32总的来说,他们都是以情感激荡、文辞华丽为美的。这一时代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三曹和七子在文学领域大放异彩,并且形成了“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时代风貌。至此中国文学又掀开新的一页,如大幕开启,引人注目的是台上人物的歌哭笑骂,或裂眦长啸,或风情万种,性情挥洒,淋漓尽致,使人看到了浓烈的情感。[15]126
作为曹魏政权的统治者,曹丕当然是引领时代风气的一个关键人物。时风的转换除却儒道中衰的原因,也得力于统治者的提倡。《晋书·傅玄传》中,傅玄上疏称:“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曹丕确实是一个文士气颇重且慕通达的人,他的生活作风及人生态度偏向于随意、自然,甚至是有意识对抗和破坏儒家礼法制度。[16]188和谨言慎行、丝毫不敢违背礼制的徐幹相比,曹丕以言语为笑乐、在丧礼之上学驴鸣、在曹操死后丧不废乐等,都是纵情任性的表现。陈寅恪先生曾将曹氏的社会阶级归于非儒家寒族。[17]1可见在曹丕的思想中,儒家的成分并不是很多,自然他的文学理念也不会在儒家的规范之下。在《典论·论文》一篇中,曹丕对于文学对个人人生的价值有着明确的认识,认为文章“乃不朽之盛事”。在辞采方面,他也明确提出“诗赋欲丽”的主张。
徐幹身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并不以文学自称,然曹丕是将其作为文人加以评价的。他的文气说,以“气”论人,当说某作家具有某种气时,虽是指其作品而言,但也兼指作家本人的气质,总的说来,“气”应该就是指评论对象总的风貌给人的一种总的印象与感受。[14]30曹丕说徐幹“时有齐气”,即是如此。徐幹因受儒家道德价值规范,在为人为文方面诸多限制。清初陈祚明曾评价徐幹的拟古诗“伟长诗,别能造语,匠意转掉,若不欲以声韵经心,故奇劲之气高迥越众,如广坐少年中,一老踞席兀傲不言,时或勃然吐词,可以惊骇四筵矣。”[18]699此语虽是对其拟古诗的褒奖,从中也可想见徐幹平日持中沉潜的儒士风范。而这对于意气风发的时代以及随意通脱的曹丕来说却是颇不相宜的,因而他对徐幹颇有微辞也就可想而知了。
[1] 谭家健.试谈曹丕的典论·论文[J].新建设,1964(2):93-103.
[2] 志洋.释“齐气”[N].光明日报,1960-11-20.
[3] 黄晓令.典论·论文中的“齐气“一解[J].文学评论,1982(6):123-124.
[4] 吴孟夏.曹丕“文气“说浅析[A].建安文学研究文集[C].合肥:黄山书社,1984.
[5] 项念东.典论·论文“齐气”研究略评[A].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1辑[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 孙启治.中论解诂附录二目录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4.
[7] 钱大昕.跋荀子,转引自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8]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9] 房登科.礼法同行天下——治荀子礼法思想研究[D].扬州大学,2004.
[10]孙启治. 治学第一[M].中论解诂.北京:中华书局,2014.
[11]王先谦.荀子集解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2]孙宝.儒学嬗变与魏晋文风建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13]徐湘霖.中论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0.
[14]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二·魏晋南北朝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5]汪春泓.“徐幹时有齐气”新解[A].中国诗学第五辑[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6]王永平、胡学春.魏文帝曹丕之“慕通达”及其原因与影响考论[J].求索,2005(11):188-192.
[17]万绳楠整理.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0.
[18]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59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石长平
2014-12-25
胡清清(1990—),女,浙江金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I206
A
1671-9824(2015)04-005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