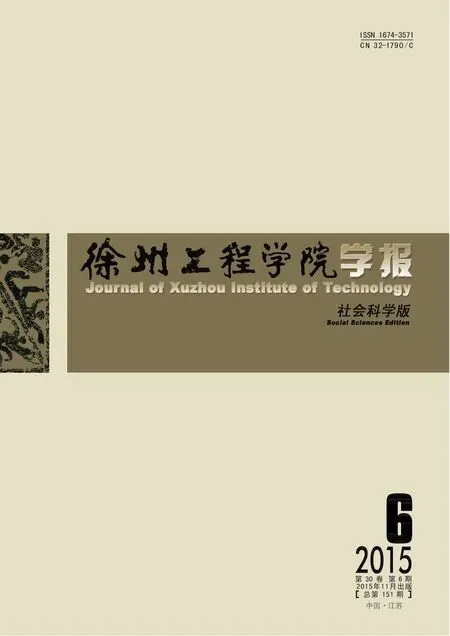论《远东来信》的艺术特点
张卫中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论《远东来信》的艺术特点
张卫中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221116)
摘要:《远东来信》是一部反映二战时期在华犹太人生活的小说,但它并不是一部仅仅以题材取胜的作品,事实上,小说更成功的还是它的艺术形式。小说中谢东泓对雷奥故事的调查被作为主要线索写进小说,这种安排增加了小说的纪实成分,创造了近似实录的效果;小说双线交替的结构使作者能够更灵活地观照生活,避免了由对生活“正面强攻”带来的繁琐与生硬;小说丰富的民间叙事提供了真实的乡村生活,也给“雷奥在中国农村”的故事提供了真实的背景。
关键词:《远东来信》;纪实与虚构;艺术结构;民间叙事
《远东来信》作为一部以二战为背景、反映在纳粹排犹浪潮中流落中国上海犹太人命运的小说,出版以后首先引起关注的自然是它的题材;引发读者联想的应当是《辛德勒的名单》《拉贝日记》和《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一类的作品。小说中的犹太儿童雷奥一家在希特勒上台后受到纳粹的迫害,其后雷奥随母亲流落上海,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迫害,他又避难到了河南上蔡,这个题材本身对中国读者就足够有趣和新鲜。然而文学史上很少作品能仅凭题材就获得很大的成功,一部作品重要的不在于它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更何况《远东来信》所讲述的看上去只是许多中国人出于同情和正义感,挺身而出保护德国儿童的故事,但是因为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人与西方人在生活水平和习惯上的悬殊,要讲好“雷奥在中国”的故事、特别是“雷奥在中国农村”的故事其实有着很大难度。换言之,没有艺术上的深入思考和探索,这部小说就很难获得较大的成功。
为了讲好“雷奥在中国”的故事,作者在艺术上着力甚多;小说在艺术上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这样三个方面。
一、在纪实与虚构之间的选择
像《远东来信》这类以二战为背景的小说在题材上大都应当归于历史小说,作家的写作也面临着一个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想象虚构关系的问题。《辛德勒的名单》的作者托马斯·基尼利就非亲身经受纳粹的迫害,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在辛德勒帮助下幸免于难的波兰籍犹太人列奥波·比兹夫妇的委托和启发创作了这部小说。为了尊重历史真实,托马斯·基尼利在列奥波·比兹的陪伴下,做了大量调查走访工作:他对分布在澳大利亚、以色列、德国、奥地利、美国、阿根廷和巴西的五十位“辛德勒幸存者”做了采访;实地考察了作为小说背景城市的克拉科夫、普拉绍夫和阿蒙·格特劳役营和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搜集了由辛德勒救助的犹太人提供的大量证词,以及有关辛德勒的文件和信件等。在谈到如何处理“纪实”与“虚构”的关系时,托马斯·基尼利谈到:“用小说的结构和手法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现代作品中屡见不鲜。”他说自己在创作中“有时有必要在奥斯卡和其他当事人只留下最简略记录的基础上合理地虚构少许的对话内容”,但是他更关注的却是如何保证小说忠实于历史真实。他说:“我一直力避一切向壁虚构,因为任何虚构都会贬损我的记录。”他说自己的小说“大部分的对话内容,所有的事实,均基于由辛德勒犹太人、辛德勒本人以及其他亲眼见证奥斯卡那非凡拯救行动的人士提供的详尽回忆之上”[1]10-11。中国作家张雅文写作《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前也曾数次自费去布鲁塞尔采访,搜集了许多第一手的材料,在创作中她也是尽量尊重历史真实,《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因而被称为“纪实体长篇小说”[2]。
《远东来信》的作者张新科在创作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1996年,一次偶然机会,他在一家德文报纸上读到了二战期间30 000犹太人避难上海、曾得到中国人无私救助的报道,从此立意写一部反映二战时期犹太人在中国生活的小说。然而作者反映犹太人在二战时期的遭遇与澳洲作家托马斯·基尼利虽然有很多相似,但他们面临的问题却有很大差异。因为托马斯·基尼利不是泛写犹太人的命运,他写的是辛德勒拯救1 200名犹太人的故事,他的一个最有利的条件是,辛德勒实有其人,有关他的真实材料也大量存在,这样作者就比较容易处理历史真实与想象虚构的关系,对人物、故事的处理也比较容易。中国作家张雅文创作《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面临的情况与《辛德勒的名单》也很相似,即它有一个真实的人物可以作为摹本,这样作者对基本事件不需要虚构,可以基本依靠相关史料;作者要做的只是对一些细节和场景做一些补充。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张新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首先,“由于时间久远,大量历史资料遗失等都对还原事件真相造成了困难”[3],就是说,作者不可能仅仅根据已有的材料写一部二战期间30 000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史,他必须以点代面通过重点讲述少数犹太人的故事,反映整个在华犹太人生活的情况。而另一方面,现有史料中又缺少在华犹太人典型的材料,找不到一个或几个典型人物,找不到相关的日记、书信等,这样作者必须虚构主要人物和他的生活,就是说,一方面作者选择的题材带有历史小说的特点,需要创造历史小说特有的真实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没有真实人物和人物真实的故事作为支撑;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写作的难度。
当然,作者即便面临这种特殊困难,他也并没有放弃对历史真实的追求,相反,他在搜集材料方面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力求通过多方搜集犹太人在中国生活的材料,弥补由于缺少真实人物作为摹本带来的不足。自1996年作者萌生创作的念头,他用了十六七年的时间“搜集整理德语、英语、汉语对这一事件的档案、报道、采访、画册等材料,并先后自费投入50多万元,遍访欧亚各国”[4]。访问了德国、法国、波兰、捷克等有关国家,探访纳粹集中营。同时认真考察犹太人在上海的旧居、教堂、经营的店铺等,力求让小说的虚构、想象更多地以史实为基础。
在《远东来信》中,作者自萌发创作念头就一直追求的尊重历史真实的努力在小说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也成为了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这种追求在小说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远东来信》不是像《辛德勒的名单》和《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小说中直接讲述二战期间历史人物的故事,而是分出了调查犹太人的生活与讲述犹太人的故事两个部分。小说的一条线索是德国留学生谢东泓在跳蚤市场淘得雷奥寄给音乐老师索菲亚·施密特女士的8封信,其后谢东泓用了多年时间考证8封信的内容;另一条线索就是8封信展示的内容:犹太儿童雷奥和其母亲在上海的生活,以及雷奥离开母亲在河南上蔡的生活。在《远东来信》全部的16章中,谢东泓对8封信调查、考证就占了8章,就是说,这个部分占了整个小说近一半的篇幅。虽然严格地说,留德学生谢东泓以及他对雷奥母子在华生活的调查、考证也是一种虚构,但是从各种相关材料看,这个过程与作者自己的经历高度相似,小说的这一部分就明显带上了纪实的特点。这样小说的两条线就有一个明显的区分:谢东泓对8封信的调查带有较多纪实成分,而对雷奥母子命运的讲述则更多地是一些虚构。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猜测,作者在创作中未曾直接讲述雷奥的故事,而是设置了“调查”与讲述“调查”结果两个部分,目的就是要增加小说的真实感,通过“事件调查”这种带有纪实特点的讲述,创造一种“纪实”与“实录”的阅读效果,以弥补小说没有现实“摹本”的不足。文学史上采取这种以调查写故事、或者将调查与故事兼容的小说最典型的就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这部小说的每一集都是由福尔摩斯和他的助手华生医生对案件的调查与他们调查的案件两部分组成——但是《福尔摩斯探案集》是侦探小说,而《远东来信》是历史小说,前者使用这种套叠式结构主要是为了制造悬念,而后者则是要在小说中融入更多纪实与实录成分,创造接近历史真实的阅读效果。
其次,小说融入一些调查、考证的内容,力求创造某种纪实的效果。小说第五章讲述谢东泓专程从汉堡回到上海考察三四十年代犹太人在上海的居住区,作者写到在老华德路上的摩西会堂、写到舟山路上几位后来成为名人的犹太人的住处: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长的布鲁门撒尔13岁时居住的房子、以色列原驻美国联合国大使Y·特科阿住过的房子,以及美国亚美公司总经理约瑟夫·甘结和美国耶希大学校长戴维·柴斯曼等当年住过的地方。小说第七章有谢东泓到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参观的记述,这些描写都相当严谨、朴素,以说明、介绍为主,有类似纪实散文的特点。
小说中甚至还有一些类似专业考证方面的文字。谢东泓对雷奥8封信的解读很多都用了考证的方式,对雷奥在河南上蔡生活的那个村庄也是通过考证确定其现在的名字。小说第一章写到谢东泓拿到雷奥的信以后为了确定8封信的书写者,他认真考察了这封信发信的地址、时间、信封的格式、信封上地址、人名的书写方式、写信人的笔记等,叙事方式相当严谨。
二、双线交替的结构
《远东来信》在艺术上最显见的特点是它使用了一种双线交替的结构,而且这种结构有着复杂的构成,作者正是借助于这种结构成功讲述了二战期间在华犹太人的故事,也凸显了中国人拥有仁慈、大爱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主题。小说中谢东泓通过8封信对雷奥一家的调查和小说对雷奥故事的讲述构成了平行发展的两条线索,但作者又不是简单地列出两条线,两条线之间包含了一系列差异:在时间上谢东泓的调查是“现在时”,雷奥的故事是“过去时”;在空间上,谢东泓的调查主要在德国汉堡和中国上海这些城市展开,而雷奥一家的生活则涉及德国汉堡、中国上海、河南上蔡,雷奥在中国的生活更多地是在河南上蔡的一个叫别津的小村庄。因而小说中两个线索的交替也意味着时间和空间的交替与转换,小说正是用这种交替与转换打破了线性叙事的冗长与沉闷,显示出变化与多样。
小说中两条线索涉及的时间显然经过作者的精心安排:谢东泓的 “现在时”与雷奥的“过去时”由开始的分离、交替出现、平行发展,到结尾实现了完美的叠合。小说的起点是谢东泓在跳蚤市场淘得了雷奥写给音乐教师索菲亚·施密特的8封信,得到这8封信后,他开始仔细研究每一封信的内容,考察它写作的时间、背景,然后通过虚构、想象建构了一个完整的雷奥故事。雷奥8封信的内容是按自然时序展开,而雷奥的故事也是依照自然顺序展开,这样谢东泓的时间与雷奥的时间就形成了一种平行。这两个时间段在开始是谢东泓的时间快于雷奥的时间:谢东泓的调查只有几年时间,而雷奥的故事从1936年开始到1945年,经历了近10年时间。然而1945年以后,雷奥失联,雷奥这条线出现了一个叙事时间的“停滞”,而谢东泓的调查仍在继续,这样谢东泓的“现在时”很快就“赶上”了雷奥的“过去时”。在“尾声”部分,谢东泓见到了从美国回到上蔡的雷奥,于是“过去时”与“现在时”叠加,实现了两条线索的汇合。
《远东来信》这种双线交替的结构是作者在艺术上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对小说的艺术效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
1.它让作者的创作能够扬长避短,在反映生活时拥有更多的主动权。
《远东来信》所写主要是犹太裔德国儿童雷奥和其一家在二战期间的遭遇,而就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积累来说,这个内容如果要做平铺直叙地描写具有相当大的难度。首先,就雷奥一家在德国的这一段生活经历来说,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文化、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作者虽然有在德国留学的经历,但是这点时间对深入了解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远远不够,更何况作者所写不是现代的德国,而是纳粹肆虐时代的德国,作者与所写生活之间既有民族文化上的膈膜,又有历史的膈膜。其次,就雷奥在中国的这一段生活来说,虽然作者对中国城市、乡村的生活都比较熟悉,但是小说所写却是一段很特殊的生活。主人公雷奥来自德国大城市汉堡,而雷奥在中国生活过的上蔡却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同时雷奥经历了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特大饥荒,经历了一段最贫困的岁月,这样雷奥在生活上就必须有一个艰难的适应与转换。除此而外,雷奥还面临着从语言到文化的一系列更困难的转变。雷奥1941年到上蔡,1945年日本投降时离开,在上蔡只有4年多一点的时间,而这段时间雷奥要从基本不会汉语,到最后能说河南方言,能用农民的方式思维,最终融入农民中,这中间的变化也是很难把握。
鉴于作者生活积累与小说素材之间较大的差距,作者很明智地选取了双线交替的结构,使用这种结构最大的益处是能够做到扬长避短。所谓“扬长”是指作者作为一个德国留学生对谢东泓的生活非常熟悉,作者对“调查”这个线索的讲述游刃有余。小说中谢东泓的精明、算计与开朗、热情都写得有声有色,谢东泓无疑是小说中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围绕谢东泓的叙事也是小说中最成功的叙事。所谓“避短”,是指小说在使用了双线交替的结构以后,作者对不熟悉的生活可以有所选择,例如,对雷奥一家在德国受纳粹的迫害主要写了一个“水晶之夜”,并未展开;对雷奥在上蔡的生活也是有所选择,小说重点写的是几个转变。主要是雷奥在物质生活上由不适应到勉强适应;与中国农民的关系,在经历了几个事件以后,由陌生、好奇,转变为同情、亲近,并产生了感恩心理。使用双线交替这种结构以后,作者对不太熟悉的题材可以避免做“正面强攻”,他更多地使用了以点带面的方式,也较多地使用了“侧写”,这样就获得了比较好的艺术效果。
2.小说的两条线索相辅相成共同凸显了中国人民勇于牺牲,拥有大仁、大爱的主题。
小说中“雷奥的故事”直接表现了犹太人在中国受到的呵护与关照,对表现小说主题至关重要,但是谢东泓这条线索对表现主题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作者本人对在华犹太人的调查与谢东泓的调查有很多相似之处,作者很大程度上可以把自己写作这个故事的缘起、动机,包括故事的主题都在谢东泓这条线索中间接地予以说明。与作者本人的情况类似,谢东泓调查和写作雷奥的故事也有一个特殊动机,就是反驳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用二战期间中国人对犹太人宽容与呵护表现中国人拥有大仁、大爱的主题。小说第一章,谢东泓在拿到了8封信以后,他的思想有一个转变过程。开始他是打算将这些具有史料价值的信件卖给汉堡汉学研究所或中国上海的档案馆,但是信的内容触动了他,他最终决定把这些信翻译、整理好,“让信中的故事告诉美国人,告诉英国人,告诉犹太人,告诉德国人,告诉日本人……中国人也和其他民族一样,不但在乎自己,也在乎别人”。说到他产生这个意念的原因,谢东泓更具体地提到,他在汉堡读书期间,各国留学生常常一起谈论二战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很多留学生根本不知道中国人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一位来自非洲的学生问谢东泓:“你们中国人当年也反侵略、反纳粹吗?”一个英国同学的提问更具有挑战性,他说“谢,你们中国人二战期间是不是只顾打‘内战’,根本不关心国际上的事?”最让谢东泓受不了的是“英国同学的这句话在欧洲是很普遍的一种观点,在他们眼里,中国人喜欢‘窝里斗’”,认为“‘东方睡狮’是缺乏人性关爱的‘冷血动物’”。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谢东泓在得知二战时有30 000犹太人在中国上海得到保护,特别是看到雷奥的8封信以后,产生了强烈的冲动,他要充分利用手中的材料,证实中国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证实中国人是一个讲仁义,有大仁、大爱,有牺牲精神的民族,还中国人一个清白。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小说中谢东泓写作雷奥故事的缘起、动机与作家本人写作这部小说的缘起、动机高度类似。事实上,作者张新科有过与谢东泓类似的经历,在现实中遇到过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即一些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贡献,他们认为中国人自私、冷漠,只关心自己,是一个冷血的民族。而作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也就是要纠正外国人的偏见,还原历史真相。作者在访谈中曾明确说过:“写这本书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二战期间,中国人民在自己遭受日本侵略者迫害和屠杀的时候,还在无私地庇护着大批的犹太难民。”[3]在小说中作者很大程度上是借谢东泓之口明确指出了小说的主题。
其次,雷奥的故事讲述的大都是人物在历史事件中具体的经历、遭遇,而事件大的背景、过程主要都是在谢东泓的这条线索中被说明的。作者在说明中还使用了一些真实的历史资料;小说在雷奥的故事之外另开一条线有利于容纳相关史料,更清楚地交待主要事件的背景。例如小说中雷奥的故事讲述了1942年雷奥居住的小村庄别津遭受旱灾的情况,但是读者对当时河南整体的情况并不太了解。而在小说第十一章,作者引用美国著名新闻时政期刊《时代》派驻中国的记者白修德《十万火急大逃亡》中的报道说明这场饥荒的范围、原因和严重程度。白修德的报告指出:“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上千万人面临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为:1.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2.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5]小说中谢东泓这条线索给“雷奥的故事”提供了大的背景,给这个故事提供了必要的补充。
三、丰富的民间叙事
在《远东来信》中作者面临最大的困难是真实叙述“雷奥在上蔡”的故事。小说写雷奥初到上蔡的别津村时,且不说雷奥如何适应当地的生活,仅仅是村民把雷奥看作一个“人”,而不是什么怪物,就遇到了很大问题。别津村偏僻、落后,村子里所有的人都从未见过任何外国人,因而乍见雷奥,连其后要承担抚养任务、日后要被雷奥称为“大”和“娘”的潘进堂和喜鹊夫妇都以为自己见到了“鬼”。在王家甫把雷奥背到潘进堂家的当天晚上,潘进堂这个带着戏班子曾经走南闯北、全村最有见识的人也大为惊讶,他拿着煤油灯“从头到尾打量这个怪物,以为见到的是个‘鬼’”,听过王家甫的解释后还是“满心蹊跷”。在语言上雷奥几乎完全听不懂汉语。在生活上原来可以吃黄油面包,到了别津,即便受到照顾,他也只能吃杂有粗粮的面食,到后来只能喝红薯干做的汤。就连上厕所雷奥也面临很大困难,在德国他用的是陶瓷马桶,在上海用的是木制马桶,而在别津只能上“屎茅子”:在一个粪坑上排列的两块木板。以至于雷奥第一次独立地上“屎茅子”就掉进了粪坑;擦屁股则只能用砖头。让这样一个孩子在4年的时间,学会中国话,能说河南方言,适应中国极端恶劣的物质生活环境,最终融入中国农村的生活环境,对作者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处理不好,这个故事就会显得生硬、虚假,让读者难以信服。
为了克服这个障碍,作者在艺术上最重要的选择就是使用了丰富的民间叙事,《远东来信》中的民间叙事既为“雷奥在中国农村”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背景,同时作者通过书写民间人物、场景和故事也使小说具有了更丰富的内容,舒缓了由单一描写雷奥与环境冲突造成的简单与生硬。
所谓民间叙事是指源自“生活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的叙事活动”[6],即按照民间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语言方式反映民间的人物、场景和故事的叙事活动,民间叙事更多地体现民间的趣味与理想,也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雷奥在中国农村”的故事中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活跃在小说中的众多民间人物,即按照民间认知方式和趣味塑造的、带有鲜明民间特点的人物,在小说中潘进堂、喜鹊、八仙、剃头匠老纪、开染坊的王拐子,以及具有传奇经历的伪县长孙宝康、土匪陈杆子都是这类人物。在小说中,即便那些着墨不多的次要人物,因为作者按照民间逻辑书写,也都写得生动有趣。小说中的老纪是个剃头匠,六十多岁,与八仙是“老伙计”。老纪一开始出场就与雷奥有关系。雷奥初到别津,被隐瞒了身世,他的真实身份只有潘进堂、喜鹊和八仙知道,为了不惹出麻烦,潘进堂、八仙虚构了一个故事:八仙外出算命,在商丘火车站捡到了来自上海的流浪娃雷奥(到别津后易名雷娃),潘进堂和喜鹊无儿无女,八仙就把雷奥送给他们做养子;同时潘进堂的戏班子演《狸猫换太子》一直缺一个狸猫,雷奥不用化妆也正好能演狸猫。雷奥安顿下来以后,村民中第一个见到雷奥的就是老纪。老纪被喊来给雷奥剃头,他第一眼见到雷奥就充满了诧异,雷奥卷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和高鼻深目都让老纪深信雷奥不是汉人,他在给雷奥剃头时忍不住提出一个疑问:“这头不是汉人的头!”随后八仙和老纪有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对话。八仙首先解释了雷奥的头发为什么特别软和卷曲。他说“南蛮子生活在南方,南方日头毒温度高,温度一高这头发就软”,头发一软就卷曲起来。其次就皮肤的白,他说:“娃的家在上海,上海上海肯定靠海,海边空气里盐多,一点一点沉积到脸上,这么一腌,谁的脸皮不白?”经过这样一说,老纪有点相信了。随后,八仙再要解释雷奥为什么高鼻深目时,老纪为了逞能自己就抢着做了发挥,他说:“娃的家在上海,上海上海肯定靠海,海边风大,大风成天在鼻孔里和眼窝里盘旋,慢慢不就把鼻梁掀起来了,把眼球给吹进去了?”说完以后,他还洋洋得意起来,为自己的聪明深感自豪。
后来有一次在安息日雷奥做犹太教的祷告被老纪看到,老纪立刻认为雷奥是在念诵经文,就断定雷奥是个小和尚,于是在村里到处说,引起很多人到雷奥家围观。潘进堂害怕这事说出去会让雷奥引起注意,就给老纪和众村民说,雷奥的亲爹亲娘不在了,每逢忌日,他都要给爹娘说说话,雷奥是个大孝子。这一次,老纪又相信了。其后他逢人就说:“进堂那个龟孙这辈子算有福气,捡了这么个懂事的娃,看来今后两腿一蹬,翘了辫子后不愁烧纸磕头的啦!”
小说第十四章,潘进堂的戏班子在山陕会馆唱戏,第二场唱《铡美案》,日本军官高野中尉和伪县长孙宝康都来了,戏中雷奥扮演赵虎时因为看到台下的高野十分紧张,一再失误,引起高野的怀疑,谢幕后,高野下令把四个跑龙套的孩子、包括雷奥一起抓来,他要细细盘查。在日本兵把四个孩子抓过来这个紧要当口,老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突然跳出来大喊失火了,他发疯一样地大叫大跳,转移了日本人的注意。但日本兵发现老纪说谎时,用枪托猛击老纪头部,将老纪打成重伤。老纪弥留之际最后的话是问潘进堂“娃不是咱汉人吧?”他说“俺剃了一辈子头,没有见过这样的头发!”这说明其实从一开始,老纪就并不真的相信雷奥是汉人,最后他舍命救雷奥也正是因为并不真的相信八仙编的那个故事。小说中老纪的善良、天真与淳朴,他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显示了鲜明的民间色彩,这些都显示了他是一个血肉丰满的民间人物。
其次,在“雷奥在中国农村”这个故事中,作者还描绘了很多鲜活的民间场景。所谓“民间场景”是指能够集中反映民间文化、民俗的聚会、活动等,作者往往通过对一个空间场面的描写表现一个地方特有的文化、风俗和习惯等。中国农村的庙会、元宵节的灯会、围绕民间戏曲演出的一系列活动和舞龙狮、赛龙舟等都属于民间场景。《远东来信》中最典型的一个民间场景是1942年春节雷奥正月初五在县城看到的那个上蔡著名的“玩会”。这个“玩会”包含了踩高跷、舞狮子、龙灯舞、旱船舞、竹马舞、鹤舞和扁担桥等一系列节目,高潮则是上蔡特有的“打铁花”。这段描写最特殊的地方是所有这些节目都是从雷奥的视角予以描述,这个视角的特殊在于:第一雷奥是一个外国人;第二雷奥还是一个孩子,从雷奥的眼睛看这些节目就创造了一个特殊的陌生化效果。在上蔡的“玩会”中,每一个踩高跷的人都化妆成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人物:白蛇、青蛇、猪八戒、孙悟空等,这样在一个外国儿童看来这个节目就充满了神奇。特别是看到孙悟空,雷奥马上就联想到他在德国时王家甫给他讲过的“中国神猴”,而这个神猴正是他从小就深为迷恋的,“中国神猴”在他心目中就是中国的代表。踩高跷的“中国神猴”,他的一招一式都让雷奥深为倾倒。上蔡“玩会”的高潮是“打铁花”。这个节目的要点是在一个用木头搭起的五六米高的“花棚”上栓满了鞭炮、烟花和“二踢脚”,“花棚”顶上还有一根一丈多高的长杆子,长杆子上也缠绕了很多鞭炮和烟花。活动开始时,三四个“打铁花”的艺人,赤裸上身,挑着一根顶端能盛铁水的“花棒”,将翻滚的铁水洒在“花棚”上,喷溅的铁水引燃鞭炮、烟花,于是鞭炮、烟花响成一片,火光映红了夜空。而这个时候高跷队、舞龙队、狮子队则围着“花棚”载歌载舞,翻跟头、竖倒立、钻桌子,使狂欢达到了高潮。这段描写并不是一段单纯的民间场景的描写,它是通过雷奥的眼睛在看中国乡村文化,它增加了雷奥对中国乡村文化的兴趣,也让雷奥亲近中国乡村文化,为让他最终融入这种文化提供了重要铺垫。
另外,“雷奥在中国农村”的故事中还融入了许多民间故事的元素,即在叙事中吸收一些在民间长期流传,带有传奇性的故事,丰富了小说的叙事,增强小说的可读性。例如在小说第十二章“陈杆子”的故事中,讲到陈杆子在农村抢劫的惯例是以用半截铡刀砍去人的脚作为手段勒索农民的钱财。在被抢时凡有不顺从者,这伙土匪辄卸下人的一只脚,他们甚至将这些脚带回,在匪巢内建了一个“百足堂”。这种以砍去人的肢体相威胁的抢劫方式在北方农村很多民间传说中都可以找到,也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小说第十四章别津村邻近一个村的崔保长的父亲过世,这位老爷子是一个老戏迷,特别喜欢听潘进堂的戏。老人咽气之前给儿子提出一个要求,要求死后也要听一场潘进堂戏班子演的《南阳关》,他给儿子说:“儿啊,听戏的人都说‘听见进堂喊,吃饭扔了碗’,明儿俺可能就吃不上饭了,最后让爹听着进堂那龟孙的戏把碗扔了吧。”于是第二天下午潘进堂的戏班子就在崔保长的村子演了一场戏,台下摆着崔保长父亲的棺材,死人与活人一块听这台戏。小说中这段叙事当然是作者的虚构,但戏台下面摆棺材,死人与活人一块听戏,这也是民间故事中能够见到的一种说法。作者将这类民间故事、传说融入叙事提升了小说的趣味性,也增加了故事的民间色彩。
参考文献:
[1]基尼利.辛德勒的名单[M].魏明,译.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
[2]吴井泉,王秀臣,张雅文.以生命作抵押——张雅文访谈录[J].文艺评论,2002(3).
[3]郑晋鸣,陆金玉.张新科:一位大学校长的《远东来信》[N].光明日报,2014-12-11(3).
[4]张新科《远东来信》 丁捷《依偎》获长篇小说大奖[N].扬子晚报,2015-01-21.
[5]白修德.十万火急大逃亡[J].时代周刊,1942-10-26.
[6]柯玲.民间叙事界定[J].上海文化,2007(2).
(责任编辑蒋成德)
On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LetterfromtheFarEast
ZHANG Wei-zh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Jiangsu, China)
Abstract:Letter from the Far East is a novel that reflects the life of Jews in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The most attractive feature about it is its artistic form rather than the theme.Taking Xie Donghong's investigation of Reo as the main clue and the dual-clue as the main structure, it not only adds the documentary elements into the fiction to produce the authentic effects but also enables the author to be more flexible in reflecting life without the tedious and blunt description.The rich folk narrative also provides an actual background to the story of Reo's real rural life in China.
Key words:Letter from the Far East; documentary and fiction; artistic structure; folk narrative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5)06-0065-06
作者简介:张卫中(1955- ),男,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