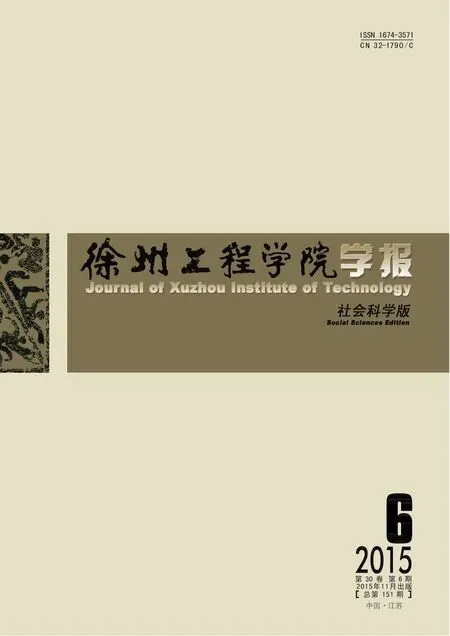将军“顾曲”胜文人——漫谈徐树铮之诗文词曲
蒋 凡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将军“顾曲”胜文人
——漫谈徐树铮之诗文词曲
蒋凡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433)
摘要:北洋军阀中,徐树铮不仅以军政才干闻名,而且颇具文人面貌,能诗会文擅词曲,武中生文,乃是其人生亮色。徐树铮之文,学习桐城又出乎桐城,因其积极参与军政大事,故文风因时因地而生变化,非桐城古文可拘束;其诗虽曾学杜甫,但因性情所致,诗风更近于苏(轼)陆(游),多直抒胸臆而豪气干云;其词作多宫商谐协,音韵宛然,曲高调雅而自然流畅。其韵味直追姜(白石)吴(梦窗)而自成一家。
关键词:徐树铮;拍曲;诗文;词曲
一般人印象,民国初年北洋军阀中的将军,个个都是粗鲁无文的一介武夫,他们提笔立感千斤重负而不胜其苦,不如舞刀弄枪杀人放火那样挥洒自如。不过其中也有例外,如北洋军阀中直、皖二系的二当家——直军阀吴佩孚和皖军阀徐树铮,两位将军在前清时,都一样是好文的秀才出身,诗词文章,挥毫立就,虽非一流,但称其为文人并无不妥。关于吴佩孚,暂略不讲。这里先介绍皖军上将徐树铮之文采及其文学影响。
一
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号铁珊,又号则林,以表示对林则徐的崇敬。民国年间,为别于总统“大徐”徐世昌,人称树铮为“小徐”。江苏徐州萧县人。小徐青年时投笔从戎,一生追随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成为段氏幕府中的智囊谋主,段对小徐几乎是言听计从,从而成为皖系军阀中不争的二当家。连当时的几任总统,如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对他也颇多畏忌。他动辄自称军人,如其《上大元帅(按:指袁世凯)书》称“树铮军官也,请言军事” ;《对奉军之演说》示人以“军人天职”,平生以整军经武为事;他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历任陆军部次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等,确系军职,军衔为陆军上将、远威将军;他在《平报周年纪念日感言》中明白宣称:“余军人也。军人之天职,在保民,在卫国。而保民之良法,在去暴;卫国之能事,在却敌。然则军人者,杀人之人耳。”一片以杀止杀之声,是一个地道的职业军人。但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仍能不忘诗词文章,却是小徐有别于其他北洋军阀的地方。武中生文,乃是小徐的人生亮色。
小徐好文,自小已然。这和他的家学渊源分不开。其父徐忠清,字葵南,前清拔贡生,授教谕改州判,皆不就,一生教授乡里,学生千人,研究经史文章,并以一生所学,亲授儿子。因此小徐从小即受到较为严格的学习训练。柯绍忞撰《远威将军陆军上将萧县徐公墓志铭》称其“少颖悟,有神童之誉”。树铮在其《先考妣事略》中也说:“树铮于昆弟序最幼,先考妣抚爱规教,倍切于兄姐。甫学语,即使辨认文字。五六岁时……先考设帐郡城,伏腊归省,间以树铮往来。尝于风雪中,攀缚驴背,口授诗歌,亦戏令效其句。乡里争传七岁能诗,夸以神童。……居馆职则携之附读,留于家,则杂取书史骚雅,折角授先妣分日督课。”*徐道邻编述,徐樱增补《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视昔轩文》卷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增补版,第25页。以下简称《合刊》,不另注明版本。他自小能诗会文擅词曲,既关乎天赋,更与其家教及后天的勤奋密切相关。
二
对于徐树铮文学,蒋复璁《重印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序》 曰:“又铮先生文武兼资,诗古文辞,无一不精,且与马通伯、林畏庐、柯凤荪、姚叔节诸先生游。”*见《合刊》前序,第1页。熟读经史百家文章,以开其文学胸襟。王树柟(晋卿)《远威将军徐府君家传》称:“(树铮)以诸史诸子骚赋诗歌词曲,皆中国文粹,分拟目录,博为采辑……君善为诗古文辞,尤长词曲。其论文导源班马,而以唐宋八家为正宗。诗嗜少陵,词嗜白石、梦窗诸家。”*见《合刊》,《先生墨迹》后附,第162页。指出了小徐诸体文学的大致风貌及其渊源所自。
树铮擅昆曲。古人称“曲有误,周郎顾”,指的是三国时赤壁之战中大败曹军的东吴统帅周瑜。周瑜不仅善兵,而且是一个拍曲行家里手。他的音乐耳朵,容不得唱曲有丝毫的错误或跑调。其文采风流,近代徐树铮似之。他身为上将,与周瑜一样,雅好拍曲,亲自歌唱,擅名一时。其《即席赠国司少将》诗曰:“寒涛历历激清商,素手弹琴秋夜凉。著意红牙休误拍,座中顾曲有周郎。”以擅曲自负,不减当年周瑜。据高拜石《纵横客——张、孙、徐的结合与“廊坊之变”》一文载:1925年底,树铮率考察团外访归国,特赴江苏南通拜访啬翁(按:指张骞),“啬翁殷拳挽留。第二日,邀往参观彾工学社与更俗剧场。徐固擅北曲,功力相当深厚。见有昆曲班之设,知张四先生对于昆曲亦有深嗜,便从弦索音声,谈至昆弋递变。啬翁难得知音,遂点唱《弹词》与《议剑》两阙,徐一时兴发,引吭高歌。北曲以激昂慷慨为主,徐潜气内转,哀音外激,旧笳声楚,常钧曲凄,一阕既竞,啬翁为之击节不已。旋赴狼山西山村庐清宴,从词曲谈到诗文,越谈越对劲。啬翁本为张濂卿(裕钊)门人,文宗桐城,亦喜作骈俪体,诗词亦复擅场。徐为文私淑吴挚甫(汝纶),也是属桐城派信徒。因此对于扬弃国粹、敝屣孔孟的一般时流,同声排觝。”临别之际,张骞“摛藻下之笔,赠诗于徐,徐亦即席次韵以酬,浮觞竟日,尽欢尽意”*见高拜石《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9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词曲诗文能与张状元即席酬唱应和,受到赏识,自然绝非泛泛之辈。后来,树铮的拍曲艺术,又通过家学传给了子孙,复又传唱海内外。其女徐樱《徐树铮将军生平概略及其电稿所揭示的史实》提到1925年出洋考察期间,徐树铮在伦敦应英国皇家学院之邀,作《中国古今音乐沿革》的专题报告,对于中国音乐与文学的内在互动关系,多有深刻的阐述,故第二天英国《泰晤士报》赞称徐树铮以军人而有此文艺修养,深表敬佩。又曾在归国途经日本的轮船上,竟然有一位巴西的小姐,听徐唱昆曲饶有兴趣,徐“教她数遍以后,曲中意虽不了解,然发音清脆,合拍中矩。可见她听觉之敏锐及我父诲人不倦的态度”。又蒋复璁序称,复璁与树铮之子道邻(原名审交)是同学,“道邻与余同有昆曲之好,春秋佳日,每一度曲,彼吹我唱,颇以为乐也。……道邻度曲,承自家学,于音乐文词讲究甚精,盖亦能填词与谱曲也”。儿子如此,女儿亦同样娴习词曲。如其女徐樱,据徐小虎(按:道邻之女)《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序》称其姑母徐樱:“娴昆曲,能写作,她出版了食谱、游记、翻译、散文等。……她宣扬中国文化,她教久居海外的中国人唱昆曲,教外国人吹笛子。她的第一位最聪明大徒弟就是大语言学家李方桂(按:徐樱为李方桂夫人)。她那种乐而不疲的精神,使周围的人都蒙受了快乐的感染。当然,昆曲是我们徐家看家本领之一。谁能不着迷呢?因此,他们每次回到台北,那里的两大曲会蓬瀛、同期都争相邀请,每个周末,就可以看见她们双双出现于两个曲会之间。昆曲既是我父(道邻)、我祖(树铮)、我伯父(审义)大家的偏好,我想这也是姑母如此热心的缘故吧。”徐家的昆曲传统及其文学世家的形成,与其代代薪火相传有关,徐家子孙从国内唱到国外,声韵绕梁之美,给人以深刻印象,论其始作俑者,树铮开拓之功不可没。
徐树铮诗词文章,散佚颇多。1932年,大儿子审义编其遗集,有《视昔轩文》《兜香阁诗》《碧梦盦词》三种,北平文楷斋印行,但传本稀少。后经其儿道邻、女徐樱继续努力搜集整理,重编为《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本,较为完备,于196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初版,1989年又出增补版。本文称引徐氏词曲诗文,均见于1989年增补版,不另一一注明。其文《视昔轩文》即在其中。树铮另有关于政治方略的《建国真诠》手抄本及《徐树铮电报稿》(中华书局1962年版),因无关文学,故不在此合刊本中。
树铮之文,学习桐城又出乎桐城,因其积极参与军政大事,故文风因时因地而生变化,非桐城古文可拘束。如其《上大元帅书》《上段执政书》诸文,因重经世事功,而有战国纵横家之风,文辞犀利而铺张扬厉。如《上大元帅书》,力劝袁世凯放弃皇帝美梦,要求袁氏下罪己诏,同时指出劝袁称帝的筹安会诸子为“今之良臣,古之民贼,孟子之言何其痛也”,批判锋芒甚锐。政界腐朽,军界又如何呢?他直接剖明当日北洋军已是“将骄军惰,形同乌合”,“欲责以保国卫民,能乎不能?”文章扬弃了桐城文派那温柔敦厚、简练含蓄的隐约吞吐功夫,直陈厉害,辞旨剀切,与其经世致用的政治用心相同。据蒋复璁序说:“洪宪帝制,(树铮)有《上大元帅书》痛切指陈,劝请取消。在项城(按:指袁世凯)迷梦之际,言人所不能言,尤为难得。”王树柟在其《故旧文存》中评云:“其《上大元帅书》,反复指陈,痛切事理。词婉而意直,言人所不敢言,运笔亦极尽屈曲郁盘之势。”所论甚是。
还有,树铮把自己勤奋读书作文并写日记的优良传统,传与子孙。徐道邻在其父《怡经书屋记》一文中题注曰:“民国十年,我们跟着父亲到上海亡命。他把我们弟兄安顿在新闸路武林里。一天他来了,带来两个十行本子来,嘱咐我们要每日写日记。他并且叫我磨墨,一方面提起笔来,就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这篇文章。……文章后面还附有‘日记宜忌’若干条。我自从那一天起,每天写日记,至今四十年了,还没有一次间断过。……从前母亲尚在时,我和她谈到这件事。她说:‘你父亲以前也是天天记日记的,自从留学日本回来以后,就不记了。他说:以后会有人替我记。’”*《视昔轩遗稿》文二,载《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第39—40页。写日记有助文章,树铮这一良好写作习惯,已成为了徐氏家风。此非一介武夫之所为,乃文人学者良好积习之所致。
在北洋军中,小徐以能文称。如辛亥革命爆发南北鏖兵之际,段祺瑞率前方四十二将领逼着清帝退位之通电,虽由袁世凯授意,但具文实出自树铮之手。小徐文章,颇见功力而非凡响,可见一斑。
至于诗歌创作,其艺术又在文章之上。这可读其《兜香阁诗》来加以体味。前人以小徐诗拟杜甫,具沉郁顿挫之美。话有一定道理,但评价过高,并不全面。树铮乃军人政治家,年轻时不乏忧国忧民之心,解民倒悬,振兴中华是其理想,求治之心甚切。小徐性格爽朗果决,敢言人之不敢言,敢干别人不敢干之事,故其诗虽曾学杜,但因性情所致,诗风更近于苏(轼)陆(游),多直抒胸臆而豪气干云。如《三月十五夜泰安道中忆同社》云:“搀枪吐焰兵兆逼,伤哉民隐奚繇室?稍从接膝问疾苦,惶顾似雀遭凤鹯。”学杜新乐府,为民请命,颇见悲痛。又《写照》云:“夜读《阴符》朝试剑,无情日月重徘徊。中年哀乐人间世,故国山川劫后灰。浊酒要留青眼在,天河谁挽素波回。东风万里催暖和,可有春华取次开。”欲挥利剑,披荆斩棘,扫除山川劫灰,令故国春华次第绽放。又《即席迭杉山韵》四首之三云:“天定胜人人胜天,无以故步对年年。天下之大匹夫责,不自我后不我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留日时的青年树铮,是个富有理想的热血男子。“拔剑高歌斫地哀,忧时怀抱为谁开?”(《钤川道中》三首之二)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引发悲鸣。又《枥下行》云:“挚骥之四足,强与驽骀齐。削足以就履,是谓范驰驱。……汗血会有时,筋力要夙储。无徒引悲嘶,忧戕神明驱。志以千里远,貌勿恒群殊。天山种苜蓿,待子骋良衢。谁能促羲驭,匿景西北隅。”以受困于庸夫之手的汗血千里马自喻,悲而不伤,喷发了一腔豪情壮志。又《雪行口占》云:“自矜胆勇惯前驱,冰雪泥沙路有无。借得绿沉枪在握,何时匹马取单于。”企望立功边庭,报效祖国,何其壮哉!《江西舟中》云:“天意茫茫未可知,摧残神物付群儿。悲来歌向酒边发,卧看山从窗罅移。并世英雄曾几辈?横流沧海不多时。澄清毕竟吾侪事,立马中原好护持。”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当然,因其所持北洋正统的立场,树铮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愿望难以实现。他在政治得意之时,神采飞扬,如1919年收复外蒙古,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率师赴外蒙途中作《叼林蚤(早)发》云:“冲寒自觉铁衣轻,莫负荒沙万里行。似丹似霜唯马啸,疑云疑雨问鸡鸣。中原揽辔信孤愤,大海回澜作夜声。日占毡车趁遥曙,沉沉阊阖渐清明。”结合其《西北筹边计划大纲》一文来看,见其思理深沉,信心十足,似乎国家统一之清明即在眼前。而在其政治失意之时,他也绝不垂头丧气,仍然不会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比如1920年7月直皖战争军败后,除段祺瑞通电下野外,徐树铮名列全国通缉要犯第一名。他辗转逃亡,于1922年作《六月十五夜对月》(五首之五)云:“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闭门大索喧严令,侧帽清游放醉吟。白日歌沉燕市筑,苍波梦引海舟琴。雪天不尽缠绵意,敢负平生报国心。”豪情不衰,性灵尽现,平生抱负,跃动于字里行间,颇为动人。
至于词的创作,因树铮擅拍曲,精通音律,音韵文辞,无不细密推敲。故其词作,大多宫商谐协,音韵宛然,曲高调雅而自然流畅。其韵味直追姜(白石)吴(梦窗)而自成一家。其文学观念,持传统的诗庄词媚之见,诗见理想壮志,热情奔放;词重抒展性情,追随骚人雅士的婉约之风,委婉蕴藉而呈艳丽之色。如其《蝶恋花·岁暮有咏》之二:“晓日流苏帘影碎,懒起梳头,镜里成憔悴。判更温馨填锦被,惊魂长是愁无寐。 酒可忘忧宜小醉,争奈金樽,都化歌边泪。斜倚薰笼偎暖意,朝寒悄悄侵红袂。”凛遵婉约词派艺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具温婉含蓄之美。又《忆秦娥·高邮道中》之二:“《阳关》咽,鬓云松掩眉山叠。眉山叠,暗传心事,乍明乍灭。秋灯洗研华堂月,春花睹酒红阑角。红阑角,待来迎你,渡江桃叶。”行旅春风,男女之思,风调宛然。又《六丑》,序曰:“石田翁画西山归棹图,姚石甫先生谪蜀,张松廖举以送行。乙卯(1915)四月,先生孙姚叔节解元同客京师,出以属题。”说明此乃赠姚永概的题画词。词云:“正孤帆半卷,向十里,青山吹笛。送春未归,移舟先送客,客去春寂。怕说江南路,路旁丝柳,颤垂垂千尺。山程水驿牵行色,梦里惊波,瞿塘远谪。回头太湖遥隔。胜愁鬓七二,空际凝碧。 春归谁惜,恰浮家泛宅。怪底红飞早,难再觅。疏钟慢打云隙,遍孤山寺外,夕阳如泣。愁深浅,酒杯宽窄。都分付一剪吴淞腻染,娟花微湿。风飘云,莫问踪迹。待夜潮暗长还吹送,冲烟片席。”词用入声韵,犹如大钟鸣鼓,叩击心胸,很有震憾力量。此词一出,报刊争载,一时京师纸贵。据徐道邻回忆:“民国四年,我那时十岁。在报上看见这首词,很喜欢,几遍就背上口。在午饭的时候,就大声地背诵起来。可是报上没有标点,我把‘路旁丝柳颤垂垂’读成一句,又把‘愁深浅酒杯宽窄’读成平平仄仄上二下五的句子。父亲给我改正过来。这是我一生中,第一首背出来的词。”道邻后来弃政学文,成为作家,当与其家学修养有关。对于树铮词作艺术,当时林纾《畏庐续集》中有《徐又铮填词图记》一文,曰:“呜呼,腔律之失传久,必谓词家当按箫填谱,则舍清真(周邦彦)尧章(姜白石)外,几乎不能词者。康伯可、柳耆卿声律至协,人又往往恶其鄙俗。故先辈尽有佳词,而笛家恒不之用。凡流传于教坊者,多稍通于文字之乐工为之。复沓伧谬,而人人皆能上口,正以稍协律腔耳。……余嗜词而不知律:则日取南宋名家词一首熟读之,至千万遍,俾四声流出唇吻,无一字为梗。然后照词填字,即用拗字,亦顺吾牙齿,自以为私得之秘。乃不图吾友徐州徐又铮已先我得之。又铮尝填《白苧》,两用入声。余稍更为去声,而又铮终不之安,乃复为入声而止。余寻旧谱按之,果入声也。因叹古人善造腔,而后辈虽名出其上,仍无敢猝改,必逐字恪遵,遂亦逐字协律。余之自信,但遵词而不遵谱,此意固与又铮符合。又铮之年半于余年,所造宁有可量?旧作填词图赠之。”树铮精于声律,对于文学与音乐的关系,了然于心。其词作艺术,音调和谐,宫商婉转,而情意绵长,更在耆宿林纾之上。故其词的创作,在其诗文之上而传颂一时,非偶然也。当与其擅拍曲精音律有关。树铮与当时昆曲名伶多有交流酬唱。如作于1924年的《寿楼春》序云:“春夜,偕叔明(按:姜中奎字)携儿子审交(道邻)同集徐凌云宅。坐客徐静仁、俞振飞、项远村、馨吾兄弟、李旭堂、徐念萱,皆曲坛巨子。乐工数人,闲次以坐。当歌对酒,万情酣适。俯仰宇宙,诚不知何者可哀,何者可欣。彼牛栏马皂中,鸡虫得失,更复何预吾事?主人藏酿至美,客多健饮。余虽禁杯数岁,引满亦豪。因请以酒与曲,互角胜负。于是负者举爵,胜者抗喉,争相迭和,乐而忘醉。夜漏三下,始勉抑余兴,坚订后约而罢。十来年朝野辛苦,尘俗满胸。今乃得此雅集,不可不有咏以为之记。……甲子二月,树铮识。”所与游者,无一非曲坛之巨擘。得此雅集,忙里偷闲,涤尽凡俗,尽兴而归,一扫其十年从政之郁积,而重现其词家文人之本色。当然,由于小徐戎马一生,影响其文学创作,故其词作之中,又不乏变调之音,时有直抒胸臆而豪雄天纵之风的展现。如其《解连环·闻歌》曰:“哀歌自成跌宕。却微闻笑我,归计辽旷。谁与唤,桃叶桃根,便轻趁东风,渡口双桨。燕子飞来,道花雨,一江春涨。更焚香,卷帘镇日,系舟不放。”《大酺·雨后凭栏》曰:“天涯多风雨,况倦销英气,易成哀乐。问身世能禁,几番欢笑?几番愁绝?”《念奴娇·笳》曰:“还想中夜哀歌,唾壶敲缺,胜怨填胸臆。空外流音,才睡浓,胡笳乌乌惊逼。高妇琵琶,阳陶觱篥,万感真横集。琱戈推枕,问君今日何日?”又与苏(轼)辛(弃疾)词风之豪放刚健有相近的一面。
三
树铮虽为皖系军阀的二当家,但并非只干坏事。1919年末,他乘苏联十月革命爆发而无暇东顾之机,曾以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的身份,亲率劲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鼓作气收复失陷已久而独立出去的外蒙古,有力打击了俄、日侵略阴谋,从而维护了国家的主权。这一丰功伟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绝无仅有。当徐氏收复外蒙后,首先向二人报喜:一是上司段祺瑞,另一是孙中山。在政治上,孙、徐立场对立;但在收复失土方面,却是二人同心。《诗经·棠棣》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此之谓也。当时孙中山复电徐树铮:“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对徐氏功劳的称赞,来自于政敌孙中山,这就更加真实和可贵。所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噩耗传来,当时徐树铮率考察团在巴黎,就在其巴黎驻所建灵堂悼念,树铮亲撰长联以寄哀思:“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据周游《扪虱谈》称,中山仙逝后,举世哀悼,挽词极多,但“当时竟共推徐氏此联为第一”。问其所以,包括国民党政要胡汉民、汪精卫、张继诸人在内,“一致认为,徐之才气,横揽一切,远不可及”。
虽然树铮因其军政而掩其文人面貌,但其文学才华,终是难以掩抑,远超一般世俗作家而颇生影响。如康有为对徐树铮也有盖棺定论之评。康氏助张勋复辟清帝,徐则辅助段祺瑞马厂誓师而“三造共和”,兵进北京,一举粉碎了复辟美梦,康被通缉。康、徐二人明显是政敌,康有为不会故意为徐说好话。又,康“圣人”眼界很高,他能看上的又有几人?但徐暴亡后,康于1926年初作挽词悼念,曰:“其雄略足以横一世,其霸气足以溢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识通乎新旧;既营内而拓外,翳杜断而房谋;又扬厉乎域外,增学识于四州;其喑呜废千人,其洞视无全牛;其飞动高歌擅昆曲,其妩媚清词追柳周。大盗竟杀猛士兮,无人起邦家殄瘁之愁!假生百年之前,为人龙而寡俦。哀世乱而内争兮,碎明月于九幽。”虽不无溢美之辞,但其评价之高,大致客观。“其才兼乎文武”,概其全貌;“其妩媚清词追柳周”,独推其词曲兼擅,近代词家并不多见。康氏颇具只眼卓识。因此,我们说徐树铮具文人面貌,乃民国时人共识。只因现代人多重白话诗文,因而把他遗忘。以此,我特撰此文,以补文学史家之漏失。
(责任编辑蒋成德)
The General's Lyrics Outperformed the Literati:
On Xu Shuzheng's Traditional Literary Inditement
JIANG F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Among the northern warlords,Xu Shuzheng was famed not only for hi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talents but for his traditional literary inditement,which highlighted his military life conversely.His verse style learned from Tongcheng but far beyond it due to hi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His poetic style once learned from Du Fu but more close to Su(Su Shi)and Lu(Lu You)due to his strong temperament. His Ci was natural and smooth with sweet and harmonious rhythms and elegant melody whose taste was unique of his own style.
Key words:Xu Shuzheng; poetry and prose; Ci and Qu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5)06-0049-05
作者简介:蒋凡(1939- ),男,福建泉州人,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论学会顾问,中国文心雕龙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丛刊编委,文心雕龙研究学刊编委,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