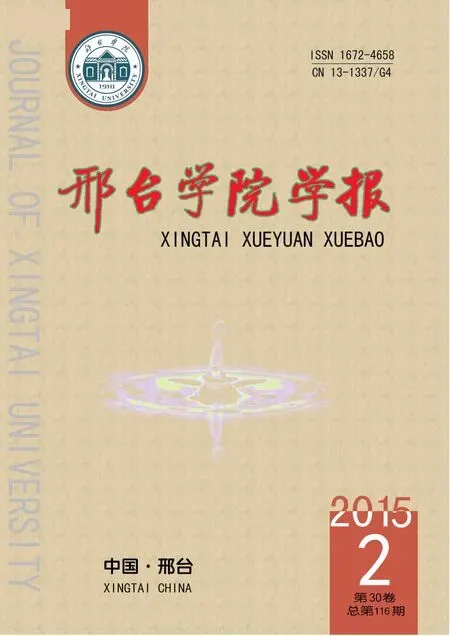探析《无名的裘德》之生态意蕴
林晓青
探析《无名的裘德》之生态意蕴
林晓青
(三明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三明 365004)
作为哈代小说封笔之作的《无名的裘德》无愧“天鹅绝唱”之美誉,经世流传,最终被列为哈代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同属威塞克斯小说系列,有别于他作,虽然一如既往地关照自然,关注生态整体的发展,但是此前作品中曼妙田园风光,诗情画意的乡村生活早已渺无痕迹,取而代之的是残缺凋敝,混沌模糊的自然书写。他深深眷恋的,赖以创作的田园牧歌“威塞克斯”已被历史车辙碾碎,空留余音,回响着遗憾与无奈。惟有放弃欲望导向的人生,转变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融入自然去感受大地的脉动,倾听自然与万物心领神会的交流,尊重自然体验宇宙大生命的美妙与庄严。
生态意蕴;自然缺失;文明凋敝;回归自然
托马斯·哈代以诗歌入行文学界却因小说成名于世,在其30年的小说创作生涯中,硕果累累,留有14部长篇小说和4部中短篇小说集,文坛地位不容置喙。1895年《无名的裘德》的出版在主流评论界掀起轩然大波,几乎众口一词地对作品大加挞伐,遭此非议,哈代毅然决然放弃了小说创作,全心致力于青年时期所倾心的诗歌写作,成了名副其实的“双料冠军”,而且更是一座跨世纪的桥梁,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文学与20世纪现代文学紧密衔接在一起。作为哈代小说封笔之作的《无名的裘德》无愧“天鹅绝唱”之美誉,经世流传,最终被列为哈代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同属威塞克斯系列小说,有别于他作,《无名的裘德》虽然一如既往地关照自然,关注生态整体的发展,但是此前作品中曼妙田园风光,诗情画意的乡村生活早已渺无痕迹,取而代之的是残缺凋敝,混沌模糊的自然书写。作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生态意识作家,面对城市的物欲横流、自然甚至于人的生存权利遭到威胁的悲惨境况,深感痛心疾首,进而大力批判。作为一名文人哈代的生态思想哲思对于改变生态危机所带来的种种恶果虽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他的意志和愿望,是扑入时代河流之中的种子,必定会在遥远的他处开花结果。
一、田园:一个离析的、破碎的农业文明的自然生态
随着人类认知及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人与自然的关系持续恶化,从原始蒙昧时期的仰望崇拜到宗教教化下的敬畏顺从直至现代工业文明笼罩下的冲突对立,给人类身心带来了难以弥合的创伤。自然之子哈代一直以来倾心于自然的描绘,技巧高超纯熟,从1874年的成名作《远离尘嚣》曼妙优雅、恬淡静谧的田园牧歌到1878年的《还乡》的气势磅礴,苍莽冷峻的广袤荒原至1886年的《卡斯特桥市长》沉默寂寥、黯淡灰败的高墙城市直至1895年的小说封笔之作《无名的裘德》终于光明隐于黑暗,自然风景缺失,分崩离析、支离破碎的景致取代了生机勃勃、生趣盎然的农业社会劳动场景。在这二十多年间,英国已然发生了重大变革,工业革命越来越深入诸如威塞克斯这样的诗意栖居地,另一方面,当时发生了两次农业危机和三次牲畜瘟疫,冲击了当时的农业社会,这是由于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一步步地渗透、瓦解使农业无节制地工业化,最终人类因一己私欲酿成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
《无名的裘德》从一开始就以残缺破败,沉闷黯淡的基调来描绘自然:“许多用茅草盖的带屋顶窗的住房近年来都被拆毁,许多草地上的树也被砍倒。尤其是原先的教堂也已被拆除。”[1]P6损毁的画面无处不在,马格里林如此萧索,曾经的勤奋不屈、欢乐嬉戏成了回忆里的往事,现今纵目而望,映入眼帘的是:“刚耙过的一行行地就像灯芯绒上面的条纹一样向前伸去,给这个地方造成一种平庸功利的气氛。”[1]P8离开故乡马里格林裘德怀揣一颗赤诚热心来到了心之所往的基督寺,然而他发现“那一个个学校竟背叛了他,变成另一番模样,不再给人以同情之心:有的十分浮华,有的像是一个家庭的墓穴由地下移到地上,而所有砖石建筑都露出一种粗野的气氛。”[1]P87从乡村到城市,破坏已经随处可见,裘德的理想国度也不过如此,这里经济价值替代了自然世界的生态价值,裘德幻想中的学术王国已然露出腐朽的气息:“这里一座座古老的建筑物都遭到了严重摧残和虐待……还时而遭到人类的侵害,在这种殊死搏斗中,它们遍体鳞伤,处处断裂,层层脱落。”[1]P87
哈代以心去观照、感受万物,让主体情感在对物的感动中与物融为一体。痛心于农业生态的不堪重负,他将这份情感投射在作品男女主人公身上,体现哈代生态思想的崇尚追求:非人类中心主义,众生平等。因而裘德与淑具有相同的热爱自然,同情弱小,善待动物的美德。裘德厌恶对某一类生物仁慈就是对另一类生物残酷的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他是“一个不忍伤害任何东西的孩子。每次他从外面带回家一窝小鸟,总是心里难过得半夜睡不着觉,常常次日早晨又把它们连窝放回原处。他简直不忍看见一棵棵树被砍倒或修剪,好像那样便伤害了它们的心。”[1]P11为了不踩死雨后潮湿土壤上密集的蚯蚓他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走路,一条也没踩死。不得已杀猪的时候,他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让猪慢慢流血而亡保持良好肉色以换取更高的价格,尽管经济窘迫他仍选择刺中要害让它快点儿结束痛苦:“我宁可不要这头猪也不愿做这件事了!那可是我亲手喂大的生物啊。”[1]P63哈代赋予动物与人类共通的情感:“一只知更鸟从最近的一棵树上往下盯着他做准备,它不喜欢这个凶兆的场面,飞走了,尽管很饿。”[1]P63杀猪这样血腥的场景,连一只鸟儿都不忍目睹,宁愿选择饥饿。而猪呢则“痛苦的尖叫,愈来愈呆滞的眼神带着一只动物意味深长的强烈指责,盯住阿拉贝娜,因为它终于意识到表面看来是自己惟一朋友的人竟然背叛了它。”[1]P64相较于阿拉贝娜的麻木不仁,淑体现了与裘德一样的悲天悯人、关怀生命的美德。一只兔子被夹子夹住发出的痛苦叫声同时惊动了裘德与淑,想象着那只兔子腿被撕裂、痛苦挣扎的情景,裘德难以入眠起身入园给兔子一个痛快的了结,而淑也正有此打算:“听到了兔子的叫声,止不住想到它受的痛苦,觉得必须下来把它打死算了!不过我很高兴你先到了……不应该让他们放上这些钢夹子的,对吧!”[1]P241正是对这只小兔子的仁慈让他们彼此的心更贴合在了一起,促成了日后的相知相守。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人理应得到幸福的权利。裘德与淑不是没有幸福过,只是工业文明的社会刚硬如同冰冷机械,没有给他们的情感以容身之所罢了。在他们计划离开奥尔德布里克汉对财物进行拍卖,淑最难以忍受的是对自己心爱的一对鸽子进行拍卖,“她感到比失去所有家具还忧伤。”[1]P353随后天色昏暗之际她经过家禽贩子的店看见自己的那一对鸽子忍不住打开笼子放飞了它们。鸽子回到自然,获得了自由,他们却继续在工业社会的牢笼里夹缝求生。他们可以为小动物们争取飞翔的天空,却无法为自己谋得生存的空间。裘德所追寻的看似近在咫尺,却不期然地都在不断向远处逃离,生活环境的恶劣,使人失去想象力和对理想的期待。
在工业革命的作用之下,“那些现代的小教堂,坟墓和灌木丛,在一堵堵破碎衰败、长满常春藤的古墙里,个个都像入侵者似的。”[1]P332新的建筑摧毁的并不仅仅是自然生态的原貌还有传统的文化内蕴。工业文明之下田园牧歌已是幻灭的想象,农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有机融合所展现于人前的那份赏心悦目的和谐之美荡然无存,为人所津津乐道生机勃发的自然生态遭致毁坏,面目全非。面对农业文明的离析与破碎,哈代不堪忍受于是将小说的场景搬到了城市喧嚣繁杂之中将自然风光隐没。
二、樊笼:一个畸形的、凋敝的工业文明的社会生态
工业革命时代是辆轰隆隆势头迅猛的欲望号列车,所有人拥挤其中,身不由己,即使前面方向不清,人心惶惶,却无人可以试图跳车或逃脱。自然对于人而言不再是怀有温度的有机体,人类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物质利益之余,却疏于完善自身的精神世界,心灵萎颓,道德沦丧,自私自利,对自然投入的情感极其有限。人与自然的关系日渐疏离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难逃淡漠异化的命运。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畸变在裘德与阿拉贝娜夫妻关系上得以体现。阿拉贝娜是典型的跟着物质欲望走的生态侵略者。哈代赋予了她浑圆强壮的外表,她对生态的掠夺力量是巨大的。这个“血液里就有虚假本能”[1]P57的女人对于裘德不过是利用,只是想依靠这个男人来将养自己。裘德一直清楚阿拉贝娜非灵魂伴侣,和她在一起“不过是好玩罢了。”[1]P40然而裘德面对诱惑,情感的冲动战胜了理智的判断,最终落入阿拉贝娜的圈套被迫与之成婚。很快她意识到裘德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提升,并没有放弃到基督寺生活,且有“在有生之年成为一名神学博士”、“过一种纯洁明智、精神饱满的基督徒生活”[1]P34的崇高的理想。对金钱淡泊的裘德实非阿拉贝娜的良人,她意识到裘德无法满足自己的物质理想,决定远走高飞,移民澳洲,另觅佳缘。身犯重婚的她被第二任丈夫卡特勒特抛弃,回到英国巧遇裘德寻求复合,可是卡特随后来到英国表示和解,阿拉贝娜再一次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裘德选择有钱的卡特,可一切并没有就这样结束,之后卡特离世,她失去了经济的支撑,又将裘德算计与之复婚,她从未珍惜所得,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在裘德病重之时仍喂以春药,在他弥留之际置之不理,发现裘德离开人世没有丝毫伤感反而说:“想想看他竟然要现在去死!干嘛要现在去死呢!”[1]P472她弃抱恨终天的裘德于不顾,按计划去看船赛欢喜雀跃:“多有趣啦!真高兴我来了”[1]P473,而且还不忘与人调情。从裘德的角度来说,与阿拉贝娜的两次婚姻皆非心中所愿,却总因难以摆脱欲望的驱使而受了摆布,虽然再婚却对另一个人恋恋不忘。在灵与肉的生死搏斗中,肉体的每一次胜利都使裘德更接近万劫不复的悲剧深渊。他们之间畸形奇特、无稽荒谬的夫妻关系反映了工业革命之下,物质利益当前人与人关系的凉薄冷漠,是社会生态危机微缩写照。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导致社会生态失衡唯一的因素,另一内因则是人与社会关系的疏离异化。即使是在基督寺这个裘德打小立志为之奋斗的梦想之地,他也一直未能找到自身的立足之地和身份认可,更勿论成长之所马里格林、梅尔彻斯特、沙斯托、奥尔德布里克汉。
成长于马里格林的裘德,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收养他的姑婆对他感情淡漠:“要是全能的上帝把你和爹妈一起带走,那才是福呢。”[1]P7小小年纪便已饱尝人世心酸,感知人间冷暖。无怪乎他同情那些渴望吃食却不断受他干扰的鸟儿:“它们似乎和他一样,生活在一个不需要它们的世界。”“那些鸟儿的生命弱小而可怜,与他非常相似。”[1]P9他将自己的境遇和鸟儿联系在一起,实现鸟儿与人类的一体性,又通过对鸟儿命运的描述,为裘德后来的悲怆经历及凄楚的结局奠定基调。在马里格林的裘德总是孤身一人,没有朋友相互依傍,没有亲人嘘寒问暖,只有姑婆的训斥,农夫的奚落,卖假药的欺骗……而在裘德心驰神往的梦想之地基督寺高墙将他拒之门外,求学无门,他满怀希望地写信请教高墙之内的学界名人们,只有一个院长给他回复,劝他“坚守旧业,安于本分,而不应好高骛远,另辟蹊径。”[1]P127
那个满怀幻想的青年在残酷现实的打压之下幻灭流离,带着爱人淑几经辗转来到奥尔德布里克汉艰难谋生。当地居民得知裘德与淑同居而未婚之后,从面包师的小徒弟和杂货商的小伙计到手艺人的妻子都对淑视而不见,待之漠然。之于裘德,生意变得冷清,生活难以为继,好不容易揽到个刻《十诫》的活,在教区执事的冷嘲热讽中无果而终。又因被孤立不得不从艺人共同促进会辞职。连小时光老人这样无辜的孩子在学校也受同学的欺辱。压抑的气氛始终笼罩着他们,让人喘不过气来,从未有人给予他们宽容与理解,愿意成全他们情感的淑的前夫菲洛特桑自己也落得被迫离职,寄人篱下,落魄度日的下场,无奈感慨:“残酷就是贯穿着整个自然和社会的法力,我们想逃也逃不脱它!”[1]P336这个社会仿若一个苦涩无情的樊笼,将他们深困其中,并投以冷漠疏离,投以流言蜚语,投以无情打压,在选择逃离拍卖家什之际,人们讨论的“不是他们的家具,而是他和淑私人的往事和行为,其详尽程度出乎他们意料,使他们忍无可忍。”[1]P351淑不怕贫穷苦难,她说:“大自然赋予了我们什么样的本能,我们就要尽这些本能去寻求欢乐——尽管这些本能受到了社会文明的阻挠。”[1]P391但是社会文明并不仅仅阻扰他们寻求欢乐而是致以万劫不复的打击。当裘德与淑带着三个孩子重返基督寺,找个临时住所都连连遭拒,导致悲观的小时光老人深感自己的多余累赘,同自己的弱妹幼弟一同吊死。逢此巨变,淑腹中胎儿早产并夭折。淑只能选择向社会屈服,离开了深爱的裘德,放弃了自由的思想,抛却了独立的人格,舍弃遵循自然的信念成为一个灵魂飘零的人。裘德则终日纵酒,郁郁成疾,甫届三十含恨而终。
裘德的孤独是尘世喧嚣焕彩繁华中的孤独,是熙攘人群中的遗世独立。城市的喧闹与繁盛之中,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无间,没有心灵契合的朋友,只有逼仄的生活空间,还有他与淑无处安放、无人理解的爱恋。基督寺这个伟人奇士盘踞之地却给了裘德最致命的一击,人与人的淡漠、人与社会尖锐冲突到了生存都受到威胁的程度,这正是社会生态失衡的结果。
只能说:“没有哲学的科学技术文明是盲目的,危险的。科学技术的巨人,世道人心的侏儒。——这种畸形是可怕的!”[2]P41
三、回归:一个救赎的、引领前进自我重建的精神生态
生态批评理论关注自然在文学文本中的表述或压制,也关注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态,即人在与自然、社会、文化的关系中持有的精神状态。在工业革命的大力推进之下,城市化进程加快了步伐,大批农民被迫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来到城市成为居无定所的无根游魂。城市建设原是社会进步的产物,科学技术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哈代对这样的文明进化并不是持全然否定的态度,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接受新兴事物,只是希望工业文明卸去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姿态,结束与自然征服对立、巧取豪夺的恶劣关系,能够给美丽自然、传统文化、淳朴精神留有一席之地。
而“生态平衡要走出进退维谷的境地,就必须引进一个“内源调节”机制,在动态中通过渐进式的补偿,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而这个“内源”就是“心源”,就是人类独具的精神因素。人类的优势仍然在于人类拥有精神[3]P11。我们在此之所以如此强调“精神”在人类系统中的地位,是因为科技时代的“精神问题”并不会随着科学技术向着尖端的快速发展而自行消失。裘德与淑都携带着自然的印记,他们惺惺相惜,但是随着工业文明进入乡村,他们都背井离乡,无法再融入自然,只能在都市伤痕累累的景象中感同身受自己的命运乖蹇。他们尊重自然的法则,保护弱小的动物,追求崇高的理想,保持向善的力量,然而阳光却照耀不到他们的角落。洁身自好、善良淳朴的他们无法融入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城市生活,像无根的野草四处飘零,精神地游牧难返其乡。阿拉贝娜则不同,她符合城市的特质,对物质无止境的追求,在不同的男人中来去自如,满足肉身的欲望,然而精神注定在这样的追逐中沉沦。崇尚自然且道德高尚的裘德与淑,一个以死亡的代价、一个以剜却精神信念的苦痛来宣告精神生态危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价值观褊狭与精神世界凋敝的阿拉贝娜却求得生存的空间,这便是工业文明下的畸形精神生态。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急切盼望着精神的回归。远离社会,回归自然一直是文艺创作的主题,卢梭率先打出了这一口号。他认为“回归自然环境与回归人类的自然天性,是人类健康生存的必需。”[4]P147人若能泯却一切的占有欲望而纯任自然,则人类精神自然能澄然清明,保持心灵澄澈不受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的之困扰。
哈代认为,工业文明不仅严重摧残了自然,同时也严重摧残了人类美好的天性。《无名的裘德》用凋敝、破败的自然景观诉说着哈代心中对工业文明渗透之下的条分缕析、井然有序的理性社会感到无望,他深深眷恋的,赖以创作的田园牧歌“威塞克斯”已被历史车辙碾碎,空留余音,回响着遗憾与无奈。“工业文明把自然当作材料,把人当作机器,既把自然破坏得满目疮痍,也使人的精神世界瘫痪,使人丧失生命活力。惟有回归自然、回归本性,才可能挽救人类。”[4]P163然而,回归并不意味着要逆潮流而动,回到过去,耽溺于过往的历史,而是充盈着一种坚定的与时代精神相同的未来主义意识。意味着放弃欲望导向的人生,转变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融入自然去感受大地的脉动,倾听自然与万物心领神会的交流,尊重自然体验宇宙大生命的美妙与庄严。只有放下“万物灵长”的身段,去掉居功自傲的脾性,忘我地、无目的地感受自然,感悟越来越多,自然也越来越美轮美奂。
[1][英]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M].刘跃荣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2]赵鑫珊.飘忽的思绪(七)[J].党政论坛,1998,(11).
[3]鲁枢元.文学与生态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4]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王喜绒,等.生态批评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7]魏懿颖.异化之果:《无名的裘德》中的生态危机[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4,(5).
[8]吴靓媛.从田园诗到哀歌——生态视角下的《远离尘嚣》和《无名的裘德》[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4).
2014-12-23
福建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托马斯·哈代作品中的生态批评研究.编号:JBS14158;三明学院科研发展基金项目.编号:A201315/Q
林晓青(1981-),女,福建三明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I106.4
A
1672-4658(2015)02-01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