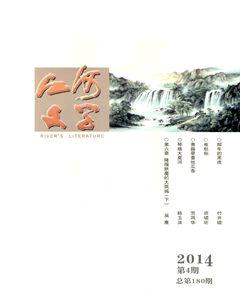那年的黑虎
付开镜
它的妈妈是我大姨家的一只黑犬。和它的妈妈一样,它全身通黑,没有一丝杂色。我老爸因此为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黑虎。
黑虎是由我带回家的,时间在1971年的初春。那年我六岁。
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只知道我爷爷时常被挂着高牌游村批斗。全大队有七个村庄,每次我爷爷和几名地主都要被押送着一起游完这七村。
我已经知道大队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大队上面是公社,公社上面是县,县上面是省,省上面是毛主席。全国最大的官是毛主席,全大队最大的官是书记。我们大队的书记姓屈,叫屈代银。人们都喊他屈书记,从不叫他屈代银。我们大队下面七个村庄分成了七个小队,七个小队都编了号:从一队到七队。我那时学会了一首儿歌:“一队长的干饭二队长的馍,三队长分粮没秤砣,四队长偷油炸油馍,五队长半夜开小锅,六队长舔了书记的脚,七队长的女人书记的婆。” 我的家就在七队,我不知道我们七队长的女人与书记的婆是什么关系。当然,当我再大几岁时,才明白这首儿歌的真实意思:无非是说生产队长多吃多占啦、偷盗集体的粮油啦、低三下四巴结大队支部书记啦、把自己老婆送到书记床上啦,等等。总之,都是编排七个生产队长的。这儿歌是听村里小娃娃唱,我跟着学会的。当时我最喜爱的是“四队长偷油炸油馍”。因为我老想吃油馍,一想到油馍我就会流出口水,我觉得四队的队长最会搞。我回家唱时,被我妈听到,她在我屁股上狠狠地批了一掌,警告我绝对不能再唱了。
我五岁时,在村中玩,队长十五岁的儿子大敢带着全村十多个小娃娃,把我拉到村头,让我站在中央,对我进行批斗。大敢用一根木棍点着我的头骂道:“你爷爷是老国民党,你老爹是中国民党,你就是小国民党。今天,我们要打倒你这个小国民党!”他们批斗完我,每人都向我身上吐了一口唾沫。我妈当然也知道孩子们欺负我,她就把我送到我大姨家。我姨父是贫下中农,又做村长,没人敢欺负他们。我是过了春节去大姨家的,等再要过春节时,我和表哥表姐们已混得不想回家了。就在这时,妈妈来接我了,说过了春节,就得去上学,我只好回家。回家时我提出一个条件,要带一只小狗回去。于是这只不到二斤重的小不点,就被我带回家了。经过一年的饲养,小虎变成了大虎,长成一只二尺高矮、三尺长短的家伙。当时,好多人都吃不饱饭,好多家的狗因为缺少食物,都瘦骨嶙峋,而黑虎却长得非常强壮。原因在于我家把它当人看待,不只我照顾它,更重要的是我老爸在每次饭做好后,要先给它留下一碗。
我从小与黑虎为伴,它来我家第二年初夏的一天,我不小心掉进水塘中,黑虎竟然把我从水塘中叼了起来。同年深秋的一天早晨,桐柏山中的三只狼娃子窜进我们村庄,把一户人家二十多斤的一只小猪叼走了,好多男人在后面追赶这三只饿狼。没想到黑虎也带领全村的十数只大狗追在最前,咬死了一只豺狼,把小猪救了回来。黑虎从此出了名,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认识了黑虎。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想不到这话不久也应验在黑虎身上了。
这年的冬天冷得特别,天没下雪,却总是阴沉沉的,堰塘结出了一尺多厚的凌冰。一天,公社的武装部长来到我们大队检查军民联防抓国民党特务的事情。我们公社在桐柏山南麓,桐柏山位于河南桐柏、湖北随县、枣阳两省三县交界处,据说,桐柏山中有国民党特务隐藏,是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先遣军。我们公社归枣阳县,当然是联防重点。我们小学召开学生大会时,校长宣布过这事,要求我们时刻提高革命警惕性,发现陌生人,马上汇报。我们大队部的院墙上就写了一幅大标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是用石灰刷上去的。一个字有半人高,八个字加一个感叹号占了整整一面墙体。大队部建在一个高坡上,人在一里外都能看清这八个大字。
武装部长是我们公社唯一行走带手枪的人。他来到我们大队,屈书记跑前跑后地孝敬他。屈书记问这位部长爱吃什么,武装部长说最爱吃黑公狗的肉。支部书记问:“为什么最爱吃黑公狗肉?”武装部长说:“我吃过上百只狗,才发现黑公狗的肉最香。”当然,这话是民兵连长后来转述给我父母,我听到的。屈书记就拍了胸脯:“小事一桩,好办。”就让民兵连长打听全大队谁家有黑狗。民兵连长带人到我们队调查,生产队长立刻说我家的黑虎最合适。 民兵连长为了保险,又调查了其他几个村庄,最后向屈书记汇报:“全大队有五只黑狗,其中三母二公。母狗肉不中吃。两只公狗,一是七队‘老国民党家的,另一只是六队‘大老粗家的。‘老国民党家的,很肥;‘大老粗家的,太瘦。”屈书记说:“带两个民兵,拿两块钱,就要‘老国民党家的。”
民兵连长来到我家,说明了来意。他带了两个民兵,其中一个肩扛扁担,一看就知道是准备抬狗回去的。没想到我老爸一口回绝了他们。民兵连长说:“这可是公社的武装部长啊。你敢得罪?”
我老爸说:“他就是天王老子,与我何干!狗是我自己的,你管得了?”
民兵连长回大队部一汇报,屈书记大怒,“‘老国民党是反革命,‘中国民党也不是好东西。我亲自去搞。”
屈书记带着民兵连长又来到我家,没想到又吃了一次闭门羹。
这时,我正好在家,知道他们要吃我家的黑虎,就悄悄移开了院墙边堵狗洞的石头,对黑虎一招手,黑虎似明白了我的用意,很快钻了出去。
屈书记临走时怒道:“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老爸并不在意。
未料到第二天上午,屈书记带着民兵连长一群人又来到我家,我以为他们又要捉黑虎,早让黑虎从狗洞逃了。没想到他们一进门,就拴我老爸。屈书记露出满口的大黄牙,笑道:“老子要办成的事,谁敢阻拦。我宣布:把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带走!”我妈问:“凭什么说他是特务?”屈书记喝道:“老子说他是特务,他就是特务!”
我老爸被捉,我妈不知道如何是好,在家只是哭。这时,屈书记让大队妇女主任捎来话,把狗送去,就放你男人回来。
我妈哭着把黑虎用绳子拴上,边拴边说:“黑虎,不是我狠心,是你的主人有难了,你得去救他啊。”黑虎似乎明白了,呜咽不停。
我放学回家,见妈妈要牵黑虎出门,大惊,拦住哭求不让。说:“我去求我大姨父,我大表哥在部队当连长。”
妈妈眼睛一亮,放下黑虎,立即前去大姨家。
没想到我妈走这一趟,真起了作用。我表哥在部队上虽然只是个连长,但他与部队团长的女儿结了婚。武装部长的儿子,是他的高中同学。武装部长和部队关系密切。我表哥一个电话打给武装部长儿子。第二天,我老爸就被放回家中,但却大病一场。
据说屈书记没搞成我家的黑虎,只好花了二十元钱,从邻近的大队买回一只。当然啦,狗皮归屈书记所有了。
黑虎死里逃生,它似乎明白是我救了它的命,对我感情更深了。
每次上学路上,它都要送我到学校门口,再回到家中。等我放学,它又从家中跑到学校大门口等我。
我上学很是孤独。上学路上,没同学和我一起走,在学校里,也没同学和我玩。因为我爷爷是国民党员,做过国民党的干部。我老爸是国民党员的儿子,我是狗崽子。即使是老师排座位,也没人和我同座。起初,我有一个好伙伴叫大喜,他爱和我一起上学。有一天上学,他爸看到他和我一起,就训斥他:“大喜,你再和小国民党一起上学,小心我打断你的腿!”从此,唯一的伙伴也不和我玩了。可是,我的黑虎却喜欢我。我每天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它在学校门口迎接着我。
春季里有一天,全大队的社员都集中到我们学校校园里面开起了大会。
我们学校,解放前是我们傅家的祠堂,祠堂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周围有近百株参天大树,都上百年了,枝叶浓郁,可容纳近千人坐其荫下。祠堂有三重房屋,解放前,里面有一排房子当了教室,族人的男娃,只要愿意,都可免费入学就读。解放后,祠堂充公,大队在祠堂前又盖了两排房子,在祠堂前围起长长一圈的院墙,祠堂前的空地和大树全被围在院内,这样就建成了大队小学。大队每次召开社员大会,都选择在学校进行,就是看中了校园有大树,前面又有一个五六百平方米的空场子。当然,更重要的是,场子前还有一个戏台,解放前是用来演戏的,现在领导在这里开会可以坐在台上讲话,高高在上。
这一天上午,全大队男女老少四百多人来参加一场批斗大会。我爷爷、我老爸两人都被拉到主席台前,胸前各挂着一块黑牌子,我爷爷胸前牌子上大书六字:国民党反动派。我老爸胸前的牌子上大书六字:反动派狗崽子。和他们一起被批的还有八个地主分子、国民党军人崽子,也都挂了牌子,加起来正好十人。
原来的戏台,现在成了主席台。主席台的正中央,摆着一把红木太师椅,上面坐着大队第一把手屈书记。那把椅子解放前是祠堂专用品,只有族长才有权坐于其上。屈书记的左右,各摆了两条板凳,坐着大队副书记、大队长、民兵连长等人。再向两边,各站了四个民兵,手持半红半白的栗木红缨枪,一样的打扮:身披黄装,足穿黄鞋,腰上扎着宽宽的武装带。
全大队七个村的社员,按顺序坐在周围的大树下。社员们有带凳子的,就坐在凳上;但好多男人却坐在他们带来的草腰子(很粗的稻草绳子)上。全校近二百名师生,也排好队,坐在批斗会场主席台的正对面。
批斗会的第一个程序是书记宣布开会,然后,民兵连长带队押送我们大队十名“反革命”上场。然后就是贫下中农代表上台发言批判。
我虽然很小,也参加过几场批斗会了。因为每次开批斗会,都要在我们学校举行。我们学校的全体学生,必须参加。毛主席说过,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学校的校长,是由大队支书任命的,大队支书的大儿子,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看到爷爷和老爸都被绑着,心中伤心欲哭,但我终于忍住没哭出声来。
已有五人上台发了言。他们大多讲的是在解放前如何受到剥削压迫,如果不是解放了,他们家就活不下去了之类的话。当然,剥削和压迫他们的,是地主,也包括我爷爷这个国民党员。
第六个走上台的是一位老农,叫张兴富。他是我同学张有财的爷爷。张有财的老爸叫张万钱,他们一家三代都想发家致富,可是,三代人都好像与富字有仇。张有财上学,穿的裤子,破得露出了小鸟,他老娘也没时间补一下,张有财因此被同学们起了个绰号:张露鸟。张兴富用一根稻草绳当裤带,扎在腰上,脚上的一只鞋,已露出了大脚趾,上衣的扣子,也脱落一颗。他一走上讲台,就开始诉苦:我家可是三代贫农啊,我小时候从没吃过饱饭。高音喇叭把他对旧社会的仇恨放大了多倍,震耳欲聋。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学生娃们啊,我打八岁起,就给地主放牛。斗大的字,我不认识一个。你们现在有学上,多好啊!我活了六十多岁,没有享过一天的福。六零年吃食堂,我没少吃椿树叶。这几年我家生活还是不好过啊,你们看看,我连个裤带也没有啊,只好用根草绳当裤带。”说着就掀开上衣,露出半截腰来。
台下一些年轻人哈哈大笑起来。屈书记连忙起身挪开张兴富面前的高音话筒:“下去,不要说了。让你批斗这些反动派,你却胡说八道。”
张兴富委屈地走下台,小声嘟囔道:“我说的可都是实话。”
另一位老农又走上前台,开始揭露我爷爷当国民党地方官的反动罪行。
就在这时,我家的黑虎和屈书记家的红狼突然咆哮着冲进了了主席台前的场子中间。屈书记家的老七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他常带那只红毛狗来学校上课,有一次,老师让他把狗送走,他竟然让红狼去咬老师,从此老师再不管他,他也就天天带红毛狗到学校。他对学生们说:“这是我家的红狼,你们以后只能称它红狼。”因此,我早认识了红狼。
主席台原来是祠堂用来演戏的台子,台前原来是一个大场子,是观众听戏的地方。广场周围,大树环绕,来听会的社员就坐在树下乘凉。广场前除我爷爷、我老爸等十个挂牌者外,更无一人,几百平方米的场子上,被火热的太阳照耀着,光秃秃的,这时突然窜进两狗,这才显示出空白场子的生气来。
红狼全身通红,养得膘肥体壮。我家的黑虎全身通黑,长得体大腰圆。黑虎和红狼是撕咬着跑到这个地方的。春暖花开的季节,正是公狗母狗的发情期。黑虎与红狼起初的咬斗,原是为了争夺交配的权力。两雄相斗,必有雌犬在旁处静观,更有败者在雌犬周围等待。果然,我扭头一看,在场子的边上,还有十数只雄犬和一只白色的雌犬。那里的雄犬都垂着尾巴,表明它们已承认失败。而白色的雌犬对这群雄犬不理不睬。我细看那只白犬,认出它是我同学小林家的,小林叫它小白。显然,小白在等待最后的胜利者。
黑虎已和红狼咬斗起来。我暗中为黑虎加劲,狠狠咬啊,咬死那只杂种!我看到我家的黑虎表现出强悍的精神,把红狼咬得嗷嗷怪叫。这时,只见社员们都伸长脖子,兴奋地观看两只猛犬的撕咬。有不少年轻者,还吼叫起来,再没人听老农的批判。
红狼虽然肥壮,却没我家黑虎矫捷,一不小心,被我家黑虎咬住脖子,扑到地下。支部书记坐在高台之上,早看到了这一幕。他一招手,民兵连长就带了两个民兵挥着木棒赶来。黑虎一见这形势,丢下红狼,走到十多米处的小白身边。小白立即迎上来,用嘴舔起黑虎身上的伤痕,极尽献媚之态。
红狼哀嚎着逃到台上屈书记脚下,呜呜地叫着。屈书记一脚踢开,走到话筒前,骂道:“妈个巴子,连国民党家养的狗也成反革命分子啦!”
台下社员以及全校师生,都哈哈大笑起来。会场立即乱了套。
屈书记喝道:“笑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老国民党家养的狗,为什么是黑色的?知道吗?解放前,国民党的警察,都穿着黑皮!不就是黑狗子嘛!老国民党家为什么要养黑狗?是在盼望黑狗子们回来变天啊,让天变黑啊!我家为什么要养红狗?就是我们喜欢红太阳,拥护红色政权。红色政权,就是我们共产党的政权。黑色政权,就是国民党的政权!”
我心中说:全大队家家都养黑猪,是不是都黑了心,都想拥护国民党!
屈书记越说越激动,最后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反动派!”我看到台下所有的社员都举起了手,随着他的声音在动嘴唇。只有一部分人声音特别响亮,而多数人发出来的声音,像是蚊子在嗡嗡。
屈书记呼罢口号,还不过瘾,握紧话筒,喝道:“我宣布,大队民兵连长立即带领二十个民兵,把国民党反动派家的黑狗活捉到会场,进行批斗!”
民兵连长得令,立即选派二十名民兵,身边有现成的绳索木棍,是随时捆人打人用的。二十个民兵各持绳索木棍,乐呵呵地迈开大步,要捉我家的黑虎。
这时候,黑虎还在会场边和小白耳鬓厮磨,并未交配。忽见多人不怀好意,冲它而来,立即露出锋利的牙齿,以示警告。
我看到黑虎没有一点逃跑的打算,心里十分着急,这时还不逃跑,不是自寻死路?黑虎,跑啊,快跑啊!
二十多个民兵已把黑虎和小白围了起来。
黑虎似乎感觉到了危险。不过小白却依然舔着黑虎身上的伤口,两只家犬深情地表达着它们的感情,对面前的人类毫不在乎,并未把世人当成它们谈情说爱的灯泡。就在这时,一条绳索忽地抛了过来。
是带着活圈的长绳。只要被套中,逃无可逃!
黑虎本能地跳开了数尺。
绳索没套住黑虎,却套住小白的脖子。
套小白的是我们村的大雷。大雷才二十出头,外号雷轰,领导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民兵连长说:“雷轰,这只白狗也不是好东西,别放了。”大雷于是就拉紧绳索。就在这时,小白的女主人、小林的老娘吴春花出现了。吴春花体高臀圆,她手持一只还带着针线的鞋底子,从树下跑出来,两只大乳房左右摇摆着:“雷轰,给我放了!这是我家的小白,你认不认识?” 大雷说:“连长说了,不让放。要放,你去问连长,和我没关系!”
吴春花骂道:“放你娘的狗屎屁。老娘的狗,你套的,你敢不放!”
上去就夺绳子,大雷却不给。吴春花大怒,一鞋底拍过去,只听“啪”的一声,大雷被拍了一个趔趄。吴春花一把抢过绳索,一边放狗,一边骂:“操你妈的,老娘家的母狗要搞皮判,碍着你了?想看搞皮判,回家看你爹妈搞!”大雷虽雷,遇到猛女,挨了打竟不敢吱声了。我心中很高兴。后来我听我老爸说,吴春花生了七个儿子,七个儿子中,五个已长大成人,个个膀大腰圆,把吴春花的肥硕优点全都继承下来。雷轰平时天不怕地不怕,连父母也敢打,却怕吴春花的五个儿子。因此,他被吴春花打了,竟然不敢还手。
民兵连长喝道:“吴春花,太不像话了。”屈书记也吼道:“反了,反了!”
吴春花骂道:“你们算个毬!老娘五代贫下中农,你敢咋的老娘!”边骂边把小白脖子上的绳索解开,扔在地上:“小白,我们回家去。”小白摆着尾巴跟在主人后面离开会场。屈书记和民兵连长竟然没有话说。吴春花的堂哥在县里当官,她当然不怕屈书记和民兵连长啦。
小白走了,黑虎也想逃走,但是,为时已晚。民兵连长下令关闭了学校的前后两道大门。二十多个民兵前后左右追赶起黑虎。
黑虎刚逃到大门口,就被守门的四个民兵用木棒打了回来。
几百社员看着几十个民兵追赶我家的黑虎,不时发出“啊”、“啊”的呼叫。黑虎沿院墙转了数圈,一不小心,被民兵连长用绳索套住了脖子。民兵连长等人把黑虎拉到了主席台前。
屈书记大为高兴,命令把黑虎拴在台前一桌子腿边,清清嗓子,对着话筒喝道:“我宣布,现在开始批斗这只反革命黑狗!”
只见几个民兵拿起棍子,朝黑虎身子打去,黑虎被打得大声惨叫。我的心也随着它的惨叫而阵阵惨痛。
屈书记召唤民兵连长耳语一番,民兵连长笑逐颜开,向后屋走去,一会儿,掂着一把长柄砍刀出来。
屈书记又操起话筒:“现在,我宣布,判处反革命黑狗刀劈之刑。”
就在这时,只听一声巨吼:“住手!”
在台上接受批斗的我老爸,突然冲到民兵连长身边,一把夺过砍刀。民兵连长以为我老爸要砍他,转身就逃。屈书记也慌不择路,踏翻了椅子,向后屋逃去。
我老爸哈哈大笑,用砍刀斩断黑虎身上的绳索,带着黑虎径直走到前门,开了门,黑虎一溜烟逃出校园。
我老爸转过身,回到批斗场,把砍刀放在桌上,然后转身站在我爷爷身边。
全场鸦雀无声。
当我老爸重新放下砍刀之后,屈书记这才缓过神来,立即喝道:“把国民党黑崽子给我拴起来!”
民兵连长和三个民兵一拥而上,把我老爸五花大绑起来。
屈书记大声道:“广大社员同志们,你们看到没有,国民党亡我之心不死。刚才这个反革命是想谋杀我们革命干部哪!只是慑于我们干革命的威力,才放弃了!”
接下来,我老爸被民兵连长几人用木棍狠狠打了三十二棍。这是我数下的。
批斗会结束的第二天,民兵连长就带了十多个民兵来到我家门口,通知我家:“屈书记说了,你家的狗必须得杀。是你们自己杀还是我们杀?”
这天我老爸去我大姨村找一个老中医治棍伤去了,只有我妈和我在家。我妈总是怕事,就说:“不就是一只狗,死活都由你们,想杀就杀。”
我说:“不行!凭什么杀我家的黑虎!”
我妈说:“唉,人的命都管不了了,还管什么狗啊。”
民兵连长于是把我家大门拴了,用大石头关了狗洞,举起木棒追黑虎。黑虎早认识了这个家伙,眼见他们要打自己,一个跳跃,在院中躲闪。但是院子太小,几个男人追着黑虎,黑虎开始还只是躲避,总是躲避不开,怒从心起,找准一个机会,朝民兵连长的屁股咬去,民兵连长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屁股外裤子上出现一道血印。另一个民兵一不小心,也被黑虎狠咬一口。剩余的两个民兵再不敢紧追,黑虎瞄准机会,跳上花坛,再一纵身,翻墙而去。
民兵连长没能打死我家的黑虎,反而被黑虎所伤。屈书记听说后,立刻打电话上报公社,说我们大队出现了一只疯狗,已咬伤群众多人。公社领导下令动用民兵所用步枪射杀。
次日,公社派出十名民兵来到我们村,准备射杀黑虎。面对到来的民兵,我老爸敢怒而不敢言,我妈更不让我再说一句话,小声告诉我:“黑虎是死是活,你别管了啊。”
黑虎经过数次大难,早对生人产生了警惕。尤其看到民兵打扮者,更是怒目而视。
十个民兵虽然都对着黑虎噼里啪啦开了枪,但是,黑虎却未中一枪,竟然从枪口下逃了出去。民兵们追赶着它,喝声不断,一直追到桐柏山中。
黑虎消失在山林深处。公社所派民兵们扫兴而归。
屈书记以为公社派来的民兵可以打死黑虎,没想到派来的十个在村里住了两天,吃了鸡,吞了肉,喝了酒,放了枪,却连一根狗毛也没打着,就撤走了。屈书记对民兵连长道:“靠人不如自己,我们自己组织打狗队,进山打狗。” 没想到打狗队刚刚成立,还没进山,屈书记家的老二竟然在大白天强睡了邻家一位姑娘,被告发逮捕,打狗队也就夭折了。
屈家老二强睡了邻家的姑娘,屈书记根本不在乎这事。因为屈书记本人也强睡过别人家的女人,屁事没有,相好也有好几个。我们班的一个同学,他家和屈书记家相隔不远,他长得很像屈书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位同学应该是屈书记播下的龙种。
逮捕屈家老二上演了一出戏。是公社革委会领导和武装部长合演的。当时县里化肥厂招工,每个大队招一名,当然,招上者就吃商品粮了。这种好事,在我们大队,除了屈书记家,其他家很难得到。屈书记早把屈家老二作为我们大队招工的唯一人选。于是,公社就给屈书记打电话,说是上面已批准了屈家老二的招工名额,让屈家老二到公社报到。屈家老二兴冲冲带着行李到了公社,一进大门,就有两个大汉走过来架起他的胳膊。
第二天中午,我刚从学校回来,老爸就唤我:“给老子打酒去!”把家中仅有的一块钱递到我手中。我问:“要来客了?”老爸哈哈大笑:“没来客就不能喝酒啦!”老妈说:“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一块钱的盐可吃两个月,一块钱的酒喝到肚就没了。”老妈从我手中拿回一块钱,进了屋。老爸笑说:“不喝就不喝。老子今天照样快活。过来,儿子,听我说,屈家老二坐牢了。”又对我妈说:“上天有眼,上天有眼!”
我看到老爸仇恨的眼神中充满了得意。当然,我听了也高兴。
自从儿子坐牢后,屈书记说话的底气再也没以前硬了。屈书记平时最爱开社员大会,一个月至少开一次。但此后将近半年,竟然没开过一次社员大会了。不开社员大会,我爷爷、我老爸就不用挂黑牌被批斗了。这段时间,我老爸脸上常常露出笑容来。我知道老爸为什么高兴,可我却再也高兴不起来了,我老想我的黑虎。
光阴荏苒,两年很快过去了。我在同学们的嘲笑中长高了许多。
屈书记依然是屈书记。屈家老二也从监狱放回来了,这是我老爸完全没有想到的。而让他更没想到的是,被屈家老二强睡的姑娘的父母,托人把姑娘嫁给了屈家老二,从此化仇为亲。屈家老二结婚之时,全大队好多人都参加了他家举办的婚宴。那天,我们班好十多位同学没来上课。等第二天来上课,他们兴高采烈地嚷嚷昨天在屈书记家吃到的美味。
我爷爷依然是老国民党,我老爸依然是中国民党。打屈家老二回来并很快结婚之后,我看到我老爸再难笑过一次了。
我依然被人称作小国民党,同学们依然不跟我玩,我更加孤独了。
可我家再没养犬。
又一个冬天到来了,我们公社好多男男女女都开始进入桐柏山腹地挑炭。桐柏山中的山民们,一到冬天,都会砍伐橡木烧炭,等着山下人去买。山下的人从山上买回木炭,再挑到镇上卖掉,一斤可赚二分钱。这年我九岁了,也随老爸等人一道去挑炭,我一次可挑二十斤,赚四角钱。
清晨,当太阳才升起之时,我们都进入山中,忽然,有人叫道:“快看那,好多狼啊。”
果然,在我们对面五百米处的山洼中,有十多只狼围着一只黑灰色的大狼嬉戏。有人道:“奇怪,竟然还有黑色的狼,这辈子我可是第一次看到。”
挑炭的一行数十人统统驻步不行,大声呦喝。
众狼听到人声,望望人群,很快窜入密林之中。而那只灰黑色的狼,却没有离开。它竟然朝我们走过十多米来。这时男人们都操起了砍刀,敲击手中的扁担,大呼起来。
我感觉它就是我家的黑虎,虽然毛皮有点变化了,但是,它的神态我还认得。我大叫着:“黑虎,黑虎,过来啊!”
可是,没等我继续呼叫,它就冲进了密林。
从此,我再也没见过黑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