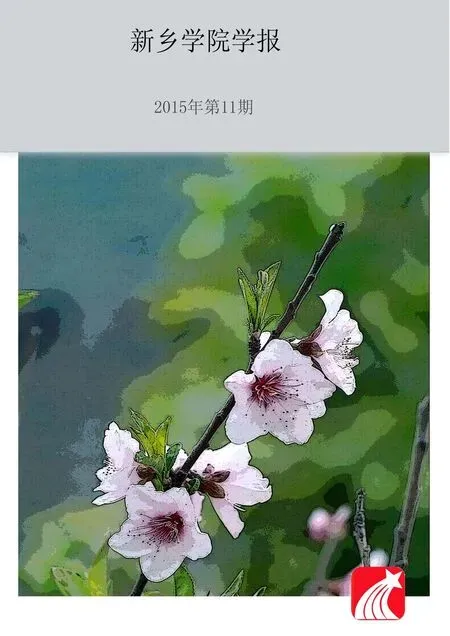狄德罗和莱辛的戏剧表演观之比较
左攀峰
(新乡学院 文学院,河南 新乡453003)
狄德罗(Diderot,1713—1784)和莱辛(Lessing,1729—1781)是同时代人,他们分别是18世纪法国和德国的杰出启蒙运动思想家、美学和文艺理论家、作家。作为启蒙运动思想家,他们都特别重视戏剧这种大众性的艺术,不但创作剧本,而且探索和研究戏剧理论。狄德罗的戏剧理论著作有《关于〈私生子〉的谈话》《论戏剧诗》《演员奇谈》,其表演观集中于《演员奇谈》;莱辛的戏剧理论著作是《汉堡剧评》,其表演观集中于该书前10篇。有人说莱辛的表演观受到狄德罗表演观的影响,其实不然。狄德罗的《演员奇谈》写于晚年,在他死后的1830年才出版;莱辛的《汉堡剧评》写于他受聘担任汉堡民族剧院艺术顾问的1767—1768年间。应该说,他们的表演观是各自具有的,是他们各自独立思考的结果。当然,他们的表演观也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比较他们的表演观,以促进人们对他们的戏剧理论的认识和戏剧表演艺术的发展。
一、表演与美
在《演员奇谈》中,狄德罗说:“你且想一想戏剧里所谓‘真’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表现它们?绝对不是。要这么理解,‘真’就成了普通常见的。那么舞台上的‘真’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里指的是剧中人的行动、言词、面容、声音、动作、姿态与诗人想象中的理想范本保持一致。”[1]264这里,狄德罗明确指出,戏剧的“真”,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表现它们”,而是指“剧中人的行动、言词、面容、声音、姿态与诗人想象中的理想范本保持一致”。狄德罗为何反对戏剧“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表现它们”?第一个原因是,凭感情去表演的演员总是好坏无常,他们的表演没有什么一致性。另一个原因是,凭感情去表演的演员,像现实中受感情支配的人一样,其表情、声音、动作都是丑怪的。狄德罗说:“一个不幸的女人,真正不幸的女人的痛哭流涕并不能打动你……当人感情冲动到极点的时候,几乎都要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怪相 。”[1]264-265还有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是 ,凭 感 情 去 表 演 的 演员不能很好地跟其他演员相互配合。狄德罗认为,戏剧表现的整体美要靠演员的相互配合与合作。例如,针对街头发生的一桩惨祸,狄德罗说:“倘若艺术家要把这个场面搬上舞台或者画布,他必将在其中引入一种巧妙的配合。街头自然发生的场面经得起与这种由和谐产生的场面的比较吗?如果你认为前者比后者毫不逊色,那么我要问你,人们赞不绝口的艺术魔力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1]266这里,狄德罗强调戏剧的“巧妙的配合”,重视由此而产生的“和谐”,并且认为它是艺术魅力之所在。纵观上述可以看出,在戏剧表演中,狄德罗既反对主观真实的自然表现(即动真情),也反对客观真实的自然再现(如照搬街头惨祸),原因在于它们与戏剧的“真”相违背,而这种“真”,其实就是指戏剧表演的美。狄德罗说:“一部悲剧只是一页美丽的历史。”[1]286所以,狄德罗是以美作为戏剧表演的原则的。
在《拉奥孔》中,莱辛认为,美是造型艺术如雕刻、绘画的最高法律,它避免表现因激情而导致的表情和形体的丑。莱辛说:“有一些激情和激情的深浅程度如果表现在面孔上,就要通过对原形进行极丑陋的歪曲,使整个身体处在一种非常激动的状态,因而失去原来平静状态中所有的那些美的线条。”[2]19所以,造型艺术对于这种激情或是完全避免,或是加以冲淡。在莱辛看来,戏剧由于是通过演员表演所刻画出来的生动图画,就必须更严格地服从造型艺术的法律。他以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菲罗克忒忒斯》为例说道:“从演员身上我们不只是假想在看到和听到一位哀号的菲罗克忒忒斯,而是确实看到和听到他哀号。在这方面演员愈妙肖自然,我们看起来就愈不顺眼,听起来就愈不顺耳,因为在自然(现实生活)中,表现痛苦的狂号狂叫对于视觉和听觉本来是会引起反感的。”[2]29
在《汉堡剧评》中,莱辛承袭并发展了他在《拉奥孔》中的对戏剧表演的看法。他说:“演员的艺术,在这里是一种处于造型艺术和诗歌之间的艺术。作为被观赏的绘画,美必须是它的最高法则;但是作为迅速变幻的绘画,它不需要总是让自己的姿势保持静穆,静穆是古代艺术作品感动人的特点。它可以而且必须常常带有那种坦佩斯塔式的村野粗俗,那种白尔尼尼式的胆大妄为;在表演艺术中演员所表现的一切,都不应该带有令人耳目不悦的东西,造型艺术则是通过静态做到这一点的……绝不可让演员所表现的东西,像作家在创作时表现的那样强烈。这种表演是直接让我们用眼睛来理解的诗歌。”[3]30这里,莱辛虽然承认戏剧表演可以带有“村野粗俗”“胆大妄为”之类,但是他强调“在表演艺术中演员所表现的一切,都不应该带有令人耳目不悦的东西”,还强调“绝不可让演员所表现的东西,像作家在创作时表现的那样强烈”。因为,“作为被观赏的绘画,美必须是它的最高法则”。
二、表演与感情
如前所述,在《演员奇谈》中,狄德罗为戏剧表演的美而反对演员凭感情去表演。实际上,狄德罗是主张演员绝对地排除感情而只凭理智去表演的。他说:“易动感情不是伟大天才的长处……一遇到预料之外的情况,易动感情的人就会失去理智。这种人不能做明君、贤臣、良将、辩才无碍的律师、妙手回春的医生。你可以让这些爱哭鼻子的人坐满剧场,可是千万不要让他们中间的任何一 个 登 上 舞 台。”[1]258-259狄 德 罗 还 以 感 情为尺度把演员分为三类,并拿不动感情的演员跟虚情假意的人相比。他说:“极易动感情的是平庸的演员;不怎么动感情的是为数众多的坏演员;唯有绝对不动感情,才能造就伟大的演员……演员的哭泣好比一个不信上帝的神甫在宣讲耶稣受难;又好比一个好色之徒为引诱一个女人,虽不爱她却对她下跪;还能比做一个乞丐在街上或教堂门口辱骂你,因为他无望打动你的怜悯心;或者比做一个娼妓,她晕倒在你的怀抱里,其实毫无真情实感。”[1]261
在《汉堡剧评》中,莱辛并不像狄德罗那样要演员绝对排除感情。他说:“关于一个演员的热情是否太多,往往争论得很厉害……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热情’这个词。如果说嘶喊和做怪相就是热情,那么演员的热情可能表演得过分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说热情就是敏捷与活泼,而演员身体的各部分都借此使他的表演具有真实感,那么我们绝对不愿意看见这种真实感被过分地夸张成为幻想,即使演员可以运用许多我们所理解的这种激情。莎士比亚所要求的在热情的激流、雷雨和旋风中加以节制的,绝不可能是这种热情。他所说的一定只是那种激烈的声音和动作。为什么在作家未感觉需要丝毫节制的地方,演员在两方面都必须加以节制,其原因是不难想象的。声嘶力竭的叫喊,无不令人觉得厌恶;过于匆促、过于激烈的动作,很少给人以高尚之感。总而言之,既不应该让我们视之刺目,又不应该让我们听之刺耳;在表达激烈的热情时,只有避免一切引人不愉快的东西,这种激动的热情才能给人以强烈的印象。”[3]29-30这里,莱辛区分出两种“热情”,其实是“热情”的两种外在表现:一种是“嘶喊和做怪相”,另一种是“敏捷与活泼”。前者是由于热情的过分而导致的,应该加以避免;后者,揣摩莱辛的意思,应该是适度的热情之外在表现,它使演员的表演具有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感可能被“激情”过分地夸张成为幻想。接着,莱辛用戏剧表演的美来解释为什么作家可以不节制感情,而演员必须节制感情。可以看出,莱辛并不反对演员在表演时动感情,像狄德罗那样,他只是反对演员因“热情”而导致嘶喊和做怪相,让观众感到不愉快。换言之,他只是反对演员因“热情”而破坏戏剧表演的美,让观众感到不愉快。
三、感情与标志
狄德罗反对演员表演时动感情。那么,演员凭什么打动观众呢?狄德罗认为是凭表演感情的外在标志(笔者按:感情的外在标志包括表情。关于表情,狄德罗在《画论》中说:“一般说来,表情就是情感的形象。一个不懂绘画的演员是一个蹩脚的演员,一个不懂看相的画家是一个蹩脚的画家。”[1]330)。演员通过模仿、练习将这些外在标志谙熟于心,演出时把它们准确地表演出来就行了。狄德罗说:“他(笔者按:指演员)的全部才能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在于易动感情,而在于毫厘不爽地表现感情的外在标志,使你信以为真……他嗓音发抖,欲言又止,压低或者拖长腔调,四肢颤动,双膝摇晃,有时昏晕过去,有时暴跳如雷:所有这些纯属模仿,都是事先记录下来的功课,虽然做作却悲怆动人,尽管虚假却达到崇高的境界。”[1]260因此,在狄德罗看来,“最伟大的演员就是最熟悉这些外在标志,并且根据塑造得最好的范本最完善地把这些外在标志扮演出来的演员”[1]295。他以当时英国著名演员嘉里克为例,来说明伟大的演员在表演中不动感情,而只表演情感的外在标志:“嘉里克从两扇门之间探出脑袋,不到5秒钟的功夫,他的脸部表情先是大喜欲狂,然后是有节制的喜悦,然后是平静,再从平静到惊奇,从惊奇到大惊,从大惊到忧郁,从忧郁到沮丧,从沮丧到恐惧,从恐惧到恐怖,从恐怖到绝望,最后从绝望又回到开始时候的表情。难道他的灵魂果真感受到这些情绪,并且与脸部肌肉合作奏出这一整套音节?我不相信,你也不这么认为。”[1]274他还说:“我们不是常听说某人很会做戏吗?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此人感情很丰富,相反是说他即便毫无感受,也善于装出动了感情的样子。”[1]313
在《汉堡剧评》第3篇,莱辛说道:“感情通常是一个演员才能的最容易引起争执的因素。在它存在的地方,人们却往往看不出来;在人们自以为看出它来的地方,却又不存在。因为感情是某种内在的东西,我们只能凭它的表面特征来判断……演员可能有某种面部造型、某种表情和某种声韵,使我们联想起与他目前所表达和表现的能力、热情、思想完全不同。这样纵然他感受得再深,我们也不会相信他,因为他是自相矛盾的。相反,另外一个人……他能够借助一切表演哑剧所必需的才能,做到高度成功的表演,使我们感到他对自己(不是根据原样,而是按照某个好的范例)扮演的这些角色,似乎有着十分深刻的感受。其实呢,他说和他做的一切,都无非是机械的摹仿。毫无疑问,虽然后者的表演是无动于衷的、冷淡的,但在舞台上却远比前者有用。”[3]17可以看出,莱辛认识到感情或感受与其外在标志的矛盾,并且认为没有什么感受而能成功地表演这种感受的外在标志的演员,远比尽管有着十分深刻的感受却不能表演这种感受的外在标志的演员有用。
莱辛还认为,灵魂的变化引起身体发生某种改变,而身体的改变反过来又影响灵魂的变化。因此,当一个演员准确地表演感情的外在标志时,他心里会产生相似的感情[3]17-18。
四、范本与创造
在《演员奇谈》开头部分,狄德罗说:“在行文最明白、最确切、最有力的作家笔下,文字也不过是,而且只能是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感情、一种念头的近似符号,而这种符号的意义需要动作、姿势、语调、脸部表情、眼神和特定的环境来补充。”[1]253这里,狄德罗谈到演员的创造作用,即作家笔下的文字符号的意义,需要演员用动作、姿势、语调、脸部表情、眼神来“补充”。狄德罗对演员的创造作用的认识,还表现于他所提出的“理想范本”。他说:“范本有3种:自然造成的人、诗人塑造的人和演员扮演的人。自然塑造的人比诗人塑造的人小一号,诗人塑造的人又比演员塑造的人小一号,后者是3种范本中最夸大的。演员扮演的人踩着诗人塑造的人的肩膀,他把自己装在一个巨大无比的用柳条编成的人体模型里,而他自己就成了这个模型的灵魂。他操纵起这个模型来甚至能使诗人感到害怕,叫诗人自己认不出这就是他自己塑造的那个范本。”[1]209-210这里,所谓演员扮演的人就是他一再强调的理想范本。他以当时法国著名女演员克莱蓉的表演为例说道:“伏尔泰有一次听到克莱蓉演他写的戏,不由惊呼:‘难道这真是我写的吗?’他这个感叹却有来由。难道克莱蓉对角色了解得比伏尔泰还要多?至少在克莱蓉朗诵台词的这个瞬间,她的理想范本远远超出诗人写作时候的理想范本……她到底有什么才能呢?她的才能在于虚拟一个伟大的幽灵,然后天才地模仿这个幽灵。”[1]284狄德罗关于理想范本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演员的创造作用。
莱辛认为,演员的宝贵的天赋,比如漂亮的身段、迷人的表情、寓意丰富的眼神、兴味盎然的步伐、讨人喜欢的风度、娓娓动听的声调,远远不能满足他的职业的要求。他说:“他(笔者按:指演员)必须处处跟作家一同思想;凡是作家偶然感受到人性的地方,演员都必须替他着想。”[3]4这里,尤其是后半句话,揭示了演员在表演中的创造作用。莱辛也谈到理想范本——他称之为“好的范例”——的问题。他说:“他(笔者按:指演员)能够借助一切表演哑剧所必需的才能,做到高度成功的表演,使我们感到他对自己(不是根据原样,而是按照某个好的范例)扮演的这些角色,似乎有着十分深刻的感受。其实呢,他说和他做的一切,都无非是机械的摹仿。”[3]17这里,莱辛谈到演员不是根据“原样”而是按照“某个好的范例”扮演角色,话虽然比较简略,但同样指出了演员的创造作用。
[1]狄德罗.狄德罗文集[M].王雨,陈基发,编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
[2]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7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
[3]莱辛.汉堡剧评[M].张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