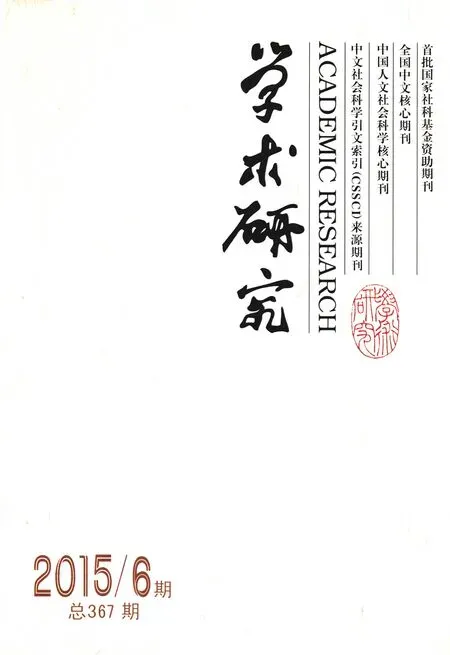清末民初笺扇店与书画市场*
陶小军
清末民初笺扇店与书画市场*
陶小军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清末民初时期,中国书画市场发生了重大变革,在书画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笺扇店,其作用与功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传统的笺扇店经营商品以信笺、扇骨、扇面为主,到此时则转为主要经营书画作品,这种转变使其成为了书画市场中的重要成员。同时,笺扇店的经营模式在不同区域存在着显著差别,北方以北京荣宝斋为例,其选拔制度、经营形式和宣传方式都充满着封建色彩,经营成本较高;南方以上海朵云轩为例,其经营方式、宣传手段则较新颖自由,充满着新兴活力与勃勃生机。这种区别是历史和地域的差异,也是由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我们亦可从清末民初笺扇店之变化中感受时代变迁下的中国书画市场流变。
清末民初 书画市场 笺扇店
一
鸦片战争后,随着封建王朝的逐步解体,与之相适应的封建经济也逐渐瓦解。西方的物质与文化涌入新兴城市,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日新月异,新的生产关系在新文化与新经济的催化下逐步形成。随着经济的发展,清末民初的书画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书画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笺扇店,其作用与功能此时也发生着转变。
笺扇店,在南方称为 “笺扇店”,在北方则多称为 “南纸店”。顾名思义,所经营的商品最初为信笺、宣纸、扇面、扇骨之类,后来逐渐扩展至文房四宝等文化用品。据清人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载:“九日,晴。观书,备讲义。薄午,趋署。昳,上堂讲天文浅义。晡,至施家胡同义善源小坐。又至厂肆,遇妻及两妹,并女师迈达,在荣宝斋购笔研杂物。余亦买笔数枝,先归。观书”,[1]可知在晚清时笺扇店的经营范围早已扩展到文房四宝以及其他文化用品,这使得它几乎成为了集购物雅赏为一体的文化休闲中心,许多文人即便没有购物需求也会去笺扇店闲谈休息,如 《忘山庐日记》即记载孙宝瑄曾往“荣宝斋小坐”,[2]这种环境氛围无疑是极为适合书画艺术品销售的,更何况许多笺扇店的经营者本身就
是技艺高超的书画家,如据 《寒松阁谈艺琐录》载:“李春颿铨,同邑人,工花卉,尤善草虫,体物入微,生动有致。设蕊珠阁笺扇铺”,[3]这是笺扇店兼营书画作品的另一大优势,于是在书画市场日渐扩大的清末民初时期,笺扇店也逐渐成为了代售书画作品的交易场所。
据 《沪游杂记》载:“笺扇铺制备五色笺纸、楹联,各式时樣纨、折扇,颜料、耿绢、雕翎,代乞时人书画”,[4]似乎笺扇店与书画家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笺扇店只是在购买者与书画家之间起着代为介绍的作用而已,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一般来说,笺扇店的经营方式大致可分为普通中介与半雇佣中介两种。普通中介自由性比较大,所占市场比例也较大,这种方式的书画交易是围绕 “笔单”展开的。
笔单即润例,是书画家为鬻艺制定的价格标准,其上标明画家作画的尺寸、种类及价钱,兼具价格表和销售广告的功能。在中国古代,书画家润笔的支付形式比较随意,无论是茶食、器用还是文玩,只要书画家本人同意,都可以用于支付润笔,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鬻艺润笔的支付形式也出现了货币化的倾向。 《骨董琐记全编》转记有一则明人李日华于1629年撰写的 “竹懒书例”润例,其文如下:
凡持扇索书者,必验重金佳骨,即时登薄,明注某日月,编次甲乙,陆续送写,不得前后搀越。每柄为号者取磨墨钱五文,不为号三文。其为号必系士绅及高僧羽客,方许登号,不得以市井凡流,蒙蔽混乞。每遇三六九日辰刻,研墨,量扇多寡,斟酌墨汁,禀请挥写。如乞小字细楷者,收笔墨银一钱,磨墨钱只三文。写就藏贮候发,亦明白登记某日发讫。其有求书卷册,字多者磨墨钱二十文。扁书一具三十文。单条草书每幅五文。纸色不佳,或浇薄渗墨者,不许混送。昔山阴谗口,自笼羽人之鹅;莆阳奢望,竟驱昵友之婢。我悉贷除,以润汝辈。既居橘栗术葛之俦,应修玄楮泓颖之职。恪供乃事,毋横索也。已巳闰月示。[5]
从这则材料看,李日华的润例已使用制钱结算,这为书画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巨大便利。到清初时,书画家戴易将自己的润例 “榜于门,书一幅止受银一钱,人乐购之”,[6]而稍晚的著名书画家郑板桥亦制定了公开润例,叫卖称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7]还说 “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8]润例的形式已臻成熟。清末时书画家将笔单列于笺扇店,使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了解鬻艺价格,购买者可根据自身需要,定制画作的尺寸、题材,并由学徒送至书画家处,后者依据笔单上所标样式创作,如此一来,书画家少去了接待之苦,购买者也多了选择的余地,书画市场的运转效率因此得以提高。
另一种经营方式是半雇佣中介方式,清末民初的笺扇店往往与一些未出名的书画家建立这样的合作方式。笺扇店为这些初出茅庐、生活困顿的书画家提供食宿,并供给绘画所需的笔墨纸砚,书画家 “往往借住在笺扇店里”,[9]为买家作画,笺扇店从中抽取提成。
笺扇店因其自身经营范围的关系,得以与书画家建立起长久的合作关系,因而能获得源源不断的作品。其在书画市场中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书画作品从创作到出售,书画家从初出茅庐到声名显赫,笺扇店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末民初书画交易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两大书画市场,北京和上海两地都开设有大量笺扇店,笺扇店的经营范围、形式、方针各有异同。北京的笺扇店主要集中在琉璃厂附近,较知名者有荣宝斋、清秘阁、秀文斋、懿文斋、静文斋等。[10]上海的笺扇店主要集中 “在外国门左近及庙园”,[11]其中,“洋场以古香室、缦云阁、丽华堂、锦润堂为最。城内以得月楼、飞云阁、老同椿为佳。”[12]在这些笺扇店中,北京之最著名者首推荣宝斋,而上海之最著名者则非朵云轩莫属,笔者就以这两家笺扇店为代表对京沪两地笺扇店的经营面貌作一对比。
二
笺扇店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书画中介机构,它的经营有一定的套路可循,因此即便相隔千里,荣宝斋和朵云轩的经营方式基本依然遵循前文所介绍的笺扇店一般运行规则。但是,从目前为数不多的史料中
可以发现,在具体的实施细节上,二者还是存在地域性差别。北京为多朝都城,封建色彩十分浓厚。在封建统治中心创立的荣宝斋,和京派的画家一样,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十分强烈,从管理到销售的各个环节,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古老的气息。在管理上,荣宝斋采用一套极为严格的员工选拔制度,对外招聘时一开始先要进行面试,继而进行考试,“每人写一篇毛笔字,交一篇作文,看字写得如何,语文水平怎样”,通过者进入试用期,试用期一般为一个月,之后可转为学徒。成为学徒后,店员便进入了荣宝斋的等级编制中,其薪俸与级别密切挂钩。学徒期为三年零一节,每月薪俸只有五毛,出徒后成为正式店员,月薪二元,每干一年增加五毛,加到七元为止,此后再从中提拔掌柜,可以享受人力股分红,数额从三厘到七厘不等。[13]在非营业时间,店员不能在外自由活动,只能在店内习字学画,至于嫖赌之类的恶习,更是一概禁绝。[14]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发现,员工薪俸的高低与他的业绩是没有关系的,而完全取决于在荣宝斋工作时间的长短,且日常行为受到传统观念的极大制约。这种以资历论级别的逻辑和以文明道德来规范下级私人行为的规定显然是受到了封建家长制度的影响,而用类似科举的考试制度来决定任用,则更是表现出传统文化行业对于旧时代的眷恋。这样的管理制度,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并不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反倒容易使员工产生消极度日的懒惰心理,不利于发掘与提拔真正有才能之士。
荣宝斋在经营方针上也是如此。在北京,知名笺扇店总是坚持着传统的服务理念。由于封建时期等级制度严明,笺扇店作为商业店铺,处于社会的底层,而光顾笺扇店的顾客,多为豪绅地主,地位等级显赫。习惯了以往等级分明的交流方式,荣宝斋在日常的经营中极力放低自己姿态与顾客或书画家沟通。不论是在总店,还是在分店站柜台,不论顾客买不买东西,只要走进门来,店员就得赶快笑脸相迎地说请坐、让茶。在请坐、让茶的时候,得一口一个 “您”字,如果要是一疏忽,露出一个 “你”字来,让掌柜的听见了,那是要训话的……进荣宝斋,买不买东西,都要主动同顾客交谈介绍商品,并与顾客交朋友,所以当店员知识要丰富,使顾客感到你有水平、对人热情,虽然多花点钱也愿意到你这里找你买东西……有时来了身份高的顾客还要掌柜亲自出面接待。[15]
从迎宾到让座让茶,再到积极逢迎、交谈,荣宝斋都体现出交流的殷勤。尽管待客有礼是中国商人历来遵循的原则,但像荣宝斋这样有着具体严格的规定,并且细化到要为客人端茶倒水的地步的店铺,恐怕还是不多。由于笺扇纸品种类繁多,顾客上门之后往往顾此失彼,不能尽得所需之物,于是荣宝斋总是在一定的周期后主动上门请熟客列出购买清单,如据 《忘山庐日记》载:“久之,厂肆荣宝斋有人来,因将所欲购笔墨纸札及另杂等件列单,嘱其翼日携至”,[16]其所描绘的正是荣宝斋员工上门取单的情况。而事实上,不仅仅是普通店员,当遇到知名人物时即便是作为总掌柜的王仁山也会极力地放低姿态与之沟通。如张大千 “为使自己的画流传久远,宁可多花些钱,也要买些经久不变的颜料作画”,王仁山知道此事后 “便在北京请师傅精心为他研制朱砂、石青、石绿等颜料,只要自己能抽出时间,尽量亲自送到大千先生手里,实在抽不出时间了,大千又等着用,才派小伙计或别人送去”。[17]客观地讲,这种放低姿态的交往方式的确收到了不错效果,张大千在这样的交往中,形成了对荣宝斋绝对的信赖,对他们的要求尽量满足,在业务上也是尽量光顾荣宝斋。此后 “只要荣宝斋的主人,不管是大掌柜的、二掌柜的、三掌柜的,甚至伙计,只要找到大千先生,说明荣宝斋需要大千先生的画,大千会二话不说,挥毫即画”。[18]在选择装裱服务时,只要在北京,张大千也一定会选择荣宝斋,“别的装裱店是没有资格为他装裱字画的。”[19]这种销售习惯的形成和成功背后有深厚的封建传统文化积淀,彬彬有礼的姿态使顾客与画家都体会到了尊重,尽心尽责的服务宗旨则使笺扇店的顾客、画家感受到被服务的满意。这样的经营方针,使得荣宝斋成为了北京书画交易的龙头店铺。
除此之外,在销售广告上,北京的笺扇店也有颇多有趣的传统,如 “窗档画”便是其中一例:
每到过春节的时候,从年三十晚上开始到正月初五,琉璃厂的古玩铺、南纸店、旧书店等,都关门放假。在这个期间里,都提前组织画家们画窗档画,由于有一种竞赛的性质,所以画家们都很用心来画,与一般商品画不同对待,都想拿出自己最高水平的画来挂在玻璃窗里边,从大街上透过
玻璃窗往里看,可以清楚地看到挂的画,这叫挂窗档……荣宝斋有十几个玻璃窗对着大街,全都在里边挂起了最有名的画家 (如张大千、齐白石、溥心畬等)最新的名作,供来往行人观看购买。在全琉璃厂,荣宝斋的 “窗档”最好,最吸引人。有的铺子不服气,也和荣宝斋比着做,可不管怎么努力,总比不过荣宝斋……荣宝斋为了气他们,到了正月十五、十六两天,还要再换一次更吸引人的 “窗档”。[20]
这种有趣的广告方式,很可能是从北方春节贴窗花、挂墙画的民俗习惯中发展而来。从荣宝斋对“窗档画”不惜工本、热心、执着的态度来看,这种特殊的广告在北京书画市场的宣传效果应该是相当优秀的。这样的效果,使得同行笺扇店都争相效仿,以至于形成了笺扇店贴窗档的习惯。当然,恐怕也只有在拥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北京,我们才能看到这种宣传方式。
三
上海在鸦片战争后发展迅速,成为新兴的大都市,一时间聚集了国内外众多富商贵胄,民众的鉴赏能力与经济能力都十分出众,书画市场在清末民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北京相比,上海的书画市场发展程度要高很多,经济效益也更为出众。当荣宝斋在上海开设分店一年之后,王仁山惊奇地看到上海分店的经济效益竟然数倍于总店,以致于来往顾客迎接不暇,不得不加租一二层小楼以供商用,[21]这正是上海与北京整体商业环境差距的体现。上海的笺扇店拥有大批的顾客群,而且社会氛围更加活跃,市场充满了新兴元素,日新月异的思想也使人们很早就跳开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因此,笺扇店不需要为日常的经营行为做太多规定,店员的经营形式非常活跃,只要能招徕顾客,也不必花大成本做费力的广告,就能获得不错的收益。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笺扇店,上海笺扇店经营者的眼光更长远,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强,他们抛弃了传统思想,在新思想的氛围中开拓了属于自己的经营方式,这种方式更加活泼,更加新颖。这些优秀的商业品质使他们在日常经营之外总结出一套体系化的培养职业书画家的方法,使他们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以朵云轩为例,包括张大千、赵子云等一大批优秀的书画名家,正是在其培养下成名于世的。
在与书画家的交往中,上海的笺扇店也不拘泥于传统,开创了更多双赢互利的形式。前文已经提到,半雇佣式的中介方式是传统笺扇店的经营方式之一,这种经营方式虽然给予了无名书画家一定的机会,却也同时限制了他们发展的后续动力。受助于笺扇店的书画家,由于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便会减弱创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作品的艺术水平也很可能停滞不前。因此,无论对于书画家自身还是笺扇店,半雇佣式的中介方式可希冀的利益都十分有限。朵云轩经理孙吉甫深谙此道理,当面对一些较有才华的无名书画家时,他并不像前人一样,将之纳入自己的笺扇店进行创作,而是在不限制书画家自由的情况下竭力给予其帮助。如赵子云初到上海时,孙吉甫就热心地为其招徕生意,以供其立足之需。[22]而当面对像张大千这样尤为难得的艺术奇才时,他更是不惜动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将其介绍给沪上著名书法大家曾农髯为徒,[23]为日后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情感基础。这一方面为无名书画家站稳脚跟、自给自足提供了门路,并且由于身份自由,书画家的创作能力不会被局限;另一方面,心理上的感激会使得书画家与笺扇店之间建立起无形的联系,这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盈利不亚于半雇佣式的中介方式。
当然,仅仅是帮助无名书画家在上海站稳脚跟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尽快让他们成为能为自己带来丰厚利润的著名书画家,朵云轩在日常宣传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一种新的销售活动,那便是美术展览。美术展览是清末民初新兴的一种书画交流模式,从博览会发展而来,首先在上海、杭州等新兴都市兴起,常利用同乡会、商场等地作为展览场地,参与者有单人与多人之分。在众多的销售方式中,美术展览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最大,因此是无名书画家一夜成名的最理想选择。
朵云轩常常积极地充当各类书画展览的推荐者,这一策略毫无疑问是颇有见地的,“在与朵云轩交往的著名书画家中,有不少画家就是依靠朵云轩办的画展出了名的”,而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张大千,“1925年他在上海宁波同乡会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展品百幅,全部售完,自此以后,他以卖画为生。
可以说他的卖画生涯是从上海开始的,而其中朵云轩又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24]很明显,朵云轩所采用的快速培养知名画家的方法是一种 “双赢”策略,正是由于这种对待书画家和书画市场的主动态度,使它赢得了许多书画家的尊敬和青睐。
在与书画家的交往过程中,朵云轩的经理孙吉甫总是以艺友的身份出现,他在朵云轩楼上开昆曲社,常邀同样嗜好昆曲的书画家好友们汇聚一堂,唱曲论艺,饮酒挥毫。[25]这种与书画家建立关系的方式,与荣宝斋所坚持的方法又是完全不同的了。朵云轩以一种平等的方式与书画家相处,与之建立朋友关系,这种交流方式使笺扇店与顾客之间多了一份情谊,少了一份铜臭,从长远角度来看,无疑是非常理想的经营方式。而荣宝斋则以一种谦卑的态度与书画家相处,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将自己放在服务者的位置上,这种经营理念上的差异,与二者所处文化环境的差异无疑是相关的。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的观点可以被归纳为如下内容:传统笺扇店主要经营笺扇,兼带销售书画作品,但到清末民初时,经营书画作品变成了大多数笺扇店的主要职能。从地域上看,南北方的笺扇店经营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北方以北京荣宝斋为例,其经营方式有着浓厚的封建色彩,例如,用考试作文的方式选拔职员,不看业绩只凭任职年限给予升迁的管理模式。卑躬屈膝、殷勤备至的服务理念,以及不惜工本的宣传方式,不仅无法鼓励职员的营销积极性,而且经营成本较高。南方则以上海朵云轩为例,其经营方式较自由,例如,职员工作形式自由,与书画家建立深厚的友谊关系,摒弃半雇佣式中介方式,采用书画展览的形式来经营书画家。这些新兴的经营和管理方式,使得上海的笺扇店盈利丰厚,充满着勃勃生机。
[1][2][16]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23,948、981,940页。
[3]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80页。
[4]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5]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15页。
[6]潘耒:《隧初堂集·戴南枝传》,亦见孙静庵 《明遗民录》,卷43《戴易》。
[7][8]郑燮:《板桥润格》,《郑板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84、184页。
[9]钱化佛:《三十年来之上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第25页。
[10]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页。
[11][12]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06、76页。
[13][14][15][17][18][19][20][21]郑理:《荣宝斋三百年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第42、41、64、68、86、68、46、58页。
[22][25]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7、79页。
[23][24]严慈:《朵云轩》,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责任编辑:张 超
F719
A
1000-7326(2015)06-0086-0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近现代书画市场发展史”(14BA011)、国家民委关于民族问题研究项目课题“民族民间艺术产业开发研究与对策”(2015-GM-030)、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 “艺术品传播与艺术创造活力研究”(14DH49)的阶段性成果,也是江苏省文艺产业研究基地成果。
陶小军,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在站博士后,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副研究员 (江苏 南京,21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