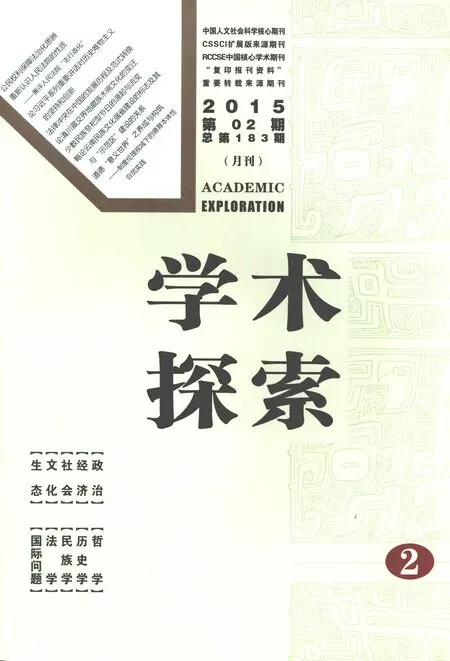道德“意义世界”之养成与构筑
——制度伦理视域下的德育本体性自觉实践
李 晔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道德“意义世界”之养成与构筑
——制度伦理视域下的德育本体性自觉实践
李 晔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德育实践是一个朝着原始而纯粹的道德“意义世界”的“真”“善”“美”而踯躅前行,守护人对幸福生活美好期待和向往的漫漫征程。公民道德“意义世界”的养成与构筑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且不断面临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观照于道德“事实世界”,道德“意义世界”更加纯粹而稳定,蕴涵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和希望。有着科学合理的制度伦理价值纬度的现代化德育实践,因饱含着对人的生存活动的现象实情的强烈关切,以大无畏的勇毅气度承担了对人的道德“意义世界”的形塑和再造,持守最美好的道德“真”“善”“美”,能够丰富和坚定人的思想和精神世界,缓冲和降低人的生存压力,提升人不断追寻幸福、获得幸福的精神和能力。
德育实践;主体自觉;制度规约
道德“意义世界”并不纯全是概念的和逻辑的,也不是完全脱离社会现实,毫无意义的“理想空场”。相比于道德“事实世界”,道德“意义世界”更加纯粹而稳定,蕴涵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和希望。
一
道德“意义世界”蕴含的真诚,善良,勇毅,互助,坚强等精神修养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懈追求的内心力量。人之义务,理应卑以自牧,修身养性。而经济社会条件有限,人们仍于生活中苦苦追寻俗世的适得其所与飞黄腾达,或忍受匮乏,或达成所愿。人们需要越来越强大的精神力量去面对拥挤的生活和思绪,进一步领受和体味广大的生活,形成对生命和成长沉静而深邃的颖悟,追寻内心的宁静和幸福。这种颖悟源于人之本性对善、对美、对真理的怀想和向往,也源于对道德意义世界的探寻、构建和确证。旨在对生命更彻底的尊重和对道德“意义世界”的全面坚守,道德教育是生动鲜活、含义丰富的。她的价值理应体现在生活中。人的感性生活的纷繁复杂和日常生活的自在性为有价值的道德教育实践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道德教育也无法等同于生活本身,这种思想技艺的志趣源于现实生活,高于现实生活,为生活意义的取获提供精神性的价值支撑,使每一代人的精神动能薪火相传下去的时候,都能踵事增华,使人们更贴近原初信仰的精神家园。这就是道德教育存在的价值。存在需要行之有效的实践践履予以负责任的证明,目前看来,教育仍是一种有效的工具性手段。柏拉图说,教化的本质在于面向个人灵魂的内在的和谐的形成。[1](P77~82)有效的道德教育是人不断进行自我提升、自我解放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努力的主体性活动过程,能够提高人对本体的自我认识,自我管理和自我革新的能力。当然,任何道德教育过程都需要经过主体本身对思想和精神进行重组和建构,以主体自觉的精神再生产推动德育内容转化为自身的品行和德行,内化为人的感情、意志和信念,外在为人追求幸福生活的行为和举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变迁,原有单纯的精神动员已无法克服人的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现状的矛盾,旧的价值秩序已被打破,新的秩序尚在建立的过程中。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较之以往时代无法比拟的物质进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网络、媒介、信息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迅速加大,工具理性张扬,价值理性式微。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巨大的物质资源和生活便利中,成为工具理性人,经济实力人,甚至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暇向往彼岸世界,失去了情感体验和共情的能力。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2](P61)人的生活是需要尊严和意义的,有效的道德教育能够开辟出一条洞察感性生活秘密的运思路向,向幸福致敬,为人回归精神上的彼岸家园提供真实而有力量的思想支撑。
德育实践在风云际会的时代变迁和人们不断被唤醒主体自觉的文化生态背景下持续坚守其存在意义与价值。但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普泛化使传统的德育实践失去了往昔的社会功能,以至难以存在,或者至多只在日常生活中还具有某种极其微弱的意义。学校德育被一种知识论的德育范式所统摄,人被淹没在技术理性之上的思维范式中,疏离了人的精神家园和生活世界,遗忘了人的情感,使得人性,人的需要,人的生命,人的多样性存在等根本问题被忽视或畸化,缺少应有的生命活力和育人魅力。[3](P1)更为严重的是,社会成员,包括受教育者甚至教育者自身,已经对德育实践表现出信心不足或拒绝认同的态势,人作为教育主体和受教育主体同时感到价值选择和判断的困惑和面对感性生活的疲惫与不轻松。作为一种塑造人、建设人、发展人的社会性教育活动,道德教育凝聚人心和社会方向的保障作用无法显效,这些负面趋向都直接危及德育实践存在和持续发展的基础,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持续拷问德育工作者的智慧。另外,培育德育在多元文化中实现主导的气度和能力,如何在人的感性生活中产生更大的社会辐射力,进而塑造更高层级的现代德育“精神气质”,也是德育工作者在实践中必须创新的问题。
二
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来看,制度作为人们处理社会关系实践的产物,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定社会关系,是一个社会基于权利和义务分配的公共理性而建立的对各种社会关系、各种社会行为方式和各种社会力量进行调整、规范和整合的约束体系。
制度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约束规范或行为模式,无论是自发源起或是自觉制定的,都具有形成公共认可和保证实施的功效。制度在本质上又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的体现,因而具有一种“底线道德”的意义。在传统的德育实践中,思想教育和舆论宣传始终是必须坚持、不可或缺的工具性手段。但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们的道德生活受到多元利益格局、多元文化价值观和多元社会角色的影响和制约,道德心态、道德观念和道德意识日趋多样化、复杂化,仅靠思想教育和舆论宣传进行道德建设、推动社会道德进步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作为人类社会和群体有效运转的组织、指挥、管理和协调的力量,在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对道德“意义世界”的认知得到制度伦理的支持和认可,能够促进自我道德责任与道德义务的统一,使形成普遍的社会道德自觉成为可能。这样,制度伦理就成为沟通道德“意义世界”和道德“现实世界”的桥梁,对制度伦理的遵守也就为每个社会个体从道德认知到道德自觉的转化提供了一种现实实践的路径。
如前所述,道德“意义世界”的确立,自然有德育实践过程中思想教育和舆论宣传的作用。诚然,现阶段道德“意义世界”的确立需要通过思想教育和舆论宣传才能把先进的思想理念灌输到社会成员之中,只有为社会成员自觉理解和接受,才能内化为自我的思想意识,成为个体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信念。但是,要解决道德“意义世界”的合理建构问题,仅停留在低层次号召的层面的思想道德灌输是乏力的,必须从制度伦理的角度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为道德教育提供扬善惩恶的制度支持。同时,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应该以道德关系所反映的各种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得到合理调整、利益矛盾得到有效解决为前提。如果道德“意义世界”与人感性生活中的道德的“事实世界”存在疏离甚至对立,那么道德“意义世界”的合理化建构也就成为不能。由此,苍白乏力的道德教育则是这样一番面目: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利益矛盾,只是以抽象空洞的理性观念和泛理想化的道德尺度来要求一般社会成员,或以超现实的思想道德原则范导社会伦理秩序。那么,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当人们原来普遍习惯的传统道德规范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生态发生改变的时候,原有的德育实践价值基础就会随着人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而发生变移。如果只在思想教育领域就思想论思想、就道德论道德,那么道德“意义世界”的建构就会因为脱离社会现实而变成没有实际价值的“理想空场”。因此,道德“意义世界”的确立既需要通过道德教育来引导道德理性的形成,更需要社会道德实践对道德行为的价值升华。而在各种追求道德“意义世界”的努力中,最基本的道德实践就是对社会各种制度规约的遵守,这就意味着作为社会道德底线的制度伦理是形成道德“意义世界”的理论预设和存在基础。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纠正或克服道德失范,弘扬社会正气,推动社会道德进步,充分发挥制度伦理对约束、调控和导向社会成员遵守道德准则成为人们迈向道德“意义世界”实在的实践旨归和深切想望。
如前所述,道德自觉作为一种无形的、非程序化的意志和精神力量,蕴藏于人的品性、意念和生活态度之中,内化为人的感情、意志和信念,外显为人追求幸福生活的行为和举动。道德自觉首要的应该是人们内心世界的一种思维运动,要以一定道德意识的形成为基础。传统的德育教化总是以理想的人性美德和假定的道德生成路径为前提,向人们传扬道德精神的高尚,却往往忽视现实社会的道德严峻。虽然道德“意义世界”的道德理性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陶冶人的情操,激励和鼓舞人们为实现超现实的理想而奋斗,但它毕竟无法解决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就意味着,只有先验性和想象中的劝导,不可能让每个社会成员都在现实的利益冲突面前保持道德的璀璨荣耀与崇高。另外,由于道德“意义世界”的道德教育是通过宣传手段、树立榜样、营造舆论等非刚性手段和途径来进行的,如若没有人的主观自觉的自我认可和自融自洽,充满美好愿景的道德教化之结果只能是“劝善”而无法有效的“惩恶”。因此,要保证社会道德意识的普遍养成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共同遵守,必须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强化制度的规约,使社会公众内心形成的道德“意义世界”在向道德自觉的行为转化过程中得到制度伦理的坚定支持。
《人文主义:全盘反思》一文中提到,我们遇到了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有着诸多权利和期许,现代人仍然生活在现存的,历史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倔强地保持着它一直以来的那个样子:混杂着起起落落,充满了不完善。[4](P177)可见,人所做的表达自己在生存场域中思想和精神状态的诸多努力,不得不且一定会处在风云际会的时代背景囿限之中。但是,对善、平等、自由、尊严、幸福的执着追寻贯穿着人类历史的始终。但就目前的形势看来,德育实践在理论上的建构和改进与实际的社会进步之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对于德育实践的改铸和再造,意义非比寻常。德育理论的全面璀璨与繁荣并不代表德育实践的态度和效果能持续跟进。若仅限于对概念、信念及理念的深入挖掘和重铸一隅,不可避免地使德育由“身心之学”蜕化为“口耳之学”,失去了作为道德“意义世界”一直向往的精神性心灵性价值。如何使道德“意义世界”以更为直观、更易接受的形象展示于人们面前,避免流于形式,使人们自觉趋于遵从和持守,科学合理的制度伦理价值内核为道德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可以分享的思维资质和伦理预设。尤其是当今社会中,在传统强势的德育实践带来的积极影响的延伸下,人们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感普遍增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身的感性生活倾向于道德“意义世界”的“真”“善”“美”,虽然尚未建制起一个科学合理、合乎逻辑的规范意识体系,但为新质德育实践的酝酿与形成提供了一个机遇优良的因缘和更为贴近道德“意义世界”问题根本的视野。
三
德育实践是一个朝着原始而纯粹的道德“意义世界”的“真”“善”“美”而踯躅前行,守护人对幸福生活美好期待和向往的漫漫征程。公民道德“意义世界”的养成与构筑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并不断面临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有些问题需要倚靠强制性制度发挥刚性干预,有些问题则以人们内心的道德自律自省来软性约束。从制度和道德的关系来看,二者科学合理的内在同质性决定了制度可能介入道德实践领域,规范人们的某些道德行为,共同作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首先,就实现基础而言,制度与道德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同一经济根基上的现实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以及这些活动和关系产生的利益纠缠,调整的是相同社会结构下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这就决定了二者不可避免地在同一经济体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中共同发挥作用,调整人的行为,规范社会关系和人的感性生活秩序。其次,就实际功能而言,二者都以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主体身份出现,对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具有特殊的价值。制度伦理的道德合理性使其在社会成员中逐渐产生共情和认同感,并通过执行机构予以推行,使制度效力更加稳定持久,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及其关系的调节强度明显胜于纯粹的道德规则。而制度化了的道德规范更加明示和客观,也更易于人们遵照和执行。所谓“道穷为尽,道尽必穷,无道无德,无德无路,寸步难行”,道德以感性、充满人情味的方式规定着人们的自省和自律行为,强调社会成员主体自觉地对道德观念予以悦纳和发扬,一经确定则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第三,制度与道德机制互补,相互联系。制度伦理兼收制度与道德所蕴含的志趣和理念,在引导社会朝着符合统治阶级意志方向发展中逐步形成共信的见解,使人们自觉遵循现存的社会秩序。道德作为代表社会成员精神正能量的价值取向,需要严格检审其单纯的精神动员对于现代人的影响,正确认识道德在制度规约中发挥的力量。比如在利益面前一味强调道德的约束,其实是对人性的拷问。正如别尔嘉耶夫在《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中说:“不能指望强者因自己的道德完善而停止对弱者的虐待,不能指望完全依靠人们道德上的完善而导致社会变革。应该依靠改变社会结构的行为来支持弱者。抽象的道德主义用在社会生活上就是伪善,因为它支持的是社会的不公正与恶。社会不是圣徒的社会,而恰好是罪人和不完善的人的社会,不能指望在这样的社会里出现人的完善。”[5](P245)
在制度与道德机制互补、价值共生的关系前提下,道德教育实践具有了明确的意义旨归和运行逻辑。公道、合理的制度安排越来越成为社会成员道德进步的诉求。在这一背景之下,道德教育必须扎根于生动、鲜活、丰富的现实世界和感性生活,明确阐释制度规约视域下的道德规范不容挑战,社会群体合理的权利需要更彻底的尊重和保护。道德教育作为如何育人、如何育“好”人的学问,不是纯粹的知识性建构,不是表面化、外在化、边缘化、单向度的教育,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生产过程,其蕴涵的深厚的人文精神和饱含着的对人的生存实情的尊重和关切是我们研究德育实践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现时代的道德教育呼吁以制度化的形式推行具有普世意义的幸福信念和价值取向,促使社会成员内化为自身的道德情操和意志信念,以坚定勇毅之力推进社会公德建设,为人们进一步追寻幸福的额度和美的生活营造氛围,创造机会。
制度伦理视域下的德育实践应具备惩恶扬善、塑造高尚德行人格和美德禀性的绝对承担。道德辩证法阐明,道德行为对于社会和他人是善的,而对于自己却是恶的。因为“每一则道德都侵犯了自由”,“每一则道德都压抑了欲望”,而且“道德规则所要求的境界越高,对自己的自由和欲望等利益的侵犯就越严重”。也就是说,任何道德的遵守都是一种自我利益的牺牲,是对自我欲望的节制。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经常用道德陶铸自身,反躬自问。那么,道德主体在履行了一定的道德义务后,理应得到相应的回报。罗国杰先生在《道德建设论》一书中指出:“尊重他人的人,应当受人尊重;奉献社会的人,社会应使他有所获得。这是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特殊关系的要求,也是体现道德领域中的一种社会公正。履行义务就应得到公正客观的回报,行善就应得福,这应当成为一条客观普遍的道德法则”,“轻视个人道德权利的给予,只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奉献和义务,少强调或不强调社会对个人的义务,在理论上有缺陷,在现实实践中必然使道德义务的履行陷于不良的循环机制中”。[6](P6)在这种背景下,一个社会普遍的道德自觉就需要依靠制度伦理来维系道德公平的最低限度。因此,在德育实践过程中,应该以制度化的外在形式规定社会成员“从善得福祉,从恶得惩戒”的行为信念,引导个体理性选择最为合理的行为价值取向,在明确的制度安排下的伦理帮助中培养和化育个体的“善”“平等”“自由”等高尚品格和美德。
制度伦理视域下的德育实践应以一种合乎逻辑的、确定性的教育姿态呈现于个体面前。一般说来,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善恶观念、道德原则是比较笼统和抽象的,作为一种道德“意义世界”的价值判断也只能以一种抽象的或超验的逻辑判断存在于人们的思维当中。相反,人们的感性生活却是鲜活的、具体的、实在的。制度伦理视域下的德育实践将道德精神和价值意义平面化,实体化,明确地向生活在该制度中的人明示或默示着德育实践的内容和要求。可见,制度规范的明确性有利于提升人们对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认识和遵守效率,有利于高效率地落实社会成员本应履行的基本道德责任。制度伦理将社会基本道德规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变成在法律上明确的道德行为应当遵守的具体要求,同时按照行业、部门的特点把道德规范和目标化为工作岗位上的具体职责和要求,从工作范围、标准、程度到工作态度、责任、义务都进行细化和量化,让人们便于把握和执行。德育实践通过对各种把抽象的道德原则转化为明确的行动指南的制度规约准确、明确地加以阐扬,使社会公众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的养成得到制度力量的支撑、调整和激励。
制度伦理视域下的德育实践应培育影响和推动社会进一步成熟与进步的“舍我其谁”的自信和魄力。虽然当前德育实践招致着“保守”“退步”“僵硬”等负面判断,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只是德育实践在前进征途中的曲折。首先,制度伦理视域下的德育实践在社会范围内强化了社会道德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的作用,成为建立和发展完善、规范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环,也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需要。其次,德育实践将把提倡和反对、引导和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促进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对营造人更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氛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再次,借助制度规约的稳定性,在德育实践中强化人们遵守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自觉,有利于人们在反复践履的行为过程中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并形成较为稳定的美德禀性。当然,德育实践所肩负的使命是推动个体向善的内心力量更加强大,并形成基本稳定的意识基础,而个体内在意识的形成和化育是一个较为漫长并持续被周围环境影响的过程,德育实践的效果难以在短期内显现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此,新时代的德育实践应带着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和魄力,以推进社会走向成熟和进步的气度胸怀,建构当代思想道德建设的理论追求和现实维度。
蕴含着较高程度道德合理性的制度规约一经形成便具有明确的规范、引导和约束功能,为人们对道德“意义世界”的主体自觉的持存与追寻创造了最大限度的可能,也为德育实践的有效进行赋予了发言权和解释力。在现实的德育实践中,人们业已形成的道德“应当”必须转化为在事实面前能够付诸向善行动的“是”,这种道德行为的自觉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德育实践才能兑现自己的价值承诺,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当然,上述观点并不意味着要将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置于制度规约的监控之下。正如道德对制度的制约一样,制度的执行与实施也会反作用于道德。“彭宇案”审结之后频频出现的老人跌倒众人远观而不敢救助的相关事件,提醒我们需在廓清制度与道德的边界问题上继续反思。
[1]郭凤志.德育的现代困境、归因分析及其超越[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
[2]海伦·杜卡斯.爱因斯坦谈人生[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3]唐汉卫.中外道德教育经典案例评析[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4]三联书店编辑部.人文主义:全盘反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M].张百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6]经纬.制度安排的伦理考量[J].思想战线,2002,(3).
Developm 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M orality“M eaning W orld”——Research on the Noum enon Conscious Practice of M or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Ethics
LIY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710062,Shaanxi,China)
The practice of moral education is a winding progression toward the original and pure morality“meaning world”of“truth”,“goodness”,“beauty”and a long journey to guard people′s expectation and yearning for the happy better life.The culti vation and building of citizens′morality“meaning world”is a longer and more arduous process,in which we have to face and solve new problems continuously.Compared with themorality“facts world”,the“meaning world”is pure and stable.Modern practice ofmoral education,with its own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ystem ethical values,holds deep concern for the conditions of human survival activities,shoulders themission of shaping and re-engineering human beings′morality“meaning world”with undaunted courage and keeps the bestmoral virtues of“truth”,“goodness”and“beauty”.Therefore,it can enrich and strengthen people′s thought and spiritworld,butter and reduce their survival pressure and enhance their courage and capability to pursue happiness.
the practice ofmoral education;subjective consciousness;system restriction
G410
:A
:1006-723X(2015)02-0143-05
〔责任编辑:李 官〕
2013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021)
李 晔,女,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