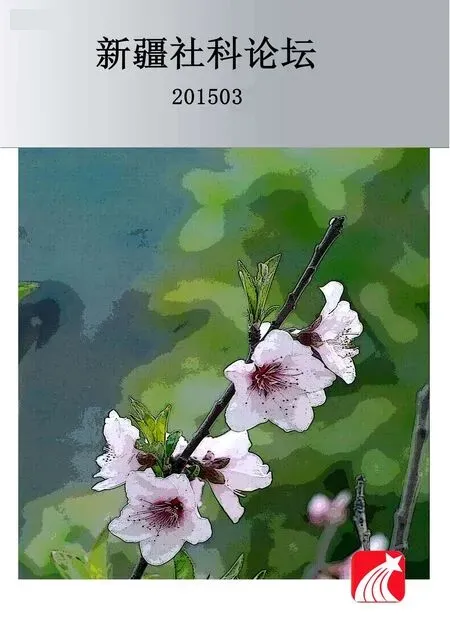试论康德对休谟哲学的解读
试论康德对休谟哲学的解读
张连富
摘要康德成功地发现了休谟的经验主义,并且也正确地理解了它,可他并没有发现休谟哲学中更为根本的自然主义,所以仍然把休谟看作是一个纯粹消极意义上的怀疑论者。康德认为,休谟错误地把因果性等概念归于经验,错误地认为因果性不具有必然性,只具有或然性,没有发现因果性概念的先天性和其理性起源。
关键词康德休谟怀疑主义经验主义理性因果性形而上学
文章编号中国图书分类号B561.291
文献标识码A1671-4741(2015)03-0051-09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
一般认为,大卫·休谟是比洛克、贝克莱还彻底的经验论者,因为他坚持我们不能依据经验从经验推断经验之外的东西,不能从经验推断实体(康德称之为物自体)的存在。休谟认为,经验就是经验,不能超出经验的领域,人们的认识只能局限在经验界限内,因而任何非经验的东西都应该从合法的知识当中排除出去。如果人们所依据的仅仅是经验,那么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超出经验的领域。如果人们试图利用因果性推理从经验跳到经验之外的领域,那么就是越界使用知性概念了,这不管是对休谟而言还是对康德而言都是独断论。一切试图通过因果性推理证明物质实体、心灵实体和上帝实体的企图都是独断论。因果性(知性概念)只能运用于现象界,而且也只能推出属于经验领域的东西,而不能运用于本体界。这就是休谟对康德的最大启发,也是康德在休谟哲学中所发现的真正精髓。
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人们在谈起康德批判哲学的动机时不得不引用,即“正是休谟的提醒,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人的独断论迷梦,并且给予我在思辨哲学领域的研究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①正是休谟的“提醒”让康德走上批判哲学的道路,摆脱独断论的困扰。这一“提醒”就是休谟对因果性的分析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彻底的经验主义和现象一元论。
康德曾指出,“休谟主要是从惟一的一个形而上学概念、但也是重要的概念,亦即因果联结概念(因而还有其派生概念如力和行动等等)出发的,并要求在这里伪称从自己内部产生出这一概念的理性说话并作出回答。它有什么权利设想某种东西能够具有这样的性状,即如果设定了这种东西,就必须必然地设定某种别的东西,因为原因的概念就是这样说的。他无可辩驳地证明道:理性完全不可能先天地从概念出发设想这样一种结合,因为这种结合包含着必然性;但根本看不出来何以由于某物存在,某种别的东西就必须也必然地存在,何以能够先天地引入这样一种联结的概念;他由此推论出理性在这一概念上完全是在欺骗自己,它错把这一概念视为自己的孩子,而实际上这一概念无非是想象力的私生子。想象力凭借经验而受孕,把某些表象置于联想规律之下,并把由此产生的主观必然性,亦即习惯,硬说成是洞察到的客观必然性。他由此推论说,理性根本没有能力哪怕只是一般地思维这样的联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概念就会是纯然的虚构;而它的一切所谓先天存在的知识都不过是打上错误烙印的普通经验罢了。这就等于说,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形而上学,也不可能存在形而上学。”②
休谟对知性概念因果性以及理性的考察直接宣告了一切先天知识的不可能,因此也宣告了形而上学的不可能,对康德来说,这就是近代所引起的形而上学危机,也正是康德的批判哲学所面对的启蒙哲学的困境。
一、休谟与近代哲学
一般认为,近代哲学开始于笛卡尔③。笛卡尔试图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哲学体系,而完全不顾及已有的传统和权威。笛卡尔要寻找全新的确定性,他通过怀疑一切来扫清一切旧权威,抛开一切假设,而完全运用人的理性确立一个开端或第一原则,然后根据这个第一原则建立起整个的形而上学体系来。④在《第一哲学沉思录》开篇的“致索邦神学院的信”中,笛卡尔认为:“我一直认为,这两个主题——即上帝和灵魂——是应该借助于哲学而不是神学来进行理证性证明的主题中的首要范例。”⑤就是说,一切事情(包括科学、政治、社会、宗教等等)都必须以哲学和理性为根据和权威,而不应该以信仰和宗教为根据和权威——或者至少不应该以它们为最终的权威——因为即使它们有根据和权威,那也必须是建立在自然理性的基础上的,因为没有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信仰没有普遍性,而自然理性却是具有普遍性的。
所以,在讲到为笛卡尔所开创的近代哲学时,黑格尔认为:“哲学站在它自己的固有立场上,根据原则,把神学完全抛弃了。哲学宣称思维的原则就是世界的原则,世界上的一切都受思维的制约”,“哲学是大家的共同事业,人人都对它作出判断;每一个人都是生来就能思维的。”⑥启蒙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哲学精神的鼓舞下进行的,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大胆地批判、创造,并大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人们深信,人类只要充分利用理性,运用理性,那么人类的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于是,每个人都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勇敢地探索这个世界。
可正是在这样一个对人类理性、科学和知识无比自信的时代,哲学和理性却越来越陷入困境,以至于要么走向机械唯物论,彻底否认人的自由和精神,要么依赖于上帝走向独断论,要么走向怀疑主义,最终都否定了理性,因此也可以说,理性走向了它的反面。对于启蒙哲学和理性的这种危机,休谟看得非常清楚,他就是要试图告诉我们,如果严格按照近代哲学或理性的原则推演下去,会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就是说,启蒙理性会把人们带人如此荒谬的境地,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它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对理性的依赖和信任,考察理性的职责、能力和界限。
在《人性论》中,休谟按照当时为哲学家们所坚持的哲学或理性原则,推导出许多荒谬的结论。⑦休谟为各种各样的哲学理论提供了一个自由发挥的舞台,让它们完全按照自己的原则充分地推演,推到极致,以便显示出它们的逻辑结果。结果是触目惊心的,休谟发现,现存的哲学体系中没有一个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不会导致荒谬的结论。这些哲学理论,没有一种能够取得绝对的优势,战胜另一种理论,谁都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以便获得人们的信任。
“我们对那些能够提交人类理性法庭的最重要的问题仍然很无知”,⑧于是,形而上学就成了各种学说、体系厮杀、争夺地盘的战场,在这种残酷激烈的厮杀中获胜的不是理性,而是口才,不是战士,而是鼓噪的乐队。⑨休谟向人们表明,那些怀疑主义结论是那些哲学或理性原则的逻辑结果,只要人们接受了那些原则,就必须接受那样的结论,不管它们有多荒谬。
把当时所流行的各种哲学理论的荒谬揭示出来,这只是休谟工作的第一步,休谟并没有止步于此。休谟对于那些极端怀疑主义的结论,同样不能接受,因此也作出了回应。因此,第一个对休谟所揭示出来的哲学怀疑主义做出回应的,不是里德,也不是康德,而是休谟自己。休谟看到并揭示了问题,看到了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清楚地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休谟都被看作是他自己所揭示出来、并试图去克服的哲学怀疑主义的拥护者、鼓吹者,里德是这样,康德是这样,黑格尔也是这样,直到康普·斯密对休谟哲学的卓越解读出现,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人们只注意到休谟的第一步工作,甚至还错误地把休谟所归谬的哲学理论看作是休谟自己的,而没有或者很少注意休谟的第二步工作,即休谟对于所揭示出来的哲学困境做出了积极回应,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不管休谟的主观动机是什么,不管休谟的主观意图有多宏伟和积极,不管休谟对于所谓的道德科学有多大的野心和自信,哲学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把休谟哲学理解为纯粹消极意义的怀疑主义,把休谟哲学看作是启蒙哲学必然陷入的哲学困境,而没有看到休谟对此困境做出的积极回应。休谟哲学所造成的这种客观效果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为何哲学家们对《人性论》的副标题“把实验的推理方法运用到道德科学”和休谟在导论部分对人性科学所表达的雄心壮志不闻不问呢?休谟对自己的工作的定位、说明和后来的哲学家对它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的反差呢?笔者认为是因为休谟由于其怀疑主义后果所否弃掉的某些东西,对于里德、康德等哲学家来说是根本性的,是不能被抛弃的,它们也许是有一定的问题,可这只是说明了,它们需要某种改进,而不是被抛弃掉。比如,对康德来说,理性是要进行某种考察、批判,要被限制,但这仅仅是为了划界和设定,而不是去贬抑和否定它,但休谟的工作恰恰是在贬抑理性,否定理性的自主性和自足,这是康德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对其来说,休谟根据那些原则所推演出来的哲学怀疑主义不能成立,或者说,它必须被克服。虽然针对那些怀疑主义结论,休谟自己也提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案,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的哲学主张,可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和重视,原因就在于此。
康德所面对的是和里德所面对的相同的近代启蒙哲学,但他对启蒙哲学或近代哲学的理解与里德完全不同。在康德看来,启蒙哲学的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即形而上学的问题,理性的问题。休谟的怀疑主义所关涉的是哲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启蒙哲学家根据理性批判、重新评估传统的宗教和世俗国家的权威,并依据理性建立新的权威。然而,他们自己所运用的理性又是有问题的,无法完成它所自诩、本应完成的使命,反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怀疑主义和机械决定论,无法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启蒙哲学家对传统权威(宗教的和世俗的权威)的攻击、破坏,使得人们对理性的理解越来越狭隘,又由于近代数学和自然科学对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理性渐渐被理解为一种算计、推演或逻辑演绎的能力,只是概念间的一种逻辑运算。这种理性并不能创造什么,也不能对人类知识有所扩展,它只能在已有的概念间徘徊。它没有自身的目的,也没有自身的内容,它只是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只能服从欲望和情感休谟的“理性是、且应当仅仅是情感的奴隶”⑩是这种工具理性最准确而大胆的表达。对于这种对理性的狭隘理解,休谟是接受的,而且也是非常赞同的,认为理性就“应当”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隶,因为它必须为人的自然本能或倾向让路。休谟所攻击的不是这种理性观,而恰恰是站在这种理性观的基础上,攻击之前的哲学家错误地归于理性的那些职能。比如,他们试图根据理性做出因果推断,通过理性认识经验之外的对象,或者根据理性探讨道德的本质。休谟告诉我们,只能对观念的关系做出判断的理性并没有这些哲学家们错误地归于它的职能。它至多只能在数学领域有效,在实际的存在或事实的领域就无效了。
康德非常认可休谟对理性的这种考察工作,因为它正确地揭示出启蒙的理性观(至少是休谟的理性观)是有问题的。康德认为,要解决这种根本性的形而上学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理性必须恢复它的自主性和自足性,恢复它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人的本性就是理性,理性是人得以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如果理性像休谟说的那样要服从欲望和情感,服从人的自然本能,那就等于是说,人要像动物一样活着,而且也应该像动物一样活着,这样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而不至于陷入空洞、无聊的思辨和极端怀疑主义的泥潭中。形而上学之所以陷入危机,遭到怀疑主义的攻击,就是因为理性出了问题,因此,哲学急迫的任务是重新认识理性,批判理性,考察理性的本质,重新确立理性的权威。
下面笔者从细节上阐述康德是如何看待休谟的怀疑主义的。
二、休谟问题
和托马斯·里德一样,康德也把休谟看作是怀疑主义者,但不同的是,他不把休谟的怀疑主义看作是西方有着悠久历史的观念理论的必然后果,而看作是经验论的后果,这种经验论否认理性在经验领域(知识和道德)内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否认理性的权威,不承认经验中具有客观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东西,因而不承认有任何先天的东西,最终否认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康德认为,虽然休谟的怀疑主义结论是荒谬的,可怀疑主义本身却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说到底是一种批判,一种对理性自身的批判,是对理性能力的限度、范围的一种考察;它揭示出来的是一切旧形而上学所固有的问题,因此本身具有某种合理性。因此在康德看来,休谟是最接近理性批判并进而考察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的哲学家。“休谟并没有给这一类知识带来任何光明,但他毕竟打出了一颗火星,如果这颗火星遇到一个易燃的火绒,而这个火绒的火苗有得到细心的养护并燃烧起来的话,人们就有可能用这颗火星燃起一片光明。”
在休谟之前,因果联结概念据说来自于理性自身,休谟便对理性发问,要求理性作出回答:“有什么权利设想某种东西能够具有这样的性状,即如果设定了这种东西,就必须必然地设定某种别的东西,因为原因的概念就是这样说的。”追问的结果是,理性并不能为自己自诩的权利辩护,“理性完全不可能先天地从概念出发设想这样一种结合,因为这种结合包含着必然性”。“理性在这一概念上完全是在欺骗自己,它错把这一概念视为自己的孩子,而实际上这一概念无非是想象力的私生子。”“理性根本没有能力哪怕只是一般地思维这样的联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概念就会是纯然的虚构;而它的一切所谓先天存在的知识都不过是打上错误烙印的普通经验罢了。”因果联结概念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来自于经验想象力,因果联结所表现出来的必然性也不过是某种联想规律,是一种习惯,因此只是一种主观的必然性,不足以建立起形而上学来。关于我们的世界,关于实际的存在,我们根本不存在任何先天的知识,因此也不可能具有什么普遍的和必然性的东西。
休谟对因果联结概念的来源、权限的考察的一个结果是,直接否定了知性概念的先天起源和客观有效性,否认了一切先天知识的可能性,从而也否认了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这促使康德必须重新考察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理性的目的、权限等问题,使得康德走上了批判哲学的道路。“正是休谟的提醒,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人的独断论迷梦,并且给予我在思辨哲学领域的研究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显然,休谟所揭示出来的问题为康德的批判哲学指明了方向。
休谟之前的独断论者(主要是指理性形而上学哲学家或所谓的“理性主义”哲学家)试图通过理性自身的概念(他们常常称之为“天赋观念”)自身的演绎,推导出一个经验的世界来,完全用不着现实的感觉经验。形而上学者们认为,通过抽象概念之间的推演,就能够对我们的经验世界做出解释。最高的存在上帝、实体等概念中就已经包含了一切经验对象的存在,从这些概念推演出具体对象的存在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是一个逻辑演绎的过程。比如,斯宾诺莎就用理由和结论的关系来取得原因和结果的关系,用理性推理来取代因果推断,“世界依赖于上帝被认为是一种数学结论。这样一来,因果关系概念完全剥夺了在偶因主义者那里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创造’的经验标志,并且用理由和结论的逻辑-数学关系取代了生动活泼的直观概念。斯宾诺莎主义一贯把因果关系与理由和结论的关系等同起来。
因此,神的因果关系不是一时的,而是永恒的,即无时间性的;真正的知识是在永恒的形式下考察事物,从神性概念是普遍本质这个概念很容易得出上述依赖关系的概念:从此本质出发,其结果无穷无尽地产生此本质的变相,正如从空间的性质中得出几何学的一切命题一样。利用几何学方法可能认识的只能是‘永恒的结论’;对于理性主义来说,只有思维本身独有的那种依赖形式即根据理由得出结论的逻辑推论过程,其本身才是可以理解的,并从而也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模式:真实的依赖既不应该机械地理解,也不应从目的论上去理解,而只能从逻辑-数学上去理解。”
而且,只有通过实体、普遍者,个别物才能被理解,被把握,概念是思维和把握具体对象的前提,我们必须依靠概念来思维存在,把握存在。如,笛卡尔说,物质的本质是广延或形体,心灵的本质是思维;物体的一切性质和状态都不过是广延的样式,精神的一切性质和状态都是意识的样式;只有通过本质,样式才能得到理解。知性概念与经验事实、心灵与物质之间的对应、相符必须依赖于上帝概念才得以可能。就是说,一切知识的有效性和客观实在性都依赖于上帝的存在,一旦失去上帝的保证,一切形而上学体系都将土崩瓦解。
现在休谟却告诉人们,其所面对的是一个事实和经验的世界,而不是一个超验的世界。人们无法运用人们的理智论证上帝的存在,人们无法认识上帝。因此,人们不能借助上帝来保证其的知识的有效性和实在性。在人们的事实领域得把上帝排除出去,因为它毕竟不是人们经验或知识的对象。没有了上帝的保证,所谓的先天概念或天赋观念如何能够先天地运用于经验对象呢?如何能够必然地思维存在呢?如果它们没有原来所自诩的先验出身,那么它们如何能够先天地运用于经验对象呢?如果它们和普通的观念一样,只是经验的出身,那么它如何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呢?既然它们原来所自诩的出身只是伪造的,那它们又是如何在经验中产生的呢?休谟的考察告诉人们,那些自称来源于理性自身的天赋观念或先天概念,如实体、心灵(自我、灵魂)、同一性、因果等,其实不过是经验的产物,是知觉的衍生物,而不是知觉的原因;它们是源始知觉之后的东西,而不是它们之前的东西。它们不是经验的前提或条件,而是经验的产物,或者不过是想象力的产物。它们的合理性根据仅仅在于,它们是人们长期习惯所形成的,是出于简便、需要,出于自然的本能和倾向,不能不相信的观念。它们依然还是有效的,因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它们,我们不能不“信”它们,否则人们在实践生活中寸步难行。但是,它们并没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它们并不能提供理性的证据证明自己对于其对立面的绝对优势,人们只是出于自然和实际的需要选择了它们,而不是出于理论上的优势去相信它们。就它们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是人们的自然本能和倾向的产物而言,它们是自然的,是人们的自然信念。理性可以揭示它们在理论或思辨上的欺骗性和虚妄,可它并不能对抗它们,因为理性并没有自己的内容和原则,不足以对抗强大的自然本能。
休谟实际上是把之前哲学家所谓的先天概念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自然信念,前者的根据在理性,并且最终的根据来源于上帝;后者的根基不在理性,而在人们的生活习惯,在人的自然本能,在人自身,在自然。如果说人的理性以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要有什么前提或条件,那么这个前提或条件不是超绝的上帝,也不是经验之外的先天概念,而是自然。外在的物质世界属于这个自然,人也属于这个自然;支配外在的物质世界的运动的自然与支配着人的思维、意识活动和行动的自然,是同一个自然。思维和存在统一于自然,心灵和物质统一于自然,在和谐一致的自然中,人们看到了最高的协调统一。外在的自然,即自然世界的自然,与人的自然是同一个自然,是自然保证了人对外在世界认识的客观有效性,保证了人在道德和社会生活中的和谐有序,因为自然有它自身的合一性、规则性和一致性,这种规则性规定了物质世界的运动,也规定了人的活动。人们显然是按照自然信念来思维和行动的,而不是按照形而上学家们所杜撰出来的抽象而深奥的思辨体系来思维和行动。人们并不需要懂得某一事物的本质之后才来相信它的存在,也不需要懂得上帝存在的证明之后才来相信它的存在。
休谟明确告诉人们,经验之前(或先),并没有什么先天的东西,即使有,人们也无从知道,因为那超出了人们的理智范围。只有纯粹的经验,没有经验之外的东西,更没有经验之“先”的东西,那些所谓的经验之“先”的东西其实不过是经验的产物,或者是想象力的虚构。在事实或存在的领域,人们始终只能在经验的前提下谈问题,一切关于存在的观念都只有经验的出身,更没有什么先验的东西。这些概念既然仅仅是经验的产物,那么就不能运用到经验之外的领域,如宗教和信仰的领域,不能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独断论者所谓的理性概念要么仅仅是经验的产物,产生于想象力的虚构,要么根本就是虚妄的,没有任何的实在性。
康德非常认可休谟对理性概念的这一考察工作,并且也认同休谟的这一看法:单纯从经验中断不可能获得先天(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概念和知识。康德同样认可休谟。如果理性概念不能证明自己在经验中的合法性和客观有效性,不能先天的思维对象,那么被斥为不过是经验、甚至是想象力的产物,是再合理不过的要求。如果理性概念还坚持自己的先天性,并且还仍然坚持自己的权利,坚持自己在经验领域的权威和合理性,那么它们就必须为此提供一份证明(因为它们毕竟不是从经验中归纳而来的)。不从经验中来,如何能对经验对象具有先天的规范、综合作用呢?如何能先天地运用于经验对象呢?休谟就恰好证明,理性既然不能把因果性概念归于自己名下,不能拿出自己对于它的合法权利和权威的证明来,那么它就得放弃这一要求,把它还给它本来的主人(经验)。因果性概念既然只是经验性概念,只是从经验中来的(虽然不是直接从经验中来),那建立在因果联结基础上的一切经验知识都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任何先天知识都是不可能的。
表面上看起来休谟对理性自身的概念的考察直接宣告了理性科学的破产,给形而上学以致命打击。“自从洛克的研究和莱布尼兹的研究出版以来,或者毋宁说就形而上学的历史所及,自从它诞生以来,就这门科学的命运而言,还没有发生任何事件,能够比休谟对它的攻击更具决定性。”休谟对形而上学的这种打击看起来好像是完全消极的、破坏性的,可在康德看来,休谟的这一工作非常积极,对于真正的形而上学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休谟所打破的,毕竟只是独断论的形而上学,而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真正的障碍就是独断论,休谟现在宣告了独断论的破产,怎么不算是在科学的形而上学的道路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呢?如果没有休谟的这一工作,或许人们还继续做着独断论的大梦——就像康德在走上批判哲学的道路之前那样,因为人们还没有觉察到人们正走在一条根本错误的道路上,更不知道人们到底错在哪里,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人们。既然休谟给未来的形而上学指出了不得不面对、无法逃避的问题,自然也就给真正的形而上学指明了一个方向,尽管他是无意这么做的。
休谟对形而上学的质疑和挑战不是休谟自己凭空捏造、虚构出来的,而都是有根据的;不是随意的指责,而是有的放矢。他所揭示出来的确实是已经存在的形而上学都具有的问题,因而也都是未来的可能的形而上学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康德把休谟所提出的、但又是形而上学自身不得不面对的这一问题称为“休谟的问题”。“休谟问题”所针对的主要是知性概念的出身(来源)以及对于经验对象的客观有效性问题,康德认为这些问题直接关涉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因此极为重要。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花了不少的精力去回应“休谟问题”,集中地体现在“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一节。康德声称,“这一演绎是为了形而上学所曾经能够作出的最困难的工作”,也是对知性的考察中最为重要的工作,由此可以看出休谟问题对于形而上学的重要意义以及康德对它的重视程度。
三、康德的回应
休谟试图把理性概念从经验或事实中清除出去,只留下一个不夹杂任何先天概念和形而上学成分的纯粹经验或存在领域,并且,他还进一步向人们证明,那些原以为来自于理性的先天概念其实亦不过来自于经验,来自于人的想象力,只不过是普通的经验概念罢了,没有任何的理性根据。对此,康德的先验演绎就要向人们证明,理性概念在经验对象上的先天运用是具有合法性的,它们是可能经验的先天条件,因此不仅不可以像休谟那样从可能经验中被剔除出去,而且还是这种可能经验的先天条件,它们必然地对经验对象有所认识。首先,康德需要证明,先天的理性概念是有的,它们不是产生于经验,而是产生于理性自身,来自于人天生的判断能力,而这种判断能力是形成一个可能经验所必不可少的。“它们并不像休谟所担忧的那样是从经验派生来的,而是从纯粹知性产生的。”其次,康德需要证明,这些纯粹知性概念对于经验对象的客观有效性,康德是通过证明它们是经验的先天条件来达到这一目标的。康德表明,“一切经验在某物被给予所凭借的感官直观外,还包含着关于一个在直观中被给予或者显现的对象的概念,据此,一般而言的对象的概念就作为先天条件成为经验知识的基础。所以,范畴作为先天概念的客观有效性的依据是惟有通过它们,经验(就思维的形式而言)才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范畴就以必然的方式并且先天地与经验的对象相关,因为一般而言,只有凭借范畴,经验的某个对象才能被思维。”任何事物要成为人的经验对象,就必须不仅在直观中被给予人们,被直观,而且必须在一般对象的概念中被思维,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人的对象。概念是对事物的基本规定,没有这种基本规定,事物不可能向人显现,成为人的对象。要形成一个理性知识,不仅需要一个对象被直观,形成一个知觉,而且还需要这个在直观中被给予的对象被思维。而像洛克、休谟一样的经验论者以为,没有思维和概念,对象照样能够被给予,照样能够成为人的对象——单单凭借感性直观,对象就能够被给予人们,并形成知识。
康德很清楚地看到了休谟和洛克之间的分歧,不像里德那样把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或者把休谟仅仅看作是洛克忠实的继承者。对于洛克、休谟和康德三人在概念和知识问题上的关系,人们可以引用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介绍康德哲学时讲的一段话,“康德从休谟出发。休谟与洛克相反,指出在知觉中找不到必然性和普遍性。洛克认为人的心灵如一块白板,人们可以通过经验获得必然性和普遍性。康德立刻完全同意在知觉中,亦即在外界事物中,没有必然性和普遍性这种说法,但是同时承认存在着必然性和普遍性,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为例证。现在问题是哪里去寻找必然性和普遍性?人们要求普遍性和必然性,首先认为它们是构成客观性的,这个事实康德表示承认。但是跟着他就反对休谟道,由于必然性和普遍性既然不在外界事物内,则它们必然是先天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理性本身内,存在于作为自我意识到的理性那样的理性之内;换言之,它们是属于思维的。另一方面康德又反对沃尔夫的形而上学,去掉了他的形而上学范畴的客观意义,并且指出这些范畴如何只应该划给主观的思维。”确定了这一点之后,康德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说明包含着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理性概念如何能够运用于经验对象,休谟就由于理性概念不能证明这一点而否认它的有效性,独断论没有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所以才让休谟的怀疑主义有了可乘之机。
休谟虽然否认了理性概念的存在,认为所谓的理性概念——其实根本不是理性概念,而是普通的经验概念——亦只是经验的产物,但他并没有像洛克那样只是简单地把它们从经验中归纳、抽绎出来,因为个别经验的简单归纳并不能给出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证明——休谟显然认为因果性是具有某种必然性和普遍性的。休谟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自然主义的解释。以因果性为例,它不是理性概念,因为谁也不能先天地设想它,在一个对象出现时先天地设想另一个对象的存在;它也不能从经验中归纳而来,因为经验观察只能告诉人们已经过去了的事情,而不能使人们超出已有的知觉,对未发生的事情作出判断;它不是产生于对过去相似事情的归纳、总结,总之,人们不能在客观的对象中寻找它的根源。那它到底产生于哪里呢?人们只能在人的主观倾向中找,就观察的对象而言,因果关系的基本特征是恒常的联结,即两个相似对象的重复出现,这是人们所观察到的客观效果,但这种客观效果并不能成为因果推断的根基,因为它并不能把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告诉人们。但是,这种客观效果却在作为观察者的主体身上造成了某种效果,产生了某种新的东西,这种新的东西便是习惯,即心灵的一种自然倾向,一种决断力。这种决断力使得心灵很容易由一个对象的出现推断另一个对象的出现,很容易在恒常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对象间转移,而这便是因果关系的本质。“必然性(即因果联系)是存在于心中,而不是存在于对象中的一种东西;人们永远不可能对它形成任何哪怕是极其渺茫的观念。”因此,因果性显然也是一种必然性,尽管只是一种主观的必然性。休谟反复强调因果律的这种主观性。休谟之前的哲学家,不管是唯理论者还是像培根、洛克一样的经验论者,都丝毫没有怀疑过经验只具有一种偶然性和或然性,不具有客观必然性,现在休谟要颠覆哲学家们的这一成见,试图证明,因果性概念虽然出自经验,不具有理性所要求的必然性,可他仍然具有某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一种主观的必然性,是人类心灵的一种自然倾向或者自然本能,是人无法抗拒的,也是人与生俱来的思维、行动能力的表现。没有这种主观必然性,人无法思维,也同样无法行动,人几乎不能做出任何判断和选择。休谟对这样一种必然性的阐明就是人们所称之为“自然主义”的主要内容,这种必然性不同于自柏拉图以降的理性主义所理解的必然性,他仅仅来自于人,来自于人性的原始性质,并且只在人的日常经验中起作用,与超验的对象上帝、实体无关。
休谟给予像实体、共相、原因、外界存在、灵魂、自我同一性等概念不同于之前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同的解释,这个不同就在于他完全摒弃了前人都免不了地诉诸上帝的做法,而完全是从人的层面,从人性的层面对它们作出一种独立而新颖的解释。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康德。康德也认为,这些概念不是来自于对上帝的沉思或认识,其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是自足的,不需要求助于一个超绝者上帝。只要人有判断,对这世界有认识和经验,那么这些概念就必定具有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因为它们必然要对人的认识活动和经验起作用,否则人们就不可能对任何对象有所认识,不可能有经验。它们与上帝没有关系,它们只与人的认识能力有关。知识和科学的普遍必然性不需要上帝来保证,而且,人们这些来自于先天的理性能力的概念也不能运用到超绝者上帝或理念的对象灵魂、世界整体、自由上面去。人们要区分一个现象界和一个本体界,一个知识的领域和一个信仰的领域。康德的这种划分不可能没有受到休谟的影响,休谟的自然主义就是在于没有上帝的“外在”干扰之下重建知识和道德的体系,完全在人的自然本性的基础上建立知识和道德体系,这就是休谟的“人性科学”的目的,也是休谟自然主义的精神。
四、结论
虽然康德成功地发现了休谟的经验主义,并且也正确地理解了它,可他并没有发现休谟哲学中更为根本的自然主义,所以仍然把休谟看作是一个纯粹消极意义上的怀疑论者。
康德一方面回应休谟的怀疑主义,为自然形而上学奠基,把自然科学奠定在具有普遍必然性和经验实在性的先天知性概念(范畴)的基础上,让自然知识重新奠定在理性(知性)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康德又要限制这种理性(知性),“以便为信仰留下地盘”。康德一方面要为自然形而上学奠定基础,建立一个服从因果必然性的体系;另一方面,康德又要把自然限定在现象领域,好给自由和信仰留地盘,这个地盘就是自然领域之外的本体界。康德之所以这样做,保护自由和信仰不受侵犯,是因为在当时正有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自然不断地侵蚀到自由和信仰的领域,使得后者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人们试图用自然科学来解释一切,用人性来解释一切,这就把自由和道德给驱逐出去了,或者把它们解释为某种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必然性。道德和宗教正遭受着危机,不断地受到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攻击。康德未必认识到休谟在认识论领域的自然主义,但他一定意识到休谟把道德也纳入自然领域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康德非常“明智”(也可以说非常不明智)地采取了这样一个策略:自然与自由的二分,或者现象与物自体、自然界和本体界的二元论区分。自然归自然管,服从自然规律,“人为自然立法”,但本体界必须在在自然之外,是道德和信仰的对象,不是认识的对象。正是这样一个二元论区分,使康德得以开启他的批判哲学的道路。而这样一个区分显然是在休谟的启发下作出的,休谟告诉人们,人们不能把因果性运用到经验之外,推断并认识实体(康德称之为物自体)的存在,知性概念不能运用于本体界。正是在休谟的这一限定之下,康德才得以将现象与物自体做存在论上的区分。
休谟考察因果性是为了限制因果性,分析它的人性基础。休谟的分析表明,因果性只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只能在经验范围内有效,它不过是习惯性联想。为什么一个事物出现,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它的通常伴随物呢?为什么人们的心灵会从印象A会自然地转移它的通常伴随物B的观念呢?这是因为印象A所具有的生动活泼性由于一种恒常的联结顺利地转移到了B上了,形成了B的信念,使人们不仅可以设想B,而且还相信B立即出现。这就是真实发生在人们身上的因果性推断的本质。这不是发生在事物身上的事情,而是发生在人身上的事情;因果性不是对象的性质,而是人的心灵的某种性质,某种决断,这种决断就是人的一种本能。因果虽然是主观的,是心灵所具有的一种特征,可是它具有必然性。
康德认为,休谟错误地把因果性等概念归于经验,错误地认为因果性不具有必然性,只具有或然性,没有发现因果性概念的先天性和其理性起源。休谟只是摧毁了因果性的虚假的基础,却不为它奠定另一个坚实的基础,只是指出了因果性的或然性,却并不试图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奠定基础。“我以为我正是这样一个人,虽曾多次遭遇过浅滩,并且在驶过狭窄的海岔时才勉强幸免于难,然而我仍有勇气驾驶那条饱经风雨的漏船驶向大海,甚至有如此雄心,以至想在这些不利的条件下去环球航行。”休谟并非像康德理解的那样,因为害怕碰礁,出于安全的考虑,所以就靠在一个无论哪一个安全的岸上,在那里腐烂、发霉,而不到危险的大海中航行。实际上,对于自己的使命和处境,休谟也用了大海中航行的船的比喻:“我以为我正是这样一个人,虽曾多次遭遇过浅滩,并且在驶过狭窄的海岔时才勉强幸免于难,然而我仍有勇气驾驶那条饱经风雨的漏船驶向大海,甚至有如此雄心,以至想在这些不利的条件下去环球航行。”
注释:
④笛卡尔认为,他的这一工作就好像是之前阿基米德“只要求有一个稳固而可靠的支点,用来撬动整个地球”。
⑤René Descartes,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with Selections from the Objections and Replies[M],tran. and ed. by John Cottingh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p.3.
⑥黑格尔(德):《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2页。
⑦笔者注:正是由于其荒谬性,哲学家们忽视或故意回避这些结论,因此也使得当时很少有人重视休谟哲学。
〔责任编辑:郭嘉〕
●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