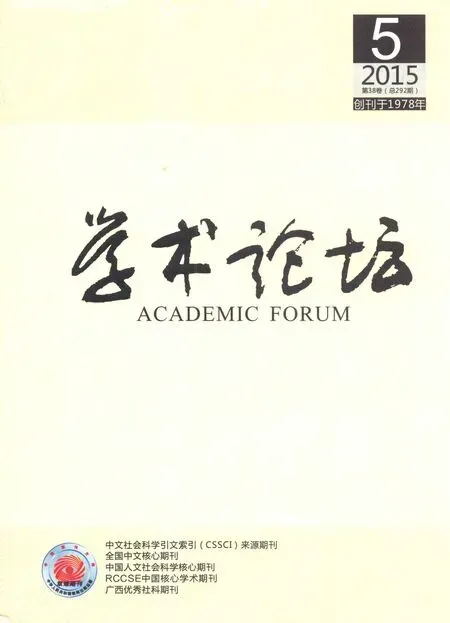法治悖论及其消解
陈伟斌
法治悖论及其消解
陈伟斌
法治的目的是要限制国家权力,而为了限制国家权力又需要国家权力,这就形成了法治悖论。法治悖论的解决不能依靠国家权力间的相互制衡,而必须依靠向市场和社会分权,用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来制衡国家权力。
法治悖论;国家权力;权力制衡;市场权力;社会权力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一句越来越流行的口号。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句口号是个简单明了的比喻:制度就是笼子,权力就是老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用制度制约权力的滥用。但是,对于法律学人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真正做到把权力这只老虎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而杜绝权力的滥用?
一、法治与“三权分立”的虚幻
毫无疑问,法治的首要问题是限制权力的滥用。问题是:如何限制权力的滥用?在现代社会,利用法律对权力进行制度化约束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利用法律对权力进行约束并不容易。一旦离开抽象理论进入现实操作,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约束权力,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离不开权力。
第一,限制权力就必须使权力的使用依照规则运行,为了使权力依法律规则运行,就必须考虑到权力在实际生活中运行的各种具体情形,并对其使用的范围和方式等加以限制。因此,必须制定详细的法律规则。然后,国家机构要能够设计并实施一套有效的选举制度从人民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代表。这是对国家机构能力的考验。
第二,为了防止权力的运作给公民带来伤害,保证权力的行使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必须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对其加以监督。这就需要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防止权力在运作过程中的滥用。这就意味着国家政权首先必须要有能力投入足够多的财力和物力设立监督机构,制定监督规范,保障监督机构履行职责。更麻烦的问题是:监督者监督被监督者,但谁来监督监督者?所以,国家必须解决监督者自身的问题。
第三,天下没有不会产生争议的法律规则,权力是否被滥用常常会引发争议,而为了解决这些争议,国家必须要设立中立的第三方对争议进行裁决。这又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另一次应用:国家权力首先必须设立中立的司法权力机构,投入足够的人财物保障其平稳运作。
更复杂的问题是:国家权力必须要有能力保证这一整套的国家机构相互衔接、彼此独立。所有这些机关各不相属,都有自己的权力,但又不能侵犯其他机关的权力,还要彼此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
仔细思考以上每一个环节,其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运作和支持。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立法机关不能成立;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立法机关的立法无法执行;没有国家权力作为支撑,行政机关无法实施社会管理,没有国家权力,司法机关的裁决只能是纸上谈兵,更不用说所有的这些权力机关都必须首先依靠国家权力才得以存在,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要有强大的国家权力作为支撑。
于是,在此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我们可以称之为法治悖论,即:法治的目的是要限制国家权力,而为了限制国家权力又需要国家权力。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法治需要强大的国家权力作为支撑,而国家权力的强大又会增加限制它的难度。用老虎和笼子的比喻来说就是:想把老虎关进笼子又需要老虎帮忙。问题是:不情不愿的老虎凭什么愿意帮忙?
如何解决这一悖论?或许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对权力的策略:用权力对抗权力,用野心对抗野心[1](P95)。美国宪法就是依据这一原理而设计。国会享有立法权和财政预算权以对抗总统,司法任命权以限制联邦最高法院;总统有立法否决权和大法官提名权以对抗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则有司法审查权以对抗国会和总统。美国的成功为这一制度做了最好的广告,引得无数不发达国家如菲律宾,利比里亚等国竞相模仿,然而其效果却大相径庭。在美国领土上成功实践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在其他国家却造成了三权纷争及相互倾轧。这些失败的美国式三权分立实践最直接地证明了以为用权力对抗权力就可以实现权力制衡、实现法治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想法。
从权力的角度我们也能分析出试图仅仅依靠三权分立实现法治是不大可能的。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P104)。权力的首要本能是扩张,而非与其他权力对抗。无论把权力分成三权还是五权都是如此。分权只是制衡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分权未必就会带来制衡[3](P121)。权力无限扩张的本性恐怕带来的首先会是权力斗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并没有写入美国宪法。联邦最高法院获得这一权力是行政权和司法权斗争的产物恰好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没有其他手段能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的地方,最终的结果更有可能是权力之间相互拆台、党同伐异、政治倾轧,权力制衡最终难免沦为权力僵局。这一权力分立的死结直到今天仍然在三权分立的鼻祖美国时不时地上演。克林顿总统在任时,美国国会和总统就预算问题发生的争执导致政府停摆,奥巴马总统与国会就医疗改革、政府预算等问题与国会之间的争吵不断就是三权分立所导致的权力争斗混乱的典型。而在效仿美国搞三权分立的菲律宾等国家,立法权还没出国会就干脆直接变成了议员们打架斗殴。
另一方面,三种权力即使不争斗,三权联合也是实现权力的最大化扩张的一种方式。如果三种权力谁也无法压制其他两方而获得支配性地位,如果互相争斗彼此受损,而相互妥协三权合谋能够获得最大利益,为什么还要彼此对立?划定权力范围坐地分赃岂不是比相互争斗要划算?三权分立在此格局之下完全可以演变为三权同谋,奴役人民,腐蚀国家。拉美许多国家就陷入了这样的陷阱。
因此,简单地以为用权力之间的相互斗争就可以解决权力悖论是低估了权力扩张的本性,低估了权力对人的腐蚀性。美国式的三权分立能在美国运转,是和美国自身独特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销美国式民主和三权分立没有产生过第二个成功的范例,这一事实或许可以提醒我们要解决权力悖论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博弈。
二、走出权力悖论:向市场分权
尽管存在着权力悖论,但权力悖论并非无解。虽然三权分立无法实现法治所需要的权力制约和相互制衡,但三权分立所包含的思路是正确的,那就是:向其他权力主体分权。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也是正确的,但不能简单地把权力局限于同质的国家公权力之间。真正的权力制衡只能发生在异质的权力主体之间。从本质上来说,民主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国家权力,原因就在于民主的主体——选民团体本身是不同于国家权力主体(官僚或者政治精英)本身的。民主选举制度就是一种分权制度。民主选举就是通过给予民众选择政府官员或政策的权力让国家权力服从民众的偏好。在公平的民主选举制度下,民众的意愿通过选票得到表达,并通过多数规则形成了对国家权力应用的制约,而民众自身的规模和数量决定了购买民众支持的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立法、行政、司法这三个权力主体由于数量少而形成的寡头格局中总是可能的。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用民主制度来实现对权力的限制也是有相当难度的。间歇性的民主选举难以保证民众对国家权力的持续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作为选民的代理人其效用函数是不同于选民的[4](P206)。民众自身的分散和利益冲突也常常使人民的力量成为一盘散沙,再加上政治宣传的蛊惑、自身利益的诱惑等等因素,都使得现代民主制度难以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国家拥有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却无法成为法治国家。
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就意识到了权力之间的差异。迈克尔曼把人类社会的权力分为四类:军事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5](PP28-36)。每一类权力都不同于其他三类权力并足以构成对其他三种权利的限制。这几种权力之间的相互限制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世纪欧洲。在中世纪的欧洲,诸侯国林立,各国君主掌控着自己的军事力量(军事权力),一般也是其下属封臣们的领袖(政治权力),但不一定能够完全掌控经济权力。下属封臣们往往拥有自己的领地,在自己的领地上握有军事、行政、税收等完全自主的权力。而对君主权力最大的掣肘则来自于罗马教廷所掌握的精神性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君主的合法性往往必须要得到教皇的认可。教皇对君主和民众的影响力在很多时候超过君主,如教廷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有史学家认为,宪政最早在欧洲诞生,原因就在于欧洲四分五裂的权力格局导致的权力制衡使得各种社会权力无法统一到政治权力之下。与之相比,中国之所以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君主专制国家,原因就在于中国政治权力的早熟在驯化了军事权力之后吞并了社会原本拥有的经济权利,并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掌控了意识形态权力,为自己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资源。诸种社会权力统一于政治权力之下使得国家权力独大到足以压制其他社会权力,社会失去了制约国家权力的可能。
因此,从迈克尔·曼的四种权力划分理论,我们可以理解市场经济的政治意义。市场不仅是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拥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市场经济还是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
国家公权力的滥用,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国家权力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要实现市场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首先必须要保证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得到完全确立,为此,清晰地界定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限制政府对市场经营主体的干预是市场限制国家权力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是政府权力有限的经济,它要求政府从配置自然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退到居辅助作用上来,还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只对关系到重大国计民生的有限自然资源进行必要的配置,以保证社会安全和资源充分的利用。
最后,市场经济要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必须要保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资本和劳动力是逐利的。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资本和劳动力必定将逐步向政府干预最有效、法治环境最好的地方流动,从而促进各地政府间的社会公平制度竞争。这种压力的存在才是限制政府权力的重要压力。
三、走出权力悖论:向社会分权
同样,社会权力也是制约国家权力的重要力量。所谓社会权力就是社会主体(公民特别是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物质和精神资源)对社会和国家的支配力[6]。向社会分权意味着把权力交还给社会中为数众多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契约性社会团体。
社会权力的重要性在于,它赋予个人生活以意义,它塑造个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现代社会,社会主体所拥有的强大权力甚至可以改造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知和看法。例如,宗教对信徒强大的洗脑作用,新闻媒体对公众意见的强大影响。早在1878年,英国政治家伯克就将报纸称为“第四种权力”。社会权力的载体主要是政府组织以外的各种社会组织,或称非政府组织(NGO)。在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中的规模巨大。仅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国内税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美国登记的非盈利组织共计156万家,其中包括100万家公共慈善组织和10万家私人基金会。平均下来,每1万名美国人就拥有34.2家非盈利组织,以及近50万家其他类型非盈利组织[7](P42)。由于美国税务机关规定只有年收入达到5000美元以上非盈利组织才需要登记,而没有登记的非盈利组织规模占到所有非盈利组织的90%以上。如果把这些未登记的非盈利组织算上,数目将会更加惊人。除此之外,由于美国宗教团体免于登记,而根据美国教会列表(American Church Lists)2010年的统计资料,在美国大概有278772家宗教团体。而美国非盈利社会组织相当发达与活跃,2009年,非盈利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达7790亿美元,占到GDP的5.5%。除了规模和数量之外更重要的是,美国的非盈利组织对美国政府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美国的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协会、外交关系协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对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而美国两千多所大学则为美国科技领先全球奠定了坚实基础。美国非盈利组织广泛参与人权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裁军、反核、社会福利保障与服务、文化教育卫生问题、国际犯罪、自然灾害等诸多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行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遍布社会的各种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其拥有的大小不等的社会权力的影响力和支配力也无处不在。有些社会事务是政府不能或不愿做、不该做的,非政府组织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并且利用其资源优势,有些可以比政府做得更好。它们的崛起还可以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使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
在制衡国家权力方面,毫无疑问,独立自主的新闻媒体是对抗国家权力滥用的最有效武器。国家的监督权力,虽然强大,却是有限的。而独立自主的新闻媒体在履行社会监督职责方面可以弥补国家权力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无处不在的媒体监督使得国家权力无处藏身,在强大的媒体监督压力下,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不得不依照法律规定行事。国家权力在新闻媒体面前受到了坚硬的约束。
最后,宗教、传统文化等社会团体的自主存在也能够为国家权力受到制约提供精神资源。市场经济并不是人间天堂,城市化和市场经济所造就的陌生人社会和生活事务经济中心导向往往会造成公民道德的悬置,即一种政治冷漠的状态。这种政治冷漠在面对国家权力的侵蚀时只会转变为一种政治犬儒主义。国家权力的侵害在很大程度上与民众的道德冷淡和政治责任感的退缩相关。而传统宗教、传统道德复兴等社会团体的存在通过团体自主教育往往能够将现代社会存继所需要的公民责任感和道德意识注入团体成员心中,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沉默面对邪恶的道德困境。而大规模的社会团体教育如果成功的话,将会造就更多有热情和责任感的社会成员,只有当他们普遍存在时,控制国家权力所需要的无处不在的监督之眼才能出现,国家权力才真正无处可逃。
四、结语
制约国家权力是人类社会走出部落形态形成国家以来面临的千古难题,而法治无疑是人类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好的制约国家权力的武器。但是,正如上文所述,仅仅试图依靠同质的国家权力之间的职能分工和权力相争来实现权力制衡是不现实的。真正的法治必须依赖于市场权力和社会权力的独立和自主性。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也是建设法治中国必须要发展的重要支柱。国家权力必须要在强大的市场权力和社会权力的抗衡下才会真正被关进牢笼。在建立了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和社会组织体系的地方,国家权力由于才能受到充分的限制。在这一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两点不仅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也是实施法治的关键。而深刻理解国家权力和法治,尤其是真正能克服法治悖论的诸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依靠法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步。
[1]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等.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凌斌.行政法治的伦理困境:法治的中国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5]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2卷·上)[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6]郭道晖.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J].法学研究,2001,(1).
[7]王名,李勇.美国非盈利组织[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索原]
陈伟斌,广东海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广东省地方立法研究评估与咨询服务基地研究人员,广东湛江524088
D90
A
1004-4434(2015)05-0127-04
广东省地方立法理论研究基地广东海洋大学“创新强校工程”2014年省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GDOU201305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