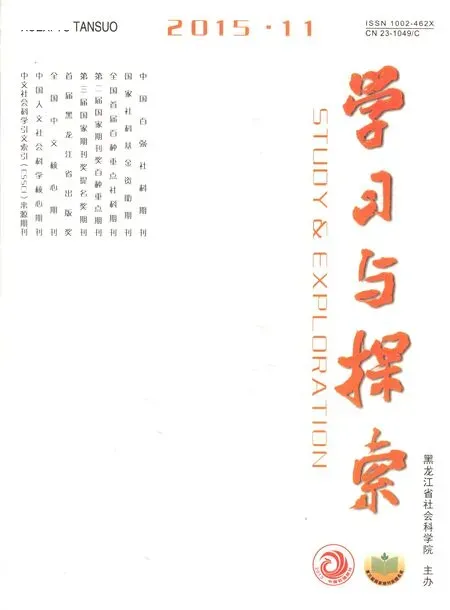“创造性的破坏”:理解戴维·哈维空间理论的关键词
毛 娟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6)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创造性的破坏”:理解戴维·哈维空间理论的关键词
毛 娟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6)
“空间”一直是人类感受客观世界的重要维度。把“空间”看成是相对的和变化着的,其内涵要取决于人类的不同社会实践和创造,这是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戴维·哈维理解空间问题的理论基点。哈维借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的破坏”这一概念,用以分析现代性的社会进程、巴黎的城市改造和空间关系。这不仅是其空间理论包含的重要内涵,也是我们理解哈维关于现代性理论的关键词之一。
“创造性的破坏”;戴维·哈维;现代性;空间理论
“空间”和“时间”是我们探讨世界与存在之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点。任何一种社会构建既包括空间的维度,也包括时间的维度;人类始终都是在空间和时间的共同建构中存在着的。同时,空间和时间也是我们感知和体验客观世界的重要维度。从19 世纪末开始,随着资本和社会生产的快速扩张与发展,给人类的社会实践带来了巨大变化,从而也带来了我们在体验空间和时间方面的深刻变化。在经济全球化和大规模城市化的背景下,资本以及虚拟资本以最快的速度和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空间在其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日渐受到人文学科研究的重视,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各种传统的空间观念。亨利·列斐伏尔说:“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1]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生产。这种观点无疑开启了20世纪社会理论研究中最令人瞩目的“空间转向”。理论家们把研究时间问题的热情转移到了空间问题的研究之上,这也带来了传统空间观念的重大转变。
和“时间”概念一样,“空间”概念是我们的语言中最为复杂的词语和概念之一。按照当代社会理论对空间概念的理解,空间不是某种空洞的容器,而是在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同时,空间还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改变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行为方式和关系。因此,列斐伏尔指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2]列斐伏尔的观点极大地凸显了空间概念的社会学意义,并由此把空间问题看成是特殊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物质性的空间形态的变化与社会形态的变化紧密相关。此后,其他一些西方学者,诸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戴维·哈维、爱德华·索亚、曼纽尔·卡斯特尔、安东尼·吉登斯等人,在看到空间与时间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关系后,纷纷从不同视角打破了纯粹地理学研究领域内和传统理论中单一并且固定的空间观念,赋予空间概念以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从此,空间概念不再被看作是僵死的、固定不变的、静止的和非辩证的了。
在这些当代西方学者中,戴维·哈维关于空间的理论观点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人文地理学者,哈维非常明确地指出:“对空间和时空的恰当思考,对于如何阐明和发展各种理论与理解,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尽力解决作为关键词之空间问题的要点,因而在于:要确定这个概念怎样能更好地被整合到现有的社会、文学和文化的元理论之中,以及会产生什么效果。”[3]与此同时,哈维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旗手,“空间”问题也是他在后现代时代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切入点。在他看来,“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对于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论述,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中还缺乏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的维度”[4]。哈维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引入到传统的地理学研究中,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把空间问题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创立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
在人类的感知领域,“空间”和“时间”是人类主体感知和把握客观世界的重要维度。从一个方面说,客观物质世界中的空间是相对稳定的物质性存在;但在另一个方面,相对于人类的感知来说,空间既是相对的,又是相关的,因为对空间的感知要取决于人类的不同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同时也要取决于人类的创造和感知模式。因此,在哈维看来,空间具有物质性、关系性和相关性这三个基本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哈维所理解的空间概念的主要内涵。哈维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然而,我们很少争论它们的意义:我们倾向于认为它们理所当然,赋予它们普通的意义或者自证的属性。”[5]252空间概念之含义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物质性、关系性和相关性之间相互关联和相互涵盖的关系。对此关系的强调,实际上是强调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和内心感知活动在空间与时间的建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空间和时间是“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与过程而创造出来的”[5]255,“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5]255。在这个问题上,正如阎嘉教授所言:“哈维反对单纯从哲学上来解释空间与时间的问题,而认为应当坚持实践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研究路径正是新马克思主义与先前坚持哲学批判与文化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异。”[6]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哈维通过对空间理论的引入和阐释,为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和理论解释的基石。在哈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了很多富有穿透力的思想和概念,诸如“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时空压缩”“创造性的破坏”“空间修复”“剥夺性积累”“地方与全球的辩证法”等。本文主要探讨的“创造性的破坏”,正是我们理解哈维关于西方现代性理论中的关键词之一。
“创造性的破坏”的概念最初是由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来的。熊彼特认为,“创造性的破坏”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存在的本质性事实之一,研究此一问题的目的,是为了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如何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和体制,以及如何创造出新的经济结构和体制。从全球范围来看,“创造性的破坏”的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不断增强,并且成为主流经济研究中的重要理路。哈维借用熊彼特的这一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总体特征。哈维认为,“‘创造性的破坏’隐藏在资本本身的流通之中。创新加剧了不稳定、不安全,最终成为把资本主义推进到周期性的危机爆发的主要力量。”[5]142在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进程发展迅猛。蒸汽机、自动化工厂、密布的铁路、新兴工业区、新型城市、各种大众媒介相继出现,并且带来了大规模的信息交换、资本聚集和不断扩张的世界市场。同时,文化产品的市场化与商业化,迫使文化生产者进入到市场竞争中,艺术家们试图通过销售自己的作品来改变普通大众的审美判断。因此,在审美领域里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创造性的破坏”。可以说,在19世纪后半期,创造性的破坏景象随处可见。“他们都最为强有力地存在于复制人本身的形象之中,他们被以惊人的力量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尽早成为破坏性的,并最为肯定地要‘隐退’,只要他们真的专注于自己的情感,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发展自己的能力”[5]390。1848年的欧洲革命、巴黎的城市改造都是资本主义的都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和艺术的表现也随着这种社会转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中,哈维以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为例,阐述了“创造性的破坏”在现代性建构中的力量与作用。
在19 世纪欧洲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巴黎成了资本主义快速崛起的一个典型样板。从1852 年到1870 年,时任巴黎市长的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奉路易·拿破仑之命,对中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旧巴黎城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此举被认为是巴黎城市现代化的标志,成了欧洲现代性的缩影之一。在城市改造之前,整个巴黎市环境恶劣,充斥着污水、肮脏、疾病和瘟疫,散发着腐烂的味道。而奥斯曼的城市改造,正是对当时巴黎的人口、经济、环境等社会危机所做出的某种挑战性的和创造性的回应。后世对奥斯曼的这一举动褒贬不一。正面的评价认为,此举提高了巴黎市民的生活品质,极大地改善了公共卫生条件和交通状况,新的建筑和大街更加实用、美观;反对者则认为,这场改造造成了许多下层市民流离失所,野蛮地摧毁了很多历史遗迹,割断了人们对历史的想象。面对种种正面和负面的评价,哈维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出发,跨越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艺术等诸多学科的边界,将时间、空间、资本、城市改造活动,以及置身于其中的不同人群的体验作为研究对象,思考并阐释资本的运作和流动在大都市改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勾画和把握市民对大都市体验的变化,以及文学和艺术中的现代性转变的历程。哈维用“创造性的破坏”的概念从总体上来概括这一历史进程。正是这种进程,使巴黎完成了现代性的城市改造,让我们在此后看到的巴黎既是帝国的殿堂,又是革命的废墟;既有历史的遗迹,又有创新的印痕:一个在过去的遗址中耸立着的大都市,最后成为旧式欧洲的象征。这个新巴黎,完全可以被我们看作是理解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大都市的典型。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改造,并不完全是对中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巴黎的野蛮破坏。作为“现代性之都”的巴黎的诞生,并非历史的偶然或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奥斯曼只不过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受命完成了这一使命。对此,哈维做出了如下评价:“奥斯曼所部署的都市空间概念无疑相当新颖。他并不是要兴建‘与各地区毫无关联也毫无纽带关系的大道通衢’,相反,他希望能有一个‘通盘的计划,能够周详而恰当地调和各地多样的环境’。都市空间应视为一个整体,城市各个分区与不同功能应互相支持以形成可运作的整体。这种对都市空间整体的持久关怀,引领奥斯曼致力于将市郊并为巴黎的一部分,但皇帝对此并不是完全支持,因为市郊的任意发展将对巴黎都会区空间秩序的合理演进构成威胁。1860年,奥斯曼终于成功了。”[7]121这个新巴黎城不仅是一个现代性的场所,更是现代性本身的一个标志。它以巨大的破坏力量和似乎要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坚决态度,将自身作为一个不断突破的对象,通过破坏与创造得以保全和发展。哈维评价说,这种态度“就如同一道命令,它将世界视为白板(tabula rasa),并且在完全不指涉过去的状况下,将新事物铭刻在上面——如果在铭刻的过程中,发现有过去横阻其间,便将过去的一切予以抹灭。因此,不管现代性是否将以温和而民主的方式呈现,还是将带来革命、创伤以及独裁,它总是与‘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有关”[7]11。这是一种从过去的废墟中孕育出的新生状态。它向我们宣告:那些坚固的东西在资本的力量面前,或者灰飞烟灭,或者得以重构。这使我们想到了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著名阐释:“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8]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或短暂的。巴黎的新空间的诞生,不仅意味着它要同过去决裂,也意味着它造就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空间的生产不仅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是新的城市理念的再生产,而且也是新的情感结构的再生产。“在这个破坏性的创造和创造性的破坏的巨大破坏性力量中,即使结果必定是悲剧性的,但证实自我的唯一途径就是行动,就是显示出意志”[5]25。奥斯曼借助历史的力量,用“创造性的破坏”使他自己和巴黎一起进入到历史的暂时的永恒之中。所以,我们很难说是奥斯曼市长成就了巴黎,还是巴黎成就了奥斯曼市长。“资本主义永远试图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地理学景观(物质基础设施这些嵌入在国土中的固定资本)来便利其行为;而在另一段时间,资本主义又不得不将这一地理学景观破坏,并在另外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地理学景观,以此适应其追求资本无限积累的永恒渴求。因此,创造性破坏的历史被写入了资本积累真实的历史地理学景观之中。”[9]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或许就是通过对过去的种种摧毁和破坏,从而创造出了崭新的大都市面貌。
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走向现代性的构建过程中,对传统社会、都市、城市空间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是其核心任务之一。除了资本运作和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外,就是对过去遗留下来的遗迹进行前所未有的、全面性的空间改造和再生产,或者说是一种对于现存社会秩序和空间景观的再生产。“以现代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创造性的破坏’,通过大规模的物质与空间的改造,实现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物质、交往、阶级关系、劳资关系的根本转变。并且,这一进程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一直伴随着剥削、压迫、反抗、暴力、血腥、起义、镇压、监禁、流放、革命、反革命等惊心动魄的历史情景和史实。”[10]资本主义的大生产需要开辟新的空间,以消除资本周转的空间障碍,因而资本、时间、空间三者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空间和时间实践在社会事物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他们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5]299空间关系的剧烈变化改变着人类原本的时空视野、时空关系和时空体验。哈维分析了特定时空下巴黎变迁的动力,阐释了在重建巴黎的过程中,资本是如何与现代性互动结合的。
哈维敏锐地看到:“1848年,戏剧性的事件席卷了全欧洲,尤其是巴黎。当时的巴黎在政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上表现出与过去完全决裂的态度,对此,有人提出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合理的论点。1848年以前的都市观点,顶多只能粗浅地处理中古时代都市基础建设的问题;而在1848年之后则出现了奥斯曼(Haussmann),是他强迫巴黎走入现代。1848年之前有古典主义者如安格尔(Ingres)与大卫(David),以及色彩画家如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之后则有库尔贝(Courbet)的现实主义与马奈(Manet)的印象派。1848年之前有浪漫主义诗人与小说家,如拉马丁(Lamartine)、雨果(Hugo)、缪塞(Musset)、乔治·桑(George Sand)和波德莱尔(Baudelaire)。1848年之前,所谓的制造业者多半都是散布各处的手工业者;之后则绝大部分手工业都被机械与现代工业所取代。1848年之前只有小店铺沿着狭窄、弯曲的巷弄或骑楼开张;之后在大马路旁出现了巨大笨拙的百货公司。1848年之前盛行的是乌托邦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后则是顽固的管理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从这些方面来看——还有更多的方面——1848年似乎是个关键时间点,许多新事物于此时从旧事物中孕育。”[7]2哈维把1848年视为一个重大时刻。这一年对很多思想家和艺术家来说,都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分水岭,奥斯曼、波德莱尔、马克思、福楼拜等人都是在1848年之后崭露锋芒的。时空视野的变迁,都市空间体验方式的变化,必然在文学、艺术和文化上引起回应和共鸣。各种闪现的意象和新的都市空间给人们带来新的艺术感受力,就好像“正是从这样的感受——焦虑和骚动,心理的眩晕和昏乱,各种经验可能性的扩展及道德界限与个人约束的破坏,自我放大和自我混乱,大街上及灵魂中的幻象等等——之中,诞生出了现代的感受能力”[11]。在对巴黎城市改造的分析中,哈维非常关注由“创造性的破坏”所带来的空间体验的变化。他借助巴尔扎克的小说《人间喜剧》,展开了对巴黎的社会、历史、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思考,把研究视角放到城市改造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上,努力阐释在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中人们的内心体验和艺术创作的改变,以及现代艺术发展的新方向。
据哈维在《作为关键词的空间》一文中的研究,他把“空间”范畴划分为三种:“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相对空间”(relative space)和“相关空间”(relational space)。艺术作品的各种物质媒介和材料构成了艺术作品物质性的“绝对空间”,这是一个能让观众直接感知到的物质实体层面。艺术作品的“相对空间”与不同空间的关系性相联系,也与艺术家使用的艺术手段和艺术技巧——即使用何种方式来表现世界有关。就此而言,艺术家们的艺术表现方式与他们的艺术观念、创作态度有着密切关系。艺术作品的“相关空间”与艺术家内心的想象、情感、梦想、幻觉、心态、记忆等有关,它们全都通过艺术作品的表现得以呈现出来。当人们在这种相关性的内心空间的影响下进行创作或审美的时候,人们便会产生出新的审美体验,并且会唤起不同的内心感动。在哈维看来,“这种相关性是艺术作品要表达的最为重要的内容。”[6]在哈维关于空间的理论中,他始终都非常强调这三种不同空间之间的复杂性、相对性和辩证性。当现代大都市经历过创造性的破坏和改造之后,我们需要在新的视野中重新审视空间及其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历程,实质上就是对传统的社会空间进行“创造性的破坏”的过程。城市通过大规模的物质性改造和空间改造之后,实现了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等方面的巨大转变。哈维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显然无所不在,社会关系便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各项物品之中。任何物品的重新制造都将造成社会关系的重新排列:在建造与重建巴黎的过程中,我们也建造与重建了自我,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把巴黎想成有知觉的存在,等于承认巴黎隐约是个身体政治体。”[7]65经过这种剧烈的改造之后,生活于全新都市空间中的艺术家们强烈感受到都市空间变化的巨大冲击,经历着空间体验方面的全新感受,并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表达出来。例如,就波德莱尔来说,他每天都生活在两难之中,仿佛被不同的力量撕裂一般:一方面,他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一个摆脱世俗常规、愤世嫉俗的“浪荡子”;另一方面,他却有着热烈追寻的目标。他对破坏和创造有着一种原始的兴奋,对于毁灭的产生有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愉悦感。在他看来,为了牢牢抓住现在、创造新的未来,旧的传统就必须被颠覆。然而,丧失旧传统又使人感到茫然无力。波德莱尔时刻都处在现代性的矛盾之中,所以他写道:“每个地方都充满了欢乐、金钱与放浪;每个地方都保证明天一定有面包可吃;每个地方都爆发出汹涌的生命力。”[7]7
巴黎,在19世纪后半叶被资产阶级的力量塑造成了一座资本之城的首都,一座西方现代性的首都。破旧立新,要创造出新的社会和空间形态,因而“创造性的破坏”就成了这一过程的关键性因素。“创造性的破坏”塑造了巴黎的新城市空间,催生了现代性的空间体验及其在艺术中的表达,使巴黎的城市空间成为资本与政治角力的场所。社会和城市的历史,在这种破坏与摧毁中创造出崭新的面貌。它意味着现代社会中新的共同体、新的都市观念、新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新的巴黎人的产生。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孕育了破坏性与创造性,这就是理解哈维关于现代性的思想的重要基石。哈维曾经指出,空间化的逻辑将主导和支配着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社会及其物质实践:“它在赞美普遍性和空间障碍的崩溃之时,也以默默加强了地方身份的各种方法探索空间和场所的各种新含义。”[5]341可以说,空间是历史演变的产物、社会变迁的产物,是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同时,空间也是动态的、流变的。生活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不只是生活在特定的物质空间之中;人们的想象、意识和表达方式同样也在调节着这样的社会空间。因此,人与空间的辩证关系,始终都是一个动态的变化和呼应的过程,而哈维关于“空间”概念的理论,确实是我们正确认识这一切复杂关系的一把钥匙。
[1] 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M].Wiley-Blackwell,1992:22.
[2]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8.
[3] 哈维 戴. 作为关键词的空间[C]//外国美学:第22辑.阎嘉,译. 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137.
[4] 阎嘉.马赛克主义:后现代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3:99.
[5] 哈维 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 阎嘉.不同时空框架与审美体验:以戴维·哈维的理论为例[J].文艺理论研究,2011,(6).
[7] 哈维 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黄煜文,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8] 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郭宏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485.
[9] 哈维 戴. 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沈小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3.
[10] 阎嘉. 现代性的文学体验与大都市的空间改造——读戴维·哈维《巴黎,现代性之都》[J].江西社会科学,2007,(8).
[11] 伯曼 马.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徐大建,张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9.
[责任编辑:修 磊]
2015-07-18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西方后现代文艺理论关键词研究”(SC14C034S)
毛娟(1980—),女,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
I0
:A
:1002-462X(2015)11-013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