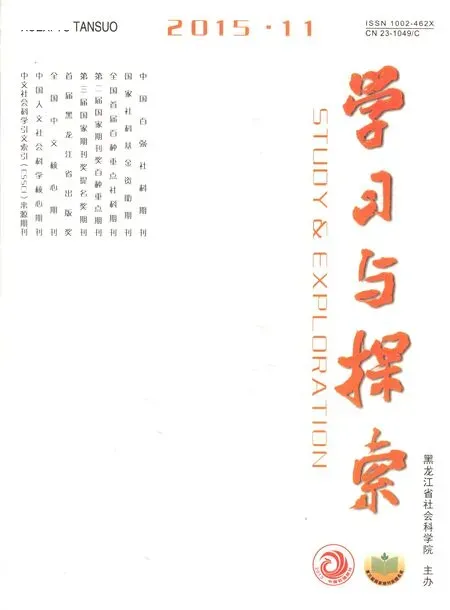视觉艺术中的后现代空间:戴维·哈维如是说
阎 嘉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视觉艺术中的后现代空间:戴维·哈维如是说
阎 嘉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戴维·哈维对后现代视觉艺术空间问题的论述,始终立足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把艺术表征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变迁所带来的空间体验的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他通过对舍曼、劳申伯格等人的作品、建筑、形象工业等视觉艺术的分析,抓住了后现代在空间呈现方面的无深度的面具、异质性的“他者”世界和碎片式的拼贴等重要特征,认为这些特征是后现代时代新一轮“时空压缩”在艺术表达方面造成的后果。
戴维·哈维;文化研究;视觉艺术;后现代主义;空间;时空压缩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用“后现代主义”一词来命名美国文学和文化中出现的新趋势,并提出:“我们不能只理解文学上的后现代主义,而不去考虑一个后现代社会现象,甚或西方人文主义的一次突变。”[1]哈桑还以列表的方式对比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文艺和其他领域里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欧美学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争中,戴维·哈维基本赞同哈桑的观点,并于1989年出版了《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角度,探究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所造成的新一轮“时空压缩”及其在艺术和文化方面的表征。在哈维看来,艺术表达实际上是空间化的一种特殊方式,它通过不同的符号和代码系统将流动着的内心体验凝固下来,同时也折射出导致不同空间观念所由产生的物质实践活动的推动力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化变迁。
在论述后现代空间观念的变迁时,哈维列举并分析了建筑、绘画、摄影、广告、时装、电影、电视等视觉艺术中的大量作品,以说明“我们也不是以各种任意的方式来设想或呈现空间的,而要寻求某种适当的、即便不是精确的反思,通过抽象的表现(词语、图示、地图、图表、图画等等)来反思围绕着我们的物质现实……我们也试图呈现这种空间在情绪和情感方面的状态,以及在物质方面依靠诗歌意象、摄影构图、艺术重构生活的状态”[2]138。哈维相信:“美学理论要在流动和变化的旋涡之中寻找出使永恒不变的真理能够传达出来的各种法则。以最明显的情况为例,建筑师试图通过建造一种空间形式来传达出某些价值观。所有的画家、雕塑家、诗人和作家都这么做。”[3]257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哈维对后现代视觉艺术中体现出来的空间及其价值观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深入剖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视觉艺术中的空间问题的独特视角。
一、后现代视觉空间与无深度的面具
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1954—)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摄影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她的成名恰逢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走向高潮之际。她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拍摄以自我为模特儿的照片,经常通过道具、服饰、化装和特殊光线效果来呈现美国不同年代的典型女性形象,以唤起人们心目中的各种流行影像。哈维在80年代后期参观过舍曼的摄影作品展,他在《后现代的状况》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观感:
那些照片描绘了表面上不同的、来自各界的妇女们。稍加注意就会有些震惊地发现,那些都是穿着不同装束的同一个女人的照片。只有目录告诉了你:那位女人就是艺术家本人……作者们自我指涉的定位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就是主题。辛迪·舍曼被认为是后现代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人物[3]12。
舍曼的摄影作品最明显的视觉特征就是以人为的、多重伪装的影像来制造不同“面具”的幻象,并且进一步成为各种影片和媒介形象的明显参照物。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里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当代文化生产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丧失深度”,其后果是只关注外表、表面和瞬间的冲击力,但却不具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持久力量。哈维认为,舍曼的摄影作品恰恰具有这样一些典型的后现代特质。面对她所呈现的那些视觉影像,“我们的主观体验可以把我们带入感知、想象、虚构和幻想的领域,它们产生了内心的空间和图像,就像很多想象上‘真实的’事物的幻象”[3]253-254。
哈维所揭示的舍曼摄影作品无深度的“面具”特质,可以借用鲍德里亚“拟像”(Simulacra)理论中的“仿真”(simulation)概念来做更为精确的说明。鲍德里亚认为,在后现代时代,人们看到的由媒介呈现出来的世界并非真实的世界,而是一个由被操控的符号和形象所构成的“超真实”世界,真实的世界早已消失。他以摄影术为例,指出了“仿真”所犯下的“完美罪行”。
被拍摄成照片的物体,都只能是为所有其他物体的消失而残留下来的痕迹,几乎是完美的犯罪。世界几乎全面地融解,结果,只有残留在这里那里的幻觉在闪闪发光。在这个时候,物体的形象成为了难以捉摸的谜。从这个根本的例外朝世界望去,你会获得永远无法遮掩的景象[4]78。
在二维影像的空间中,固然存在着某些看似逼真的“闪闪发光”的细节乃至表面的肌理,但它们都不过是真实世界的一种幻觉,一种与真实世界相分离的面具。在舍曼共计69张系列照片的《无题电影剧照》中,虽然由影像呈现出来的各种旧式电影主角或场景的仿真剧照旨在唤起人们的怀旧情绪和形象记忆,但在另一方面,面具影像掩盖了真实物象,空间幻象制造了感知错觉,因而真实的主体和物象消失在了高仿真的细节与肌理之中。或许,这才是舍曼要达到的真正视觉效果,就如她大胆声称的:世界出自我的扮演。于是,后现代视觉空间中面具的消费价值,通过舍曼等人的作品得以彰显。
与舍曼的摄影作品相似,在后现代时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把充斥于各种视觉艺术形式中的形象本身变成了商品,致力于流行符号、符号系统和形象的生产,由此催生了被哈维称为的“形象生产工业”。在很多情况下,艺术符号和形象往往与物质空间中的实体无关,甚至与创作主体的内心感受和趣味无关,其价值主要在于通过符号与形象来操控观众的欲望和趣味。因此,作为商品的符号和形象,既不指涉人们内心的情绪表现的空间,也不指涉客观世界的物质空间。这种情形,正如哈维以广告为例尖锐地指出的:“如果我们把现代广告同直接有关的金钱、性和权力这三个主题剥离开来,那么几乎就剩不下什么东西。”[3]369然而,由于很多符号和形象可以像舍曼的摄影作品那样通过空间即刻大量销售(如各种广告、电视等),因此,它们经常会在艺术之外起着其他众多非审美的功用,经常要为企业、政府、政治、知识分子等机构和群体服务,变成了他们的权威、权力和魅力的一部分。符号和形象服务于政治,可以成为政治审美化的重要力量。在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中,符号和形象也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以至投资于形象建构(展览会、广告、营销等)经常变得跟投资于固定资产一样重要。符号和形象还可以服务于在公共领域里建构个人身份的需要,可以成为个人财富、地位、名声、权力、阶层的象征,以至于个人形象顾问如今在西方世界成了可以赚大钱的行当。
在哈维看来,后现代艺术实践不同于现代艺术实践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体现在当代西方的文化生产极为关注各种事件、表演、偶然性和媒介形象。大多数文化生产者都已经学会了探索和运用新技术、新媒介以及多媒体的各种可能性。文化生产的效果最终是要重新突出当代社会流变的特质,并且要赞颂那种特质。哈桑曾经提出,后现代的大众消费文化明显出现了风格上的转变,调动时尚,流行艺术,普及电视,其他媒介形象和各种都市的生活方式,都已经构成了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哈维认为,对哈桑的这一观点值得反思,即我们不应该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某种自发的艺术潮流,因为有各种明确的表征揭示了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根源。就此而言,哈维非常精辟地剖析和刻画了作为一种幻象的“面具”的作用与特征。
有很多更加明确的领域,幻象在其中具有一种被强化了的作用。运用现代建筑材料可以使复制古代建筑达到很精确的地步,以至于真实性或原物都可能受到怀疑。古董和其他艺术品的制造完全成为可能,这使高级赝品成了艺术收藏行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因此,我们不仅有能力折中地和同时地在电视屏幕上堆积来自过去或其他场所的各种形象,甚至也能以人造的环境、事件、表演和类似的东西而把这些形象转变成物质幻象,它们在很多方面都难以同原物区分开来[3]362。
视觉艺术空间中充斥着的大量面具、幻象、高仿真的赝品、与实质相分离的表面形象,以及通过日新月异的媒介和技术迅速而大量地传播,凡此种种,无一不表征着后现代视觉艺术中的表达危机。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种现象,除了舍曼的摄影作品和“形象生产工业”之外,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中还专门对里德利·斯科特的科幻电影《滑刀》(一译《刀锋信使》)和维姆·温德斯寓言式的电影《欲望的翅膀》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旨在强调:“近年来对于时空压缩的体验,在转向更加灵活的积累方式的压力之下,已经在各种文化形式之中产生了表达的危机,这是认真的美学所关注的一个主题……这样的文化实践很重要。”[3]405这样的后现代文化实践的结果,实际上打碎了原本连续的时间链条、意义链条和逻辑链条,把这些链条上原本相互联系的面具、形象、符号变成了碎片化的、孤立的空间存在,变成了视觉艺术作品中脱离了实质、真实的种种形象和幻象。这是后现代艺术中表达危机的关键之所在。
视觉艺术中的诸种表征必定有着它们产生的根本原因。哈维从其独创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立场出发,不是在艺术自身发展演变的内部或艺术家个人经历的探索中去寻找根源,而是把探求的锋芒指向了社会历史和政治经济实践——因为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已然从“福特式”的大规模生产转向了灵活积累的弹性生产,时空体验随着物质财富和技术的不断更新已然发生了变化,艺术家与历史的关系也已经转变。因此,哈维最重要的结论性的观点是:“始于60年代晚期、并在1973年达到顶点的过度积累的危机,恰恰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结果。对时间与空间的体验已经改变,对科学判断与道德判断之间的联系的信念已经崩溃,美学战胜伦理学成了社会和知识关注的主要焦点,形象支配了叙事,短暂性和分裂的地位在永恒真理与统一的政治之上,解释已经从物质与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领域转向了思考自主的文化和政治实践。”[3]410
所有这些,便是哈维为我们揭示的后现代视觉艺术的面具与幻象背后的真实。
二、后现代视觉空间与异质性的“他者”世界
在后现代视觉艺术领域里,我们经常会在视觉空间中发现将不同的、异质性的“他者”世界拼接在一起的视觉呈现。在绘画、建筑、广告、表演等艺术形式中,尤其是在电影和电视等“活动着的”视觉形式中,异质性的“他者”世界的并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视觉现象。例如,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 1925—2008)作为后现代主义绘画的开拓者之一,经常将废品、实物、照片、颜料等异质性材料拼贴组合在一起,在试图打破雕塑、工艺品、绘画和日常生活材料之界限的同时,也创造了使异质性的“他者”世界共存于二维平面之中的视觉“奇观”。哈维认为,劳申伯格将17世纪西班牙巴洛克画家委拉斯开支《镜中的维纳斯》和17世纪尼德兰巴洛克画家鲁本斯《梳妆的维纳斯》的照片投射到有卡车、直升机、汽车钥匙等物体影像的丝质屏幕上,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在直接引用、堆积和“复制”早已存在的各种异质性的形象,取代了创造性主题的虚构。
哈维借用福柯“异位”的概念来说明异质性的他者世界:“福柯说的异位是指在‘大量分裂的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不可能的空间’里的共存,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互相并置或附着的没有共同尺度的各种空间。”[3]69这就是说,完全不同的元素被人为地并置在某个人造的空间里,彼此之间并非按日常生活的逻辑共存。哈维用后现代电影中常见的情景来说明这一问题:
我们在一部像《蓝色天鹅绒》那样的影片中发现了一个穿梭于两个完全不一致的世界之间的核心人物——20世纪50年代一个普通的美国小镇,它的高中、药房文化的世界,与毒品、老年痴呆症和性反常的稀奇古怪、暴力和性疯狂的下层社会。看来不可能的是,这两个世界竟会存在于同一个空间里,那个核心人物在它们之间运动,无法确定哪一个是真实的现实,直到这两个世界在冲突中达到一种可怕的结局[3]69。
问题的核心在于,是否要承认他者世界的真实性或“本真性”?如果是这样,就势必会触及现实世界与他者世界之间交流和控制的方式问题。显然,对后现代艺术来说,它更关注的是差异性、多元性和复杂性,而不是统一性、同质性和一致性。现代主义对元语言、元理论、元叙事的强调,经常会忽略或者掩盖对后现代主义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往往与个人的主体性、性别、种族、阶级、时空感受以及在地理位置上的错位相关联。因此,强调差异、分离、细节、异质性等特质,构成了后现代视觉艺术空间之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哈维非常明确地承认了后现代主义在强调他者世界的差异性和异质性方面的重要意义:“应当如何从总体上评价后现代主义呢?我的初步评价如下,那就是它对差异的关注,对交流之困难的关注,对利益、文化、场所及类似东西的复杂性与细微差别的关注,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了一种积极的影响。”[3]151他甚至还援引了法国学者利奥塔的观点来形象地描述后现代的知识状况:“我们的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座古代的城市:一座由狭小的街道和广场、旧的和新的房屋、不同时期附加于其上的各种房屋所构成的迷宫;这座迷宫被大批具有笔直规则的街道和相同房屋的新村镇所包围。”[3]66这种错杂和分离的景象使人想到,生活在那个“城市”之中的每个人都会依赖一套完全不同的代码,而所使用的代码则取决于人们在其中发现自己的情景——在家里,在工作中,在教堂里,在街上或小酒店里,在追思礼拜上等等。
鲍德里亚在讨论摄影术时曾对“他者”做出过这样的界定:“不以我的意志为存在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大写的‘他者’,才真正是根本的他者性。”就摄影术来说,“拍摄照片不是将世界作为物体理解,而是将世界看成物体,把埋藏在叫作现实的东西之下的他者性发掘出来。让世界作为奇怪的吸引者出现,并且把它的奇妙的吸引力在影像中固定下来。”[4]79照此理解,“他者”不仅是与自我的“主体”相对立的某种存在,而且是一种隐藏于现实事物之下的根本性存在。后现代视觉艺术的一个特别关注点,就是要将这种本真的“他者”揭示和呈现出来,以引起观众的注意和震惊。从这种意义上看,在视觉上引起我们好奇、关注和震惊的“他者”,实际上也可以引起我们在内心和理智上的反思。尤其是在后现代状况下,当物质生产和技术发展带来的新一轮“时空压缩”造成了我们对时空体验的碎片化、短暂性和易变性之时,对本真性、不变和永恒的探寻与追求,就会变得越发强烈。因此,辛迪·舍曼的那些自拍照,通过呈现一个“自我”经过化装改变后的形象和幻象,实际上提出了本真与幻象、自我与他者、外表与实质之间对立的问题,同时也暗示了追寻不变、永恒、本真的意图。电影《滑刀》中的“复制人”与真实的人类之间的关系,也触及到了同样的问题。正如哈维所说:“复制人们生存于杰姆逊、德勒兹和瓜塔里以及其他人认为是后现代生活之核心的精神分裂症式的时间的急流之中。他们以一种同样跨越空间之广度的运动的流动性,使自己获得了一大笔体验的资金。他们的角色在很多方面都与全球即刻通信的时间和空间相吻合。”[3]388
看来,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一样,总会在波德莱尔所揭示的一组矛盾对立之间摆动和徘徊:“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5]哈维认为,短暂、偶然与永恒、不变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由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资本在全球地理空间中的扩张这种现实物质活动造成的;只要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和资本主义追逐物质、金钱的本性不变,由此造成的我们在体验时空方面的这种矛盾就不会消失。
历史地看,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急剧扩张,以及伴随着这种扩张而来的“创造性的破坏”,加剧了人们在时空体验与艺术表达方面的紧张感和焦虑感。哈维正是从这一角度对现代主义艺术的变革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述:“毫不偶然的是,第一次伟大的现代主义文化突进于1848年之后出现在巴黎。马奈的画笔开始分解传统的绘画空间并改变其构架,探索光线和色彩的分解;诗歌和波德莱尔的思考力图超越短暂和狭隘的地方政治,寻求永恒的意义;福楼拜的小说及其独特的空间和时间叙事结构与冷冰冰的孤僻语言并驾齐驱;所有这些都是彻底突破这样一些文化情绪的征兆:反映了在一个不稳定的、迅速扩张的空间范围的世界里对于空间和场所、现在、过去和未来之意义的深刻追问。”[3]328这种发展脉络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则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就毕加索和布拉克来说,他们从塞尚那里得到了暗示,而塞尚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用各种新方法分解绘画空间,用立体主义进行试验,因而抛弃了自15世纪以来起着支配作用的‘线性透视的同质空间’。德洛奈1910年至1911年描绘埃菲尔铁塔的受人欢迎的作品,也许是一场试图通过分解空间来表达时间的运动中最使人吃惊的公共象征:拥护者们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比得上在福特的流水生产线上的实践,虽然选择埃菲尔铁塔作为象征物反映了整个运动与工业主义有着某种关系的事实。”[3]335
我们从这些分析和论述中可以看出,哈维对艺术史、艺术家及其作品不仅非常熟悉,而且将它们放到历史语境中做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问题而言,很重要的是,哈维指出了现代主义艺术与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一方面存在着内在逻辑联系,另一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别:现代主义在迅速变化着的时空体验中力图去把握和揭示“永恒不变”的东西,后现代主义则敏锐地觉察和呈现了时空体验中偶然和短暂的一面。现代主义专注于发现表达永恒真理的特殊方式,把大部分艺术变成了一种“自我指涉”的建构,而不是当成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后现代主义则致力于表现面具、幻象和他者的世界。然而,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这种看似不同的背后,始终都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后者并不是某种全新的艺术探索和文化运动,而是晚期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新趋势的某种反映。
因此,艺术表达要面对的短暂、偶然与永恒、不变之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是一个涉及艺术技巧、艺术风格或艺术家个人追求的问题,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和辩证的关系。哈维认为,如何表达一切混乱之中的永恒不变,就艺术家、建筑师和作家来说,必须寻找到表达它的某种特殊方式:
像詹姆斯·乔伊斯和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像马拉美和阿拉贡那样的诗人,像马奈、毕萨罗、杰克逊·波洛克那样的画家,都显示出了对于用他们自己建构的语言创造新代码、意味和隐喻的一种极度关注。但是,如果词语真的是流变的、短暂的和混乱的,那么正因为这样,艺术家就必须通过一种即刻的效果来表达永恒,制造“震撼的手法,违反期待的连续性”,这对于艺术家们力求传达之信息的冲击目标来说至关重要[3]31-32。
根据重庆市传统商贸流通业发展现状,建议在全市批发行业、零售行业、住餐行业、对外贸易、生活服务、商务服务、物流行业、现代农业等八大行业中实施“+电子商务”创新应用。
在某种意义上,对异质性的他者世界和差异性的关注与艺术表达,制造艺术上的震惊效果,体现了后现代艺术对本真性和永恒问题的极度关注。
三、后现代视觉艺术空间与碎片式的拼贴
后现代视觉艺术在空间表达方面的碎片化特征,最明显地表现在普遍而广泛地使用拼贴的手法,即将源于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不同地域、不同特质、不同风格、不同趣味的艺术质素,通过剪切、拼贴与组合,构成如“万花筒”或“百衲衣”般的整体,造成一种在视觉上极具冲击力的异质性视觉奇观。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哈维援引德里达的观点指出,拼贴和蒙太奇是后现代话语的主要形式,它们表现在建筑、绘画和写作之中,以其内在的异质性激励观众参与作品的创造过程,从而创造出某种既不可能是单一的、又不可能是不变的文本意义。文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参与了意义的创造,因而强调了过程、表演、偶发事件和参与的重要性。通过把文化产品生产者的权威性降到最低,为大众参与艺术生产和民主确定文化价值提供了机会,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支离破碎的视觉形象,以及操控大众文化市场的脆弱性[3]72。
哈维列举的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美国著名的后现代建筑设计师查尔斯·穆尔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设计的新奥尔良的意大利比萨饼店。比萨饼店位于一个象征着比萨饼的圆形广场,广场吸收了附近一幢摩天大楼的黑白线条元素,由一圈由大而小的同心圆构成。入口处有一个小小的神殿,广场的地面镶嵌着意大利地图,同心圆中央的喷泉象征着从阿尔卑斯山高处瀑布般奔流下来的水,为地中海中靴形的意大利“沐浴”。两侧是多立克式、爱奥尼亚式、科林斯式、图斯坎式和混合式五种经典的古典柱式,再配以奇幻微妙的色彩变化和霓虹灯:
所有这一切带来了古典建筑高贵的词汇、直到最新的流行艺术技巧、后现代主义的调色板和戏剧性。它把历史设想为便于携带的附属品的连续统一体,反映了意大利人自身被“移植”到新大陆的途径。它呈现了一幅意大利文艺复兴、巴洛克宫殿及其比萨饼的怀旧图画,但与此同时,又有一种错位的感觉[3]129。
哈维通过对这一经典的后现代建筑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虚构、分裂、拼贴和折中主义,全部都弥漫着一种短暂和混乱感,它们或许就是支配着今天的建筑和城市设计实践的主题。显然,它们与其他很多领域里的实践和思想有着很多共同之处,如艺术、文学、社会理论、心理学和哲学。”[3]132对比之下,现代主义建筑体现了大规模、理性和效率的精神,形成了强调功能和简朴的“国际主义风格”,其典型代表是包豪斯的设计理念。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建筑则奠基于一种分裂的、碎片式的都市结构理念之上,用彼此叠加和层层相覆组合成一种拼贴物,暗示着一种不可控制的短暂性,呈现出某种对地方传统、地方历史、特殊审美需求和癖好的敏感,呈现出光怪陆离、眼花缭乱和令人惊奇的视觉效果。它打破了连续性、统一性、明确的功能与目的等现代主义的观念,追求一种表演性的炫目。在哈维看来,建筑作为一种具有“永久性”的物质形式,应当具有明确的功能和目的,应当体现出某种价值理念的权威性和重要性,而不应当是一种随意性的拼贴物。他以美国纽约的世贸大厦遗址为例提出:“我们可以无限制地争论表现世贸大厦遗址之关系性的各种各样的理念和设计,但在某个点上,某种东西必须在绝对空间和时间里被物质化。一旦建成,那个场所就获得了一种物质形式的‘永久性’(怀特海语)。虽然人们总是容易把那种物质形式的意义重新概念化,以便人们可以学会以不同方式去经历它,但建筑在绝对空间和时间中的纯粹物质性,传递出它自身的重要性和权威性。”[2]151就这个例子而言,它的物质形式应当传达出与2001年的“9·11”事件相关的历史和重要理念,而不是花哨的碎片式和拼贴式的外表。
在绘画和摄影领域里,后现代主义艺术将20世纪达达主义所发明的“拼贴”技巧发挥到了极致,出现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和劳申伯格等人的拼贴画,以及丹尼尔·斯波里(Daniel Spoerri,1930—)和安德雷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1950—)等人的拼贴物摄影作品。他们不仅把作品所使用的媒材的范围扩大到废品、垃圾、死尸、尿液等一切可以利用之物,而且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平庸、琐碎、恶俗、惊悚乃至恶心的视觉感受和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拼贴技巧的普遍运用,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更加快捷便利的制作手段,在各种新媒体的助推之下,加快了视觉影像即时、迅速、多维度的呈现方式,彻底改变了手工呈现时代的作品面貌。与此同时,突破影像呈现的媒材的局限一方面为大众参与制作作品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则向传统视觉艺术的审美理念和价值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广告、包装、表演等形象工业借助拼贴技巧迅猛发展的同时,博物馆文化在后现代视觉呈现领域异军突起,与“遗产工业”一道,构成了文化工业领域里前所未有的视觉景观。博物馆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根据个人或机构的某些权宜之计和价值选择,随意裁剪、拼贴、组合、并置不同历史和文化传统,将时间链条上某些线性的瞬间拼贴为一种共时性的空间形象,由此产生出时空交错和混杂的视觉感受。据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英国每3个星期就有一家博物馆开张,日本在15年间竟有500多家博物馆开业。以此为例,可以推想从那时到现在,全世界有多少博物馆先后诞生出来。这种情景加上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起飞并迅速增长的“遗产工业”,按照哈维的说法,这两者的结合“为把历史和各种文化形式商业化增添了又一种平民主义(尽管此时只是中产阶级)的花样”。后现代主义和遗产工业的联姻,使“双方共谋创造了一道介于我们现在的生活与我们的历史之间的肤浅的屏幕”,对历史的呈现被依赖拼贴发展起来的遗产工业彻底改写,使历史变成了一种“当代的创造,更多的是古装戏和重新演出,而不是批评性的话语”[3]87。
除此之外,我们在世界各地还可以看到,大型的广场表演、时装表演、电视表演等等大众参与的商业化视觉呈现形式,无不普遍使用碎片化的拼贴和蒙太奇手法来制造后现代的视觉奇观与幻象,以至于造成了鲍德里亚所说的通过“拟像”来制造“超真实”的景象。这在后现代时代已然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状况。
那么,应当如何说明这样一些碎片化的、拼贴的“视觉盛宴”和高仿真的赝品呢?哈维对此做出了如下解释:
还出现了更加深刻的意义和解释的问题。短暂性越强,需要发现或者制造某种存在于其中的永恒真理的压力就越大。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宗教的复兴,和在政治之中追求本真性和权威性(以及它的所有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装备,对那些具有超凡魅力的和“多才多艺的”个人及其尼采式的“权力意志”的崇拜),都是这个问题的例证。对于基本构成(如家庭和社群)的兴趣的复苏与追寻历史根源,都成了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寻求更加可靠的支撑物和较为持久的价值的征兆……家庭成了防范时空压缩之劫掠的私有博物馆。此外,正是在这个时候,后现代主义宣告了“作者的死亡”和在公共领域内反对有韵味的艺术的崛起,艺术市场更加意识到了艺术家签名的垄断力量,以及本真性和赝品(无论劳申伯格的作品本身仅仅是一种复制的蒙太奇)问题的垄断力量[3]365-366。
哈维的这一解释透过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幻象,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后现代时代随着资本全球扩张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弹性生产与灵活积累,给人们带来了内心深处的“时空压缩”的感受。因此,“我们就这样逼近了核心的悖论: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对各个场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就越大。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集中化与分散化之间在历史上有名的紧张关系,现在以各种新的方式产生出来了。”[3]270质言之,时空压缩的感受所造成的短暂性成了碎片化拼贴和复制的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则在于资本扩张、物质生产与技术发展,由此导致人们试图在迅速流变的外表和碎片之下去抓住某种仿佛是“本真的”、永恒不变的实质。在视觉艺术中,碎片化拼贴和幻象的外表之下,往往隐藏着某种焦虑与惶恐;在打碎时间链条的空间组合与叠加中,暗含着寻求某种统一性的意图。不过,艺术家们凭借对外表变化的敏感和探寻艺术表达方式更新的执着,往往能在感性的呈现中同时把握住某种内在的深层变化——“时空压缩”给我们的感受和体验带来的挑战、刺激与困惑。
在论及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文化表征与空间表达的问题时,哈维始终都以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作为对比和参照系。他坚持认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历史与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之间,更多地存在着的是一种连续性,而不是彼此之间的差别。后现代主义更明显地呈现为现代主义内部的一种特定的表达危机,它突出了波德莱尔所说的分裂、短暂和混乱的一面,对它的深度分析和透视,应当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所看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整体的一个方面。它深刻怀疑在艺术中表达短暂性之危机的一切特定解决处方,同时也怀疑应当如何设想和表达永恒与不变。
与此同时,哈维对后现代主义始终都抱着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尖锐地指出了它的一些弊端,诸如它对“享乐”之短暂性的强调,它坚决主张“他者”的不可测知性,它专注于文本而非作品,它爱好几近于虚无主义的解构,以及它偏爱美学而非伦理学等等。哈维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所有这些弊端,都使问题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太远。
然而,面对后现代主义视觉艺术所呈现的种种迷离错乱的幻象,哈维却坚信历史唯物主义和新的启蒙规划终将得到复兴:“经历过第一次复兴之后,我们可以开始把后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历史—地理状况。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之上,有可能发动一场叙事反对形象、伦理学反对美学、规划‘形成’而不是规划‘存在’的反攻,并在差异内部寻求一致,尽管是在一种清楚地理解了形象与美学的力量、时空压缩的各种问题以及地理政治学和他者之意义的语境之中。”[3]446
[1] HASSAN I.The Postmodern Turn: 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M].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89.
[2] 哈维 戴.作为关键词的空间[C]//外国美学:第22辑.阎嘉,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
[3] 哈维 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 鲍德里亚 让.消失的技法[C]//罗岗,顾铮,译.视觉文化读本.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 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郭宏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24.
[责任编辑:修 磊]
2015-07-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戴维·哈维‘时空压缩’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11BWW004);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当代西方后现代文学理论专题研究”(skqy201320);四川省“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时空压缩与现代审美体验研究”(15ZD01)
阎嘉(1956—),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理论、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研究。
I0
:A
:1002-462X(2015)11-01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