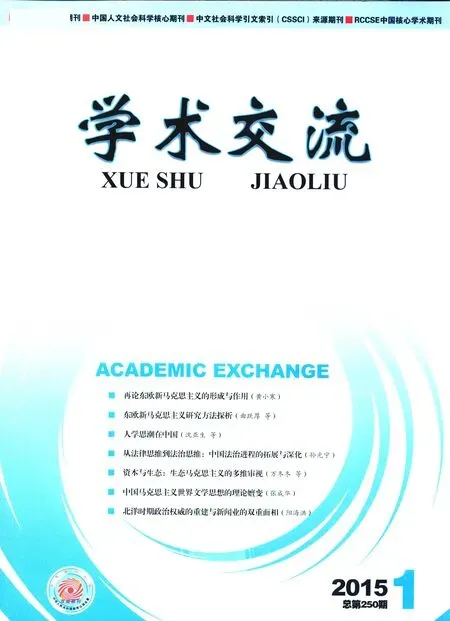作为一种理论假设的“共产主义世界文学”
——对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新路径的探讨
谭 成
(重庆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政治学研究所,重庆 400020)
世界文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专题·
作为一种理论假设的“共产主义世界文学”
——对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新路径的探讨
谭 成
(重庆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政治学研究所,重庆 400020)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是由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文学和共产主义时代的世界文学两部分构成。共产主义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理念存在对当前的文学研究具有引导性意义,它不仅将反抗当前的世界文学体系作为理论建构的首要目标,还在方法论上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作家而言,反抗西方帝国的中心文学需要一种真实的形式创新;对批评家而言,反抗帝国文学需要借助文学事件和文学真理等新的概念范畴重写世界文学史,为重建世界文学秩序提供一种可能性。
世界文学;马克思主义;阿兰·巴迪欧
当今,世界文学问题已经成为众多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然而,两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对世界文学的认识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莫莱蒂甚至认为,对于世界文学,我们仍未进行过真正的理论梳理,还缺乏确切的概念性认识,总之,“我们不知道究竟什么是世界文学”[1]242。此话并非虚言,至少在许多左翼理论家看来,世界文学依然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
如果我们追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文学的最早论述,会发现“世界文学”是以一种理论假设的形态出现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文字曾被无数的研究者所引用:“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2]这一论述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认识之上。资本主义全球性市场的拓展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物质生产的世界化带来了精神生产的世界化,并且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精神消费方式。这是民族文学和地方文学能够成为世界文学的前提。然而,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他们用理论假设的形式“预言”了这一时代。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在其时代宣称世界文学已经到来,而是将目光朝向了未来。进而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性立场使得《共产党宣言》中“世界文学”概念具备了双重内涵:其一,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文学。这是《宣言》中“世界文学”的实际所指。其二,共产主义时代的世界文学。这是《宣言》中的潜在所指。为何这么说呢?当马克思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之时,我们就难以否定同样存在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别、区域的,崭新的世界性文化,即在共产主义时代会出现一种新的世界文学。如果要建立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理论,就必然要提出这一理论假设,因为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理论实际上是由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文学研究和共产主义时代的世界文学研究两部分构成的。前者具有批判性的理论意义,后者具有建构性的意义;前者是针对现实文学环境的认知框架,而后者则是跳出当前研究视域、实现理论革新的思想起点。因此,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时代提出共产主义的设想一样,我们需要通过确立“共产主义世界文学”的观念,向当下世界文学研究提出新的任务和新的使命。
一、作为方法论的起点:共产主义世界文学的理念
共产主义世界文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理论假设的重要构成,并不直接关涉其现实性存在,而是关涉其作为“理念”(idea)的功能性存在,即共产主义世界文学作为一个真实理念如何对现实文学研究产生影响。在此,我们借助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对“共产主义理念”的思想贡献,来进一步阐明共产主义世界文学理念的功能性内涵。
巴迪欧在现时代重提共产主义,主要是针对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反抗运动的观念性缺失。例如,“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性造反,尤其是埃及和突尼斯……这些反抗者并没有生产出一个观念——以此为基础,造反运动的忠诚能被组织起来。因此从纯形式的立场来看,阿拉伯世界的优柔寡断,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几乎已被见证。”[3]巴迪欧在阿拉伯世界的反抗运动与1848年欧洲革命之间发现了相似性,这些革命都没有使国家和社会发生根本变化。但不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欧洲革命背后的观念性缺失,为冲破旧意识形态的禁锢,开启新的历史进程,他们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因为他们相信解放政治必须通过一种终极观念的引导才能成功实现。巴迪欧采取了同样的策略,提出了他的“共产主义理念”。巴迪欧把共产主义称为解放政治的最高理念(Idea),这是他对柏拉图哲学的改造。对于理念(Idea),他有如下说明:“我将‘理念’称之为个体(她/他自身)对世界的表征,建基于她/他与一个真理过程的合并且必然成为忠诚的主体类型之上。理念是使个体,即人类的生活按照真实(True)来引导自己。或换一种说法:理念是个体和真理主体之间的中介(在此处用‘主体’指涉,在世界中为后事件性的身体定位)。”[4]结合巴迪欧的具体论述,我们可以提炼出“理念”的两个重要特征,并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的概念讨论之中。
其一,理念能够引导个体成为主体。巴迪欧曾经列举出共产主义运动的群英谱:斯巴达克斯、托马斯·闵采尔、罗伯斯庇尔、杜桑·卢维杜尔、布朗基、马克思、列宁、罗莎·卢森堡、毛泽东、切·格瓦拉等等。[5]250他认为共产主义理念通过勾勒一种英雄主义的图谱,激发并引导个体参与到真理进程中,使日常个体转变为真理的主体。因为日常个体毕竟不是主体,真正的主体是参与真理进程的个体,这样的个体依靠决断在环境状态中开启“例外”时刻,与日常生活构成决裂,在真理的感召下用生命创造新的历史。因此,在理念的引导功能中,我们看到的是个体忠诚于偶然的“例外”(事件),与当前的环境状态进行决裂,最终成为事件-真理的主体的过程。
其二,理念的存在能够让我们预见真理-事件的可能性意义,也就是说更容易抓住事件的真理特质。事件是真理的起点,在环境中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有事件的存在,环境才有改变的可能。对于解放政治而言,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中,每一次群众的抵抗、起义、造反性事件都是解放政治开启真理进程的一次机会,即让“一个事件”成为“一个惊喜”。然而,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机会,共产主义理念在此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了预见(至少是意识形态或理智上的)新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拥有一个理念。”[5]256因为理念关涉可能性的新奇(newness),关涉可能性的形式可能。理念总是坚持一个新奇的真理是历史可能的。例如,一次偶然爆发的群众反抗运动,如果拥有共产主义理念,会让群众的运动摆脱无组织、无目标状态,进入到真正的政治和历史的意义序列之中。也就是说,理念的存在能够让事件成为历史创造的起点。
理念的两个功能性特征为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提供了基础。共产主义世界文学是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的一个真实理念。这首先意味着从事世界文学研究的学者要与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环境保持思想审视的距离,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定位在如何突破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文学的虚假形式,并借此向一种真实形式推进,促成新的研究范式的诞生。比如,卡萨诺瓦否定了卡洛斯·富恩特斯关于世界文学秩序的建立就是实现多元文化主义的观点,并揭示出当前世界文学体系不平等结构中的中心与边缘的抗争关系,她实际上向我们表明了一种真实的世界文学形式正是对当前不平等的、虚假的世界文学关系进行反思和抗争的结果,她称之为“漫长而残酷的文学战争”。[6]20同时,共产主义世界文学的理念能够让我们理解文学环境中文学事件的意义。真理是通过事件的形式在环境中现身的,事件是突破环境的表现结构,让新事物突现的机缘。通常,文学批评对文学事件的理解基于其所在文化环境的知识结构,并试图在结构中给文学作品和文学创作行为定位,但这却消解了文学事件的真理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握文学创新的价值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如果能在既有知识结构之外确立一个真实理念,为不寻常、偶然、奇特的文学事件提供全新的认知框架,就为改变事件所在的环境提供了可能性。当前的世界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知识不断累积的结构,要突破这一固化的结构,实现研究环境的整体变革,需要重新审视和整理世界范围的文学事件,通过确立共产主义世界文学的理念,世界文学研究借助事件真理的潜能,突破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学研究范式,创造出全新的思想形式。
如果将共产主义世界文学的理念作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新路径的一个起点,那么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事实:在当前世界文学的研究中,世界文学的地理学研究似乎更得到左翼学者的青睐,在研究范式上占据主导地位。结合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国际文学市场化、文学和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等多种因素对世界文学进行地理测绘是该研究的主要趋向,其研究模式的核心范畴是“中心”和“边缘”,即考察中心地位的强势文学与边缘地区的弱势文学的互动关系成为研究的焦点。无论是卡萨诺瓦还是莫莱蒂都认为中心文学和边缘文学的不平等关系是当前世界文学空间的主要特征。这种不平等关系因国际文学商品市场的扩展而不断加强,莫莱蒂指出:“市场运作的关键机制是扩散:中心的小说不断出口到半边缘和边缘区域,在那里得到广泛阅读、欣赏、模仿并被树为样板——于是把这些地区的文学吸收到中心小说的轨道上来,实际上‘干涉’了它们的自主发展。接着,这种不对称的扩散给文学体系强加了一种令人震惊的相似性。”[1]244由此,中心和边缘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就转化为边缘地区的作家对中心地区生产的文学形式的妥协接受。这意味着在中心和边缘的文学权力的斗争关系中,边缘始终处于被‘干涉’的弱势地位,莫莱蒂甚至认为边缘的“反向影响几乎从未发生”,因此,他也不得不指出这种建立在不平等关系之上的世界文学并不是马克思所希望的世界文学,但如何实现那真实的世界文学,他却显得相对沉默。
与之不同的是,尽管卡萨诺瓦也采用了中心和边缘的范畴关系来展开世界文学空间的研究,但她对边缘地区的文学反抗抱有一线希望。她通过研究表明,“拉丁美洲文学的情况又一次证明了文学领域的相对自治性,说明了政治经济力量与文学权力或合法性在国际层面是不存在直接的因果性关系的。”[6]15文学空间具有相对自治性和独立性,因此边缘地区的文学并不始终处于被干涉的状态,而是会通过自身的创新对中心地区的文学形式和观念构成反向影响,因此在世界文学空间的不平等结构中,文学抗争依然是实际存在的。卡萨诺瓦指出了她的研究目标:“对文学不平等进行理论思考的时候,最关键的难题并非边缘作家是否借取中心,也不是文学交往流是否从中心向边缘流动,而是要原原本本地为文学世界的被压迫者复原其斗争的形式、特殊性和艰难情形。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自由的创新——往往是被掩盖着的创新——正名。”[6]19边缘地区的文学抗争与其文学创新相关,但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些“创新”?正如卡萨诺瓦所说为何会发生创新被掩盖的情况,又如何“正名”,是在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空间中“正名”,还是在这一空间之外?边缘地区文学抗争的结果是什么,是与中心地区文学达成一种协商状态,还是彻底地与中心敌对不容?一种通过文学抗争而形成的平等的世界文学空间是否可能?由于这一系列问题直接关涉文学反抗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定位,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然而,遗憾的是,卡萨诺瓦的研究却在此处止步了。
当我们提出共产主义世界文学的理念之时,实际上也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卡萨诺瓦和莫莱蒂研究工作的终点处,正是我们尝试提出一种新方法论的起点。两人的研究对认知世界文学的总体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以不同的理论叙事形式再现了环境的结构,对结构的历史演变和实际运行进行了详尽讨论。不过,对环境的认知并不一定能实现环境的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卡萨诺瓦和莫莱蒂的研究实现了对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世界文学的批判性认识,但却没有涉及如何从批判转向实践,推动一种新的世界文学关系的形成。因此,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中将理论建构的积极性和创作实践的勇气结合起来。这也是提出共产主义世界文学的主要意图。共产主义世界文学并不能从当前的文学环境中演变而来,它需要通过文学创新来颠覆环境结构的压迫性关系,从而彻底改变环境,确立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世界文学是穿破当前文学环境的全新的事物。这要求研究者要将文学创新作为建构方法论的关键点。
二、挑战世界文学秩序的可能:文学的反抗与创新
然而如何认识“文学创新”,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巴迪欧哲学的基本关注是“何为‘新’?”的问题,在他谈论当代艺术状况时又提出了艺术环境、艺术事件、艺术真理等概念,这对我们建设一种新的世界文学研究范式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果从方法论建构的角度来看待他关于当代艺术的讨论,我们能够在以下两个层面的问题上获得一种解答:
其一,如果当前的世界文学空间是中心压迫边缘的不平等结构,那么被压迫者该如何进行文学抗争?抗争的思想姿态是什么?策略又是什么?巴迪欧在谈论当代艺术的使命问题时,强调了艺术反抗姿态上的不妥协性和彻底性。“艺术的使命,在其所有的形式中,都反对艺术的当前潮流,朝向不连续的多重性,再次拾起狂放不羁、非道德性,以及——一旦有成效——根本上的非人化,肯定性的活力。”[7]134在抗争对象上,巴迪欧毫不掩饰地指出:“当代艺术的唯一发展就是不能成为‘西方的’,如果民主意味着遵循西方政治自由的观念,那它也不应该成为民主的。”[7]146“西方的”同时也指涉“帝国的”。帝国艺术世界的形成依靠国际商品市场的流通,并通过西方民主观念的传播加以巩固。“帝国文学”就是对当前世界文学的西方强势中心的象征性表达。因此,反帝国的文学斗争就是一个双重任务,拒绝帝国的美学形式及帝国的政治观念。这种绝对的反抗姿态和卡萨诺瓦关于“距离的艺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卡萨诺瓦认为边缘地区的作家在寻求文学创作的独立性之时,采取的策略是“将自身在美学上定位得既不太近也不太远,……以非凡的老练精到的手法为自己谋求着被人所感知、在文学领域内存在的最佳机会”。[6]19然而,这种寻求妥协的机会主义有低估帝国文化霸权的统治力以及高估文学领域自治性的嫌疑。
其二,如果在文学形式和审美趣味上都要彻底拒绝“帝国文学”,要实现文学抗争而不是折中妥协,那么就要取决于文学创新的力度。这就引出了第二问题:在当代世界如何进行文学创新?或者说什么意义上的创新才是“真实”的创新,而不是与帝国文化妥协的产物。创新首先是一种否定、一种突破。在巴迪欧看来,要做到真实的艺术形式的创新,就应该认识到在帝国艺术之中存在着一种虚假的创新,即他所说的“浪漫的形式主义”,这是当代艺术的主流,其特点是:一方面是对新形式的绝对渴望;另一方面是对身体和有限性的迷恋。[8]这两个特点看似矛盾,实则是统一的。因为一旦追求形式的多变性只是为追求感官享乐、性和死亡的身体质感,则成为一种虚假的形式创新。这一点从商品的呈现形态来看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具有同一功能和用途的商品为了激起购买者的欲望总是在变换外在形式,给人一种不断翻新的假象。边缘文学地区的作家一旦借用这种“浪漫的形式主义”与本地生活相结合进行创作,就十分容易陷入一种伪创新的状态,产生出边缘文学能够独立于帝国文学系统之外的幻象。那么,边缘地区通过借用形式的方式来实现创新,并向帝国中心的文学权力进行挑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挑战的最终结果可能只是向中心寻求认同,在帝国文学系统之中获得一席之地,挑战行为对系统本身就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因此,否定“浪漫的形式主义”,突破帝国文学环境中的形式扩散系统,是实现文学创新的第一步。
只有当边缘文学的形式创新是一种真实的创新,反抗帝国文学的统治才是可能的。然而什么是真实的创新?当艺术形式的革新伴随着某种真实之物(即艺术真理)的现身时,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新。在巴迪欧的哲学中,“新奇”是真理的属性,并且和事件相关。就艺术而言,艺术创新就是艺术真理的确立。但是艺术真理是什么呢?巴迪欧认为艺术真理是由艺术构型(artistic configuration)生产出来的:“艺术构型不是一种艺术形式、风格、或艺术史中的一段‘客观的’时期,也不是一种‘技术性’机制。宁可说,它是一种由事件引发的可辨别的序列,构成一个近乎无限的作品混合体。当谈论它时,这样说就合乎情理了:它生产了(从所谈及的艺术的严格的内在性角度)这个艺术的一种真理,一种艺术真理。”[9]艺术构型实际上是由众多的艺术作品构成的作品群,具有相似的形式风格,类似于某种艺术流派的作品集合。当然要开启一种新的艺术构型,还需要依靠艺术事件和忠诚于事件的主体。因此,我们会看到巴迪欧对艺术真理的一个定义:“艺术真理是感性进入理念事件的变形。”[7]144如果绕开巴迪欧复杂的概念表述,我们可以将艺术创新和艺术真理的关系表述如下:一个艺术事件(可以指艺术家的创作行为,也可以指一件艺术作品的诞生)发生在艺术环境中,环境的知识结构无法认识和把握该事件,环境潜在地排斥和模糊事件已经发生的痕迹。但有少数主体识别出该事件的真理意义,忠诚于事件,依循事件承载的观念进行创作。这时,艺术事件下的真理就通过作品的美学形式被确立下来。如果艺术环境要接纳艺术真理及其美学创新,就不得不调整甚至重建自身的表征结构,我们就将这一过程称为艺术创新。如果结合巴迪欧关于非帝国艺术的论述,我们对反帝国的文学创新会有更具体的认识。“非西方(帝国)的艺术必然是抽象的艺术……非帝国艺术的抽象化不关注任何特殊的公众。它和一种无产者的贵族主义相联系:对人群不加区分地去行动。”[7]146这里的“抽象化”是指艺术创新要不断消除特殊性,向普遍性推进。非帝国的文学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思想上都需要从民族、地域、宗教等特殊性因素中抽象新的普遍性,与帝国文学的商业流通中的市场普遍性形成一种对抗。这也表明了在不平等的世界文学空间中,边缘弱势文学通过强调特殊性来反抗中心地区的普遍性是难以获得成功的。“今天,艺术建构自身应当以——对帝国的流通(媒体和商业)而言——不存在或稀有的存在为基点,通过艺术抽象化的构造使非存在变得可见,这一点应当统合全部艺术的形式原则:使人们都能看到对于(帝国的)媒体和商业而言是不存在的东西。”[7]148对帝国文学世界而言,那个“非存在”(non-existence)或“稀有的存在”正是事件的发源点,也是颠覆帝国文学权力结构的可能性所在。文学通过对事件的扑捉,创造新的形式来传递事件的真理,这样边缘文学的形式创新才具有变革世界文学格局的力量。
三、重建世界文学秩序的可能:文学事件和文学史的书写
如果说作家可以通过文学形式的创新来挑战世界文学秩序,那么对文学研究者而言,配合以新的思想观念来编写世界文学史,则有可能实现世界文学秩序的重建。因为个体性的文学创新无论有多大的成就,都需要在文学史中被恰当定位,才能对整个文学世界产生持续性影响。但在旧的文学史结构中,新作品的价值总难以完全彰显,重写文学史的必要性就在于要将文学创造中的真理价值显现出来,并最终确立在世界中。在此意义上,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是难以分离的。不过,要重写文学史,就需要一种全新的书写原则,但当前最大的难题或许还是:一种全新的思路从何而来?结合前面的论述,应该说巴迪欧对“事件”的哲学研究为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我们的问题还要进一步深化:如何在文学事件、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并由此形成一种书写原则?通过思想的事件来书写一部新哲学史,曾经是尼采的设想。得益于朗佩特的研究,我们获悉,尼采使一部新哲学史成为可能,至少有三条主导原则:“伟大的思想就是伟大的事件”(《善恶的彼岸》,285条)、“真正的哲人是命令者和立法者”(《善恶的彼岸》,211条)、“以前的哲人都知道显白与隐微的区别”(《善恶的彼岸》,30条)。[10]结合事件哲学的思想,我们将其转换为写作文学史的原则,可简述为:
(一)“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伟大的事件”,这一原则要求我们考察文学作品与其所在的文学环境的关系,并且要追问这一问题:具有事件性意义的文学作品如何在既定环境中成为一种文学真理或文学经典。格奥尔格·卢卡奇在其《小说理论》中给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极高的地位,但同时表示自己并不能很好的评价其作品,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新世界的史诗。[11]这看似矛盾的说法,实际上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事件性意义,他的创作已经颠覆了当前文学环境的认知,成为改变环境认知结构的真理创造。
(二)“伟大的作品是新的美学形式的创造者”,如同真正的哲人是立法者,文学经典也同样是美学法则的创制者。创造新的美学形式关键不是对传统的延续,而是对传统的突破。一个文学事件突破环境,实现了文学真理的显现,真理在具体作品中凝结为崭新的美学风格,为作品创造了新的形式法则。因此,如果要写作一部世界文学史,从美学形式而言,更应该注重文学交流中的美学形式的突变性事件,而不仅仅是关注风格的继承、模仿以及借鉴。
(三)“要注意作品中的美学风格和思想内容的关系”。哲人有独特的言说真理的方式,文学同样如此。一部文学作品的美学风格和思想形式是不能分离的,因为伟大的作家通常不是从别处借用形式来表达思想,而是为言说思想去创造美学形式。巴迪欧对贝克特的作品有过深入阅读,他发现贝克特的作品在语言形式和文本风格上显得怪异,是因为贝克特并没有按照“美”的通常标准来进行写作,而是自行定义了“美的风格”,从而为他的思想表达提供了合适的方式。[12]如果我们至今仍在用某一类美学主张来写作文学史,那将错失了许多有价值的文本。
以上三条原则只是为重写世界文学史提出的一些设想,还算不上一套完善的、有操作意义的方法论。但是它们如果能够与共产主义世界文学的设想相结合,就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因为,根据文学事件、文学真理以及真理的美学形式等范畴建立起来的文学史原则必然与当前的世界文学史编撰方法迥异。这本身就是对当前世界文学体系的一种反抗。同时,我们也从中意识到,世界文学史就是文学真理的斗争史,它不只是要认识和批判当前的文学世界,更是要促成一个新世界的到来。
[1]弗兰哥·莫莱蒂.进化、世界体系、世界文学[G]//大卫·达姆罗什.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70.
[3]Alain Badiou.The Rebirth of History[M].New York:Verso,2012:47.
[4]Alain Badiou.Second Manifesto for Philosophy[M].New York:Polity Press,2011:105.
[5]Alain Badiou.The Communist Hypothesis[M].New York:Verso,2010:250.
[6]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作为一个世界[G]//张永清,马元龙.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Alain Badiou.Polemics[M].New York:Verso,2007.
[8]Alain Badiou.Fifteen Theses on Contemporary Art[J/OL].Lacanian Ink,2004,23[2014-10-21].http://www.lacan.com/frameXXIII7.htm.
[9]Alain Badiou.Handbook of Inaesthetic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13.
[10]朗佩特.尼采和现时代[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
[11]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M].London:Merlin Press,1971:152.
[12]Alain Badiou.On Beckett[M].London:Clinamen Press,2003:42.
〔责任编辑:曹金钟 屈海燕〕
I109.9
A
1000-8284(2015)01-0169-06
2014-10-18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化研究——以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为重点”(12AZD091)
谭成(1984-),男,四川岳池人,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