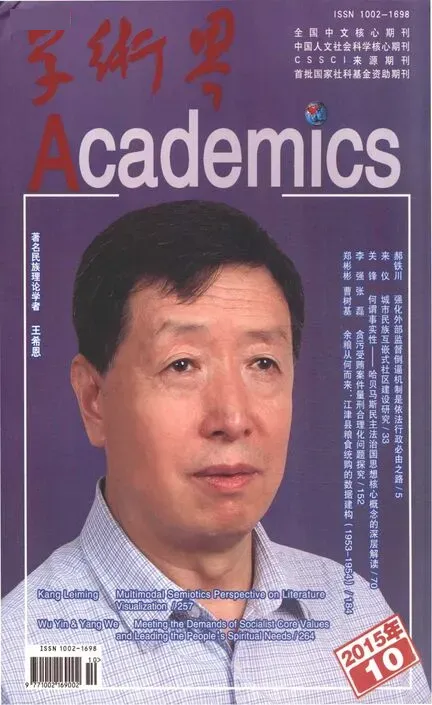晚清法律文化观念的演进与启示
○ 夏 邦
(上海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由于自古“天下”的观念,正如李良玉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民族主义的历史考察》一文所说,中国在近现代之前一直没有建立代表国家的价值系统,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当然也就缺乏国家主义的内容。〔1〕直至近代的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之际,中国人开始以寻求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来挽救自身文化的危机,据此,近现代的法制变革,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民族国家观念觉醒的背景下而拉开序幕的,中国晚清时期的法律文化观念也从此发生了深远的变化,由先前仅停留在法律文化的物质层次——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开始向法律文化的心物层次——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心理层次——法律价值观、法律意识、法律思维〔2〕演变,并给后人带来了深刻的思考和启示。
一、晚清法律文化观念的特征
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晚清时期的法律文化观念呈现出民族性、继承性、被迫性、互融性以及社会政治性等多元特征:
(一)民族性和继承性。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民族意识由此而勃发。在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下,当面临亡国灭种的屈辱,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要求愈显强烈。张玉法在《中国现代化论集》一文中,曾这样描述了晚清时的历史现状:当在介绍“中国”的概念以取代“大清”时,中国人发现中国不是一个国家,中国人也还不是民族国家的公民,这使许多有政治自觉的中国人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只有建成一个民族主义〔3〕的中国,才能摆脱外侮。一时间,“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主权观念。在民族国家的思潮里,国人的意识也随之演进,终于如梁启超所言,从“器物层次的现代化”到达了“制度层次的现代化”。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中国不仅需与西方科学技术,而且需与西方政治原则和普通知识相竞争。此种趋势的初步,是在天与天子之间插入一部宪法,而将皇帝置于天命与百姓二者之下。由于一部宪法是具体的、明确的、不能规避的,人民的意见势将取代上帝的意旨。”〔4〕由此,无论是清廷的修律还是民间制宪的呼声,都汇集到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洪流之中。法制是否近现代化,成为了衡量民族国家存在的一个最有力的注脚。而法律文化总是在具体的民族中产生发展,并在批判地继承旧的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法律文化。
(二)被迫性。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对于风雨飘摇中的满清政府来讲,其统治的基础遭到了重创。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但打开了中国的海关,也打破了传统的中国中心的老大帝国迷梦。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深入,封闭的晚清不得不被迫打开国门,迎接传统的法律观念、政治思想必然遭受的挑战和冲击。在外来强大的压力下,一场被迫性的近现代法律文化观念的变革袭击了整个晚清时期传统法律观念的思维。晚清法律文化观念的转变是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多次沉重打击及民主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为维护自身封建统治而被迫进行的,本身带有被动性和不彻底性。
(三)互融性。19世纪,民族主义国家的形成使得欧洲各国家之间的贸易殖民活动的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向东方的扩张脚步日益增强,东西方联系越来越密切,近代中西法律文化的相互交融也日益密切。晚清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官僚士大夫开始重新考察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并逐渐了解西方法律文化。譬如既宣扬“变法图强”又认为封建主流法律思想的基本原则不能变的龚自珍、魏源,主张采撷西法、改革刑律的康有为、梁启超,主张“中体西用”的曾国藩等等,反映出晚清时期的法律文化观念是在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交融过程中整合而成的。又如《法院编制法》《大清新刑律草案》等大量新律也体现了中西法律文化在冲突中相互融合。
(四)社会政治性。法律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构成内容,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法律文化的演进始终与政治密切结合在一起,法律从属于政治。一定的法律文化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相联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生产条件、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文化。同时法律文化又是一种用来调整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调整性文化,承担着特定的政治使命和目的。
二、晚清法律文化观念的演变
晚清法制变革的过程中,人们的相关意识形态也发生了一连串的更替。法制的近现代化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近现代化,近现代的国家管理体制的建立也不仅仅是几部宪法的出炉。法律的落实,宪政的开展,司法的科学,都需要近现代化的法律理念的确立,特别是人的近现代化的因素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以人的意识、行动所综合的法律文化观念的变迁就特别值得注意。“无论在初民社会还是在发达社会里,法律文化都是传递行为传统的重要工具。”〔5〕可以这样说,晚清的法制变革,其实就是要把传统以儒家学说家族本位为基础的法律文化转化为近现代意义上的以民主、自由、平等为特征的法律文化,从而形成新的法律传统。
对于法律文化,有各种解释。有人以为,所谓法律文化,“乃是人类在法律生活方面活动的一切现象的总和,它是由法律规范、法律思想和人民法律意识及法律运作等因素所组成的一种特有的文化机制,包括有形的立法、司法等外在因素,也包含人民对法律的认识及态度等内在因素。”〔6〕这较为准确地勾勒了法律文化的范围,也体现了法律文化在晚清法制近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
晚清法制变革,是基于一个“被迫现代化”的过程。金耀基说,百年来中西文化的冲突,从根本上说,实是一“社会变迁”的问题。要了解社会变迁的原理,我们就不能不了解人类学者所研究的文化与原始社会,社会学者所研究的社会结构以及心理学者所研究的人格形成。〔7〕中国虽然不是原始社会,但传统社会与近现代社会无论从经济体制还是组织理念都有很大分殊,而对于晚清的社会结构和相应的人格形成的认识确是对把握法制的变革有着深远的意义。晚清法律文化观念的演变,从鸦片战争的爆发,到洋务运动的发韧,再到戊戌维新的戛然而止,以及随后的变法新政,可以说,法律文化的观念在每个阶段都有所侧重,法制的步伐在每个阶段都有所调整,与传统的割舍与断裂日益加剧。随着思想到行为,纸面到实际,晚清的法律观念变革与法律制度的变迁成为了互相促进的动力因素,这一切反映为法律文化上巨大转变。
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深入,传统的法律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领事裁判制度是一个最为显著的标志,预示着老大帝国的法律已经遭到侵蚀,以至于最终唯有变革,才能摆脱衰亡的命运。“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8〕,这对于诺大帝国来讲,是个莫大的讽刺。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都卷入了文明的漩涡,“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9〕西方的压迫使人们有家国之痛,出于民族意识的觉醒,士大夫中往往激发出反抗的呼声。“从来外夷,非畏威不知怀德,故驭夷必先剿而后抚,自宋至明,边患不同,要之申国威者,皆忠义之臣,而不顾国体者皆奸佞之辈,虑远者皆智勇之士,而苟图目前者,皆庸懦之流。”〔10〕但徒然以旧的手段,去面对新的问题,在实践中往往捉襟见肘。鸦片战争中所暴露的愚昧〔11〕,使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开明官员,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战争背后的社会问题。魏源记载曰,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12〕反映在法律上,开始翻译一系列的公法类书籍,寻求另外一种解决危机的方式。当时的西方法律文化观念影响,主要还是以国际间交涉为主,还包含着较浓厚的夷夏之分。以林维喜一案为例,针对英国当局藏匿杀人凶手,由于知晓国际间“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因此指出“杀人偿命,中外所同,但犯罪若在伊国地上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官宪审办?”〔13〕最终得以严惩凶手。
但由于清廷的反应迟钝,一次大炮显然还无法震动天朝慵懒的身躯,和日本的奋起直追不同,中国却“在炮声沉寂后又昏昏睡去”〔14〕。到了19世纪60年代,连曾国藩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朝廷重臣还发出“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15〕这样的哀叹,显然,要想让“睡狮”醒来还是需要更大的刺激的。在面对漫长的政治军事失败时,人们开始用新的理路来思索东西方的碰撞与法律的变革,洋务派的人士因此逐渐形成了中体西用的主张。应付外侮,必须“借法自强”,既要“修明义,以忠义之气为根本”,又要“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其尽窥其中之秘”,这同“用人行政之长经,其有关圣贤体要者”,并不冲突〔16〕,以此强调变通成法,引入西学弥补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冯桂芬即以春秋列国对峙比附当时的列强环伺,提出了加强外交的建议和进行改制的主张〔17〕,为一时世风所归。但是持续的危机使得随后而起的维新人士认为中国弊端并非炮不利,船不坚,而在于政治上的“上下之情不能相通”,到70年代,王韬、郑观应发出了“君民共主”的呼吁,要求仿行泰西各国“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之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18〕。批评洋务派的活动是“遗其体而效其用”〔19〕。在他们的言论里,已经有了民主主义的宪法思想。“君者,民之所拥戴,而非天之所授权……是亿兆议定律法授君遵办,所以限制君权使之受辖于律法也。如有非法自恣者,兆民拒之,不得谓之叛逆”〔20〕。这些带有现代法律文化观念的言论对于清末的法制变革指明了方向,并在局势的推动下最终提上了日程。特别在1894年的甲午之战,惨淡经营了三十余年的洋务付之一炬后,随着民族意识的更加勃发,“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21〕的呐喊使得西方的宪政法律思想全面地播散开来。以至于谭嗣同喊出“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二千年来的儒学“皆乡愿也”,二千年的帝王“皆独夫民贼也”〔22〕。就这样,在反思传统制度的基础上,近现代的法律文化观念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出来了。
维新者们盛赞西方法制,“泰西素重法律……所谓治罪法一书,自犯人之告发,罪案之搜查,判事之预审,法庭之公判,审院之上诉,其中捕拿之法,监禁之法,质讯之法,保释之法,以及被告辩护之法,证人传问之法,凡一切诉讼关系之人之文书之物件,无不有一定之法”〔23〕。在这样的认识下,康有为上疏光绪帝,恳请设立法律局,主持立法修律。“吾国法律,与万国异,故治外法权不能收复。且吾旧律,民法与刑法不分,商律与海律未备,尤非所以与万国交通也。今国会未开,宜早派大臣及专门之士,妥为辑定”〔24〕。这样,现代法律文化观念就进入了具体的制度设计的层面,虽然由于政治斗争等因素戊戌维新很快失败,但变法修律的活动却就此展开。
1901年,庚子之变惊魂未定,清廷下诏变法。“惟是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著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总期切实平允,中外通行,用示通变宜民之至意。”随后,即“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25〕到了1908年,又在允许颁布各省咨议局及议员选举各章程的谕旨中,清廷决定甄采列邦之良规,折衷本国之成宪,速定君主立宪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开始制宪。〔26〕
但是,历史显然没有再次给予清廷以机会,或者说,在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思想观念作为一种软件的存在明显在升级换代中要快速于那个步履蹒跚的制度实相;在如此的时代洪流中,甚至来不及让一些老成持重者作出理性的(亦或理想的)全局安排,历史的车轮就不耐烦地将其碾压过去。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是各领风骚却只有瞬间。仓促的局势让任何企图整合重建的努力只能成为喧嚣背景下的瞬间即逝的毫光,闪烁一下却再也难以发现。更何况这些喧嚣的声音具有诱人的宏大叙事的魅力,民族、国家这些个新语汇显然要比朝廷、天下对初看世界的芸芸众生来讲更有吸引力;法治的全面西化的美景蓝图也似乎在印证着众生对“美丽新世界”的憧憬。法治本身的保守要素与文化传承的规律在那时却已经被遗忘在迅速变换的时代场景里;而对这种关键性要素的忽视与漠视直接导致了法律文化观念上的先天不足,流弊深远却又无可奈何。
三、晚清法律文化观念的启示
晚清时期伴随民族国家理念的形成,法制变革顺势而行,法律文化观念也呈现出民族性、继承性、被迫性、互融性以及社会政治性的多元特征,这些特征和特征背后的晚清法律文化观念给后人带来了深刻的思考和启示。
(一)对待外来法律文化,保持“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包容性。法律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不同的法律文化有着各自的特性和精髓,法律文化的差异是促进法律文化观念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因。对待不同的法律文化,在知晓法律文化的互融性和开放性特征的同时,要注重保持一种“海纳百川”的开放和包容态度。晚清时期,西方列强的入侵所带来的西方法律文化与当时传统的封闭的法律文化观念相碰撞,清王朝在冲突、被迫和不情愿中逐渐接受并吸收西方法律文化,清王朝的被动、不情愿和不彻底性,当辛亥枪声响起的时候,无论是《钦定宪法大纲》还是后来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并没能挽救清廷的统治,带给我们深刻的思考。不同的法律文化都是在互相吸收、渗透中不断得到繁荣和发展。多元的法律文化,既有助于给单一的法律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也有助于丰富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促使一个民族去思考并逐步确立和完善自身的法律文化观念。
(二)对待外来法律文化,注意批判性吸取。晚清时期西方法律文化的传入,给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观念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不可否认,当时西方法律文化有很多可供我们吸收和借鉴之处。然而,更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西方正处于殖民扩张的资本主义发展上升时期,从总体上来看,西方的法律文化集中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制度、历史传统、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与当时正处封建社会末期的清王朝相比,各自都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因此,对待西方法律文化或其他外来文化,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现实需要和具体国情批判性引进和吸收,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注重整合和积累外来文化的资源,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大胆借鉴外来法律文化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充实自身,以使我国的法律文化建设符合世界法律文化发展的潮流和特征。
(三)从制度和观念上紧跟时代脚步,理性继承传统的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中国的法律文化历经了组织机构到法律意识的演变过程。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民族危机异常严峻。为了挽救民族,实现国家的富强,一些爱国人士开始放眼看世界,打破传统观念,进行制度革新。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他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魏源没有像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样,向资产阶级转化,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此时魏源的“师夷”思想实质,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范畴,未摆脱传统文化的乳臭味,以致晚清法律文化观念始终一边遭受着西方法律文化的侵蚀,一边遭受着传统法律文化的羁绊,未完全跳离时局的困境。因此,晚清时期法律文化观念告诉我们,应注重法律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同时,理性对待传统的文化和制度,忌全盘否定,亦忌过于沉浸,固步自封,不思进取。
新思潮新事物的诞生,应是时局多元化因素综合的结果。我国晚清时期民族国家思想从萌芽到形成,离不开内忧外患时局的激化和推动。而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打破了往昔王朝的政治模式,必然引发领导者或统治者的思考——治理方式和标准问题。于是,法律文化、法制顺应时局油然而生。当然,就法制的近现代转型与现代法律文化的构建来看,晚清并非是一无可取的,它所首倡的现代法律文化观念依然成为20世纪后来阶段的法制近现代化的努力方向。只是因拘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依然是一个需要进行思想启蒙的国度的局限性,在这个没有自然法思想基础的国家里移植和实施以自然法思想为基础建立的近代法律体系,当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现象。〔27〕就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路来看,晚清的法律文化观念上的演化虽然对清廷统治的崩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也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化法制的基础。
注释:
〔1〕李良玉:《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民族主义的历史考察》,《江海学刊》1994年第4期。
〔2〕王申:《法律文化层次论——兼论中国近代法律文化演进的若干特质》,《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42期。
〔3〕民族主义,源于一种族群的意识,是一种民族内各成员的自我体认同理论。张启雄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10页。
〔4〕陈志让:《现代中国寻求政治模式的历史背景》,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化论集》第一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277页。
〔5〕〔美〕H·W·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22页。
〔6〕张仕享:《中国传统法制与思想》,台北: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第247页。
〔7〕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8〕魏源:《海国图志》(卷81),同治丁卯郴州陈氏重刊足本,第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70页。
〔10〕《清道光朝留中密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6页。
〔11〕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176-177页。
〔12〕〔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13〕〔清〕林则徐:《林则徐公牍》,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9页。
〔14〕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5页。
〔15〕《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9年,第655页。
〔1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期》(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5页。
〔17〕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
〔18〕〔清〕王韬:《韬园文录外编·重民下》,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
〔19〕〔清〕郑观应:《感世危言·议院上》,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
〔20〕〔清〕钟天纬:《刖足集·综论时势、与程禧其书》。
〔21〕〔清〕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汤志钧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11页。
〔22〕〔清〕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37页。
〔23〕〔清〕黄遵宪:《日本国志·刑法志序》,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24〕〔清〕康有为:《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折》。
〔25〕《清德宗实录》(卷495)(卷498),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26〕朱寿朋编纂:《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27〕王涛:《中国法律早期现代化保守性价值评析》,张晋藩主编:《20世纪中国法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