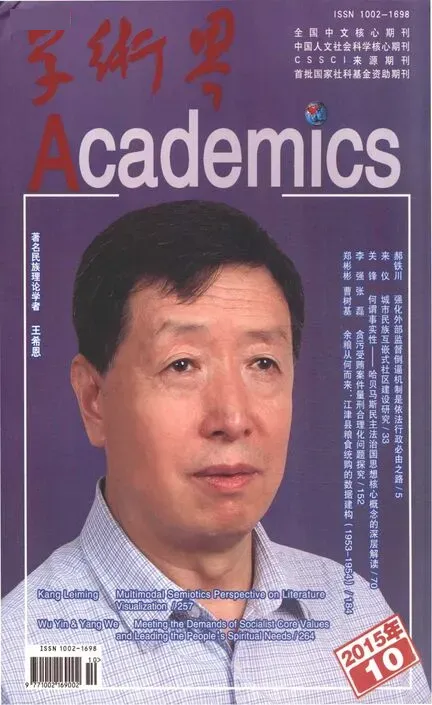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元小说的叙事策略
○ 黄立华
(安庆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0)
一、引 言
根据杰罗姆·克林科威茨(Jerome Klinkowtz,1998)的说法,“元小说是探求自身创作的虚构叙述的一种风格。元小说字面上意思是‘小说之后’或‘小说之前’。这种写作风格的实践者倾向利用元小说技巧破坏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虚幻成分。”〔1〕在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1979)的影响力专著《虚构情节和元小说》中,他将元小说称为将批评特性注入自身创作过程中的“反省”小说。迈克尔·博伊德(Michael Boyd,1983)在《反省小说:作为批评的小说》中指出,“元小说研究写作本身的行为,摆脱虚构世界去研究自身的机制。”〔2〕另据帕特丽夏·沃(Patricia Waugh)的说法,元小说这一术语是美国小说家威廉·盖斯(William Gass,1970)在他对豪尔赫·博格斯(Jorge Lius Borges),约翰·巴斯(John Barth)和布赖恩(Flann O’brien)的作品进行评论时提出的。帕特丽夏·沃(1984)本人将元小说定义为专为“小说创作”设定的术语。“这种小说创作自觉地、系统地注意自身的地位。它是一种人为方法,其目的就是要提出关于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3〕沃认为元小说不是小说的次类,而是小说的一种趋向。这种趋向是通过夸大张力、隐含在小说中的对立、框架与破框架、虚幻的建构与解构来进行操作的。本论文从反省式叙述、多种隐秘叙述切入探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元小说叙述策略。
二、反省式叙述
作为叙述文的元小说定义规定元小说写作的所有方式和选择性方法。这一定义确实包括反省,但并不把反省视为元小说文本的必要条件。然而,许多元小说文本在探究虚构性问题时,探究虚构和现实之界限时,探究作者与读者以及其他之间的关系时采取反省式叙述。俄罗斯后现代元小说在这一方面也不例外。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元小说怀疑自身的虚构性,探究小说创作的过程,叙述传统施加的限制以及发现满意视角、声音和讲述故事的风格。反省在诸如安德列·比托夫(Andrei Bitov)的《普希金之家》(1971)(Pushkinskii dom),叶甫盖尼·波波夫(Evgenii Popov)的《爱国者的心》(Dusha patriota)(1983),亚·卡巴科夫(Aleksandr Kabakov)的《假装的人》等作品中很明显。在文学规则而不是与现实规则支配下,所有这些文本将写作行为置于叙述中心,并使用写作行为作为揭示虚构世界构建的特性。在叙述层面上,这些文本凸显作者—人物叙述者,读者明显的戏剧化,以质疑文学规则和文学传统以及公开表达虚构意图。
(一)凸显作者—人物叙述者
在这些纷杂的元小说技巧中,没有比凸显的作者更明显的了。凸显的作者不断地用他/她对创作小说文本本身的过程,取材的难处,作品缺点的估计以及通过改写有选择的段落努力删除缺点等的评论方式来打断叙述。在某种情况下,改写包括整个部分,新版本添加到已经存在的叙述。凸显作者—人物叙述者在叶甫盖尼·波波夫、亚·卡巴科夫、根里奇·萨普格尔(Genrikh Sapgir)等许多作品中很明显,但是,首当其中的还是安德烈·比托夫(Andrei Bitov),特别是在他的小说《普希金之家》。这部小说有两个明显区别的叙述视角:用第三人称讲述廖瓦·奧多耶夫采夫(Odoevtsev)家庭故事的外叙述者;用第一人称评述该故事,故事的要素以及故事书写的行为的作者—人物叙述者。外叙述者摆脱自身的方法,将故事置于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现实语境中创造逼真的幻想,而作者—人物叙述者通过揭示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和建构第二表征的过程以强调他的作品的虚构人物。
作者评论以简单的元小说评论的形式分散在整个叙述中以及较大部分段落中,如“斜体是我的评论——A.B.”,“附录”。这两部分通过使用不同的字体、斜体与叙述的其余部分分开。这是对传统小说的公开质疑。作为广泛的元小说评论功能,“斜体是我的评论——A.B.”聚焦一般文学传统,提供小说生成和结构的批评性讨论。特别是,他们质疑文学与外在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叙述的主客观方法以及虚构时间与现实时间之间的不相容性。就当前文本的生成而言,作者—人物叙述者揭示其对“不合适的”标题的不满意,因为该标题是从习俗中“偷来的”,缺乏人物与情节的联系,不能提供满意的结尾。
类似的元小说功能归于小说的作者和主人公之间的关系的附录。在第二部分(Part 2)的附录中,作者—人物叙述者对主人公学者职业的重要性进行了评述。学者职业允许他将精力集中在文学传统问题和文学批评上。有意义的是,作者—人物叙述者宁愿总结主人公的开拓性的作品,而不允许他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相同的作者—人物叙述者态度在最后的附录中很明显的。该附录在内容表中作为主人公书写的评论列出的,但是在最后的版本中表达作者的观点。作者—人物叙述者再次控制素材并将它转变成高度个人化的对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以及争议中的小说生成和出版的评论。
预示小说人为特性最激进的形式在第三部分附录中得以介绍。该附录描述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直接对峙。作者描述他造访普希金之家,和主人公相遇,两个参与者体验的不舒服的感觉。作者—人物叙述者清晰地知道打破文学传统,将自己引进文本的意义,反复警告读者不要将小说作品视为现实的真实反映:
人人已经知道,如果作者像是在生活中那样行事,文学会是什么情况。文学将不再是文学。文学将与生活融为一体,…。但是我们也要检测。我们拙劣地在文学中如同在生活中那样行事,完全打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距离。我们允许与主人公的对峙,我们无原则地让这种对峙经受文学风味的检测,如同作者无原则地经受文学风味检测一样。〔4〕
(二)读者戏剧化
除了作者—人物公开叙述之外,比托夫将读者范畴引进《普希金之家》。作者区分两种读者:理想化的、知识型的读者和无知型的读者。理想化的、知识型的读者可以托付共同创作文本的任务;无知型的读者不知文学传统,对非现实主义小说表示谴责。小说的第一部分往往致力于理想型读者,而第二部分明显地承认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敌意:“你们的寓言让我迷惑。”读者说。我将回答,“那么就别读。”如此。读者有权问我,我有权问他。〔5〕
总体来说,特别是当与文本许多部分大量的作者叙述相比时,这样元小说公开地致力于读者叙述的现象在小说中并不常见。
《普希金之家》中以读者为导向的叙述相对稀少,不那么重要。与之相比,有几个关注阅读行为,公开将读者概念戏剧化为文本要素的后现代元小说文本。后现代主义以读者为导向的文本独特性在于他们通过公开的元小说评论超越传统的研究读者的方法,将读者直接引进文本并赋予影响小说传统的史无前例的权利,在某种情况下最终成为文本的合作者。这种明显的读者戏剧化例子可以在叶甫盖尼·波波夫的作品中找到,如《爱国者心灵》(1983)、《绿色音乐家正传》(1998)等。在《爱国者心灵》这部作品中,读者以弗费什金(Feifichkin)的形象引入到文本中,有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小人物的名字。处在书信地址位置,弗费什金似乎是个抽象类人物,展示苏联读者的理想化形象,精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完全为叙述者所提供的非政治证言所迷惑。叙述者以公开戏虐的方式嘲弄可预料到的弗费什金反映:从烦恼到失望再到不同意。有意义的是,弗费什金的消极反映在文本中不是以他的言语反映而是通过叙述者对弗费什金的身体反映以及他的脸部表情的描述得以体现。叙述者不断指弗费什金的“窃笑”、“傻笑”,或“烦得皱眉”。〔6〕
整个文本,叙述者直接与弗费什金说话,一会儿奉承他的博学和聪明,转而又批评他缺乏兴趣和不信任。随着叙述的推进,叙述者越发坦率地表达他与弗费什金的紧张关系。
因为《爱国者心灵》是读者戏剧化的最始终如一的例子,没有其他的后现代主义文本。这种文本通过插入对读者的评论发出他们的虚构特性。读者直接介入在弗拉基米尔·索罗金(Vladimir Sorokin)的《标准》(Norma,1994)和《盛宴》(Pir,2000)。在《标准》的第三部分,高度文体化的叙述高度戏虐了19世纪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叙述者邀请一位没有身份的读者来评论他的文本,对一些消极评论的反映构成了供别人阅读的一个嵌入故事,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叙述结尾。插入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批评式交流强调小说创作的人为特性,警告读者不要模仿文本阅读。〔7〕
三、多种隐秘叙述
除了公开插入作者和读者叙述的虚构类别文本,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元小说依靠多种隐秘策略。这些策略破坏虚构世界的幻想,揭露叙述者的建构特征。一些最隐秘策略包括多重叙述者,不可靠叙述者,甚至缺席叙述者。
(一)多重叙述者
多重叙述者缺席并不破坏现实主义传统,因为只有当不同叙述文本中出现蓄意歧义和矛盾(intentional ambiguity and contradiction)时才会发生多重叙述者缺席现象。这种情况在许多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叙述中很明显,如瓦西里·阿克肖诺夫(Vasilii Aksenov)的《烧伤》(Ozhog),萨沙·索科洛夫(Sasha Sokolov)《一种新型:狗与傻瓜之间》(Mezhdu sobakoi I volkom),根里奇·萨普格尔(Genrikh Sapgir)的《新加坡》(Singapur),和弗拉基米尔·莎罗夫(Vladimir Sharov)的《之前和期间》(Do i vo vremia)。
阿克肖诺夫在他的小说《烧伤》中使用了不同的叙述者,主要由几个内叙述者和外叙述者叙述。在外叙述中,五个主要代表该小说的主人公,所有都有源于父名的谢尔盖·格拉西莫夫(Appolinarevich)名字。尽管不可能将他们视为第二卷中青少年主人公的代表,但是他们的态度和他们对叙述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却是不同的。这五个格拉西莫夫大多用第一人称单数叙述着他们故事,偶尔他们在高度个人化的第三人称叙述中扮演着聚焦者的角色。
五个内叙述者的个人化的故事在文本通过外叙述者联系起来。外叙述者话语的标志是第三人称的使用以及明显的无情感语调。遵从传统惯例,外叙述者提供一些背景信息,故事的一般语境和人物背景。偶尔,外叙述者直接评论故事和故事的参与者,或者俄罗斯知识分子历史。第二部分开始,叙述者公开地评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被动性和受虐狂的服从:
不是我们的过错?真的吗?但是谁让魔鬼从瓶子里出来;谁将自己与人们隔绝开来;谁在人前卑躬屈膝;谁在他人后发胖;谁让鞑靼人进城,煽动瓦兰吉人来通知他们,舔欧洲人的靴子,将他们与欧洲隔离开来,反对政府,顺从缺心眼的独裁者?我们做了所有这一切——我们,俄罗斯知识分子。〔8〕
《烧伤》中多重叙述者的使用由于不同视角的不断变换而变得复杂起来。结果,读者常常不知道他们正在读谁的故事,在什么节点上故事被打断以引入一个不同视角。由于断裂的年代和从虚构现实到梦幻、虚幻和酒精中毒性谵妄的没有动机的变更,复杂的叙述变得更加复杂。不同的现实和不同叙述视角的不断变换使得小说大部分不被读者所理解。
与《烧伤》中明显的多重叙述者相对照,萨沙·索科洛夫《一种新型:狗与傻瓜之间》只有两个叙述者,但是由于相同事件的矛盾叙述和故事之间缺乏联系,总的效果同样含混。处于主要叙述者地位,巡回磨工(Il’ia Zinzirela)讲述死后出版的写给公诉人的信中的故事。这些信捕捉他的人生的一些重要时刻,将不同时间维度并列起来,呈现同一事件的矛盾说法。小说中第二叙述声音是猎场看守人兼作者雅科夫(Iakov Il’ich)的声音。明显与分布在不同章节中的伊利亚(Il’ia)的叙述以及复杂文学语言的使用不同,雅科夫叙述的故事同样使人迷惑和含混。如同伊利亚的叙述,雅科夫故事含混不清,极端破碎。它模糊不同事件之间的联系以及叙述者和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两种叙述一直互不相关,各行其是,只是在伊利亚误认猎场看守人的狗为狼而将它杀死,猎场看守人因报复而杀死伊利亚这一节时才相互融合。然而,仔细研究一下文本就可以建立两种描述有缺陷的姑娘伊莉娜或玛丽亚(Orina/Maria)叙述之间的一系列联系以及伊利亚和雅科夫之间可能的父子关系。
(二)不可靠叙述者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元小说最普遍的叙述策略是不可靠叙述者的使用。不可靠叙述者的准则和行为与隐含作者或读者的规范或行为相冲突,其可靠性因叙述的各种特征而受损。根据阿格萨·纽宁(Ansgar Nunning)的观点,叙述不可靠性有两种:事实不可靠叙述(factual unreliablility)和规范性不可靠叙述(normative unreliability)。采用事实不可靠叙述讲述故事时,读者有理由怀疑,而规范性不可靠叙述反映叙述者的缺乏了解和可疑判断。〔9〕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利用这两种不可靠叙述,但他们却对规范性不可靠叙述情有独钟,因为这种叙述具有高度怀疑性和不胜任的叙述者。不胜任叙述者的评价和阐释与牢靠的判断的传统理念不一致。在各种各样不可靠叙述中,最突出的是不受社会传统约束的青少年叙述者(adolescent narrators),通过酒精中毒性谵妄(alcoholic delirium)和吸毒逃避现实的麻醉叙述者(alcoholic narrators)和不能够掌握和应对周围现实的精神病叙述者。上述最突出的叙述种类中,精神病叙述者常常要忍受着精神疾病的痛苦,特别是精神分裂症的痛苦(schizophrenic preoccupation),所以这类叙述者很盛行以至人们能谈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对“精神分裂症”的关注。
精神分裂叙述者有其独特的世界观,他们不能区别现实与虚构,所以这种叙述者允许后现代主义作家质疑物质现实和可变换的心理状态之间的界限,提出高度不可靠的,不断在真实经验和虚幻之间变化的虚构现实。有意义的是,不同领域之间的转换在文本中没有标示,读者很难决定怎样去阅读和阐释故事。
精神分裂叙述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弗拉基米尔·莎罗夫的《之前和期间》(Do i vo vremia)。这部小说描述具有严重精神病人的世界。这些精神病人监禁在莫斯科精神病院。该小说由几个叙述构成。所有这些叙述都来自精神病人,因而他们的可行度值得怀疑,他们不能区别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构的。该小说是由为他人人生中遇到的且成为朋友的那些人“悲叹”的叙述者收集的一系列个人故事架构的。作为文本中的主要叙述者,由于他自知记忆的丧失和其他药物引起的虚幻,阿列克谢(Aleksei)明显不可靠。而且,因为他包括二手的、偷听到的或者根据不可理解的笔记重构的故事,他收集故事的方式受到人们的高度质疑。所有第二叙述者都是慢性精神病人。这种独特性的第二叙述者的世界观加强了文本的不可靠性。有点荒谬的是,这种高度不可靠的、明显荒诞的叙述是用很明晰的、创造写实表达的虚假印象的风格来表达的。实际上,小说阐释了高度神秘的俄罗斯历史和文化。这种历史和文化都采用虚幻叙述,将现实和奇异、荒诞与虚幻、事实和虚构并列。
根据劳拉·劳曾(Sarah Lauzen)的元小说策略的类型,不可靠叙述者运用古怪的、有着高度无理性、无连贯性的叙述。〔10〕这种类型也包括其他种类的不同寻常叙事视角,譬如无生命物体叙述视角、狼人叙述视角,或死尸叙述视角。一些最明显的古怪叙述的例子包括基辛纳(Iuliia Kisina)的《脂肪视野》,维克托·佩列文的《狼人神圣的书》(The Sacred Book of the Werewolf),以及佩楚雪夫斯凯雅(Liudmila Petrushevskaia)的《第一:或者在其他可能性的花园中》。
在《第一》中,化身的主题,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轮回”的主题(这一术语是佩楚雪夫斯凯雅)包括小说中神秘地名叫“第一”的内叙述者,曾经有一次被叫做伊凡(Ivan Ts)。而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第一”有着主观的、非现实主义的思想。他要求他的老板支付绑架同事的赎金的叙述者所有特征。在小说的随后部分,他起着他的杀手——一个犯罪团伙的成员身份。“第一”的“轮回”最显著的是他的个性完全改变;这位受过很高教育的、民族志学者具有普通犯罪分子的心理和行为。“轮回”如此彻底,影响着叙述者的语言能力,而在第一部分他却用复杂的文学准则表达自己。在随后的部分,他使用犯罪行话,沉浸在俚语、大话和脏话中。这种不同寻常的叙述视角允许佩楚雪夫斯凯雅(Petrushevskaia)表达在后苏联现实中知识分子解体的思想以及犯罪分子的盛行。
在不同寻常的视角叙述中,没有哪一个比基辛那(Iuliia Kisina)的《脂肪视野》更突出了。《脂肪视野》不仅有高度不同寻常视角,而且公开形成叙述独创性的新原则。文本介绍了下列对文学中不同寻常的视角重要性的评论:
至于从作者的视角描写沉思、感情和事件的文学,或者至于有关被人操纵,屈服于作者意志的人物的文学,主要焦点放在个人上,即便叙述遵从桌子腿的视角。当文学从某一物质视角来书写时意想不到的事件的轮换发生了。这就是脂肪视角(fat)。〔11〕
上述评论作为女主人公早期小说的引用而出现在文本中,而现行文本描述女主人公寻找她最近作品失落的一章,因而小说《脂肪视野》可解读为失落的文本的重构,或者作为同一故事书写的延续。情节遵循传统犯罪故事,但却颠覆这一体裁的绝大部分叙述模式。它代表着涉及绑架和杀戮等犯罪书籍的非常不同寻常的形式:一个以受人尊敬的律师形象出现的令人吃惊的恶棍,许多受害者,意料不到的结局等。用第三人称单数叙述,故事想必使用了上述的“脂肪视角”。选择脂肪做为聚焦器是由标题以及表示女主人公的奋斗和她由于这一神秘物质而最终失败的几个参考来表示的。由于这一高度不同寻常视角和奇异风格,将幻想和平凡事情结合起来,戏仿犯罪故事的传统,《脂肪视野》毫无疑问在语言技巧上具有一席之地。该技巧创造了虚构世界而不是模仿外在现实。
(三)缺席的叙述者
还原的或者缺席的叙述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元小说中很明显是不足的。因为叙述小说就其定义而言就是使用某种叙述视角来讲述故事,所以上述现象不足为奇。然而,一些小说文本特点是作为可认识的和稳定的实体的叙述者的分解,如弗拉蒂米尔索罗金的《排队》(1985),《标准》(1994)和《盛宴》(2000)的大部分。在这些小说中,大量的名词短语替代了传统的叙述。譬如,《标准》的第二部分代表着有一长串名词构成的目录结构。每一名词都有由一个正常的修饰词。没有标点符号,但在印刷上安排成诗一样的结构。总共950个短语目录讲述相当透明的“正常”苏维埃男人的人生故事。从他出生和早期童年开始,到他的读书岁月和第一次与姑娘们相识,到他的军旅生涯,再到他的工作和家庭责任,最后是他的退休和健康问题以及他的住院和死亡。
第二部分依赖形容词“正常”的重复,而第六部分则把带有名词“标准”的28个短语并列起来。“标准”一词的意义随着诸如“社会”或“道德”标准的变化而变化,从表示生产配额的苏维埃术语,到表达可接收酒精消费量的习语,或者同伴之间满意的性交。几乎一半的短语都带有真实的或者虚构的名称。这些名称包括具有“标准”名称的人物、城市、工厂或体育城。不像使用讲述普通苏维埃市民经历的目录结构的第二部分,从本质上说,第六部分这些短语的并列形式上玩弄着没有叙述功能的同音异义词(homonym)的游戏。
关于叙述缺席最令人信服的例子当属索罗金的《排队》。这部小说由没有任何叙述描写或评论的扩展目录构成。这种高度不同寻常的小说全是由碰巧为某一不甚特别的商品而排队等候的陌生人之间的直接交流构成的。这些涉及排队自身的一些普通细节以及从报纸上选取的段落、通俗笑话、恐怖故事等等。尽管文本并没有提供任何背景或人物描述,读者还是能够区别不同的声音,鉴别一些主人公,从而读懂他们的故事。尽管缺席叙述评论,文本尽量提供相当有连贯的苏维埃生活的荒唐画面:没完没了的排队、酗酒和随意的性交等。
四、结 语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得知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叙述策略是相当多样化的,同时具有高度新颖性。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强调虚构世界的建构特性,揭示小说创作的过程。通过使用公开的元小说评论以及巧妙使用不同的叙述技巧,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提醒读者,小说作品是语言建构,不是作为现实世界的真实再现。所有叙述层面上的不同的元小说策略本质上都与其他诸如情节、语言等叙述结构要素息息相关。
尽管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元小说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有很多共同特点,例如戏仿、游戏、荒诞、缺席和反省等,但它在形成的来源及发展过程中融入许多传统文化因素,如继承和延续白银时代和苏联时期的创作风格以及融入宗教思想资源等。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元小说已成为俄罗斯文坛中重要的文学潮流,不但影响俄罗斯文学界,而且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其意义和价值不可小觑。
注释:
〔1〕Klinkowitz,Jerome.“Metafiction”,Encyclopedia of the Novel,vol.2,ed.Paul Schellinger.Chicago:Fitzroy Dearborn,1998,p.836.
〔2〕Boyd,Michael.The Reflexive Novel:Fiction as Critique.Lewisburg: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p.15-42.
〔3〕Waugh,Patricia.Metafictio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London:Methuen,1984,p.2.
〔4〕〔5〕Bitov,Andrei.Pushkinskii dom.Ann Arbor:Ardis,1978,pp.344,246.
〔6〕Popov,Evgenii.Dusha patriota,ilRazlichnye poslaniia k Ferfichkin.Moskva:Tekst,1994,p.53.
〔7〕Sorokin,Vladimir.Norma.Moskva:Obscuri viri,1994,pp.145-146.
〔8〕Aksenov,Vasilii.Ozhog.Ann Arbor:Ardis,1980,p.221.
〔9〕Nunning,Ansgar.“Reconceptual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eds.Phelan,James and Rabinowitz,Peter.Oxford:Blackwell,2005,pp.89-107.
〔10〕Lauzen,Sarah.“Notes on Metafiction”,Postmodern Fiction:A Bio-Bibliographical Guide,ed.Larry McCaffery.New York:Greenwood,1986,p.98.
〔11〕Kisina,Iuliia.“Videnie zhira”,Mesto pechati,No.7(1995),pp.146-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