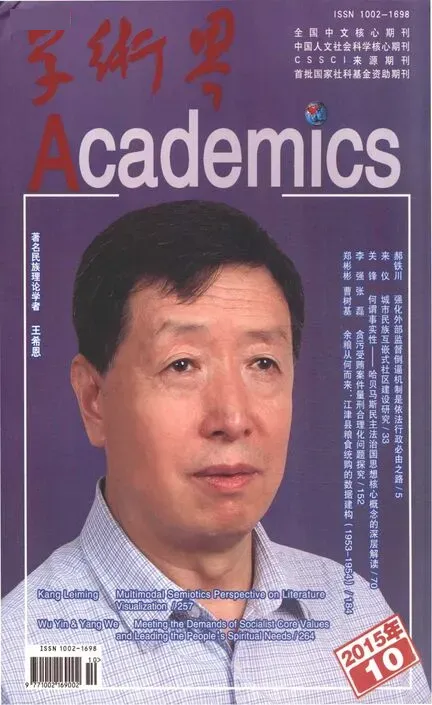乡土苦难叙事的视角变化〔*〕——世纪之交安徽乡土文学侧影
○金大伟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党委宣传部,安徽 合肥 230022)
苦难是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乡土叙事的母题,也是世纪之交安徽乡土文学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乡土世界的一部分,新时期以来,安徽乡土世界历经政治反思、文化探寻、经济变革、现代转型、主体自觉等诸多时代命题,一次次演绎着痛苦与坚忍、离土与归乡的苦难叙事逻辑。90年代以来,安徽乡土苦难叙事在叙事视角、叙事立场、精神文化走向等方面均发生了变化与转移,这既有历史与时代的缘由,又与安徽乡土世界自身的特质,以及乡土叙事者的时代使命、历史责任等有着必然的联系。其横向的视域扩展与纵向的主题挖掘,对呈现安徽地域文化、把握时代发展命题、提升乡土叙事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能回避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安徽乡土叙事是否将被城市叙事所取代,当下苦难叙事呈现日渐弱化的趋势,苦难叙事深度不够、易导致虚无情绪等。安徽乡土苦难叙事的种种变化,成为世纪之交安徽乡土文学的一个侧影,值得深入探究。
一、苦难叙事视角的转移与变化
90年代之前,安徽乡土叙事中的苦难叙事普遍呈现单一化特征,叙事视角更为关注国家民族苦难,更加注重苦难的外在形态,更多从政治文化视角和社会学层面透视苦难,乡土世界的苦难叙事视域仅限于乡土本身。90年代以来,宏观文化境遇变化、地方经济社会转型等因素对安徽乡土世界产生重要影响,苦难叙事的形态、主题等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呈现多元化特征,叙事视角也因此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与转移。
(一)由关注社会群体苦难、国家民族苦难转向关注个体生命苦难。作为“反思文学”的代表,80年代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从政治、社会层面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反思历史经验与教训,成为新时期安徽乡土苦难叙事视角变化、转移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在关注社会群体苦难、国家民族苦难的同时,开始把叙事视角投向个体苦难。80年代思想界关于“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坚定了安徽乡土苦难叙事关注个体生命苦难的立场,苦难不再仅仅指涉整体性和集体性。90年来以来,安徽乡土苦难叙事一方面延续80年代苦难叙事的视角,另一方面叙事视角发生转移,特别是关注个体生命苦难,对世俗苦难的体认并将世俗性或平民性作为叙事立场,是90年代以来安徽乡土苦难叙事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一切社会苦难的回顾或总结,如果单单空洞地指向抽象的‘历史’、‘社会’或者‘政治’意义,忽视个人苦难,增加的只是个人内心的沉重。”〔1〕在创作上,绝大多数乡土叙事或者将国家、民族等宏大命题后置为个体生命苦难叙事的背景,或者避开宏大命题而直接聚焦个体生命苦难,苦难叙事关注的主体已悄然发生变化。
(二)由关注肉体苦难转向关注精神苦难。一般而言,苦难叙事的表现形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婚恋、生存、历史等多个方面,苦难大体可划分为肉体苦难与精神苦难。绝大多数情况下,苦难更为深刻和潜在的意义是精神性的,无论哪一种苦难,“都应该对苦难有一种精神感受,而不是仅仅有经历过身体苦难的切肤之疼。肉体苦难融合着精神苦难的感受时,就不只是面对具体的、个人的苦难,而是面对一种广泛的、整体性、人类的苦难,这样的写作才会超越因个人苦难而产生的狭隘和偏见。”〔2〕90年代以来,安徽乡土苦难叙事经历了由关注肉体苦难向关注精神苦难转移的过程。它首先关注的是苦难的外在形态,侧重表现肉体苦难,具体体现为物质贫穷、强权压迫、婚恋悲剧、进城务工遭遇等苦难。在此基础上,一部分乡土苦难叙事开始关注精神性苦难,如《迷沼》(鲁彦周)、《秋声赋》(潘军)、《钱楼纪事》(杨小凡)、《肉身》(黄复彩)等。它们一方面将叙事视角转向个体,关注个体受难与苦难的成因与过程,另一方面注重关注受难主体面对苦难时的态度、选择与追求,并试图超越个体苦难的局限,努力实现苦难的整体性与普适性价值。
(三)由政治文化视角转为文明对立视角至抒发现代性乡愁。80年代初,安徽乡土苦难叙事主要立足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以政治文化视角切入,重点叙述乡土苦难与专制政治的必然联系,以此配合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变革转型和文化上精神反思的需要,并在其中彰显乡土文学与苦难叙事的社会价值。进入90年代,两种文明对立的时代背景成为苦难叙事选取叙事视角的主要依据。立足文学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使命,关注商品经济冲击下乡土世界的变化,凸显现代文明的负面价值,成为这个时期乡土苦难叙事的主要视角,如许春樵的“季节三部曲”。进入新世纪,安徽乡土苦难叙事在延续90年代叙事视角的同时,增加了对日益解体中的传统乡土现代性乡愁的抒发,叙事上“更关注农民的灵魂状态、文化人格,更关注他们在急遽变革的大时代中道德伦理的震荡和精神的分裂,从而把表现的重心放到中国农民在现代转型中的精神冲突和价值归依上”〔3〕,如《农民工》(许辉、苗秀侠)、《白雪覆盖的村庄》(洪放)、《流泪的剑》(贾鸿彬)、《你凭什么能听懂鸟语》(张诗群)等。从上述变化轨迹不难看出,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安徽乡土苦难叙事的视角发生了根本转换,历史时代要求与叙事主体自觉追求是其主要缘由。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宏观体制机制改革的长期性和地域文化的稳定性等特征,新世纪与90年代乡土苦难形态具有一致性,叙事视角具有连续性和承接性,抒发现代性乡愁将成为当下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乡土苦难叙事的重要视角。
(四)由叙述乡土苦难转向关注进城苦难。进城苦难是乡土苦难在城市中的延伸,安徽乡土叙事所秉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品格,决定了叙事视角由乡土苦难转向进城苦难的必然性。新时期伊始,“向城求生”的主题开始出现在安徽乡土叙事中,而真正思考进城苦难、进行苦难叙事则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乡土苦难叙事的视角继续对准那些通过“学而优则仕”的路径向城求生的主体,他们是从乡土世界走出的知识分子、乡土能人,是高家林似的乡土人物。因为恰逢城乡两种文明、文化的对立与碰撞,进城之后他们遭遇了种种不适甚至苦难,如李圣祥的《蜡烛泪》、胡进的《我从山中来》等,对乡土知识分子进城后遭遇的家庭、婚姻危机,以及精神苦难进行深入叙述,但受难的主体最终还是乡土世界的父老乡亲。随着城市的扩张、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等际遇,农民工进城得到了更多便利,农民工日渐成为进城的主体。与之相关的是,更多的乡土叙事融进了都市叙事,乡土世界的苦难与城市有了更多关联。此外,由于当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仍处在初期阶段,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体制制度仍不完善,乡土、城市两种话语的不平等现象仍普遍存在,农民工进城后体验与遭遇更多的是苦难与不幸,因此,此时的安徽乡土苦难乡土叙事将更多的视角对准进城的农民工,聚焦农民工进城后遭遇的苦难与悲剧,如鲁彦周的《迷沼》、许春樵的《不许抢劫》、陈家桥的《祝月记》等。
二、对待苦难的态度与精神文化走向
一般而言,正视苦难,体验、认知与思考苦难,改善对待苦难的态度,并经由苦难认知生命和存在的意义,以此达到精神上超越苦难,是苦难叙事的最高价值追求所在。然而,苦难的存在形态、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地域文化的特殊性等因素,决定了世纪之交安徽乡土苦难叙事的精神文化走向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总体而言,90年代以来安徽乡土苦难叙事对待苦难的态度和精神文化走向大致体现在三个维度上。
(一)沉默与坚忍——悲悯情怀与道德审视
90年代以来,城乡一体化与城乡差异化成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现状,城乡一体化是宏观体制机制改革努力的目标,而城乡差异化则是改革过程中重要的社会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时候安徽乡土世界是作为现代城镇的对立面而存在,总是以苦难、落后、衰败的弱者和受难者形象出现。在面对苦难的立场和态度上,相当一部分乡土苦难叙事选取了沉默与坚忍的态度,即选择默默忍受苦难,不作反抗挣扎。究其原因,一方面,受难主体对待苦难的态度影响了苦难叙事的立场与态度。对绝大多数受难者来说,他们是乡土世界的弱者,沉默与坚忍是他们面对苦难时的唯一选择。另一方面,叙事者的话语权、叙事风格等因素,决定了叙事文本的结构方式与表述方式。对于苦难叙事者来说,缺乏强力话语权、面对苦难无能为力的现实困境,容易产生沉默与坚忍的叙事态度。此外,90年代以来客观冷峻、零度情感等叙事风格也对安徽乡土苦难叙事的态度产生了一定影响,尽量摆脱、排除主观意图和情感态度对叙事的影响。如自90年代初开始,许春樵的“季节三部曲”、戴玉的《新嫁娘》、周恒的《父老乡亲》等苦难叙事就选择了面对苦难的态度——沉默与坚忍,这种对待苦难的叙事态度持续至今。
如果说沉默与坚忍是这部分乡土苦难叙事的外在表现形态,那么悲悯情怀与道德审视则是潜藏在苦难叙事背后的精神文化追求。悲悯情怀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折射出叙事者对待苦难的普遍态度;道德审视是苦难叙事的立足点、制高点,与叙事者的历史责任、使命要求有必然的关联。它们是叙事者的第一层精神文化追求,也是绝大多数乡土苦难叙事的第一选择。如“季节三部曲”(许春樵)、《水水》(李光南)、《你凭什么能听懂鸟语》(张诗群)中对待受难者的态度体现的是悲悯情怀,《草儿的村落》(胡恩国)、《拷打春天》(陈源斌)折射的是道德审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苦难易引起怜悯和可怜,但悲悯情怀不等于简单的可怜与怜悯,而是以博大的、爱的眼光、以感同身受的情感和心境来看待苦难,如《走入枫香地》(崔莫愁);道德审视不同于道德批判,二者的叙事力度有所不同,绝大多数乡土苦难叙事中,是与非、善与恶、道德与不道德等叙事立场都十分明确,但真正能够进行道德批判的深度苦难叙事较少,停留在道德审视层面的浅层苦难叙事较多。
(二)抗争与虚无——反思苦难与探究生存
在面对苦难的态度上,较之于沉默与坚忍,抗争与反思的方式显得更为积极、主动。在现实层面上,苦难危及乡土世界的生存和秩序,尤其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现代文明的入侵,对安徽的乡土世界带来颠覆性变化,严重损害乡土主体的肉体与精神,势必引起反抗与挣扎。于是,抗争苦难成为乡土苦难叙事的必然选择。《古老的黄颜色——老人和大江的故事》、《古船》(汪海潮)中的乡土世界守望者对现代文明即将造成的苦难做殊死搏斗,《不许抢劫》(许春樵)、《农民工》(许辉、苗秀侠)、《我从山中来》(胡进)中的受难者对城市文明制造的苦难进行自发抗争。在历史层面,苦难改变乡土世界的秩序与结构,毁灭乡土主体的生存家园和生命,乃至影响历史的抉择与进程,如《望儿山》(陈登科)、《不屈的大清河》(曹无为)、《寻找组织》(赵宏兴)等。然而,绝大多数情况下,在历史长河和现代文明面前,乡土世界是苦难的承载体,乡土主体抗争苦难的资本唯有身体(肉体)。在话语权缺失、抗争力量薄弱的处境下,很多时候抗争苦难是无谓的抗争,如鲁彦周的《双凤楼》、江少宾的《狗事》、贾鸿彬的《流泪的剑》。在这部分苦难叙事中,抗争苦难只是徒劳,抗争苦难导致抗争无果,受难主体无法消弭苦难带来的伤痛,似乎只能选择沉默与坚忍,由此容易导致对待苦难的虚无态度和消极情绪。在此情境下,思考苦难成因,思索人性善恶,探究生存法则,便成为苦难叙事的另一重要精神文化追求。
应该说,反思苦难是安徽乡土苦难叙事的传统,“反思文学”代表《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就是从政治、社会层面还原专制政治的荒谬本质,总结反思文革历史的苦难与教训。90年代以来,安徽乡土苦难叙事在现实和历史两个层面进行反思。一是反思苦难成因。造成苦难的原因主要包括历史军事斗争、专制政治统治、体制机制改革、社会发展转型、地域文化民俗等外部因素,它们是造成苦难的主要原因,安徽乡土小说的历史与现实苦难叙事都体现了这个特点。二是反思人性善恶。90年代以来,安徽乡土苦难叙事走出了人性善恶二元论的模式。乡土世界的受难主体是人性善的代表,但同时也存在自身的局限与不足;苦难的直接制造者代表着人性之恶,其恶的产生又有一定的历史、时代与地域原因。但无论反思的结果如何,高扬人性之善、批判人性之恶是乡土苦难叙事的共同追求。在上述反思的基础上,乡土苦难叙事着力探究生存法则。这既是苦难叙事担当社会责任的体现,更是历史与时代的使命使然,如农民工进城后所遭遇的身份危机、生存苦难,就成为绝大多数进城苦难叙事的重要表现内容。
(三)救赎与担当——精神超越与回归乡土
如前所述,经由苦难认知生命和存在的意义,以此达到精神上超越苦难,是苦难叙事的最高价值追求所在。在“彼岸”与“此岸”之间实现苦难的能量转换,是实现苦难叙事终极价值的路径。然而,中国没有西方的苦难意识与宗教救赎传统,缺少“彼岸”情怀,二者苦难救赎和精神超越的方式与目标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很大程度上,国家、民族等整体性、群体性的社会需求才是中国苦难救赎的追求目标和价值所在,而牺牲个体则成为苦难救赎的普遍方式。进入90年代以来,安徽乡土苦难叙事已经历并正在实践这样的苦难救赎方式。面对群体性苦难时,总会出现敢于担当受难的个体,他们凭借一己之力拯救群体,完成苦难的救赎,如《望儿山》(陈登科)、《不许抢劫》(许春樵)、《汴河》(周恒)、《寻找组织》(赵宏兴)、《少年王》(陈家桥)、《农民工》(许辉、苗秀侠)等。这类具有苦难救赎精神的个体,能力出众,敢做敢为,具有担当精神,是乡土苦难的拯救者。与之同时,他们的苦难救赎具有一定的历史与时代特征。在身份上,他们是来自乡土世界的受难主体,与救赎对象具有相同、相近的人生与价值追求,如《不许抢劫》(许春樵)中的杨树根形象;在动机上,道义与情感等最朴素的需求是救赎的主要出发点,如《少年王》(陈家桥)中的王小二;在精神境界上,他们是乡土世界的平凡个体,精神囿于既定的阶层范围,很多时候并没有上升至一定的历史、社会和政治高度。
需要指出的是,行动上积极解决苦难、拯救受难群体,精神上认知、超越苦难,理应成为对待苦难的两种选择方式。可是,当沉默与坚忍不能改变苦难的现状,抗争与反思易导致现实颓败与虚无主义,而苦难救赎的现实作用毕竟有限时,那么,实现苦难的精神超越便成为苦难叙事的最高精神追求,表现苦难生存背后的美学价值便成为苦难叙事的魅力所在。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以来安徽乡土苦难叙事的视角由关注社会群体苦难、国家民族苦难转向关注个体生命苦难,关注个体生命苦难会使苦难叙事视角下移,弱化对国家民族苦难的叙述。然而,90年代以来一部分安徽乡土苦难叙事并没有局限于个体生命苦难的叙述,而是在努力探寻另一条关乎广泛性、整体性的苦难叙事路径,即通过关注乡土个体的苦难,走向苦难的精神超越,以此实现苦难叙事的群体性、普适性价值。“因为苦难的更深刻和潜在意义是精神性的,它遍及人类每一个人,而且更大程度上指对人类整体性和超越性的苦难以及人类整个历程的苦难”。〔4〕这种叙事实践主要体现在一部分乡土历史小说和关注生存人性主题的苦难叙事中,如《秋声赋》(潘军)、《钱楼纪事》(杨小凡)、《肉身》(黄复彩)、《碑》(许辉)等。在这类叙事中,苦难无法避免,具有宿命色彩,受难主体遭受肉体和精神双重打击,最终得到释然与解脱,实现精神上的超越。其中,受难是达到释然、解脱与精神超越的共同方式,而推动受难主体精神变化转型的则是源自乡土文化中的朴素生活智慧,如许辉的《碑》,洗碑匠王麻子平和、静默的生存方式拯救了被苦难压抑得近乎绝望的“我”。乡土世界的苦难由乡土自身实现救赎与超越,那么,回归乡土便成为世纪之交乡土苦难叙事的最终精神文化选择。
三、苦难叙事的隐忧与思考
乡土苦难叙事视角的变化转移,精神文化向度的拓展探索,使得世纪之交的安徽乡土小说在拓宽叙事视域、丰富叙事内容、深化主题意蕴、挖掘地域文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进一步彰显了苦难叙事的社会价值。与之相关的是,90年代以来部分安徽乡土苦难叙事对苦难的认知与理解存在误区,精神文化走向存在价值追求良莠不齐、精神境界高低不均的特点,这些不足与隐忧亟需作深入思考。
(一)误区:认知与理解模糊、不准确,甚至消解、歪曲
不可否认的是,苦难叙事源自苦难自身,很多时候乡土世界的苦难更多体现为底层生活的物质贫穷与落后,正因如此,90年代以来安徽乡土苦难叙事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将苦难简单等同于底层生活形态,苦难叙事缺少精神向度。苦难是乡土世界最直观的存在状态之一,成为很多乡土叙事的主题选择和表现内容。90年代以来,安徽乡土苦难叙事中苦难的外在表现形态较为丰富,涉及物质生活的匮乏、婚恋观念的落后、生存秩序的混乱,以及历史乡土的衰败等,将这些底层生活形态作为乡土苦难叙事的重要表现内容,具有其合理性。“底层生命的确承受着更多的生活苦难,但底层生活不能代替苦难,也不能代替文学的苦难意识与苦难表现”。〔5〕如果将苦难叙事简单等同于对乡土世界底层生活的叙述,甚至作为唯一表现内容时,便存在着认知与理解的误区。部分乡土苦难叙事便存在上述问题,过度关注底层生活的外在形态,止于对苦难形式的叙述,缺少探索苦难的精神意义。
二是不加提炼,模糊、消解苦难与苦难叙事的界限。苦难叙事建立在苦难的体验、感知基础之上,但是苦难叙事不等同于苦难。90年代以来,不少乡土苦难不经艺术的转化直接作为苦难叙事的对象,苦难叙事直接参与现实问题,因情感宣泄等需要而不加克制地沉溺于苦难不能自拔,模糊了苦难与苦难叙事的界限,甚至消解了它们之间的距离感。“文学的悲剧不是对现实苦难的模仿,更不是对它的复制;那些不经考察价值、纯粹顾及现状而胸中顿生悲哀之情的现实苦难,不仅先天缺乏悲剧艺术的崇高素质,就连能否上升为悲剧,都令人怀疑……对现实苦难不加提炼,必然会使苦难叙事丧失博大的人类关怀精神”。〔6〕此外,从文学审美角度来说,苦难与苦难叙事之间必须存在一定的距离,消解距离感会影响到苦难叙事的艺术性和文学价值,“无论是在艺术欣赏的领域,还是在艺术生产之中,最受欢迎的境界乃是把距离最大限度的缩小,而又不至于使其消失的境界”。〔7〕
(二)导向:容易导致消极情绪和虚无主义
一是无法提供解决乡土苦难的路径,容易导致消极情绪。如前所述,90年代以来安徽乡土苦难叙事三个维度的精神文化走向,与三个层面的叙事立场和态度有着必然的联系。乡土世界受难者的弱者地位与强力话语权的缺失,导致受难者与苦难叙事选择沉默与坚忍的态度;抗争与反思折射的是苦难的无法抗拒,以及知识分子对苦难的思考;因阶层、认知和能力的局限,救赎和担当的社会效用毕竟有限。可以看出,上述种种立场、态度并没有能够为解决乡土苦难提供路径,相反,90年代以来安徽乡土苦难叙事中始终弥漫着一股消极、哀怨与无奈的情绪。一般意义而言,苦难叙事理应产生刻骨铭心的记忆,激发崇高的精神力量,实际情况却是,部分苦难叙事未能导向对光明的向往、促进精神的提升和人性的净化,而是留下了受挫的颓败阴影、悲哀的生存状态和畸形的生存态度。苦难叙事无法提供解决苦难的路径,反而导致、助长了消极情绪的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二是质疑苦难与苦难叙事的价值,容易导向虚无主义。就历史层面而言,苦难与苦难叙事的价值在于帮助体认历史本质、廓清发展规律,构建正确合理的历史观;在社会现实层面,推动解决苦难,提供解决苦难的路径,改善对待苦难的态度,认知生命和存在的意义,达到精神上超越苦难是苦难叙事的价值所在。然而,90年代以来部分安徽乡土苦难叙事囿于苦难自身,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叙事能量,其历史与社会现实价值未得到充分实现。在叙事文本中,苦难的存在具有宿命色彩,既无法回避,也难以消解,更没有历史价值与现实效用。因此,苦难与苦难叙事的价值必然遭到质疑,并导致虚无主义的出现。
(三)境界:止于关注当下、制造怜悯和个体苦难
学界普遍认为,当代中国乡土小说的苦难叙事深度不够、终极追问缺失。安徽乡土苦难叙事也存在这样的共性问题。90年代以来,一部分安徽乡土苦难叙事止于关注当下、制造怜悯,限于道德审视、个体苦难,导致叙事境界、精神追求走低,以致出现终极追问、精神超越与整体意识缺失的症状。
止于关注当下。“当苦难被充分生活化,没有哲学的支持和对人类困境的反思,生存苦难就很难得到一种审美上的提升”。〔8〕90年代以来,安徽乡土苦难叙事更多彰显了关注当下的品格,即关注乡土世界的现实生存困境、婚恋悲剧、经济掠夺、权力压迫,以及向城求生的苦难等。应该说,关注当下本无可厚非,它是文学社会价值和历史使命的体现,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如果苦难叙事仅仅止于关注当下,一味沉入对“此在”问题的关注,“苦难叙事不仅被明确的时间和空间所限制,失去了超越‘此在’的可能;而且实用意识又常常使苦难演变成作家手中操纵的道具,对之功利性的诉求,导致了‘彼岸’追问意识的缺失”。〔9〕关注当下是90年代安徽乡土苦难叙事的亮点,如在具体叙事文本中,物质化生活和生存苦难成为苦难叙事的主要表现内容,苦难叙事更为积极参与、回应各类乡土社会问题等。但是相当一部分乡土小说的苦难叙事仅仅止于关注当下,缺失终极追问意识和“彼岸”意识。
止于制造怜悯。从接受美学角度来说,苦难叙事首先且极易引起情感共鸣,容易催生怜悯感。如果说怜悯感是苦难叙事的情感底线,那么90年代以来安徽乡土苦难叙事均胜任这个要求。可是,“真正的苦难文学,并不是要把读者引向身临其境般的痛苦体验,它传达的是一种经感悟后对苦难的理解、超然与达观的态度”。〔10〕如在部分农民工务工题材的苦难叙事中,对留守农民所遭遇的生存境遇、情感断裂作了细致入微的叙述,可是关于人性、生存困境等问题的思索却戛然而止。另外,从苦难叙事美学效果来说,崇高感是苦难叙事的最高美学追求。然而,在一部分婚恋题材的苦难叙事文本中,婚姻与恋爱的悲剧仅止于制造怜悯,限于对悲剧人物的同情,婚姻与爱情的崇高感与神圣感却难以彰显。因此,要避免这些倾向和现象,务必要充分关注受难主体在受难过程中,为克服自身观念和各种压力所承受的精神撕裂、灵魂挣扎和情感煎熬。
止于个体苦难。中国的苦难意识不同于西方,没有宗教性的精神忏悔传统,但是苦难的精神指向却是一致的,即指向人类群体,具有整体性和广泛性特征。无论是道德审视、抗争苦难,还是苦难救赎、终极追问、精神超越,通过体验、感知具体苦难,经由具体苦难认知人类生命和存在的意义,以此达到精神上整体超越苦难,才是苦难叙事的唯一精神指向。如前所述,90年代以来一部分安徽乡土苦难叙事努力探寻另一条关乎广泛性、整体性的苦难叙事路径,以此实现苦难叙事的群体性、普适性价值。然而,在苦难叙事中,这部分叙事文本毕竟数量有限。相当一部分苦难叙事或囿于个体苦难,自怜自哀,或关注某一类群体,只做现实层面的表象性叙事,缺乏整体性的精神指向是它们叙事上的共同缺憾。
作为安徽乡土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世纪之交的安徽乡土苦难叙事主动顺应既定文化境遇的转型,继续坚守文学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充分彰显苦难叙事的文学自觉和精神价值,其叙事视角发生移位和变化,并在精神文化探寻方面付诸努力与实践。移位与变化、努力与实践,使得安徽乡土苦难叙事既与时代命题和社会思潮保持同步,又提升了地域文化和乡土叙事的价值,丰富了安徽乡土文学的内涵。同时,不能回避的是,叙事视角的移位与变化,意味着乡土苦难叙事需要在当下文化境遇急遽变化中形成文学积淀;精神文化走向的多维努力,仍然难以提出彻底脱离苦难的方略,造成苦难叙事很难形成深度。这些不足与隐忧值得对苦难叙事做进一步研究。此外,当前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进城”与向城求生成为乡土世界主体的主要追求;在强大的城市叙事面前,乡土叙事日渐沦为“亚叙事”,甚至有沦为城市叙事附庸的可能性。这些变化需要安徽乡土苦难叙事继续保持发展变化的视角,不断探寻苦难叙事中的精神文化价值。然而,无论怎样变化,贴近乡土世界,保持乡土情结,感知乡土苦难,仍然是安徽乡土苦难叙事获取叙事动力和精神价值的唯一途径。
注释:
〔1〕刘俐莉:《苦难叙事与20世纪中国文学》,《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2〕〔4〕〔5〕施军:《苦难叙事的看点与立场》,《文艺评论》2009年第3期。
〔3〕雷达主编:《新世纪小说概观》,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6〕〔9〕〔10〕斯炎伟:《当代文学苦难叙事的若干历史局限》,《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7〕爱德华·布洛:《作为艺术因素和审美原则的“理距离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美学译文》(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2页。
〔8〕王东凯:《论底层文学苦难叙事的美学缺失》,《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