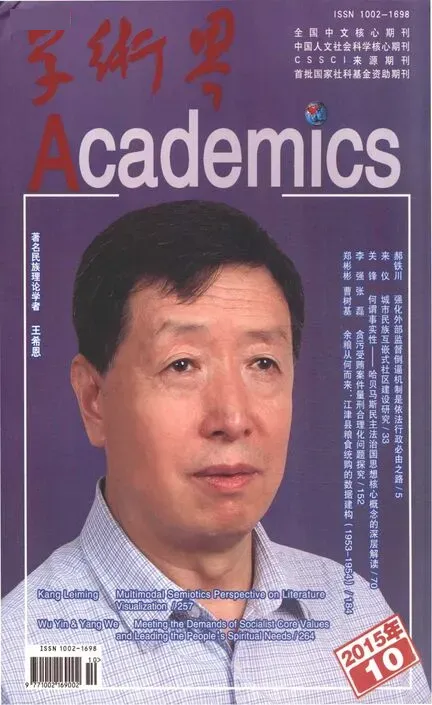生态公共产品及其社会合作〔*〕
○ 张 静,张 陈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2.西南大学 研究生院,重庆 400715)
人类认识生态环境问题经历了从局部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从自然资源保护到自然生态服务的视阈转换,积淀着对生态环境的深刻认识,进而为生态弱化的现实矫正提供了重要指向。1935年,英国生态学者阿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率先向全世界亮出“生态系统”的观点,将人与自然纳入由复杂生物、生态群落及其物理环境因素构成的生态框架之中,把生态系统的研究视角延伸至制度与政治的话语场域。20世纪70年代韦斯特曼(Westman·W)首次提出“自然的服务”这一概念,90年代达利(Daily·G·C)和克斯特(Costanza·R)相继发表论著阐述人类社会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依赖,重视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服务及其价值,开启了重视生态供给服务的理论研究。
一、生态公共产品的现实困境: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
作为人类生活资料的重要内容和进行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基础,生态公共产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生态公共产品供给是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统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条件。关于生态公共产品的范畴,受到生物学重要影响并察觉生态异化端倪的马克思认为,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1〕。这一界定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在各国生态保护政策文件中都有不同程度涉及。毫无疑问,生态公共产品涉及范围宽广,几乎涵盖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全部内容。
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迅猛发展时期就发出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呐喊,尽管如此,强化人类主体地位的工业化不断“异化”自然,阻碍着重构人与自然和谐的探索方向。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美国人乔治·P·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的代表作《人与自然》、德国人卡尔·弗腊斯(Karl Fraas)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一书中也详细描述了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展现了自然界平衡与和谐被人类肆意横行的破坏性力量扰乱之后满目荒凉的景象。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绚丽的万花筒下所展现的,是人与生态环境的剑拔弩张和日益对立,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生态破坏等日益成为制约工业文明与城市发展的瓶颈,严重威胁个人的身体健康、生产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没有维护生态公共产品,反而丧失了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还任由资本操纵下的人类活动向生态环境单向地无限度索取,加速了生态公共产品的质变、失衡甚至消泯。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系统日益脆弱和恶化。空气污染、全球变暖有目共睹,陆地干旱与洪水泛滥同时并存,森林被毁、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催生了水资源危机,促使人类重新思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各国生态与环境保护运动风起云涌,对环境运动的普遍关注由人类反思资源有效利用与经济发展方式到进入政治领域影响公共政策过程,从哲学伦理层面的角度解读到社会应用层面的实践框架,在此基础上谱奏科学和理性的绿色和谐韵律,期冀建构整个生物有机系统与生态环境内在协调的经济与社会秩序。然而,“现代生态环境领域作为一个系统,已经越来越向我们呈现出无序性、随机性、非线性、非平衡性、不确定性等各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往往使我们感到生态环境问题的难以预测性和难以预防性”。〔2〕大量事实已经表明,人类在应对生态弱化和生态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复杂性、尖锐性、挑战性的严峻现实面前,依然经常性地展现为拾遗补缺的局面甚至激烈的利益博弈。
中国虽然在生态公共产品领域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进展较快。20世纪80年代,中国制定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并依法制定了一系列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方针和政策。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仍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的根本任务,生态环境问题虽有所显现但还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环境破坏的景象无情地展露在眼前:荒漠化程度加剧加快,植被破坏、草场草地退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农村污染突出,生态公共产品破坏速度惊人。在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人民的生活愈加富裕,对天蓝、水清的生态公共产品诉求也日益强烈。“人民群众过去是‘求温饱’,现在是‘盼环保’”。〔3〕近年来,“非点源污染”〔4〕成为新增的生态困境,人们活动的“生态足迹”〔5〕越来越广。2013年,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的雾霾天气持续不散,再次敲响了生态环境失衡的警钟。根据2013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显示,在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围绕大气、水体和土壤污染治理三项重点工作,加大环境保护工作力度,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扎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取得新进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化,生态公共产品有所好转。与2012年相比,化学需氧量下降2.93%、氨氮排放量下降3.12%、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3.48%、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4.72%。但是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环境风险不断凸显,污染治理任务仍然艰巨。〔6〕
从本质上讲,生态公共产品作为关乎人类的重要资源,没有人与人的“差别对待”,亦无不同群体间的“序差结构”,均等分享是其基本前提。长期以来,生态公共产品及服务水平与个人生态预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存在着“鸿沟”,表现为生态消费过度、生态公共产品短缺和供给水平不高,以至于生态领域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和不对称现实凸显。这是因为,一方面,生产力水平直接影响生态公共产品的质量和供给方式;另一方面,生态公共产品的需求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变化,相应的供给是一个动态过程。对此,马克思指出:“需求”是一个历史概念,最初人类的需求也是极少的,“需求本身也只是随着生产力一起发展起来的。”〔7〕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共同利益需求日趋多元化,催生了层次、规模不断变化和扩充的复杂的需求结构。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多样性与生态公共产品的有限性、稀缺性之间的矛盾派生出供求结构的“非对称性矛盾”,甚至进一步显现为区域分化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意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这就需要寻找更加符合生态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规律的社会发展机制,解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释放生态公共产品的自然价值,在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系统服务和人类爱护生态公共产品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绿色中国梦”。
二、生态合作机制的形成:生态公共产品与社会组织形式的嵌合关系
生态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其供给的数量与质量、内容与形式、途径与方法涉及到每一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关乎着人类利益矛盾的发展趋势和解决路径。人类的利益矛盾冲突需要采用一些措施或手段来消解,需要一种机制来解决。“源自进化经验的基本技能为人类行动提供了战略选择”,其中技能之一就包括“协作、合作和互助”〔8〕。纵观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以一定社会组织为基础的、以群的联合力量来寻求生存与发展,是人类社会中的经常和必然现象。
然而,面对生态危机,人类社会又将通过何种社会组织形式以达至公共利益最大化?法团主义主张政府与社团的联盟,通过代表制度“将有组织的社会经济生产者团体整合起来,形成有组织的合作与互动,并实现对社会的动员与控制。”〔9〕社团中心主义弱化国家的行动目标与主导功能,强调社团的参与主动性,采用多元化互动模式以有效遏制垄断。社会生态学则坚称,生态危机的出现几乎都是由人类社会引起的,只有生态化的社会机制才是解决深植于人与人之间冲突的生态矛盾的价值目标和根本向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协同治理”(Cooperative governance)理论是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复杂性的合作机制,在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不断延伸和拓展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实质上,基于国家还是社会为中心的理论分析均秉持世界所有生物的整体性与有机融合的理念,强调人类与其它生态形式的物种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只是通往各种要素紧密合作与持续互动目标的组织模式选择各有不同。
资源的公正分配依赖于某种组织形式——在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中,每一社会主体充满对生态和谐的追求和环境保护的诉求并付诸行动,齐心协力地维护和保障共同的公共利益,创立彼此相联的归属感并形成集体活动、连接机制或决策过程。在生态危机不断加剧的进程中,“全球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被认为是对于实现人类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最大结构性障碍。”〔10〕显然,外部强制的契约规范、组织框架与利益操纵并不能使共同行动具备整合力量,防范毁约的相互警惕以及自我的利益预期置换了社会性行动所需的自主性意愿、对称性依赖和共在性行为,社会组织演变成个人谋求利润最大化而毫不犹豫进行破坏性资源开采的外在形式。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威胁的时代条件下,生态公共产品供给包含着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折射出社会生活的交往行为模式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从感性“互助”到工具理性“协作”再到更高级的价值理性“合作”,人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结合程度”及其组织形式既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映射,又是人类所处时代主要追求目标的存在反映和社会历史进程的建构方向。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合作发展趋势,其实质是所有受决策安排影响的利益攸关者为避免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导致生态灾难采取的积极应对机制,同时也是社会合作在生态公共产品领域的一种现实观照。
毋庸置疑,生态公共产品供给作为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人类所有力量的相互依托、彼此契合与共同发展。从顺应自然规律的角度来说,生态资源再生的周期性和生态系统自我恢复功能的长期性,催生了生态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的有限性,需要人类运用生态公共产品循环再生的客观规律,通过广泛有效的社会合作网络构建互相形塑的螺旋式互补关系,克服因生态公共产品无法通过显性的货币形式表现、缺乏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不愿进行大量投入的现象。例如,某一区域流失掉的生态公共产品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被漠然视之,得不到任何补偿,需要全国性的跨区域合作治理和政策协调。由生态公共产品问题引起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深刻而普遍,其基础性、全局性的地位决定了这个问题有效解决的长期性、艰巨性,其治理成本和服务效率成为困扰全社会的重大公共难题,必须整合各种力量与资源,才能有望得到化解。
当今时代,生态是一种生产力,生态公共产品资源的量足质优、供给的高效均等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新的标志之一和区域竞争力的实力显现。生态公共产品资源再生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在一系列的发展生产、调整社会组织形式、变动工作方式等活动中,通过社会合作机制的制度安排有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解消极因素,合理解决生态公共产品与生产需求、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合作社会所依据的是合作理性,它与竞争社会的区别只在于后者所依赖的是工具理性,合作社会则是要把当前存在于社区中的互动关系和行为扩展到整个社会,改变工业社会中那种工具理性的非人格化趋势,创造出完整的人之间的互助与合作。”〔11〕实际上,受到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深远影响或现有体制滞后于生态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障碍,生态公共产品决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的途径和渠道匮乏或者失效,相关的程序、组织和法制不健全、不完善,甚至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严重缺位。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一些为数不多的环境评价的文件中明确公众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是生态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公众知情权缺失、参与度低下、监督不到位成为普遍现象,各生态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造成生态公共产品维护与保障的合作机制难以形成。
社会合作的根本目的在于帮助人类更好地应对自然资源匮乏、能源供给不足、生态环境脆弱的现实状况,使之在生态公共产品风险性、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更加自觉和自制,必定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具备必要的公共理性和公共责任。面对这种情况,“一个促进合作的极好方法是教育人们关心他人的利益,推己及人地为他人着想”,因为“在一个关心他人的社会中,即使遇到‘囚徒困境’,成员之间也容易达成合作”〔12〕。同时,社会合作思想为当前生态公共产品的有限性和短缺性寻找到了一条新的方向,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并积极拓展,各种“合作型治理”方案大量涌现。在国外,“合作型环境治理”被普遍视为“一种解决性政策策略”,“在广义上被认为是融合工业、公民群体、或者地方政府的探讨、协约以及一系列的正式以及非正式的管理的治理类型”〔13〕。在国内,“环境合作治理”成为摒除生态公共产品区域屏障、消解生态公共产品优质资源短缺困境的方法被一致认同:“只有通过广泛的基于公共利益和怀有合作意愿的环境合作治理,才能真正地避免‘公用地的悲剧’和‘集体行动的困境’,也才能最大限度地谋求人类与自然共存共荣的公共生态环境利益。”〔14〕
三、“生态合作型政府”的建设: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关系
“问题就是时代的格言”〔15〕,问题的合理解决就是时代的进步。生态领域的公共产品问题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安全、社会的发展安全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推进程度与中国梦的实现程度。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面对破坏严重、灾害频繁、治理困难、供给不足的全球生态大环境,积极应对与有效解决当前生态公共产品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促使人们以人与自然和谐的视角去考量政府的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管理水平。
不可否认,政府是生态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力量。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明确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政府的责任。自90年代伊始,加拿大与美国等先后开始实践“绿色政府”计划,确立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领导作用。诚然,在生态公共产品领域,国家与政府具备许多优势,在公共财政投入、确立标准质量、进行监测评估、推进生态环境修复、健全生态法制、增进生态技术研发、动员全社会力量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即使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为了社会合作的稳定性,政府的强制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需的”〔16〕。因此,政府在生态公共产品供给上必须发挥其“主导”作用,承担相应的生态职责,通过全方位的必要措施保护和发展生态公共产品。“政府从适应于向自然界索取资源的传统工业化社会的行政管理,转变为适应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行政管理,其重要标志就是建设生态型政府。”〔17〕生态型政府不是纯粹单向度地规范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而是对政府与自然关系的拓展与营造,是对生态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
当然,“生态责任型政府”不等于“生态万能型政府”,承担职责不同于孤军奋战、单兵突进。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传统的思维定势对于生态公共产品的认知还存在着“偏见”。这是因为,“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18〕。在这样的“权威意识”指导下,大多数人认为,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仅仅是生态公共产品的享有者而不是创造者、维护者和供给者,把个人定位于被动接受的角色因而忽视个人的积极作用,与生态公共产品的整体性供给特征所要求的广泛参与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及其财政投入以解决现实的窘况,致使部分个人、群体、组织和区域对于生态公共产品的“自觉”意识和“自为”表现差强人意,缺乏应有的生态责任和担当,“搭便车”成为生态公共产品领域必然发生的结果。
生态公共产品供给不仅仅是生态资源的保护与提供的过程,更是政府运用其行政力量,与生态公共产品的维护者、建设者——社会主体开展广泛的社会合作,让多元生态主体参与具体过程并逐步提高生态意识,使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遵循生态规律并取得生态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的综合效益过程。“由于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以及不同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管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生态保护制度都不能自发形成,这就需要权力机构——政府逐步提供并强制推行,包括企业、区域间、国家内部以及国际间的整体性的生态保护制度。同时,也由于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公共产权性和外部性,生态保护制度的创新和提供需要企业、区域间、国家内部以及国际间的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密切合作。”〔19〕积极建构以合作精神为导向、政府服务为基础、大众参与为内容、制度安排为保障的社会治理模式,是社会的客观要求和时代的现实召唤,展现为遵循生态规律的总体性视角、倚重生态合作的正确价值认知、依靠全社会的自愿性共同行动以及普遍互惠的科学管理体系。与之相应,生态合作型政府是在政府职能中融入环保理念,使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社会主体的共同价值判断,引导全社会走向可持续的生态治理模式和合作型的社会发展模式。
目前,政府提高生态治理水平的重要方式就在于,调动一切积极的社会力量,推行第三方治理,尤其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鉴于政府在某些生态事务领域的管理“失灵”,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政府在生态管理中的运行范式,将生态公共产品服务与供给作为政府职能、政策目标、制度安排等的生态规定和行政指向,实现生态公共利益最大化。“生态协同治理”理论主张“既不能主要依赖国家集权管理,也不可能以地方自治管理为主;既不是简单加强国家统一管理,也不能简单引入市场机制,而是一个以‘良治’(good governance)为目标,追求经济和生态综合效益最大化,新型的统一集中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网络管理体制的现代综合治理模式”。〔20〕总之,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互动,倡导政府主导价值为基础的各生态主体相互依存的多元治理结构,在为社会充分提供量足质优的生态公共产品的具体实践中实现其服务性,必然成为生态合作型政府的发展趋势。
同时必须注意到,由于生态公共产品的特殊性,不能完全放手让市场配置、让无数“经济人”不断试错后探索出一条最优选择方案。在当前生态危机日益显现的状态中,实现一种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集体与个人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及在生态公共产品政策设计与实际运行中纳入功能分化重组的供给范式,进而将社会合作的视角及其思想内核贯穿于政府职能的执行过程中,建构生态合作型政府在生态公共产品领域进行资源分配、利益整合与矛盾平衡的关键特色,以有效解决诸多生态利益和矛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政府充分发挥市场职责,加强生态规划和生态投入,逐步推进生态的市场化管理、组织化参与和公众化治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用政府主导和市场配置进行配套组合,充分调动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在互动对接的合理作用下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形成保护生态、合作治理的巨大合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公共产品供给需要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号召力、凝聚力,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推进相结合,促使社会主体在政府引导下更好地发挥建设性作用。不过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社会主体是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力量,并不是说围绕个人偏好或群体利益来提供生态公共产品,而是强调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是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前提,社会主体是生态公共产品的维护者、供给者、创造者,也是优质足量生态公共产品的享有者和受益者。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6页。
〔2〕〔14〕黄爱宝:《论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环境合作治理》,《社会科学》2009年3期。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26页。
〔4〕非点源污染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NPS),参照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解释是:溶解和固体的污染物从非特定地点,通过降雨和地表径流冲刷,将大气和地表中的污染物带入受纳水体(包括河流、湖泊、水库和海湾等),使受纳水体遭受污染的现象。
〔5〕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EF)由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里斯(William E.Rees)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意指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利用自然的量需要的土地和水域的面积,形象地被理解成一只负载着人类及其创造成果的巨脚踏在地球上时留下的脚印大小。
〔6〕具体数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网站:《2013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http://zls.mep.gov.cn/hjtj/qghjtjgb/201503/t20150316_297266.htm.2015-03-16。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5页。
〔8〕〔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评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5页。
〔9〕〔英〕米切尔·黑尧:《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10〕〔英〕简·汉考克:《环境人权:权力、伦理与法律》,李隼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11〕张康之:《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合作治理渴求》,《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2期。
〔12〕钱箭星:《人类的合作是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必然选择》,《生态经济》2002年第11期。
〔13〕〔英〕蒂姆·佛西:《合作型环境治理:一种新模式》,谢蕾摘译,《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16〕〔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30页。
〔17〕王彬彬、刘祖云:《解读生态型政府:提出、意旨及其价值》,《晋阳学刊》2008年第4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19〕冒佩华:《市场制度与生态逻辑》,《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8期。
〔20〕张连国:《论复杂性管理范式下的生态协同治理机制》,《生态经济》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