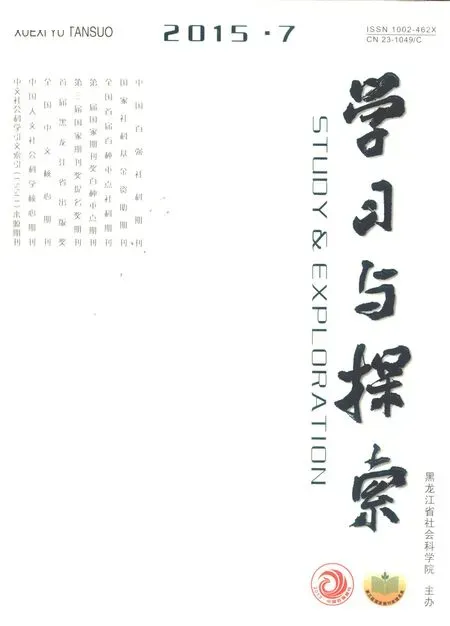政治哲学与促进公平正义
杨玉成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北京100091)
一、政治哲学认识和处理公平正义的理论框架
从字面上看,所谓政治哲学就是以政治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政治的要素包括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和政治行为。政治哲学主要以政治中最稳定的要素即政治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从人类历史上看,国家是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所以政治哲学集中研究国家制度。在西文中,“政治”这个词就脱胎于古希腊文的“城邦”或“国家”,因此从词源上看,政治哲学也就是关于国家的哲学,即以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当然,政治哲学对国家的研究不同于政治学对国家的结构及其运行所做的经验研究,而主要是阐述和讨论用于评价国家制度的道德标准。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正义、自由、平等、民主都属于对政治制度进行评价的道德范畴,其中正义经常被看作是首要范畴。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情况也类似。儒家经典《论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这句名言代表着儒家对“政”的理解。政就是“正”,就是要“帅之以正”“正己而正人”。当然,儒家重视的是“为政者”的道德品质之“正”,如果我们按照偏重制度正义的现代观念,从“为政者”个人品质延伸到国家或社会制度的品质,那么,所谓“政治”也就是以“正”施治,即以正义为基本原则来进行国家治理。
什么是正义?当我们把正义作为国家或社会的品质时,指的是国家或社会恰当地对待它的每一个成员,给每个成员以“应得”之物——给每个成员提供相应的职位和报酬等,同时也要求每个成员承担相应的职责或义务。但是,对于“应得”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正义观。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等级论正义观、权利论正义观、功利论正义观、社群主义正义观和公平正义观等。可见,公平正义观只是各种不同的正义观中的一种。“公平正义”的意思是“公平的正义”或“以强调公平为特征的正义”,其中“公平”是修饰“正义”的。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把公平和正义并列。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去掉“公平和正义”中间的“和”字,正式使用“公平正义”概念。此后中央文件用的都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中间有没有一个“和”字,意思大不一样,表明我们党所追求的正义是公平的正义,而不是别的什么正义。这一字之差,实际上体现的是我党对公平和正义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认识的深化。
西方学界认为,马克思和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是“公平正义观”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公平正义观的建构一方面当然应该以马克思的公平正义思想为指导,另一方面也应该适应新的时代条件充分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进步的正义观特别是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的合理因素,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罗尔斯在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公平和正义的内涵综合起来,用公平来规定正义,率先提出“公平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观念。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平正义”概念应该有来自罗尔斯的启发。罗尔斯使用“公平正义”概念意思是他的正义原则是社会成员在一种公平的初始状态中一致同意的,是公平契约的产物,而依据这种正义原则进行制度安排所产生的也会是一种大致公平的结果。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1971年)中详细阐发的两个正义原则是:“第一,每个人对与所有人享有的类似自由系统相容的最广泛的、完整的基本自由系统,享有平等的权利;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必须这样安排:(a)在与正义的储蓄原则一致的情况下,给处于最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带来最大的利益;(b)依系于机会公平平等条件下地位和职位向所有人开放。”[2]
第一个正义原则其实是对近代权利论正义观的坚持和重申,而且把这个原则作为第一原则又表示罗尔斯对保障公民基本自由或权利的强调优先于对经济和社会利益分配的强调。罗尔斯所说的“基本自由”包括政治自由(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良心自由与思想自由、人身自由(免于心里压迫、身体攻击和肢解的自由)与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法治概念所界定的不受任意逮捕及拘禁的自由等一系列自由或权利。对西方国家而言,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一贯强调保障公民基本自由或权利,并且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原则也落实得比较好,所以西方学界通常认为这个原则创意不大,讨论的空间也不大。然而,对我们国家而言,罗尔斯对这个原则的坚持和强调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在保障基本自由或权利方面尽管已经取得历史性的进步,但存在的问题还是很突出的,所以我们不能像西方学界那样忽视对这个原则的讨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个原则的关注还不够,以致在讨论公平正义时,往往过分聚焦于收入分配方面,对基本权利保障方面的公正关注不够。
罗尔斯的第二个正义原则处理的是“基本自由”外的重要价值的分配,包括收入、财富、机会、权力等的分配。这个原则的大致意思是,分配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制度安排在符合机会公平平等原则的前提下,一方面要尽量照顾社会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也要保证和激励社会精英群体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这个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修正功利论正义观或经济自由主义正义观,既要对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干预经济和社会利益分配的做法进行辩护,又要对国家干预的程度进行限定,避免过度干预所导致的低效率。国内外学界通常很重视这个原则,认为它对处理当代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有较大价值。
二、从政治哲学角度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公平正义问题
由于当前舆论界过度聚焦于收入差距,导致有些学者把当代中国的公平正义状况看得很糟糕。笔者的总体判断是:当代中国社会公平正义从总体上看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存在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这个总体判断主要依据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罗尔斯把保障基本权利看作是第一正义原则,把调节经济和社会利益分配的正义原则看作是第二原则,认为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从第一原则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保障基本权利方面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不容置疑的。比如,改革开放前,中国民众自由权极为有限,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众的自由权获得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民众的思想自由、择业和创业自由、迁徙和流动自由、生活方式自由得到很大程度的释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从罗尔斯的第二个原则即调节经济和社会利益分配的原则看,进步也很明显。比如,社会财富分配方式逐渐从平均主义转向按贡献分配,这就是公平正义的进步。
当然,尽管当代中国公平正义总体上取得重要进步,但是由于法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等复杂原因,我们在这个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难题,有些问题还相当突出。其一是公民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保障还不够充分。比如,近年来一些典型的冤假错案引起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广泛关注。湖北佘祥林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福建平潭念斌案等等一系列典型案件所暴露出来的刑讯逼供、贪赃枉法、假公济私等等严重的司法不公问题确实会使人发出“冤假错案到底有多少”的质疑,这不禁让普通民众对自己的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感到担忧:假如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不幸陷入这类刑讯逼供,我们还有安全感吗?所以,司法不公是国家对所有人的不公,让所有人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这可以说是最大的不公。其二是经济和社会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正,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公平性不足、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差、教育公平问题突出等诸多方面。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政治哲学中寻找应对问题的思路和措施。一是以公平正义为原则进行基本制度和政策安排。公平正义不仅是一个事关扶贫解困具体政策层面的问题,而是事关基本制度层面的问题。我们讲维护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罗尔斯讲公平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是建国立宪的总原则,说的都是基本制度层面的事情。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就事论事是治标不治本。要从根本上理顺各方面关系,应当加大顶层设计力度,立足于公平正义原则制定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从制度框架方面进行有效布局。比如,应该从国家立法层面上保证国家公共财政支出优先用于基本民生方面。当前中国的民生保障体系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碎片化”问题,应该从国家立法层面进行有效整合,真正建立起一个系统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二是加强法治建设,使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的公正得到更加切实的保障,为社会平稳安定运行奠定坚实的基础。现代社会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或权利,唯有通过法治这条根本途径。这就是说保障公民基本自由或权利终究要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法治建设环节加以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了全面部署,思路清晰,“亮点”措施引人注目,其效果值得我们热切期待。三是加大经济和社会利益分配的社会调节力度,避免社会阶层区分固化。二战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引导下,广泛采用公共政策(主要包括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来对经济和社会进行调控。对于西方国家积累的成功经验以及它们所采取的一些切实有效的政策工具,我们可以更大胆更充分地借鉴、使用。有些政策工具,如所得税、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我们已经开始实施。有些政策工具,如房产税、遗产税等,我们可以探索尝试。我们可以采取的手段、工具还是很充足的,可调节的空间还很大。对于经济调节如此,对于社会的调节也是如此。所以,对于党和政府进一步调节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力度和成效,我们应该要有信心。
[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3:199.
[2]RAWLS.A Theory of Justic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