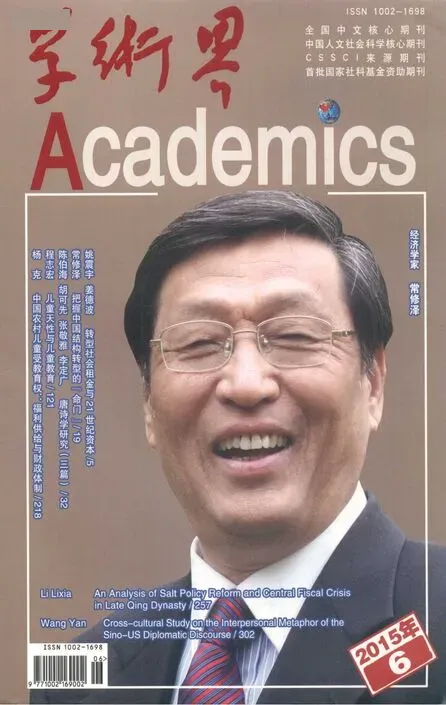再议“孔子删《诗》”说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徐正英、刘丽文、马银琴商榷
○ 谢炳军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孔子是否删《诗》的问题迄今依然系现代《诗经》学探究之热点。《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以此为学术专题,刊登了徐正英《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刘丽文《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说》和马银琴《再议孔子删〈诗〉》三篇论文,立论均主“孔子删《诗》”说;前两文胥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为孔子删《诗》的新证。笔者对此未敢遽信,是以略加考论。
一、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真义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之真正内涵,学者或未之深考,以致易将之泛化,〔1〕故此甚有必要考证之。推原所始,“孔子删《诗》”说肇自《史记·孔子世家》,其云: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2〕
司马迁之初心,以笔者考之,可略论三点:
其一,“古者《诗》三千余篇”,指明孔子之前《诗》已是“三千余篇”之规格,〔3〕此“三千余篇”作为《诗》之诗,各自成篇,并无重同者。
其二,“去其重”,“重〔4〕”系“多”义,因《诗》之诗多,简牍甚重,故孔子删要之。然则“去其重”与“去其重复”〔5〕并不划一。
其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阐明了所采之《诗》之年代,“上、中、至”年代次序粲然,然则司马迁以为孔子所取之诗的年代下限为幽厉之时。〔6〕
据上,史迁之言传达的信息截然分明:一是孔子之前,《诗》已有定本,并行于世;二是孔子之时,依定本之《诗》,删要以剟去其多,最后裒次成编。以《左传》《国语》等载籍考之,第一点于古有征;第二点,史迁当亦有所据,〔7〕然所据未必可靠。
学者今论“孔子《删》诗”说,或已泛化其内涵,已非史迁之初心,有郢书燕说之歉。如学者于“孔子删《诗》”说之外,又起“孔子拆《周颂》诗”新论,并称之为孔子删《诗》之一法。〔8〕笔者以其意有未安,兹略加考论。
首先,“删〔9〕诗”与“分诗”,两词意义歧异:于《诗》而言,前者系剟去其篇数之多,后者系增益其篇数之寡。据此,以“分诗”作为“传世本《诗经》使用的‘删诗’法”,意有未安之处。
其次,“传世本《诗经》使用的‘删诗’法”与“孔子使用的‘删诗’法”系两个不同概念,除非证实传世本《诗经》确系孔门真本,否则,两者无对等关系。
再次,孔子若“分《周颂》”,是为窜乱诗、乐,绝非孔子素怀。刘文称孔子未尝亲览《周公之琴舞》,然则孔子芟薙周公、成王组诗就成不根之论,以不根之论考定“孔子删《诗》”说,恐难成理。学者或又谓成王组诗系孔子所删削,然此亦不类孔子素志:孔子如删原属《诗》之成王组诗,则既系删乱《诗》,又系妄削乐,如此正乐乃系乱乐。
最后,刘文所据之例未足以申明“拆诗法”,其例复称引如下。
《左传》宣公十二年(前597年)传,楚庄王曰:
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10〕
据此,刘文称现行本《诗经》将原本属于《武》之诗,分拆成了今所见之《武》《赉》《桓》三篇。以笔者考之,恐未见其然,兹略作考索:
第一,“其三”“其六”当系以篇说,不以“章”说。遍览《左传》,所赋之诗标明“某诗之某章”者,文意胥为“某诗之第某章”,凡计二十三处;“其三”“其六”之后未标示以“章”,是以不能将之系以今本之《武》。杜预《注》云:“其三,三篇;……其六,六篇。”是以“三、六”为篇。王国维云:“以《赉》为《武》之三成,以《桓》为《武》之六成……。”〔11〕是王氏亦以“三、六”为篇。
第二,《左传》之“《颂》”“《武》”与《赉》《桓》同属《大武》,《赉》《桓》非“《武》”之章。
入《周颂》之“《武》”与周乐《武》同名异义:前者系入《周颂》之《武》,后者系《大武》。可以上举事例之文证之:楚庄王所引《诗》之章句皆源自今本《诗经·周颂》,然而前称《颂》,后称《武》、“其三”、“其六”而不称《颂》,而《诗》于楚庄王之时早行于世,是以庄王于《周颂》颇为精熟,然则《武》、“其三”、“其六”亦系《颂》〔12〕诗。楚庄王继引《诗》后又云:“夫《武》〔13〕,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是为避免周乐《武》与《周颂·武》重同之弊,引《时迈》时称“颂”;然则《时迈》系《大武》之首篇,《武》《赉》《桓》分系第二、第三、第六篇。〔14〕
综上所述,司马迁“孔子删《诗》”说之初心系“孔子因《诗》三千余篇数目多、简策多,故删要而排纂成书,定著三百五篇,以备王道”,即“去重”系“去多”之意,而诗之年代下限系幽厉之时。学者对史迁之意的阐发,或已离其真义,“孔子删《诗》”说已被泛化。
二、清华简《周公之琴舞》非“孔子删《诗》”说之证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载录周公诗半遂、成王组诗九遂,且有一首与《诗经·周颂·敬之》相合,学者或据此推衍《周公之琴舞》组诗为繁本《诗》之诗〔15〕;进而以成王之诗九遂仅余一遂之事例,类证孔子删《诗》“十分去九”之说可信〔16〕。以笔者考之,认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非“孔子删《诗》”说之显证,兹分两点简论之。
(一)周公诗、成王八篇诗未入《诗》
迄今,传世载籍与其他出土文献未见清华简周公之诗、成王八篇诗。然则在未再有新材料之情形下,周公、成王之诗于《诗》采编之时,是否被收入《周颂》之问题当再斟酌之。
显然,诗之采集、删要、定篇、润色、配乐、定本等等工序,皆需各司其职的王官们分工合作,方能完成《诗》之定本这项繁琐的工程,非集一人一时之才力可为。然则《诗》之结集,乃是官学所为。定本之《诗》,既是周一代之乐舞的歌唱文本,又是官学之诗、乐教本。教本之性质决定了《诗》之规制,其整体上不宜累牍。是以欧阳修所言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其一篇者”,可视为官方制撰《诗》之时的选诗方法。由此观之,周公、成王之诗未被录入《诗》,于理有协。
首先,周公、成王之诗本身可独立成篇,国史或乐师不必全用之。〔17〕准此,周公、成王之诗有未入《诗》者,亦不为异事。
其次,入《诗》的《周颂》之诗,已被赋予类化新义。如前文所述,《大武》之诗六篇,入《周颂》者四篇;〔18〕且入《诗》之《六武》诗篇比次并不相依。学者或以之为简错篇乱,以笔者考之,未见其然。《诗》定本之时,所选之诗被赋予新义,次序随之而易,其势必然。显然可见,《大武》诗六篇,本与武王文治武功之事相涉,然入《诗》后不啻次序改易,意义亦已泛化。寻《毛诗序》,《时迈序》“巡守告祭、柴望也”,《武序》“奏大武也”,《赉序》“大封于庙也”,《桓序》“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然则,较之《风》《雅》诗旨的人物、事由之指实,《周颂》旨趣与之异辙,三十一篇诗,仅九首涉入人名,且其中六篇所祭对象系后稷、文王、武王,为周王朝告神颂祖之常乐,亦已具类化意义。概而言之,述后稷、文武盛德,记郊宗柴望大事,录助祭、祈报、合乐、朝见、敬毖、自励、类祃,《周颂》之诗分门别类,施用亦胥已类化,已足备论功颂德之礼乐。由此而观,周公、成王之诗有未入《诗》者亦不足为怪。值得重申的是,入《周颂》之《敬之》旨趣亦已类化。《毛诗·敬之序》云:“群臣进戒嗣王也。”《周公之琴舞·敬之序》云:“成王作敬怭。”是前者以“嗣王”代易了后者“成王”,诗之意蕴由此而异。
最后,今本《诗·周颂》未见组诗,形制短悍正是《周颂》之诗本色。
学者或称今本《周颂》诗篇形制短悍,已非繁本《周颂》原貌,其原本系气势磅礴之组诗,〔19〕以此方足彰显周王朝礼乐歌舞之盛美。〔20〕然而,王朝、诸侯奏乐,可取一诗,可合几诗,〔21〕王朝可合六代之乐而奏之、舞之,〔22〕亦可造气势恢宏之歌舞。故此笔者于此意有不同。《周颂》形制短悍,正是其本色。而篇章较之宏大的《鲁颂》与《周颂》分途,“《鲁颂》之文,尤类《小雅》,比于《商颂》,体制又异。明《三颂》之名虽同,其体各别也”〔23〕,是《三颂》体制各异。然则体小思精、分合自如,正是《周颂》诗之本色。考之《周礼》《礼记》等载籍,歌《周颂》仅是祀天神、祭地祗、祀四望、享先祖等乐舞仪式中的一小环节,若歌以组诗,则既耗时,又加重乐工之负担,观乐、听乐者必倦而烦之。准此,《周颂》诗之制撰、精择,以体小意全为胜,而非以体雍势壮为优,此乃《周颂》形制短悍之主因,亦是成王八篇诗未选入《诗》之一端。此外,组诗未能入《诗》与周王朝“乐不可极”、“乐盈而反,以反为文”之选乐哲学理念殆亦有渊源。
(二)尚未有成王组诗为孔子所删之明证
徐文称:“孔子删定流传至今的《诗经》文本仅保留了《敬之》一首,九去其八……它就是孔子删《诗》‘十分去九’的典型个案和实证,具有示范意义”。〔24〕以笔者考之,未见其然。
其一,抄写《周公之琴舞》之楚简首尾完备,并无残阙,然则刊削周公诗之人或是书手,或是周公诗外流之时已亡佚其八。此可作为孔子未必自行己意删《诗》的旁证。也即孔子所得《诗》本,早亦已不录成王八篇诗。另有旁证,商之《颂》诗在孔子之前已有亡佚现象,“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25〕。孔子距正考父的年代已两百多年,若十二篇《商颂》得以顺利传承,孔子断然不会去其大半:其一,孔子视“礼乐”为文化之生命,信而好古,曾为考稽殷礼而适宋,寻访礼之文献,而《商颂》作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礼乐仪式,孔子会录而存之;其二,《商颂》亦系王室诗、乐的歌唱、演奏对象,属于雅言雅乐;其三,孔子乃宋之后人,无理由数典忘祖,删汰其先世在周太师处校对过的、用之祭祖的《商颂》诗。〔26〕
其二,孔子将三千篇之《诗》删削成《诗三百》,于孔门必是惊天动地之大事,本当值得子嗣或门徒大书特书一笔,然考之研究孔子的第一手资料《论语》,无片言只语与之有涉。孔子亦无一言半语论及删《诗》及删《诗》之动机,仅仅是自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而孔子所“正”之对象恰是孔子私家《诗》本。然则孔子所据以校正己本之《诗》版本必是善本,或许此善本就在卫国,故孔子言“自卫反鲁,然后乐正”。
学者或以为孔子“正乐”与“删诗”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侧面,〔27〕又或以为:“正乐”,孔子造之于晚年;“删诗”,孔子为之于中年。〔28〕此两论所援据皆系孔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之语,而在阐释上分途异辙。其实,孔子之只言片语不足征“孔子删《诗》”说,反之,其言甚有可能暗示着孔子未曾删《诗》。《诗》,《风》《雅》《颂》之结集者;然孔子之言仅涉及《雅》《颂》,未及《风》。而依学者所言,季札观《周乐》之后,孔子若调换了《豳风》和《秦风》次序,〔29〕孔子不应一字未及《风》诗。
其三,教官、礼官等王官组成的《诗》的编定组系剟去周公、成王之诗者。“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夏造殷因周仍,官府教化制度相沿袭,于古有征。《诗》被编定于王朝,载籍亦有明文。然则周朝教化系统中教官和礼官是《诗》教本的编著者;正本清源,《诗》的定本系教官和礼官协作之结果。其或至迟于康王之时已结集,《风》《雅》《颂》一体,尤其是作为王朝祭祀仪式文本的《周颂》,被编定入《诗》成为王朝祭祀乐歌范本。显然,乐歌的选编、润色、定本除与教官和礼官择取教本理念相关外,周王对乐歌文本之审美志趣亦与之渊源甚密。周康王恰是“辞尚体要”之王者,〔30〕是以教官、礼官在“定乐歌”〔31〕之时,裒次成篇之《周颂》亦以短悍精要一以贯之。准此,删削周公、成王诗者乃系《诗》结集之编定者,而非孔子。
其四,成王组诗九去其八,无法类证“孔子删《诗》”说:一、溯本求源,未有成王组诗确为孔子所删之显证;二、刘向等人校书十分去九等例,系删削其重同者,与史迁“孔子删《诗》”说意蕴歧异,且一是官方修书,一是私家编书,性质亦异,然则两者无类证关系;三、孔子若自行己意删削《诗》,必然与行世已久之官府《诗》本分途,以一删本《诗》出使四方,必然与东胶虞庠之繁本《诗》难以“专对”,是以刊削繁本《诗》非孔子素怀。
其五,礼崩乐坏与《诗》之短缺不侔,不能成为孔子删《诗》之动机。一、礼乐和《诗》分属于两大教化体系,同源而分流,礼官体系崩坏,教官体系尚未离散。二、礼崩乐坏,从一定程度上说,恰是《诗》大行于世的助力,讽谏、聘问之际,宴飨酬酢之间,引《诗》、赋诗、断章以明理、发德〔32〕、言志。由此观之,《诗》文本在使者的赋诗仪式活动中,不仅不会短缺,反而会形成一个各方去异存同、趋向统一、齐整的经典范本,即《诗三百》。三、经过教官或礼官几次修订《诗》,裁成庠序教本,凡《风》《雅》《颂》业已独具风格,其各自句法之长短、篇章之多寡,措辞之雅俗等等,已生成稳定的文本形态。准此,孔子乃不必舍近求远,争于才力而芟薙《诗》之诗。
其六,孔子私家本《诗》与今本《诗经》亦存歧异。考之《论语》、上博简《孔子诗论》,孔子不仅不删窜属于今本《诗经》的诗篇,反而在他的私家本《诗》中,存有被后世称为《诗》之“逸句”“逸篇”。学者或称今本不存之,此必为孔子所删削,而于教学之时偶有所及而已。考之《论语》,“逸句”远非孔子偶有所语,而恰系孔门弟子常习之《诗》的疑问者。
最后,在王朝、诸侯国广为流传之诗未必入《诗》。如祭公谋父之诗《祈招》、清华简芮良夫之诗以及《左传》一些仅言“某人赋某诗”的“某诗”而未明标“《诗》曰”者,皆于王朝、诸侯国广为流传,并成为赋诗断章之共享资源,故史官录而存之。
此外,若将《周公之琴舞》置于“历史场景”中考察,组诗率系王官失守、宫廷文籍外流之时,散至诸侯列国。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33〕,本由教官、礼官归管保存之《周公之琴舞》传播至楚地,或就在王子朝奔楚之时。
综上所述,迄今尚未有成王组诗为孔子所删之明证。《周公之琴舞》组诗余者自始至终胥未收入结集之《诗》,然则未入《诗》之组诗皆不能称为“《诗》之逸诗”,是以不能援据《周公之琴舞》而论定“孔子删《诗》”说。
三、余 论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学者或有将之泛化之嫌,已离司马迁初心之真。跃出“孔子删《诗》”说真膺性之困囿,重审之,“孔子删《诗》”说确系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论题:与古本《山海经》“后羿十日射落九日”之神话相类,“孔子删《诗》”说以饱含神话色彩的姿态出世,其殆与儒家文化传承和西汉礼教制度及司马迁“一家之言”等有颇深渊源。
周公之诗、成王八篇诗未入《诗》背后的意蕴,可资探究《诗》成书之情况:反映出《诗》之诗被采编成集时的情形,即组诗并非都被录入《诗》;入《诗》之诗旨趣已被赋予类化意义,与原诗之《序》已分路。学者或多关注孔子订正《诗》之功,而忽视了王官之《诗》编定者之首功。
注释:
〔1〕如马银琴将司马迁所言之“孔子对《诗》三千的删定”换成“孔子对《诗三百》的删定”,又牵合“去其重”与“增删诗篇”两者(马银琴:《孔子对〈诗三百〉的删定》,《两周诗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然则马氏之“孔子删《诗》”乃系“孔子对行于世之定本《诗》先删削旧诗、后增补新诗”;徐正英称“孔子删《诗》”系删削繁本《诗》之单篇、重复篇章及相近章节,最后附益晚出之诗。(徐正英:《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载《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第21页。按:余文所引皆省称“徐文”及标示引文页码);刘丽文以“现行本《诗经》确实对古《诗》删削过”、“传世本《诗经》使用的几种‘删诗’法”等表述代替“孔子删《诗》”之意蕴(刘丽文:《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说》,载《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按:余文所引皆省称“刘文”及标示引文页码)。
〔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36-1937页。
〔3〕后文“及至孔子”之“及至”一词,是表示时间之顺延,意为“定著三千余篇之《诗》,行于世,至孔子之世”,明孔子之前《诗》已系史迁所言之篇数,且已经定本成书,行于世;否则,不能以“诗”之名命之。
〔4〕《说文》云:“重,厚也。”《左传·成二年》云:“重器备。”《注云》:“重,犹多也。”《礼记注疏》云:“尊其位,重其禄。”《疏》云:“‘重其禄’谓‘重多其禄’。”,然则“厚”可引申为“多”,多方厚,重量多。孔颖达云:“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诗谱序》,《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3页)是孔颖达之意亦以“重”为“多”。显而易见,若干篇相同之诗,仅能称为一篇。欧阳修云:“以予考之,迁说然也。……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焉!以《图》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诗》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欧阳修:《诗图总序》,《诗本义》,《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678页)是欧阳修之意,亦以“三千余篇”为不重复者。
〔5〕赵坦云:“删《诗》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复焉尔。”〔清〕赵坦:《孔子删 <诗 >辨》,《宝甓斋文集》,《清经解》,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10260页。
〔6〕东汉班固早已发现司马迁之说有未安处,故云:“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班固:《艺文志》,《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8页。
〔7〕《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汉书》,第1708页),是“孔子删《诗》”之说或源自“杂说”。又“与不得已”言明三家《诗》说皆离其真,然其真义茫昧无可详考,姑且以《鲁诗》为近本义。据学者考证,史迁所学正是《鲁诗》,因为“《史记》中的《诗》说最接近《鲁诗》。”陈桐生:《史记与诗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8〕刘丽文以成王组诗九去其八之现象,逐推“传世本《诗经》确实对原始诗作进行过删节”(刘文,第38页),进而推衍“司马迁说的孔子删诗并非无据之言”(刘文,第38页)文末又称孔子“甚至采用对原诗‘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等形式”(刘文,第43页)将一首诗分拆为几首,以备《周颂》之篇数。
〔9〕《说文》云:“删,剟也。”剟,即删削之意。
〔10〕秋左氏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82页。
〔11〕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页。
〔12〕赵逵夫称“《周颂》中作品,全为周王朝宗庙祭祀和朝廷礼仪乐歌,自然是以‘颂’为名。”(赵逵夫:《诗的采集与〈诗经〉成书》,《文史》2009年第二辑)是言甚确。乐师或史官归类武王之乐歌,必然将之编入“颂”。
〔13〕古今学者多以“武”为武王,笔者以之为《武》,因其承前启后,概引诗之意,与“其章”相应。
〔14〕《申培诗说》曰:“《武》,《大武》一成之歌;《赉》为《大武》之二成;《时迈》盖《大武》之三成也;《般》为《大武》之四成;《勺》盖《大武》之五成;《桓》此《大武》六成之歌。”(明程荣纂辑:《诗说》,《汉魏丛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页)是乐歌次序虽不类楚庄王之说,然《时迈》隶属《大武》之一成,以笔者此文所考,可成一说。
〔15〕徐正英称“之所以判定成王所作九首组诗为《诗经》‘逸诗’,是因为该组诗的第一首即为今本《诗经·周颂》中的《敬之》篇”(徐文,第20页);刘丽水称“毫无疑问,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现行本《诗经·周颂·敬之》是繁本和删节本的关系”(刘文,第38页)。
〔16〕徐正英称“《周公之琴舞》九首组诗的发现,则首次从正面为‘孔子删《诗》’十去其九展示了文本范例。未经孔子删定的《周公之琴舞》所存成王诗篇是一组九首,而经孔子删定流传至今的《诗经》文本仅保留了《敬之》一首,九去其八……它就是孔子删《诗》‘十分去九’的经典个案和实证,具有示范意义”(徐文,第21页)。
〔17〕王国维云:“疑《武》之六成,本是大武,周人不必全用之,取其弟二成用之谓《武》,取其弟三成用之谓之《勺》,取其四成、五成、六成用之谓之《三象》。”(王国维:《说〈勺〉武〈象〉武》,《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王氏言之成理。奏乐如斯,取诗亦可如是。
〔18〕王国维称余者系《昊天有成命》与《酌》两篇。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6页。
〔19〕刘丽文称“今天我们看到的三十一篇《周颂》,几乎篇篇都那么短,失去了《周公之琴舞》所昭示的颂诗应有的磅礴气势”(刘文,第43页)。
〔20〕赵敏俐称:“从‘成王之诗’看,我们已经可以想象到西周初年的王朝礼乐歌舞表演之盛大。……让我们领略了周初乐舞在当时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对《诗经·周颂》的原初形态也会有全新的认识。”赵敏俐:《〈周公之琴舞〉的组成、命名及表演方式蠡测》,《文艺研究》2013年第8期,第41页。
〔21〕《左传·襄公三年》载:“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是《雅》乐可合而奏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孔颖达《疏》云:“舞时堂上歌其舞曲也。”是取六篇诗入歌。
〔22〕《春官·宗伯下·大司乐》载:“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88页。
〔23〕韦昭注云:“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颂,颂之美者也。太师,乐官之长,掌教诗乐,《毛诗叙》曰:‘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余五耳。”
〔24〕《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81页。
〔25〕〔28〕徐正英:《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第21、19-28页。
〔26〕宋刘恕编《资治通鉴外纪》卷三《周纪一》云:“(周)宣王二十八年(前800年),宋政久衰,商之礼乐散亡。戴公时,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归以祀其先王。”朱彝尊《经义考》卷九十八《诗一》称:“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归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归祀其祖者,删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
〔27〕马银琴:《两周诗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15页。
〔29〕马银琴称:“这种变动正好说明,在季札之后,必然有人进行过调整乐次,即所谓‘正乐’的工作。承担这项工作者则非孔子莫属。”马银琴:《两周诗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15页。
〔30〕其时,三监顽民已靖,世变风移,较之周成王之时,已是“垂拱仰成”,社会安定,为编定诗、乐,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物质基础。然则《竹书纪年》所载“康王三年定乐歌”可信。
〔31〕《竹书纪年》云:“康王三年定乐歌。”徐文靖笺云:“《周颂序》曰:‘歌《清庙》以祀文王;歌《天作》以祀先王、先公;歌《执竞》以祀武王;歌《思文》祀后稷,以配天;歌《昊天有成命》以郊祀天地。’如此类者必皆其所先定。”(〔清〕徐文靖:《竹书统笺》,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9页)。又称:“《竹书》‘康王三年,定乐歌,吉禘于先王,申戒农官,告于庙’,《臣工》之诗当作于是时。”(〔清〕徐文靖:《管城硕记》,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46页)。
〔32〕从“升歌发德”(《礼记·郊特牲》)到“赋诗发德”,是乐、诗分途之显证。
〔33〕《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