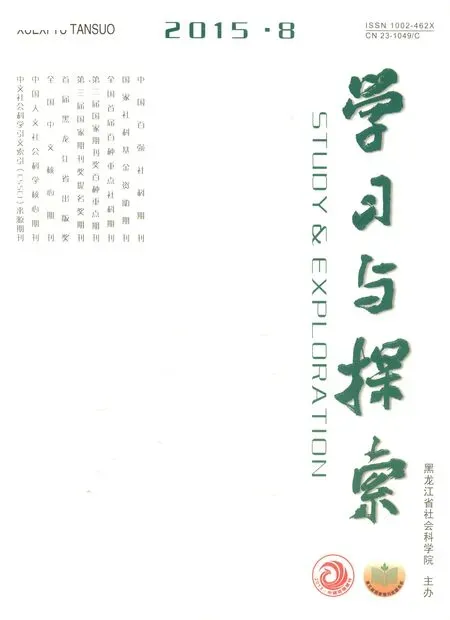社会时间的结构分析
于 飞
(1.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哈尔滨 150080;2.中共上海市嘉定区委党校,上海 201800)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社会时间的结构分析
于 飞1,2
(1.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哈尔滨 150080;2.中共上海市嘉定区委党校,上海 201800)
传统的自然时间观认为时间是一维的、无生命的、机械决定的。随着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提高,这种自然时间观从物理学与天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从社会学研究角度来看以及从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均暴露出诸多弊端。在此情况下,社会时间观应运而生。社会时间观认为时间应当具有多重结构,包括自我时间、互动时间、制度时间、文化时间,它是属人的、生态的、文化的、历史的。只有当我们正视了社会时间的多重结构,认识到时间内容的丰富性,才能在现实当中克服自然时间观的各种弊端。
自然时间;社会时间;自我时间
在人类历史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自然时间观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自然时间观认为时间是由天体的运转而形成的,它是一维的、无生命的、机械决定的。而随着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提高,自然时间观的主导性受到了挑战,社会时间观应运而生。社会时间观认为时间应当具有多重结构,它是属人的、生态的、文化的、历史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深刻的过程和结构,它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与层次。
从物理学与天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在自然时间观当中,人们对时间的理解主要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基于天文学的认识,另一个是基于物理学的认识。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时间是自然的日出日落、潮起潮落。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时间与物体的空间距离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人们已经习惯和熟悉了自然时间观这两种看待时间的方式,但是这两种方式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忽视了时间的存在依赖于人的感知这样一个事实。
从社会学研究角度来看,在传统的时间观念里,认为时间是由自然所决定的,每一天、每一周都是由太阳的起落、月亮的圆缺所赋予的。但是众多社会学家经过研究,却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他们认为时间的区分都是由天文学现象决定的那种一般的信念抽取了时间自身的内容,仅是一种假象。社会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在人类丰富多彩的文明中,时间被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
从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在自然时间观念那里,时间是作为物体运动的测量手段出现的。机械决定论是自然时间观的哲学基础。这种时间观念认为时间是纯粹客观的,它脱离了时间中的充满生命力量的因素。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柏格森将其称为“纯一时间”。“纯一时间”是与空间不可分的,它通过空间的可分隔性而成为测量运动同时性的手段。在这里,时间被空间化而失去了其持续性的真实含义。柏格森认为这是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的通病,即从静止的角度来思考运动或是把绵延不绝的时间空间化[1]。他的时间哲学中对传统时间观的批判就是由此入手的。柏格森曾经对“阿基里斯悖论”进行过深入的批判。他认为,这一悖论的错误在于把具有持续性的运动(“绵延”)与运动所经过的空间距离等同。“绵延”是不可分的,但是空间距离却具有无限可分性。如果一定要对持续着的运动进行空间上的分割,那么运动就不复存在,余下的仅仅是空间距离而已。因此,在以“阿基里斯悖论”的创造者芝诺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时间观中,用空间化的思维取代运动的绵延性是有悖于客观事实的。时间失去了其真实内涵,成为与空间相同的纯一形式,并且服从于空间的纯一形式而存在。这种思维方式在科学中得以延续并发展。
可以说,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什么是时间,它具有怎样的特质,它蕴含着如何的意义和内容,一直是人类哲学思考的重要内容。同样,也是人类的思考赋予时间以内容,否则,时间就是空空的框架。
既然自然时间暴露出诸多悖论,那么时间是什么?应该说,时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自然时间,它反映自然界本身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二是社会时间,其本质是时间的社会化,是人的实践赋予时间以意义。时间的存在依赖于人的感知,时间的度量依赖于人的活动,时间的内容依赖于人的思考。
事实上,在今天,当人们提到“时间”的时候,所指的通常就是社会时间。它或者是被时钟测量和分割的时间片段,或者是掺杂了人类感情的时间描述。思想家们对社会时间问题曾经做过很多的思考。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时间的实践本性决定了时间必然具有社会性。在结构化理论当中,时间总是带有社会性的,因为时间反映和规范着人的实践,正如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所说时间是一种“社会构成”。在现象学家那里,时间只能互为主体性地得以构建,是人赋予时间以意义,因此时间必然具有社会性。在生态哲学那里,实现了时间的主体归依,如柏格森就认为时间只有对于人才是真实的。
相对于自然时间观所认为的时间是一维的、无生命的、机械决定的,社会时间观认为时间应当具有多重结构,它是属人的、生态的、文化的、历史的。对社会时间的探究,是对人的社会性的一种基本特征的探索。时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深刻的过程和结构,它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与层次。社会时间在结构上是由几个相互依存的层次所展现的。
1.自我时间。社会时间的最基本的层次表现为个体层面的自我的时间,是个体的主观时间感受。在这一方面,存在主义者进行了深入阐述。海德格尔提出了“自我时间”的概念,指出自我时间是直接出现在孤独的自我体验当中的,如果没有理性的自我,也就不存在什么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甚至也没有什么此前或此后。这些结构是由我们的心灵强加于世界的。它们并不是给定于存在之中的,而是以被记起的过去、被体验的现在和被想象的未来这种形态而被投射在存在之上的。
不像物理学的时间,自我时间不是同质的。在自我时间里,相当遥远的个体生活中的事件,在意识中可能会被描述的就像对5分钟之前刚刚发生的事情的记忆那样生动。柯特尔把这种时间称为立体的时间,因为我们的记忆能够操纵时间中的事件,似乎他们就是平常的物体,能够被随意到处推动。立体的时间与那种线性的时间形成对照。依据后者,事件是以一种不可违背的时间次序出现的。在立体的时间中,我们能够把一个过去的时间带到现在,并且使它进入一个不同的事件之中;历史和生活从来都不是固定的。在诸如下棋、做手术这样使人全神贯注的活动中,人的主观体验到的是一种无形的流动感。在其中,时间似乎停止了[2]。一个人所具有的体验的类型,它们的时间上的接近,以及它们的立体的形态,确保每个人的时间感受是独特的,而且对个体与他人的互动有着重要的影响。
此外,海德格尔的“第四维的时间结构”,也是自我时间的一种延伸性的观点。他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一种可以称之为第四维的时间结构,海德格尔追随康德,称第四维的时间结构为“正在接近的接近”或“接近的状态”。它是我们所体验到的空间意义上的接近在时间上的相同之物。例如,当我们的汽车沿着道路快速行驶时,我们看到远处的物体慢慢向我们靠近,快速闪过,然后又消失在远处。除了对物体的体验,我们也体验物体变近或变远的这个过程本身。这是对空间意义上的“正在接近的接近”的体验。与此类似,时间上的“正在接近的接近”,把过去和未来与存在于时间体验之中的现在连接起来,而存在于过去和未来之中的事件,是根据它们与被看作是现在的东西是近还是远来进行排列的。海德格尔把现在想象为在两个方向上伸展出去,拥抱过去和未来,而不是把它看作我们被放置其上的即刻的尖尖的山脊。正如物体因为它们空间上的接近而有不同的呈现一样,事件在时间上接近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呈现。人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对于快速接近自己的事物会产生一种恐慌。在社会快速变革的时代,自我的时间恐慌发展为文化上的“未来冲击”。
2.互动时间。“自我时间”是处于社会时间结构当中的第一层次,但是在社会时间的结构层次中,仅有“自我时间”还是不够的。自我通过与他人交往而在时间上必然与他人产生一种互动关系。时间因与人相连而获得主体性地位,但个体只有将自身的生命时间融入社会当中,并与社会时间相协同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无论何时,只要两个人或者更多的人发生了直接互动,人的主观时间就会与一种时间模式发生部分重叠,这种时间模式就是“互动时间”。互动时间是一种主体际性的存在。互动时间的流动与互动过程中的“自我时间”观念与“他者”的时间观念密切相关。
首先,互动时间的流动存在一种相关性,它依赖于互动过程中他人的行动。群体中,其他个体的社会地位使支配群体时间中进行轮换和其他时间规范的规则成为必要。除了诸如进行“轮换”这种一般的互动时间的文化规范之外,还存在诸如朋友、好朋友、熟人、陌生人、对手或服务员与顾客等等这样的社会双边关系中形成的特殊互动规则。如果某人似乎在遵循着互动时间的规则,而他人却认为这个人的做法就他或她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界定来说是不恰当的,这个时刻,立刻就要求某种类型的解释或话语的弥补行为。否则,他们的关系就要重新界定。举例来说,一个人在交通高峰时间去公共汽车站的路上停下来买报纸,他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与卖报纸的人进行闲谈;反过来,卖报纸的人也知道他不应该试图与顾客有更多的交谈。如果不遵循互动时间的规则,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打乱日常生活的有序流动,影响所涉及的人,甚至间接影响更多的人。
其次,时间的互动性除去反映在构成整体社会的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上,还反映在掌控自我时间的每个个体的多样性上。人们因为他们首要关心的是短期的未来还是长期的未来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是采取宿命论的观点还是自我决定论的观点而在显著的时间关注点上形成差别。与未来相关的时间结构上的这些变化,对人们处理在群体中的时间嵌入有着种种影响。例如,长时间的朋友或爱人,一起回忆过去,展望未来,相互之间有种种内心的呼应、感动,从而使他们的互动时间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他们共享的经验的这种特殊品质是在其他任何互动的群体中都找不到的。生活中的各种群体,比如说家庭的成员,如果他们希望作为称职的家庭成员达成时间上的协调的话,就必须使他们与符合他们身份的时间保持同步。
3.制度时间。社会时间不仅体现在个人的时间感受以及人与人互动过程中的时间感受上,同时也体现在群体的时间安排上,时间的这样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制度时间。每一个社会群体都会含有由社会活动的共同节奏而构成的内在关系,会设定其特殊的时间制度来固定其行为周期。
具体说来,制度时间所指的是组织内部的时间安排、时间规划。在每一制度领域内形成的特定组织,是在制度的范围内来建构该组织的时间表和有关时间的规则的。虽然组织成员会考虑他们必须与之进行交流的其他组织的时间结构,但是,在任何具体组织中支配时间使用的规范和处罚措施,只会直接影响到该组织自己的成员。
在现代组织中,高度严格的官僚化体系依赖于对时间的周密安排部署。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从出生起就要服从制度时间安排。这也是人们社会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婴儿出生在一所医院里,何时洗澡、何时体检都有固定的时间设定,在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后他就又要开始体验到幼儿园的那种官僚化的时间表。每一个这样的机构都有有效的、标准化的、完善化的时间规划。接下来,就是12年、甚至25年的预期的社会化,在此期间,个人的教育经历是在种种学校所组成的官僚化组织之内展开的,他们必须与组织的制度时间相同步,否则就会遭到批评甚至排斥。
官僚化的时间制度的严格性是组织时间未来取向的特定结果。高度严格的官僚化体系依赖于周密的组织计划。就其面向未来的时间指向而言,与大多数的个人相比,组织是更加一致、更具系统性,也是更理性的。官僚机构持续地评估完成目前的项目所需要的时间,以及预先指定有未来展望的时间规划。一旦以这些时间为基础资源得以分配,人们就被强制遵守时间表。虽然紧凑的时间结构是官僚化组织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组织的特征,但是,即使是自愿性的组织,一旦某人在这个组织中承担了一个核心的角色,那么,组织也总是会对这个人的时间进度以及总的时间投入情况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组织时间中的严格性的基本社会根源,是其高度的分层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性。在工厂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组织中,生产是按照由许多时期和阶段所构成的一种固定次序来安排的。这一过程的某一阶段花的时间太长,就会打乱其他阶段的时间安排。因此,在现代社会当中,制度时间是社会时间结构层次中的重要一环。
4.文化时间。在社会时间的几种构成当中,无论是自我时间、互动时间抑或是制度时间,都处于特定的文化当中。在各种文化中,对时间的看待方式有所不同,这也证明了时间观念与人类活动的密切相关,它不是孤立于人类社会之外全部归于自然的,而是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的时间。文化与时间的联系是时间社会性的重要体现。各种文化看待时间的不同是时间社会性的重要体现,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时间的形态方面来看, 在人类社会的时间观念当中,时间观念在形态上分为循环时间观和线性时间观两种。不同的文化看待时间走向总体上有这样两种不同的方式。循环时间观是通过观察自然界循环往复的周期现象和对灵魂不灭的坚定信念,将时间理解为一种循环运动, 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虽然肉体可以被毁灭, 但是神和灵魂是不会消失的。循环时间观的显著特征是相信人在死后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转世, 相信历史会依据某种神秘的力量和根据某种不可知的逻辑循环往复地上演[3]。与循环时间观弯转周而复始的形态不同,线性时间观的形态始终是延展的、射线性的。它反映了时间流动的不可逆性。以现在为原点指向未来,它的方向始终是单一的。
其二,从时间结构的取向方面来看, 世界上存在的各种时间观大体可以分为过去取向、现在取向、未来取向这样三种时间观。在这一方面, 古代社会和历史悠久的民族更加倾向于时间的过去取向。在过去取向的时间观念中,人们崇尚祖先与传统,尊重历史。这种时间取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容易促成整个民族的团结和稳定, 但是与此同时也容易因为总将目光投向过去而故步自封,从而产生衰退。中华文化就是时间过去取向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儒家思想是最为崇尚历史和传统的。例如,在治学思想上主张“信而好古”“述而不作”, 与此相类似,在治国理念上主张要“以史为鉴”, 总的原则是厚古薄今, 将过去看作是现在的标准, 同时也是未来的目标。
其三,从时间的使用习惯方面来看,不同的民族与文化, 由于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的差异, 他们对时间的感知也是不尽相同的,从而使得他们在计时、守时和用时习惯上也有所差异。在计时习惯上,西方人习惯把5 分钟认定为最小时间单位,而在阿拉伯国家中人们的最小时间单位是 15 分钟。在偏远游牧民族中则与这两种用时习惯差异更大,例如在蒙古,人们把 “备马鞍的功夫”用来作计算时间的单位。在守时方面,欧美国家的人比较守时, 将守时看作是一种社会美德[4]。他们习惯于将时间用较短的单位来计量,在时间的安排上较为精确。而非西方文化中,很多国家秉承多元时间观,恪守时间的意识并不强烈,生活节奏比较慢。
近代以来,西方价值观念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守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但是,稍加思索,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时间的使用习惯上并没有严格的孰优孰劣之分,严格的计时、守时并非必然是最好的时间观念[5]。在经济没有发展到今天这样,通信、交通都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的时代里,人们的时间往往是依据自然现象来确定的,例如“日上三竿”“日落西山”,这些说法虽然不够精确,但是却营造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使人的生活节奏变慢,心灵得到滋养。
总的来看,与时钟时间的线性、单一性不同,社会时间是具有多重结构的。它体现为每个人自我的时间感受、时间知觉,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产生的互动时间,人被投入社会之中必须遵循的制度时间,以及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都身处于其中的文化时间。只有当我们正视了社会时间的多重结构,认识到时间内容的丰富性,才能在现实当中克服自然时间观的各种弊端。
[1] 马俊苹.论柏格森哲学中的时间问题 [J].龙岩师专学报,2003:1.
[2] 王敏.“巴扎”(集市)的时间流程 [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3] 汪天文,王仕民.文化差异与时间观念的冲突[J].学术研究,2008,(7).
[4] 霍尔.无声的语言[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
[5] 埃里克森.时间快与慢[M].周云水,何小荣,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8.
[责任编辑:高云涌]
2015-05-11;
2015-04-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舆论格局的嬗变与地方政府执政理念研究”(12CXW004);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课题“从居民参与角度探寻当代我国社区营造的实现路径”
于飞(1978—),女,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从事哲学研究。
B1
A
1002-462X(2015)08-0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