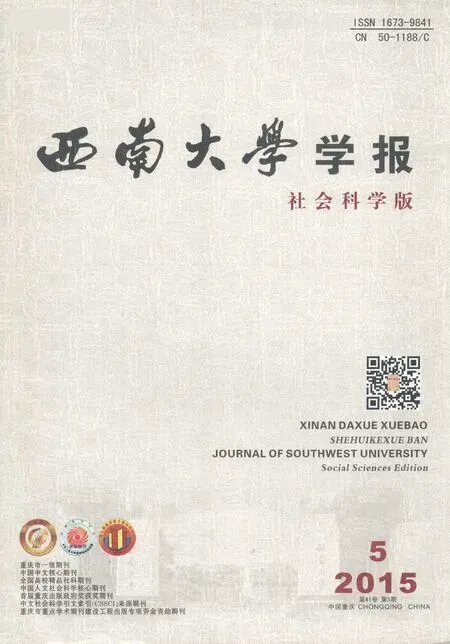《艾凡赫》骑士精神对19世纪初英国矛盾的消解
陈彦旭,陈 兵
(1.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23;2.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艾凡赫》骑士精神对19世纪初英国矛盾的消解
陈彦旭1,2,陈 兵1
(1.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23;2.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司各特1819年创作的小说《艾凡赫》标志着其创作主题与体裁的突变,动机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司各特在小说中书写的中世纪骑士精神,是可能解开这一疑问的答案.作为团结各阶级与民族的粘合剂,骑士精神具有跨越阶级与民族的特征,对法国大革命后英国社会所面临的阶级矛盾问题与民族冲突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指导作用,彰显了司各特作为保守党人对稳定与和谐的社会秩序的渴望,以及对国家认同感与身份归属感的追求.这才是他创作《艾凡赫》的真正原因以及意义所在.
艾凡赫;骑士小说;骑士精神;历史小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国族同构
一、引言:《艾凡赫》创作动机之疑
享有“欧洲历史小说之父”美誉的英国作家司各特一生创作了20多部历史小说.其处女作《威弗莱》(The Waverly)发表于1814年,以1745年苏格兰詹姆斯党人起义为背景,讲述英格兰青年威弗莱与本家族效忠的斯图亚特王室决裂并最终加入苏格兰高地叛军的曲折故事.这部小说确立了他创作的基调与特色,将个人命运置于具体而广阔的历史时代,通过个人经历以点及面地展现英格兰与苏格兰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的矛盾冲突.《威弗莱》之后的多部作品,如《盖伊·曼纳林》(Guy Mannering,1815)、《我的主人的故事》(Tales Of My Landlord,1816)、《罗布·罗依》(Rob Roy,1817)、《惊婚记》(The Bride Of Lammermoor,1819)、《蒙特罗斯传奇》(A Legend Of Montrose,1819)等,均以17、18世纪为背景,描写了英格兰封建社会与苏格兰氏族社会之间的多重矛盾冲突.评论家普遍认为,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的司各特,作品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苏格兰情结,“将他出身的苏格兰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人民介绍给世人”[1].长期以来,这一主题被当作司各特历史小说最重要的特征.
然而,在司各特1819年创作的《艾凡赫》中,却发生了重大转变.就主题而言,与17、18世纪苏格兰完全无涉,描写的是中世纪英格兰本土萨克逊人与诺曼人的矛盾,在时间与地点上都发生了较大的跨越.体裁则从力图与客观史实保持一致的历史小说转变为骑士传奇小说.骑士传奇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具有很大程度的虚构性,如《亚瑟王传奇》《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等主要描写虚幻的游侠与冒险经历,表现逸出现实的理想,这在《艾凡赫》中也有明显体现.历史上的狮心王理查并非小说中那般仁政爱民,而是一个横征暴敛的国王.历史上的罗宾汉也与小说中对狮心王理查忠心耿耿的罗宾汉大相径庭,他是个桀骜不驯的草莽英雄,终生与诺曼王朝为敌,从未向君主效忠或妥协.因为以上原因,《艾凡赫》广受诟病.柯勒律治不无讽刺地说,这部小说只不过是给孩子看的历险故事罢了.大卫·戴希斯对小说中不符史实之处提出了批评,他说:“事实上,司各特对中世纪并不了解.尤其是对当时的社会与宗教生活他几乎一无所知.”[2]对此,司各特本人说:“事实的确如此:我既没有这个能力,也不能煞有介事地装出一副能够掌控全部准确事实的姿态来.小到外在的人物服饰,大到语言与风俗都是如此.”[3]那么,司各特为何要冒险涉足一个自己既不熟悉又不擅长的创作领域呢?《艾凡赫》中的英格兰本土中世纪骑士传奇故事在他的创作轨迹中显得十分突兀,这种转向背后隐藏着什么动机呢?
这一问题曾引起文学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主流看法包括“经济效益论”“语言影响论”“个人嗜古论”“骑士理想论”等,分别从读者心理、语言使用、司各特个人喜好等角度进行了阐释.有学者认为,作为一个精明狡黠的书商,司各特极具商业头脑,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被更广范围的读者所接受,从而扩大销量以取得更加可观的经济效益.从这一角度来说,《艾凡赫》能够更好地迎合英格兰读者的阅读趣味.也有学者尝试从另外的角度进行解读.洛克哈特(J.G.Lockhart)的《司各特生平回忆录》认为,司各特与好友威廉·克拉克曾有过一次交谈,克拉克提到当代英语词汇受到盎格鲁萨克逊古英语与诺曼语的杂糅影响,这引起了司各特的关注,成为他撰写《艾凡赫》的最初动因.另外,19世纪英国兴起了收藏中世纪兵器之风,司各特对此十分痴迷,早在19世纪20年代,他在阿博茨福德的家的门廊就用这些古兵器进行装饰,他在这方面的爱好被用来解释为创作《艾凡赫》的一个重要原因.马里恩·舍伍德提出,在19世纪复古主义复兴的影响下,中世纪的歌谣、叙事诗、浪漫传奇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艾凡赫》顺应了这一潮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司各特在1818年所写的《有关骑士精神的一篇散文》,塔洛克认为《艾凡赫》是一部以骑士精神为主题而融合了历史叙事与浪漫传奇两种文体的作品.以上观点各有道理,但都未将司各特的创作转向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还原其创作语境,考察当时的重大事件与他创作转变的关联,是探究该问题的合乎学理的进路.
司各特创作《艾凡赫》的动机是复杂的,必须结合欧洲动荡政局和革命现实进行研究.司各特是一位具有深切历史责任感的作家,“林纾将司各特的作品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4],高度认同其历史借鉴意义.在《艾凡赫》这部以“骑士精神”为灵魂的浪漫传奇小说中,表现的是作家试图缓和英国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努力,以及建构一个具有稳定秩序的英国社会的渴望,这才是他写作风格与主题突变而创作《艾凡赫》的根本原因.
二、19世纪初英国国内的两大矛盾与“骑士精神”
19世纪初英国面临多重矛盾.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思想传到英国,很多英国人持同情、支持态度,认为革命清除了欧洲封建主义与旧贵族的残余力量,也让人认识到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诸多问题,激发了在英国本土实施政治改革的愿望.伯克说:“法国大革命对英国制度、传统和根本安全形成巨大风险……建议对革命宣传和平封锁.”[5]法国大革命提供了通过极端革命方式解决政治民主化问题的途径.站在英国统治者的角度看,这种激烈的方式并不适用于崇尚温和改革的英国.在历史上,英国通过1688年“光荣革命”完成了从绝对君主专制到多元寡头的政治转型,但究其本质只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一种妥协.王权虽然在光荣革命后被大幅度削弱,但君主制下的爵士、贵族等一套复杂的头衔与制度仍得以保留,中低层人群依然不享有参政权与选举权,那些尊贵的头衔“明显地表现出上层阶级与人口中大多数人之间的差异.其实,英国人都很明白,他们的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6].
19世纪初,在工业革命影响下,新兴资产阶级与工人的力量发展壮大,激发了他们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希望通过变革打破贵族的政治垄断,并围绕选举权与议会议席分配两个问题展开,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就是抗争的成果.在抗争中,游行示威甚至暴乱冲突时有发生.1819年8月16日的彼得卢广场大屠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英国政府惧怕法国大革命激进思想波及英国本土,实施高压政策,引起强烈不满,数万民众聚集在曼彻斯特的彼得卢广场,要求英国议会做出选举权等多方面改革,英国政府派骑兵实施镇压,导致15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同年,英国政府颁布被称为“封口令”的六项法令,禁止集会、游行,限制出版自由.该事件反映了19世纪初英国不同阶层之间不可回避的矛盾.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关系,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使得当时的阶级矛盾更加错综复杂.
19世纪初英国面临的另一尖锐问题是民族矛盾,主要是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之间的冲突.北美独立运动作为殖民地摆脱宗主国控制与压榨而兴起的一场民族解放运动,摧毁了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神话,民族独立浪潮暗流涌动,直接影响了爱尔兰与苏格兰.1798年,爱尔兰爆发大规模群众起义,遭到英国军队残酷镇压.对苏格兰而言,虽然于1707年与英格兰签署了《联合法案》,但苏格兰人尤其是高地人仍然有着极强的民族独立情结,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剧烈冲击下,19世纪初爱丁堡等地爆发了多起反英格兰的起义,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再次成为英国社会的焦点问题.
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冲击下,19世纪初英国内部面临巨大压力.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体来说是对英国缺乏情感上的认同,急需具有弥合作用的精神力量来消解这些矛盾,“骑士精神”则可以很好地扮演这一角色.
何谓骑士精神?塞缪尔·约翰逊在《英语大词典》中指出,该词chivalry的源头是法语的chevalier.而这又来源于拉丁文的caballus,意为马.骑士就是骑马的战士.法国人赋予骑士精神的内容包括优雅的举止、风度、礼节以及浪漫爱情等元素.骑士精神的发生与演变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还包括日耳曼条顿骑兵所代表的“具有尚武精神的骑士”、崇尚封建家臣制与基督教精神的“基督教骑士”、具有新时代理想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的“浪漫的骑士”.骑士精神之所以有可能成为各阶级与民族的粘合剂,源于其“跨阶级性”与“跨民族性”.
就骑士的“跨阶级性”而言,在中世纪如果想要成为骑士,必须先由扈从(骑士候选人)做起,一旦失败便只能做些为主人喂马待客的下等兵工作,如果能幸运通过晋封仪式得到骑士封号,就意味着进入了上层社会,得到某种封建贵族的特权,从而实现“跨阶级性”的人生重大转折.司各特在《艾凡赫》中书写的“骑士精神”,就与“阶级”密切相关,他强调中世纪以“忠诚”“义务”“责任”为核心的领主与附庸之间的牢固关系.附庸要为领主提供生产或军事服务,领主要为对方的生命与财产提供庇护.在历史上,自从日耳曼民族攻陷罗马帝国之后,作为封建贵族的骑士本身在自己的领地上就是领主,但同时又是大领主的家臣与封臣.骑士应对领主绝对忠诚、敬仰与服从,为领主保卫领地或出征,而领主因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并有较广的见识,有资格以“父亲的身份”来统领骑士,并为其提供保护与采邑.这种古老的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体现为“父权主义”,鲁思玛丽·高德纳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父权主义”与“骑士精神”这两个词可以通用[7].发轫于以土地耕种为经济基础与基本形态的封建农业社会的父权主义理论,有助于形成等级和谐、互惠互助的社会制度,促进其平稳运行.汤普生在《英格兰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共有的习惯》中,结合18、19世纪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也认为“父权主义”是用来描述“贵族”与“平民”之间关系的.贵族的身份相当于“人民的父亲”,他们“慷慨而坚定,希望能从统治中获得爱戴与尊重”[8].汤姆生·卡莱尔在《过去与现在》中指出,新兴工业化社会阶层分化日益严重,雇主与工人之间蜕变成赤裸裸的金钱与劳动力的交易,缺乏必要的“爱”与“忠诚”等宝贵的情感因素,他呼吁人们向中世纪农业社会中的领主与附庸之间的相处模式学习,而这些正是骑士精神的重要内容.
骑士精神也带有明显的“跨民族性”.由于它在发展历程中汲取了条顿人、萨克逊人、诺曼人等多民族文化精髓,本身就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更准确地说,骑士精神是一个集合了各民族特征的带有各历史时期文化烙印的复杂精神产物与行为规范,其源头可追溯到条顿骑兵.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详细记载了条顿骑兵的组织、训练与作战制度,他们没有任何道德观念,挥霍无度,烧杀抢掠,将一切都诉诸于武力,这一阶段的骑士可称为“野蛮的骑士”或“具有尚武精神的骑士”.11到12世纪,由日耳曼人尚武传统结合封建家臣制与基督教精神的骑士制度初显端倪,教会试图用基督教精神来驯化好斗而残暴的骑士,告诫他们要忠于主人、上帝与教会,学会保护弱者与穷人,圣殿骑士团是这个阶段骑士精神的典型代表.诺曼人后期对宫廷文化的培育造就了“浪漫的骑士”,封建君主与贵族赞助的诗人学者们塑造了新的理想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给骑士精神增添了优雅的风度礼节和向女士献殷勤等社交技巧.19世纪,冷兵器时代的骑士精神在英国通过本土化、现代化与世俗化方式,以道德理想与行为准则的形式保留下来,发展为城市贵族乡绅精神、基督徒精神与现代绅士精神.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演变,骑士精神原初的内涵与界限已模糊不清,但作为一种传统,有助于建构国民对国家的统一认同感与身份归属感,具有消弭民族差异观念、加强民族团结的功能.
三、《艾凡赫》的骑士精神对阶级矛盾的消解
《艾凡赫》虽以中世纪萨克逊人与诺曼人的民族矛盾为主,而阶级矛盾也是其重要主题,这在小说开头最先出场的两个人物葛尔兹与汪巴的项圈刻字可见一斑.两行字分别是“别乌尔夫之子、葛尔兹,出生后即为罗泽伍德的塞德里克氏家奴”与“傻瓜之子、汪巴,罗泽伍德的塞德里克氏家奴”[9]6.两人对主人塞德里克忠心耿耿,但一直因下等人身份感到沮丧,梦想有一天成为“自由人”.正如小说所称,一个英格兰人心目中最宝贵的东西便是“他们的独立自由”[9]2.那么,自由要通过何种手段来获取与实现?
小说提供了两种模式.艾凡赫的父亲塞德利克一直希望以暴力手段推翻诺曼王朝的统治,把“我们祖先根据自由和独立的权利占有的产业”夺回来.在与约翰亲王的对话中,他道出了与儿子艾凡赫决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艾凡赫接受了理查赐予他的领地,甘愿降为人家的臣仆[9]132.在抗争中,他表现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壮志豪情:“像我和尊贵的阿尔则斯坦这样两个撒克逊人,在我们祖先留传下来的基业上占有一块土地,难道是过分的吗?把我们杀掉好了,你们开头是夺去了我们的自由,索性让你们残暴到底,连我们的生命也夺去吧.”[9]185不过,小说结尾还是见证了塞德利克的妥协:他和儿子达成和解,默许儿子对理查的效忠,他本人“不止一次地咨嗟叹息,不愿接受召命,但最后还是归顺了”[9]455.塞德利克的反抗不完全基于民族矛盾,更多还是阶级矛盾.司各特称,亥斯丁斯战役之后,政权为诺曼贵族所掌控,所有的撒克逊亲王与贵族不是被赶尽杀绝就是被剥夺了继承权,剩下的少数能够保有祖产的人,不过是次一等级或更低阶层的小业主罢了[9]2.塞德利克复国计划的破产,意味着下层阶级通过暴力方式获取自由的方案行不通.
另一模式以小丑汪巴与猪倌葛尔兹为代表.两人是最底层的农奴,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摆脱农奴身份,“带上自由人的腰刀和盾牌……用不着隐藏我的脸和我的姓名了”[9]99.当主人塞德利克遭到伪装成绿林好汉的诺曼人伏击被俘时,两人侥幸逃脱获得自由,但心里十分矛盾:“这勇敢的小丑在安全逃脱以后,又再三思量:是否应该转身回去,和他衷心爱戴的主人一块儿当俘虏?……常听人说自由是多么幸福;我现在是得到自由了,可是我倒希望有个聪明人指点我一下,我拿它做什么用呢?”[9]171这段内心独白显示了农奴对主人的忠心,也道出了他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农奴在以土地为唯一财富来源的封建社会,对主人有相当程度的依赖,一旦离开主人就无法自力更生,人身自由没有现实意义.这符合中世纪的普遍观念,附庸自身缺乏保护自己的能力,因而并不需要过多的自由,只有在领主保护之下才能更好地生存.
作为社会底层的农奴,若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找到“社会向上流动性”的途径与空间,通过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来实现.两位农奴后来不惜以生命换取主人塞德利克的平安,其忠诚与爱使塞德利克感动万分.这位执拗的老人曾因亲生儿子与自己意愿相悖而剥夺其继承权,但面对忠心耿耿的农奴却感动了,将“洼白鲁格汉姆田庄分给你百十亩地……由你永久执业”[9]306.如此一来,农奴拥有了生产资料,就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现在不再是农奴了,而是一个自由人,一个土地执业者”[9]306.这使农奴感激涕零,对主人更加忠心不二.葛尔兹说:“您的赏赐已经使我气力增长了一倍,我以后就加倍替您出力打仗.我觉得我的胸腔里头有一股子自由精神.我这人已经变啦!对我自己,对别人,我都变啦!”[9]307葛尔兹所说的变化,不只是个人精神状态与气质的变化,更是社会地位的提升.司各特讲述的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构想,试图说服社会底层的人们:依靠对雇主的忠诚与辛勤劳动,有可能跨越阶级界限,上升到更高的阶层,彻底改变自己在“人类食物链”中的下游位置.
综上,对于阶级矛盾,司各特提出了两种解决方式:一是暴力方式;二是通过充分的信任和忠诚而获得领主的恩泽,实现自身地位的上升.显然,司各特并不赞同前者,而是对后者表现了更大的兴趣.这一倾向背后有着司各特深刻的思想根源.
针对彼得卢广场大屠杀,司各特曾以“梦预言诗”的形式撰写了三篇文章,收在小册子《幻想》(The Visionary)中.司各特说:“希望它可以对当前这场特殊的危机有所帮助.”[9]3第一篇文章驳斥发表在1819年11月13日《苏格兰人》上的一篇号召所有反对派团结起来推翻政府的社论.第二篇文章谴责“财产平等分配的疯狂想法”,认为这一旦成为现实,将给社会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而且“对穷人造成的伤害要数百倍于对富人的伤害”[9]11.第三篇文章对“激进改革与普选权”报以“讽刺与嘲笑”,认为公民普选权的扩大只会导致“变化无常、没有头脑、残暴成性的一群暴徒”[9]14的出现,认为那些“自由的古国”的某些做法值得借鉴,因为在那时“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是奴隶.他们不仅没有选举权,甚至他们本人都只是主人的货物与财产罢了”[9]13.
在司各特这种近似冷血的政治立场背后,隐藏着他对可能爆发的革命深深的担忧.在写给好友约翰·理查森的一封信里,在谈到彼得卢广场大屠杀时,他说:“我并不十分害怕这些家伙.然而,我也回想起了1793年和1794年所发生的事情,那些更令人恐惧的人们(由农民、商铺店主等组成)有着同样的想法.一群由暴民所组成的乌合之众永远就像是在干柴上所点燃的一把烈火.”[10]司各特所指的是法国大革命1793-1794年间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由于施行高压手段与独裁统治,雅各宾派很快失去了城乡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和下层人民群众的支持.缺少了群众基础的雅各宾派摇摇欲坠,接着发生的“热月政变”彻底终结了其短暂的统治.在司各特看来,对当时的英国而言,阶级矛盾是国家所面对最突出、最严峻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社会分裂将日益严重,英国很可能会重蹈法国的覆辙,被激进、血腥、可怖的革命所推翻.就政治立场而言,通常学术界对司各特的评价是典型的托利党中的保皇党人,他坚守传统,反对革命,支持王权.从这一角度说,司各特是埃德蒙·伯克政治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后者强调忠诚君主的重要性,认为推翻君主制会带来无秩序的混乱局面.作为保守党成员,司各特认为社会阶层的存在作为社会的客观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进行调和.
在法国席卷各地的革命浪潮中,独具慧眼的司各特发现了一处与众不同之地,那就是法国的旺代地区.1793年8月,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内忧外患,对外要应对欧洲君主国的联合进攻,对内是旺代等地区爆发的大规模叛乱.叛乱队伍主要由当地农民组成,战斗时他们头戴象征王室家族的白色帽徽,高喊“国王万岁”.对这次叛乱的原因,历史学家众说纷纭,但在某一点上取得了共识,即旺代的农民与当地贵族之间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亲密关系,因而农民才会听从贵族的指挥与号召发动叛乱.司各特作为出版商,曾出版过一本鲜为人知的小书《罗彻佳裘蕾恩夫人回忆录》,此书原文为法语,体裁为自传体,于1827年作为译著在英国发行.故事主人公罗彻佳裘蕾恩夫人是路易十六的亲属,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逃到旺代,嫁给了当地保皇党领袖之一的兄弟.这本书根据她的亲身经历写成,记录了对当时血腥战争的恐惧与反思,以及对动荡政局的担忧与不安.司各特为该书作序,谈到了对旺代地区叛乱的看法,他认为,当社会有高下之分的两个阶层之间出现“不团结”时,就很容易爆发下层阶级针对上层阶级的革命.在法国大部分地区,本该是保卫贵族权益的佃户,在革命中反而成了其最可怕的敌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旺代地区却是个例外,两个阶层相处极为和谐.这种和谐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司各特认为,除了宗教信仰与非强制兵役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两个阶层的人群都能尽职尽责地履行各自的社会责任,旺代的贵族非常爱护追随他们的人们,旺代的农民也对贵族极为忠诚,这是构成两者和谐的根本.可惜,司各特感慨地说:“这种品德专属于遥远的古代,却与现代无缘.”[11]
司各特并没有明确阐释他所指的这种专属于遥远古代的珍贵品质为何物.但在1819年写给好友的一封信中,他对英格兰动荡不安的局面大加批评,认为苏格兰的阶级矛盾就要缓和很多.究其原因,他提到了两个差距悬殊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苏格兰的地主(包括他本人)与当地农民之间是一种“父子关系”[12].他的这一观点与高德纳、汤姆生、卡莱尔等历史学家关于“骑士精神”与“父权主义”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思想核心是着重强调社会中被统治群体与统治群体彼此之间的义务与责任,并用家庭伦理中的父子关系作为家国同构的隐喻,来加强这种义务与责任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艾凡赫》这部小说中的骑士精神,就蕴含了卡莱尔等人“爱、忠诚”等情感价值与基于责任与义务的社会契约内容,与司各特的思想暗合,表达了反对通过极端形式进行社会变革的态度,主张下层阶级通过遵循该模式下的原则来实现“阶级向上流动性”,作为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冲突的手段.在《艾凡赫》中,除了旺巴与葛尔兹以外,小说中的绿林好汉罗宾汉向理查归降,也是以与史实不符的理想化骑士精神来消弭阶级矛盾的绝好实例.
四、《艾凡赫》的骑士精神对民族矛盾的消解
在小说开端,司各特开宗明义点出作品的宏观背景:“虽然经过了四个时代,诺曼和盎格鲁·撒克逊这两个敌对民族的血统还没有融合起来……一个民族依然因胜利而意气扬扬,另一民族则呻吟于败亡后的灾患之中.”[9]2同一国家内两个民族之间势同水火的矛盾,导致双方彼此不认可,因此引发了“谁才是真正的英国人”这一论题.
在《艾凡赫》第二版中,针对人们对其创作动机的种种猜测,司各特在序言中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这是一次有意而为之的尝试,意图探索新的领域,在‘纯英国’(purely English)主题上的一次实验.”[13]司各特的这一答案耐人寻味,蕴含着强烈的文本实验色彩以及民族观照意味.事实上,有关“英国性”(Englishness)的讨论在19世纪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马里恩·舍伍德(Marion Sherwood)指出:“‘英国性’是19世纪时产生的专有名词,也是那个年代值得持续关注的一个话题.”[14]克里尚·库马尔(Krishan Kumar)认为,19世纪时,英国经历了“对英国性的探索”(discovery of Englishness)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15].这种强烈的“英国性”意识,一方面是对外的,马克·奇塔姆(Mark Cheetham)说:“英国的艺术家与作家会将法国与德国作为他们创作灵感的来源.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标榜自身的‘英国性’要远比他们优越.”[16]这一观点为安洁莉亚·鹏(Angelia Poon)所认同,她说:“19世纪的英国文学,从最初在塑造国家精神以缓解民族冲突与团结国家上就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与日趋强大的‘英国性’所蕴含的文化力量有着明显的关联.”[17]“英国性”的另一方面则是英国内部有关各民族的辩论,对多数人来说,英语中的British与English这两个词是可以互通的.而司各特对English这个词特别强调,显示了他清醒认识到大不列颠帝国各组成部分之间尚存在着泾渭分明的民族差别.这印证了杰拉尔德·纽曼(Gerald Newman)《英国民族主义的兴起:1740-1830的文化史》中的说法:“‘英国性’这个词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强烈的、轮廓分明的民族主义的意识.”[18]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进一步将滑铁卢战役之后到维多利亚时期之前的这段时期称为“民族主义的高涨期”(the era of high nationalism).
事实上,“民族主义”是司各特小说中的一个常青主题.在他创作的苏格兰主题系列小说中,苏格兰人的国家身份问题(Scottish identity)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在《艾凡赫》中,他追溯了中世纪盎格鲁萨克逊人与诺曼人之间的冲突,指出“虽然没有像战争或起义之类的重大历史事件标志出他们是另一个民族,可是他们和他们的征服者之间的巨大的民族差别……使胜利的诺曼人的子孙和败亡的撒克逊人的后裔之间,始终保持着一条分界线”[9]4,从而凸显了对英国国家身份问题的挖掘与探求.在《艾凡赫》的诸多英雄人物中,最能够全面充分代表英国国家身份特征的,当属英格兰国王狮心理查.首先,他对自己的国家身份十分在意.当塞德利克得知理查的真实身份时,曾惊愕地叫道“安茹的理查呀”(Richard of Anjou).而理查纠正他说,这个说法不准确,他是“英格兰的理查”(Richard of England).其次,他对解决英格兰内部的民族矛盾非常关注.针对撒克逊人与诺曼人之间的冲突,他声称“我关心在我的忠实人民之中消除一切隔阂”[9]429.
威廉·布卢姆(William Bloom)认为,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度与认同感在两种情况下会被激发出来:一种是众志成城对抗外来威胁势力的时候;还有一种是国家以民生为本处处为民谋福利的时候[19].理查率军发起的十字军东征正是为对抗伊斯兰对欧洲的威胁而战,他本人仗义疏财,心系民心,处处为国民利益着想,是个公认的好国王.他说:“还有谁比我更热爱英格兰、更热爱每个英吉利人的生命?”因此,连他那图谋不轨、意图篡权的弟弟约翰亲王也不得不承认理查是众望所归的真正国王.然而,小说中却唯有一个人对理查的王权合法性提出了质疑,那就是撒克逊的贵族塞德利克.在与理查一次面对面的交谈中,他指出,理查的母亲玛蒂尔达原本是苏格兰麦柯姆王的公主,并不是英格兰王朝的合法继承人,而具有纯正撒克逊王族血统的阿泽尔斯坦才应该是英格兰的真命天子.因此,塞德利克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促成具有撒克逊贵族血统的养女与萨克逊族唯一皇裔阿泽尔斯坦的联姻,进而完成萨克逊人的复国大业.
塞得利克的“血统论”在19世纪相当流行.英国政府一直在为对外扩张的殖民行为寻求合法性论证,“高贵的白种欧洲人”这一带有强烈种族优越感的说法为英国人侵略其他种族提供合法性.而在这所谓最为高贵的人群之中,又数撒克逊族最为尊贵,其地位的确立可以追溯到17世纪.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法学家爱德华·寇克(Sir Edward Coke)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历史上的撒克逊时期是一个“黄金时代”,那时的英格兰安居乐业,为强大而有秩序的法律所保护,并有各类代表机构来保证社会的民主与自由.这一观点在光荣革命之后为辉格党人所津津乐道.他们认为,那曾经的伟大时代在诺曼征服中被彻底毁掉了,但英国人民血液中所流淌的热爱自由与独立的撒克逊人精神从未丢掉,他们也从未放弃找寻那个失落时代的努力.英国历史上的几桩重大事件,如宪章运动与推翻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等便是明证.这一血统论背后隐藏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它过分强调甚至夸大撒克逊人在历史上对英国国民性的塑造,同时否定诺曼人对英国民族性建构的贡献.更为严重的是,这一论调使得撒克逊文化与诺曼文化形成势不两立的对峙局面.19世纪初出版的众多历史著作都涉及这一话题,如莎伦·特纳(Sharon Turner)的《盎格鲁萨克逊族之历史(1799-1805)》(History of the Anglo-Saxons:1799-1805)、奥古斯丁·蒂埃里(Augustin Thierry)的《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England by the Normans)都过多地渲染英国民族性中“为自由而反抗”的撒克逊人英雄传统.而诺曼人则被塑造成暴虐、贪婪、丑陋的外族人.正如19世纪初的一首歌谣中唱到的那样:
英国人(Englishman)生来自由;
虽然他们的臂膀被你的铁链束缚,
他们自由的思想依旧汹涌澎湃,
在胸膛中奔流不息。
诺曼人,无论你做了什么,
永远都不会摧毁英国人![20]
显然,诺曼人已经从“英国人”范畴中被剥离出去.这种割裂的意识在《艾凡赫》中也随处可见,绿林好汉罗宾汉在称呼撒克逊人与诺曼人时,总是习惯性使用“我们英吉利人”与“外族人”这样的称谓;甚至小说的叙事者在描写比武大会场景时也采用了这样的说法:“许多骑士,其中有英格兰人,也有诺曼人,有本地人,也有外来的人.”[9]111
理查敏锐地感觉到了两个民族间的隔阂,以及他自身诺曼人的身份有可能招致的质疑.为了化解这一矛盾,他采取的策略是以“父亲”自居.小说中多次出现过以下说法:“我的国家和我的子民中,最优秀的分子都与我一样爱冒险”[9]151;“这次得把机会让给我,瞧理查如何为他的子民作战”[9]152;“我最热忱的愿望,就是看到英格兰的儿子们互相团结起来”[9]428.理查作为一位强大而仁慈的父亲的形象跃然纸上.贵为一国之君,理查自称“父亲”,表面上看可以起到放弃自己的高贵身份、拉近与人民距离的作用.但从深层次讲,这一“父亲”形象具有偷梁换柱的欺骗性.在家庭中,父亲与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毋庸置疑,这一关系也是父亲的家长权利的合法性基础.而在国家这一更大的“家庭”中,倘若国民将国君认作父亲,下意识中他们会产生与之血脉相连的错觉,从而产生极强的依附感与认同感.因此,理查的“父亲”身份会让撒克逊人忽略甚至忘记他的诺曼人身份,不再去质疑他的血统,进而全心全意追随他并为其效忠.这种基于“父权”的忠诚,与“骑士精神”有着逻辑与内容上的密切关联,其本质也是骑士精神的一种体现.
在小说中,“父亲”的形象不止理查一人.艾凡赫的父亲塞得利克、蕊贝卡的父亲艾沙克,都与理查形成了鲜明对比.塞得利克脾气暴戾,举止粗鲁,不谙礼节,粗暴地剥夺了儿子的继承权,父子矛盾激烈,最终在理查的规劝下才和解,是“蛮横父亲”的典型.艾沙克作为犹太人,行事谨慎,对女儿没有掌控力,无法履行监护人职责,导致女儿数次遇险,落入敌方手中,是“软弱父亲”的典型.由此可见,血缘关系是父权的基础,但权威的树立仅靠血缘关系是不牢固的.理查通过“父亲”形象的塑造解决了血统的合法性问题,还要靠强大的力量和高尚的品德来赢得民心,这种力量与品德的集中体现,同样要依靠他身上广为人们称颂的骑士精神.
狮心王理查受到各民族拥戴,是因为他是一位公认的真正的骑士,他所展现出来的骑士精神综合了撒克逊人与诺曼人的宝贵品质,是两者融合的完美化身.骑士精神的内容错综复杂,但总体原则如勇敢、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信奉基督教、保护女性弱者等,总是能够得到人们的公认.按以上标准,小说中唯一符合真正骑士标准的就只有理查一人.他神勇无比,在比武大会上凭借一己之力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最棘手的几个圣殿骑士;他也是基督教的忠实教徒,亲自发动了史上有名的十字军东征;他虽贵为国王,却愿意亲身涉险率领众人深入虎穴去拯救弱女子罗文娜与蕊贝卡.
反观小说中其他的几位主要骑士,离骑士精神的标准均有差距.圣殿骑士波阿-基尔勃狂热追求异教徒女子蕊贝卡,违反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与禁欲精神;艾凡赫虽智勇双全且忠心耿耿,但他也是一个为实现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为了得到比武大会所需装备而接受了犹太人的借款,猪倌葛尔兹批评他,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合基督教义的[9]93,却被艾凡赫斥责为“死心眼的奴才”[9]93.塞得利克虽然骁勇善战,但却缺乏基本的礼仪知识,在诺曼人的宴席上举止粗鲁,大出洋相.阿泽尔斯坦虽有撒克逊人的贵族血统,对女性彬彬有礼,却又贪生怕死,好逸恶劳,缺乏阳刚之气.
司各特付出的努力是在特定的历史片段中重新挖掘国家身份认同的不同层面,通过共有的民族历史记忆,找到一个合适的代表性事物,将这种认同整合并统一起来,在小说《艾凡赫》中集中体现为骑士精神.这种统一与整合的结果证明,双方只有互相取长补短,彼此借鉴学习,才能建构起真正的、狮心王理查所代表的“英国性”.正如司各特在小说结尾说的那样:从那以后,诺曼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倨傲,撒克逊人也比以前文雅得多[9]457.
五、《艾凡赫》之于“国族同构”的现实启示
曾经担任过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曾公开表示,《艾凡赫》是他最喜爱的一本书.迈克尔·亚历山大(Michael Alexander)就此评论道,就其首相身份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去喜欢这个主题为相互理解、接受与包容的现代寓言”[21].安妮卡·宝茨(Annika Bautz)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她认为司各特在《艾凡赫》中流露出了一种基于“妥协(compromise),而非对抗(antagonism)”的总体态度,以此解决英国现实中种种矛盾冲突.
《艾凡赫》中书写的骑士精神,本身作为一个集合了各民族特征的、带有各个历史时期鲜明文化烙印的复杂精神产物与行为规范,典型地体现了“理解、接受、包容与妥协”等原则.从最初野蛮的条顿骑兵、禁欲的基督教圣殿骑士、浪漫的法国骑士一直发展到现代绅士,骑士精神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于各个时期的英国人民身上,并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显现出跨阶级与跨民族的特征,体现出修复性、弥合性的重要功能,从而成为团结各阶级与各民族的良好粘合剂,进而建立一个在现代社会各阶级与各民族之间有序、稳定、和谐的相处模式,有助于国民对国家形成统一的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认识到骑士精神的这一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无论是最近发生的引起全球关注的苏格兰公投独立事件,还是历史上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法国的科西嘉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俄罗斯的乌克兰问题,都是尖锐的民族矛盾冲突的典型例子.在这些独立意识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西方民族理论的核心“一国一族论”.由于历史上大不列颠、法兰西、德意志等欧洲国家的“近代民族”是在资产阶级国家统一过程中形成的,实现了国家与民族的同步发展,互为表里的统一,于是“一国一族论”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民族自决论”在二战后得到了美国与前苏联的极力吹捧,并赋予了它国际基本法的地位,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削弱英法这样的传统殖民帝国.然而,这一貌似充满善意,秉承着正义原则的论调,在现代却往往暴露出了分裂主义的倾向,被打着人权、民族自决旗号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利用,造成了破坏多民族国家地域及文化完整性的严重后果.
作为对以上极端思想的反拨,我们应该认识到,作为统治者工具的“国”与作为共同体的“族”之间确实有着对立的一面,但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建构作用也不可忽视.在如何妥善处理这两者关系方面,司各特在小说《艾凡赫》中以骑士精神为例树立起了“求同存异”的典范,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与现实意义.
[1]文美惠.司各特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209.
[2]Alexander Norman Jeffares.Scott's Mind and Art[M].New York:Barnes&Noble,1970:46.
[3]Walter Scott.The Novels,Tales and Romances of the Author of Waverley[M].Boston:Samuel H.Parker:ix.
[4]范荣.林译小说——“以中化西”的文化坚守[J].外国语文,2013(2):132-137.
[5]霍特.卡斯尔雷的对欧政策:1812-1822[M].孙克强,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36.
[6]伊恩·罗伯逊.社会学[M].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313.
[7]Rosemary Gartner.The Oxford Handbook of Gender,Sex,and Crim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552.
[8]John Rule.Albion's People:English Society 1714-1815[M].New York:Routledge,2014:48.
[9]司各特.艾凡赫[M].刘尊棋,章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0]Ian Duncan.Scott's Shadow:The Novel in Romantic Edinburgh[M].New York: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31.
[11]Walter Scott.The Complete Works of Sir Walter Scott[M].London:Conner&Cooke,1833:318.
[12]La Rochejaquelein.Memoirs of the Marchioness DE LA ROCHEJAQUELEIN[M].Edinburgh:Ulan Press,2012:8.
[13]Andrew Lincoln.Walter Scott and Modernity[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68.
[14]Chris Worth,“Ivanhoe and the Making of Britain”[J].Links&Letters,1995,1(2):63-76.
[15]Marion Sherwood.Tennyson and the Fabrication of Englishness[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2:2.
[16]Krishan Kumar.The Making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202.
[17]Mark Arthur Cheetham.Art writing,Nation,and Cosmopolitanism in Britain:The‘Englishness'of English Art Theory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M].London:Ashgate Publishing,Ltd.,2012:16.
[18]Gerald Newman.The Rise of English Nationalism:A Cultural History,1740-1830[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97:52.
[19]Joseph A.Leo Lemay,Carla Mulford,David S.Shields.Finding Colonial Americas:Essays Honoring J.A.Leo Lemay[M].New Yo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2001:420.
[20]Holger Hoock.Empires of the Imagination:Politics,War,and the Arts in the British World,1750-1850[M].London:Profile Books,2010:17.
[21]Michael Alexander.Medievalism:The Middle Ages in Modern England[M].New York: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43-44.
责任编辑 韩云波
I561.074
A
1673-9841(2015)05-0128-09
10.13718/j.cnki.xdsk.2015.05.018
2015-03-12
陈彦旭,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国历险小说与民族身份建构研究”(14BWW070),项目负责人:陈兵;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3-0269),项目负责人:陈兵;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转型期的英国历险小说研究”(13WWA001),项目负责人: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