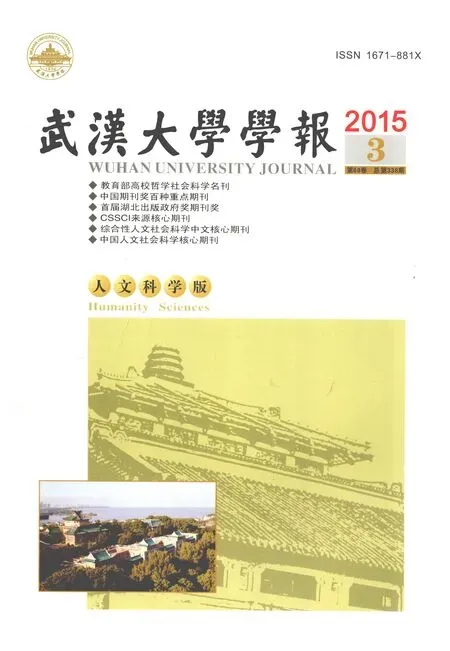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文学中的“美国形象”
孙 霞 陈国恩
20世纪8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文学中的“美国形象”
孙霞陈国恩
摘要:20世纪80年代大陆留美学生笔下的美国,是一代青年带着历史阴影的“负重”心理与试图寻找新的梦想的“超越”心境下的创作,总体上表现出“梦幻之城”和“彼岸世界”的特点。梦幻的理想化特征和彼岸的脱离实际的性质,在反映出美国社会面貌的同时,也折射了特定时期中国人的美国观。其中的欣喜与误会,是改革开放之初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人在认识西方发达国家时的一种富有时代感的社会心态的反映。
关键词:1980年代; 留美学生文学; 美国形象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从那时起至今的30年时间,这些旅美者中有些人在异域文化与生活经历的刺激下,开始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形成了我们所谓的美国新移民文学。而80年代走出国门的第一批留美者,大多经历了“文革”,心中盘桓着极左年代的各种恐怖景象,又从父辈口中听说过困难年代的生活艰辛,或者身受了这种苦难,因而他们基本上是怀着梦想远去美国的。当从事文学创作时,他们对美国的最初印象就溶入笔端。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这种带有作者强烈主观感情的美国书写,在今天有了文化史的意义。相较90年代后的中国旅美者,改革开放初期的留美学生,中国新一代的精英人物,他们当时是怎样看待美国的,他们又怀着怎样的心情远走美国,到美国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种种问题折射出了特定时期中国人的美国观,让今天的我们可以从这些留学生笔下的美国形象中看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在认识西方发达国家时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心态,因而又能更好地认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和中国发展的不平凡历程。
一、 负重与超越:“美国”书写的心理基础
20世纪80年代的留美作家,是背负着“文革”历史阴影与国家民族落后的重压留学美国的。他们的心理,是一种典型的游子心态。
首先是负重的心态。很有意思,这些留美作者在不同场合多言及“包袱”、“负重”、“压力”、“痛苦”。显然,这些词汇集中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作者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以苏炜为例,他是留美作家中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一位,作品常常充满忧国忧民的情调,民族主义色彩也很重。他曾将自己的写作概括为“过去情结”或“中国情节”*查建英:《边缘人的通信》,载《小说界》1988年5期,第132页。。对苏炜这一代理想主义者来说,目睹了发达的美国以及个性张扬的美国人,很容易激起他们悼过往、忧今日的爱国情感。他们的创作,如苏炜所说,就是留学生文学中的“伤痕文学”,因而说教味比较重。不过,正是这种比较直观的说教透露了苏炜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字里行间尽是对过去历史阴霾的愤恨以及对祖国深沉的爱。如苏炜作品《杨·弗兰克》中的旅美者杨蔼伦想忘记“过去”又止不住回忆,想切断与“中国”的情感,又“天天晚上做咱们中国人的梦”。
苏炜称查建英等更年轻一代留美作家的作品基本不存在“过去情结”,认为他们那种“过去”与其说是包袱,不如说是怀想与憧憬*苏炜、陈建功:《小楂及其他》,载《文汇》1989年2期,第59页。。确实,相对苏炜这代“老三届”而言,查建英这代人的“过去情结”没有那么浓烈,而查建英也强调了个体意识的重要性,认为过于沉重的群体思维具有狭隘性且是一种自我折磨。她的自传式小说《丛林下的冰河》写到“我”怀着飞的愿望来到美国,可回国后又忍受不了落后压抑的现实。与祖国紧紧相联的“过去”,承载着作者远离祖国时的矛盾心理:既是重负又是情感的寄托。
再说“超越”心理。其实,当作者大呼“累”的时候,就已经蕴含了想要摆脱这种状态的希求。人最可怕的是麻木,一旦觉醒了,翻身奴隶都可以做主人,何况是这些身处“自由异邦”的知识精英?于是,透过层层“负重”的迷障,便可看到一个个鲜活的跃跃欲试的灵魂:他们希望超越过去,重新树立作为个体“人”的存在价值与尊严。如果说“负重”是作者心理一极的话,那么摆脱过去阴霾、追求理想人生,则是作者心理的另一极。有心灵“负重”,才有“超越”的动力。
作为新时期第一批留美学生,在他们要走出去时,就已隐含了想要超越过去的愿望。与90年代以后那些迈出国门者相比(后者往往怀抱着一种更切实的目标,或者是为“掘金”,或者是为“求知”),80年代的留美学子因为多了一重精神上的负累,他们的出国梦还包括希望获得精神上的解脱与救赎,因此更具超脱意味。苏炜曾说,他们是被“驱逐”的*苏炜、陈建功:《小楂及其他》,第59页。。不管是被未来所诱惑,还是被“过去”所驱逐,其实都是积极的自我拯救,是企图与过往告别。可当置身于“自由”与“民主”的美国时,由于切身感受到了中美经济的巨大差距以及两种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差异,这些刚从贫困的岁月中走出来的年轻学子所受到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
对查建英等“更年轻的一代”来说,比较容易摆脱“重负”。查建英虽曾“不甚恰当”地将留学美国比喻为乡村姑娘进城,但也道出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心声:明知道有了选择的自由不见得必然会得到理想的选择,只不过他们还是要这个自由*查建英:《边缘人的通信》,载《小说界》1988年5期,第132页。。因而,当这些留美学子书写其内心感受时,就会在小说中刻画虽“负重”而又不忘奋力前行的形象。为了在美国开始新的人生,斩断与故国一切联系的伍珍,哪怕是以婚姻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查建英:《到美国去,到美国去》)。这种强者形象,与90年代旅美文学作品所讲述的在异域求生存和发展的故事有类似之处,但两者毕竟不同。如陈雪丹在90年代初期所创作的短篇《美霓》,讲述求学上进、感情真挚的女主角美霓,因利益的驱动,不惜以婚姻为代价,最后成为敛财的“机器”。然而,陈雪丹视美霓的转变为金钱的驱动,是消极被动的;而查建英强调,伍珍对婚姻的处理是缘于她希望摆脱如影相随的过去,是积极主动的。
“理想主义者、民族主义情结很重”的苏炜,是否会因为一味沉湎过去而无力实现“超越”呢?答案是否定的。苏炜的中国“包袱”固然沉重,可是对“过去”的“回首”并没有使他沉溺于其中而不可自拔*《留学生座谈纪要》,载《小说界》1989年1期,第182页。。因为过去也许还占有一席之地,但它的终极是面向当下与未来的。而且相对于更年轻一代的作家来说,他们所受“文革”或中国文化的影响虽然很深,但在“文革”期间他们毕竟还是履历简单的年轻一辈,身心不至于遭受毁灭性的伤害。因此,一旦时代翻开新的一页,他们就如被碾轧过的草苗,在春风的吹拂下,绝大部分又能重新站立并成长起来。
超越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超越的实现。“过去”并不是遥远的过去,而且身受中国文化的滋养,要想不受其影响也不可能。这种为了展开新生活须有所放弃却又有所保留的心态,为大部分留美作家所共有。留美作家于仁秋等人在讨论如何处理民族情感与追求未来生活的关系时提出,不妨通过健康的个人主义来升华深沉的民族情感。这样的思考,无疑有价值。
二、 理想与虚无:留美学子构想的“云中城”
《云中城》是20世纪80年代留美的常罡所创作的一部小说,写出了留美学生在承载“过去”重负而又试图超越自我时心中那个美国集理想与虚无为一体的特点。近百年旅美文学不乏对美国的赞美与羡慕,却很少如此阶段作品能集中地表达对美国的向往。“梦”、“梦境”或与此有关的词语在作品中不断出现*如《纽约的白日梦》《梦》《梦,献给我的友人》《云中城》等小说,标题就与梦有关。,就隐含了这一时代特点。从贫穷中国走出的青年,赴美留学犹如查建英所比喻的,是乡下姑娘“进城”,美国是他们眼中的“云中城”。这一“城市”形象,就是由初入异域的新奇感、怀抱梦想的充实感以及梦想破灭后的虚无感所构建起来的异域形象。
先说新奇感。作为“云中城”美国形象的建构,首先基于学子们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新奇感。艾丹80年代留美时所创作的纪实小说《纽约札记》,在文学界的影响力虽不甚高,却较为典型地反映了一位初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感受。小说以留学生“我”的视角,写他所看到的纽约“仿佛是梦中的城市,仿佛是海市蜃楼”:一个穿着用星条旗做短裤的黑人,一个在自家窗口摆着巨大的野羊头骨的老头……。作者采取限定视角,将纽约稀松平常的街景文学化,从而带来了奇幻戏谑的效果。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在将美国描述成为一个梦幻帝国的同时,也涉及到了美国物欲、肮脏等丑陋的一面,就如90年代初中期旅美小说所反复书写的——如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对美国社会唯利是图的批判。但我们从后者中感受更多的是丑陋,而不是新鲜和奇异。美国观的差异是因为80年代作品较少涉及人物生存的艰难,更主要的是以初来乍到者猎奇的笔触写他们所看到的美国,因此,一旦“新奇”压过“生存”主题,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丑陋”美国,便是“景观”,而不是所生活的现实。当然,“新奇”感的产生,从根底上说,缘于初入异域的作者自身对美国的认识与感受。由于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过于短暂,他们呈现给读者的往往是那些令他们觉得新奇的东西。此外,作为学生,他们还未能完全体会到美国社会由于激烈的生存竞争所带来的残酷。
再说美国是梦想的承载者。“新奇”并非构成“云中城”的核心因素,而只是其基础,核心因子应该是梦想的承载者。因为只有寄托了希望和梦想,才符合可以给人带来美好感受的“云中城”的要义。1980年代留美文学所构建的美国,便是留美学子心中的一个“梦想的寄托地”。
这些留美的游子,怀着各自的梦想,期待一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的人生。有些人去美国只是为了逃避国内了无声色的现状,希望能在美国实现他们成功之梦。如《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中的伍珍积极上进,可是满怀豪情壮志在国内却无用武之地。美国对她意味着荣耀、机会、见识。于是,她摆脱了无情趣的婚姻,扼杀腹中的胎儿,来到了美国。除了追求物质的满足,一些作品还涉及到追求事业梦想的主题。一些旅美者认为美国可以让他们发挥在国内难以施展的才华。如《云中城》中的王凡声言要在美国这块“民主与自由”的土地上实现他哲学家的梦想,要将那些在国内难以出版的哲学著述拿到美国来试试运气。
可以说,有很多作家都讲过“美国梦”,但作为一种群体性的现象,也许没有哪个时期的作家会如此集中地表达对美国的倾慕与褒扬,美国仿佛已成为他们的“诺亚方舟”。这也许与20世纪80年代的人刚从一个物质与精神极端匮乏的年代和国度乍然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有关,他们将自己的梦想无限地夸大,将一个新的世界无限美化。
三说美国是梦醒之地。美国毕竟不是“诺亚方舟”。这里虽然不乏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充分的个体自由,但物质财富并非唾手可得,个体的自由也包括“没有饭吃的自由”。于是,一些人逐渐意识到发财梦、事业梦、逃避梦等,毕竟只是梦想。梦想的难以实现、理想的不易坚守,美国对这些留美学子来说,又成了梦醒之地,一切皆是空幻。
当这些人满怀热情来到美国,期待施展自己才华、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却发现美国并非他们所预想的那样充满了机会和自由。《云中城》便是这样一篇梦醒美国的寓言之作。作品讲主人公王凡虽满怀憧憬来到美国,可在他的梦想还没有开始时就已破灭。而有时,那寥寥几位人生事业的成功者,如伍珍,几经挫折,看似实现了她的美国梦,但充溢其心的并非人生的圆满,而是由美国的实利主义以及人情淡薄所带来的情感空虚。伍珍的悲哀理应是众多理想失落者的悲哀,美国成为了他们理想的丧失之地。如同《丛林下的冰河》中的“我”怀着找找看的愿望飞到了美国,可是几年之后她却发现,找到的已不是她要找的,而在埋头找的时候,却与一长串宝贵的东西失之交臂。
其实,旅美作家对“梦醒之地”的美国形象的建构,是80年代留美学人自身处境映射下的产物:一方面与他们对美国寄予过大的期望因而产生心理落差有关;另一方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第一批留美学生,他们正处于人生事业的初创期,要想在美国立足并开始自己的事业并非易事,往往需要“7—10年左右”*程稀:《当代中国留学生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2页。的准备期。一道人生之旅的重新起航,理应不会这么容易,而一旦面临困难险阻,失望之情会油然而生。
在美国想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就像在悬崖上牵出钢丝,那头放一箱你最想要的宝藏,你得走过那条钢丝,才能拿到它。可那悬崖下有多少白骨啊!”*陈谦:《望断南飞雁》,载《人民文学》2009年12期,第25页。持这种看法的人大有人在,从留美伊始,一直延续到当下。既然如此,为什么“梦醒之地”是此阶段美国形象的主要特点呢?那是因为,既然是“梦醒”,那自然也因为有“梦幻”感。而90年代初中期的旅美小说所讲述的在美求学、求生存的艰难故事,其中生存的现实压力已超越了理想精神,因此,“梦醒”就不能贴切地反映作品“梦幻”的精神内涵。
作为“云中城”的美国,如果说新奇是其诱人之处,那么理想的寄托地则是它存在的核心,而梦想的幻灭就是它的真实图景,它终归会带来虚无和失落。
三、 放逐与乡愁:边缘人视阈下的“彼岸”
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留美学生来说,美国是空间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彼岸”,是“流放地”,具有与故土不同的文化语境,激起内心深处的疏离与隔膜是很自然的。留学生涯的短暂与不屑于“融入”美国*刘俊:《北美华文文学中两大作家群的比较研究》,载《比较文学》2007年2期,第100页。的姿态,又使这些作者对美国少了一份深入的了解,美国于是成了一个模糊的背景,往往是触发他们愁思与忧愤的媒介。
首先,美国是“流放地”。后殖民主义所理解的“流放”不仅指地域意义上的流放,也指由此所带来的文化和心灵的流放,这已成为众多寓居他国的人所共有的处境与感受。求学美国的游子在遭遇文化与生存困境时,同样感受到了这种文化与心灵的流放。在他们的眼中,美国就是“流放地”。
苏炜说他们这些人是被“驱逐”的。被驱逐的情形各不相同,但实质都是流放,美国就是他们自我流放之地。跨地域的流放不可避免地又会带来心灵和文化的流放,从而产生文化归属上的失落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困惑。这些人往往把自己看成是“边缘人”*查建英:《关于“边缘人”的通信》,第132页。,这种心理状态就反映在留美文学中。如《丛林下的冰河》中留学美国的“我”,是他人眼中的“阳光”、“天使”、“闲云野鹤”,而“理想”的失落与难以融入美国社会却给她带来了彻底的无归属感。《杨·弗兰克》中的杨蔼伦想摆脱与中国的一切联系,她找了位美国丈夫,俨然是真正的美国人了,可她同样没有归属感。她虽然不想回忆有太多伤心往事的中国,但中国又会时时在她的梦中出现。不过应该看到,一些作家在诉说流放的虚无时,本意并不在批判美国。比如,王凡和伍珍之所以“梦醒”美国,并不是因为美国社会的敌对和排斥,而是与他们自身有关。王凡来美后的失落是因为他对美国认识太肤浅,伍珍找工作时的屡屡碰壁则是个人工作能力问题。这种让人感到纠结的美国形象,显然与作者自身对美国的认识程度有关。这反映出这些留学美国的青年想超越以往的负重心理,当然也潜在地反映了中美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毕竟开始了和缓。在这样的背景和心态中,美国只是流放地,而没有成为敌对的“他者”。正因为如此,这种“流放地”的含义,已不太同于20世纪90年代作品所流露出来的情感。
其次,美国是触发“乡愁”的媒介。自古以来,羁旅情怀都是漂泊游子的普遍心态。已有论者指出,百年美华文文学,就是一个从“怀乡”到“望乡”的过程*李亚萍、饶芃子:《从“怀乡”到“望乡”:20世纪美国华文文学中故国情怀的变迁》,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期,第26~30页。,而反映于80年代的留美文学作品中,则更多是对往昔的追忆,对乡愁的渲染。只是这种乡愁,并非主体的抑郁之情浓得化不开而无法排解,如白先勇等台湾留美作家因为回归故国无望而落寞惆怅;也并非乡愁淡化而难以寻觅,一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留美作家,或奔命于生存问题而没有闲情吟咏,或因“日久他乡是故乡”而乡愁逐渐淡化。它往往是通过外界的诱发,激发出内心深处潜藏的愁思。于是,他乡明月、天涯芳草等等,不但没有给作品里的人物带来心灵慰藉,反而引发了他们更浓郁的思乡之情。富裕发达的异国他乡,不但没有让他们感受到物质生活富足带来的舒适,反而触发了对过去苦难的回忆、对贫穷祖国的担忧……
这些作品中,以苏炜的创作最为典型。《杨·弗兰克》中的杨蔼伦已经与美国人结婚了,可她还是不能忘怀中国与“过去”,而她的不能忘怀往往又是通过叙述美国在场而得以体现:她与弗兰克举行婚礼时,教堂的鸽子令她想起曾经灰色的婚姻;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使她回忆起往昔美好的恋爱;婚礼进场秩序使她想起与昔日恋人的反目为仇……大婚之日应是幸福和快乐的,杨蔼伦却在婚礼现场的刺激下情绪格外紧张,引起内心深深的自责与痛苦。这种悖论起因于作者自我内心情绪的矛盾。对此,苏炜曾将其归结为他们这些老三届留美后所背负的故国沉重的包袱*苏炜、陈建功:《小楂及其他》,第59页。。
其实,在查建英等更年轻一代的作家作品中,“美国”同样具有触发人的愁思的媒介作用。小说中触发式的联想,同样与作者自身心境的投影有关。查建英曾说他们不是完全为今天活着,也不是没有过去*《留学生文学座谈纪要》,第185页。。正因为他们也有“过去”,所以他们才有可能在外界的刺激下,引发对“过去”的回忆,美国在此时只是充当了这个触发的媒介。虽然心灵的“负重”与美国发达的现实触发了旅美者的“忧愁”,但即如前文所提到的,这种“忧愁”并非沉重得化不开: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已步入改革开放之路,正以昂扬的姿态开始新的征程;而作为时代的佼佼者,能“留学美国”又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他们这种并非愁苦潦倒的“忧愁”,确实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
四、 结语
文学是人类心声的表达。随着中美两国交往的扩大,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有力提升,中国人看待美国的态度和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留美学生文学创作中的美国形象已经与本文所述的20世纪80年代不同了,“美国”的神奇色彩开始减退,逐渐出现物欲化的“美国”,冷漠与孤独的“美国”,再进一步,则是陷于日常苦恼的“美国”,就像严歌岺的《无出路咖啡馆》中所书写的。留美作家笔下美国神奇色彩的消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开始以一种平视的态度看待美国,他们发现了美国式的问题。这中间明显地包含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理性批判精神,显示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在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时的从容和执著。换一个角度说,这代表了中国人参与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入和中国人社会心态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成熟。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后新移民文学作家看待美国心态的日渐成熟,80年代中国大陆留美文学中的美国形象由于是仰视美国的产物,似乎“简单”和“肤浅”。但我们又不能不说,这种“简单”和“肤浅”的美国观,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在经历长久的与外界隔绝后国人重新睁开眼睛看世界时审慎而又向往的矛盾心理。它好像一支青春序曲,带着天真和稚嫩,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民族正在告别封闭,以昂扬的姿态走向开放。
DOI:10.14086/j.cnki.wujhs.2015.03.0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1XZW036)
●作者地址:谢海林,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Email:xhl0926@163.com。
●责任编辑:何坤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