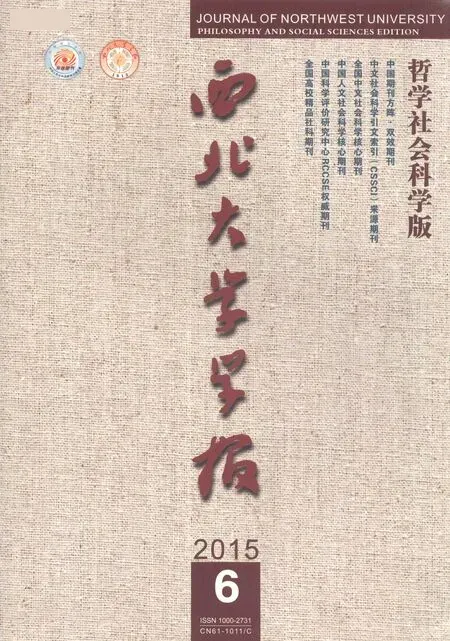理学美学视域下朱熹的文艺批评观探究
刘桂荣
(河北大学 艺术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理学美学视域下朱熹的文艺批评观探究
刘桂荣
(河北大学 艺术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摘要:朱熹不仅哲思渊深,且广涉博览,其文艺批评思想丰富而独步。“文从道出”成为其文艺批评的本体建构;“心统性情”倡言以“心”为主体;“法度即自然”的创作观尊崇法度也推崇自然;提出“得意妙神,以寄真赏”的鉴赏观;强调“观乎德性”的价值观,其文艺批评思想彰显出对自身生命及艺术精神的独到理解。
关键词:朱熹;文艺批评;理;德性
朱熹不仅理学思想博而有统、精深通贯,且广涉博览、独出古今,正如钱穆先生所言:“盖朱子之为学,格物必精,游艺不苟,虽曰余事,实皆一贯。本末精粗,兼而赅之。昔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闻之,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云:吾不试,故艺。后世学者,惟朱子其庶几焉。其曰余事,乃谦言之,犹孔子之谓君子不多也。”[1](P344)钱先生对朱熹的评价可谓中肯,朱熹在艺术方面不仅多方涉猎,而且留下了丰富的文艺批评思想。
一、 “文从道出”之本体观
朱熹的文艺批评思想建立在理学基础之上,“理”是宇宙万物之根本,具有本体地位,在“理”与“道”的问题上,朱熹认为:“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2](P103)“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3](P2755)“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4](P1573)朱熹的“理”与“道”都是从本体意义上而言说的,“道”即“理”,“理”或“道”既是物之所以然之故,也自然是所当然之则,即本体论和价值论是统一的。朱熹正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上阐释了其文艺本体论思想。
朱熹明确提出“文皆从道中流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5](P3319)道是文之本,文是道之枝叶,所以出之于道的文自然要体现道,呈现道,这即是朱熹的“文道合一”“文道两得”观,依此,朱熹批评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及宋初柳开、欧阳修等古文革新运动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观点,修正了周敦颐和二程贬低文之地位的思想倾向,尤其批评了苏轼的“文与道俱”说,“今东坡之言曰:‘无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如东坡之说,则是二本,非一本矣。”[5](P3319)朱熹这里强调“文道合一”,反对苏轼的文道为二的观点。
朱熹对“文”有多处阐释,其基本涵义包括:“天之文”:即阴阳刚柔相交而形成的天地四时之更迭、经天纬地之条理、万物山川之物理等天地之道和自然之理;“社会之文”:即君臣之仪、经籍义理等礼乐制度;“艺之文”:即诗文六艺等。后二者都应属于“人之文”,因此,“文”的概念涵纳着天人及其关系,天人为一整体,都根源于“道”。
朱熹认为艺是文的一部分,“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2](P121)朱熹基本从“六艺”之说定位“艺”,但又明确不止于此,而且朱熹对“艺”之功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艺是“至理所寓”,人们“日用之不可阙者”;虽然朱熹认为艺是小道末节,但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德性之养的功能,“盖艺虽末节,然亦事理之当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则焉。曰‘游于艺’者,特欲其随事应物各不悖于理而已。不悖于理,则吾之德性固得其养,然初非期于为是以养之也。”张子曰:‘艺者,曰为之分义也’,详味此句,便见得艺是合有之物,非必为其可以养德性而后游之也。”[4](P1368)因此,在朱熹的视野中,“艺”虽然不及“道、仁、德”重要,但对“艺”仍给予足够的重视,据此,他批评程门弟子上蔡贬抑轻视艺之观点,“虽然,艺亦不可不去理会。如礼乐射御书数,一件事理会不得,此心便觉滞碍。惟是一一去理会,这道理脉络方始一一流通,无那个滞碍。……‘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5](P866)朱熹立基于文艺本体之存在,修正了前人观点之不足,肯定了艺术的价值存在,这对艺术地位的确立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心统性情”之主体观
“心统性情”首出张载,但张载对此未充分展开论述,而朱熹将这一命题纳入到他的哲学体系中,依此阐发了其文艺主体观。
朱熹的“心统性情”之“心”包含两个方面,一为“道心”,一为“人心”。“道心”是自其天理备具、随处发见而言;“人心”是自其有所谋虑而言。“道心”本于“天理”,是圆善之心;“人心”则是出于“形气之私”,是人之情欲。但朱熹并没有因此否定人心,而是承认其自然性的一面,只是要以道心为一身之主来统摄主宰,从而归乎纯正至善。朱熹之“心统性情”之“统”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兼”“包”之义,心兼体用,未发为性为体,已发为情为用,然而“体用一源”,这里之“心”是涵纳性情两个方面。“统”之另一方面的意义是指统摄主宰之意,这是朱熹此命题所强调的主要意义。朱熹的“心统性情”是要以“心”来主宰统摄性情,也就是“天理”通过“心”来实现对人之现实生命的统领和主宰,实质上,是要对容易偏执泛滥之情欲进行规约,“心统性情”在现实层面主要还是强调“心”对“情”之主宰之义。
朱熹以“心”来评书品画,倡言胸怀本趣之自得,强调作品之“写意”“写神”,执著于胸次之涵泳,诸多渊丰之品评,都是以“心”为核心而展开的。“心”在朱熹的思想中是作为精神主体而存在的,建基于此,“心”也就成为朱熹文艺批评思想中所指涉的文艺主体,这一主体既可是创作者,也可是接受者。
朱熹在对书画的批评中提出“谛玩心画”的观点,“杜公以草书名家,而其楷法清劲,亦自可爱。谛玩心画,如见其人”[6](P3953)。在朱熹的思想中,书法作品即为“心画”,从中可见作者其人。“至于心画之妙,刊勒尤精,其凛然不可犯之色,尚足以为激贪立懦之助。”[6](P3882)正是因为书艺能够写心,所以才能有“激贪立懦之助”,也就是说,创作者的心性能够通过这种“心画”通达接受者的心中,在二者的交流互动中从本根上起到人品德性之助。这种潜移默化之功也正是朱熹所言心画之“妙”处。朱熹以心评书画着眼于道德功利,这有利于道心的发见流行和主宰统摄,从而将这些艺术形式落实到了德性之本根,但从中也可看出,朱熹将这些艺术归根于人之生命的内在,并建基于“天理”之自然,强调其德性也表明这些艺术形式具有无遮蔽的心灵沟通交流之功。
朱熹主张心对性情的统摄和主宰并不意味着压抑或否定情欲的表达,而是提倡从心出发的真性情,他提出的“感物道情”即是以发乎真情作为批评的标准,如朱熹就批评《毛诗序》对《诗经》的穿凿附会的理解,指出《诗经》是出于真情的抒发表达,而不是以“美刺”为目的,他明确提出应该“去《序》观诗,以诗观诗”,这已经是深入到艺术自身来评价艺术了。朱熹也以“感物道情”的观点来评价屈原的作品,认为屈原的《天问》正是因为屈子看到了庙堂上楚国的天地山川,因之满腔悲愤涌动而书其壁上,这完全是感物而触动真情的创作,发自灵府,成之为艺。“感物道情”说明朱熹的艺术评价并不是以道德为唯一的判定尺度,真情实感与艺术感染力都是其品评依据。
三、“法度即自然”之创作观
朱熹认为文艺创作一定要讲求法度,以“端楷”为标准,而不能任意放纵,如同做人之“方正”,朱熹极力赞誉“端庄厚重”之书法,“蔡公大字盖多见之,其行笔结体往往不同,岂以年岁有早晚,功力有浅深故邪?岩壑老人多见法书,笔法高妙,独称此为劲健奇作,当非虚语”[6](P3954)。朱熹推崇古法之法度,同时也注重书法之功力,笔法之精妙。朱熹批评那些过于纵意狂怪之作,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等人的艺术创作即在他批评之列,“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5](P3336)。“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近岁朱鸿胪、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远览,追迹元常于千载之上,斯已奇矣。”[6](P3868)朱熹认为“字字有法度”,米芾、黄庭坚的欹倾之字受到朱熹的否定也是自然之事。朱熹的《朱子语类》中有一段是对艺术法度的讨论,反映了朱熹的这种艺术观。
邹德父楷书大学,今人写得如此,亦是难得。只是黄鲁直书自谓人所莫及,自今观之,亦是有好处;但自家既是写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须要得恁欹斜则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为是,但自要如此写;亦非不知做人诚实端悫为是,但自要恁地放纵。……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则。及至米元章黄鲁直诸人出来,便不肯恁地。要之,这便是世态衰下,其为人亦然[5](P3338)。
此段批评黄鲁直虽自知做人要诚实端悫,创作要讲究“端楷”,但却任由自己放纵而为,这在朱熹看来,正是世态衰下、人心惟危的表现。朱熹是以“立人立世”的儒家思想谈论法度的,因此更关注文艺创作的道德意义和社会价值。
朱熹秉持文艺创作“法度”的同时,也倡导“自然”原则。朱熹思想中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之本性,朱熹将这种自然性归属于“天理”,“天理”流行自有自然之妙,因此说,他是将文艺创作中的自然性归根于最高的具有终极价值的“天理”,从 “理”出发建构他的文艺批评本体,从而支撑文艺创作自然性的批评观。
朱熹强调“文从道流出”“文自胸中流出”。他曾批评苏轼及其弟子“刻意为之”“一向求巧”之弊,主张自然、平淡、真味之作品,推崇陶渊明平淡自然之诗作。他认为作诗不多吟,不少吟,亦不不吟,亦不必吟。“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其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5](P3333)完全是不假思量,自然从胸中涌出,这样才能有“真味”之诗作。
朱熹在对书画、音乐的批评中一直秉承这种自然为上的创作观,认为这是由本根之“理”使然。如他评论伏羲画八卦,虽然是极简数笔,但是穷尽天下万物之理。基于此,他认为“理”即存在并支撑于绘画的创作中,“握管濡毫,伸纸行墨。一在其中,点点画画。放意则荒,取妍则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6](P3993)。此中所谓“一”即指“理”,“点点画画”即是形式笔墨,有“理”之支撑,通过笔墨形式的塑造,则会有气脉贯通,神韵流荡。
画之如此,书法亦然,都是根源于理,朱熹认为仓颉造字是本于“理”,基于“理”之所当然,字从“理”中流出,“流”字显示出朱熹对本于“天理”而出的自然性的强调。依于此,朱熹提出“写字不要好时,却好”[5](P3337)的创作理念,这与苏轼“无意于佳乃佳尔”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朱熹认为音乐本于自然,他说:“礼乐者,皆天理之自然。节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乐也是天理自然有底。”[5](P2253)“礼乐”本于“理”之自然,“律吕乃天地自然之声气”,“向见一女童,天然理会得音律,其歌唱皆出于自然,盖是禀得这一气之全者。”[5](P2349)朱熹这里提出了音乐的本体论问题,音乐乃天地自然之气,这意在表明音乐本身之自然性,而孩童禀赋这种自然之气,其歌唱自是一任天然。这里,朱熹的赞美既是关注到演唱主体,即天真烂漫的孩童这一形象,又关注到其歌唱的自然性,这说明朱熹对音乐自然性的强调和欣赏态度。
朱熹在文艺创作上既强调法度,又有对自然的坚守,表面上看似乎颇为矛盾,但从根本上来讲二者并不抵牾。朱熹的法度是指要合乎“天理”之根本,这本身即是自然而然的当然之则。因此,法度即自然,自然即法度。朱熹在评邵雍的书法时也表达了这种观点:“康节先生自言大笔快意,而其书迹则谨严如此,岂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者耶?”[6](P3932)在朱熹看来,文艺创作是根源于“理”,出乎于心,自然而然,但合乎法度。
四、“得意妙神,以寄真赏”之鉴赏观
朱熹主张艺术鉴赏要以“意”和“神”来把握作品,鉴赏者要领悟创作者之精神意趣,“须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须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动有意思,跳踯叫唤,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5](P2755)朱熹明确提出欣赏作品要得其言外之意,要领悟悦动人心的审美旨趣。
在“形神”上,朱熹更加推崇神韵,如在《跋东方朔画赞》中谈道:“平生所见东方生画赞,未有如此本之精神者。笔意大概与贺捷表、曹娥碑相似,不知何人所刻,石在何处,是可宝也。”[6](P3954)赞赏此画能够“本之精神”。朱熹的《题画卷·吴画》评论道:“妙绝是生笔,飞扬信有神。群仙不愁思,步步出风尘。”[7](P320)将吴画人物飘然出尘之神气风韵评点出来,通过朱熹这一评点使读者似乎看到了吴画中神仙的道骨仙风。
朱熹所谓“神”是从“理”和“气”之本根层面进行定位的,他认为“神”即“理”,是气之精英从生命内在发越出来的,自然超越于形器之表。“神”的特点是“妙”,所以从作品中要抓到这“神”就要体会到其妙处,这样,捕捉作品之“神”的过程也就成为体悟其“妙”的过程,是心灵的契合与悟解。钱穆曾解读朱熹之“神”:“理附泊在气而不可见,属形而上。神则是气之发出光彩处,是就形而下说也。以能比迹,固可谓之形而上,以神比理,则犹是形而下。或可谓理是宇宙之本体,神则宇宙之化工,即所谓良能也。”[1](P299)钱穆认为“神”即是宇宙之本体“理”的发见流行、妙化万物者,所以称其是“良能”。也就是说,“神”是源自宇宙本体而呈露出来的宇宙万物内在的精神生命,它虽不可见,但可妙悟领会。朱熹以这种“神”来解读品评艺术作品,正是触及到艺术作品深处,以彰显艺术主体之精神。
朱熹进而提出了“真赏”说。“米老《下蜀江山》尝见数本,大略相似,当是此老胸中丘壑最殊胜处,时一吐出,以寄真赏耳。苏丈粹中鉴赏既精,笔语尤胜。顷岁尝获从游,今观遗墨,为之永叹。庆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6](P3963)那么,何谓“真赏”?朱熹的“真赏”思想首先包括“图真”的一面,也就是对所绘物象的真实呈现,如《跋唐人暮雨牧牛图》云:“予老于农圃,日亲犁耙,故虽不识画,而知此画之为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顾而徐行,后者骧首而腾处,目光炯然,真若相语以雨,而相速以归者,览者未必知也。良工独苦,渠不信然!”[6](P3907)这其中就有对“形”的赞赏。朱熹也曾经参与“雪中芭蕉”的讨论,但他对王维是持批评态度的。“雪里芭蕉,他是会画雪,只是雪中无芭蕉,他自不会画了芭蕉。人却道他会画芭蕉,不知他是误画了芭蕉。”[5](P3287)朱熹此评不仅批评了王维此画不问四时,也批评了沈括等人对王维的肯定。这也反映出朱熹对此画并没有完全领悟,还停留在“图真”层面,其品评自然要稍逊一筹。
“真赏”之鉴赏观另一个层面即是对作品“神”的把握,这也是朱熹一再强调和重视的层面,他认为只有把握住作品之“神”才能“真为我有”。 “盖尝闻之先生君子,观浮图者,仰首注视而高谈,不若俯首历阶而渐进。盖观于外者虽足以识其崇高钜丽之为美,孰若入于其中者能使真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层累结架之所由哉?”[4](P1719)朱熹以观赏“浮图”为例提出自己的鉴赏观,他认为要真正领悟作品,首先不能只停留在“关于外者”,也不能停留在“美”的层面,而是应深入其中,真为我有,即深入到作品之生命内在,从而感知、领悟、觉解这一生命,实现观赏者和观赏对象之间的生命交流。这样,艺术家之作品才能契入观者灵府,观者从而得到鉴赏之快慰。朱熹曾指出,观赏咏歌舞蹈要体会其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之处,而不能专靠义理去研究,要“熟看得,待浃洽”,也就是要进入到作品深处,得其意、妙其神,待透彻明白、融会贯通,自会有全身心的愉悦感。
五、“观乎德性”之价值观
朱熹认为文艺作品根源于“理”,那么道德价值就成为其批评的重要标准,他在对诗歌音乐和书画的批评中,都强调了其德性价值的一面。
朱熹在品评《诗经》时论到:“诗,古之乐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5](P2066)朱熹非常重视《诗经》中乐的功能,认为《诗》之吟咏讽诵自然足以感发善心,并能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由人心之善到德政之仁,这成为朱熹音乐批评的进路。朱熹曾论到音乐美善的问题,“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2](P92)“或问韶、武善美之别。曰:只就世俗论之,美如人生得好,善则其中有德行耳。以乐论之,其声音节奏与功德相称,可谓美矣,善则是那美之实。”[5](P636)朱熹沿着孔子对乐之美善的品评展开,虽也关注到音乐本身的声容之美,但最终还是将美归之于善,音乐之美是声音节奏要与功德相称,善才是美之实。孔子之“尽善尽美”的美善合一思想在朱熹这里,几乎是被“善”所垄断,不过,“善”既是“美之实”,那么“善”自然也是美的,这样,朱熹又为道德的“善”赋予了“美”的品性。因此说,朱熹的美善关系是以“善”为本根的美善合一思想。
朱熹对书画的品评同样落实到德性价值,因此往往是从其作品看其人品,可以说,在朱熹的思想中,艺品即人品,“吴生之妙,冠绝古今,盖所谓不思不勉而从容中道,兹其所以为画圣与”[6](P3955)。认为吴道子绘画之所以能冠绝古今成为画圣,是因为其能够“不思不勉而从容中道”,这是以《中庸》之圣人标准来评价吴道子作品,显然是从其人品来定位其作品。
朱熹主张“持敬”“主静”的修养工夫,在艺术上他同样欣赏具有“静气”的作品,反对那种过于忙躁的创作。朱熹曾对王安石和韩琦的书法评论道:“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行草势。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介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警焉,因识其语于左方。”[6](P3957)朱熹将二者的书法进行比较,称赞韩琦的书法安静和豫,而王安石的作品恰恰相反,充满了忙躁感,朱熹并依此来警醒自己与他人。
朱熹对苏黄艺术风格虽颇多微词,但又极为赞誉其作品中透脱出来的人品,如在给苏轼《枯木怪石图》的题跋中言道:“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诙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尤足以想见其人也。”[6](P3971)他从绘画中看到的是苏轼流露出的傲骨英气。在《跋东坡帖》中言道:“东坡笔力雄健,不能居人后,故其临帖物色牝牡,不复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风逸韵,高视古人,未知其孰为后先也。成都讲堂画像一帖,盖屡见之故,是右军得意之笔,岂公亦适有会于心欤?”[6](P3964)这里,朱熹从苏轼的作品中看到了其“英风逸韵”,因此对苏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甚至认为其能够超越古人。对黄庭坚的作品,朱熹不以工拙笔法来论,而是从其“老笔”中读到了黄庭坚的“忠贤流落”,笔之“老”恰是人生寥落中人之品行的坚守。从中可见,朱熹对艺术世界的评点是深入到作者的人生世界中,掘发人之德性的光亮,可以说,朱熹的艺术世界是人之德性的世界。
朱熹的文艺批评思想彰显着对自身生命和艺术精神的理解,“不是胸中饱丘壑,谁能笔下吐云烟”,自身生命虚静而明才能有萧散绝尘之作。他批评“今人”尽命去奔做,心里闹,不虚不静不明不识,虽有百工技艺之精也是枉然。他主张文艺创作“未必要人看”,文艺生命的存在不是以外在为最终目的,这一思想之于当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钱穆.朱子新学案[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2] 朱熹.朱子全书·论语集注:第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 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2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4] 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2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5] 朱熹.朱子语类[M].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2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7] 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20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赵琴]
【文学研究】
Exploration of Zhu Xi′s Literary Critical Ideas from the
Neo-Confucianism Aesthetic Horizon
LIU Gui-rong
(HebeiUniversityCollegeofArt,Baoding071002,China)
Abstract:Zhu Xi not only ha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but wide range of subjects. He has rich and unique literary critical thoughts.“Wen from Tao”as its ontology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Heart control temperament”advocate“heart”as the subject; “Testimonies is nature”creation view worship testimonies also praise highly nature; Proposed appreciation view of “Get meaning and Beautify verve and sustenance truly appreciate”; Emphasis on the values of “by virtue”. His thoughts of literary criticism highlights the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own life and artistic spirit.
Key words:Zhu Xi; literary criticism; li; virtue
作者简介:王莲,女,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副教授,博士,从事艺术学、中国艺术美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教外司留[2013] 1792号;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0YJC760072)阶段性成果之一;江苏省社科研究青年精品课题(苏社联发[2013]43号)项目号:13SQC-177
收稿日期:2014-09-26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6-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