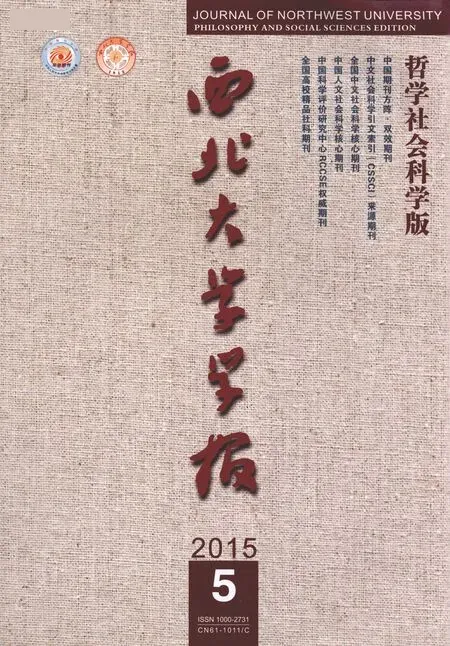“意象”研究钩沉与反思
———兼论“意象”内涵及其审美特性
田义勇(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杭州 310012)
“意象”研究钩沉与反思
———兼论“意象”内涵及其审美特性
田义勇
(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杭州310012)
摘要:在中国美学界,“意象”是一个极具学术生命力的核心范畴。当代“意象”研究的学术实绩值得肯定,但在语源阐释与思想方法上还存在诸多问题。追溯“意象”语源,应当注重“象”的中介关联性,继承早期的“言”“象”“意”三元范式,重新认识并扬弃明清时期的“情景交融”等二元范式。在研究方法上,无论“主客二分”还是“超主客二分”,都不能真正摆脱二元范式的窠臼,亦不契合中国思想实际。在基本理念上,“意象”研究应当奠基于先秦时期即有的“和实生物”“相异者相济”理念。明清时期何景明、王夫之等人并非反对“分”,而是反对“离”,其思想实质是主张“相异者相合”。基于“异在论”立场,所谓“审美意象”就是以一“意”(“游观意识”)摄三“象”(“心象”“物象”“语象”)为基础的上下贯通与三元交融的体验活动及其结果。
关键词:意象;三元范式;异在;游观意识;语象
在中国美学界,“意象”是一个极具学术生命力的核心概念。它从浩如烟海的美学史料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美学的一个学术热点,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当代很多美学家、文论家络绎不绝地对它进行思考与论证,尤其是朱光潜、宗白华、叶朗等著名学者的相关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这也表明它的学术价值之非同凡响。其他知名学者,如汪裕雄①参见汪裕雄:《审美意象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参见汪裕雄:《意象探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夏之放[1]有围绕“意象”展开的学术专著问世;还有后进健将,如蒋寅[2]、朱志荣[3],对“意象”研究也倾注过心力。这里面固然有分歧、有论争,乃至有芜杂与混乱,但若只看到不同观点的此起彼伏,只为了得出否定性的判断,显然是片面的。事实上,当代“意象”研究的学术实绩值得肯定: (1)基本理清了中国文论关于“意象”的效果历史,在语源梳理与阐释方面作出了贡献; (2)自觉运用就当时而言较新的思想方法,为“意象”研究、现代美学体系的建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3)自觉地运用“意象”研究成果,在美学理论、文学理论教材建设及教学实践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这最后一方面,它进入大学课堂所产生的理论效应是巨大的,如叶朗以“意象”为核心推出特色鲜明的美学教程①参见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叶朗:《美在意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朱志荣主持自成一体的美学教材②朱志荣主编:《美学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朱志荣:《中国审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4]也吸收了顾祖钊本人的“意象”研究成果。
然而也须看到,当代“意象”研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文献的解释性、概念的明晰性、逻辑的自洽性、方法的批判性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探求。出于学术兴趣,笔者亦曾在论著中涉及“意象”研究[5](P180-186),这里想谈一些最近的思考。
一、“意象”研究在语源阐释上存在的问题
回顾以往“意象”研究,笔者以为在语源阐释上尚存在着一些弊端。论者往往截取片言只语而忽略了其整体语境与基本立场。比如,研究者以“象”为线索,将“意象”研究追溯到《老子》《易传》,旁及韩非、王弼等人的相关阐述,这里就存在着语料解读与整体把握的问题。
首先,“象”是一个中介关联性的范畴。它一方面建立于观念层面,一方面既区别于又指涉着现实实物,但它摆脱了对于现实事物的依附,只存在于记忆与想象等精神活动中。比如韩非《解老》:“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6](P148)这段话尽管学界不断引述,但“象”的根本意义尚有待厘清。实质上,这里讲“象”基于哲学的一个基本区分:不可见、不可感、不可言的领域与可见、可感、可言的领域。这个基本区分总是绕不过去,无非表述不同,比如形上与形下、存在与存在者,等等。怀特海讲:“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具体事实是怎样体现从它自身抽象出来而又分有其自身本性的那些实有?”[7](P34)这仍是纠缠基本区分问题。韩非本段话的上一段讲:“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6](P146)就是把“道”与“万物”“万理”相区分。既有此基本区分,就需通过一种方式把两者沟通、关联起来,这正是“象”的存在意义。
韩非解释“象”,首先强调人的想象作用与图像指涉功能: (1)“图”(“死象之骨”的轮廓模样)区别于“生象”,但不妨据之“想其生”; (2)“象”只存在于人的想象活动中,所谓“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可见,“图”是人与实物间的中项,“图”经“想”而激活为“象”。“图”“象”把“希见生象”的人与“生象”关联起来,人是凭借“图”“象”间接指向现实的“生象”。韩非以此来解释“道”与“象”的关系,“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即是说,“道”可以通过“象”这个中介来接近。这段解释针对《老子·第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8](P35)可见,为了超越“视”“听”“搏”等感官局限,“象”发挥着间接指向“道”的作用,但同时导致理解上的极大不确定性,即“惚恍”。
结合美学理论,由“象”可得出的基本关系就是三项式的关系: (1)作为不可见之物的观念世界,比如审美冲动、内心体悟,这是“虚”的一端; (2)作为可见之物的感官世界,比如自然与社会,这是“实”的一端; (3)作为中介环节的符号世界,即此处的“象”。一般只关注前两项,其实第三项极其重要,它的关联作用正在于使不可见者可感,使不可言者可传,使不在场者在场。
在《易传》及其早期阐释中,涉及“象”的重要论述一般是三项并举的。笔者的一篇习作曾指出:“从《周易·系辞》到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再到魏晋时代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总是‘意’‘象’‘辞’(言)或‘情’(意、志气)‘物’‘言’(辞令)相提并论。”[9](P302-318)比如王弼讲:“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10](P609)正是“言”“象”“意”三项鱼贯的表述方式。再如陆机《文赋》,有论者亦指出:“全文紧紧围绕‘物—意—文’三者关系来展开论述……”[11](P135)
面对文献语料,“意象”研究似乎应把握两个问题: (1)不可见、不可言世界之向可见、可言世界的转化过程,这应是审美创造的基本问题,涉及如何把审美冲动、审美意识等外化、显现的问题; (2)“言”“象”“意”的三项联动结构,这是早期理论的基本范式。这个三元范式是如何被二元范式(比如情与景、主与客)替代的?这一替代是否合理?
关于“意象”一词的生成,研究者追溯到王充《论衡·乱龙》或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但阐释上亦有不足。《乱龙》的主旨是讲“土龙”等象征符号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合理性,是讨论两者之间有否必然联系。与“意象”联系紧密的话,一是:“礼,宗庙之主,以木为之,长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庙,主心事之,虽知木主非亲,亦当尽敬,有所主事。土龙与木主同,虽知非真,亦当感动,立意于象。”[12](P922)关键词是“立意于象”(或当作“示意于象”[13](P704))。另一是:“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12](P923)两段合参,“意象”一词本是讲象征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所谓“立意于象”或“示义取名”。比如祖宗牌位,明知非亲人,但孝子还是恭敬地侍奉它,原因就是“立意于象”,即通过“立意”赋“象”以意义;作为符号它虽是假的,但亲情是真的,这就赋予它指涉功能的真实性与合理性。“礼贵意象”依据的是孝子视祖宗牌位如亲人宛在的心理事实。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14](P27)“礼”的践行中最要紧者是对仪式符号灌注以至情至诚,否则就只是土石木偶。有了真情灌注,那“以木为之,长尺二寸”的符号就有了意义,就超越物表而宛如至亲,起到使不在场者(死者)宛如在场的作用。由王充的论述,顾祖钊认识到“意象”作为一般“观念意象”的特点[4](P224-225),但对“象”的中介指涉性、“意”的情感灌注性尚缺乏深入领会。对此处的“意象”真正应当把握的、且契合了审美活动实际的,正是象征符号的中介性、真实性问题。审美传达之区别于科学,正在于它不求客观真实、客观逻辑,而偏于情感真实、主观逻辑,此其一;语言符号、形象符号是中介环节,它只是间接指向现实生活,而非直接就是客观事实,审美创造的世界是符号世界,它不照搬现实世界,因此两者之间是异在指涉的关系,此其二;审美符号世界只是虚拟的真实,基于审美默契的假定性,“假”因情真意切而富有审美意味,此其三。这种符号假定性在戏曲表演中随处可见。
再看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关于“意象”的表述:“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意象”一般理解为“意想中之形象”[15](P983)。若不细究,此解似也大致不错。但可以肯定,朱光潜讲的“意象”概念只是自家意思,未必合刘勰本义:“每个诗的境界必有‘情趣’(feeling)和‘意象’(image)两个要素。‘情趣’简称‘情’,‘意象’即是‘景’。”[16](P51)在朱先生的这一规定中,“意象”仅是与“情”相并的“景”而已。再看宗白华:“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石。”[17](P160)“意象”依然只是“景”。然而,倘若阐释“意象”追求语义还原,就要遵守原句的对仗格式:“意象”对“声律”,“声律”既然由“声”与“律”并列合成,则“意象”亦当由“意”与“象”并列合成。因此,“意象”的涵义当基于“意”与“象”的相互统一,两者缺一不可、不分轩轾。由此,解“意象”为“意想中之形象”就显然不妥,是偏于“象”的讲法;解“意象”为“景”更是片面,是置“意”不顾的讲法。从“窥意象而运斤”看,“意象”只是“窥”的对象,即是说,在“意象”之上尚有“独照之匠”作为统摄者。这样,理解“意象”概念就要明确两条: (1)“意象”在刘勰的语境里,应视为并列结构,由“意”与“象”合成,英译就不当为“image”,而当按宇文所安的方式译为“concept-image”这样的合成词[18](P209-210); (2)“意象”只是下位概念,尚有高于其上的统摄者照管,它就是超越实物而抵达“道”的境界的纯粹意识。“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是基于庄子的话语背景。“庖丁解牛”“轮扁斫轮”都是讲超越外物而熟练驾驭的自由境界。“庖丁解牛”之所以“目无全牛”,就在于超越了表象的“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不再受限于感官,而以“神”为主导,这“神”就是超越了感官层面的纯粹意识。苏轼讲的“胸有成竹”、郑板桥讲的“胸中之竹”,都是超越“眼中之竹”感知阶段而达到精神主导的构思阶段。学人爱引用张怀瓘“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但严格说来,“外师造化”偏于创作前期,到了审美构思时,“中得心源”就占了主导地位。比如画家画黄山去黄山实地考察,此时主要“以目视”;但身在画室画黄山,就“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了,山就是“胸中之山”,尽在“意匠惨淡经营中”了。
尚须指出,一些“意象”研究者在追溯“象”或“意象”语源时,不顾其原文语境,径直把“象”或“意象”解为“文学形象”“艺术形象”,未免牵强附会、硬贴标签。比如《易传》中“象”“意”“言”并举,“象”只是“卦象”而已,它是由阴阳两爻组合而成的符号系统以及由此而指向现实的象征符号系统(比如“潜龙勿用”“羝羊触藩”“小狐濡尾”)。此处“言”“象”只是手段,都服务于“意”(“圣人之意”或冥冥之中的天意),而在审美创造中,“言”“象”居于核心,本身就是目的。
二、“意象”研究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的问题
当代“意象”研究者往往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这是好事,但在方法运用上由于缺乏透辟的领悟与自觉的批判精神,就出现了“方枘圆凿”的现象。无论朱光潜时代的“主客二分”模式,还是叶朗时代的“超主客二分”模式,都纠结于二元范式而跳不出。上文已经提到:“言”“象”“意”三元范式是如何被“情”“景”或“主”“客”二元范式取代的?众多研究者由于缺乏这一问题意识,在引述后期文献、尤其明清文献时就缺乏必要的批判眼光。即使主张“超主客二分”的研究者,其思路仍是拘于二元的,其论证思路仍循旧辙而无更张。
比如,叶朗为了论证“美在意象”命题,先是否定偏于客的观念,提出“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外在于人的‘美’”;接着否定偏于主的观念,提出“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美’”;最后以两方面的否定为基础,提出“美在意象”[19](P43-55)。这种三段式表明,其运思仍是“主客结合”的老路。再看这段话:“中国传统美学给予‘意象’的最一般的规定,是‘情景交融’。中国传统美学认为,‘情’‘景’的统一乃是审美意象的基本结构,但是这里说的‘情’与‘景’不能理解为互相外在的两个实体化的东西,而是‘情’与‘景’的欣合和畅、一气流通。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如果‘情’‘景’二分,互相外在,互相隔离,那就不可能产生审美意象。离开主体的‘情’,‘景’就不能显现,就成了‘虚景’;离开客体的‘景’,‘情’就不能产生,也就成了‘虚情’。只有‘情’‘景’的统一,所谓‘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虚景,景总含情’,才能构成审美意象。”[19](P55)表述很精彩,但亦有问题: (1)既然强调的只是“情”“景”结合或统一,这就必然基于“情”与“景”的区分,若两者本一何需统一? (2)王夫之讲“情景名为二”,不就证明两者已“二”吗?“名为二”毕竟也是“二”。若“名为二”而实“一”,何须叠床架屋平添统一的安排?王夫之讲“实不可离”,实是主张“合”而已。换言之,王夫之不是反对“分”,而是反对“离”。汉语的“分”字要搞清容易混淆的两义: (1)分别、识别; (2)分开、隔离。王夫之反对的只是后者。既然赞同王夫之,叶朗的美学观若准确地表述,就当是反对“主客二离”而主张“主客结合”而已。
参照王夫之的其他表述,其观点会更豁然。一曰:“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20](P736)二曰:“关情者景,自与景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21](P814)三曰:“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21](P826)可见,王夫之只是反对“截分两橛”而讲“有在心在物之分”。作为比照,再看明代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夫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是故乾坤之卦,体天地之撰,意象尽矣。空同丙寅间诗为合,江西以后诗为离。譬之乐,众响赴会,条理乃贯;一音独奏,成章则难。”[22](P37)何景明亦主“合”而反“离”。更要紧者,何景明“一音独奏,成章则难”的讲法是继承先秦时期即有的“和而不同”理念。所谓“和”是反对单一垄断性之“同”而主张“异在”方面的补充相济:“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23](P515)这种反“一”主“和”的理念实质上就是主张多元共济、相互促成。
当代“意象”研究从思想方法上反“主客二分”就中国思想而言并不能切中肯綮。因为,就“情景论”而言,至少在明清时代就明显地呈现出二元化模式。不论何景明还是王夫之,都只是主“合”,但心目中都有“情”与“景”之“分”,叶燮更明确区分了“在我之四”(才、胆、识、力)与“在物之三”(理、事、情)[24](P23-24)。倘若真要反对“主客二分”模式,至少要从明清时代算起。倘若缺乏这一批判意识,讲“意象”而引叶燮等人的话,就似乎犯了“以敌为友”的糊涂:一面反对“主客二分”,一面赞同主张“主客二分”者的话。
中国当代反“主客二分”的思想方法源于西方现代哲学,却有走向极端、盲目反对一切“分”的危险。而作为反“主客二分”模式的理论源头,海德格尔本人却一直坚持着“分”,他对“世界本身”与“世界内”[25](P76-77)、“存在”与“存在者”[26](P95)就严格区分。作为老师的胡塞尔一直把“意向活动”与“意识对象”[27](P223-224)相区分。作为后学的萨特更是讲“意识”与“存在”[28](P20)这一区分。事实上,当代学界已经有人对于反“主客二分”的思想提出了质疑①寇鹏程:《主客二分而不“裂”: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本质区别》,《河北月刊》2003年第1期,第191-194页;王元骧:《对文艺研究中“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批判性考察》,《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第76-85页;高连福:《关于主客二分模式的思考》,《哲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122-126页;李志宏、刘洋:《认识论和“主客二分”何错之有?》,《文艺争鸣》2013年第5期,第16-20页。。
在思想方法上,我们不能倒退到重浑一的老路,那是老庄哲学或佛教禅学的套路,那是“无思无虑无言”的境界②实际上老子就做不到,《老子·第一章》第一句就讲“二分”:“可道”与“不可道”、“常道”与“非常道”。。讲审美创造与体验,就要讲“有思有虑有言”的执着,放弃“思”与“言”的执着就等于取消文学。反观中外文学史,就是一部“立言”执着追求史。“语不惊人死不休”“两字三年得”,没有这种语言觉悟与追求,何谈文学?哲学与文学有区别,哲学思想方法不能照搬于文学,对于西方哲学思想方法是如此,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方法亦是如此。近年来,“天人合一”模式的讲法颇为盛行,笔者于此总是抱有怀疑,原因就是它对于“分”缺乏真正深入的领悟。细究“天人合一”命题,“天人”就是两个范畴,这两个范畴若想规定清楚就必须“分”。严格来讲,所谓“天人合一”应当只是反对“天人”隔离、对立而已。何谓“合一”?相异者之交融方谓之“合一”,仅有相同而无相异,就不是“合一”而似“以水兑水”。“水乳交融”在于“水乳”两相异而两相宜,单纯的“水水”或“乳乳”何谈“交融”?“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必须有“一”的相异者加入方可。《周易·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曰文。”即是说,“阴阳相杂而成文”[29](P603)。纯阴纯阳只是“纯一”,必须阴阳两相异而始可“相杂”。王夫之讲“乾坤并建”:“易者,互相推移以摩荡之谓。《周易》之书,乾、坤并建以为首,易之体也;六十二卦错综乎三十四象而交列焉,易之用也。纯乾纯坤,未有易也,而相峙以并立,则易之道在,而立乎至足者为易之资。《屯》《蒙》以下,或错而幽明易其位,或综而往复易其几,互相易于六位之中,则天道之变化、人事之通塞尽焉。”[30](P41)这里王夫之不是明确主张“乾坤”二元“相峙以并立”吗?讲“交列”“错”“综”,都是贯彻“相杂”原则。王夫之又说:“乾坤并建于上,时无先后,权无主辅,犹呼吸也,犹雷电也,犹两目视、两耳听,见闻同觉也……然则独乾尚不足以始,而必并建以立其大宗,知、能同功而成德业。”[30](P989)可见,王夫之明确地在本体论上有“乾”与“坤”之辨,只是反对“独一”而无“异”而已。
因此在思想方法上,就“意象”研究而言,不能盲目地反对“分”而应当反对“离”;应当主张“和合”而反对“孤一”“独一”“单一”。这种重“和合”的思想方法,就是强调“异”之相互结合与相互渗透。独“意”不立,须异于“意”的“象”相济;孤“情”不立,须异于“情”的“景”相合。但这样讲还不够,因为这种二元范式的一大问题是忽略了审美活动中符号的作用。我们主张恢复三元范式,主张“言”“象”“意”三元交融。
三、“意象”的概念规定及其审美特性
从语源阐释与思想方法上,上文指出了当代“意象”研究的诸多问题。经此批判梳理,或可赢获认知视域的“澄明”。我们既要祖述古代思想传统,追本溯源摸清来历,又要结合当代理论要求,灵活通变适当调整。由此,我们将对“意象”的概念进行规定,进而从审美特性着眼将审美意象与一般意象进行区别。
首先,我们讲“意象”概念贯彻的基本思想是“异在论”。所谓“异在论”,是强调“异的存在”的基本理论,它继承并发展先秦时期“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理念,揭示相异的必然性,主张相异者相辅相成与相互结合,反对“纯一”而无“异”。严格地讲,“和而不同”应表述为“不同而和”,唯“异”方有“和”。基于“异在论”立场,讲“天人合一”亦当讲“天人”相异而相宜,无“人”异于“天”或无“天”异于“人”,就是死寂的“同”,就称不上“合一”而是“单一”。
其次,“意象”之一般属性,就在于它的“异在性”。所谓“意象”的“异在性”,即是说,它是异于现实世界、客观世界的虚拟存在。它源于现实世界、客观世界,但它是高度观念化、高度符号化的领域,它是异于物质世界的观念世界、符号世界、虚拟世界、价值世界。我们讲“异在性”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与马尔库塞讲“异在性”[31](P74)概念不尽相同。马尔库塞讲“艺术即异在”[31](P181),是从否定现实、拒斥现实的立场讲;我们是从中国古代就已经重视的“象”的异在关联性讲,但在强调艺术世界的虚拟性与超越性等方面,马尔库塞的思想亦能引起理论共鸣,也值得借鉴。
前文已经表明,无论韩非还是王充在讲“象”时,都已经注意到了“象”与“物”的区别。强调“意象”的“异在性”,就是强调它摆脱实物依赖、现实束缚而走向相对自足的自觉努力。“象”只在人的头脑想象活动中存在,它与现实之“物”的交涉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是异质的,而不是等同的。在这里,再拘泥于、牵绊于所谓现实实物、所谓“客”,都不合时宜了。套用马克思的话讲,“意象”创造的阶段“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32](P84),或者说,现实实物在这时“已经观念地存在着”[33](P208)了。“意象”之“异在性”,正强调了它作为精神生产之区别于物质生产的一般属性。在这时,身体感官已经相对而言不重要了,身体感官之起作用主要在“感物”的阶段,是审美创造之前的准备、储备阶段。不管是陆机讲“伫中区以玄览”,还是刘勰讲“收视反听,耽思傍讯”,都突出了精神活动的首要地位而主张限制、克制身体感官的活动,这正抓住了“意象”创造以“神”为主的基本特点。
事实上,不少论者也注意到“意象”的“异在性”。比如这段话:“意象(imagery)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它是指大脑中所保持的对事物的一种映像。比如,当我们闭上眼睛在想象中看见大熊猫时,在我们大脑里就会出现代表大熊猫的形象。这个形象是建立在对大熊猫先前知觉记忆的基础之上,已经成为一种心理现实,所以不必依赖大熊猫的真实出现。因此,意象纯粹是一种内心活动的表现,它通过抽象的主观的‘意’,反映具体的客观的‘象’,是‘意’与‘象’的对立统一。”[34](P2)
强调“意象”的“异在性”,应当强调现实事物的“不在场”,即是说,“象”所关涉的现实对象已经不与审美主体构成对峙并立关系。即使李白《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个“相看”也是想象的“相看”,这时“敬亭山”是李白心中的“象”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山”。更多的时候,“物”已经不在审美主体的周遭,审美主体只是身在书斋中凭借记忆力、想象力将“不在场”虚拟化为“在场”。换言之,“物”已经从独立于、外在于作家的游离状态,化为“属我”之“象”了。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的讲法不无道理:“再没有对象和它对立,而是把对象造成自己内在的东西,懂得把对象当作自己本身。”[35](P53)
强调“意象”的“异在性”,还应当强调纯粹意识的至高统摄性。在审美创造中,必须有一统摄一切、融汇一切的至高意识,这就是“神思”。刘勰《神思》讲的“玄解之宰”“独造之匠”就是这个意识。陆机《文赋》讲“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也是一种囊括一切于头脑的纯粹意识。在审美活动中,有此至高的纯粹意识,则一切尽化为其内的一种“象”了,这时审美主体与外界事物、客观世界的利益纠葛是暂时淡忘了。庄子讲“心斋”“坐忘”,亦是讲纯粹意识对于“利害之情”的超越而已。
以上,我们只是讲了“意象”的一般属性,即“异在性”。但是,“意象”要成为“审美意象”,就要具有审美特性。关于“审美意象”,笔者主张以“游观意识”为基础,在这一意识统摄下,“语象”“心象”“物象”三元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交融。所谓“游观意识”,它区别于一般的“纯粹意识”(比如哲学意识、科学意识、宗教意识等),是独有的“审美意识”。之所以把“审美意识”称为“游观意识”,就在于它是: (1)宛转不定地游动,即刘勰《神思》所讲的“神与物游”; (2)上下环游兼平行对流,而非单向度的一意孤往; (3)超越功利的精神游戏而非执着占有的物欲竞争。(1)是从审美意识之区别于日常意识、粘滞于“物”的意识而言的,它是驭“象”于心的意识,“象”被意识流所裹挟而以记忆、想象的方式运动着。(2)是将审美意识与一般的哲学意识、科学意识等区别开来。比如一般哲学意识是强调“道”与“器”上下之间的张力关系的,但审美意识是化解二者的张力关系为和谐关系,所谓“上下环游”即上下两个层面之间自由穿行、循环往复。所谓“平行对流”,是指审美意识致力于相异者之间的打通、结合、交融,化执着于一端的“独”为相互关联的“互”。(3)是从价值角度讲,审美意识超越现实功利心而采取审美赏悦的态度,不执着于占有而专意于欣赏,比如苏轼《赤壁赋》视“清风明月”为“无尽藏”。
基于“游观意识”,我们强调在该意识统摄之下的三象交融: (1)心象,由一般情欲、情感、志气、抱负、思想转化而来,它是一般主观情思的对象化、审美化; (2)物象,由对现实物体、客观现象的回忆与想象转化而来,它实现了对于外界万物的心灵化、审美化; (3)语象,由一般日常语言、符号形式转化而来,从日常语感转化为审美语感,从普通形式感受转化为形式美感,它实现了对于语言形式的对象化、审美化。真正具有审美语感、形式美感的艺术家对于语言、形式美的领悟感受是超乎寻常的,诗人对于字眼、声调、句式有与众不同的体验,画家对于颜色、书法家对于线条,亦有敏锐于常人的体悟。比如同写叶落,屈原笔下是“洞庭波兮木叶下”,杜甫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一般的“树叶”,屈原讲就是“木叶”,杜甫连“叶”也不说,就讲“落木”。在审美活动中,语象本身就是目的与归宿,无论心象与物象,都最终转化为语象,审美创造本身就是符号审美化、形式审美化的过程。语象之区别于一般语言形式,在于它本身就有审美意味及独立的价值。这一点并不需要诉诸西方文论,仅是文字游戏这种常见的现象就证明了语象的游戏化、审美化过程,比如“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这种“拆字法”不就取得了审美意味吗?
遗憾的是,当代讲“意象”者大多将语象排斥于外,只是附加地谈语言问题。虽也有学者高度重视符号化过程,但并未单独区别出语象以强调其独立品格。比如夏之放讲文学意象“以语言为媒介将审美意象符号化”,本有很好的讲法:“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文学创作的过程也就是符号化的过程。这一符号化的过程,不仅包括用语言符号来传达审美意象的过程,而且包括构思熔铸审美意象符号来传达人生体验的过程,因而可以说,从审美感受、艺术构思到艺术传达,从审美意象的孕育、生发到物化为艺术意象,这整个的创作过程都是符号化的过程。”[1](P214)但夏先生并未明确提出语象这一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蒋寅在《语象·物象·意象·意境》[2]一文中,明确主张把语象概念引入“意象”研究领域,这是很有创意的思路。但蒋先生之引入“语象”是为了解决“物象”概念的局限性而提出的,在语象、意象、意境的概念规定方面存在着交叉重叠、区别不清的情况。韩经太、陶文鹏随后写了商榷文章,主张将概念修正为:“意象是由作者依循主、客观感动的原理和个性化的原则艺术加工出来的相对独立的语象结构,它可以由一个或多个语象构成,它具有鲜明的整体形象性和意义自足性。”[36]这个定义显然是主客二元模式的产物,但它的价值在于突出了语象的理论地位。但亦有人认为“语象概念不成立,不可能作为阐释意象的基础概念”[37],然而该作者的论证方式是错误的,局限于追溯“语象”一词的出身,仅通过论证赵毅衡、陈晓明等最早使用“语象”者的理论失误就仓促地得出这一结论。道理很简单,“语象”概念并非少数人的“专利”,仅因个别人运用不当或规定失误就判定它“不成立”未免过于武断。
“心象”这个词亦已有学人使用,比如朱志荣在规定“意象”时说:“意象是美及其呈现,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形成的心象,是生命体验和创造的结果。”[38]由“意象是……心象”的表述,可知朱先生所谓“意象”就是一种特殊的“心象”。这个“心象”是一个大于“意象”的上位概念,但什么是“心象”呢?朱先生似乎语焉不详。
笔者讲“语象”“物象”“心象”,是为了恢复古代“言”“象”“意”三元范式而提出来的,既扬弃了“情景”二元范式,亦是强调审美艺术的独特性。古代的“言”“象”“意”三元,在此转化为“语象”“物象”“心象”三元。“语象”之提出,是强调审美符号的对象化、审美化的关键作用;“心象”与“物象”之表述,是对于通常二元模式中所讲的“主”与“客”、“情”与“景”扬弃的结果。从文学审美的独特性说,一切审美对象最终是化为语象,乃至说,文学即“语象学”,就是关于审美语象化、审美化为语象的创造与欣赏活动。文学者,“立言”之学也,旨归是“立审美之言”也。笔者这样讲,并不想重复“语言是存在的家”之类,亦不想把语言绝对化。语言本身是异在指涉符号,即是说,语言总是指涉着异于它自身的他者,若语言失去了这一异于自身的他者,则语言就是空名。因此,讲“语象”既要强调语言符号审美化这一特性,又要强调异在性,强调异于“语象”的“心象”“物象”之存在意义。
“语象”“物象”“心象”三者是同级概念,它们的上级概念是“游观意识”。“游观意识”既能沉潜于三者之中徘徊漫步,又能提升为上层审美视域而统摄三者;“游观意识”与三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为上下阶层之间的回环往复的相依互化运动。由此,所谓“审美意象”就是以一“意”(“游观意识”)摄三“象”(“心象”“物象”“语象”)为基础的上下贯通与三元交融的体验活动及其成果。总而言之,我们讲“审美意象”贯彻了“异在论”的基本理念: (1)“审美世界”异于现实世界,两个世界异质而互联,“象”异在指向“不在场”的“物”; (2)审美意识及其对象化是上下异阶的关系,两者相异而互通,“游观意识”位于上阶,三“象”受其统摄,上下之间回环贯通; (3)三“象”之间是平级概念,三者相异而互化,三元交融,成就“和合”之境。
参考文献:
[1]夏之放.文学意象论[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2]蒋寅.语象·物象·意象·意境[J].文学评论,2002,(3).
[3]朱志荣.论审美意象的创构过程[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5]田义勇.审美体验的重建:文论体系的观念奠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7]怀特海.过程与实在———宇宙论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8]王弼.老子道德经注[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
[9]田义勇.中国古代诗学意象论刍议[M]∥陈飞.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第2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10]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李壮鹰,李春青.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12]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3]黄晖.论衡注释: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5]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6]朱光潜.诗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7]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8]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9]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0]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4分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21]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5分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22]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3]左丘明.国语:下册[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4]叶燮.原诗[M].霍松林,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6]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M].丁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7]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8]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9]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0]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分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31]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4]李继宏,杨建邺,李晓刚.科学意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35]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36]韩经太,陶文鹏.也论中国诗学的“意象”与“意境”说[J].文学评论,2003,(2).
[37]黎志敏.语象概念的“引进”与“变异”[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
[38]朱志荣.再论审美意象的创构———答韩伟先生[J].学术月刊,2015,(6).
[责任编辑赵琴]
【文学研究】
On the Trace of Concept-image and Reflection of its Research
TIAN Yi-y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y,Hangzhou 310012,China)
Abstract:Concept-image is a very core category of academic vitality in China's Aesthetics.Contemporary academic research performance of it is worthy of recognition,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tymology.On the trace of concept-image,the intermediary-reference of image should be focused on.And the Trinity-paradigm of language,image and concept should be recognized again.Simultaneously,the Dualism-paradigm of feeling and scene should be sublated.On the research methods,whether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or ultra-subject-object dichotomy can not really get rid of the stereotype of Dualism-paradigm and fit the reality of Chinese thinking.Based on other-being stand,aesthetic concept-image is one concept unifying three image,such as feeling,thing,and language.
Key words:concept-image; Trinity-paradigm; other-being; Consciousness of you-guan; language-image
作者简介:田义勇,男,河南商水人,浙江大学博士后,浙江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哲学、文艺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4FZW019)相关成果
收稿日期:2015-04-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5-008
中图分类号:I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