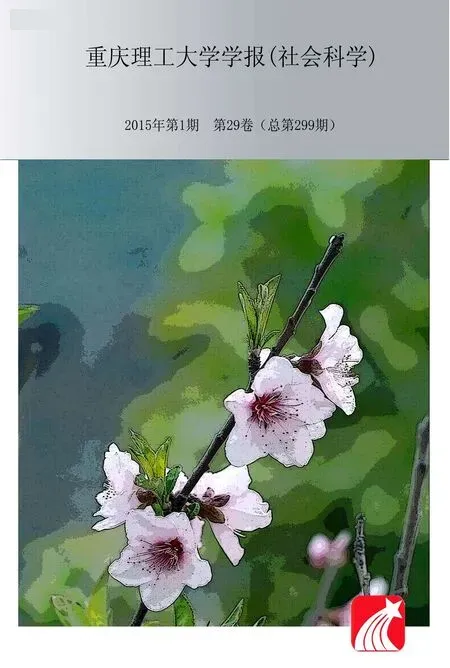“范式”转换:城市文化现代化的重要范畴
王林生
(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101)
文化城市理念确立了文化在城市中的发展导向,并将城市文化视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不仅仅是城市规模和城市居民数量的简单增加,更是城市内部价值观念、人文生态、文化形态、文化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等由传统向现代进行的整体性变革。这种变革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体现为城市文化发展“范式”的转换。尤其在城市文化重要性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城市文化的发展“范式”转换便成为城市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实践。将“范式”转换与城市文化的现代化相联系,不仅是“范式”转换为探讨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一种视角,也在于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一、何谓城市文化的发展“范式”
范式,英文是Paradigm,源出于希腊文,意思是共同显示的模式。美国学者库恩在对科学发展史的研究中提出的范式的概念并阐释其基本特征,认为范式是科学诞生的标志。“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1]在这个论述中,范式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不仅是共同体一致遵守的规范或承诺,也是“具体的谜题解答”过程,即选择了一种范式,便是选择了一种提问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范式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使人们对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有了更为深入的把握,为“典型的问题和解答”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对范式理论的使用也没有仅局限在科学发展史的范围内。
将城市文化研究与范式相结合,是新世纪以来城市研究的重大课题。这一研究认为城市文化的发展及对问题的解决受世界观、价值观的支配,在价值导向和路径选择上能够体现出共同的倾向性。对每一阶段性城市文化发展范式的分析,能够较好地揭示城市在特定时期文化的层次、结构和功能等问题。较早将城市文化与范式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是英国学者兰德利。在《创意城市》一书中,兰德利阐释了后工业社会下城市创意文化的发展范式,提出“后设范式转换”(meta-paradigm shift)、“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等命题[2]。指出任何发展范式都具有周期性和时限性,创意文化城市作为城市的新型发展范式,多围绕文化艺术对城市的资源、空间进行开发和整合,并以此为原则重构了人们对城市经济、环境、社会与文化生活的看法。珍妮特在《范式城市:香港的空间、文化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借用范式概念分析了香港在资本和市场化主导下城市文化的形态和空间布局等问题[3]。从整体上来说,城市文化的发展范式是一定时期内某一或某些城市共同体在文化发展上所遵循的一般价值观念,具有相似的路径选择、发展模式、应用范例等。它不是对某个城市文化特色或风格的具体剖析,而是对整个城市文化进程的总体性关照,是一定时期发展和审视城市文化的方式,规范着城市文化活动的整体性架构。
城市文化发展范式的转换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可以说自从出现了城市,便有了城市文化发展范式的转换。之所以城市文化的范式转换问题凸显出来,就在于现代化进程中全球的城市化浪潮给城市带来了最深刻的变革,同时也衍生出城市可持续性发展、城市“空间缺失”、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特色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当原有的‘城市范式’不能指导并解决现有的城市问题时,就会出现‘城市革命’,发生城市范式的变迁。”[4]可以说,在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城市范式的变迁,城市文化的发展范式也发生着相应的变革。
二、现代化语境中城市文化“范式”转换的特征
城市文化“范式”转换的发生伴随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化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领域流行的术语,由于概念和实践本身的复杂性[5],它至今尚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①罗荣渠从4个方面对现代化的涵义进行了归纳和概括:(1)现代化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2)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3)现代化是自然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过程的统称。(4)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参见文献[5]。但从总体来说,现代化大致是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和文化的整体性变迁。它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之上,是现代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向一切领域扩散的过程,是各领域相互联系变迁的总和,“从这些变迁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和文明类型——‘现代社会’”[6]。城市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进行着范式的转换,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城市文化的“范式”转换体现出以下五大特征。
(一)“范式”转换体现了城市文化现代化过程的集群性
城市文化的范式转换在理论层面存在一个实践共同体,实践共同体的形成标志着某种发展范式已为城市的发展所普遍接受,它们在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方法、手段、过程等环节体现出某种一致性。这一共同体在城市文化的现代化实践中,集中体现为城市的集群化发展。所谓城市文化的集群化,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化基于城市转型发展的需要,采取了相同或相似的发展指向和发展路径。这一结果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城市集群处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圈之内,它们有着相似的文化价值取向、文化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等,大致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且存在相似的问题。以文化圈层来划分,世界大致可以划分为西欧城市群、北美城市群、东亚城市群、南亚城市群、大洋洲城市群、拉美城市群、中东城市群以及非洲城市群。如东亚城市群形成了以儒学文明与现代性有机融合为特征的“东亚现代化模式”[7]。需要指出的是,城市集群或城市共同体在城市文化发展范式的选择上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即共性是针对区域而言的,在整个大的文化圈之内显现出共同或相似的特征,而个性则是根据城市的实际在选择路径的策略或侧重点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差异。如“东亚现代化模式”中存在“韩国模式”“日本模式”“香港模式”“新加坡模式”等。
(二)“范式”转换说明了城市文化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
城市文化的发展范式是城市共同体在某一时期内的集体承诺,当城市的情势发生改变,城市文化的发展范式便随之发生变化,并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从总体上来说,这种阶段性与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出的阶段性是同步的。从世界范围来讲,依照城市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城市文化现代化在发展范式上大致体现为从农业乡村文化范式向城市工业文化范式(18世纪60年代—20世纪50年代)和后工业城市文化范式(20世纪60年代—)转变。
城市工业文化范式紧密围绕机器大工业,坚持功利主义的价值导向,将工厂视为城市的组织核心。芒福德对这一时期的城市文化做过这样的描述:“芝加哥的摩天大楼必须与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工厂、水晶宫、纽约的布鲁克林铁桥,以及紧随其后的追随者,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一起相提并论。这些都是当时新的工业技术和机械文明所特有的强权和秩序的象征。这些建筑物或者构筑物,都是设计建造出来专门用以强化这个时代的组织化机械生产方式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显示技术的高超成就:都是合理的目标所要求的合理手段。”[8]244可以说,各种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业化建筑构成了城市最鲜明的特色,代表了一种“钢铁的胜利”。从审美视觉的层面看,工业城市文化在外观上机械规整,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倾向较为突出。
后工业城市文化范式以信息和知识为中心,文化资源和创意性人才取代煤和钢铁成为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在后工业城市中,城市文化资源是历史、工业与艺术遗产,都市建筑和标志性景观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节点,它们与城市的文化传统、节庆活动、风俗习惯、历史传说等一起构筑起了多样的城市文化生态。通过文化的创新与创意,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文化资本,并以此为基础激发出城市的活力和创造力,积极推动城市功能从产品生产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实现城市发展的创新与变革。
(三)“范式”转换解释了城市文化现代化的内在机制
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在城市文化的范式转换过程中,受到现代化整体进程中两种力量的推动:内源性动力和外源性动力。内源性的动力源于自身,是自下而上的渐变过程,而外源性动力来自外部,是自上而下的剧变过程。严格意义上来说,两种推动力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在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范式转换呈现出一种由“反常”到“平衡”的内在发展机制。所谓反常是对旧的发展范式而言的,即在城市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城市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转移或外部力量的强势进入,新的文化质素出现在固有的文化框架和范畴之外,并开始打破固有的城市文化观念或文化形态,使原有的城市文化生态出现一种反常。如当城市工业化的进程刚刚开始之时,“原有的开放空间被盖满了建筑物,旧有的建筑物被匆匆忙忙拆掉;整齐的中世纪市场被改建成尘土飞扬的购物区,安谧、恬静、自成一统的居住区,如今遭受过境交通车辆的侵扰,因为原有的老式街道网络都要服从新的交通规划,通盘予以展宽取直”[8]230。这种反常发展到一定程度,旧有的城市文化模式和生态便面临一种发展的危机。随着新质素在城市文化生活中的逐步深入与融合,新的文化质素逐渐代替旧有的文化质素成为城市文化的核心,城市文化生态从反常逐渐过渡到一种平衡。可以说,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化发展范式转换的过程,就是一个城市文化的发展出现“反常”,到城市文化生态出现“危机”,进而再达到一种“平衡”的过程。
(四)“范式”转换展示了现代城市主导文化的多样性
城市文化的范式转换是一个在多种因素交织的环境中不断探索的过程,库恩曾指出:“使范式与自然界相契合中总会有种种困难存在;其中的大多数困难或迟早会被正确地解决,而解决的过程往往是不能预见的。”[1]而这种不可预见性在现代化的实践中表现为城市主导文化的多样性。多样性的成因:其一,城市和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都是丰富性、复杂性,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其二,城市本身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可依赖的文化资源、文化优势、发展机遇等各有差异。布莱克认为:“在谈及现代化的过程时,必须要考虑到它的普遍特征、各种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的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根本差异,同时还要考虑到在社会之中和社会之间进行决策的领导的重大作用。”[9]其三,在文化城市理念主导下的城市发展中,文化已不再局限于文化领域本身,而成为了与经济、科技、旅游、商务等相融合发展的范畴,这就增加了范式转换路径选择的可能性。如伦敦选择了创意文化,提出要将伦敦打造成英国乃至世界创意之都;东京选择了动漫文化,且将动漫文化视为整个“酷日本战略”的核心。可以说,当代城市文化的范式转换,已将具有某种城市特质的文化提升到城市发展的关键性位置。城市文化中主导文化类型的多样化发展充分说明,在城市发展的现代化实践中,城市已充分注意到城市文化的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并将挖掘和打造城市特色文化视为发挥城市竞争优势、塑造城市文化品牌的重要手段。
(五)“范式”转换中城市文化的现代化呈现出从生产型向消费体验型转变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化发展范式的主导性因素由生产型逐渐转向服务、消费体验型,它是对经济转型发展的真实反映,即在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发展之后,体验经济正成为时代的“新宠”。体验经济之下的城市文化发展范式,文化不仅参与城市经济活动,而且发展成为了具有娱乐休闲性质并注重体验的产业形态。在文化产业的市场运行中,“不管这些文化产品的物质——经济构成如何,制造它们的部门都创造了可销售的产品,这些产品的竞争品质依赖于这样的事实:它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个人装饰品、社会炫耀方式、娱乐消遣形式或信息和自我意识的来源发挥作用”[10]。消费体验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核心,它以娱乐为手段,将城市文化建设与消费者、娱乐者相联结,并在二者的互动中,城市不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容器”,而是成为了消费和体验创意的载体。
现代化是一个没有明确终点和时限的过程,它的特殊性意义就在于它的动态性特征以及对社会发展影响的普遍性。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城市文化的范式转换始终处于一种进行时态。在不断进行的范式转换过程中,城市文化的空间形态、组织结构、作用功能等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彰显出不同的时代表征。
三、城市文化“范式”转换的本质
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范式转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特征,它不仅说明了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也反映出城市文化多样化发展的真实际遇。从总体来说,城市文化的范式转换并不遵从单线性因果式的发展逻辑,即新范式代替旧范式之后,旧范式就彻底消亡,而是旧的范式不再占据城市文化发展的主导,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隐性因素,即从某种本质意义上说,城市文化的范式转换是主导城市文化发展要素“背景—突前”的配置关系。
城市文化的构成是多元的,各种文化要素以不同的配置组合存在于城市现代化的实践中。作为一种可以解析的文化形态,在不同的层面具有不同的内涵。如以历时发展轨迹为标准包括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以表现形式为标准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以内容结构为标准包括表层文化(城市的建筑、商品以及被人工改造过的自然环境)、浅层文化(城市人进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种活动)、中层文化(城市的各种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管理功能和人际关系)和深层文化(城市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及心理意识)等。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城市文化由初级发展为高级,由简单发展为复杂,且各种文化要素之间相互交织。由于受制于城市本身的文化传统、文化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等,在现代化的实践中,当社会发展形势出现了改变,固有的文化发展范式出现了“反常”,从而进入一种非常态的发展语境需要某种新的文化要素发挥作用时,某种文化要素便具有一种相对优势并在多种文化要素中突前出来,如为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而出现的创意文化,为适应全球化需要出现的网络文化等。芒福德曾指出:在每一个城市的有机体中,“组成代谢过程与分解代谢过程、创造力量与破坏力量,两者都一直在起作用。生命和生长发展不取决于有没有不利因素,而取决于有足够程度的平衡,以及有足够多余的建设性力量去不断纠正、恢复,去吸收新鲜事物,去调节数量,去与所有别的需要维持平衡的有机物体和社区建立平等交换关系。大都市生存中的不利因素,假如在城市扩展中不让它们占优势,并且不让它们在破坏过程中所占的支配地位永久化,那末,它们也许可以为更高的发展提供条件”[11]。可以说,突前的文化要素即是一种有利于城市文化发展的具有创造性力量的元素,它之所以能够凸显并成为城市某个阶段或时代的主导,是因为在城市文化有机体的代谢中,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可以推动城市文化的有机体从“反常”走向一种新的平衡,从而完成城市文化新的配置。
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化诸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中,成为“突前”要素的有多种可能,这其中有一个删汰、选择的过程。尤其是在当代文化城市理念的宏观语境下,城市究竟选择何种文化类型作为自己城市的文化“主打”品牌,是一个构建与城市自身发展实际相符合的“对位性机制”的过程。
当支配城市文化发展范式转换的某种主导性因素凸显时,其他文化要素便成为背景隐藏在突前要素的背后。而当社会实践出现“反常”,作为背景性的文化要素突前成为拥有相对优势性的地位时,原来主导性的文化因素则转化为背景,城市文化要素间的关系在新的突前文化要素的主导下重新组合,回归一种新的平衡。罗宾斯和埃尔-库利在论述由工业文化城市向网络文化城市的转变时认为:“家庭、工厂、学校、工业化城市,当然还有城市规划过程都处在分崩离析的不同阶段,都反映出网络城市带来的规训崩溃。……影响行为的规训社会已经让位于数字社会,它借助计算机技术来进行调节控制。我们已经从需要纪律严明的劳动力和高效规划与组织的城市生产机器,进化到由全球电脑网络定义的空间流。”[12]在这一引文中,计算机技术作为网络文化城市的主导性因素取代了固有的工业城市规训,并重构了城市的文化组织方式。
可以说,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化范式转换的过程是由文化要素之间“背景—突前”的不断转化完成的。在社会学或文化学领域内,这种发展范式的转换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中新学说的出现就意味着旧学说因丧失了现实的针对性而被淘汰,而城市文化的发展范式转换,仅是原来具有优势性文化要素失去了主导性的地位,从而转为一种隐形或非主导性的存在。如在追求创意文化的城市中,工业文化、传统文化仍然存在,仅是与创意文化相比不再具有优势性地位了而已。易言之,现代化城市文化的范式转换绝不是一种范式打倒另一种范式,不是一种线型的因果替代关系,而是对城市文化发展进程中不能适应现代化的不合理部分的一种否定或抛弃,其中合理的部分不仅能够融入新的发展范式之中,而且能够与新的主导元素和其他要素共存。
[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英)查尔斯·兰德利.创意城市[M].杨幼兰,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276.
[3]Janet Ng.Paradigm City-Space,Culture,and Capitalism in Hong Kong[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9.
[4]鲍宗豪.城市范式变迁与可持续城市化[J].上海教育,2008(S1):37-38.
[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7-13.
[6](意)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M].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6-17.
[7]董正华.世界现代化历程·东亚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5.
[8](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M].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9](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段小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18.
[10](美)艾伦·J·斯科特.城市文化经济学[M].董树宝,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
[11](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M].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568.
[12](英)爱德华·罗宾斯,鲁道夫·埃尔-库利.塑造城市——历史·理论·城市设计[M].熊国平,译.北京:中国工业建筑出版社,201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