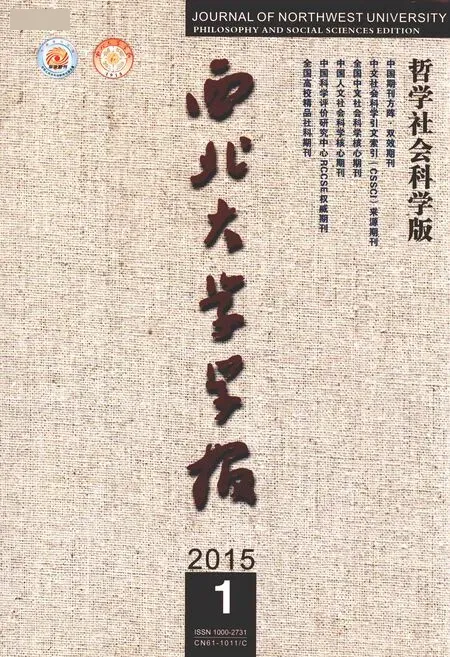论宪法权威的自我保障制度
魏治勋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法学研究·纪念“五四宪法”颁布60周年】
论宪法权威的自我保障制度
魏治勋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必须具有最高效力和最高权威,任何与宪法相冲突的立法和公权行为都必然因违宪而无效。维护宪法权威绝不能借助于个人权威,而必须依靠健全的宪法保障制度建设才能达成,此一方面的任何“天衣之缝”都可能导致宪法权威的崩解。对于致力于依宪治国的中国立宪实践而言,建立健全宪法自我保障制度乃是维系宪法权威的唯一路径选择。
宪法权威;宪法自我保障制度;天衣之缝;依宪治国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人民权利的权威载体和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因而,宪法必须具有权威性,相关国家制度必须确保宪法的权威性。这其中,作为最高规范的宪法首先自身应当承担起自我保障其权威的职能。否则,宪法将无异于仅仅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①列宁在讥讽沙皇专制政权实行虚伪立宪欺骗愚弄人民时写道:“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50页。 中国学者认为,宪法的核心命题就是“限制公权,保障人权”。“宪法本质上就是一部保障人权之法”,就此而言,真正的宪法“不仅仅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参见张郁:《宪法不仅仅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大元》,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11期。,而不会真正发挥规范政治社会生活的作用。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郑重提出“依宪治国”的情境下,回顾近代以来东西方立宪的理论争论与实践探索,并以史为鉴,梳理并提出当代中国宪法权威保障的制度之道,其现实意义殊为卓著。
一、证立模式之辩:宪法到底要求什么样的权威?
综观世界各国近代以来的立宪历程,几乎所有类型的政体都颁布过宪法,而当今世界各国也无一例外地都拥有自己的宪法。但时至当下,宪法具有权威性并根据宪法建立起稳定的立宪政治体制的国家,却仍旧只占少数,得到世界各国广泛认可的宪政国家也不过几十个;包括中国、泰国等经历了百年立宪历程的国家,迄今仍未能走向成熟的立宪政治之道。这样看来,立宪政体的建立和宪法权威的铸成,乃是一件极易反复、殊为艰难的政治筹划。相反,精心构造的立宪体制的倾覆,却是一件较短时间内就容易实现的目标,无论“魏玛宪法”及其立宪政体还是中国的“五四宪法”及其开启的立宪模式,都在较短的时间内被推翻或践踏,在东西方立宪历史上留下了令人警醒的一笔。
那么,为什么宪法权威的建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殊为不易的艰巨工程?为什么宪法权威的败坏和立宪政体的倾覆却又是较易实现、短期可成?难道人类一定要追寻一种根本上困境重重的政治法律生活形式吗,一如立宪与法治的曲折历程所昭示的那样?
宪法权威这一概念,涵括的是宪法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生活行为基本依据和准则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宪法权威意味着:与普通法律不同,宪法规范不仅是有效的法律规范,而且是统帅整个法律体系的最高性规范;宪法对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权机关、党派、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都具有最高的拘束力;任何与宪法相冲突的立法和行为都是违宪的,因而必然是无效的。从社会影响力的角度看,宪法权威还体现为整个社会对宪法的信仰和拜从。正是由于宪法的至上权威性,宪法才能够成为公民权利得以保障和立宪体制得以矗立的基石。
英国宪法学家惠尔(K. C. Wheare)认为,从理论上看,宪法权威得以证成,主要有三种立论的模式:第一种立论模式是以美国宪法理论为代表的道德论证,这种道德论证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将宪法权威和政府权力来源归结于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论,认为正是人在自然状态中拥有的自然权利构成了宪法权威的基础和政府权力的来源,“它提供了判断政府行为的道德基础;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校验宪法效力的道德基础。”[1](P61)自然法由此构成了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其二,宪法权威性所要求的服从,根本上在于它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凡人民所规定之事项,即约束每个人。”[1](P58)第二种立论模式是基于“情境逻辑”(logic of the situation)的回答:既然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创立了这个国家的政体结构,包括最高立法机关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关都是宪法的创造或基于宪法而成立。那么,宪法显然要比它创设的机关优越,因而宪法必定在效力等级上要高于法律,更不用说行政和司法机关创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由此,宪法必然是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居于最优越地位的规范形式;如果不是这样,则“宪法和制宪就没有意义”。第三种立论模式则是将某种规范的效力等级与制定该规范的机构的权力位阶相联系,由此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就取决于制定它的机构的权力等级的最高性。近代以来的主流政治法律理论将人民尊奉为唯一真正的主权者和立宪主体,而在施密特(Carl Schmitt)看来,人民主权在内容上完全等同于人民立宪权。既然人民是国家主权权力的最高持有者,当人民将其主权权力以立宪程序予以规定和落实,则人民就转化为权力效力等级最高的规范体系的创立者。宪法的最高效力和最高权威的地位,根本上取决于它是人民这一具有最高权力等级的主体的创造物。概括起来,宪法最高权威的证成,其基础在于它是人民基于维护其自然权利的社会契约的产物,在于它应当高于它所创制的一切国家机关的优越地位,在于它是国家主权拥有者的人民的创制物。实际上,一部宪法要真正具有最高效力和最高权威,以上三个方面的基础都是重要的和具有论证效果的。
凯尔森(Hans Kelses)则从实证主义出发,基于法律与道德相分离的实证主义前题,为宪法规范的最高性提供了“动静结合”的论证:从静态上看,任何一个法律规范都可以上溯到一个上位规范,进而能够上溯到宪法规范,虽然宪法规范又可以追溯到基础规范,但在实证法范围内,宪法规范无疑是最高的;而从动态的角度看,正是宪法规范的具体化才派生出法律,法律又进一步逐级派生出下位规范。因而,无论从动态还是静态的视角看,法律体系都被认为是一个以宪法为最高效力等级并统帅其他法律形式的规范体系[2](P126-128)。同时凯尔森还注重从制定和修改程序方面论证宪法的最高性,正因为宪法规定了比普通法律更加严格的制定、修改与废止的程序,它才为宪法权威预置了自身规定性[2](P142-143)。这样,在凯尔森的理论体系中,宪法权威的最高性就获得了一个较为完备的证明,可谓是宪法权威理论证立的实证主义版本。
宪法必须成为社会的最高权威,否则依宪治国和法治国家只能成为空想。学者指出:“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那么这个社会就肯定不是法治社会。”[3]因而,法治社会必然意味着这样一种秩序状态:“它要求全社会形成的主流法治信念为:只承认法律一种权威。”[3]在视宪法为最高法律的语境下,法治社会必然以承认宪法具有最高权威为前提。宪法的最高权威性是人民主权和人民意志至上的制度体现,在现代社会,“一个合法的政治社会应基于人民的同意,这种同意应在人们为建立政府而达成的社会契约中反映出来。这种社会契约通常采取宪法的形式,而宪法又会确定政治构架及其建制蓝图。通过立宪性契约,人们同意受统治。将成立的政府官员们则需要作出承诺,尊重宪法蓝图及其对他们的限制。”[4](导论P7)可见,对宪法权威的尊崇构成了现代法治国家的秩序基础和信念之源。
二、宪法权威如何保障:靠人还是靠制度?
与理论上的证成相比,宪法最高权威在宪法实践中的树立及对其具体模式的寻求,却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情,它既依赖于完备的宪法权威保障制度的设计,更取决于宪法实践对这些保障制度的完整落实和最终确立。在这里,选择什么样的宪法权威保障模式成为了问题的关键,它直接关系到宪法保障实践的效果和立宪政治的成败。
现代社会关于宪法保障或曰“宪法的守护者”*凯尔森明确指出:“‘宪法的守护者’:在原初意义上是指一个机关,其功能在于保护宪法以免受侵犯。因此,人们也称其为,而且确言之常常称其为‘宪法保障’”。汉斯·凯尔森:《谁应成为宪法的守护者》,张龑译,载《历史法学》(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页。实践模式之争,不过是以一种言辞对抗的集中形式表达出一个社会对于宪制非常状态及其走向的焦虑,按照施密特的说法,“对于宪法守护者或维护者的呼声经常是宪法状态危机的一种表征。”[5](P1)20世纪初叶德国国内关于宪法保障制度的讨论正是在一种颇具挫折性的制度转折背景下展开的:议会民主体制的拥护者力图寻求新的出路以克服其缺陷,而推崇威权体制的思潮则企图在宪制外衣下引进打破宪法固有架构的手段并为之作论证。在1929年的德国全国宪法学者大会上,施密特抛出了通过强化总统权力使之成为强有力的“宪法的守护者”的威权论观点。在随后出版的《宪法的守护者》(1931年)一书中,施密特为其“宪法的守护者”命题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证。施密特指出,近代德国自进入立宪体制以来,在谁是宪法权威的守护者这一问题上一直陷入混乱之中:一方面,人民或许出于政治秩序安定或者维护公益的想法,努力避免将宪法守护者议题政治化而规避讨论;另一方面,魏玛宪法的制定和实施进一部引发了谁是宪法守护者的疑问,基于不同的理由不同权力部门诸如国事法院、帝国法院、宪法法院、帝国裁判法院、帝国行政法院、总统、议会都自称或者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宪法的守护者”。对于这种理论与实践中的混乱状况,施密特力图寻求到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他认为:“我们所应采用的做法,不应该是使其他的国家活动领域取得单纯补充性的随附效应,而是要组织一个特别的设置或机制,使其承担确保不同权力部门依据宪法而运作、并且捍卫宪法之任务。”[5](P189)因此,“宪法的守护者”的设置必须避免某一权力部门因之取得相对于其他部门的优势地位,否则它就成了“宪法的主宰”。为此,他主张选择一种能够超越于其管辖权范围之外的具有特殊性质的权威充当“宪法的守护者”,这一特殊存在就是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在施密特看来,国家元首不但具有超越于各具体权力部门的权威,“展现着国家统一体及其统一的运作方式”,而且其道德声望以及这一职位独具的斡旋性、维护性、中立性、规制性、连续性、恒常性等特质,使得总统不但不会与各个权力部门形成竞争关系,反而成就了其在权力分立体制中的不可或缺的优越地位。尤其是,宪法所赋予的由总统实施紧急状态的权力,使之“能够成为宪法的积极屏障”,而其他权力部门因自身缺陷都无法承担此一重任。因之在施密特看来,只有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具有成为“宪法的守护者”的资格,这一设置不但完全“符合作为魏玛宪法础石的民主原则”,而且,“宪法特别尝试着让帝国总统之权威有机会能直接与德国人民之政治总意结合,并藉此以宪法统一体之守护者、捍卫者及全体德国人的身份而行动。”[5](P216)因而可以说,“在魏玛宪法的现行内容中,已经存在着一个宪法的守护者,也就是帝国总统。”[5](214)就这样,施密特将“宪法的守护者”重任托付于总统这一个权威人,并为之作出了基于德国复杂政治现实需求的理论论证。
凯尔森同样认为宪法权威天然需要一个守护者,因为“缺乏保障的宪法,对违宪立法无能为力的宪法,是没有约束力的。”不过他所看重的这个守护者却是制度而非个人权威,因而他不可能赞成施密特的方案。在凯尔森看来,施密特“试图扩大帝国总统的权限”,将总统塑造成“国家的主权统治者”,“这一地位无论如何同宪法保障者的职能是不相一致的。”[6](248)凯尔森同样也不赞同美国式的通过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保障宪法权威的实践模式。在凯尔森看来,美国的司法审查模式具有三个方面的缺陷:其一,美国式的由一般法院实施的分散审查模式,从根本上讲并不利于宪法权威的确立和宪法效力的维护,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解决方法的弊端在于下列事实,即不同的法律适用机关可能对立法的合宪性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因而一个机关可能会适用立法,因为他认为立法合宪,而另一个机关却基于其所宣称的违宪性而拒绝适用。对立法是否合宪——即宪法是否受到侵犯的问题缺乏统一决定,乃是对宪法权威的极大威胁。”[7]凯尔森的这一判断并非空穴来风,1896年的“Denney v. state”一案的发生充分证明了凯尔森的预见。其二,美国式的司法审查模式在审查启动程序上具有偶然性,原因即在于违宪审查的提起只有在审理普通案件的情形下才会附随发生,因而并不能一般性地消除违宪立法的存在。凯尔森指出:“立法的合宪性是一项公共利益,而后者不一定和有关当事人的私人利益相重合。正是公共利益才值得通过符合其特殊性质的特殊程序而加以保护。缺乏这种程序的端着受到美国法学文献的普遍承认。”由此可见,美国司法审查启动机制的偶然性与公共利益的普遍属性难以耦合,这是美国式宪法保障的又一重要缺陷[7]。其三,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容易造成社会秩序的失范。凯尔森指出,合理的违宪审查应当满足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在因违宪而被撤销的立法取代了先前的立法或普通法规则的情形中,更好的办法是恢复先前的立法或先前有效的普通法规则,而不是让法律状况变成该领域不受任何法律调控。”[7]显然,美国式的附随诉讼案件偶然启动的司法审查模式,并未对违宪法律被撤销后相关领域的失范状态作出制度上的应对,从而为社会失序开启了可能性的大门。基于上述原因,凯尔森不赞成美国式宪法保障模式,而主张建立一个与代议机关平行的专门性的违宪审查机关来保障宪法权威,此即在奥地利首创的宪法法院违宪审查模式。
当然,在同时代关于宪法保障制度及其机构设置的问题争论方面,施密特和凯尔森的观点都不具有唯一性[8]。在世界各国的宪法保障实践中,司法审查模式、宪法法院模式、宪法委员会模式以及议会审查模式,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宪法保障模式,是维护宪法权威和宪法最高效力的基本制度设置。这些不同类型的审查模式各有其优势,在维护宪法权威的实践过程中,都发挥了其制度性约束力。
三、宪法权威的毁灭:祸起“天衣之缝”
一个国家其宪法权威的树立和长期存续,并不仅仅依赖于某一项单一的宪法保障制度的设计和落实,而是更多地取决于整个宪法保障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只有当一个国家建立了多层次的、环环相扣的、致密的宪法权威保障制度体系,同时要求具有稳定而良好的制度运作机制并固化为某种尊崇宪法的传统之后,一套维护和维系宪法权威的“无缝天衣”才会最终形成,宪法权威从而宪法之治才会走上持存之道。然而不幸的是,并非每个迈向现代化征程的国家都能够像美国那样较早就能够相对顺利地确定一套完善的宪法保障制度,而更多的国家在立宪之路上经历了反复和挫折,无论是近代法国和意大利那样的宪法频繁立废,还是中国、韩国、泰国等亚洲国家在立宪道路上历经的曲折,都表明了确立和维护宪法权威的巨大难度。
至于开创了近代宪法新趋势的魏玛宪法,曾被认为是20世纪最民主最自由的宪法之一。这部宪法“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9](P85)。但这样一个设计良好的宪政体制在短期之内就被彻底推翻,却仅仅因为其宪法保障制度存在一条细微的缝隙,这就是:魏玛共和国在其三权分立体制设计中,为总统专门规定了所谓的“紧急命令权”,这一特殊权力的存在使得总统权力不断走向集中,从而威胁到了三权之间的制衡关系。随着共和国政治生活的非正常发展,总统行使“紧急命令权”的次数急剧增加,最终超越并压倒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从而为纳粹党人最终埋葬共和体制奠定了合法手段和规范依据的基础。可以说,正是总统享有的“紧急命令权”这一宪法保障制度的“天衣之缝”,成为颠覆宪法权威的制度之源,而其更深远的源头,则是存在于德国立宪理论中的过于推崇威权式的“宪法的守护者”的倾向。其实,早在凯尔森对施密特理论的批判中,已然明确指出其宪法保障方案中蕴含着一种危险:将宪法权威托付于某一高度集权的个人,这种做法“清晰地暴露出君主作为宪法守护者的立宪学说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特征。”[6](P248)而当施密特将其理论发挥到危险的极端,以至于认为“领袖的行为是真正的司法。它并不隶属于司法当局,本身便是最高的司法当局。”[10](P202)同时,现实政治生活又越发脱离正常轨道,魏玛宪法的真正危险也就难以避免了。
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同样被广泛认为是一部基本内容良好的宪法,但由于宪法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太多的“天衣之缝”,使得这部宪法短期内即遭遇不宣而废的命运。概括地讲,“五四宪法”在实体内容上暴露出的“天衣之缝”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五四宪法”对国家机关的权力缺乏明确的限制。“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国家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向它报告工作,而没有对其权力限制的明确规定,这就赋予了全国人大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对其他国家机关权力限制的规定同样付之阙如。其二,“五四宪法”没有对执政党地位作出任何规定,没有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和宪法的关系,致使“在实际生活中党和党组织往往处于宪法之上,不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事,结果只能使宪法虚置。”[11]尤其是“五四宪法”未能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和权威作出明确有效的限制,也没有对其任职期限和任职次数作出任何限制,致使领导人的个人权威凌驾于党的权威之上,而党的权威又无法受制于宪法的规定,这就使得“‘五四宪法’在公意之外,又设置了一个权威渊源。这进一步降低了宪法文本本身的权威强度。”[12]其三,“五四宪法”对其自身效力和权威的保障条款缺乏完善规定,仅规定全国人大行使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以及宪法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有关政党、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遵守宪法和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条款,当然也没有规定对违宪行为追究宪法责任的制裁条款。“五四宪法”仅颁行三年就遭遇被实际废弃的命运,不能说与这部宪法的保障制度存在的诸多“天衣之缝”没有必然的关联。
四、重构宪法保障制度的“无缝天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检讨东西方立宪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梳理并重构一个完善的宪法权威保障制度体系,对于坚定地走向依宪治国之路的当代中国而言,实在是至关重要的。但一个较为完善的宪法权威保障制度体系,必须在充分考虑中国社会历史和制度环境的基础上加以建构,以增强这一制度的适应力和实效性。从根本上说,宪法权威的保障只能求助于宪法自己,因而宪法保障制度就是宪法自身规定的保障宪法权威的规范体系。这个体系包含复杂的制度内容,应当逐步通过完善宪法规范的途径表达为有效的宪法条款。具体而言,宪法权威的自我保障制度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应加快基本权利立法,通过完善基本权利体系形成制约公共权力的有效屏障,有助于维护宪法的权威。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尚不十分完备的情况下,仍然有多项权利长期停留在宪法的字面上而无法发挥实际的效力,原因即在于,我国的宪法对基本权利的规定采取了“抽象的基本权利”的模式,这一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抽象的基本权利规范对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社会主体没有直接的实定效力,它既不能被执法机关直接执行,也不能被司法机关直接适用,更不能被公民作为权利救济的直接依据来引用,而只能作为立法机关基本权利立法的依据和效力来源。”[13]因而,“在立法机关立法之前,公民基本权利必然是一种只能主张却不能诉诸法律实践的、徒具形式的纸面上的权利。”[13]在立法机关即使消极立法也不会承担宪法责任的既有制度架构下,公民基本权利得不到立法的落实成为中国宪法实施的一个重大障碍,其对宪法权威的自我保障同样构成一个重要缺陷。这是因为:“宪法权利塑造的是积极的公民和有活力的公共生活,注重政治制度的结构性品质,这种公共性有助于中和那种把权利诉求自利化、极端化的倾向。”[14]一种有活力的、积极的公共生活的建构是以公民享有健全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的,这种积极的公共生活通过明确基本权利边界构成了对公共权力的重大限制。正如学者所言,“从结构性观点来看,现代宪法争议的关键问题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如果说政府侵害了宪法权利,它们都不过是在问政府是否逾越了权力的边界,而不是在多大程度上没能满足个人的什么要求。”[15](P25)制约公共权力是一个国家立宪制度得以健康维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因而,宪法要想真正建立起至上的权威并使之长盛不衰,就必须将完整的基本权利赋予公民并推动其立法实现,由此将基本权利立法的责任条款写进宪法就具有了重要意义。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这就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落实提供了有利契机,有助于宪法权威保障制度的建构和逐步展开。
其二,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落实公共权力的宪法责任。违宪审查制度是宪法权威自我保障制度的核心所在,没有这一制度的确立,宪法权威和宪法的最高效力就无法得到保证。学者指出:“无论基于何种宪法观念,宪法权威的实现、宪法制度的实施都是‘宪政’的应有之义,合宪性控制的具体制度设计可能存有差异,但本质上均需保障公民权利、控制国家权力。”[16]宪法控制国家权力基本边界的兜底性方式就是审查其运作行为及其结果的合宪性,通过将与宪法相违背的公共权力行为及其结果宣布为违宪,就能够牢牢地控制国家权力。宪法权威的成长和维系,根本上依赖于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程度。现行中国宪法虽然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并在宪法实践中形成了对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进行合法律性审查的有效制度,但按照违宪审查的一般理论和普遍实践,这种仅对下位法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合法律性审查的制度实践,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违宪审查,真正意义上的违宪审查的核心必须是以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为基本审查对象。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这一要求表明,执政党已经把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纳入宪法监督制度的设计中,这就为中国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违宪审查制度提供了基本指针。在此基础上,有关追究和落实违宪责任的宪法制裁条款的制度建设也应当逐步提上日程,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其三,进一步完善宪法规范变迁的制度和程序,拒绝非规范的宪法变迁和宪法破坏。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立宪历程历经艰难曲折,期间以非规范的宪法解释、宪法修改和宪法惯例导致的宪法危机事件并不少见,其根源即在于宪法对于其自身规范变迁缺乏完善合理的制度和程序性规定。具体而言,在宪法解释方面,我国现行宪法在启动宪法解释的机制方面缺乏完善规定,宪法解释权基本上处于虚置不用状态,宪法解释的程序尚不完备,没有具体规定宪法解释的提出程序、审议程序、表决程序,没有规定宪法解释的效力,亦缺乏对宪法解释功能的评价系统的设计和规定,这就使得我国宪法解释制度无法成为一种常规性的、有效的宪法保障制度;在宪法修改方面,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宪法修改的启动程序,但在宪法修改实践中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案、全国常委会接受后提出修宪草案的机制,并成为中国特有的宪法惯例,但这一宪法惯例却使原有的宪法修改条款成为具文。我国宪法解释与宪法修改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无疑是宪法自我保障制度迄今仍旧未能弥补的“天衣之缝”,不仅无助于宪法效力的发挥和宪法权威的树立,而且还可能为非规范的宪法变迁敞开了大门;只要相关制度一日不予完善,宪法权威流失的危险就始终存在着。因而,适时地完善宪法规范变迁的制度措施,尽快地弥合宪法保障制度尚存的诸多“天衣之缝”,应当是我国目前宪法保障制度建设的当行之要和当务之急。
必须予以补充的是,将宪法权威得以建立和维系的根本完全托付于宪法自身保障制度而非外在于制度的人格性存在,虽然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但却仍旧不是事物的全部。徒法不足以自行,宪法法律得以发挥效力的能动要素还是人本身。既然,“我们很难找到一种谬论,它比下述主张对于所有的秩序和美好事物以及人类社会所有的和平和幸福,更具有颠覆性。这种主张认为,任何人类群体皆有权制定他们喜欢的法律;或者说法律不论其内容的好坏,皆可以从法律制度自身获得一切权威性。”[17](P322-323)那么,在行宪过程中,必须全力提升公民的宪法意识,努力为依宪治国培育合格的公民,这才是树立和维系宪法至高权威的真正的“无缝天衣”和最为深厚的基础。
五、小 结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法律秩序的基础和公民自由权利最权威的渊源,可以说树立宪法的至上权威根本上就是赋予权利和自由以最为尊贵的地位,本质上乃是公民的自我加冕并为加冕仪典创造条件;在另一层面上,“既然宪法是被提请并接受大众的批准的,宪法就最终是源自于人民的。”[18](P8)在此意义上,所谓宪法保障制度,“最终不过是人民对自己的审查而已。”[18](P8)但无论宪法的至上权威之于人民自由权利的等值性,还是宪法保障制度之于人民自我审查的同构性,问题的关键仍旧在于,宪法权威只可能奠基于坚实而有效的自我保障制度之上,这种看似自我循环的逻辑并非没有意义,而是揭示了现代制度的一个基本特性:“实践理性仅需它自己的解靴带就能将自己拔地而起。”[19](P3-4)因而,处于最高效力等级的宪法欲建立和维护自身的权威性,就必须自己求助于自己。这一规定性充分显示出宪法保障制度建设对于宪法权威建构的构成性意义,这一认识对于致力于依宪治国和“法治中国”目标的中国而言,同样具有适用性。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为宪法权威的维护和强化开辟了新时代,全会决议郑重宣称:“坚持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明确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全会决定,“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完善以“所有规范性文件”为对象的合宪性审查制度,设立“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随着这一系列强化宪法权威的措施逐步制度化并有可能最终入宪,一个中国特色的宪法自我保障制度体系渐趋完善,这将是中国坚定地走向“依宪治国”通途的最重要、最强有力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
[1] K.C.惠尔.现代宪法[M].翟小波,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汉斯·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
[3]徐显明.论法治构成要件:兼及法治的某些原则及观念[J].法学研究,1996,(3).
[4]路易 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M].邓正来,译.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6.
[5]卡尔·施密特.宪法守护者[M].李君韬,苏慧婕,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6]汉斯·凯尔森.谁应成为宪法的守护者[M]∥张龑,译.历史法学:第一卷.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7]汉斯·凯尔森.立法的司法审查:奥地利和美国的比较研究[J].张千帆,译.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春季号).
[8]骆正言.凯尔森宪法保障思想的逻辑:兼评施密特及中国的政治宪法学[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9]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
[10]卡尔·施密特.论断与概念[M].朱雁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刘政.1954年宪法施行三年后为什么被逐渐废弃[J].中国人大,2002,(14).
[12]周林刚.宪法概念的变革: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6).
[13]魏治勋.全面有效实施宪法须加快基本权利立法[J].法学,2014,(8).
[14]姜峰.宪法权利:保护个人还是控制国家?[J].读书,2014,(4).
[15]ASHUTOSH BHAGWAT.The Myth of Rights :The Purpose and Limits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16]夏小雄.凯尔森的“宪法司法保障理论”:理论阐释和效果分析[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1,(春季卷).
[17]EDMUND BURK.Tract on the Poperty Laws,The Works of Edmund Burke[M].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67.
[18]JOHN HART ELY. Democracy and Distrust[M].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9]AMANDA PERREAU-SAUSSINE, JAPES BERNARD MURPHY. The character of customary law: an introduction[M]∥The Nature of Customary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责任编辑 霍 丽]
On the Self-Guarantee System of the Authority of Constitution
WEI Zhi-xun
(LawSchool,ShandongUniversity,Jinan250100,China)
As the highest law of the country, constitution must have the highest legal effect and the greatest authority, the legislations and the behaviors of public power which are in conflict with the constitution must be invalid because of their unconstitutionality. Safeguard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Constitution must on no account fall back on personal authority, but rather depend on a sound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 system to achieve the goal, while any suture of the system would lead to the Constitution′s breakdown.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le of constitutional law in China,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comprehensive constitutional self-guarantee system is the only way to safeguard the authority of constitution.
authority of constitution;constitutional self-guarantee system;constitutional system′s seam;the rule of constitutional law
2014-11-28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2FFX016);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IFYT1220)
魏治勋,男,山东昌邑人,法学博士,山东大学副教授,从事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律方法论研究。
D911.01
A
10.16152/j.cnki.xdxbsk.2015-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