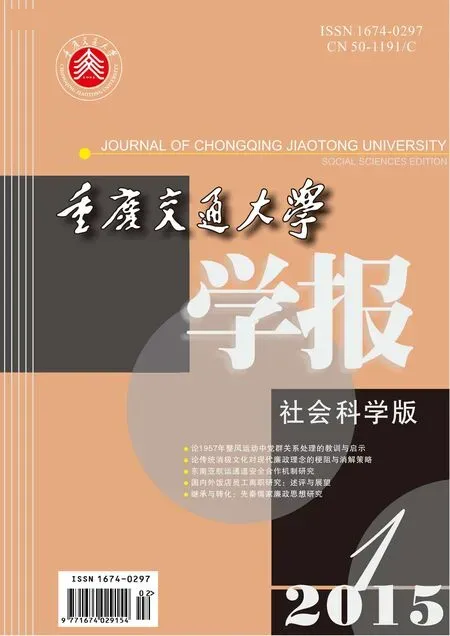论政府治理法治化
——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张振扬
(江苏省泰州地方税务局,江苏 泰州 225300)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
——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张振扬
(江苏省泰州地方税务局,江苏 泰州 225300)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政府治理; 法治化; 权力清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从“管理”到“治理”,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政府权力的下放。它将原本政府对社会的包办式“管理”转变为政府与社会组织、个人等多个主体的协同“治理”。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社会治理更加强调运用法治思维,使各方行使权力不得越界,合法权益有正当的程序性保障,政府治理法治化是其中重要的内容。本文将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尝试探讨政府治理法治化的实质与出路。
一、法治与治理的内涵
所谓“法治”,是一个与“人治”相对的概念。中国的儒家和古希腊的柏拉图都主张国家的统治者应当具有极高的品德,并以此来治理国家。儒家的治国思想与柏拉图的“哲学王”都属于人治的范畴,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却主张法治。他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虽然治国有时仍需要依靠某些人的智慧,但就算是最贤良的人难免也有不理智的时候,“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的神衹和理智的体现”[1]。本质上讲,法治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人治体现的是个人权力至上,法治则要求所有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这里的法指的是良法,应当是充分公正而被广泛接受的。如果是恶法,即使权力依照它行使,我们也不能称之为法治,更谈不上法治国家。
所谓“治理”,这里或多或少都有为了三中全会而扩大其概念的因素存在,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一个比管理更加先进的名词。现代管理学认为管理是由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及控制等职能为要素组成的活动过程。在国家层面,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手段是国家强制力,多数体现的是政府的支配地位。治理往往指“协同治理”,强调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管理。在这种模式下,尽管政府依然是社会公共管理功能和责任的承担者,但是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不同行为主体间形成了一种有机合作关系,从而让更多行为主体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关心公共利益,承担公共责任[2]。从其实际意义上来讲,从“管理”到“治理”更多的是在体现简政放权,使权力回到合适的岗位上,促进社会分工,促使社会主体依法各司其职。
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与政府治理法治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所谓“权力清单”,通俗地说,就是把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所掌握的各项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并将权力的列表清单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3]。权力清单制度的倡议者们希望借此彻底界定清楚每个部门、每个岗位的权力边界,让民众知晓每个部门权力的家底,将权力的行使过程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一旦有人越界,便有据可查。
与权力清单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负面清单”。负面清单的正式提法最早出现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所谓负面清单,相当于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学术上的说法是,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限制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4]。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的负面清单其实就是更高层次的政府权力清单。负面清单一方面告诉企业,这些你绝不能做;另一方面告诉政府,这些你才能管。这就是李克强总理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
政府治理法治化,即政府权力的法治化。必须强调的是,政府治理法治化和依法行使权力是两个概念。我们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法律许可(或者说法律从未实质干涉)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但法治与法律并不等同,而我国法律的不完善也是不争的事实。当前,我们强调政府治理或政府权力的法治化,更多侧重于两方面:一是政府职能转变。它主要强调要明确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直接干预,由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5]。二是完善立法。尤其是要加快推进保障市场、社会组织权利的立法,其中包括尽快提升税法层级和制定《社会组织法》等。
三、权力清单制度的几点思考
权力清单制度强调要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群众知晓权力的“家底”,以期能加强群众监督,促进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首先,很多群众对各个部门的“权力清单”没有意向,也没有精力去了解。以新办企业注册登记为例,其至少涉及工商、税务(一般国地税还需要分别办理)、公安、质监、统计等多个部门,假定每个部门都公示了权力清单,群众有多少意愿去了解每个部门的权力清单与办事流程仍是个未知数。有些部门只是简单地将“清单”公示在网站上,不到一月就被新信息淹没。除了网上公示,政府部门还喜欢把消息刊登在某一期报纸,或者张贴在某个不起眼的公告栏上。这些惯用的公示方法几乎起不到多大效果,很少有人会主动去看。在一整串涉及多个部门的办事流程中,只要一个部门的权力清单出现问题,其它部门的清单也多成空话。
其次,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能听到群众的抱怨——“这算什么规定,我为什么要交这个材料?我有什么义务给你们这个材料?”“你让我出这个证明,我真的有困难,你们就帮我特事特办一下。”即使办事流程已经简无可简,也会有人希望干脆就不用办;即使办事流程已经足够透明,也会有人希望走后门一步到位。权力清单也时常成为一些部门推卸责任的工具。即使是在提倡“服务型政府”的当下,很多事情不通过政府出面解决仍旧是不现实的。但在“多做多错”的意识形态引导下,一些政府部门完全可以以事项不在权力清单内为由拒绝服务,清单随时可能沦为“懒政”的借口。
从目前情况看,权力清单制度至少存在以下几种阻力:一是权力清单的法律层级太低,群众不理解不信服。二是一些政府部门只是将原本的工作流程进行了梳理,对于权力清单的质量、合理性和合法性没有进行检验。三是权力清单成了一些政府部门“懒政”的借口,凡是不在权力清单范围内的,即使群众有需求也不作为。四是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响应口号,不切实际地下达“权力削减”指标,导致很多必要的执法办事流程被削减,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五是政府抽身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没有得到来自社会的有效填补。六是基层党群组织的作用没有明确,以政府名义削减的权力改头换面成了党群组织的权力。
在缺乏立法的情况下,权力清单终归还是“人治”——拍板决定的结果,它始终不是法,更起不到法的效果。政府部门自行编撰的权力清单很难得到普遍认同。尤其是在“政社分开”“社会自治”几乎都没有什么起色的地方,在某些特殊领域政府权力过早抽离,要么造成权力真空无法填补,要么权力被无差别地转移给了某些党群组织。哪项权力该留,哪项权力不该留,需要拿到实际工作中去检验,一刀切的取消很可能导致政府工作出现断层。从清单的制定到权力的运行,再到其对工作的影响,都缺乏一套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总之,权力清单绝不能是简单地公布管理权限和事项了事。
四、政府治理法治化的出路
事实上,单纯的权力清单和以往的简政放权没有多大区别,也起不到多大效果。要想让权力清单制度达到设计者期望的效果,最终实现政府治理的法治化,至少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一)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其实应该分为两个概念,一个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另一个是党中央与地方组织。要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首先要改变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彻底理清官员向谁负责的问题。其次,必须要赋予人民选举和监督地方官员的权力,否则地方官员的错误决定得不到纠正。最后,中央必须下决心彻底废除地域上的不平等。必须强调许多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都是由地域上的不平等造成的,一切披着政策之名、刻意制造地域上的不平等都是不可接受的。
(二)扩大政治参与
从权力清单谈政治参与,主要是指政府部门在制定权力清单时,要允许与利益相关的民众或企业代表参与到清单的制定过程中。只有允许民众参与清单的制定,才能真正使民众了解和接受。很可惜,一些人至今活在“执政合法性来自建立新中国”的美梦之下,罔顾“政治参与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这一基本事实。他们始终拒绝意识到,只要人民的真实意见被排除在决策体系之外,权力清单就永远只是几个政府部门自娱自乐的游戏罢了。我们党在2007年曾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而扩大政治参与至少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手段,这里最重要的是民主。
从目前来看,扩大政治参与至少要先拓展形式民主。形式民主一直以来就为人所诟病,它被认为是“虚假的”“低效的”“形式主义的”。恰恰相反,形式民主正是保持国家民主性质的一项重大发现,是民主性质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所有那些企图用所谓真实民主代替形式民主改组国家的人们都因而把民主丢掉了。在古代许多细小的城邦国家机构中,这种意图坚持不了几个月就一定被专制制度所代替[6]。在一个连形式民主都没有的社会,民主会被当权者忘记,却不会被人民忘记。其次,我们要在形式民主之上寻求实质民主。何为实质民主,争议很大,所以我们不具体讨论实质民主为何物。但是实质民主至少要达到这样的效果——社会矛盾尽可能小,人为的不平等尽可能少,法律充分被尊重,人民的意愿充分被保障。事实上,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从来都不冲突,只有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扩大政治参与。
(三)减少行政干预
减少行政干预是权力清单制度的目的之一,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市场和社会。
市场方面,十四大以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经历了基础性到决定性的转变,促使这种转变的原因是,我们发现政府过多干预会干扰经济结构调整,应该交给市场调节,让市场成为经济良性增长的动力。中国之所以陷入产能过剩怪圈,就是因为政府对企业经济行为的过度干预,部分产业政策脱离实际,影响了企业正常的投资决策[7]。正如国资委不能替代国有企业管理层对企业的经营与发展做决策一样,政府同样不能替代市场做出最合适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社会方面,我们经历了从全面统治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演变。现在谈从社会层面减少行政干预,至少包括教育去行政化和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两部分。教育去行政化是确保学术独立与价值观多元化的基本前提,是公民理性思维训练和培养的必然途径。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强化社会凝聚力,让社会问题尽量在社会层面消化,用减少政府负担的方式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当然,这不代表完全不需要政府出面调节,就像广场舞,原本是加强邻里关系、丰富晚年生活的有益形式,现在却因为噪音扰民被广泛批评,需要政府出面协调,尽可能地兼顾多方利益,使这一有益活动延续下去。
(四)捍卫法律尊严
要实现法治化,终归是要依靠法律,尤其是要依靠宪法。长久以来,政府部门习惯把文件当法、把党委的指示当法,这显然是法律缺位造成的。诚然,法律与政府文件都是由人制定出来的,但它是由什么人制定的,是辨别它是法治还是人治的重要标志。有的地方党委不重视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而是直接赋予其决策以法律执行力。遇到重大事项,往往采取党委决策—政府执行或党政联合发文的方式,把人大的重大事情决定权抛在一边。地方政府也习惯于党委负责,执行党委做出的决策,在权力运行机制中往往出现人民代表大会的缺位[8]。
法治中“法”的主体应当是法律,是良法而非恶法,它是基于宪法至上原则,在充分保障公民民主自由权利的基础上设立的。将事关全体公民利益的事项过多地授予政府单方面决策是不合适的,将无法洗脱人治色彩的政府文件完全等同于法亦是不合适的。非经人民同意的单方面决定即使披上了法的外衣,也不可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想以政府文件来实现法治,只能是少数人的一厢情愿。所以,我们捍卫法律尊严,至少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所有层级的行政法律文件在施行到一定期限后,应提交人大进行立法确认;所有对法律的解释性文件在限定期限内,应交人大提出法律修正案。
总之,权力清单制度虽然是推进政府治理法治化的重要补充,却难免不会沦为人治的结果。当前,我们亟需加强立法,发挥人大作用,促进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政治文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目的。政府治理法治化的最终出路是以法律形式来约束政府权力,也唯有重视宪法至上,重视维护法律的权威,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才会有实际意义。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67-169.
[2] 毛莉,李玉.从“管理”到“治理”:一元单向模式转向多方交互共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1-22.
[3] 柳霞.权力清单制度:将权力关入透明的制度之笼[N].光明日报,2014-01-17.
[4] 是冬冬,胡苏敏.何为负面清单?[N].东方早报,2013-09-28.
[5] 孟川瑾,曾艳清.面向政府公共服务的政务微博应用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06-111.
[6] 赫勒尔 A,杨祯钦.形式民主[J].国外社会科学,1980(12).
[7] 谭思敏.调结构、稳增长,减少行政干预成关键[N].机电商报,2013-09-23.
[8] 赵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关系规范化研究[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4.
(责任编辑:张 杰)
Simple Analysis of Law-based Government Governance Taking “Power Lists System” as an Example
ZHANG Zhenyang
(Taizhou Local Taxation Bureau, Taizhou, Jiangsu 225300, China)
It is promoted in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that the mechanism of disclosing power lists is a major way to push on with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a’s governing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When converting “management” into “governance”, it emphasizes “governance”, that is to say, “the rule of law”, which aims at guaranteeing that the people are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while the “list of powers” aims at restricting the intervention powers of the government on the market and the society, actually, they are different. The former one is based on constitution supremacy, and the latter is originated from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We must bring it back to the rule of law in order to make the mechanism of disclosing power lists be an effective way for promoting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e. law-based government governance.
government governance; rule of law; power list
2014-06-17
张振扬(1992-),男,江西抚州人,江苏省泰州地方税务局工作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治学硕士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税法。
D601
A
1674-0297(2015)01-0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