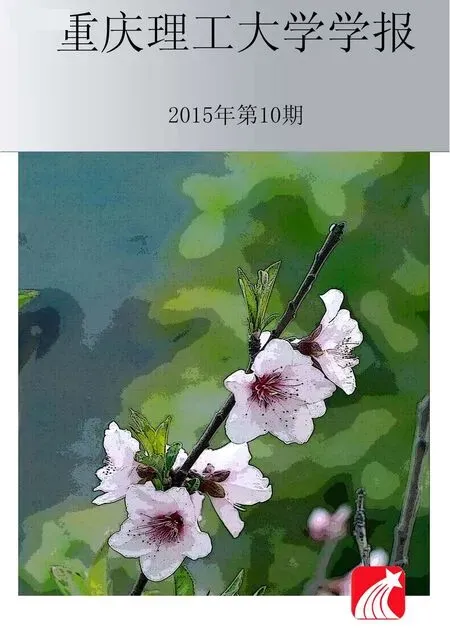多维哲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
韦忠生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外国语学院, 福建 福清 350300)
多维哲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
韦忠生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外国语学院, 福建 福清350300)
摘要:基于哲学视角对翻译开展研究有助于拓宽翻译的研究视野。在哲学思维的差异以及哲学方法论的异同两个方面对中西翻译研究哲学路径进行比较,从天人合一的辩证思维、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概念、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融合、从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生四个层面探析了中西翻译理念的异同与发展趋势。当今的翻译研究已从对立走向融合,呈现出多元互补的发展态势,翻译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
关键词:哲学视野;多维视域;翻译理念 截止2014年12月27日,“中西翻译研究哲学路径”的中国知网期刊模糊检索结果显示为2项, “多维哲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的中国知网期刊模糊检索结果为1项,说明著述者从上述两个视角探析翻译的论文并不多见。我们认为翻译哲学就是运用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哲学的多维视角探讨翻译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目的论、翻译批评,研究翻译学的学科地位、翻译的性质以及翻译中的作者、原语文本、译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的多元关系。本文将主要探讨哲学视野下的中西翻译研究哲学路径的异同以及多维哲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与发展趋势,以期从某种程度上拓宽该论题的话语空间。
Translation Study from Multipl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WEI Zhong-s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qing 350300, China)
Key word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multiple angles; translation study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425(2015)10-0128-05
Abstract:Translation study from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will be conducive to broadening its study scope. A comparison was made between the philosophical approach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y in the aspects of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A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he four sectors to reveal different Chinese and western notion of translation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such as dialectical thought based on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dualism displayed in subject and object separ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philosophy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opposition of dualism to coexistence of many different factors. Featured by the transfer from opposition to integration and multi-factors-oriented complementary development trend, current translation study has become an actual interdisciplinary, multi-layered, multi-perspective and all-round comprehensive study.
收稿日期:2015-02-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清代涉台奏折词汇研究”(14YJC740099);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认知视角下的明代笔记词汇研究”(2013C081)
作者简介:杨继光(1978—),男,江西新干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汉语词汇学、古典文献学。
doi:10.3969/j.issn.1674-8425(s).2015.10.023
一、中西翻译研究哲学路径之比较
(一)中西译论哲学思维的差异
徐行言认为中国哲学思维偏好运用直接体验的方式去获取和传达涵盖力极强、极灵活、为认识主体留有极大领悟空间的认识成果[1]121。他举例说明了中国人的形象和直觉思维方式,如“道”是宇宙本体、是自然规律、是实体、是虚空。究其实,那便是“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1]122。它回答了宇宙万物深邃又难以认识的问题,因此无法明确界定本质,这也可以说明中国许多重大的基本的哲学概念都没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这种思维方式拒绝肯定的答案,使认知具有开放性特征,这符合中国哲学对本体模糊本质的认识,称之为中国式智慧。中国译论体现了这种哲学的思维方式,如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许渊冲的“三美”说等,表述婉转、措辞简洁、内涵丰富、寓意深远。这些标准都是基于翻译家的翻译实践总结出来的体会和经验,但缺乏对概念的明确界定与阐述,其抽象性和概括性显而易见。如神似、化境的内容与实现途径没有予以明确阐述并澄清,给译者与读者留下了广阔的领悟空间。
西方的哲学思维倾向于借助严密的逻辑推理去获得和传递精确、可靠、稳定的知识,因而注重规则的缜密,力求避免认识主体理解和阐释对象的任意性,重视认识的客观性与同一性[1]121。西方译论逻辑严密、层次分明、概念清晰,从多角度多层面对翻译活动进行研究和描述。图里(Gideon Toury)提出的描写翻译理论[2]56-59,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认为翻译过程中的初始规范(initial norm)体现了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通常具有侧重充分性(adequacy)和可接受性(aceeptability)两种倾向。前者强调译文忠实于原文,后者则注重译文在目的语中的认可。他还将翻译的具体规范分为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和翻译两大类。翻译还涉及间接翻译手段的运用,包括借助第三种语言转译。按照他的观点,操作规范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即在宏观结构上对翻译内容作出取舍,如全译、摘译等;二是篇章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基于卡特福德(J.C.Catford)的转换概念,图里将转换归纳为强制性转换(the obligatory)和非强制性转换(the non-obligatory)两类,前者受到语言动机的制约,后者则基于文学或文化层面的考虑。目的语文本运用非强制性转换的比率取决于初始规范是否倾向于可接受性或是充分性规范。
(二)中西译论哲学方法论的异同
陈寿灿认为哲学方法论首先被理解为是关于科学认识活动的方式、形式和体系的原理的学说,涉及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意义[3]5。这些要素包括:(1)客体,即主体所认识和变革的对象。既可以是人和物,也可以是诸如思想文化等精神性对象,其主要特征包括客观性、对象性、受动性、社会历史性和矛盾性等。(2)主体,即参与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主体不但具有客体所拥有的一切特征,还具有自生的独特的特征,主体性为更显著的特征,表现为主观能动性和主体的多样性。(3)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即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评价与被评价的关系。由于主体自身的条件以及对客体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形成主体对客体的迥然不同的评介方式、认识方式和实践方式,从而形成形态各异的方法论。
中西译论存在本质上的相似性,都涉及哲学方法论的基本要素:主体、客体,以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传统译论主要有两种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与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4] 88。前者认为作者和文本高于一切,译者处于从属的地位;后者认为作者的地位至高无上,作者和译者的关系等同于主仆的关系,译者必须忠实于作者的意图。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译者的主体地位的最好体现。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是当代翻译研究范式的特点。然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等由于任意拔高译者的地位,使得翻译的主体——译者从某种程度上偏离翻译客体之一的原文文本和原语文化,对原文文本任意的改写司空见惯,导致翻译主体与客体不同程度的割裂与对立。将哲学的主体间性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可谓独辟蹊径,注重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翻译发起人、赞助商、原语作者、原语文本、译者、目的语文本、目的语读者、出版商、翻译批评者等均参与翻译过程中多元的互动与对话,生成了各种翻译方法论。
中国人注重整体、悟性、形象和直觉思维,往往从整体上去认识和把握世界,西方人重视逻辑分析和抽象思维,习惯于基于多元化的视角去理解和解释世界,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在翻译这一认知思维活动上得以充分体现,导致中西译论的差异[5]。中国哲学坚持整体的宇宙观,以认识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作为认识的基本前提。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在中译论中体现为注重翻译理论宏观上的概述,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如严复的“信、达、雅”, 陈西滢的“形似、意似、神似”和许渊冲的“三美”说(音美、意美和形美)。由于直觉思维的个体主观性是不确定的,认识本身亦具有随意性、灵活性和主观性,致使它可以产生无限的创造性[6]。对上述翻译标准的解读颇具灵活性,取决于译者和读者的创造性思维。为了区分二元对立的两个不同概念,或多个概念,西方译论侧重微观分析,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如以韦努蒂(Lawrence Venuiti)为代表的文化翻译理论,详细阐述了归化与异化的差别与定义,条分缕析,在归纳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理论的基础上给予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在翻译的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的视角下,阐述了异化翻译观的内涵,后来将异化称为“存异伦理”,体现了异族文化因陌生化而具有吸引力。
二、多维哲学视域下的中西翻译研究与发展趋势
(一)天人合一的辩证思维
中国古代的本体论或存在论有两大特色,一是注重观照整体的辩证法的探讨,二是注重人生伦理问题的探讨,后者的特色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3]9。中国的辩证法思想源远流长,《易经》以形象的语言体现了辩证法可以指导人们的一切活动。它以阴阳的相辅相成关系解释战争、医疗、农事等各种现象,阐释万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老子》论及了美丑、难易、祸福、荣辱、刚柔、巧拙等几十对辩证关系。作为认识论的基本范畴,“天”为认识对象,即客体,“人”则为认识主体,“天人合一”指认识论中的主客体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对翻译标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言意范畴的命题以及辩证关系对翻译标准的影响[7]。我国古代的佛经翻译提出所谓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哲学—美学命题[8];我国的传统译论中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和美学渊源[9]。所有这些论述都体现了形式美与内容美的辩证统一关系。得意忘言和得意忘象,大致相当于言外之意、言不尽意,是一种言意范畴的命题,对中国古代的文学、佛学、书画艺术产生过直接影响,其影响波及翻译理论和实践。中国翻译理论借鉴了这些领域的认识论。古代佛经翻译标准的文质之辩便是言意范畴的具体体现。质派要求以质直求真,以朴拙作为译学的美学标准,文派则认为要有一定的文采。这是我国翻译界直译、意译的开端。玄奘是我国佛经翻译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其翻译标准“求真喻俗”指的是内容忠于原文,语言通俗易懂。他还提出“五不翻”主张,着眼于内容真与形式美的辩证关系,在翻译实践中采用了补充法、省略法、转化法、分合法等翻译技巧。1894年马建忠提出“善译”,认为译者首先应该透彻理解原文,了解其风格,然后以通顺的文字予以表达。1896年严复提出了“信、达、雅”,对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阐述,认为翻译应该使用典雅的文字才能达意,而在意义与表达产生矛盾时“尔雅”的文字更为重要。钱钟书的“化境”标准则是直接借用了佛教用语。在陈西滢 “形似、意似 、神似”和傅雷的“神似说”的翻译标准中也可以窥见绘画理论的影响。这些翻译标准虽然用词简洁,但内涵丰富,是“言不尽意”的一种表现,实际上也体现了形式美与内容美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概念
西方翻译界存在许多观点迥然不同的翻译学派别,如语言学派与语文学派、规范学派与描写学派、结构学派与解构学派。西方的许多翻译理论也充斥着二元对立的翻译理念,如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卡特福德(J.C.Catford)的全译与摘译,功能翻译理论的功能与忠诚,语内连贯与语际连贯,释意理论的内含意义与外显意义。《红楼梦》全译本的译者霍克斯(David Hawkes)以目的语文化为视角对涉及中国文化的内容的翻译主要采用了意译或归化的翻译策略,而该作品的中国译者杨宪益则以原语文化为导向更多地采取了直译或异化的翻译策略。全译与摘译的选择显然会受到翻译活动发起人社会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如英语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有关性爱描写的许多场景因为有悖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而在中文节译本中被删除。
翻译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可以追溯到其哲学、语言学根源。“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dualism)的理念可以说是造成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滥觞。”[10]西方哲学的二元论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意识和物质两个实体,意识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一元论则持对立的观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或者意识,两者居其一。笛卡尔的二元论认为自我或心灵乃是一种不依赖上帝的意志的独立存在,也不依赖物体或自然的必然性而存在的东西,为人的主体性的存在和发挥开辟了道路。
主客体的二元对立构成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基本前提,构成了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等二元对立的哲学范畴。在主客对立的逻辑前提上西方人建立起无数彼此互相对立的范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有限与无限、现象与本质、理论与实践等。正是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促进了事物的发展,使人类社会生生不息、充满活力,同时正是承认事物的差异才能彰显个人在西方社会的价值,展现千姿百态的世界。然而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相伴随的价值观,容易将事物对立的性质绝对化、简单化,形成非此即彼的错误分析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二元对立对翻译的积极与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王洪涛认为在翻译研究中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激发逆向思维、活跃学术氛围,然而这种二元对立的译学格局使得翻译研究陷入了一个怪圈,仿佛离开了这种非此即彼、二律背反的理论程式,翻译研究再无其他的发展动力[11]。
(三)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融合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持何种立场决定了哲学理论的基本路径。对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其一,理论高于实践,不依赖人类实践而存在,即具有脱离实践的阿基米德点;其二,理论与实践息息相关,但并不单独存在,理论乃是生活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12]。与这两种立场相对应的便是两种不同的哲学路径:前者为理论哲学,后者为实践哲学。
中国翻译界对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重要性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冯文坤、万江松认为翻译研究正在经历从实践哲学向理论哲学的转向,因此翻译研究的焦点为理论哲学的研究,并非具体翻译实例的探讨[13]。孙宁宁则认为翻译研究已经实现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向,翻译观也相应地从语文学模式变为以实践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模式[14]。笔者对这两种观点提出商榷。诚然,理论翻译学或将成为一种可能,霍姆斯(James S.Holmes)就将翻译学分为纯理论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但任何理论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实践的总结,如奈达的翻译理论就是对翻译《圣经》过程的经验的归纳、总结和升华。倘若毫无翻译实践的基础,翻译理论理性的完全自主性、优先性与超越性似乎很难达到;倘若过度强调翻译实践哲学的作用,势必影响翻译学科的理论建构与跨学科研究。一门学科的发展与其宏观的理论建构是分不开的,只有重视学科的理论建构才能使其立于学科建设的前沿。对翻译中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其中一方的过度关注都可能造成两者的割裂,可能重新形成翻译理论二元对立的格局。中西译论总是和翻译实践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西文化中历次翻译高潮的出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不断深化和翻译实践的不断创新,同时又使理论自身得以不断完善。莫纳·贝克(Mona Baker)主持研制的翻译英语语料库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力图实现翻译研究的客观性、描述性,正是重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结合。与少量、零星的语言实例相比,翻译语料库的优势显而易见,其信度与效度有目共睹,有助于从翻译文本微观层面上予以量化分析,如文本等值概率分析,译文风格特点的量化分析,多个译本在词汇密度、词频、句子长度、搭配模式、特定词汇的使用以及使用频率等方面的比较研究。这种典型的以数据驱动(data driven)为导向的研究,其思维模式遵循自下而上的路径,基于具体数据推导结论,将信息时代的庞大信息量处理的需求纳入视野,融合了语料库语言学的理论与实现途径,注重翻译实证研究,可以界定为描述性的翻译研究,标志着翻译研究方法从规定走向描述,实现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结合。
(四)从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生
各种翻译研究的思潮与思想都有其哲学基础,所以认清哲学发展与翻译研究发展的关系,以及认识以往各种译学范式的哲学基础,对翻译研究意义重大[15]。中西翻译研究历经传统的语文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文化研究、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等范式,正步入多元化的翻译学研究阶段。语文学范式翻译研究往往重视灵感的重要作用,无疑与古典知识论哲学有密切渊源,体现了其人本主义的方法论。古典知识论哲学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将其视为宇宙的精华,鼓励人们对大自然的驾驭与征服,归属本体论哲学。在这种不分主客、注重直觉与灵感的思维的影响下,人们将文学作品的成功视为灵感的充分体现。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摈弃了灵感与直觉的语文学研究路径,开始关注客体,开展文本的语言分析,试图寻找语言转换规律,体现了认识论主体哲学的影响。然而它过分强调语言规律的作用,逐渐形成了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其结果是译者的主体作用被削弱。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以哲学阐释学为哲学基础的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打破了结构主义翻译语言学范式的静止性与封闭性的状态,从理性主义转向怀疑主义,将翻译中语言结构之外的诸多因素纳入视角,从文化、历史、意识形态、译者目的等多元视角来研究翻译问题。然而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对译者主体意识的过分强调,对语言转换规律的忽视,致使翻译活动演变为永无终止的过度诠释。以语义学为导向的卡尔纳普(Carnap)模式和以语用学为宗旨的戴维森(Davidson)模式反映了分析哲学和后分析哲学的典型思维方式,标志着思维模式从语义学向语用学转向[16]。西方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促使语言哲学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换,使主体之间的可理解性、可沟通性成为现代和后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哲学的语用学转向促使翻译从语言学的逻辑性与文化学派的阐释性进入语用学解释性的理性交往的建构时代。翻译的主体间性第一层面涵盖作者、文本、译者的关系,第二层面还涉及作者、译者、读者的关系,因此可以归为多元主体关系。哲学的主体间性理论的诞生成为翻译的主体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促使翻译跨越原作者独白、文本独白以及无限度的读者阐释,构筑多元主体之间不受时空限制的积极对话[4]89。吕俊、侯向群以普遍语用学的交往论和言语行为理论为哲学基础,提出了建构主义翻译学视角,对翻译学学科建构和翻译研究有重要的意义[17]。
三、结语
翻译学是涉及语言学、传播学、交际学、符号学、文化学、政治学、逻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美学等相关学科的错综复杂的人类活动,是一个开放性与动态性兼备的学科系统。该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其与文本之外的各种因素之间既相互对立,又互相融合,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翻译实践是丰富的、复杂的、矛盾的、多元的,所以翻译理论也应该是多元的。对于翻译理论的价值判断与认同应该超越是与非、好与坏、正确与谬误等二元对立的旧范式。”[18]当今的翻译研究已从对立走向融合,呈现出多元互补、相互融合的发展态势。翻译研究的综合性不言而喻,其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特征亦显而易见。
参考文献:
[1]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1-122.
[2]TOURY G.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1995:56-59.
[3]陈寿灿.方法论导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5,9.
[4]韦忠生.主体间性视域下译者的主体性与外宣翻译策略[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2(10):88-93.
[5]何旭明.从辩证系统观论翻译之动与静[J].英语广场,2012(2):15-17.
[6]杨毅隆.中国翻译美学史概略[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3(5):125-127.
[7]刘峥,张峰.哲学视角下中西翻译标准的对比[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60-162.
[8]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201.
[9]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7.
[10]朱安博.翻译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反思[J].外语教学,2010(3):105-108.
[11]王洪涛.超越二元对立的致思模式——当代译学格局之批判与反思[J].外语学,2006(3):98-103.
[12]熊兵娇.实践哲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探索[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65.
[13]冯文坤,万江松.由实践哲学转向理论哲学的翻译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2):99-105.
[14]孙宁宁.实践哲学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影响[J].河海大学学报,2003(3):76-78.
[15]邵璐.新视野 新研究——哲学转向对翻译学的建构性意义[J].山东外语教学,2004(6):98-100.
[16]PEREGRIN J.The Pragmatization of Semantics[C]//Turner K.The Semantics /pragmatics Interface from Different Point of View.Amsterdam:Elsevier,1999:420.
[17]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18]白爱宏.超越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生——中国译学建设的一点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12):39-41.
(责任编辑魏艳君)

引用格式:杨继光.清代奏折对语文辞书编纂的价值[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10):133-138.
Citation format:YANG Ji-guang.Value of Memorials of Qing Dynasty to Language Dictionary Compilation[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5(10):133-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