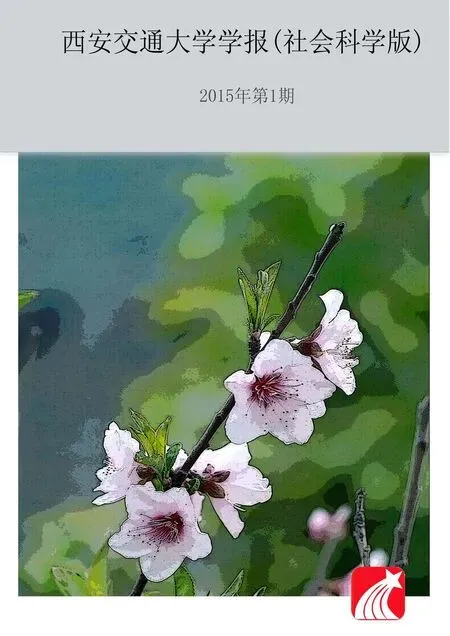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研究谱系:内涵诠释、现实表征与关系构想
刘婵君,李明德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710049)
2010年以来,随着建构于“熟人社会”基础上的社会化媒体迅速崛起,逐渐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与社会交往方式,甚至已然开始自下而上改写的政治生态。本文对2011-2014年研究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关系的文献进行检索,在梳理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的内涵、解析社会化媒体影响政治生态的现实表征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的关系构想,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展开探讨。
一、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的内涵诠释
(一)社会化媒体:定义的大同小异与类型的复杂多样
社会化媒体,也称社交媒体、社会性媒体或社会媒体。关于社会化媒体的概念,中外学界均尚未形成统一定论。戴恩·欣奇克利夫(Dion Hinchcliffe)较早给出了定义社会化媒体的一些基础规则。即以对话而非独白的形式沟通,参与者是个人而非组织,核心价值是诚实与透明,引导人们主动获取而非推给他们,分布式而非集中式结构[1]。目前,学界使用最为广泛的概念是卡普兰(Kaplan)、亨莱茵(Haenlein)于2010年提出的。他们认为社会化媒体是建构于Web 2.0的理念与技术之上、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多种新兴在线媒体,它赋予用户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2]。此外,基茨曼·简(H kietzmal Jan)强调,社会化媒体是帮助个人与社区分享、共同创造、讨论与修改用户生成内容的交互平台[3]。西方学者初步奠定了定义社会化媒体的一些基本要点:广阔参与空间、自主创造内容、促进平等沟通。
国内对于社会化媒体概念的表述也多种多样。从起源来看,社会化媒体是以网络社会化为基础、在互联网传播过程中携带和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社会性网络工具,也即是技术与社会共同进化的产物[4];从性质来看,社会化媒体是吸纳了网络媒体中符合“用户创造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和“消费者生产的媒体”(Consumer Generated Media)这两大特性的全部媒体形式[5];从功能来看,能让网民互动、合作和分享内容[6]。因此,无论是将其看作是一种媒体、平台或是应用程序,国内学者对社会化媒体的定义,与国外学者并无实质差别。社交、自主、互动、分享与合作,也被他们视为社会化媒体的基本特征。
学者们还从不同范围去划分社会化媒体的类型。美国学者梅菲尔德(Mayfield)与我国学者张杰从狭义上进行分类。菲尔德认为SNS、Wikis、博客、播客、论坛、内容社区及微博客是目前常见的六种社会化媒体形式[7]。张杰则结合我国现状,将社会化媒体划分为即时通讯工具、微博客与社交类媒介[8]。相比而言,卡普兰(Kaplan)与王明会等的划分范围则宽泛得多。卡普兰将社会化媒体划分为博客、协同项目、社交网络平台、内容社区、虚拟社交世界和虚拟游戏世界[2];王明会更为细致,将社交网络、商务社交网络、微博、视频分享、社会化电子商务、签到/位置服务、即时通讯、RSS订阅、消费点评、百科、问答、社会化书签、音乐/图片分享、博客、论坛/论坛聚合以及社交游戏全部包括在内[9]。总体而言,学者们对于博客、微博、论坛、社交网络等的社会化媒体属性已达成共识,多数也都赞同将即时通讯工具纳入其下,然而对于是否应当包括在线游戏、在线约会等,则存在明显分歧。
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我们对社会化媒体作出如下定义:建构于Web 2.0技术基础之上,允许用户自主创造并传播内容、支持用户互动沟通,以及分享信息、促进用户社会交往与合作的一系列新兴在线媒体的总称。
(二)政治生态:概念的模糊笼统与层次的细致统一
如果说学界对社会化媒体的定义不一而足,那么对于政治生态的概念表述显得则更为模糊笼统。这里列举三个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其一属宏观描述,较为抽象。政治生态是一个国家或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10]。其二从政治生态的构成要素出发,将其定义为在一定社会中形成的政治环境、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模式、政治评价标准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11]。其三认为政治生态是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领域所形成的理论概念,是政治系统或政治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良性互动[12]。笔者认为,此概念提示了政治生态学的研究视角,基本勾勒出政治生态的层次,有助于找准研究的切入角度。
学者们也专门针对政治生态层次范围的划分展开过论述,普遍赞成将政治生态划分为“政治内生态”与“政治外生态”两个层级。刘京希则将政治生态体系划分为政治体系内生态、政治-社会生态以及政治-社会-自然生态[13]。万斌、丁友文在此基础上,专门对处于核心层次的政治内生态进行更为具体的细化:从现实的政治生态系统来看,政治内生态由核生态、系统内生态和原生态三部分组成。核生态作为核心层,是政治活动、政治行为、政治决策的源心;系统内生态包括了政治制度、政策、机制等生态要素,是保证政治内生态系统运转的关键圈层;原生态作为外围环境圈,则涵盖了政治系统的流程、信息、知识和技术等生态因素[12]。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我们试图完善政治生态的概念:政治生态是指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内部机理与外部表现。
从已检索到的文献来看,针对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关系的研究,往往以论述社会化媒体在现实社会治理中对公民政治参与、政府执政方式等具体政治现象的影响作为表征。
二、社会化媒体影响政治生态的现实表征
政治主体是政治生态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政府、公众以及其他政治组织。这些政治主体同时也是社会化媒体的信息传播主体。社会舆论在社会化媒体平台生成的过程,就是源自不同政治主体的各种立场、意见的交换、互动与碰撞。鉴于此,本文以公众与政府这两大最主要的政治主体作为研究对象,梳理社会化媒体作用于不同政治主体所产生的差异化表征。
(一)社会化媒体-公众:政治参与的全新局面与发展桎梏
近年来,社会化媒体凭借其自由撰写并分享信息、即时探讨并评论观点的交流对话功能,给予用户最大限度的表达自由与参政可能,在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建构起一种信息沟通与反馈机制,从而在无形中推动了我国政治生态化建设的步伐。
陆斗细将公民基于互联网相关技术的政治参与行为界定为“围观式政治参与”,归纳其与传统政治参与相比的五个特殊性:参政主体——现实性和虚拟性的辩证统一;参政动机——非利益型动机愈显重要;参政行为——以“话语参政”为主;参政价值偏好——“以公民为本位”;活动方式——以“集体行动”为基本方式[14]。这些构筑了社会化媒体政治参与的基本面貌。马小娟提出社会化媒体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两个方面,即超越传统媒体固有局限的工具性价值与推动公民参与向着“强势民主”方向发展的社会性价值[15]。荆学民认为,这种政治参与方式,使得普通公民获得了与精英们建立平等对话关系、共同讨论问题与交换意见的机会,从而客观上建立起以虚拟环境为基础的政治互动机制[16]。
然而,社会化媒体政治参与这种“广场狂欢”的背后,同样存在着“脱域机制”的隐患。名人成为主要意见领袖导致草根话语弱势、“群体极化”造成党同伐异、把关人失效引起虚假信息泛滥、负面信息居多形成坏消息综合症[17]。由此,缺乏代表性、表达非理性与参与无序性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仍然困扰着社会化媒体政治参与的前进步伐。
1.话语权的争夺与回归。社会化媒体时代政治参与的空前活跃诱发了政治话语权的争夺现象。孟建认为,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伴随公共话语空间的快速分化与重构,多元话语力量也随之壮大,并开始与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激烈的碰撞交锋,从而引发话语权的再分配与话语秩序的改变[18]。社会化媒体中政治话语的生成,不再表现为传统媒体时代由完备的政治理论向现实政治层面运动的完整有序过程,代之以片段式、无章法与庞杂的特点[19]。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虽然话语权的回归给予社会底层一个发声机会,从而使得传统媒体不再垄断言论,但话语权的增多并不代表着社会化媒体已完全由网民自己掌控。“尽管在利益表达方面,民众因新媒体勃兴而被赋权,但如果缺乏更为现实化的组织力量,仅仅可以‘表达’的权力是有相当局限的。”[20]真正的话语权实际上仍然控制在少数人手中。
2.网络围观的显效与隐患。社会化媒体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手段与场所,一定程度上给予普通大众改写政治议程的能力。“网络围观”即是其中最具影响力与最有效的行为方式。它被认为是一种新型“舆论监督”,“本质上就是公共权力和民意之间的一种平等的互动过程。”[21]以微博为典型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不仅为网络围观的形成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同时还在围观中扮演“信息源”角色。张淑华认为,作为一种新媒体时代的公民社会政治参与方式,网络围观呈现出许多“另类”特征。“其集体无意识的参与带来的群体压力型传播效果,其建设性和破坏性共存的社会干预公用,其‘起哄’与‘使命感’、‘正义感’相互参杂的参与心态,都使网络围观超越了简单化的‘看客’定性而呈现出意义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特征。”[22]尚虎平通过对50起网络焦点案例的研究指出,网络围观将处在隐匿状态的公共权力放到了众目睽睽之下,以“凝视”权力制约了行政权力的不作为,但传统的“行政权力万能”与不打不动、打了乱动的“睡狗行政”的存在进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初现的浮躁与理性并存的网络公民社会,正在既监督又要挟着政府[23]。
3.网络反腐的威力彰显与制度缺失。网络反腐是与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政治参与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普通人影响政治决策的现实表现。作为网络围观的自然衍生现象,它同样得益于社会化媒体的迅猛发展。长期以来,制度化、规范化的社会力量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揭发机制始终难以健全。社会化媒体开放、透明、平等的环境空间,给予了渴望社会增权与权力监督的普通大众“一线生机”。“从某种意义上讲,网络反腐是社会监督制度化困境倒逼下的‘产物’”[24]。纵观现今社会的网络反腐一种模式为:网络曝光→网民议论→媒体报道→形成舆论→启动调查→惩处贪官[25]。虽然社会化媒体以其公开、透明、快捷的优势,成为“全天候的反腐利器”,形成体制外的一支重要反腐力量[26],然而其不可逆性与非正当性依然是当前法律制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网络反腐就会失去实效与意义。也有学者坚信,网络反腐是在网络普及率迅速增长而制度化的反腐渠道又不畅通的条件下出现的一种阶段性现象。它会随着制度的不断健全、反腐倡廉体系的不断完善而走向衰退[27]。
总体而言,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政治参与存在正负效应,既是推进反腐廉政建设与民主化决策建设的正能量,但也与容易陷入极端自由主义、危害社会治理的隐患如影随形。因此,我们如何制定切实可行的科学疏导策略已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
(二)社会化媒体-政府:执政方式的潜在危机与深层变革
社会化媒体极大地释放了社会表达,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场,在推动网络问政的同时,也给以往的执政理念与方式带来挑战。将社会化媒体置于社会治理对立面的普遍认知,不仅难以解决现存问题,也并未使政府执政力、公信力得到提升。
1.传统权力结构的挑战与转型。与不同政治主体话语权的争夺现象相伴随,传统政治权力结构似乎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刘文富曾指出,互联网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正在促使传统的控制型、垂直型权力结构向着分散型、交互型转变[28]。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全面兴起,这种转变更为显著与迅速。王文认为,Web 2.0时代,非国家行为体能够爆发出更富有潜伏性、威胁性、瞬间性与多样性的威力,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国家内部的等级化、秩序化与中心化。政府权威受到非政府力量的实质性怀疑与指责,旧有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权力受到了削弱、再配置甚至异化[29]。近年来的伊朗“推特(Twitter)革命”、突尼斯、利比亚等国“阿拉伯之春”骚乱、英国“世纪大罢工”等运动,社会化媒体都在扮演着信息源与煽动工具的角色。学界有观点强调,目前由线上话语竞争所形成的表达优势,尚不足以动摇线下的权利关系。邱林川等提出,尚无明确结论来说明话语权力是否由传统精英垄断实现了向底层赋权的转变,也很难说事件的社会效果是延续还是打破了传统的权力结构[30]。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即网络空间的流动性和网络信息的全球化传播,使得国家权力已难以继续沿用传统的“硬”权力模式对互联网进行绝对控制[31]。社会化媒体与权力结构变革的论题,已然成为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转型语境下的一个引人注目且不容忽视的研究热点。
2.既往执政方式的潜在危机。在社会化媒体所开创的透明、公开的社会交往方式之下,政府既往执政方式中的隐患也逐渐暴露,多重危机的来临,挑战着政府的身份权威。(1)传播能力危机。“以物为本”的传播逻辑、概念化的传播形态、单向灌输的传播方式、畸轻畸重的传播结构以及基于系统化管理的传播合力的缺失,严重桎梏了政府公共传播能力的构建[32]。(2)舆论引导危机。随着舆论主导权向新媒体的转移,舆论引导格局呈现景观多元化、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联系紧密、“众声喧哗”成为舆论常态、社会舆论中的变数增多以及舆论引导效果充满不可控性等五个新特点[33]。(3)政府信任危机。由于使用新媒体能力的有限与掌握资源的不足,地方政府多次舆情事件中的慢回应与不回应,使其在公民心中的信任度骤降。信任的建立需要长期培养。如果人们一直对政府抱有负面印象和低期望值,势必造成政府危机应对的巨大困难[34]。(4)角色定位危机。在社会化媒体所营造的多元表达环境中,政府不再是唯一正确观点与正确主张的代表者,而应该成为公共议题与各种利益的协调者,以往站在某一利益集团立场发声的舆论应对方式常常致使地方政府成为众矢之的,深陷被动泥沼[32]。最后,政府形象危机:部分官员的不作为、胡作为和腐败行为经由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人肉搜索、爆料揭穿直至声讨抨击,作为一个群体的象征,他们的违法乱纪直接导致官员整体形象在公众心中大打折扣[35]。
3.变革——政务社交媒体的全面兴起。面对扑面而来的危机,政府的执政方式也开始由以往单项强制灌输,向着互动合作交流转变。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政务公开新形式的兴起,标志着政府开始主动出击,利用社会化媒体,建立起与民沟通、走“群众路线”的全新渠道。吴云等将由政府及公务人员参与的社会化媒体应用,统称为政务社交媒体,认为其具备提升信息透明度、增强政民交流、增加公民信任以及推进民主决策四方面功能[36]。陈立丹认为随着微博问政的发展,我国政府已由断点式应对走向常规化运作、由被动关注走向主动自我推介、问政微博呈现集群化趋向、从单方信息发布转向关系的维护[37]。李(Lee)等人提出了包括初始条件、数据透明、开放参与、开放合作与普遍参与五个成熟阶段在内的、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开放政府成熟度模型,用来作为评估政府部门开放度与实施社会化媒体策略的指导工具[38]。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报告统计,截至2013年底,新浪政务微博数量为10万多个①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3年度新浪政务微博报告。,腾讯政务微博数量为16万多个;政务微信数量则已超过200万个②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3年腾讯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发展研究报告。。虽然“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双管齐下的模式已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行政双翼”,然而政府对这些社会化媒体的使用仍然存在方式单一、使用效率低的问题。现实的情况是:政务微博的发展已由数量扩张阶段向着深度运营阶段发展[39],集群化成为未来发展方向[40];但政务微信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尚存在定位混乱、自说自话、认证困难等棘手难题[41]。
政府通过限制、管理、协助和参与等方法,通过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对媒体实施干预或制约,其目的是为媒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确保社会得以健康和有效发展[42]。然而既往诸多案例已经表明,如果单纯从政治本位出发、秉持管制的思路已难以达成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的双赢协同发展。在社会化媒体伴随移动互联网愈加渗透进社会各层面的趋势之下,如何利用社会化媒体促进政治生态健康、高效运行,实现二者协同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的关系构想
基于上述社会化媒体作用于政治生态的现实表征,我们可以对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的关系进行一些构想与假设,以此提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政治生态建设为社会化媒体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媒体演进史也是媒体与政治的博弈史。从最初的媒体从属于、依附于政治,到强调媒体的至上自由而成为对抗、制衡政治的力量,再到二者平衡与协调、媒体形式独立而又受到政治的适当约束。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的角色也在不断地调整修正。因此,媒介演进史也是政治文明化、生态化的进化史。当前,政府倡导的诸如“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建设要求,应该被视为政治生态化建设在政策层面的反映。它们无不反复强调全体公民的互动、参与和共同治理。公民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表现,就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成长与公民社会的孕育。社会化媒体正是建立在这种广泛的社会交往基础之上,“圈群化”与“部落化”使普通公民在社会化媒体中形成一个个社会自组织,实现了更加自由的社会交往方式。因此,政治生态建设为社会化媒体的应运而生与蓬勃发展提供了开放包容的社会政治环境,而随着政治生态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出现更加社会化的媒介形态。
(二)社会化媒体从工具性与文化性两方面对政治生态系统发挥作用
一方面,政治发展中许多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有价值和理念,还需要有技术手段[43]。社会化媒体作为一种技术,能够被政治主体用来解决诸如“公共权力的腐败、电子政府的发展、政府管理的专业化”等问题的政治技术手段,同时形成独特的社会化媒体政治生态。由于社会化媒体政治生态是以信息为核心的动态平衡系统,信息在这里的表现形式为舆情,因此社会化媒体政治生态对整体政治生态的影响即表现为社会化媒体生成的舆情对政治生态的作用。另一方面,媒体本身也属于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组成社会的各个子系统之间是互为条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所以作为一种文化,社会化媒体通过影响文化系统的发展作用于政治系统。社会化媒体的诞生引领新的文化形态的出现,大众文化、关系文化、圈群文化、民主文化等新的文化形态均会对传统的政治观念、政治行为以及政治制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于无形中建构起新型的政治文化。
(三)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协同发展的基础在于“以人为本”
马克思指出,只有抓住了现实的人,才算抓住了事物的根本[44]。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也强调,虽然生态环境对于选择何种政治体制存在制约作用,但人却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较好的政治体制[45]。因此,国家的最后权力应当属于人民,任何政治行为的发生,都应当以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与归宿。社会化媒体能够通过构建“强连接”与“弱连接”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促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对人的关注是社会化媒体的重要特征之一[46]。因此,它是一种用户中心(人中心)型媒介。用社会化媒体中的人的活动去真正调动起政治生态建设中的人的活力,必须将二者的结合与协同发展牢牢建立在“以人为本”这个基础之上。
四、结语
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的联系日益密切,然而社会化媒体对政治生态的良性发展,始终存在正负效应。因此,未来我们的研究方向,应该是立足于发现社会化媒体传播与政治生态运行增益的交集,努力完善社会化媒体的管理机制,利用社会化媒体所构建的信息传播网络实现政治生态运转的流畅与高效,最终达成二者的协同发展。具体的目标是,借助社会化媒体的自主、互动、参与、合作等社会功能,促进政治系统与包括媒介系统在内的其他社会系统和谐共生、互动发展,形成生态联动的有机整体,并进而推动政治系统自身的生态化建设。为此,可以在下一步的研究中,通过文献梳理与实地考察,归纳二者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制定协同发展评价指标、构建协同度的测度模型、逐步建立起二者的协同发展测评体系,从而为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协同发展的机制构建与路径选择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参考。
[1] DION HINCHCLIFFE.Social business by design:Pransformative social media strategies for the connected company[M].wiley,2012:15
[2] KAPLAN A K,HAENLEIN A.Users of the world,unite!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Media[J].Business Horizons,2010,53(1):59-68.
[3] H KIETZMANN JAN,KNSTOPHER HERMKENS.Social media?Get senrious!Understanding the functional building blooks of social media[J].Business Aonizons,2011(54):241-251.
[4] 于婷婷.基于社会化媒体口碑的营销传播策略创新[J].新闻大学,2013(3):115-120
[5] 苏永华.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引导探析[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118-121
[6] 阮璋琼,尹良润.国外政治家使用社会化媒体的策略分析[J].当代传播,2012(3):85-86
[7] MAYFIELD A.what is Social Media?[EB/OL].[2007-03-21].[2013-05-18].http://www.icrossing.co.uk/fileadmin/uploads/eBooks/What-is-Social-MediaiCrossing-ebook.pdf.
[8] 张杰.“陌生人”视角下社会化媒体与网络社会“不确定性”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2(1):34-40
[9] 王明会,丁焰,白良.社会化媒体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分析[J].信息通信技术,2011(5):5-10.
[10] 栗战书.科学发展要有好的政治生态[EB/OL].[2010-12-21].[2014-05-10].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13533998.html
[11] 戴长征.社会政治生态视角下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J].探索与争鸣,2013(2):8-10.
[12] 万斌,丁友文.论和谐政治生态系统与政治宽容调节机制的构建[J].浙江社会科学,2012(7):34-41.
[13] 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37.
[14] 陆斗细.围观式政治参与:中国网络参政的深层透析[D].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5.
[15] 马小娟.论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J].中国出版,2011(12月下):22-25.
[16] 荆学民.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的“主体”问题[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24-28.
[17] 翟杉.我国微博政治参与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1(6):9-12.
[18] 孟建,卞清.我国舆论引导的新视域——关于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互动、博弈的理论思考[J].新闻传播,2011(2):6-10.
[19] 金萍华.污名与政治认同:社交媒体中的政治话语争斗——以孔庆东“粗骂”为例[J].新闻大学,2013(6):123-130.
[20] 孙藜.转化性建构:媒介事件与权力结构转变——新媒体语境下对媒介事件研究的再回顾[J].新闻记者,2013(9):80-85.
[21] 乔莉萍、刘慧卿.如何使网络围观现象发挥积极作用[J].传媒观察,2011(8):11-13.
[22] 张淑华.网络围观:新媒体时代的“另类”公民政治参与[J].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12-14.
[23] 尚虎平.网络围观下的政府效率——从睡狗行政到非满意:基于50个网络焦点案例的探索[J].公共管理学报,2013(1):117-144.
[24] 邹庆国.网络反腐:兴起缘由、价值解读与风险防范[J].理论导刊,2012(4):8-11.
[25] 杜创国,刘静静.建构网络反腐的“制度化”机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1):160-162.
[26] 黄丽萍.网络反腐的“围观效应”及其政治生态反思[J].领导科学,2013(2月上):6-7.
[27] 杜治州,任建明.我国网络反腐特点与趋势的实证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1(2):47-52.
[28] 刘文富.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46.
[29] 王文.Web 2.0时代的社交媒体与世界政治[J].外交评论,2011(6):61-72.
[30] 丘林川,陈韬文.新媒体事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8.
[31] 邹卫中.自由与权力:关于网络民主的政治哲学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5.
[32] 喻国明.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下政府角色的转型及行动逻辑[J].新闻记者,2012(4):3-8.
[33] 丁柏铨.论当下舆论引导格局[J].中国出版,2012(6):3-8.
[34] 许静.社会化媒体对政府危机传播与风险沟通的机遇与挑战[J].南京社会科学,2013(5):98-104.
[35] 闵大洪.新媒体环境下官员形象的重塑[J].人民论坛,2013(7):46-47.
[36] 吴云,胡广伟.政务社交媒体研究进展[J].电子政务,2013(5):42-50.
[37] 陈立丹,曹文星.微博问政发展趋势分析[J].编辑之友,2012(7):6-9.
[38] LEE G,KWAK Y H.An Open Government Maturity Model for Social Media-based Public Engagement[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2,29(4):492-503.
[39] 吴云,胡广伟.政务社交媒体的公众接受模型研究[J].情报杂志,2014(2):177-182.
[40] 姜秀敏,陈华燕.我国政务微博的实践模式及发展路径[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4-69.
[41] 陈超贤.政务微信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3(4):37-39.
[42] 李明德.大众传播的导向责任[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93-100.
[43] 桑玉成.政制发展中的政治生态问题[J].学术月刊,2012(8):5-13.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45]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代议制政府[M].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
[46] 李明德,刘婵君,宋宁.传统党报社会化媒体平台传播技巧初探[J].中国出版,2014(9月上):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