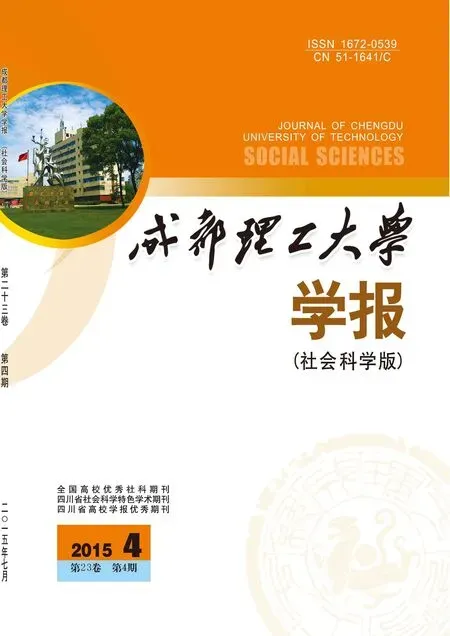人物的错位与降级
——《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与《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之深层比较
王 菁
(江苏警官学院,南京 210031)
人物的错位与降级
——《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与《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之深层比较
王 菁
(江苏警官学院,南京 210031)
福斯特的短篇小说《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与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一直是文学界热衷比较的文本。两部作品虽然在场景、人物、意象等方面十分相似,但这种表面的相似实际上与它们内在的偏离构成了强烈的反讽。通过分析两部作品中人物的构架、划分人物阵营,来全面剖析主人公卢卡斯先生和其女儿埃塞尔的身份错位与降级,从结构角度阐释《离开科罗诺斯之路》对《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深层反讽。
《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错位;降级;反讽
一、引言
《离开科罗诺斯之路》是E·M·福斯特早期重要的短篇小说,其故事情节与主题成为福斯特后期很多长篇小说的缩影。在《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中,无论是故事发生地,还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卢卡斯先生和他的女儿埃塞尔,都渗透着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痕迹。Laurent Lepaludier将这两部作品作为戏剧与短篇小说的互文本质研究的一个经典例证[1]。Catherine Belling认为,“很大程度上,故事的深意在于它与希腊戏剧的偏离”[2]。她把卢卡斯先生的悲剧归结于父女沟通的失败,认为《离开科罗诺斯之路》表达对于现代老年人尊重与关怀的期许。P·V·Subrahmaniam评论,卢卡斯先生“一方面幸免于难,另一方面则毁于一旦,在故事尾声,他被‘降级’(degraded)了”[3]。
国内学者对《离开科罗诺斯之路》的研究侧重于对文本的阐释:通过对地名与人物的互文性探讨[4]18,比较卢卡斯先生与俄狄浦斯命运的异同[5]129;通过研究泉水意象[6]73,探讨超自然幻想与现实的落差[7]36;以古为镜,探讨“古代悲剧”在现代社会中折射出的“无根空虚状态”[5]128以及这部现代悲剧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以期表达福斯特作品中一再传达的“只有连结”的祈望。
这些研究虽然都对《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与《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中的人物关系尤其是父女关系的映照与偏离进行了探讨,但是都建立在把《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作为一个浅层对应的参照系的基础上,从而忽视了两个文本中整个人物的宏观构架,无法挖掘《离开科罗诺斯之路》对《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结构反讽与深层背离。因此,只有将《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与《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平行地分析两部作品中全部人物的设置,才能从宏观上厘清人物的建构,在比较中彰显卢卡斯先生的“降级”和埃塞尔的身份“错位”,凸显《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中的深层结构反讽。
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与《离开科罗诺斯之路》故事梗概
《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是索福克勒斯“忒拜戏剧”三部曲中的一部,承接《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在这部剧中,年老失明的俄狄浦斯在女儿安提戈涅的陪伴下,流浪到雅典城外的一处圣林[8]2。了解到此处就是科罗诺斯后,俄狄浦斯记起阿波罗的神谕在预示他“弑父娶母”命运的同时,也指出科罗诺斯将是他的安息之地。在科罗诺斯人民的质问中,俄狄浦斯呼号自己也是命运的受害者,并要求面见雅典国王忒修斯。最终,俄狄浦斯的庄严风度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在当地人的指引下,他让女儿安提戈涅以“泉水”施行赎罪礼,洗净他冒犯圣林的罪过。接着,俄狄浦斯的另一个女儿伊斯墨涅也来到雅典城外。她告诉俄狄浦斯,忒拜的联合统治者克瑞翁正带兵前来。克瑞翁获知俄狄浦斯的安息之地会给所在城邦世世代代带来福祉与庇佑,打算将俄狄浦斯带回忒拜。俄狄浦斯痛恨当初将他驱逐出境的两个儿子和克瑞翁,相信只有神谕所指的科罗诺斯才是自己的安息之地,所以他断然不愿再回忒拜。克瑞翁劝说无果,只能强行带走俄狄浦斯的两个女儿,要挟俄狄浦斯回忒拜。后来,雅典国王忒修斯来到俄狄浦斯身边。俄狄浦斯告诉忒修斯,神谕指出他的安葬之地会给所在城邦带来福祉。忒修斯同情俄狄浦斯的命运,答应让俄狄浦斯安息在科罗诺斯,同时带兵救回俄狄浦斯的两个女儿。这场冲突过后,俄狄浦斯的儿子波吕涅刻斯也流浪到雅典,请求见俄狄浦斯一面。他向俄狄浦斯控诉埃忒奥克洛斯和克瑞翁夺权的暴行,哭诉自己流亡生活的艰辛,并希望父亲能够站在他一方(神谕指出获得俄狄浦斯支持一方将赢得胜利)。他说他已联合其他城邦来重夺王位,万事俱备,只欠父亲的支持。但是,无论波吕涅刻斯如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俄狄浦斯都不愿离开科罗诺斯,他痛恨这两个忘恩负义将他驱逐出境的儿子,第二场冲突结束。故事最后,伴随着隆隆的雷电声,俄狄浦斯感知到了神在召唤他的死亡。在忒修斯的帮助下,俄狄浦斯长眠于科罗诺斯。
在《离开科罗诺斯之路》[9]195中,英国游客卢卡斯先生和女儿埃塞尔来到希腊。随行的还有福尔曼太太,年轻的格雷汉姆和导游。卢卡斯先生已经老迈,他的女儿埃塞尔因对老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被福尔曼太太赞作“安提戈涅”。卢卡斯先生先于其他人来到一家希腊旅店外的一处树林,看到中空的树干里流出潺潺的泉水和当地人在树干中供奉的神龛,灵魂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因此他决定留宿在旅店,感受大自然与神灵所创造的奇迹。但是,他的女儿埃塞尔却不愿就此停留,她和同行的游客都觉得这家旅店是想榨取卢卡斯先生的钱财。在劝说未果的情况下,埃塞尔请求格雷汉姆将卢卡斯先生强行带走。于是年迈的卢卡斯先生无奈地踏上了“离开科罗诺斯之路”。最后,故事的背景又回到了英国,埃塞尔已经快要嫁人,而卢卡斯先生成了一个整天抱怨、遇事冷漠的人。后来,埃塞尔偶然得知她强行带走卢卡斯先生的当晚,灾难突至,希腊旅店被倒塌的树木压垮,旅店一家人也在灾难中全数殒命。埃塞尔感激上苍的庇佑,但卢卡斯先生却对自己的死里逃生充耳不闻,继续叨念着生活琐事。
三、主人公地位的挑战
在《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中,英国旅行团中的福尔曼太太明确指出了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与卢卡斯先生和埃塞尔的对应关系:“当然,你和你父亲,就是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所以你们理当驻足在科罗诺斯!”[9]198然而除年事已高之外,卢卡斯先生与俄狄浦斯根本没有那么类似。《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的俄狄浦斯虽然老迈失明,但他始终保有尊严与选择的权利:他受到了忒修斯国王的尊重与庇护,他可以痛斥与诅咒两个不孝的儿子,他欣然遵照神谕获得了平静的死亡。因此,悲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俄狄浦斯主人公的地位,反而凸显了他的尊严与抉择。相反,俄狄浦斯的现代对应——卢卡斯先生,却被残忍地剥夺了选择的权利,被强行带离了他心目中的“应许之地”。卢卡斯先生主人公地位的“错位”与“降级”不仅表现在他凄凉晚景中,而且始终渗透在《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中。
(一)错位:福尔曼太太言辞暗指
福尔曼太太是《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中英国旅行团的一位成员,小说对她的描写不多,但她是明确指出卢卡斯先生和埃塞尔与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对应关系的人:福尔曼太太总是称埃塞尔为安提戈涅,而卢卡斯先生只好充当俄狄浦斯的角色,这也是大众心目中他唯一能充当的角色[9]195。仔细考虑福斯特的表述,我们就会发现在福尔曼太太和同行游客的眼中,先有像安提戈涅一样孝顺的埃塞尔,后有像俄狄浦斯一样需要照顾的卢卡斯先生;而不是先有主人公卢卡斯先生,才有照顾卢卡斯先生的埃塞尔。在他们眼中,卢卡斯先生的存在不为别的,只为证明与凸显埃塞尔是一个多么孝顺的女儿。而且,卢卡斯先生倔强的脾气、古怪的性格,在同行人员看来,也只能证明埃塞尔对他的关怀是多么的有难度,多么的无微不至。
因此,本是主人公的卢卡斯先生在大众眼中俨然只是孝顺女儿的“陪衬”。通过福尔曼太太之口,卢卡斯先生的主人公地位第一次受到了挑战。
(二)降级:“唯二”的幸存者——卢卡斯先生和一头猪
在福斯特小说的结尾,埃塞尔从一份希腊报纸上得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夺走了小旅店中的五口人的性命,而那家旅店就是卢卡斯先生当日执意要过夜的地方。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埃塞尔没有强行带走父亲,那么卢卡斯先生必定也要遭受不幸。因此,卢卡斯先生是这场灾难的幸存者。同样,小说还介绍了另一个细节:随行的导游讨价还价,从旅店人家处买下一头猪,这头猪在被带离科罗诺斯时,“发出尖锐的嘶叫声”[9]200。可以说,如果导游没有买下这头猪,它很可能也会和它的主人一样在风暴中死去。因此,这头猪也成为了灾难的幸存者。“唯二”的两个被强行带走的幸存者——卢卡斯先生和一头猪——这样一个奇异的组合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哭笑不得。
但是,“唯二”幸存者并非偶然,它透露出一条重要的讯息:老迈的卢卡斯先生不仅失去了决策的尊严,甚至丧失了作为人的权利——和猪一样被强行带走,和猪一样“被幸存”在这个世界上。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如果这头猪有任何意识的话,它很可能庆幸自己的幸存;然而卢卡斯先生虽然知道幸免于难,却毫不在意:“他什么也没说,继续忙着给房东写抱怨信”[9]202。
综合以上两点,本是主人公的卢卡斯先生,在“错位”地成为女儿的陪衬后,再一次沦为和猪一起成为“幸存者”,他的主人公地位又一次受到挑战。毫无疑问,经历“错位”与“降级”的卢卡斯先生,他的主人公地位已名存实亡,比之他在希腊悲剧中的对应者俄狄浦斯,他空有小说主人公的虚名,丧失了主人公的尊严。
四、人物阵营的划分与两大阵营的斗争
长期以来,对《离开科罗诺斯之路》的人物讨论都局限于卢卡斯先生和埃塞尔,而忽视了小说中整体人物建构与《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平行比较。本节首先罗列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并通过分析人物的言行来划分人物的阵营,从结构上阐释埃塞尔对古希腊原型安提戈涅的两次角色“错位”。
(一)人物阵营的划分
《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的主要人物是:老迈失明的俄狄浦斯、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和伊斯默涅、忒拜的统治者克瑞翁和埃忒奥克洛斯、俄狄浦斯被流放的儿子波吕涅刻斯、雅典国王忒修斯和他的臣民。故事中的俄狄浦斯背负“杀父娶母”的罪名,长年漂泊。在受到神谕指引后,他获知科罗诺斯就是他的安息之地。他爱憎分明,痛恨将他驱逐的两个不孝子,信任同情他命运的雅典国王忒修斯。忒修斯亦同情俄狄浦斯,并答应为其提供庇护与安葬,后来还为挽救俄狄浦斯的两个女儿,不惜与克瑞翁大动干戈。由此可知,俄狄浦斯想要留在科罗诺斯,两个女儿和忒修斯也尊重与支持他的意愿;相反,克瑞翁和波吕涅刻斯则为了各自的利益,妄图迫使俄狄浦斯离开科罗诺斯。
《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中的主要人物有:卢卡斯先生、埃塞尔、福尔曼太太、格雷汉姆先生、导游和小旅店一家五口人。卢卡斯先生本来“庆幸他们自己带了食物,可以在野外就餐”[9]195,而不用去那家旅店。可是在受到中空树干中潺潺泉水和当地人摆放的神龛的触动后,他对旅店一家人的印象却大为改观:“这些人看起来友好而文明”,“很快我们将成为朋友”,“虽然没和他们说过话”,但他“爱这些人,就像他热爱树影下活动着、呼吸着或存在着的一切那般”[9]198。更重要的是,卢卡斯先生决心留宿旅店,因为他不愿意离开这个“某一刻,他不仅发现了希腊,还有英国,甚至整个世界和生活”[9]197的地方。他明白回到英国就意味着老无所依,而在科罗诺斯,“这个地方属于他”[9]196。与此同时,小旅店的拥有者——一位纺线的老妇人,对卢卡斯先生的留宿欢迎有加,旅店里的两个孩子也朝着强行带走卢卡斯先生的格雷汉姆掷石子,旅店里的年轻人甚至为挽留卢卡斯先生和格雷汉姆大打出手。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卢卡斯先生和旅店一家人都持有“希望卢卡斯先生留在科罗诺斯”的立场;相反,以埃塞尔为代表的英国旅行团则都反对卢卡斯先生留在科罗诺斯。
通过上述对人物立场的罗列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与《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一条共同的主线:主人公在科罗诺斯的去留问题。而对于主人公的去留,每部作品中的人物又持有鲜明的立场,构成相对的两个阵营。由此,两部作品中的人物阵营可以依据“是否尊重主人公意愿,支持主人公(卢卡斯先生或俄狄浦斯)留在科罗诺斯”划分,见表1:
从阵营的划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埃塞尔身份的第一次“错位”:被公认为“安提戈涅”的埃塞尔与安提戈涅非但不属同一阵营,反而“倒戈相向”,公然违背父亲卢卡斯先生的意愿。另一方面,被英国旅行团嗤之以鼻的希腊旅店一家却与卢卡斯先生同属一个阵营,捍卫主人公留在科罗诺斯,而他们的努力竟然对应了《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忒修斯和雅典人民为俄狄浦斯而战的英姿。因此,在古希腊悲剧的投影下,《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中人物的立场错位,尤其是埃塞尔与古希腊原型安提戈涅的角色偏离,为福斯特这篇小说增添了强烈的反讽意味。
(二)两大阵营的斗争:劝说还是武力
仔细分析《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情节,可以梳理出以武力和劝说为标志的两场阵营对抗。第一次对抗出现在克瑞翁(与俄狄浦斯的小儿子埃忒奥克洛斯联合统治忒拜)在获知俄狄浦斯的安葬之地将给所在城邦带来福祉后,来到雅典城外,妄图强行带走俄狄浦斯。但在忒修斯和雅典人民的阻拦下,克瑞翁无奈只能掳走安提戈涅和伊斯默涅来要挟俄狄浦斯。最终,对抗以雅典国王忒修斯救回了安提戈涅和伊斯默涅告终。第二次阵营对抗出现在俄狄浦斯的大儿子波吕涅刻斯与俄狄浦斯的相遇。波吕涅刻斯原本是忒拜的统治者,后被克瑞翁与弟弟埃忒奥克洛斯联合夺权。为此,他不惜集结军队,希望重夺忒拜。因为神谕指出俄狄浦斯支持的一方将赢得战争的胜利,所以他苦寻父亲,哀求俄狄浦斯支持他重夺忒拜。可是,任凭他如何劝说,这场对抗还是以俄狄浦斯不为其所动、坚持留在科罗诺斯而告终。根据对两场对抗的梳理,我们可以总结出《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阵营对抗的两种模式:克瑞翁动用武力威胁俄狄浦斯,波吕涅刻斯凭借雄辩劝说俄狄浦斯,但两场对抗均以俄狄浦斯的胜利告终。
同样,《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也分别以武力与劝说形成了两场阵营对抗。第一次是埃塞尔千方百计劝说卢卡斯先生离开科罗诺斯:“好爸爸,是我不对,我不该那么开玩笑,我知道错了。但是,我们不能离开旅行团单独行动啊,要知道,在这住一晚我们就赶不上佩雷特港的游船了”[9]199。但是,无论埃塞尔“劝说还是恳求”[9]199,卢卡斯先生仍旧一意孤行。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埃塞尔只能无奈地陪着父亲先生进了旅店,但她仍旧不放弃。同时,福尔曼太太说起了“跳蚤”,格雷汉姆说旅店老板可能“伤害”卢卡斯先生,希望借此打消卢卡斯先生留宿的念头。然而,卢卡斯先生却不在乎这些,他相信“在这个地方,和当地人一起,正有一项庄严的活动等待着他,这项活动将使整个世界变得美好”[9]200,而“他要是离开了这个赋予他欢乐与祥和的地方,他就要成为傻瓜和懦夫了”[9]199。最后,卢卡斯先生甚至提出自己可以独自留在旅店。眼看情况一发不可收拾,埃塞尔请求同行的格雷汉姆先生帮助,由此引发了第二场阵营对抗:“我不擅长劝人,但是我也许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帮助你”[9]200。在得到埃塞尔的默许之后,格雷汉姆“抬起卢卡斯先生并把他放在鞍上”[9]200,卢卡斯先生就这样走上了离开科罗诺斯之路。对于格雷汉姆的武力,卢卡斯先生“什么也没说,他也没什么可说的,即使意识到树荫不在,泉水不闻,他还是面无表情”[9]200。但是,希腊旅店一家却捍卫起卢卡斯先生,先是两个孩子朝着格雷汉姆掷石子,后是旅店的年轻人拦下卢卡斯先生的骡子。但最终他们都没有敌得过格雷汉姆的身手。可以说,《离开科罗诺斯之路》延续了武力与劝说的对抗模式:埃塞尔通过劝说让卢卡斯先生离开科罗诺斯,格雷汉姆通过武力带走了卢卡斯先生。两场对抗的最终结果是反对方获得胜利,迫使卢卡斯先生离开了科罗诺斯。对于两部作品中武力与劝说的阵营对抗模式见表2:
通过表2可以看出,埃塞尔的角色又经历了第二次“错位”:本该是支持阵营中“安提戈涅”的埃塞尔,非但进入了反对阵营,并且凭借“劝说”的反对模式,埃塞尔实际上对应了《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俄狄浦斯的不肖子波吕涅刻斯。同时,格雷汉姆凭借“武力”掳走卢卡斯先生的反对模式,对应了《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的克瑞翁。讽刺的是,克瑞翁作为忒拜的统治者,是为了城邦利益才要掳走俄狄浦斯;而对于格雷汉姆,除了可以在埃塞尔面前展示自己的“力量”(strength)[9]201外,他与卢卡斯先生没有任何利益瓜葛。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的“劝说方”与“武力方”——波吕涅刻斯和克瑞翁——是对抗关系,他们是为了对抗彼此才争取俄狄浦斯的支持。而《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中的“劝说方”与“武力方”——埃塞尔和格雷汉姆——却是合作关系。并且,他们通过合作,最后以武力的方式成功地带走了卢卡斯先生。这场武力的胜利,何尝不是另一层讽刺。
综合以上分析,本节通过梳理人物言行、确立人物立场,按照“是否尊重主人公意愿,支持主人公留在科罗诺斯”来划分人物阵营,指出了埃塞尔身份的第一次“错位”和旅店一家人与忒修斯的对应;接着根据“反对主人公留在科罗诺斯,劝说还是武力?”的分析,提出了埃塞尔身份的第二次“错位”;在此基础上,埃塞尔和格雷汉姆讽刺的合作关系以及《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中“武力的胜利”,又进一步为福斯特的这篇小说增强了反讽意味。
五、结语
在《短篇小说集》(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E ·M·Forster)中,福斯特道出了《离开科罗诺斯之路》的创作背景:“第二年,我在希腊又一次复写了这个模式,那时,《离开科罗诺斯之路》好似就悬挂在奥林匹亚不远处的中空树干上,使我灵感一现”[10]。可以说,福斯特的早期作品浸润着深深的希腊情怀,而他的整个写作轨迹都延续着“错位(displacement)”[11]与“降级(degradation)”的主线。本文正是综合了福斯特的希腊情怀与其作品中“错位”和“降级”的主线,通过《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平行比较,从文本中挖掘卢卡斯先生主人公地位的名不副实,阐释卢卡斯先生和埃塞尔错位的主人公身份;同时,在分析两部作品中人物立场的基础上,以“是否支持主人公留在科罗诺斯”为依据,划分了两部作品中的人物阵营及其对抗;并细化“反对阵营”,解析出“劝说”和“武力”两种反对模式。综上所述,正是福斯特小说与古希腊悲剧层层嵌套又貌合神离的人物关系,才为这篇小说赋予了强烈的反讽意味与高超的艺术表现。
[1]Lepaludier Laurent.Theatricality in the Short Story: Staging the Word?[J].Journal of the Short Story in English,2008,(51):17-28.
[2]Belling Catherine.Annotations of The Road from Colonus[EB/OL].(2010-11-21)[2014-5-10].http://litmed.med.nyu.edu/User?action=view Annotator&id=32.
[3]Subrahmaniam.P.V.Symbolistic Adequacy in the Short Stories of E.M.Forster[EB/OL].(2008-01-01)[2014-5-12].http://yabaluri.org/TRIVENI/CDWEB/symbolisticadequacyintheshortstoriesofemforsterjan67.htm
[4]邢海霞.福斯特的《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互文性研究 [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2,(3):18-21.
[5]叶蔚芳.平行的旅程 迥异的归宿 —— 对《离开科罗诺斯之路》现代弱者生存状况的评析 [J].外国语言文学,2010,(2):128-132.
[6]李宛悦,邱广娟.《通往柯林斯之路》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探新[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8,29(9):72-74.
[7]沈雁.幻想照亮旅途——福斯特的《离开科罗诺斯之路》赏析[J].英语自学,2007,(7):34-37.
[8]Sophocles.Oedipus at Colonus[M].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Inc,1999.
[9]王守仁.英国文学选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94-204.
[10]Forster,E·M.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E·M.Forster[M].London:Sidgwick and Jackson,1947.
[11]Christie,Stuart.Worlding Forster:The Passage from Pastoral[M].New York:Routledge,2005:2.
Displacement and Degradations of Characters: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Road from Colonus and Oedipus at Colonus
WANG Jing
(Jiangsu Police Institute Foreign Affairs Office,Nanjing Jiangsu 210031,China)
E·M?·Forster’s The Road from Colonus has been popularly studied with Sophocles’Oedipus at Colonus.Although the two works share features such as Colonus the setting,characters and symbols,their similarities actually imply great irony by hiding inherent disparities.This article is to place The Road from Colonus under a panoramic projection of the Greek tragedy.By analyzing all characters in the two works and diving each party on the basis of characters’standpoint,the article addresses the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and degradations of Mr.Lucas and Ethel from their Greek prototypes,which generates deep irony in Forster’s modern story.
The Road from Colonus;Oedipus at Colonus;displacement;degradations;irony
I106.4
A
1672-0539(2015)04-0087-05
编辑:鲁彦琪
10.3969/j.issn.1672-0539.2015.04.018
2014-09-15
王菁(1990-),女,江苏常州人,硕士,教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海外汉学翻译研究。E-mail:roy190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