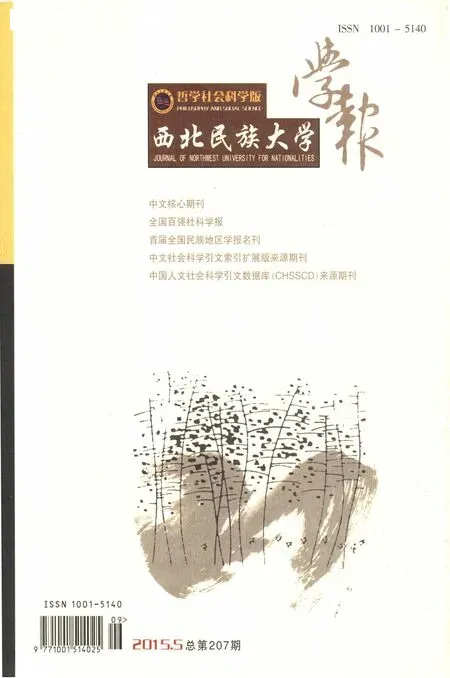民族智者的生态忧虑——朱玛拜·比拉勒小说的生态批评阐释
郑 亮,朱亚丽,张 凡
(1.石河子大学 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832000;2.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100871)
一、引言
在生态文学的发端之作《寂静的春天》中切尔·卡逊说道:“归根结底,要靠我们自己做出选择。如果在经历了长期忍受之后我们终于已坚信我们有‘知道的权利’,如果我们由于认识提高而已断定我们正被要求去从事一个愚蠢而又吓人的冒险,那么有人叫我们用有毒的化学物质填满我们的世界,我们应该永远不再听取这些人的劝告;我们应当环顾四周,去发现还有什么道路可使我们通行。”[1]自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然而由于物欲的无限增长,人们开始对养育自己的大自然大举入侵,科技的进步更是助长了这种气焰,长期以来人与自然温馨和谐的关系被打破,自然的神圣性被亵渎甚至是肢解,人类既无法回复到原始的农耕文明社会,又无法超越当下这个尴尬的局面。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紧张,生态危机时代到来。
文学反映时代,时代推动文学发展。生态危机的爆发使一大批富有责任感的作家对连同自己在内的同胞们所犯下的罪行勇敢的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以期唤醒人们的生态自觉意识,从而为人类今后发展的道路提供帮助,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文学应运而生。王诺教授在其专著《欧美生态文学》中,为生态文学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2]由于生态文学诞生的缘由是全面生态危机这一可悲的事实,所以生态文学的写作往往带有浓郁的悲剧彩色。大多数生态文学作家,在表达方式上倾向于宏大的叙事模式,在题材的选择上多选取生态冲突尖锐,生态灾难惨烈等场景来叙述,文章的主旨多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警告、控诉,感情的基调也多是悲愤痛苦。单一的写作模式使文学成为时代的传声筒,忽略了文学自身的审美要求。正如雷鸣所说:“由于拘囿于生态事件再现的真实感,一些生态小说的文本尽管不乏生活的实感,却因为作者未能发挥各自‘灵感’去对真实事件进行更大程度的提炼、加工和改造,当然更没有将富有个性化的艺术想象最大限度地融入生态叙述中……由此失去了深远的艺术韵味和魅力。”[3]这种体裁沉重又缺乏内蕴的文学在当今这个文学被边缘化的社会中明显底气不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生态文学之路走得更长远,使生态文学散发出深远的艺术韵味和魅力,成为了当下生态文学作家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朱玛拜·比拉勒就是这样一位力求寻找一条与大众心灵契合的通道,使生态文学回归文学的本源的当代哈萨克族作家。自1956年开始文学创作,朱玛拜·比拉勒便笔耕不辍,发表作品有《深山新貌》《寡妇》《原野小鸟》等5部长篇小说,另有《蓝雪》《岁月》《山影朦胧》等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曾获《民族文学》杂志1988年“山丹奖”,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以及新疆哈萨克—柯尔克孜文学“飞马奖”等众多奖项。在他的这些作品中,无处不充盈着诗意的蔚蓝天空、绿草如茵的大草原、静谧神圣的雪山以及那些鲜活可爱的动物们等有着新疆地域特色的意象,这些意象使其作品散发着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众所周知,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文化是众多少数民族作家写作表达的窗口,但有时这种标签式的地域文化贩卖往往也成为作家创作的瓶颈。在朱玛拜·比拉勒的作品中,哈萨克民族生活的地域以及历史积淀的民族气质是其作品生命的底色,然而他却不局限于此,他用寓言式的动物书写将民俗母题再度构建,不断地对新疆自然生态环境与哈萨克民族文化进行冷静分析,拓展了民族文化的内核,进一步观照人类以及整个宇宙的发展,从而引发读者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如何定位的生态性思考,为生态文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二、人与自然构建的诗意生态图
“人类的文化表述和人文精神如果离开了对自然的认识、见解、启示和物化符号系统的文化表述,人文精神几乎无从生成和传达。”[4]人类文化的发展依托于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描绘也一直是文学的经典母题之一,而今作为生态危机语境下出场的生态文学其创作已不能停留在传统文学写作中追忆自然之美或生态暴露危机这两种模式为代表的浅层写作表象上。前者多是文学文本用一种超越的姿态将实际生活距离化、审美化的形式,对于被规训世界奴役丧失了思索能力的人来说是一种乌托邦理想。后者大多数则是采用雷同形象创造的普遍悲剧,缺乏生命立体感与文学审美价值,对于生态危机显示出的丰盈的文化启示也缺乏深入的思考。那么如何突破这两种陈规模式,将生态理念在大众的阅读接受范围内潜移默化的传播,成为众多生态文学作家思考的问题。
在朱玛拜短篇小说《蚊子》中,作家这样概括哈萨克牧民与自然交融一体的平淡生活:“到了夏牧场,他们会忘却昔日的苦难,精神焕发;鲜血在他们的血管里欢快的流淌;喜悦在他们脸上跳跃;愉快的心情在他们的心里激荡,他们像冬天里被母亲奶大的小马驹那样自信豪迈。年轻人戴着漂亮的帽子,在月夜下的林间空地歌唱……那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卷。天下又有什么能比的上那如丝绸一般多情的山风拂过你的脸更惬意呢?”[5]作者采用了一系列富有情态的动词,如“流淌”“跳跃”“激荡”来表现哈萨克牧民对于夏牧场生活的热爱,同时从作者截取的一个富有诗意的场景“月夜林间欢唱”来表现人与自然关系,善良质朴的哈萨克牧民认为在大自然地拥抱下欢畅便是最大的满足。自然已不仅仅是作为哈萨克牧民生存的栖居地,很大程度上大自然已经扮演了母亲的角色,人们生活在于此,所有的喜怒哀乐围绕自然母亲生发,自然的本性根植于血液。在这里,作家选取了哈萨克民族在自然中常态化的生活片段,用些许诗意的浪漫色彩装点使得自然的神性美与野性美再度构建,让抽象的生态意识化作为具体可感的客体,逐步引导人们感受到自身与自然生命的内在契合,由此展开人类生命存在价值的深层次思考,生态理念便在美的引导下植入人心。
除了将自然作为生活依附的重心以外,哈萨克人民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深深地打上了自然的烙印。由于地处边疆,世代以放牧为生的哈萨克牧民还未被现代工业文明完全浸染,他们的生活带有人类早期如孩童般蒙昧未开的色彩。这源于世代哈萨克族人与自然相处逐步形成的宗教信仰。除了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宗教文化以外,从草原游牧文化生长出来的萨满教在哈萨克人心中一直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萨满教以万物有灵为信仰基础,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为主要信仰内容,将自然规律熔铸于日常生活,以自然规律来构建社会秩序的一种原始多神教宗教。萨满教对哈萨克人的精神性格有着重要的影响,人类生命对自然的皈依,社会秩序对自然的仿效,使哈萨克人的精神性格也走向了自然,生命之幕启落皆自然,人生之舟浮沉亦皆自然,幕之启落,岸之远近,随剧之短长,风之疾,不可强求而致。”[6]正是由于受萨满教灵魂不灭的思想观念影响,哈萨克人对生死持一种如同自然四季交替的淡然、豁达的生态生命观。
《劲草时分》讲述了74岁的哈萨克老人瓦利不幸患上了癌症,在得知这一噩耗后的一年里他仍平静生活,坦然面对死亡的故事。在老人生命即将结束的那些日子,他像往常一样很早起床做晨祷,给邻居家的牲畜松了绳索,让它们去吃草,替雪青马梳理驼虱去除痒痛,看到“雪青马犹如羚羊眉一般漂亮的额头眉头舒展了。这快感也感染了瓦利老人,他竟也惬意地动了动肩胛骨。”[7]朱玛拜在描述这一细节的口吻是平和的,甚至带着几分幽默,他没有过多的描述老人被病痛百般折磨的惨状,而是用一个人与动物温馨相处的场面将死亡的阴影淡化,仿佛只是一片树叶优雅地飘落,化为了春泥。与这种澄明恬静的生命观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追求的是不惜任何代价企图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中实现无限的资本积累,穷尽一生却被物欲左右,在城市所筑垒的牢笼中迷失自我,丧失了源于生命本质的自然属性,灵魂在荒原中游荡,不知何处是归途。
小说的结尾,瓦利老人安静地呼出了最后一口气。这时,夜空中一颗美丽的小星斗化作流星在长空里留下一道玫瑰色的光亮后,大地恢复寂静,亦如70多年前瓦利出生的那夜。这一场景隐喻着生命源起于自然,终归于自然,无论人类曾经是多么的不可一世终将如同自然的一草一木,春荣秋枯,四季兴替。在这里,朱玛拜使用了留白手法,使无限的生态内蕴隐藏在质朴简洁的文字背后,这并不是作家刻意而为之的言说姿态的调整,而是通过文本无声的恒久魅力来阐明现代社会生态与原始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试图激发读者与自然的情感共鸣,在自然的脉动中体悟万物一体的生命活力,合理构建人类自身的生存空间,使人诗意的栖居在自然之中。
三、基于生态的动物书写
由于哈萨克牧民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草原上的动物与人类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因此,本土作家常常将人与动物相互残杀或和谐共舞的故事作为切入点在文学作品中广泛表述。虽然此类作品中不乏动物的形象,但是大多数小说沿用的是以人为主体的叙述模式,动物作为背景或是承载了作家的主观愿望,作为一种精神象征的载体而存在。这种“人本位”的视角表现的仍是动物对于人的价值,动物作为生态系统中的成员之一,理应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权,获得应有的尊重。朱玛拜清醒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动物成为他所构建的文学世界当中的主角,这些动物形象鲜明生动,集灵动的兽性和深刻的人性于一体,在动物小说界中被广泛征引。他以动物观世,通过动物的思维方式反观人类世界的异质性,这种解读模式给读者带来一种新奇的阅读体验的同时,也将读者的身份从人类意识中抽离,从动物的角度感知生命体验。从这个层面来讲,这种具有强烈先验性的叙述模式本身就是生态意识观照下的产物,加之浓厚的生态情怀使得作家的动物书写散发出一种对于生态危机的强烈反思意味。
短篇小说《皮笼套》从标题的设置来看,作者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意味极浓。皮笼套是人类为使动物驯服,残忍的在动物身上设置的枷锁。小说主角黑马就是一匹被主人的皮笼套牢牢禁锢受尽折磨却仍然桀骜不驯渴望自由的骏马。文章的开头朱玛拜用丰富的想象力,诗意的文笔回忆了黑马童年的自由时光。“那梦幻一般的童年,对黑马来讲是多么的短暂啊!那个时候它是大自然里最受宠爱的孩子,是最无忧无虑的生灵。大地爱它,母亲也爱它……它在母亲的爱中享受生活,享受大自然。于是,它又向广阔的草地飞奔而去了,四只像被油漆刷过一样玲珑剔透的小蹄子,染上了淡淡的青草汁,而那青青的草地上也留下了一串串可爱的马蹄印,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自然……”[8]然而好景不长,很快它被新主人挑去作脚力,命运从此发生了巨大变化。它那原本只属于旷野上和煦的山风的脊梁,充满活力柔软的皮毛上爬上来一个人类,凶残的对它为所欲为。它的嘴里被那个人硬生生的塞进浓重的铁锈味的铁嚼子,它试图咬碎,可是从它嘴里喷出来的竟是自己的鲜血。每一次向着旷野飞奔逃跑都换来主人无情的鞭打,像无数小刀将它肉体千刀万剐。无数次的反抗换来的是变本加厉的折磨,就这样在它体内孕育的小生命——另一个未来大自然的宠儿,还没看到这个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就死亡了。
在朱玛拜看来大自然垂青于人类,同样也施爱于其他骨肉,人与动物同样受自然的哺育才得以生存,没有动物的草原是缺少灵魂的,甚至是死亡的。秉承着这种对生命的普遍关怀,作家的叙述角度突破了人类的主体性限制为动物代言,使读者忘却人类语言,深入体察动物的悲惨遭遇,以此反观人类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不顾动物的自然天性对其疯狂的折磨的冷漠贪婪人性,揭示出人类丧失自然本质呈现出病态的事实。作者出于不忍亦或是心中存有希望,在小说的结尾,安排了黑马终于挣脱皮笼套的情节,借黑马之口表达了希望人类不再自私冷漠的殷切愿望:“哦!大地,我的母亲,我的主宰,认出我来了吗,我是你的孩子,是你的财富。我知道,你的每一份爱里都有我的一份……母亲,请你不要再失去你的孩子,不要再让人类伤害你的心灵。”[9]朱玛拜的笔下,动物不仅是和人类平等共生的大自然母亲之子,而且还是自然智慧创造的生命奇迹,拥有着高贵的尊严。《白马》中牧人为了使高贵的白马群繁衍下来,用卑鄙的伎俩强行给白马交配,而这触犯了白马不找自己同种马作配偶的禁忌,当白马得知真相后“它猛地抬起头,脸上顿时透出一种烈性的神情;先是有一滴泪从它眼角淌下来,然后是一片红雾掠过指甲盖大小的晶莹的瞳仁,又一股热腾腾的汗水流遍全身……”[10]高贵的白马受到了这样的奇耻大辱在悲愤中选择了死亡以保留自己的尊严:“白马站在崖顶上,最后嘶叫了一声,震得大地颤动,谷间回声四起。然后,它甩了甩了头,猛咬一下自己的膝头,腾空而起,挥舞着云似的银鬃和尾巴,纵身跃下崖去……”[11]白马纵身一跃留给人类的是深深的震撼。在利益最大化的心理驱使下人类无视动物的痛苦,惟一的行动目标便是利益的得失,为此不惜用卑鄙的手段改变动物的本性,对非人类的生命毫无敬畏之心,体味不到它们鲜活的情感,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在精神的荒野中迷失了方向。而人类对自然所做的这一切是否真的换取应有的回报,这一切又是否真的值得?朱玛拜同样借动物之口给出了答案。
小说《天之骄子》中的天之骄子——隼,因为拥有着大自然所赐的飞翔本领而被老猎人觊觎,老猎人带着年轻的儿子精心布阵多日终于将其擒获。然而它与白马一样桀骜不驯,勇敢顽强的捍卫着自己的尊严,直到饥饿的本能使它失去了反抗的欲望,改变了它那原本在蓝天中驰骋的自由天性,乖乖的做起了人类的俘虏,为主人捕杀其他动物。至此,人类仿佛真的是胜利了,也应验了文中老猎人的那句话:“整个宇宙都是为人类而存在的。”[12]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作者精心刻画的主角——费尽心思将天之骄子擒获的老头,并没有因为这一员出色的干将而把天下的财富都据为己有,而是变做一堆腐烂的臭肉埋在枯草丛生的土堆下,任昆虫蝎子出入。一只陌生的隼落在老头的坟茔上发出轻蔑的嘲笑:“老头,你不是曾说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为了养活人类而存在的吗?现在你怎么倒了位置,为了养活小昆虫而存在了呢?”[13]
利奥波德在其1947年撰写的《沙乡年鉴》一书中提出了“大地伦理”理论,认为大地不仅包括土壤、水、空气,而且还包括在其上生长的动物、植物。它是一个共同体,人也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这意味着人也是食物链中的一环与其他生物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在人与自然的漫长的角逐中,人类似乎用自己的“智慧”和科技手段征服了自然,主宰了世界,成为世界的霸主。殊不知,这种对于自然不断征服的过程也是人类丧失自然向度和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过程,其代价不仅是人类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对于其他生物亦是如此。朱玛拜的动物书写放弃了作为人类主体话语的霸权,不再把自然作为攫取资料的客体,尊重自然界其他生物,建立了平等共生的新型话语权。而这一话语权的建立为扭转人类与自然紧张局面提供了启示。
四、双重危机中的生态呼吁
生态文学家不是政治家,无需向社会提供具体的应对良方,其写作的意义也并不是呼吁人类回到远古的蛮荒世界以求生态的和谐,而是唤醒人们普遍丧失的信念,在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双重危机中获得救赎。正如别尔嘉耶夫在《人的奴役与自由》这本书中所说:“现在的问题:如何去抗击文明。当然不能像强悍的野蛮人和善良的自然人那样,凭借自然的本性去抗击。那基点取于自然主义,而自然主义的‘枪炮’早已老得不能再老。自然本性中的善良和自由均无法遏止文明的恶和文明的奴役。自然不能战胜文明的本质,唯有精神方可制胜。”[14]
小说《再见吧,你这个倒霉的祖传业》中讲述了在工业文明的影响下世代以游牧为生的达纳别克老人一家难以再依靠祖业维持生计的故事。深夜家人都已酣然入梦,惟有达纳别克站在窗前听着屋外咆哮的风声,陷入深沉的回忆中。祖辈世代生活的那片牧场曾经有着世界上最清新的空气,最纯净的水,山上的野生山葱和爬地松郁郁葱葱,姑娘纯洁的如天山上的雪莲花一般圣洁,一切仿佛都在净化人类的心灵。然而现在外界纷繁复杂的讯息打破了这片古老的草原往日的宁静。“多年来,人们凿山开石,炸矿修路,把个风光秀丽的草场搞得个满目疮痍,到处是高炉,到处是硝烟,鸟死了,树死了,人乏了,地也毁了。”[15]除了生态环境被破坏以外,人们的精神也陷入了危机,自然失去了“家园”的意义,人们对自然的一切事物都以人类的价值利益观来计量,使得原本栖息万物的自然被挖掘利用的千疮百孔。“但是现在不比从前喽,山里的人已经学坏了,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喝酒闹事。人变坏了,环境也跟着变坏了,空气与水都成了坏脾气……这些年常有外地人来此淘金,挖山药,而他们都是一些利令智昏而且毫无法制观念的人。为了钱,可以做任何伤天害理的坏事。他们挖坏了水道,把山石从高高的崖上推下去,杀生,残害珍稀动物,还偷盗牧人家的牲口……”[16]小说的结尾,仍旧是那狂风呼啸的夜晚,达纳别克老人内心是绝望的,他绝望的不仅仅是因为自己不再是一个出色的牧人,祖业中断在他手里,更让他绝望的是曾经的青山绿水的家园变成了绿色绝迹的荒漠,而子孙们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幡然醒悟。
面对自然的荒凉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异变,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朱玛拜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思考,他用文字将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最终惨痛后果以寓言的形式展现出来,逼迫人们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在混沌中觉醒。小说《生存》就讲述了因为人类的残暴招致动物报复的故事。主角黑驼受尽主人的折磨后勇敢出逃,凭借着天生雄性力量的优势成为了一代“驼王”。然而欲望无穷的人类在征服自然土地之后又将贪婪之手又伸向了骆驼家族。随着驼群的支离破碎,黑驼悲痛万分的带着剩余的成员与人类进行了殊死搏斗,一场恶战之后驼王带着满身的伤痕重新召集驼群带领它们走向自然的怀抱。至此黑驼的故事告一段落,但是人类与驼群的斗争还在继续,无数勇敢坚强的“沙漠之舟”们顽强的对抗着人类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后来,据说在整个沙漠地带、在叶连哈布尔哈山麓出现了吃人的骆驼。”[17]这些原本天生心软、易受惊吓的、长着如少女般温柔清亮眼睛的动物们最终变成可怕的吃人恶魔,动物本性的改变是大自然向人类报复的前兆,而陷入精神危机被利益蒙蔽双眼的人们仍然疯狂地向大自然进攻,对于生态环境的恶劣所产生的后果没有明确的概念。于是,朱玛拜在小说《朦胧的山影》中向人们描述了生态危机达到无法遏制后世界失去控制人类饮血嚼骨的惊悚场景。文中的白蹄坤在主人变态式的强硬训练后成为一名出色的杀手,为主人赚取不义之财。从此以后在这个村庄里人们随处可见白蹄坤的“战利品”——沙狐皮。“女人们穿着各种各样的沙狐皮衣,扭扭捏捏招摇过市……男人们戴着狐皮帽,像春天的公牛一样威风凛凛走乡串门儿。”[18]物欲迷眼的人们将残杀动物这种罪恶披在身上堂而皇之的炫耀,理性构建的世界崩塌,于是,当白蹄坤联合主人杀尽全部善良的动物之后,大自然展开了全面的报复。“他们失去了理智,夜里惊梦,满脑虚无,嘴角喷着黏黏的涎水,他们彻底疯了,狗一样吠着,狼一样互相残杀,有的杀了人,双手捧着鲜血痛饮,嚼烂人骨吞下去;有的还敲开人脑袋,搅里边的脑汁,然后抽筋剥皮。这些衣冠楚楚的人们,此刻变得荒诞不经。”[19]
人类的荒诞、异化源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同样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也与人类的文化生态危机紧密相连。“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我们人类文化自身,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错位,在于人对待自然和生命的方式及态度违反了生态规律。人类作为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自身的各项平衡早已处于异化、扭曲的失控状态。肉体与精神、个体与群体、物质与欲望、文明与发展等文化构成都处于矛盾冲突中,这些冲突不仅让人类内心世界陷入焦虑、孤独、痛苦的失衡状态,更让大自然和其他生命存在成为人类文化无辜的受害者。”[20]
人类只有从文化思想体系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变革当下的思想文化体系,才能缓解现今严重的生态危机。朱玛拜的生态书写对于推动这一变革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站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上,结合现代生态思想,表达了人与自然最初的原生态关系,从而与现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形成对比,其意义并不是简单的高举民族文化昔日春天的招牌来迎合当下人们需要追思过往的心理,或者是将这种原生态作为一种审美理想来构建,使之成为现世中人类逃避痛苦的桃花源,而是用看似轻松的笔调书写着民族乃至世界的忧虑,在社会文明发展畸形的时刻冷静的坚守人类的本真,超越物役的痛苦回归自然,体验生命丰富的情感,唤醒人类缺失已久的自然天性,从而为拯救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双重危机做出贡献。
五、结语
“任何一种民族文学,都有其作品可能成为世界文学的机会,但是只有那些不仅在本民族范围内产生发散性影响,而且同时对其他民族的精神生活产生辐射性影响的作家作品,才具有世界文学意味,或者说进入世界文学圈内。”[21]朱玛拜·比拉勒便是这样一位在新疆乃至世界都具有影响力的哈萨克族作家。这不仅来源于他优秀的双语写作才能,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他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之中仍保持着独立但不孤僻的姿态。他用饱含深情的诗意笔触描绘哈萨克人们的朴素生活,并用极高的艺术天分挖掘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根基,将民族文化的灵魂与现代文明巧妙的结合,立足民族文化却不徘徊,体味现代文明却不盲目。对于人类生态危机的思考不止于简单的文化批判,而是深入人类文化系统,从本源剖析危机爆发的原因。他用自然元素对抗人的主体性,冲破人与自然及其他生物之间的壁垒,传达出万物平等共生的生态理念,进而唤醒人类普遍缺失的生态关怀。同时,朱玛拜对于生态观念的阐释颠覆了传统的书写模式,以全新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生态文学写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总而言之,朱玛拜这种立足民族地域性却又超越局限的文化思考是本土生态文学写作的再生,也为世界生态文学写作提供了一种范式。
[1]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244.
[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
[3]雷鸣.当代生态小说的审美迷津[J].文艺争鸣·新世纪文学研究,2008,(8):37.
[4]彭兆荣.文学与仪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5.
[5][7][8][9][10][11][12][13][15][16][17][18][19]朱玛拜·比拉勒.蓝雪[M].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译.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7.204,141,177,188,10,11,173,176,226,228,115,161,168.
[6]王吉祥,吴孝成:试析我国哈萨克当代小说作品中所蕴含的精神生态和谐思想[J].石河子大学学报,2011,(3):94.
[14]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M].徐黎明译.贵阳:贵州人们出版社,1994.99.
[20]薛敬梅.生态文学与文化[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5.
[21]王列生.世界文学背景下的民族文学道路[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