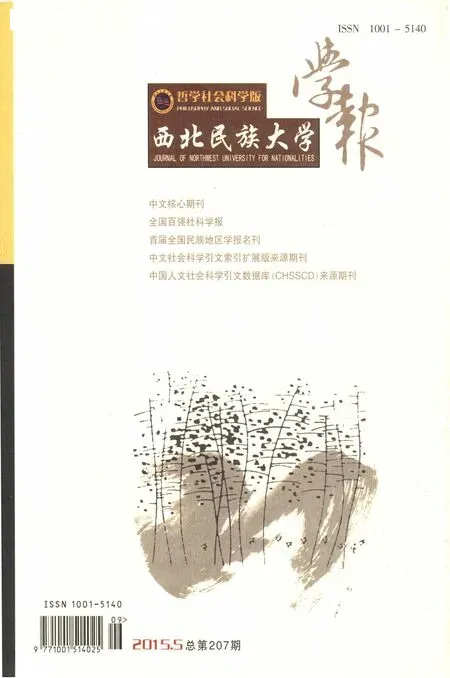家园的永恒召唤——《大地的阶梯》的人类学解读
胡志明,胡楠婷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411201)
阿来自迈入文坛以来,就以其特殊身份和独特视角,通过汉语写作,给读者呈现出一个真实的西藏,一个有着实实在在文化内蕴的独立存在体,一个绝非概念化主观化的神秘物。《大地的阶梯》就是这样一部融注了阿来真挚情感与努力心血的成果。在其呱呱坠地至成长之初,家园予他的肉身依托;在其双脚驶出藏区境地之后,母族予他的声声召唤;在其重返故乡大地之时,用身用心丈量脚下这片故土之余,所奔涌而来的情绪即在这一刻沸腾升华,响彻在大地的阶梯之巅,鸣唱出这一情感呕心沥血之作。阿来试图客观地描绘该地区的地理形貌,以投射出独特的人文历史情怀,传达出并不生活在西藏的藏族人的厚重精神寄托的切近与归来。
一、流浪之始:家园的时空断裂
自广袤的成都平原,攀级而上,至青藏高原,其间是一个群山逶迤与峡谷漫野的渐变带。这一地带在藏语中称之为“嘉绒”。单纯就字面上的意义而言,“嘉”是汉人或者汉区的意思,“绒”是河谷地带的农作区,合则意为靠近汉地的农耕区。阿来,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在河谷台地上农耕的家族,接受着藏文化的灌溉熏陶,也沐浴着汉语的文明洗礼。正如阿来在一次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上的演讲中所自况的:“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就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1]阿来始终铭记着自己是一个藏族人的本者身份,并且也始终在追溯着本民族的文化源头,凭借着他本身既往的“流浪史”来书写家园的历史。
(一)家园:阿来精神和肉体的原乡
家园,在某种程度上,指一个人的肉体和精神原乡。阿来的家园,即他肉体和精神的原乡,我们可以理解为西藏这方沃土,细言之,则可具体到嘉绒地区。从地理上看,嘉绒从来就不是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带,甚至可以说是处于边缘的尴尬位置。阿来生于兹,长于兹,虽受藏语耳濡,但始终无法触及书面藏文的熏染。那么“精神的原乡”一说从何而来呢?阿来,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的是从藏族民间口耳相传的神话、部族传奇、家族兴衰、人物故事和寓言中汲取养分。在这些故事与传说中,阿来感受到了不同于书面传统中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色彩,感受到了藏民族最璞真的思维习惯和审美特征,感受到了原始藏族人对世界朴素而又隽永的本真观点。通过这些古老神话与个体兴衰,他学会了如何去掌控时间和再塑空间,学会了如何去面对命运的跌宕起伏。这些都是藏族人这一身份所赋予阿来的能力,而阿来个人的特殊之处在于:对汉语的学习。在学校,他学习汉字书面语、使用汉化口语,但回归日常生活后,却依然用地道藏语交流,传达他眼睛所触及之景,和此景所激荡出来的心灵火花。阿来自己曾说道:“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集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2]这是阿来以及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和独特体验。在两种语言之间穿行,成就了两种语言覆盖下所营造出的别样的心灵景观。也正是因为在这两种语言间的反复穿行,孕育了阿来最本真的文学锐度。这就是西藏之于中国的特殊性,嘉绒之于西藏的特殊性,所给予阿来的特殊“精神原乡”。
(二)生命的流离:远在他乡的族人
他乡,顾名思义,他者的家乡,也就是本者家乡以外的处所。阿来作为本者肉身,就一直在诸多他乡里穿梭:从藏区到汉区,从中国到美国,从东方到西方,这其中游走的不囿于其躯体,他的精神与心灵也一直在路上。
藏区与汉地之间的穿行,可以说是贯穿阿来生命始终的流离。从最开始的身处藏区,与汉文化的浸润相依相离。直至生活了三十六载后,步入成都,身处汉地,本者走进了他者的领地。远在他乡的过程当中,遭遇是尴尬的,心境更是难以言明的,但阿来用他的笔,通过作品将他的处境寄予在小说主人公身上展现出来。
在小说《空山》中,曾涌现了一大批机村的外来者,这些外来者,不论在机村生活得怎样,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总是充斥着他们的心灵,这种孤独感绝大原因是来自于作为外来者的孤独,作为他者所缺失的本者的归属感。藏族学者丹珍草指出:“不能融入又不忍离去的矛盾和困境,是对‘边缘人’或‘边际人’文化处境的真切描述。”[3]阿来借由“我”于《空山》一文中自述道:“在美国访问……去看异国白人的村庄,黑人的村庄,印第安人的村庄,甚至夏威夷那些岛屿深处,去寻访当地土著民族,我是想知道,村庄里的人们,最后的归宿在什么地方?”[4]这里,阿来不仅仅是在藏地与汉区之间的游走了,已经走到了美国,将眼界拓展到了西方,他在探寻着外族人在异乡的处境以及归宿,他在比较着同是异乡人的感受情怀,他在审视着原乡与他乡、本者与他者的目光。汉地倏尔一齐同藏区化为了作者的家园,阿来作为远在他乡流离的族人,又是否能“欲把他乡,落作家乡”呢?结合阿来流离的经历来看,答案是随着他的现实处境和彼时心境所决定的。阿来始终在他乡与家园中穿梭流离,其精神依托也始终在他者及本者之间反复切换,这就是贯穿其整个生命的一种流离飘摇。
(三)失落的历史:断裂的故事时间
在他乡流离的阿来,心中始终恪守着藏区母族不可撼动的民族信仰。在迈出家园,走进汉区,乃至走出东方,迈向西方以及整个世界的历程中,阿来始终以一个藏族子民的身份,将眼光撒向了他族,撒向了异国,在领略了他族异国的文化渊源后,便将目光收拢回来,转至对本民族的一种自我审视,也引起了他对本民族文化渊源的探求。阿来怀揣着一颗容纳百川的心怀,开始了对本者本民族的文化历史寻根。
在《大地的阶梯》中,阿来从拉萨,青藏高原的腹心,顺着大地的阶梯、历史的脉络,拾级而下,展开了追寻步伐。他回到拉萨,中世纪的拉萨,中世纪民间传说中的拉萨,借由英国人托马斯搜集整理的《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中援引的描述:“没有人再像神人未分的时代那样正直行事了,由于没落时代的来临,人们逐渐不知害羞,肆无忌惮。他们不知羞道耻,他们不遵守誓言,一心想发财致富,不顾死活。”甚至还将笔触延伸到了宫廷生活:“从国王的妻子以下,妇女被认为比国王还聪明。她们参与国政;她们来到国王与大臣之间制造分裂,这样,国王和大臣们分裂了。”[5]这是宫廷政治在民间的一种投射。结合传统的宫廷历史而观,当时在拉萨,是藏王赤松德赞当政时期。就赤松德赞的传奇身世而言,其中出现了两大矛盾。其一,由于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和亲所生,公主的到来连带着佛教的传入。在雪域藏地,佛教的突然来临与西藏本土苯教的惯行发生了剧烈摩擦。其二,据真实可证的史书中记载,赤松德赞出生于公元742年,金城公主在此前的公元739年已经去世了。那么,在民间为什么竟附会出带着明显倾向性的传说,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时间差呢?深入分析这两大矛盾,有专家认为,这种剧烈摩擦,断裂时间恰好可以反映出藏汉两种文化接合的历史渊源流长,同时这也是藏族人民渴望藏汉团结的心愿象征。
二、远离神圣:家园的无情裂解
西藏,从古至今,一直被外族人诩为最神圣最纯净的区度,尤其在今天,更是备受全世界人民的推崇乃至朝拜。阿来,作为藏族子民,西藏就是其家园的象征。阿来以“家园”作为生命安顿的场所,试图通过家园所面临的问题来揭示藏民族所处的历史文化被无情消解的窘境。这也是阿来书写《大地的阶梯》的原因之一。阿来以一种焦虑与担当的心态来正视家园面临瓦解的现实,不断发现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
(一)自然的破坏
阿来笔下的自然描写是“万物有灵且美”的典型表征。他取景于自小赖以依托的西藏家园,雪域、高原的实体印象在早年的阿来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因此,在他早期的诗歌以及小说写作中,所触及之景都是纯净神圣之至,不可亵渎的存在。但在《大地的阶梯》书写历程中,即阿来的归途之景却全然不是这幅模样了。幼时故乡村子的一大片白桦林已经消逝褪尽,显现出混凝土一般铁灰的冷峻颜色,这是在长达上千年的战火与人类的刀斧之后,美丽的自然衍生出的一副狰狞面孔。与此同时,让人更加沉痛的是,对大自然的劫掠还在远方云雾遮掩的深山里进行。公路下边,河道里浊流翻滚,黄水里翻沉碰撞发出巨大声响的,正是那些在深山里吞云吐雾了千百年,为这条大河长青长流碧绿了几百年,为这片土地的肥沃荣枯了几百年的巨树被伐倒的尸体,它们在残喘呻吟,它们在依依不舍地向这个世界泪眼告别,最终还是改变不了倒下灭亡的结局。阿来清楚地看到,大地没有了衣被,飞鸟失去了巢穴,走兽得不到荫蔽,最终就轮到人类自己了。所以,在目睹了泸定段大渡河谷里那些漫山遍野的仙人掌时,就感到这是已经破碎的大地用最后一点残存的生命力在挣扎,在呼喊,在惊醒世人良知发现。要知道,在地球的生命进化史上,要是没有水,没有森林,根本就不会有人类的出现。阿来的良知已被惊醒,他希望用自己的良知去感召唤醒更多的民众,去保护自然,敬畏自然。
(二)神灵的没落
“万物有灵且美”,世间万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具有灵性不可亵渎,阿来笔下的自然世界则更增添了宗教式的神化与威严,而这种宗教主要就是藏族土生土长的苯教文化。苯教最初是自然宗教,人们从开始崇拜天地、日月、星辰、雷电等扩展到崇拜雪山、湖泊、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等。经过漫长的发展,逐渐完善成为藏族社会第一个正规的宗教。在7世纪佛教传入后,两种宗教文化融汇贯通,形成了当地特有的宗教形式──藏传佛教[6]。阿来在《大地的阶梯》一书中,对这种特有的藏传佛教也予以了追根溯源,宫廷历史与民间传说两条线索,其间神灵的穿插缠绕不容忽视。族人自古对神灵就有着特殊的情感信仰,从早期的图腾崇拜,及后期的神话传说,甚至是族人日常生活对自身的约束,奉行的规则都有所体现。阿来同样也是这样一位有信仰的藏族子民,但此次归途中,他已然发觉部族中有部分子民对信仰对神灵开始淡漠,也可以说是他们有信仰,可是信仰的主体不再是神圣威严的万物,而是金钱利益的指向标。这种异化在藏族群体内蔓延,甚至浸染了新一代的孩童。花草树木、虫鱼鸟兽在他们眼中不再纯净自然,取代的是它们有无市场,能不能换来人民币。阿来作为归来人,他深知这其中的反差变化,他感到焦虑,他也觉察自己有义务去维护万物有灵且美的原貌原乡。
三、行在路上:书写者的家园蓝图
作为一个漫游者,阿来这些年一直在路上,离去又归来。对于一个时刻都试图拓展自己眼界的人来说,群山环抱的青藏高原时时会显示出一种不太宽广的固守,因此他选择了离去,并且他也坚信,这片大地所赋予他的一切最重要的地方,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改变。在阿来看来,“有时候,离去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切近与归来”,“我的归来方式肯定不是发了财回去捐助一座寺庙或一间学校,我的方式就是用我的书,其中我要告诉的是我的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我的情感就蕴藏在全部的叙述中间。我的情感就在这每一个章节里不断离开,又不断归来”[7]。从阿来的自述中,我们看到的不止是他对母族,对原乡的赤诚情感,还有着作为藏族子民,作为异地游子,作为藏汉乃至世界交融产物,对家园的美好希冀与蓝图憧憬。
(一)在焦虑与责任中展开书写
作为藏族子民的阿来,以“每日三省吾身”的姿态来审视自身以及所赖以依托的家园的生存处境,发现藏民族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历史文化在日益消解。作为作家的阿来,以一种焦虑与责任的心态来正视家园所面临瓦解的现实,通过书写来传达生命根底的最真切呼唤。
1.启程流浪
《大地的阶梯》一书写作的动因最初产生,并不是在阿坝的群山之间,而是在大山阶梯的顶端,在藏文化的中心地带拉萨。因此,在深入故乡群山的时候,阿来采用了一条反向的路线。先从拉萨,青藏高原的腹心,顺着大地的阶梯、历史的脉络,一梯接连着一梯,往家的方向逶迤而去。从更深层意义上讲,之所以走进西藏,也就是为了走出西藏。阿来这些年一直在路上流浪,离去是为了更好地归来,如今的归来则是一种新的流浪的开启[8]。
回到拉萨,展开寻根的步伐。在时间上,对嘉绒的释义,对民间传说与宫廷历史,对僧侣与宫廷,乃至对管辖将军盘热都一一进行了追溯。在空间上,阿来的视角由平行的凝注转至纵向高处的俯瞰,他希望从天上,从高处,从深处,像神灵一样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而这条脉络上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走向大渡河,循着一条人们不常走的线路回家。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的大渡河,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里程碑。然而,在阿来心中这座里程碑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大渡河所奔涌而来的方向,是条蜿蜒前行的情感红线,它千折百回,向西向北,那些茫茫群山哺育了这条河流,也哺育了阿来的身体与心灵。因此,阿来有种“非走不可”的决心甚至说是义务,来走通大渡河,顺着大河溯流而上,追寻那山那水所给予的蕴藉。但回家的路上却全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公路上排开的汽车长龙,泥浆巨石覆盖下的并不平整的路面,以及被利益熏心的途经居民,都充斥在阿来的归途中。混凝土一般铁灰的光秃石山;仙人掌丛生的荒凉地带;浊流翻沉碰撞的黄水河道;以及穿着非藏非汉,面容脏污,手里提着篮子,翘首企盼着买主的孩子。这一幕幕真实图景,让归家游子的阿来触目惊心。他所忆记的那山那水是青山绿水,他所熟悉的一人一物是碧眼蓝天。回忆与现实的强烈反差,让阿来的归家情思更增添了一重焦虑。
2.因爱而生
阿来书写《大地的阶梯》的主要情感诉求是种作家生命根底的真切呼唤。阿来以一种焦虑与担当的心态来正视家园面临瓦解的现实,同时他也在自己心中升腾起一种在这个世界上显得过分美丽的想象,它不一定非去实现不可,但只要你热爱这片土地,心中存留着爱,那么就必定会绘制出属于你自己所属所爱土地的美好蓝图[9]。
矗立于嘉木莫尔多神山之尽时,阿来在现实与传说之间辗转反侧。传说中的神山是东方天际的坐标指南,它有着山神的战马与弓箭,有着清晨的螺声与野人的战石,有着无数历史遗存和瑰宝。莫尔多山周围地区,是藏族文化区中别具特色的嘉绒文化区的中心地带。此时阿来在看到自然界的满目疮痍之余,文化万劫难复的沦落也充满了其眼眦。神山不复在焉,神话传说也找不到现实归蒂,山神的子民们的新旧更替也出现了难以言说的落寞。于是阿来又继续上路了。“漫游中的写作,在我25岁之后,与30岁之前那段时间,是我生活的方式。那时,我甚至觉得这将成为我一生唯一的方式了。”觉得毕竟还是觉得,在游历过程中,阿来滋生出了另一种生活的方式,抑或说涌现出了另外一个被现实引诱出来的“我”。“我”来到了赞拉,在过去与现在的双层时空里寻觅着原乡的踪迹,寻觅自己的立足点。“在很多与青藏高原有关的书籍中,在很多与青藏高原上生活的藏族人生活有关的书籍中,有一种十分简单化的倾向。好像是一到了青藏高原,任何事物的判断都变得非常简单。不是好,就是坏,不是文明,就是野蛮。更为可怕的是,乡野里的文化,都变成了一种现代都市生活的道德比照。”[10]阿来期望从这种绝对的文明观中开拓出其中夹缝生存的领域,在科学的历史观人文观地指引下,科学地洞见历史真实面目以及其变化发展。
(二)聆听生命幽微之光
回到生命最初的地方,于阿来而言,即生长生活了三十六年的马尔康县。“马尔康”这一地名寄予了藏族人命名时所蕴藏的祈求福祉的美好愿景,衍生意为“灯火旺盛的地方”。阿来出生于这样一个灯火旺盛的地方,对于旺盛的灯火自有他独特的感受。他将这灯火化作了在荒芜的河滩上兴起的寺庙,化作了寺庙内启迪智慧的梵音,化作了梵音所激荡出来的生命之光。
1.凝视自身
回到故乡,阿来不禁想起了日益远去的童年时光,一个面孔脏污,眼光却泉水般清洁明亮的孩童似乎此时已经被现世的风沙吹刮得驳杂了模样,内心蓦地笼上了一种隐隐的痛楚与莫名的忧伤。究其痛楚与忧伤的根源,莫不是在慨叹故乡变化之余,自己也变了,面孔早已不允许脏污,眼光渴望澄澈明亮却可望不可即。与同行香客的虔诚神色比起来,黯淡的不仅是瞳孔还有再归的心绪。回想起当初选择离开的原因,莫不是整个人流中散发出来的那种略显迟缓容易让青年人失去进取心的气晕,让作为一个健康的社会青年予以摈弃,发展的缓慢与觉醒的缓慢压迫着那些社会机体中活跃的成分。于是年轻的心开始躁动,奔涌向现代化的大都市中去。然而置身于都市潮流之中后,猛然发觉,怀揣着理想,认真地进取,却与这个城市的去向毫不相干甚至说是截然相反。现代都市的灯红酒绿固然亮眼,但与故乡的旺盛灯火比起来,却同样少了虔诚的神色。故乡满城的灯火有着“我”的一份贡献,还有“我”的伙计们的贡献,这座城市不仅因灯火而明亮,还因“我”自己的记忆与劳作而闪闪发光。这光芒中,有着“我”青春时代的汗水的光芒,梦想的光芒。
2.以爱净身
“每一次即将上路漫游的时候,只要想到一连串的地名,就看到一个个字眼闪闪发光,只要念叨这些名字,就已经在路上。”[11]这是阿来在《即将上路》一诗中所写。对于此次归家之行,他同样是这么定义的。一个又一个的地名,随着目光所到之处,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各具形态真实可感的实体。拉萨、大渡河、嘉木莫尔多、赞拉、马尔康、金川,都是阿来目之所及心之所向的地方,一路的穿行变幻,这熟悉亲切的地名化作了巍峨的高原,奔腾的河流,瞭望的山峰,旺盛的灯火,满川的梨花,缓缓地驶入游子的眼帘,叩开归家的思绪,抚润离人的心扉。这些年,阿来比以往更迫切想回到这片旷远的群山与草原之间来,但在文字当中,他并没有将“西藏”这一名词定性为遥远、荒蛮、神秘的化身,也没有美化得如天堂般毫无瑕疵。他始终在用爱感受着这片土地原始的所能给予的精神蕴藉及其翩跹变化所带来的文明感召,一个有别于其他满目疮痍之地的美丽山水,一个值得热爱并加以歌颂的地方。
阿来在写作中反复提到了离开,他说:“有时候,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切近与归来。”在藏地生活生长了三十六年的他选择了离开,斗转星移,瞬息变换,阿来用自己的归来方式来完成自己的本质切近。他的方式就是用文字凝聚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特有情感,用书传达他的独立思考与判断,用爱重建美好家园。《大地的阶梯》一书中,我们可以跟随着作者归家的步伐,层层深入家园的情感递进,洞见他的归来方式。阿来旨在写出的是令其神往的浪漫过去与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从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得到了什么和失去了什么?发现问题并竭力想去解决问题,这也是阿来归来方式的特殊体现。他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字去绘制美好的家园蓝图,去感召同族人乃至外族人一齐实现这幅蓝图,一齐重建关乎爱的精神家园。
四、结语
阿来以“家园”作为生命安顿的场所,来揭示藏民族所面临历史文化被无情消解的窘境。这既是阿来书写《大地的阶梯》的原因之一,也是作家生命根底的真切呼唤。阿来以一种焦虑与担当的心态来正视家园面临瓦解的现实,不断追问“我”是谁,“我”可以是谁等生命本原问题。通过对这一本原问题的重重追溯,找到了自我的栖息立足点,如何驻足使得历史原貌以其健康稳健的态势存在下去,在本书中都有所揭示或影射。本者惟愿小我协力,世界大同。
[1]阿来.看见[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152.
[2]阿来.穿行于异质多样化文化之间[J].作家通讯,2001,(2):23.
[3]丹珍草.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26.
[4]阿来.空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94.
[5][英]F.W.托马斯.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M].李有义,王青山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68.
[6]尚莹莹.阿来——藏族文化的说唱人[J].全国新书目,2010,(1):22.
[7][10][11]阿来.大地的阶梯[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6,77,182.
[8]王妍.追寻大地的阶梯——阿来论[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2.
[9]黄立.寻根路上的心声和期望——阿来《格尔萨王》的叙事学解读[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1,(3):6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