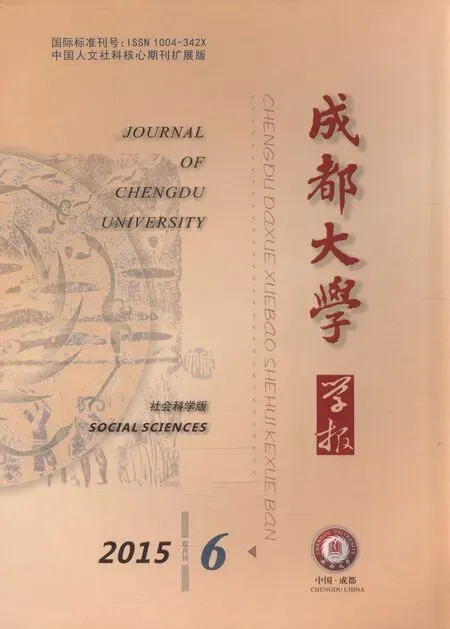奥尼尔东方之行及其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
刘文尧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奥尼尔东方之行及其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
刘文尧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已经逐步成为了美国剧坛的领军人物。同时,随着他的戏剧创作手法日趋成熟,奥尼尔的作品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然而,中国现代戏剧在20世纪20年代仍然处在“生长期”,对国外剧作家关注的广泛度有限,而且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矛盾激化,以及现代戏剧发展与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关系密切等因素,中国的戏剧工作者对国外剧作关注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以易卜生戏剧为代表的社会问题剧上。因此,20年代的中国文坛对奥尼尔依然知之甚少。与此同时,对东方一直抱有深切向往的奥尼尔在1928年底开始了他的东方之行,作为对自己“终生理想”的一场实践。这次历时四个月的远游,不仅使奥尼尔个人受益良多,更重要的是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奥尼尔;东方之行;中国现代戏剧
一、东方之行的起因
每当我们谈到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都要从1922年的那一期《小说月报》说起。当时茅盾在“美国文坛近状”一文中写道:“剧本方面,新作家Eugene O'neill着实受人欢迎,算得是美国戏剧界的第一人才。”①虽然茅盾给予了奥尼尔“第一人才”的极高评价,但是这样一笔带过的介绍却太过简短,未能引起当时中国文坛对奥尼尔的关注。最早出版了奥尼尔剧作中译本的译者是古有成。他在1928年4月所作的《天外》“译后”中,较为客观地描绘了奥尼尔戏剧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最初几年所遭受的冷遇,而即使是这段文字,也是等到1931年《天外》一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之后,才被读者看到:
本书著者奥尼尔为美国当代一大戏剧家,曾得(Pulitzer)奖金二次,美国艺术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的奖牌一次。他的声名已洋溢国外:他的戏剧在英、德、法、俄、捷克斯拉威基亚(Czechoslovakia),和斯干的纳维亚半岛各邦,都有表演和阅读;东邻日本,也曾拿他的作品来上演。但是我们中国却事事都落人后,舞台上没有著者的戏剧的踪迹固不必说,文坛上也似乎还没有人谈及他的。②
“五四”运动之后,文明新戏已经没落;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戏剧开始大规模兴起,新文坛正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关于戏剧的新观念空前活跃,大量的国外戏剧作品也开始被陆续译介进来并被搬上舞台。但在这一时期,奥尼尔的作品却并没有在中国受到广泛的关注。结合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规律和当时特定的社会现状来看,这是有其原因的。
一方面,中国现代戏剧在20世纪20年代还处于“生长期”,如饥似渴的新文坛,此时才刚刚将眼光放开来博览世界文化的宝库,而仅在戏剧方面,就有太多的大师和经典作品要去消化吸收。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易卜生、歌德、王尔德、萧伯纳、契诃夫、高尔斯华绥等无数杰出的艺术大家,已经使当时的文坛“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还无暇顾及奥尼尔”。③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现状中,中国剧坛对国外戏剧作品的吸收借鉴也是有所选择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下,由于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以及现代戏剧发展与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密切关系,当时的文学家与戏剧家们大多将译介和创作的焦点聚集在了各类与社会现实问题相关的作品上。因此,易卜生的戏剧便理所当然地率先博得关注。随着“易卜生热”的应运而生,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剧作家大多成为了“以尊重人的自由与个性为核心的‘易卜生主义’的”代表,“问题剧”也就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品类型。④而奥尼尔的戏剧与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一定的距离,他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融入了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甚至是意识流等现代戏剧各种流派的表现手法,作品主题复杂,风格多变,表现出明显的实验戏剧特征。这类作品不像易卜生的问题剧那样,能够紧密地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剧坛在当时尚未关注到它们的艺术价值,也就情有可原了。
由此可见,奥尼尔其人其作是要在经过几年的沉寂之后,才真正渐渐进入中国文学界的视野,以致后来对中国诸位现代剧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之中,奥尼尔1928年的东南亚及中国之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使这位剧作家个人受益良多,同时也加快了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速度,继而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推动力。
对于奥尼尔这次计划良久的东方之行,国内已有的研究资料大多记述得较为简略。笔者曾于2014年6月前往耶鲁大学贝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有幸借阅了奥尼尔第三任妻子卡洛塔·蒙特利·奥尼尔⑤写于1928年到1929年的日记,并在美国著名奥尼尔研究学者威廉姆斯·戴维斯·金教授⑥的帮助下,获得了由他编辑整理的该日记电子录入版⑦。因此,依据这份日记以及198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的《奥尼尔信件摘录》⑧等资料,我们或许可以更近距离地了解到奥尼尔当年这场东方之行的真实情况。1928年,对于奥尼尔来说,是波折而又重要的一年。
在个人生活方面,奥尼尔正在经历重大的家庭变故,与第二任妻子阿格尼斯·博尔顿⑨在感情上的破裂不仅引起了两人之间的婚姻危机,同时也使奥尼尔成为了美国各大媒体穷追不舍的对象,迫使他不得不于1928年2月10日,带着复杂的心情,携当时仍是情人身份的卡洛塔逃离纽约,去欧洲寻求一方清静之地。
在戏剧创作方面,1928年5月奥尼尔凭借九幕剧《奇异的插曲》第三次获得美国普利策戏剧奖(Pulitzer Price for Drama)。与此同时,他开始了三幕剧《发电机》的创作,然而写作过程并不顺利。以为远离美洲大陆就能躲避烦扰的奥尼尔依旧难得安宁,虽然他与阿格尼丝不再相见,但两人在情感上的剑拔弩张,以及在财产上的种种分歧,通过各类信件始终纠缠着疲惫的奥尼尔,使他几乎在一整年的时间里,都深陷在沮丧、愤怒、痛苦的情绪中难以自拔,精神状况多次徘徊在崩溃的边缘,很多时候都难以集中精力来进行《发电机》的写作,以至于严重影响了他在剧本上的创作进度。
或许是因为远离美洲并没能平复奥尼尔的心情,抑或是因为欧洲也没能给予他新的创作灵感,这种生活与工作的双重失意,终于坚定了奥尼尔将“东方之行”提上日程的决心。
对于东方的向往,奥尼尔此前在作品中曾反复申述。无论是借《天边外》中罗伯特之口,表达想要到地平线的另一端去探寻宇宙背后的神秘力量以及人生的终极意义,还是在《泉》中将东方刻画成一个完美的梦境,这个在奥尼尔心中酝酿了多年的梦想始终挥之不去。现在,合适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在卡洛塔的帮助下,他们订好船票,拟定路线,整装待发。1928年9月,奥尼尔在临行前给长子小尤金·奥尼尔⑩所写的信中,激动地表达了他对这场旅行的期待:“我要在东方选定一个能工作的地方,住上两个月,然后换一个地方,再住上两个月。”(11)同时,在给代理人理查德·马登(12)的信中,他更是直言了这场旅行对他的巨大意义:“你不知道这次东方之行对我有多大的意义。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从当地的环境中汲取一丝灵感,是我毕生的梦想。这对我今后的创作将有不可估量的价值。”(13)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28年10月5日,奥尼尔从法国马赛出发,与卡洛塔一同搭乘“安德烈·勒邦”号(14),开始了这场被他期盼多年的东方之行。依据卡洛塔的日记,他们的旅行路线大致如下:马赛(10月5日)—埃及塞得港(10月10日)—苏伊士港(10月11日)—红海(10月11日)—吉布提(10月15日)—艾顿(10月15日)—索科特拉岛(10月17日)—科伦坡(10月22日)—马六甲海峡(10月26日)—新加坡(10月28日)—西贡(15)(10月30日)—堤岸(16)(10月30日)—香 港(11月6日)—上 海 (11月9日)—香港(12月15日)—马尼拉(12月18日)—新加坡(12月24日)—科伦坡(1929年1月1日)—塞得港(1月15日)—地中海(1月17日)—法国家中(1月27日)。1929年1月27日,奥尼尔和卡洛塔回到他们位于欧洲法国的别墅,旅行宣告结束。(17)整场旅行历时将近四个月,据此行程,奥尼尔在亚洲游历的时间大致为两个半月,其中真正踏上中国土地的时间仅为一个月,而且只在上海一地做了 停 留(18)。
二、“失意之行”还是“获益之行”
对于这次旅行,国内目前有所记录的资料大致集中在以下两本专著和一些零散的文章中。它们都注意到了奥尼尔在旅途中的失望情绪,而且几乎无一例外都将他的这次游访归结为一场“失意之行”。
首先,对奥尼尔东方之行有较为具体记述的文献是1988年出版的《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19)一书。该书作者在第三章列有专节“神秘的中国之行”,其中提供的关于奥尼尔旅行的信息,对中国研究奥尼尔的学者而言是非常珍贵的资料。虽然该书对奥尼尔旅行的记述不过几百字,但得出的消极结论十分明确:
一踏上中国国土,上海那“十里洋场”的情景就使他失望。他以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东方文化、风味独特的文明古国,但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到处是高楼大厦,霓虹灯、摩托、汽笛,和美国毫无两样,沥青马路一样的油滑,街上的行人一样的熙攘。奥尼尔并没有找到他憧憬的东方式的“太平与宁静”,看到的只是陈列在巡捕行里残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刑具和跳舞厅昏暗灯光下受人摆布凌辱的中国舞女……对上海的极度失望和部分由此而引起的爱情纠葛,使奥尼尔打破戒规,重新酗酒,后因精神濒于崩溃而被送入一家医院治疗。(20)
其次,2006年出版的《奥尼尔研究》(21),也在“东方情结”一节中对这次重要的旅行做了记叙。作者给出了此次旅行的大致时间与路线,并指出奥尼尔在到达上海后,“心情特别沮丧”,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各种“惊人的贫富悬殊”,与他所期待的“东方恬静之美”相去甚远。此外,作者还对奥尼尔在上海停留期间曾经参观过一所“监狱博物馆”的细节做出了补充性的描述,指出奥尼尔如何在上海当地目睹了“千奇百怪、形形色色的刑具”,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奥尼尔在这次旅行中所遭受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精神折磨。(22)
除以上两本著作之外,国内还陆续出现过其他一些相关研究资料,比如:郑柏铭在译作《尤金·奥尼尔和东方思想:一分为二的心象》附录中所写的“尤金·奥尼尔为什不喜欢上海”,就借“叶公好龙”的典故比喻了这次旅行,认为奥尼尔“非好真东方不过好似东方而非东方之方也”,直指他在上海目睹的现实与理想的落差(23);《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一书在“艰涩与晦暗:奥尼尔的中国幻想与东方情调”一节中,也谈及了这次旅行,同样,作者得出的仍然是较为消极的结论。(24)其他论及奥尼尔东方之行的材料,因内容大致相似,故不在此赘述。
不难看出,国内的这些资料几乎都将奥尼尔的游访定义为了一场“失意之行”。或许“失意”是奥尼尔当时表露出的一种情绪,但这就是他旅行的全部体验吗?这场被奥尼尔视为“终生理想”的远游,真的如此一无是处吗?如果真实情况并非这样,那么为何国内的研究资料却都得出这么一致的结论呢?经笔者分析,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点。
第一,文献来源相对单一或陈旧。上文中提到过,《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和《奥尼尔研究》是国内现有资料中记述这次旅行较为集中的两本专著,其他资料即使对这次旅行有所论及,也大多是对这两本书的转引或转述。而这两本书在记述奥尼尔这段经历时,主要依据的则是美国盖尔泊夫妇所著的奥尼尔同名长篇传记(25),也就是说,以往中国学者在谈论奥尼尔东方之行时的文献依据几乎都来自于盖尔泊夫妇的这部著作。尽管这是一部非常权威的奥尼尔传记,但是这样相对单一的文献来源,必然会导致国内资料对奥尼尔这段经历的描述角度如出一辙,而对此次旅行一致得出大同小异的消极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值得一提的是,《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一书在引用文献时扩大了范围,主要选择了1988年由陈渊翻译的《奥尼尔:坎坷的一生》(26)作为依据。这本书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国内唯一一部被译为中文的奥尼尔传记,所以对中国学者而言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但可惜的是,由于该书英文原版(27)于1959年问世,出版时间较早,距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所以原作者克罗斯韦尔·鲍恩在书中涵盖的诸多细节,经后来考证,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事实性的错误(28),这一点在与后来出版的奥尼尔其他版本的几部英文传记以及相关的日记和信件等一手材料作对比阅读时,一目了然。因此,选择此书作为引用的文献来源,或许是有些陈旧了。
事实上,从国外其他的一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奥尼尔对于自己的这次旅行,并非一否到底。在刚刚归来之后,他立刻给自己的小儿子沙恩和女儿乌娜写信,字里行间仍难掩旅行带给他的兴奋之情:
尽管在旅行的最后阶段,尤其是在上海的时候,我生了病,但这仍然是一场奇妙的东方之行,即使有人给我一百万,我也不愿意错过它。我游访了许多奇异的地方,而且在我搭乘的船上和我游览的城镇里,还遇见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这简直使我感觉在自己的经历中,又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29)
尽管大大缩减了行程,没能像最初设想的那样在某个地方小住两三个月,汲取灵感并安静地写作,使奥尼尔略感遗憾,但从信中不难看出,沿途的经历仍然使他收获颇丰,各式各样的新奇事物也都令他印象深刻。单从这一点而言,奥尼尔就不虚此行。
第二,将奥尼尔在个人情感上的失意以及由身体欠佳而引起的情绪低落误读为对旅行的不满。国内研究资料在总结此行时,尽管提到了奥尼尔的情感纠葛和身体状况,但并没有将奥尼尔在旅途中的低落情绪与这些原因直接联系在一起,而只是着重强调他对现实中上海景象的失望,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走入了一个误区。
在卡洛塔1928年的日记中,几乎每天都有对于奥尼尔情绪的描述,而其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汇就是“紧张”和“担心”。让奥尼尔如此紧张焦虑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与阿格尼斯的婚姻纠葛。关于这场看似无休止的纷争,奥尼尔曾在同年4月给友人肯尼斯·麦克高恩(30)的信中写道:“现在我身陷于最糟糕的境况……我并不是在抱怨……但是这对精神而言,简直是地狱般的折磨。”(31)被这样的情绪压迫得疲惫不堪的奥尼尔,即使登上了东航的客轮也难逃厄运。同年11月初,即在奥尼尔即将到达上海的一周前,他终于因为持续的低落情绪而爆发了精神上的崩溃。卡洛塔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他看起来可怕极了。这时候交谈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我早就知道,这几个月终究会引起一次某种程度上的‘崩溃’。”(32)同时,当旅行开始而奥尼尔又无法写作时,大把的空闲时间让他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自己的这次“出逃”对于孩子们而言,是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自责愧疚的心理无疑愈发加重了他在整个旅途中的负面情绪。(33)
除去情感上的因素,另一个导致奥尼尔在上海停留期间兴致不佳的原因则是他的身体状况。在新加坡和西贡等地的逗留,使很久没有经历过如此酷暑的奥尼尔败下阵来,他的病情也逐渐由中暑继而转为感冒。后来在给长子小尤金的信中,他还对此打趣地说:“热带地区对21岁的小伙子和40岁的人(34)来说,可真是天壤之别。”(35)抵达上海后,由于精神上的全面崩溃,奥尼尔又因为再度酗酒而住进了当地的医院,这才导致了他在上海的行程被彻底打乱。这些事实表明,奥尼尔在上海停留期间所表现出的消极情绪,大部分其实是由他自己复杂的情感原因和身体不适而引起的,而且这些原因大多产生于他抵达上海之前。所以,将奥尼尔在旅途中的失落心情和不满情绪全盘归结为他对亲眼所见的现实中上海的失望,并因此得出整场旅行都非常失败的结论,是有失客观的。
第三,将上海从旅行的一系列目的地中割裂出来,打破了奥尼尔实际上对东方形成的整体印象。或许国内研究者们是为了在论述中能够更好地强调奥尼尔与中国的切实联系,所以国内的研究资料在论及此行时,都将探讨的重点落在了奥尼尔在上海停留的阶段,但这无疑大大缩小了奥尼尔旅行的实际范围。如上文所述,他的整个行程历时将近四个月,而其间在上海只停留了一个月,如果仅就上海一段而对整场旅行做出结论,显然是片面而不合适的。
其实,奥尼尔在旅行之前对东方所抱有的就是一种整体而模糊的印象。就像他在作品中塑造东方世界时经常借用错乱的东方元素一样,在奥尼尔这样一个西方人眼中,中国、日本甚至东南亚各地的文化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它们是作为一个整体被认知的,对他而言,这些文化他者中的元素都是与西方世界相对立的存在。因此在旅行中,奥尼尔对东方形成的印象也并非是对某一个地方的个别体验,而是对东南亚各地以及上海的整体感受。国内学者只看到了奥尼尔眼中上海的“不尽人意”,却忽略了他对此行中其他目的地的认知,打破了奥尼尔实际上对东方形成的整体印象。事实上,奥尼尔在新加坡和西贡等地逗留期间,心情大好,对当地的异国风情都有很深的感受。在新加坡时,他曾兴致勃勃地在当地的一个湖中游泳,即使后来发现该湖是当地的污水排放处,他也兴致不减,毫不在意(36);而抵达西贡之后,他甚至在一个被卡洛塔称为“泥潭”的地方畅快地游泳,之后还去游览了植物园,观赏到许多当地特有的动植物(37)。即使在上海,当身体状况稍有好转的时候,奥尼尔也立刻在下榻的酒店调换到了能够看到黄浦江和外滩街景的房间,以便自己能够随时捕捉到异国的景致。(38)如果我们依据这些事实,将奥尼尔在旅途中各个阶段的经历都纳入讨论的范围去考量他对东方各地所形成的整体印象,或许就不会将这次旅行定义为一场彻底的“失意之行”了。
第四,只看到了奥尼尔在旅行中当时当地的情绪,而忽略了这场经历对他人生的长远影响。国内研究者将这段经历归结为“失意之行”的时候,着眼点都聚焦在奥尼尔当时当地对旅行的感受上,这些资料几乎异口同声地引用了奥尼尔的一句话来证明他对东方的失望,那就是他在旅途中看到的是“数以百万难以消化的印象”(39),仿佛旅行带给他的就是一场“消化不良”。然而,奥尼尔此话的真正含义或许并非如此。他在旅行归来后给长子小尤金的信中说道:我遇见了各个国家形形色色的人,并且终于突破书本的限制而获得了对东方真实鲜活的感受。各种各样关于声音、色彩、面容、氛围以及奇特经历的生动印象,塞满了我的脑子,跟随着我。但我现在还没法将它们整理分类,因为我离这场旅行还太近。(40)
奥尼尔深知,一场旅行除了在当时当地会给自己带来新奇的感受之外,同样会在他之后漫长的人生中逐渐释放其深远的影响,并且他也十分了解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发强烈。因此他提到这“数以百万难以消化的印象”,并非是要强调这些“印象”的“难以消化”,而只是为了表明自己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距离来细细品味旅行带给他的收获。对此最好的证明,就是将近十年后在美国西海岸落成的“大道别墅”。如果说这次旅行让奥尼尔对他曾经憧憬万分的东方失望至极的话,那他大可以抛弃东方这位“旧爱”,去另觅“新欢”。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非但没有终止自己的东方情结,反而于1937年和卡洛塔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丹维尔市一同建造了著名的“大道别墅”。也许正像奥尼尔所说的,他现在离这场旅行已经足够远了,当初印刻在脑中的“难以消化的印象”,经过时间和距离的淘洗,已渐次清晰。所以他与同样对东方有着浓厚兴趣的卡洛塔一起,将这个别墅布置得处处充满了东方元素,把这座可以被称为他最后一个“家”的宅院,变成了一种对他当年东方之行的延续,使自己后半生中最重要的七年(41)都浸染在了东方氛围的熏陶中。
如此说来,依据以上几点,奥尼尔这场对“终生理想”的实践,就算遗憾重重,也依旧是使他获益良多、终生难忘的经历。因此,将其总结为一场“获益之行”,或许才是更恰当的。
三、“无心插柳”与“有心栽花”
这次短暂的东方之行不仅令奥尼尔个人受益匪浅,加深了他的东方情结,而且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还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以及对中国诸多著名的剧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对奥尼尔的提及,是敲响了一场剧目开演前的钟声,那奥尼尔对中国的造访,才是真正拉开了这出大戏的序幕。
首先,奥尼尔的东方之行直接带动了其戏剧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客观的数据来了解这一时期奥尼尔在我国受关注程度的大幅提高。在奥尼尔来华之前的1922年至1928年,除了茅盾发表的“美国文坛近状”,其他介绍奥尼尔的文章仅有2篇:1924年由胡逸云发表于《世界日报》的《介绍奥尼尔及其著作》(42),以及1927年由余上沅在北新书局出版的《戏剧论集》中所写的《今日之美国编剧家阿尼尔》(43)。而到了奥尼尔来华之后的1929年,立刻就出现了一个介绍奥尼尔的小高潮。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与奥尼尔相关的文章便至少有7篇被刊登出来,分别为张嘉铸发表于《新月》的《沃尼尔》(44),查士骥发表于《北新》的《剧作家友琴·沃尼尔——介绍灰布尔士教授的沃尼尔论》(45),寒光发表于《戏剧》的译文《美国戏剧家概论》(46),以及春冰发表于《戏剧》的《戏剧生存问题之论战》(47)、《英美剧坛的今朝》(48)、《最近两个月的世界剧坛》(49)和《欧尼尔与〈奇异的插曲〉》(50)4篇文章。因此,单从与奥尼尔相关的论文数量上来看,1928年奥尼尔东方之行作为一个分水岭的重要性便一目了然。
这些文章对奥尼尔的介绍虽然不能算是面面俱到,但它们终于让中国的文学和戏剧爱好者可以对这位剧作家的生平和作品特点窥见一斑。而紧随这些文章之后,各类与奥尼尔相关的评介论文便开始纷纷见诸报刊,其剧本的中文译作以及舞台演出也开始陆续涌现,发生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奥尼尔热”迅速兴起,大大加速了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
同时,奥尼尔的东方之行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28年底奥尼尔前往上海的计划完全是无心插柳,他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这次远游会对另一个国家正在兴起的戏剧事业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但他的“无心插柳”,却成全了中国戏剧界有识之士的“有心栽花”,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张嘉铸。张嘉铸曾赴美学习美术批评,虽然从未专攻文学与戏剧,却一直对文学戏剧抱有强烈的热爱。1926年回国后,他依旧热衷于各类文学戏剧活动,且恰好定居上海,因此当奥尼尔抵达上海之后,张嘉铸便抓住机会,多次访问了奥尼尔本人。这一事实在他《沃尼尔》一文的开头,由当时《新月》的编者做了说明:“沃尼尔(Eugene O'neill)是美国现代最伟大的戏剧家,新近游历到了上海,张嘉铸先生就到旅馆里访问了几次;又给我们写了这一篇介绍的文字,大(体)(51)是译自克拉克(Clark),从此我们可以略知沃尼尔的生平。”(52)张嘉铸会对奥尼尔到访感兴趣,绝不是偶然的。他在美国留学期间,与当时同在纽约学习的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熊佛西等人同住万国公寓,关系密切,因此,他也成为了20世纪20年代“国剧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国剧运动”是1925年由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张嘉铸等留美学生提出的戏剧改革口号,他们提倡“纯艺术”的戏剧观,主张艺术地表现人生,反对将戏剧作为直接反映社会问题的工具。当时的中国剧坛“易卜生热”盛行,而“国剧运动”的倡导者们发出了不同的个性化声音,试图打破中国现代戏剧在发展过程中单一化的倾向。虽然这场运动很快就因为与时势不合而宣告失败,但是它在戏剧理论方面的大胆探索以及它所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戏剧艺术的论题,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探讨的空间和价值。
奥尼尔作品中的诸多特点都与“国剧运动”的一些主张不谋而合,而且张嘉铸在纽约留学时,奥尼尔已经是美国剧坛的明星,所以想必他在当时对奥尼尔就已经有所了解。那么,当奥尼尔抵达上海时,这位当初“国剧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也就是必然的了。这一时期,以张嘉铸的《沃尼尔》为代表的各篇文章,借奥尼尔东方之行为契机,将其作品中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戏剧观念和戏剧技巧介绍进来,这与之前“国剧运动”将大量的西方现代戏剧理论与技巧引入中国剧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无疑都为中国现代戏剧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不仅开阔了当时中国戏剧工作者的视野,同时也为后来中国的戏剧家们创作出多样化的本土戏剧提供了参照,对推动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和丰富中国现代戏剧的内容都具有积极意义。
随后,奥尼尔的东方之行对中国诸多现代剧作家也产生了间接影响。由于奥尼尔来华加速了其戏剧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他的作品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戏剧工作者阅读或是搬上中国的舞台,从而对诸多剧作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洪深、熊佛西和曹禺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洪深作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能编、能导、能演,是剧坛的全能”(53),就连“话剧”一词最早也由他在1928年提出(54),并沿用至今。早年在哈佛大学师从曾经教导过奥尼尔的戏剧教授乔治·皮尔斯·贝克(55)的经历,不仅使洪深成为中国赴美留学专攻戏剧的“破天荒第一人”(56),更使他成为了奥尼尔唯一的中国师弟,这条特殊的纽带无疑加深了奥尼尔与他的潜在联系。洪深先是在1922年依据奥尼尔的《琼斯皇》创作了以中国社会为背景的九场话剧《赵阎王》,之后在奥尼尔开始被中国文坛广泛译介的时候,他又于1934年与顾仲彝合译出版了《琼斯皇》的第一个中译本。除此之外,由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与美国都在经历戏剧改革的风浪,洪深与奥尼尔所处时代的契合,在确立严肃戏剧的艺术理想上的高度一致,以及奥尼尔戏剧中所运用的多元化的戏剧技巧,都使洪深对奥尼尔格外关注,从而对洪深自己从事了一生的戏剧事业产生了深层影响。
熊佛西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拓荒者之一,与田汉齐名,并称“南田北熊”。他无论是在戏剧实践,还是在戏剧理论、戏剧教育方面,均成果卓著。1924年,他远赴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戏剧和教育以及在现场观看《琼斯皇》演出的经历,使他对美国小剧场运动和奥尼尔当时所在的“普罗文斯顿剧社”一直密切关注。在这些戏剧活动的参与过程中,对熊佛西触动最深的就是奥尼尔戏剧所具有的多样化的戏剧表现手法,以及美国小剧场运动敢于创新、勇于尝试的实验精神。(57)受到这种精神力量的鼓舞,他先是于1928年4月创作了明显受《琼斯皇》影响的独幕剧《王三》(又名《醉了》),紧接着在奥尼尔来华之后的1929年6月,又在《戏剧与文艺》第1卷第2期发表了与奥尼尔《天边外》多有相似之处的三幕剧《喇叭》。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熊佛西还是将奥尼尔戏剧中译本搬上舞台的第一人。在“奥尼尔热”刚刚开始的1931年4月,时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的熊佛西,根据赵如琳的中文译本导演了奥尼尔创作于1917年的独幕剧《捕鲸》(58),这是奥尼尔戏剧的中文版本在中国的首次公演。
曹禺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成就最高的剧作家,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早年虽然没有洪深、熊佛西直接赴美学习戏剧的经历,也没有观看美国现代戏剧及奥尼尔作品演出的直观感受,但是随着奥尼尔戏剧在中国迅速传播,曹禺通过阅读文本的途径,同样受到了多维度的启发,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做出了比前两位更高的艺术成就,他所创作的《雷雨》、《日出》更是“标志着中国话剧文学的成熟”(59)。曹禺的戏剧创作受到过奥尼尔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他熟读奥尼尔早年的海洋独幕剧、《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悲悼》三部曲、《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等作品(60),也曾多次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过奥尼尔的影响(61)。除了在他1937年出版的三幕剧《原野》中,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奥尼尔戏剧表现主义的影子,曹禺的许多其他作品也都与奥尼尔的戏剧风格有着共通之处。比如,他们在作品中蕴含的浓厚的自传色彩,对极富生命力的女性角色抱有的长久迷恋,以及对宇宙间神秘力量的不倦探索等等,都可以说是奥尼尔在戏剧创作上对曹禺产生潜在影响的有力证明。
综上所述,我们足以看出1928年底奥尼尔东方之行的重大意义。它不仅丰富了奥尼尔个人的人生经历,为他后来的戏剧创作带来灵感,同时,也终于引起了中国文学界对这位剧作大家的重视,继而使他和他的作品在中国遭受冷遇的境况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并且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和诸多重要的剧作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沈雁冰.美国文坛近状[J].小说月报,1922,13(5).引文中奥尼尔的英文名应为O'Neill,此处《小说月报》印刷的名字有英文大小写错误。
②【美】尤金·奥尼尔.古有成译.天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1月初版.其中“译后”由该书译者写于1928年4月20日。
③刘海平,朱栋霖.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81.
④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8.
⑤卡洛塔·蒙特利·奥尼尔(Carlotta Monterey O'Neill,1888-1970),曾为美国著名舞台剧及电影女演员,因1922年出演奥尼尔的作品《毛猿》而与其相识。1926年两人相恋,并于1929年7月在巴黎结婚,卡洛塔也因此成为了奥尼尔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
⑥威廉姆·戴维斯·金(William Davies King),1983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获戏剧理论与批评专业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为戏剧与舞蹈学院教授,2011年开始担任美国著名学术期刊《奥尼尔评论》主编至今。
⑦Carlotta Monterey O'Neill.Carlotta Monterey O'Neill's Diary for 1928and 1929.Ed.William Davies King.(【美】卡洛塔·蒙特利·奥尼尔著.威廉姆·戴维斯·金编.《卡洛塔·蒙特利·奥尼尔日记——1928年至1929年》.笔者译,下同。)该日记原稿现仍存于耶鲁大学贝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笔者引用的版本为金教授于2009年编辑的电子录入版。
⑧Bogard,Travis,and Jackson R.Bryer,eds.Selected Letters of Eugene O'Neill.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美】特拉维斯·博加德,杰克逊·R·布莱尔编.《奥尼尔信件摘录》.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8.笔者译,下同。)
⑨阿格尼斯·博尔顿(Agnes Boulton,1893-1968),美国著名通俗小说家,1917年与奥尼尔在美国格林尼治村相识,并于1918年结为夫妻;1929年两人离婚。
⑩小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 Jr.,1910-1950),奥尼尔与第一任妻子凯瑟琳之子。
(11)Bogard,Travis,and Jackson R.Bryer,eds.Selected Letters of Eugene O'Neill.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313.
(12)理查德·马登(Richard Madden),奥尼尔在美国戏剧公司(American Play Company)的代理人。
(13)Gelb,Arthur,and Barbara Gelb.O'Neill.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3:678.(【美】阿瑟·盖尔泊,芭芭拉·盖尔泊.《奥尼尔》.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73.笔者译,下同。)
(14)Carlotta Monterey O'Neill.Carlotta Monterey O'Neill's Diary for 1928and 1929.Ed.William Davies King.船名原文为法语Andre le Bon,中文名为笔者译。在国内的一些资料中,此船被译为“马赛莱斯”号,经笔者考证,“马赛莱斯”应是Marseilles的音译,指法国港口城市马赛,而并非船名,故该译法有误。
(15)地理位置大致为现在越南首都胡志明市所在地。
(16)堤岸(Cholon),胡志明市最古老的地区,当地的唐人街亦位于此。
(17)Carlotta Monterey O'Neill.Carlotta Monterey O'Neill's Diary for 1928and 1929.Ed.William Davies King.
(18)奥尼尔虽然在旅途中随船抵达香港,但因天气炎热并未下船,故不计算在内。
(19)(20)刘海平,朱栋霖.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
(21)(22)汪义群.奥尼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3)【美】詹姆斯·罗宾森.郑柏铭译.尤金·奥尼尔和东方思想:一分为二的心象[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209-217.
(24)吴戈.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251-257.
(25)Gelb,Arthur,and Barbara Gelb.O'Neill.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3.
(26)【美】克罗斯韦尔·鲍恩.陈渊译.尤金·奥尼尔传:坎坷的一生[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27)Bowen,Croswell.The Curse of the Misbegotten:A Tale of the House of O'Neill.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Inc.,1959.
(28)该书在第十七章“离乡背井”中,关于奥尼尔东方之行的路线、入住饭店及在各地停留时间等细节都存在与事实不符的偏差。
(29)Bogard,Travis,and Jackson R.Bryer,eds.Selected Letters of Eugene O'Neill.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322-3.
(30)肯 尼 斯 · 麦 克 高 恩 (Kenneth Macgowan,1888-1963),美国电影制片人,曾于1922年在普罗文斯顿剧社担任制作人,与奥尼尔成为合作伙伴,后来二人成为终生挚友。
(31)Gelb,Arthur,and Barbara Gelb.O'Neill.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3:672.
(32)Carlotta Monterey O'Neill.Carlotta Monterey O'Neill's Diary for 1928and 1929.Ed.William Davies King.
(33)Gelb,Arthur,and Barbara Gelb.O'Neill.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3:681.
(34)写这封信时奥尼尔40岁,而他所说的21岁,应该是指他在1909年前往洪都拉斯勘探金矿的探险经历。
(35)Bogard,Travis,and Jackson R.Bryer,eds.Selected Letters of Eugene O'Neill.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324.
(36) (37) (38)Carlotta Monterey O'Neill.Carlotta Monterey O'Neill's Diary for 1928and 1929.Ed.William Davies King.
(39)此句原文出自奥尼尔于1929年1月29日写给好友Horace Liveright的信件,刘海平和朱栋霖在《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中首次将其译为中文(第76页),后被《尤金·奥尼尔和东方思想:一分为二的心象》(第209页)、《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第256页)等书转引。
(40)Bogard,Travis,and Jackson R.Bryer,eds.Selected Letters of Eugene O'Neill.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323.
(41)1937年到1944年奥尼尔和卡洛塔一同居住在大道别墅(Tao House),其间他创作了后期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如《送冰的人来了》、《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月照不幸人》等。
(42)胡逸云.介绍奥尼尔及其著作[N].世界日报,1924-08-24.
(43)余上沅.戏剧论集[M].上海:北新书局,1927:51-56.当时奥尼尔的中译名还没有统一的译法,“阿尼尔”即为其中一种。
(44)张嘉铸.沃尼尔[J].新月,1929,1(11).“沃尼尔”为“奥尼尔”当时的另一中译名。
(45)查士骥.剧作家友琴·沃尼尔——介绍灰布尔士教授的沃尼尔论[J].北新,1929,3(8).
(46)寒光译.美国戏剧家概论[J].戏剧,1929,1(4).
(47)春冰.戏剧生存问题之论战[J].戏剧,1929,1(2).
(48)春冰.英美剧坛的今朝[J].戏剧,1929,1(2).
(49)春冰.最近两个月的世界剧坛[J].戏剧,1929,1(3).
(50)春冰.欧尼尔与《奇异的插曲》[J].戏剧,1929,1(5).“欧尼尔”也是“奥尼尔”当时的一种中译名。
(51)原资料此处有一字不清,故括号中内容为笔者所加。
(52)张嘉铸.沃尼尔[J].新月,1929,1(11).
(53)引文选自1942年曹禺在洪深五十诞辰时书赠的寿联。
(54)阎析梧,孙青纹.赞洪深在艺术上的首创精神[J].戏剧艺术,1981,(2).
(55)乔治·皮尔斯·贝克(George Pierce Baker,1866-1935),美国著名现代戏剧理论家和戏剧教育家,1905年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首开戏剧编撰课程“英文47”;1914年,奥尼尔在贝克教授的指导下,在此课程中学习戏剧编撰;1919年,洪深也成为了贝克教授的学生。
(56)洪深.现代戏剧导论.洪深文集(第4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78.该文原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九集《戏剧集》的导言。
(57)林碧珍.熊佛西评传[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21-24.
(58)上海戏剧学院熊佛西研究小组.现代戏剧家熊佛西[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189-190.
(59)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255.
(60)曹禺.我所知道的奥尼尔[J].外国戏剧,1985,(1).
(61)曹禺.原野·附记[J].文丛,1937,(8);曹禺.让中美友谊之花盛开[J].人民戏剧,1979,(1):25-26.
I712.073;I207.3
A
1004-342(2015)06-66-10
2015-10-08
刘文尧(1986-),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