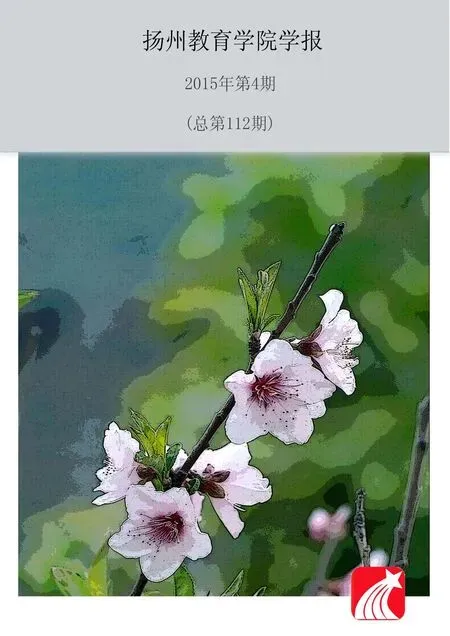论禅宗语录中“不可说”的语言艺术
莫照发, 王小华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云浮 527200)
论禅宗语录中“不可说”的语言艺术
莫照发, 王小华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云浮527200)
摘要:禅宗语录中蕴含着丰富的语言艺术,其说教语言艺术主要强调学习者的自我体验即禅“不可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是指禅宗说教时不拘泥于固定的文字形式,但并非不要文字。
关键词:禅宗;不立文字;“不可说”;语言艺术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禅的特点是以心传心,也就是强调学习者的自我体验而淡化语言文字的作用,《坛经·机缘品》述当年六祖慧能听到比丘尼无尽藏诵读《大涅槃经》即为之解说,并提出“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一说[1]。可见禅之“不可说”实有所本。不少人据此以为禅宗说教不需要文字,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禅宗不仅留下来很多文字如语录、公案等,而且都很有特点,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说教语言艺术。禅宗自称“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是因为不像其它佛教流派都有自己开宗立派的印度佛教经典,而透过禅宗历史文献发现,其语录、公案中具备非常高超的说教语言艺术[2]。禅宗的很多语录、公案,一问一答之间看似极不合理,但深入细品,乃是由禅的“不可说”旨趣决定的。本文从禅宗的语言特色“禅说三非”——非“理性的说”、非“明确的说”、非“详细的说”来论述禅“可说”与“不可说”的辩证关系。
一、矛盾言辞——非“理性的说”
通常,语言表达要符合逻辑、前后一致的基本原则,前后矛盾的语言表达是历来被人所诟病的。但是,神秘主义者都喜欢运用看似毫无道理、自相矛盾的“无理性”去阐述他们的哲学,禅也不例外。德国哲学家赫里格尔在日本学习6年的弓道和禅后认为,在所有宗教里,最神秘的莫过于禅了[3]。相传当年傅大士留下一首非常有名的偈语——“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明明空着的手如何握了一把锄头?明明步行着竟还骑着水牛?更不可思议的是,明明水流桥不动,偏偏说 “桥流水不流”!这便是禅非常特别的说教语言风格——看似十分矛盾的语言逻辑,却体现出非常生动具体的禅学哲理。“花不红,柳不绿”是禅宗最有名的说教案例之一,其实表达的意思和“花红柳绿”是一样的。这是因为禅宗表现自己哲理的方式就是“否定对立”,禅师们说教最重要的原则是不要“落入”如下四句格式:(1)是A;(2)非A;(3)既是A,又是非A;(4)既不是A,亦不是非A。如果落入这四句格式,则陷入了二元对立推理方法的误区,这与禅的宗旨是相违背的,在禅看来,只有我们既不加肯定也不加以否定时,才可以悟道。铃木大拙甚至在《禅:答胡适博士》一文当中说:“我们一般推论:A是A,因为A是A;或A是A,所以A是A。禅同意或接受这种推论方式,但是,禅有它自己的方式,这种方式并不是一般可以接受的方式。禅会说:A是A,因为A不是A;或A不是A,所以A是A。”[4]禅的真理显然在日常语言与一般推理之外。如同云门所说:“禅里面有绝对自由;有时否定,有时又肯定;高兴用什么方法,就用什么方法。”曾经有一个和尚问他:“如何肯定?”云门说:“冬去春来。”和尚又问:“春来有何事?”云门说:“肩上横着杖子,不分东西南北;漫步田野中,敲击残桩为乐。”这就是他想表达的自由自在的方式。当年有和尚询问禅宗六祖慧能:“黄梅意旨什么人得?”六祖回答:“会佛法的人得。”和尚又问:“和尚还得否?”六祖回答:“我不会佛法。”和尚又问:“你怎么不会佛法呢?”六祖的回答仍然是:“我不会佛法。”慧能这种矛盾、否定、不合理的回答,是基于禅不可用理智表达而传授给他人的特性决定的,即禅是不可说的,禅只有学习者自己靠身心去体验和参悟,在任何情况下对于那些未入法门者,禅师都是爱莫能助的。禅师们在说教的时候,对逻辑的忽视甚至是故意的,它的本意是让提问者明白一个道理——禅的最高境界是独立于理智之外的,如同《波罗蜜多经》中所说:“无法可说,是名说法。”《金刚经·如法受持分》亦载: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不?”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铃木大拙曾说:“任何文学上的成就或者理智的分析都不能用在参禅上面。”因此,你可以认为禅师们的说教相对于提问者的“逻辑性”而言,是非常矛盾的,但是,当你把禅师的回答对照着禅的要义及旨趣进行分析时,“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就会觉得禅师的回答是多么的富有哲理。他们并不急于说教以免影响悟禅的进程,因为他们知道,过多的说教只会对学人有干扰作用,于是用他们对禅的本质理解这种最神秘、但又最亲切的方法来帮助对方。
二、问指答月——非“明确的说”
通常人与人的语言交流要符合“有问必答”的基本要求,不能“答非所问”。但是由于禅要求我们要自己认识到真善美之心,如铃木大拙所说:“禅本质上是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艺术,它指出从奴役到自由的道路。”亦即禅宗所谓“明心见性”。如果一个迷途中的学习者自身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本所在,即他所问的问题是明显违背禅宗法理的,这个时候禅师们面对的是一个未识本心、未见本性的门徒,如果禅师坚持“答如所问”就已经失去了禅宗说教“教外别传”的基本原则。例如《文益语录》载——僧问: “指即不问,如何是月?”师曰:“阿那个是汝不问底指?”又僧问:“月即不问,如何是指?”师曰:“月。”曰:“学人问指,和尚为甚么对月?”师曰:“为汝问指。”这就是禅宗有名的公案“问指答月”。“指”、“月”之辩,能够帮助学僧确立基本的禅宗语言观。“月”实质上是“诸佛妙理”,“指”乃是“佛经文字”,“ 文字”之中蕴含“妙理”,但妙理绝然仅仅局限于文字本身;如果执着于文字本身,妙理就无法获得。一开始学僧问:“指就不问了,什么是月呢?”此时文益禅师反问学僧:“你那个不问的‘指’是什么呢?”这足以让学僧幡然醒悟自己将“指”和“月”分离、“指即不问”而问“月”的错失了。但是学僧却执迷不悟,再问:“‘月’就不问了,什么是‘指’呢?”这一问又把“月”搁置一边而径直问“指”是什么。所以,文益禅师只答一个 “月” 字[5]。回答虽然只有一个“月”字,但是胜过千言万语。学僧如果此时能够顿悟,便能明心见性。问指答月的语言艺术在禅宗许多公案中都可见到,例如马祖道一病重,院主前来探望,问:“大师近来身体可好?”马祖道一答:“日面佛、月面佛。”院主顿感莫名其妙,不能意会。其实,马祖并不直接正面回答对方的问题,却以问指答月、不为说破的方式来巧妙回答对方的提问,你会或者不会,禅的寓意就在那里,从对方的反应可以验证参禅的境界。表面上看,一问一答,你问东,他答西,犹如指在手上,月在天空,两者相距甚远、毫不相干,但一语而令当局者从迷失中惊醒,认识到不丢失自我本性的重要性,实在是一种让人叹为观止的语言艺术。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一切存在的事物之“存在”意义,都必须从人的时间性的“此在”领悟这一中心去阐发[6]。所以,海德格尔用“存在是人的存在即此在”来回答“什么是存在”,是多么富有哲理的语言艺术。
禅门问指答月的故事有很多。相传当年赵州禅师在佛堂前扫地,有学僧问:“您是得道高僧了,怎么还扫地啊?”赵州的回答非常令人吃惊,他答:“尘埃是外面飞来的。”学僧又问:“此处乃清净圣地,怎么会有尘埃呢?”赵州答道:“瞧,又飞进来了一粒尘埃!”此禅宗公案的寓意在于,僧人当机带有高低贵贱的问话明显违反了佛法的“众生平等”基本原则。赵州暗示学僧未见本心,不识本性,然而僧人依旧执迷追问,因此禅师只好间接地说他就是尘埃了。又如,当一位禅师把痰吐在了佛像身上后,周围许多门僧责骂他:“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把痰吐在佛祖的身上呢?”这位禅师却连续反问:“你们告诉我,哪里没有佛?我现在还要再吐,请问哪里没有佛?”这位禅师已经参悟到“法性遍满虚空,法身充满宇宙”的哲理。而旁人却怪罪于他把痰吐在了佛祖身上,表面上看学人对佛祖虔诚至极,毕恭毕敬,实际上恰恰对佛理有严重的误解。佛的法身是遍满虚空,充满法界的,明心见性,众生是佛,反之则“佛是众生”。所以这位禅师利用未开悟者的误解反问:“请你们告诉我,哪里没有佛?”这种语言艺术的高超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说出佛法的要义,而是顺势利导,直指人心,不明确说破却在反向责问中隐含着禅学中“人人是佛”的道理。
三、惜字如金——非“详细的说”
禅师引导门徒,常常只用一个字或几个字,简单明了,斩断纠葛,使门徒无路可通,直接开启顿悟法门,这种语言艺术往往应用简短机智的机锋式问答来考量参禅者。云门化导学人时,惯常以简洁的一字道破禅的要旨,禅林美称为“云门一字”。如《人天眼目》卷二载:“杀父杀母,佛前忏悔;杀佛杀祖,甚处忏悔?”师云:“露。”其他如:问“什么是道?”答以“去”字;问“什么是禅?”答以“是”字;问“什么是云门一路?”答以“亲”字;问“什么是正法眼藏?”答以“普”字等等。云门宗对津津于参禅问答的形式主义之风,以截断众流来加以破除,对滔滔不绝谈禅说法的风气时常加以批评:“问者口似纺车,答者舌如霹雳。总似今日,灵山慧命,殆若悬丝。少室家风,危如累卵。”指出那些执着于文字的学人“食人涎唾,记得一堆一担骨董,到处驰骋驴唇马嘴,夸我解问十转五转话。” 面对不识本心未见本性的凡夫俗子和长篇累牍的文字,云门一字诀这些简单无比的语言形式,如铁山横亘在面前,使参禅者湍急奔驰的意念之流陡然中止,在窄不通风的关口,让参禅者脱离原来的思路,于片言只语之际、电光火石之间消除知见妄想,扫除旧念,彻见本心[7]。德国哲学家赫里格尔与日本著名弓道大师及禅师阿波研造,曾就学箭有一段经典的语录——“那我应该怎么办?”赫里格尔若有所思的问道。“你必须学会正确的等待。”“怎样才能学会正确等待呢?”“你要放下自我,毅然决然地舍弃自我以及一切属于你的东西。除了无意的紧张,什么都不要留下。”“那么我必须有意去变得无意?”赫里格尔疑问。“没有一个学生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不知怎样答复你。”“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这些新的练习?”“等到了时候再说”[8]。通常按照常理来讲,提问者问得越仔细,老师应当是感到高兴并且乐意为之给出详细的解答。但是基于禅是不可说的,正所谓“言多无益”,禅师过多的解答反而是不利于学人的自我体验和参悟的,所以,在公案中禅师们都采取了“惜字如金”的应答策略。
更不可思议的是,由于禅宗说教特别强调时机和分寸,如果学习者的内心体验和感悟未到,禅师甚至是不会透露一个字的,时机不到,与其细说,不如不说。《碧岩录》卷七载:有一次梁武帝召请傅大士讲《金刚经》,傅大士走上讲台后“于座上挥案一下,便下座。”梁武帝“愕然”,大士上讲台后本来是要说法的,但是众目睽睽下只字未提佛法,就从讲台上下来了,这太不合常理了。倒是旁边的高僧志公赶紧问了梁武帝一句:“陛下您领会到了吗?”梁武帝根本就没有听到傅大士对《金刚经》的讲解,一个字都没有听到,谈何“领会”?志公或许看出梁武帝真的没有“领会”,便提醒他说:“(其实)傅大士已经把《金刚经》讲完了。”像这种只有肢体动作,却没有只言片语的说教艺术,表面上看空无内容,实际上充满禅门的玄机,禅宗的许多佛理实已蕴含其中。有时候千言万语难以说清楚禅的主旨,表面上看傅大士沉默不语,却间接地暗示出一个很高深的参禅道理,使人肃然起敬。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一个人可以喋喋不休地讲,却始终什么也没说。另一个人可以保持沉默,但正因为一言不发,他说了许多。”[9]著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其名著《逻辑哲学论》一书深刻警示后人:“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默而不语,意味着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表面不说,其实内心已经间接告诉了学习者问题的所在,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四、结语
不管是毫无逻辑的“说”,还是问指答月的“说”,亦或者是惜字如金的“说”,甚或闭口不言,禅师们毕竟还是“说”了。只不过,相对于参禅的门徒而言,听不听得懂禅师“说”的意境罢了。因此,禅宗说教中“不可说”的语言艺术,其形式上还是注重“说”的,其本质上则是“不为说破”。据《五灯会元》卷一记载,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法会上拈花示众,众人皆不能意会,只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心领神会,知其意旨。于是释迦佛便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檠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禅宗说教的这种看似非逻辑、非常态的语言艺术风格,最终令禅宗“不可说”的旨趣一脉相承,以至后世第三十三代六祖慧能开坛布法,概莫能外。禅宗公案的盛行,将禅“不可说”的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10]。禅师古德常示意学人“不可说”,既然禅是不可“说”的,说了也等于白说,那“说破”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或许这正是禅意“不可说”的内在缘由。“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其实是说明禅宗说教时不拘泥于固定的语言及文字形式,但并非不要文字——孔子说“余欲无言”,但还是留下了《论语》;老子说“道”“不可道”,还是留下了五千言;释迦牟尼说“不可说,不可说”,却还是说了四十九年法。禅宗六祖更是于旷世奇著《坛经》中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传禅佳句,慧能在《坛经·付嘱品第十》指出:“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这表明禅宗佛理还是“可说”的,但是它强调运用三十六对法说法时,语言一经说出就要脱离两端,不落实处,“说”万法皆不离自性,最后把生灭、有无全部扫除干净。
总之,矛盾言辞、问指答月、惜字如金等禅宗“三非”即“不可说”的教学语言艺术,恰恰是禅师们通过“说”来指引学人重新找寻正确的悟禅方向——一切佛法尽在人自心之中,要在自心之中当下顿见真如本性。因此,通过“可说”以使学人“明心见性”、“自性真佛”,这才是禅“不可说”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参考文献]
[1]赖永海.坛经[M].尚荣,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
[2]李如密.禅宗语录中的教学艺术初探[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1(3):39-42.
[3]铃木大拙.禅与生活[M]. 刘大悲,孟祥森,译.合肥:黄山书社,2010.
[4]铃木大拙.禅:答胡适博士[EB/OL].(2009-02-18)[2015-10-25].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429525/.
[5]李如密.《坛经》中的教学艺术初探[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1(2):85-89.
[6]周裕锴.百僧一案:参悟禅门的玄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法光.函盖乾坤、红旗闪烁的云门禅风[EB/OL].(2015-08-13)[2015-10-25].http://cz.zgfj.cn/WZ/CD/2015-08-12/21376.html.
[8]欧根·赫里格尔.学箭悟禅录[M].余觉中,译.合肥:黄山书社,2011.
[9]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0]刘方.禅门公案的性质、特征与价值[J].宗教学研究,2003(1):26-32.
(责任编辑:杨洁)
On Language Art of “Inexpressibility” in Excerpts from Zen Buddhist Texts MO Zhao-fa, WANG Xiao-hua
(Luod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Luoding 527200, China)
Abstract:Excerpts from Zen Buddhist Texts is rich in language art, which emphasizes the learners’ self-experience, i.e. Zen’s “Inexpressibility”. When delivering a sermon, Zen insists the philosophic theory of not being confined to the form of language instead of being wordless.
Key words:Zen; no dependence on words and letters;“Inexpressibility”; language art
中图分类号:B 94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36(2015)04-0001-04
基金项目:广东省云浮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2015云社研[8号])。
作者简介:莫照发(1976—),男,罗定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讲师,硕士。
收稿日期:2015-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