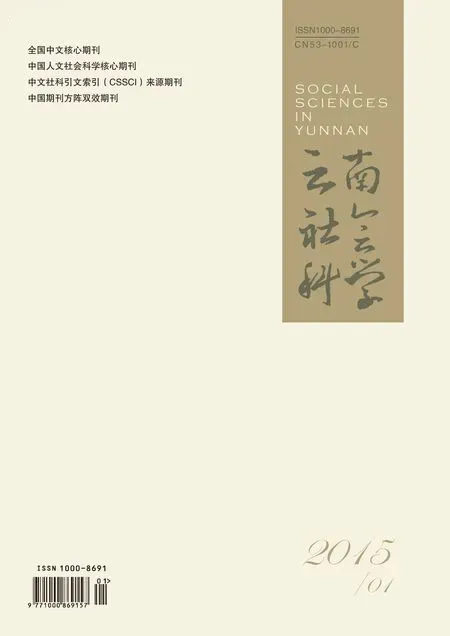庄蹻王滇千年争论的学理反思
杜玉亭 杜雪飞
一、从《中华史纲》的庄蹻王滇说起
一再拜读史学大家蔡美彪先生的《中华史纲》[1](P56),受益良多,特别是其以“中华史”作为书名,为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开拓了一种新境界,极具创意。如书中第七章题名“辽宋金和战”,看似平平常常,却打破了传统史学“唐宋元明清”的序列,还中国古代史一个民族平等的现代史观。又如“第八章 蒙元一统”,“第九章 汉族王朝的再建——明朝”,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也是一种突破。即使第三章第二节的“征服南国”,即汉武帝时征服越国(广东广州)、夜郎国(贵州牂牁江畔)、滇国(云南昆明)等,皆以国家对待,亦为中国古代地缘政治史中的一种新意。总之,《中华史纲》创意较多,不具。
因为《中华史纲》将5000年中国史浓缩至30万字的书中,“纲”的精要特色明显,故即使是字斟句酌,也难免百密一疏。以下所引有关滇国的论述,即为其中的一疏:
今云南滇池地区,楚国将军庄蹻曾领兵占据。值秦灭楚,遂留在今晋宁一带称滇王。夜郎归附后,武帝发兵入滇,滇王降汉。汉朝加封,赐给官印“滇王之印”(今存)。设益州郡(治今云南昆明)统辖。[1](P56)
全文120字,却对滇国始末史表述得清清楚楚,确实是史学大家的大手笔。其权威性也自在言外。同时还说明,它认同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的楚将庄蹻王滇说。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庄蹻王滇事属千年争论无结果的一道史学难题,现代史家也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近年较有影响力的两家之言见于以下两本名著:一是《云南通史》的观点:楚将“庄蹻王滇”,“二万甲士融入‘滇人’”,“极大地促进了滇国的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2](P27)。即它认同并发挥了《史记》的楚将庄蹻王滇说。另一名著是一版再版的《云南简史》的观点:楚国“起义军的领袖庄蹻”,失败后“撤出楚境”,“南下入滇”、“变服王滇”,“庄蹻是内地第一个开发西南边疆的伟大历史人物”[3](序,P34、36)。它又是否定《史记》的记述另有新说的一家之言。看来,《中华史纲》在“庄蹻王滇”的立论中,曾参考了云南史家的著作,并且是有所取舍的。
笔者一研究云南史有年,且曾与滇川黔学人多次合作,在庄蹻王滇问题上亦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近因《中华史纲》的启发,并与有关学友商讨后,谨提出庄蹻王滇两个方面的问题,以供思考。
二、蒙文通《庄蹻王滇辨》的史学价值
蒙文通(1894~1965)《庄蹻王滇辨》(以下简称“蒙文”),近2万字,首发于《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一期*数十年前笔者一在成都与四川友人完成合作项目时,曾拜读此大作,受益良多却无存稿,近因困于学,求教蒙文通先生令子川大蒙默教授,幸得转载此文的《古族甄微》(《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巴蜀书社,1993年),谨铭感致谢。。就庄蹻王滇的问题而言,它是我国现代史学界首次系统的考据性论证。全文共分无题式五个部分。其为首的两段开宗明义,说明全文宗旨,兹照录于后。
无论是探讨西南民族的古代史,还是探讨战国时期西南的民族关系,无有不征引“庄蹻王滇”这一传说的。这一传说始见于故事发生后约一百八十年的作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史记》的原文是: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应依《汉书》删蜀字)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俗以长之。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
就在这短短百多个字的记叙中,不论是在事件发生的时间上、路线上、地域上和人物上,都有问题。因而这一传说究竟有多大可靠程度、有多少史料价值,是值得考虑的。我愿在这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同志们讨论。[4](P275~276)
蒙文(一)首先指出,“司马迁的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随后班固著《汉书·西南夷传》“除个别文字差异外,全是照抄”司马迁的说法。但是,东汉末年荀悦著的《汉纪》,虽是据班固《汉书》删约改编而成,唯独在庄蹻王滇一事上首次提出了“不同的说法”。足见司马迁的说法“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发生动摇,已不为史家所信奉了”,“紧接着《汉纪》之后,《后汉书·西南夷传》又提出和《史记》《汉书》不同的说法,而且和《汉纪》的说法也不相同”。特别是此后蜀人常璩著的《华阳国志》中,更对庄蹻王滇提出了许多新看法。因此,从校订过的古本《华阳国志》之文以与《史记》《汉书》《汉纪》《后汉书》进行比较,有以下种种差异(原文实录):
1.所遣人物:《史记》作庄蹻,《后汉书》作庄豪。
2.遣将时间:《史记》是楚威王,《后汉书》《华阳国志》是楚顷襄王,《汉纪》是楚庄王。
3.西进路线:《史记》是循江,《华阳国志》是溯沅。
4.占领地域:《史记》是滇池及其旁数千里,《后汉书》、《华阳国志》是夜郎、且兰,《汉纪》是靡莫。
5.《史记》明确指出庄蹻为“王滇”,《华阳国志》则指明所王之地为“夜郎”,《汉纪》则明言其为“王靡莫”。
6.《史记》以庄蹻为楚庄王苗裔,《华阳国志》无此说,而以“庄王”为庄蹻称号。《汉纪》又以庄蹻为楚庄王将军。
7.《史记》以秦通五尺道在统一六国后,《华阳国志》则以为在秦并蜀后。[4](P275~276)
蒙文(一)列举《史记》问世300多年间5本书的七点差异后,从(二)至(五),就对庄蹻王滇的问题进行了详尽考证。限于本文的体量,以下谨对其主要观点加以概说。
1.遣将时间的问题
蒙文(二)“先从遣将时间”说起:“第一个对《史记》所说遣将时间明确提出异议的是杜佑,他在所著《通典》卷一八七《边防》三中滇条下全录《史记》原文,而独将楚威王改楚顷襄王,并用详细的按语加以说明。此后的作品如郑樵《通志》卷一九八、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九、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九等,都根据杜佑的考证而采用顷襄王时的说法。”
蒙文还引用多家先秦诸子书中的记述,作为佐证。进而说明,“遣将时间当以《华阳国志》所载较为合理”。换言之,蒙文通过遣将时间的考证说明,中国古代史家的著作已经否定了《史记》的楚威王说,而选用了《华阳国志》的顷襄王说(前298~前263)。
2.西进路线的问题
蒙文对庄蹻西进路线的问题的诸多考证,具体而微,这里仅概说如下。《史记》说是“循江上”,汉魏以前典籍的“江”字单举,一般都“专指长江”,但由楚国至云南的滇池,首先要经今重庆地区,但这里“早已为秦国所占”,再前进则要经今贵州中西部地区,这里正是秦将司马错“大军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所要夺取的“楚巴黔中”之地,而同时的楚是“庄蹻一介偏师”,为何能抵敌,“又何能以兵威平定数千里之地呢?”更何况,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秦将张若就攻取了今四川西昌到云南大姚一带,即《华阳国志》所说的张若取筰及其江南地,已临近滇池了呢?因此,《史记》的“循江上”行不通,《华阳国志》的“溯沅”说两军各走一路,可以避免矛盾,“显然是较合理一些”。
至于秦国在云南东北地区修的“五尺道”,即蒙文(一)“种种差异”之“7”,是在秦并六国之后,还是秦灭蜀之后,事关西进路线的军事形势,也是《华阳国志》的秦灭蜀之后正确,《史记》的秦灭六国之后不正确。
3.“种种差异”的焦点在庄蹻是否“王滇”
蒙文(一),即上述西进时间、地点与形势问题,看似不太重要,实则不然,因为正是它才为蒙文的主题,即庄蹻是否王滇问题立起了学术标杆。而蒙文(一)种种差异之(1)人物、(4)占领地域、(5)王都之地、(6)人物身世,四点合而为一的焦点,就是庄蹻是否王滇,且这几点中的每一点都众说不一,各执一词,从而对《史记》庄蹻王滇说的真实性进行了质疑。为了辨明这些难题,蒙文对有关古代史书包括先秦诸子之说,进行了认真考订。考订中还涉及了四点中不曾涉及的人物,如楚国有两个庄蹻,一是作为楚将的庄蹻,另一个是“发动暴动”的“大盗”庄蹻,进而从时间、地点、形势等说明,两个庄蹻都不存在“王滇”之事。
蒙文开宗明义引用《史记》庄蹻王滇百余字的八句话,经考订后,每一句话都有问题,如第一句:“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后依《汉书》删蜀字)黔中以西。”时间、地点、人物三者都不正确,即使最后两个简明句:“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时间与史事上也有问题。
总之,蒙文(一)之所以要列举庄蹻王滇的七点“种种差异”,并给以详细考辨的原因与结果,最终在于认定:《史记》的庄蹻王滇是本不存在的人为传说。
4.蒙文的一家之言
蒙文(一)举出庄蹻王滇的七点“种种差异”,更在(二)、(三)、(四)、(五)中进行具体考订,从而否定庄蹻王滇真实性的最终原因,还在于阐明自己的一家之言。因为,无论其多层次的微观史实考订,还是蒙文具有系统性的宏观架构,目的都在比较与弥合庄蹻王滇的七个“种种差异”中,引申出自己如下的一家之言(原文照录):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庄蹻王滇”一故事的原形应当是这样:在牂牁江流域,有一个古国名牂牁,其古君长中有一个号称庄王(庄豪)的,是牂牁国的开国君长。当其在距战国末年几百年以前,沿牂牁江而北来,征服了夜郎、且兰、牂牁、滇池等国,地方数千里,成为这一地域的联盟首领,并分封了滇、劳深、靡莫等兄弟之邦。
庄王所建立的牂牁,由于文献缺乏,不知什么时候便衰微了,在遁水流域又有夜郎竹王的建国。但庄王所建立的滇、劳深、靡莫等国,一直存留到了汉代。庄王建国的故事,流传在这些国家中,也逐渐流传到了临近的昆明等地。庄蹻则是楚之大盗,本无入滇之事,他和庄豪原不相干。[4](P290)
蒙文总结自己一家之言的这两段话,虽是推论,却有理有据,且又留有余地,没有把话说尽。与本文上述两家庄蹻王滇之言有别的是,它们在“庄蹻王滇”上并无分歧,其唯一的区别在一家主张王滇庄蹻的身世是楚国将军,另一家主张王滇的庄蹻是楚国农民起义领袖,且都对自己的观点坚信不疑。
5.庄蹻王滇千年争论难以厘清的根源
蒙文据《史记·太史公序》自巴蜀“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句,认定司马迁西征返京时在武帝元封元年(前110)。而“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中之“昆明”,指多年来一再阻止汉使求“身毒道”的昆明人,他们是“毋常处,毋君长”。但与汉军不断作战的游牧部落,不可能接待汉使,故司马迁之“奉使”亦即奉命,其角色是“中郎将郭昌”征昆明人中的一位“武官”“郎中”,时在元鼎六年(前111),即滇王降汉置益州郡的前一年。因此,司马迁的足迹“最南可能只到达了”昆明人所在的今云南大理地区,而《史记》的庄蹻王滇事属几经转述后成形的百余年前的传说,由此而出现了种种“错误”,故引起后世学人的种种误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说到蒙文的史学价值,应当承认,它是对庄蹻王滇千年争论系统考证的科研成果。因为它既考订了千年争论的“种种差异”问题,又阐明了千年争论无定论的原由,进而在宏微通观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达到现代史学研究的一种新境界。
蒙文对于蔡美彪先生的《中华史纲》而言,可以洞见其百密一疏的以下真切原因:庄蹻王滇千年争论之所以没有结果,是因为云南古代史的难题与中原大不相同,即使当今云南史学名著的定论,也不一定可取。因此,中国史学名著在做云南民族古史难题的结论时,宜宏微通观,在谨慎求实中创新。
三、滇国史学研究与考古学结缘的问题
1.滇国史学研究与考古学结缘的必然性
滇国考古从1954年进入现场至今已60年,1955年第一次试掘就出土100余件奇异的青铜器,当时莅昆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为之惊叹不已,并誉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5](P5)。1956年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多种文物4000余件。奇珍异宝,美不胜收,举世闻名的滇王金印,就是这次发掘的6号墓出土的”[5](P5)。滇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促进了滇国历史研究的大发展,考古学与历史学人之外,更有民族学、文化学人的介入,真可谓诸家斗胜,其论述林林总总,难以计数。
60年的事实证明,滇国史学研究与考古学的结缘,有其必然性。即使以其与司马迁《史记》的有关记述相比,也可见其一斑:其一是,《史记》中的“滇王”只是2000多年前的书面文字,并不等于事实,而滇王之印出土就有了实证,二者一结合,就是“名”副其实,既再现了2000多年前的真相,也提升了司马迁《史记》的学术价值。其二是滇国青铜文化展现的种种人物形象,为滇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研究提供了真实依据,则是现代考古学对古文献的一种超越。这对笔者一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1958年参编《彝族简史》时,云南调查组领导特请四川大学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研究滇国青铜器人物与彝族的关系。当然,冯先生的研究是客观的,并未说滇国的王族是彝族的先民,但其与彝族有关的研究结果亦如实写入了《彝族简史》*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载《考古》1961年第9期。冯先生1959年临别赠给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同名稿件,即此文的原稿。。当时云南多个少数民族的“简史”中,也据此论述了他们与古滇国民族的关系。尽管类似的研究属于比较性推论,但仍是对《史记》有关云南民族百字简述的一种实证性超越。
事实还证明,滇国考古不仅超越了古文献的记述,还引导滇国史研究进入了现代史学领域。为此,仅以滇国考古学专著《滇国与滇文化》第十章的章、节、目为证:“第十章 滇国奴隶制社会及其特征,第一节 滇国的奴隶制,一、农业生产中的奴隶,二、畜牧业生产中的牧奴,三、纺织业中的女奴,四、青铜器图像中受刑和被出卖的奴隶。第二节 滇国奴隶社会的特征,一、原始公社残余形态的存在,二、商品经济薄弱,三、战争俘虏和被征服民族是滇国奴隶的主要来源,四、奴隶的占有和使用仅限于滇国王室。”滇国考古史学专著认定的上述滇国奴隶制社会,亦如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现证实了商朝的奴隶制一样,为学界与社会广为认同。
2.滇国史学研究与考古学结缘的难点
多年的事实证明,滇国史学研究与考古学结缘的关系,是始终存在的。但不可忽视的是,二者关系的不和谐乃至矛盾的现象,仍然存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因为考古学的方法重实证,而古代史学的研究方法重文字思辨,故两种方法的研究结果也会大相径庭。如滇国王都与所辖区域出土文物虽同属于滇国文化,但因时间与地点的差异会有不同的分期,故考古学人特别注重滇国时空不同点之间的差异性,而历史学人则不然,因为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多注重各取所需,虽利用了考古资料,也往往会事与愿违。
滇国史学研究与考古学结缘的难点,与当代云南史学的两大名著密切相关,其一是马曜主编的《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1991年再版“增订本”,2009年第3版),马曜先生为此书写的“绪论”中明确提出:“约在公元前286年,庄蹻率领数千楚国农民起义军到达滇池地区,同当地居民融合,控制了滇东地区。”此即为滇王身世是楚国农民起义领袖说。但是,有关此说的争议甚早,被誉为滇史泰斗的方国瑜先生早在1975年就发文提出异议,其中的题目之一就是:“开滇的庄蹻是楚将,不是农民领袖庄蹻。”*见方国瑜《从秦楚争霸看庄蹻王滇》,载《思想战线》1975年第5期。此题所争论的是《思想战线》1975年第1期载马曜《庄蹻起义与开滇的历史功绩》一文。[6](P17~27)这就形成了与王滇者是农民领袖说对立的另一大家:王滇者是楚将庄蹻说(认同《史记》的说法)。此说在近年出版的云南史学名著《云南通史》(何耀华主编)中又得到充分发挥。
以王滇者是楚将还是楚农民领袖相区别,由云南两部史学名著代表的两大史家,至今已对立了数十年,仍未见有定论的迹象。其原因在于二者皆由传统史学的史料性思辨主导,无支撑立论的实证。二者的另一弱点值得特别注意,即他们都忽视了滇国考古的实证性科学研究成果。
3.滇国考古史学专著取得了与史学结缘的主动权
有关滇国的发掘报告与论文数以百计,它们是出于不同时间的滇文化的实证,在推进滇国历史研究中都具有某种人文价值。但至今60年间,属于滇国考古的史学性专著,只有一部,即张增祺著《滇国与滇文化》,46万字,摄影图片100幅,插图81张,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笔者拜读张先生的大作后深有感触,因为它是现代考古微观实证研究与现代宏观史学有机结合的硕果,其科学性显而易见。为此,且简列此大作的十一章目录为证:绪论,滇国都城所在和滇国分布范围,绚丽多姿的滇国青铜文化,滇国的民族,滇国的经济,滇国的生活,滇国的军事,滇国的宗教,滇国的文化艺术,滇国奴隶制社会及其特征,滇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还要说明,此十一章之下还有节。如第五章“滇国的经济”之下,就有农业、畜牧业、狩猎业、渔业、建筑业、冶金业、纺织业、漆器制造业、陶器制造业、珠宝玉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含竹器、木器、角器、皮毛制品四个目),共11个节。节之下更有目,具体而微,不具。由此可知,对滇国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如此全方位的具体论证,与《史记》几百字的记述相比,真可谓判若天渊,不能同日而语,因为二者缺乏可资比较的平台。这就是《滇国与滇文化》的第一个特点:源于实证的全面系统性。
《滇国与滇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其“历史分期”对庄蹻王滇千年争论的判定。其第一章“绪论”第一节“滇国历史概述”,开宗明义头一段,就对滇国形成时间、地域、历史分期与兴衰过程,给以言简意赅的全面说明:
“滇”是我国西南边疆古代民族建立的古王国,主要分布在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云南省中部及东部地区。考古资料证实,滇国出现的时间至迟不晚于战国初期,战国末至西汉初为全盛时期,西汉中期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西汉末至东汉初被中原王朝的郡县制取代。滇国存在的时间大致有500年左右,即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初。[5](P1)
如果联系有关章节,还会发现该书的十一章皆与这一基本结论密切相关。由此可知,滇国是在500年的特定时间、特定地域与特定历史机遇内出现的古代民族王国。它虽与中原民间商家有联系,但全盛期的滇国文化,却处于中原王朝的文化圈之外。大作还特地将全盛期滇国文物与楚国出土的标准器物相比较,竟“丝毫看不出两地文化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5](P25)。为史的笔者因些许疑惑请教张增祺先生时,得到的答复更为简明:“全盛期滇国与楚国出土的各种标准器中,无论大件小件,没有一件有共同点。”且云其曾亲至楚国出土文物处进行比对。这就是说,《滇国与滇文化》用滇国考古历史分期的实证,否定了《史记》庄蹻王滇传说的真实性。换言之,它客观上支持了现代史学三家言中的庄蹻王滇是本不存在的人为传说一家。
《滇国与滇文化》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个性非凡。青铜文化可以展示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滇文化异于人类其他青铜文化的一大特色。正是在这种全方位的文化展示中,突出了滇国青铜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其中已引起中外考古学界重视的一点,是滇国骑兵的马镫,被认为是世界考古学中的首次发现[5](P192~193)。它虽然比较原始,却开启了古代军队快速攻击的战斗力。看来,滇国文化中许多部落首领向滇王进贡的场景,应与马镫的发明有关。滇国青铜文化个性的另一非凡处,是其文化信息涵有南北两个方向,其南来的是贮存于瑰丽多姿的铜鼓中来自印度洋的数十万枚海贝[5](P169),是为海洋文化的信息,北来的是向滇王献艺的高鼻深目佩剑的斯基泰人的托盘舞[5](P280、284),此为北方欧亚草原文化的信息。2000多年前的高原湖泊平坝区准农耕型的滇国文化中,同时涵有南方海洋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两大信息源,这在同期中国乃至世界文明中,亦属罕见。当然,它称不上什么世界性的人类文明,但作为一种地区性的特色文明,也弥足珍贵。
总之,《滇国与滇文化》的上述三个特点,就是滇国考古史学专著取得与传统史学结缘主动权的三个标志。它同时也伴有相应的实证性与科学性。但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它问世17年,却并未引起云南两大名著史家的正视。《云南简史》一版再版,是在《滇国与滇文化》问世多年之后,其王滇的庄蹻是楚国农民起义领袖说依然故我。而由《云南通史》代表的另一家仍发挥着司马迁《史记》的楚将庄蹻王滇说(《中华史纲》也持此观点)。看来,千年争论无结果的庄蹻王滇问题,不仅是立意不同的诸多史家间各持己见的问题,更与中华民族史学理论的根基有关,需要深入研究。(张增祺先生、林超民教授曾对本文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