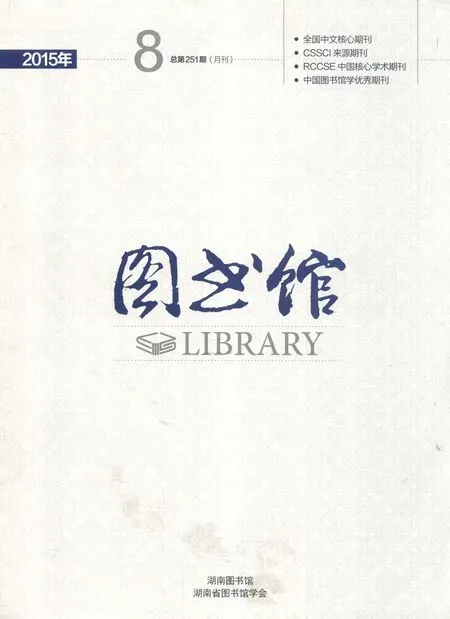权利理论视阈下图书馆权利概念的辨析与解读
——图书馆权利若干命题的困惑与思考之一
魏建琳(西安文理学院图书馆 陕西西安 710065)
权利理论视阈下图书馆权利概念的辨析与解读
——图书馆权利若干命题的困惑与思考之一
魏建琳
(西安文理学院图书馆 陕西西安 710065)
〔摘 要〕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权利概念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多元分歧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图书馆权利”是普遍的权利文化在图书馆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其概念不应是新创出的一种权利,而是在已有人权体系中寻找自身的定位与归属。图书馆权利是图书馆活动中为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定为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参与图书馆活动的所有人都是权利主体,不同权利主体有不同的权利内容,宪法是最终衡量正当与否的标准。
〔关键词〕权利 权利理论 图书馆权利 概念
1 问题的提出
2005年1月8日,在黑龙江大学召开了“中国图书馆学会首届峰会”。峰会共探讨了5个议题,“‘图书馆权利’是本次峰会讨论最为热烈的议题”[1]。“峰会”之后,《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图书情报知识》等专业期刊相继推出专栏“专门探讨‘图书馆权利’的一些相关问题”[2]。同年7月, 在广西桂林召开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年会以“图书馆权利”为主题专设“分会场”,继续为“研究”推波助澜。“自2005年起,中国图书馆学界掀起了一股‘图书馆权利’研究热”……[3]时至今日,讨论越热烈,分歧与差异似乎越大。由于缺乏对基本概念和命题的共识,似乎都在探究“图书馆权利”,但各自所指却南辕北辙。这不能不说是“图书馆权利研究”热闹喧嚣背后的一种隐忧。“学人们对‘图书馆权利’概念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4]
“权利”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不是图书馆学专有的研究范畴。“现代社会人们一般把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权利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至少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也是一个伦理学和社会学的概念。”[5]因而,笔者拟探赜图书馆权利的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的理论渊源,打破成见,在法学、政治学的权利理论视阈下对图书馆权利概念做一番全新的辨析与解读。
2 权利概念理论探赜
2.1 权利概念的产生
从历史上看,权利的概念产生于中世纪的西欧。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人必须高度依赖群体……人的权利观念淡薄。”[6]中世纪的欧洲,实行土地封建制度,土地归领主或贵族所有,平民只能租种贵族的土地。因而,平民必须绝对服从贵族的权威,向贵族尽各种义务,如缴纳大量的赋税、服徭役与兵役等。而贵族对平民则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此时此地,只有贵族的“权利”,而“权利”等同于“权力”。
到了公元十二世纪,“西欧的农业生产力开始迅速提高……农产品出现剩余,贸易开始重新出现,而这种状况所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城市的出现。伴随着城市出现的就是市民阶级的壮大”[7],此时的欧洲出现了一个与“政治社会”对立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市民阶级,市民阶级从事的主要活动是商业贸易,“这种商品经济关系所要求的行为意志自由和契约行为的对等性,使得原来自然经济关系中不具有自我意识的广大社会成员开始感到自己的存在,感到自身的人格尊严和生存价值,从而追求自主生存的生活。”[8]对上述社会背景,“唯物史观的经典作家对此做过精湛分析……马克思把权利产生的社会形态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9]
“人的独立性”一旦成为社会普遍的诉求,就必然会与中世纪的黑暗现实产生尖锐的矛盾。矛盾冲突中,市民阶级萌生了强烈的权利意识,“提出权利来与封建专制制度相对抗。”[10]西欧一批思想巨擘,如洛克、康德、孟德斯鸠等“立足于商品经济社会关系发展导致的人的主体状态变革的现实趋势,借助传统思想资源,将市民群体要求享有的平等自由的基本权利,论证为人的本性要求,论证为人拥有的出自自然本性的绝对权利……以先验论的方法,赋予它们神圣的社会地位”[11],在欧洲掀起了一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导致人的思想和精神的觉醒,催生了个性解放和个人利益的追求意识,催生了思想和信仰的自主意识,培育了人们追求权利人格的主体自觉性”[12]。从此,西欧社会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与“权力”相分离的“权利”概念。从此,“权利”概念逐步成为西方价值观的核心并发展为一种全球文化。特别是从此,世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人类走进了“权利时代”。
2.2 权利概念的发展与演变
权利的概念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权利概念在欧洲诞生之初,其核心内容是“自由权”。这是因为“市民阶级最不可缺少的就是个人自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行动、营业与销售货物的权利”[13]。这类朴素的权利要求被洛克等启蒙先驱论证为“天赋人权”,“归结为自由、平等和所有权”[14]。“天赋人权”是一种“要求国家不得侵犯与干扰的权利”[15],其所指的自由“是一种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其范围包括宗教自由、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16],“作为思想自由胚胎的宗教自由……逐渐发展为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出版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等‘表达自由’。”[17]“表达自由”一般是指“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其延伸权利也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此项权利应该就是图书馆学术界热议的“知识自由”、“智识自由”以及“信息自由”的本源。
以“自由权”为核心的“天赋人权”,被后世的权利理论研究者们命名为“古典人权”、“自然权利”、“第一代人权”。“第一代人权”通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经历了欧美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血与火的洗礼,经过了《权利法案》(英国)、《人权宣言》(法国)、《独立宣言》(美国)的不断确认与宣示,逐步发展为欧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继而发展为“普世价值”。
“第一代人权理论”为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提供了理论武器,“但这一理论的唯心论破绽又是显而易见的”[18],它的逻辑前提假设与人类的经验事实相距甚远。对此,“不要说用马克思主义去击破,就是休谟、边沁、密尔、奥斯汀等分析法学家以及萨维尼等历史法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发难,就足以摧毁它的哲学基础。”[19]“第一代人权理论”“实质上是其所处时代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形态中的社会主体状态的一种非历史性的曲折反映”[20],“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其人权保障的重点是资产阶级要求的财产权和契约自由”[21],而对于广大劳动者的人权则在表面自由平等的商品经济关系中“被否定、限制或虚置化……仅具有形式意义”[22]。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做过深刻的剖析。由于过分强调竞争和自由使自由资本主义在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实现了物质财富的高度积累之后,对公平的漠视又使其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助长了人性的进一步堕落,致使社会矛盾加剧。在经历了不断的“经济危机”与“阶级冲突”后,国际社会出现了二元分化,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涵之一是平等,该价值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思和否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结果。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一般都将“平等权”置于诸项权利之首[23]。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亦“不再公开确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将福利国家上升为国家理念”[24],开始关注“实质平等”,开始保障“劳工权益”。从权利理论的视角,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殊途同归”,以“平等”价值为核心的“社会权”成为两大阵营共同的关注点。
“社会权”又称“福利权”、“受益权”、“平等权”、“积极权利”或“第二代人权”。广义的社会权利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这一权利还可以再分为经济权利、狭义的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社会权”中所说的“经济权利”并非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而是指“工人享有的、与劳动场所有关的权利”,包括劳动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休息的权利;接受就业培训的权利;丧失工作能力时获得救济的权利;失业时享受生活保障的权利等。“狭义的社会权利”是指“与社会保障和社会安全有关的权利”,包括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免于饥饿的权利;健康的权利等。“文化权利”虽然与经济和社会权利一起提了出来,但是人们对文化权利的关注远不如后者。由于对“文化”一词理解上的不统一,所以“对于这一基本概念,任何关于人权的文件都未做出确切的界定”,“人们对文化权利任意组合,文化权利散见于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各种文件”,对文化权利的认知抵牾矛盾之处甚多。一般认为“文化权利”[25]包括:文化认同的权利;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权利;信息权;文化遗产权等。
从“第一代人权”到“第二代人权”,从“自由权体系”到“社会权体系”,从“追求自由”到“主张平等”,“人类追求的权利的范围也日益扩大,人权的内涵也日益丰富。人们对人权的理解也从普遍的自然权利、政治权利,日益扩大到社会经济生活权利等各个方面”[26]。“二战”以后,联合国先后制定了《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进一步确认与明确了“权利”的相关概念。从此,“权利”由“利益主张”固化为“国际规则”,成为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成为现代文明的核心概念。
2.3 权利概念的多元与迷茫
权利的概念产生于历史发展的需要,历史与现实的需要引起对“权利”问题的学术探究。自近代以来,“权利”一直作为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特别是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被学术界所关注。“概念”是一个学科的基石,是学术探究的基础,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前提。古今中外,“到底有多少人给权利下过多少次定义,似乎还没有人作做具体的确切统计,但就目前学界所掌握的现有资料分析,仅从国外引进的并为大家所耳熟能详的权利概念或定义就不下十余种”[27]。但是,“无论中外哪一位法学家、学者对权利所作出的诠释均未获得普遍的共识;而且每一种权利定义皆遭到过批评或质疑”[28]。
虽然不同的学者“站在各自的、不无一定局限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界定权利,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权利问题的理解”[29],但是权利概念的多元化导致了“权利这个词在不同的背景中具有不同的含义”[30],“权利”成了一个最具有“歧义性”的“受人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权利语言经常被滥用,关于权利及其涵义的讨论也时常发生一些误解。”[31]权利概念的多元与分歧导致了“权利概念的滥用与迷茫”。
3 图书馆权利概念的辨析与解读
3.1 图书馆权利界定的个人之见
2000年以来,图书馆业界围绕“图书馆权利”诸命题展开了大量探讨,其中不乏对“图书馆权利”概念的各种界定。笔者以为,对“图书馆权利”的界定不能忽视和淡化了对“权利究竟是什么”的探究,应该对“‘图书馆权利’的‘权利’到底是什么,它具体的抽象的范畴是什么”的探究作为“图书馆权利”研究的前提与基础。要回答“‘图书馆权利’的‘权利’到底是什么”的命题,首先必须厘清“图书馆权利”的“权利”是对图书馆活动原生命题的抽象概括,也是普遍的权利文化在图书馆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因此对图书馆权利界定就不应该是在图书馆活动的范围内的“创新”,而应是在已有人权体系中找到自身的定位与归属。这是因为“如果仍然把人权看作是最高的道德权利,就要使其数量尽可能地减少……我们需要承认新的权利,但是,人权无谓的扩展,只会引起使人权的真正思想贬值的危险,因而逐步地削弱所有人权。我们应该对于承认既不清楚又不迫切需要的新人权的潜在危险保持高度谨慎”[32]。另外,从学术角度而言,“学者在使用概念并确立命题的过程中须慎之又慎。如果有新的认识因而需要确立一个命题,则必须经过证明。”[33]如果说对“国际上‘图书馆权利’研究是否已有成熟的理论”的命题尚有分歧、尚有争议的话,那么中国的“图书馆权利”研究毫无疑义尚处于萌芽状态,尚不具备把握本质并定义新概念的充分条件。
3.2 权利概念的再探究
在“权利理论”的视阈下对“图书馆权利”的概念进行辨析与解读,意即从已基本形成共识的“权利理论”出发,对“图书馆权利”的概念内涵做出定义或诠释。但是,由于现代“权利”的概念在发展丰富的同时也导致了权利概念的多元与分歧,使“权利”成了一个“受人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34]。故之前的理论探赜尚不足以对“图书馆权利”的概念内涵做出定义或诠释,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究与辨析。
“迄今为止,中外思想家、学者对权利所作的界说可分成两大类:一为从权利本质属性的界说,可称为权利本质论;一为从权利具体情形的界说,可称为权利实证分析论。”[35]
关于权利的本质,格劳秀斯和19世纪的形而上学法学家们强调的是伦理因素,认为“权利”的本质是“道德”,把权利看作“道德资格”。而耶林等学者则使人们注意到权利背后的利益,认为“权利的实质是普遍的功利”,“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36]。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角对“权利”所蕴涵的“经济关系”属性做了更进一步的剖析,其理论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利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权利本质论的代表人物是夏勇和张文显。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夏勇教授曾对“权利的本质”做过精到的分析,“他归结出权利成立必不可少、也是基本的五大要素:利益、主张、资格、力量、自由”[37],认为“上述五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能表示权利的某种本质,那么,以这五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要素为原点给权利下一个定义都不为错。究竟以哪一个要素或哪几个要素为原点来界定权利,则取决于界定者的价值取向和理论主张”[38]。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张文显教授系统归纳了近代以来思想巨擘、法学名人从本质属性界定权利的最具代表性的八种学说,即资格说、主张说、自由说、利益说、法力说、可能说、规范说、选择说,“对中国当代相关学界之权利理论影响深远,以至于中国相关学界对权利本质的认识,要么是对某一学说的肯定或认同,要么是对相关学说的概括或折衷。”[39]
“由于从权利的要素或属性界说权利的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分析法理学的法学家开始了对权利分类和具体情景的实证分析……他们注意分析权利概念包含的丰富内容,并把义务和法律关系等概念联系起来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法学家霍菲尔德。”[40]霍菲尔德认为:“分析法律概念的最好方法,是诉诸‘相反者’(opposites)和‘相应者’(correlatives)的关系图表,然后举例说明它们各自在具体案件中的范围和应用。”[41]霍菲尔德归纳了四对相反的概念和四对相应的概念进行逻辑分析 ,“把权利置于现实的利益关系来理解,并侧重于从实在法的角度来解释权利”[42]。虽然“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图解远非在逻辑上严谨科学,在内容是完整无遗”[43],但是他在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里通过实证分析来理解和叙述权利概念,“细致地揭示权利概念的丰富内涵”[44],为全面和深入地认识权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作为法学等学科基本范畴的权利,尽管界定起来如此之难,却仍是国内外学界孜孜以求其精确性的范畴。因为,每当概念的一些含义被弄得明晰易懂以致为许多人所知时,就标志着自我认识和理解的增长,并使富于智识的思想和行为成为可能。”[45]很显然,正是由于这些学者们孜孜以求的探索,才使得“图书馆权利”的研究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3.3 图书馆权利的内涵诠释
如夏勇教授所言,“从以上可见,仅仅从某个特定的角度给权利下一个定义并不难,以这五个要素(利益、主张资格、力量、自由)中的任何一个要素为原点给权利下一个定义都不为错,但这样做容易导致权利问题的简单化、庸俗化”[46]。同理,为“权利”的“下位类”——“图书馆权利”下定义也是如此。如果随意撷取一个“权利界说”,在其前加上“图书馆”的限定,似乎一个“图书馆权利”的定义就直接“跃然纸上”。但是,如此简单、机械地“照搬”,很明显有悖于学术研究的宗旨。
笔者查阅了许多中外专家学者对于“权利”所下的定义及其阐释,但仍感觉“一头雾水”。困惑中“避重就轻”四字让笔者豁然开朗。既然“现代图书馆核心价值或最基本的理念,包括对全社会普遍开放、平等服务、对弱势群体优先服务,以及支持智识自由等,就理论的源头而言,都可上溯到权利这一概念”[47],那么,对于“图书馆权利”概念的探究就是每个图书馆从业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对“图书馆权利”这一概念的内涵,即其本质属性的总和,尚有认识盲点,尚不能用简洁而明确的语言加以界定的话,那么就不妨暂且“避重就轻”,回避“下定义”,仅是“作诠释”,仅对“图书馆权利概念内涵”的某些性质或特点进行适当辨析与解读。
在“作诠释”前,必须先借用夏勇教授的定义作为逻辑起点。夏勇教授曾经给权利下一个这样的定义“权利是为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定为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48]。既然认同夏勇教授的观点,那么理所当然也可以为“权利”的“下位类”——“图书馆权利”下一个这样的定义:“图书馆权利是图书馆活动中为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定为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但是,夏勇教授却如此评价他所做出的这个定义:“这个定义并不是完美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49]。既然如此,那么笔者简单、机械地“照搬”,所给出的定义自然更不是完美的,更没有多大意义。如果要使这个定义尽可能地接近于完美,尽可能地有点意义,就必须要做进一步的探究,做进一步的辨析解读,然后对这个定义中的一些模糊之处做出适当的解说。
这个定义的第一个模糊之处是“图书馆活动”。“图书馆活动”,顾名思义,就是在图书馆这个场所(也可以界定为“空间”,包含“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所发生的一切行为。这个“一切行为”可以概括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物的关系”两大范畴。“权利”就是“人权”,自然需要在“人与人的关系”范畴中进行探究,探究图书馆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如果要将“图书馆活动”具体化,就包括传统的文献搜集、整理、保存、提供等活动与创新的文献检索、信息咨询、知识服务、展览、讲座、阅读推广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管理关系与服务关系,而这些不同的关系中都存在共同的权利关系。
厘清了“图书馆活动”的概念后似乎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模糊”,即“人与人的关系”中的“人”是指哪些人?答案似乎很明确——读者、馆员与图书馆组织(法人)。但是这个明确的问答在权利理论的视阈下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辨析与说明。在权利理论的视阈下,上述问题应表述为:在图书馆活动中所存在的权利关系中的“权利主体”是哪些人?“权利主体”具有哪些性质或特点?
2000年以来,图书馆业界围绕“图书馆权利主体”的界定命题展开了大量探讨,或支持“读者权利”,或认同“馆员权利”,或认定“图书馆职业权利”,观点分歧,各执己见。笔者以为,在权利理论的视阈下认知,“权利时代”,人权具有普遍性,是人人都应享有的权利。所以,在权利时代,参与图书馆活动的所有人都是权利主体,包括读者、馆员、法人以及其他,只是不同权利主体的权利内容会有所不同。
所谓“权利时代”,是人们对近现代社会特征的一种主观概括,只有在“权利时代”才能生成健全的“权利人格主体”。对于“权利人格主体”的特征,马克思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具体讲就是,一方面,社会主体普遍摆脱传统社会的人身依附,拥有自主平等的经济人格,享有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人格尊严,每个人都能自由平等地追求个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社会主体普遍认同“人道主义”,产生了“人的道德权利或应有权利的观念”[50],这种权利观念提倡“既珍视自己的权利又尊重别人的权利”,使权利在“本质上带有‘正当’的意味”[51]。这是普遍意义的“权利人格主体”的特征,自然也是参与图书馆活动的“权利人格主体”的特征。
明确了“图书馆活动”与“图书馆权利主体”后,接着需要辨析的认识盲点是“为道德、法律或习俗认定为正当”的标准是什么?
夏勇教授之所以对他所下的定义评价不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道德、法律或习俗认定为正当’,也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52],因为如此就无法对“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做出清晰明确的界定。对此,笔者以为“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是“权利时代”“启蒙阶段”的必然现象。启蒙时期,人权一词停留在应然层面上,是政治哲学和法哲学讨论的话语形态,权利理论建立在不同的价值观之上,自然“见仁见智”,这是不同价值基础与不同研究方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2004年“人权入宪”使人权获得了实然的法律地位,成为法律规范,实现了人权由道德形态向法律形态的转变。这就意味着宪法作为最高的规范层次,会凌驾道德、法律或习俗之上,成为最终衡量正当与否的的标准。
4 结论与讨论
2004年“人权入宪”标志着一个“权利时代”的到来,社会各界激起了对“权利”话题的浓厚兴趣,图书馆行业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国图书馆人对于权利的研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学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性研究之一”[53]。
但是,同法学等研究领域已形成了成熟的“权利本位范式”,“提供了共同的理论背景和理论框架……足以空前地把一批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瞄准一个方向、围绕一个论域开展大兵团研究”[54]的状况相比,图书馆权利的研究却显得差距明显。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业界对“图书馆权利”概念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貌似都在探究“图书馆权利”,但各自所指却南辕北辙。概念的混乱使研究难以为继,讨论亦不可能。故蒋永福先生在“‘图书馆权利’研究反思”[55]中将“‘图书馆权利’概念的具体内涵如何把握?”列为我们仍需研究并澄清的首要问题。
笔者以为,当前业界对“图书馆权利”概念的认识存在分歧,其具体内涵无法把握的根本原因在于:绝大多数的“图书馆权利”概念界定都是围绕着“是谁的权利”而展开,而对于“权利究竟是什么”的命题或语焉不详,或刻意回避。这也许有其各种原因,但是,在有意无意间忽视和淡化了对“权利究竟是什么”的探究,却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与误读,导致概念的具体内涵无法清晰把握。
“权利究竟是什么”是法学等学科“权利理论”探究的核心论域,因而笔者以为,“图书馆权利”的概念应在“权利理论”的视阈下进行辨析与解读。
笔者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权利”概念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多元分歧的现状进行了简单梳理,在此基础上认为,“图书馆权利”诸现象是普遍的权利文化在图书馆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因而“图书馆权利”概念不是新创出的一种权利,而是在已有人权体系中寻找自身的定位与归属。是故笔者“移植”夏勇教授的界定为“图书馆权利”下了一个定义:“图书馆权利是图书馆活动中为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定为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并对定义中“图书馆活动”、“图书馆权利主体”、“为道德、法律或习俗认定为正当”的标准做了诠释解读。
倍感惭愧的是,由于对“图书馆权利”命题认识盲点颇多,故文中避重就轻,对有些命题有所回避,希望今后能与业界专家同行围绕以下命题继续探究。
首先,关于“图书馆权利主体”的话题,围绕此话题,业界观点分歧,争议不断。笔者以为,如果将“图书馆权利”界定为“图书馆”的“权利”,那么毫无疑义,这个“权利”是“职业权利”,“权利主体”是“图书馆(法人)”。但是,如果将其界定为“图书馆场所”“图书馆活动”中所存在的“权利现象”,那么,在权利时代,参与图书馆活动的所有人都是权利主体,只是不同权利主体的权利内容会有所不同。
其次,关于“图书馆权利内容”的命题,如文中所述,当今“权利”存在“自由权体系”与“社会权体系”的划分,那么“不同图书馆权利主体”的“不同权利内容”其实都可以最终归结为“自由权”和“社会权”。否则,或是“伪权利”,或是“不同的权利概念”。
最后,关于“衡量正当与否的的标准”命题,如文中定义,如果“不正当”则构不成“权利”。但是并非只要自己认为是合理、正当的需求,就可以称之为“权利”,“正当”应有客观的标准。笔者在文中认为,宪法会凌驾道德、法律或习俗之上,成为最终衡量正当与否的的标准。但是,“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只是一种框架性规定,具体内容当然有赖于部门法来规定,宪法不能替代部门法律的功能”[56]。而“图书馆立法”的窘境却无疑让这个“衡量正当与否的的标准”显得异常“模糊”。
如果说“衡量正当与否的的标准”只是让人觉得“模糊”的话,那么“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在图书馆活动中的具体所指则更加让人“迷惑”。许多“迷惑”也成为文章的一个未竟的话题,留待下次的进一步探究……
(来稿时间:2015年2月)
参考文献:
1. 毕红秋.权利正觉醒 激情在燃放——中国图书馆学会2005年峰会综述.图书馆建设,2015(1):12-14, 29
2-4.程焕文.图书馆权利的来由.图书馆论坛, 2009(6):30-36
5,10,30,51.辛世俊.公民权利意识研究.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
6,8,9,11,12,18,20-22,29,35,37,39,40,43,45,50.菅从进.权利制约权力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7,13.方新军.权利概念的历史.法学研究,2007(4):69-95
14-17,23-25,32,33.郑贤君.基本权利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
19,54.张文显,姚建宗.权利时代的理论景象.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5):3-15
26.尹奎杰.权利思维方式论.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1):18-30
27,28.范进学.权利概念论.中国法学,2003(2):15-22
31,34,36,38,41,42,44,46,48,49,52.夏勇.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法学研究,2004(3):3-26
47,53.范并思.权利、读者权利和图书馆权利.图书馆,2013(2):1-4
55.蒋永福.“图书馆权利”研究反思.图书馆建设,2008 (4):59-61, 65
56.吴家清,杜承铭.论宪法权利价值理念的转型与基本权利的宪法变迁.法学评论,2004(6):3-9
〔分类号〕G250
〔作者简介〕魏建琳(1967- ),男,西安文理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Concept of Library Rights in the Visual Threshold of Rights Theory——Perplexity and Thinking on Some Propositions of Library Rights
Wei Jianlin
( Library of Xi’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mbs that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present state of multiple divisions of concept of rights and thinks that “library right” is common culture of right’s concrete embodiment in the library activities, its concept should not be creates a new kind of rights, but to find their own positioning in the existing system of human rights. Library rights are interests, claims, qualification, strength, or free that are recognized as legitimate by the morals, laws or customs in the library activities. Everyone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of the library is right subject, different subject has different rights content, spec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s the ultimate measure of legitimate or not.
〔Keyw ords 〕Rights Right theory Library rights Conce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