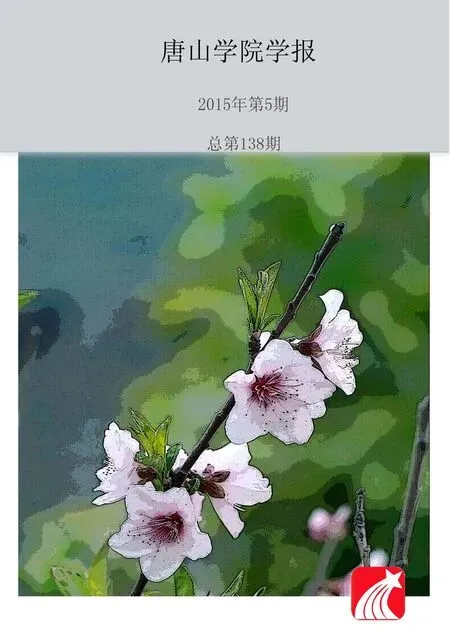制书发展演变考略
魏 昕
(北华大学 文学院,吉林 吉林 132013)
制书发展演变考略
魏 昕
(北华大学 文学院,吉林 吉林 132013)
制书的发展演变,可从制度层面和文体本身两个角度进行考察:就制度层面来讲,制书作为诏令之属,其发展和完善,是在皇权的维护和国家制度的规范下实现的。随着制书规范性的明晰与强化,其名称、格式、行文、执行制书的程序等等,都具备了明确的标准和严格的律法规定。从制书文体本身来看,其演变则发生了两种情况:一方面,制书功能由普遍地颁布“制度之命”,转而变为用于“行大赏罚、授大官爵”等授命封官之事;另一方面,制书文体则衍生出“德音”这一变体形式。
制书;体式;功能;变体
制书乃源于秦代“改‘命’曰‘制’”,它的着眼点在于突出和强调皇帝诏令的权威性。《独断》载:“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上迁,书文亦如之。”颜师古注《汉书》有云:“天子之言曰制书,谓为制度之命也。”*《汉书·高后纪》:“太后临朝称制。”颜师古注曰:“天子之言曰制书,谓为制度之命也。”《后汉书·光武帝纪》引《汉制度》注曰:“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1]由此可知,在汉制中,制书既是“天子之言”,又是制度之命,也就是说,天子的命令便是制度。不难看出,这些表述对制书的功能性说明,远多于对其体式特征的介绍。而这种倾向,恰恰与制书文体在秦汉时期得以确立、初成的客观情况颇为符合。
秦汉以后,制书作为皇命的重要载体,始终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制书在发展过程中,随着国家制度层面对其规定的不断强化,它的文体特性得以明确地展示和凸显;同时,制书的功能与体式也在不断调适,以符合制度层面在变迁过程中的不同规定与需求。
一、制书规范性的强化
汉代以后,制书作为皇命的重要载体,其在国家制度层面的规范化进一步凸显。曹魏元帝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十一月,有司奏议燕王不称臣时,提出:
礼莫崇于尊祖,制莫大于正典。陛下稽德期运,抚临万国,绍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体尊戚属,正位藩服,躬秉虔肃,率蹈恭德以先万国。其于正典,阐济大顺,所不得制。圣朝诚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礼。臣等平议以为燕王章表,可听如旧式。中诏所施,或存好问,准之义类,则“宴觌之族”也,可少顺圣敬,加崇仪称,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问大王侍御”。至于制书,国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轨仪于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诏燕王”[2]。
燕王曹宇乃魏元帝曹奂之父,身为皇帝的曹奂为了表示孝心,下诏允许燕王上表不用称臣,为此,有司奏议称,尊祖与典制同样重要,处理此事可以做出一些变通:由宫中直接发出的中诏,可行存问之礼以示长幼有序,宜称“皇帝敬问大王侍御”。至于制书,则是国家典仪制度的象征,是向天下昭示仪式规范的标准,不可任意改动,故而制书在下达时,宜遵循一贯的制度规定,称“制诏燕王”。可见,中诏在现实使用中,其行文可以做出一定程度的变通,相比之下,制书的行文则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不可任意改动,体现出制书行文上的规范化。
就制书名称来看,其在汉代以后经历了几番规定和调整:北周时,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春正月乙丑,“改制诏为天制”[3]。唐代时,武则天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因避讳而“改诏曰制”[4];唐代七种“王言之制”中则列有制书和慰劳制书两种形式;唐玄宗时,根据草拟制书人员的不同职能,将制书分为内制和外制,内制中又包括书写于白麻纸的制诰之词,称为白麻制诰。清代时,制书则称为制辞。可以说,国家在制度层面对制书名称有意识地加以各种界定,客观上更加凸显了“制书”这一文体概念。
在书写格式方面,与汉代制书相比,唐代制书则形成了更为具体的固定模式。日本学者仁井田升在其所辑《唐令拾遗》中,将唐代制书格式进行了复原:
制书式 门下,云云,主者施行。
年月日
中书令具官封臣姓名宣
中书侍郎具官封臣姓名奉
中书舍人具官封臣姓名行
侍中具官封臣名
黄门侍郎具官封臣名
给事中具官封臣名等言,
制书如右,请奉
制付外施行,谨言[5]。
由这则制书格式来看,除了制书命令的主体部分之外,还包括制书的颁布日期、宣读者、奉制者、颁行者,以及进言请奉制施行者等诸项要素。制书中融入这些要素,一方面说明制书的书写格式在唐代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和完善,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唐代制书的颁布和下达更加系统化和程序化。
由于唐代设置了翰林学士院这样的机构专门草拟“内制”,而翰林学士在选拔入仕过程中,更以制书批答为考试内容,这便使得制书的拟制,在实用性之外,更增添了形式上的要求:“制用四六,以便宣读。”[6]3682
逮至北宋徽宗“政和辛卯始以制命题”,制书的创作标准更进入了追求形式审美的新阶段:
制头四句能包尽题意为佳,若铺排不尽,则当择题中体面重者说,其余轻者于散语中说,亦无害。制起须用四六联,不可用七字。制头四句说除授官职之职,其下散语一段略说除授之意。文臣自内出则说均劳佚之意,武臣宿卫则说忠孝拱扈之意,换镇则说易地之意,其余可以类推。……制头四句四六一联,散语四句或六句,不须用联。‘具官某’一段颂德,先需看题,文臣专用文臣语,武臣专用武臣、宗室语,不可互用……一段说旧官,所谓叙旧官者,非止叙前任也。先略说履历,不可指定官名,但随文武官泛说数句,然后说前任。……一段说新官。‘於戲’用一联,或引故事,或说大意。……后面或四句散语,或止用两句散语,结不须更作联,恐冗。制辞须用典重之语,仍须多用《诗》、《书》中语言及择汉以前文字中典雅者用,若晋宋间语及诗中语不典者不可用。魏晋以来文史中语间有似经语者亦可于制中用,但其间名臣,非人共知者不必称引以为故事。除帅制‘具官’后说新除处须略说地望,只须四句,如‘眷巧荆南,应于鹑尾’之类;建节不须说本镇地望。官名须于《职官分纪》寻替换字。如尚书为中台,吏部为选部,礼部为仪曹,似此类须每件寻两三般,盖临时有声律虚实之不同也。郎曹以下不必记,非从官而记者止卿监司业。节镇须记地名,每镇须地名两三件,若止记一件,恐声律虚实不同,难作对也。亦止是记在境内者,每常多记洲名,如越为镇东,湖为昭庆是也。然州名亦不须记,但云镇东乃会稽,昭庆乃(上雨下言)水可也,盖制中惟用地名,州名无用处耳[6]3682-3683。
到了清代,“凡大典礼宣示百寮,则有制辞”[7],其在行文上呈现出整齐划一的特点。以祭祀为例:
①(冬至日,南郊大祀礼节)制辞于群臣曰:某年月日冬至,朕恭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惟尔群臣,其蠲乃心,齐乃志,各扬其职,敢或不共,国有常刑,钦哉毋怠。
②(夏至大祭方泽礼节)制辞于群臣曰:某年月日夏至,朕恭祭皇地祇于方泽。惟尔群臣,其蠲乃心,齐乃志,各扬其职,敢或不共,国有常刑,钦哉毋怠。
③(每岁孟春上辛祈谷礼节)制辞曰:某年月日上辛,朕恭祀上帝于祈年殿,为民祈谷。惟尔群臣,其蠲乃心,齐乃志,各扬其职,敢或不共,国有常刑,钦哉毋怠。
④(每岁孟夏常雩礼节)制辞曰:某年月日,朕恭祀皇天上帝,祗秩常雩。惟尔群臣,其蠲乃心,齐乃志,各扬其职,敢或不共,国有常刑,钦哉毋怠[7]。
四则制辞只在祭祀时间、地点和祭祀对象这几个具有实用功能的要素上有所不同,而关于告诫群臣的表述则完全一致。这一倾向表明,其时中央集权高度集中,这使得作为皇命而颁布的制辞,在制度层面具备了更为严格的规定,故其行文亦不可随意变通。
汉代以后,关于违反制书的相关律条,也规定得更加细致、繁复。以唐代为例,针对制书的律条有:
诸稽缓制书者,一日笞五十,一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唐律疏议·职制》)
诸被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徒二年。失错者,杖一百。(《唐律疏议·职制》)
诸受制忘误及写制书误者,事若未失,笞五十;已失,杖七十。转受者,减一等。(《唐律疏议·职制》)
诸公文有本案,事直而代官司署者,杖八十;代判者,徒一年。亡失案而代者,各加一等。《疏议》:依令:“授五品以上画‘可’,六品以下画‘闻’。”代画者,即同增减制书。其有“制可”字,侍中所注,止当代判之罪。(《唐律疏议·职制》)
诸受制出使,不返制命,辄干他事者,徒一年半;以故有所废阙者,徒三年。余使妄干他事者,杖九十;以故有所废阙者,徒一年。越司侵职者,杖七十。(《唐律疏议·职制》)
诸诈为制书及增减者,绞;未施行者,减一等。(《唐律疏议·诈伪》)
其收捕谋叛以上,不容先闻而矫制,有功者,奏裁;无功者,流二千里。(《唐律疏议·诈伪》)
诸盗制书者,徒二年。(《唐律疏议·贼盗》)
诸弃毁制书及官文书者,准盗论;亡失及误毁者,各减二等。(《唐律疏议·杂律》)
诸私发官文书印封视书者,杖六十;制书,杖八十。(《唐律疏议·杂律》)
值得一提的是,《职制》中所涉及的律条乃是针对制书执行者而言,若其未能履行职能,便应按律处置;然律条出于《职制》者,其数目远多于“诈伪”“贼盗”等类属。如此严密的处罚,反映了制书的制定和执行程序,在当时已经具备了严格、完备的规章制度。
唐律对制书的相关规定,为后世提供了极好的参考和借鉴。自唐以后,历代律法中关于制书的律条,大多因袭唐代成法,并在此基础上稍做增损:《宋刑统》在“职制律”下设“制书稽缓错误”各条,“诈伪律”下设“诈为制书及增减”各条,其内容均同于《唐律疏议》的记载。明律亦以唐律为基础,在刑罚轻重方面略有参差。《历代刑法考·明律目笺》载,唐律“被制书施行违者”,明律改为“制书有违”,与“稽缓制书”并于一条,其刑罚较唐律更轻;唐又有“受制忘误”“制书误辄改定”二条,明律无;唐律“弃毁制书官文书”条,明律亦有此条,但规定“弃毁即斩”,量刑重于唐律。清律仍明律而定,制书律条更加详细、具体,以“弃毁制书印信律文”为例:
凡弃毁制书及各衙门印信者,斩。若弃毁官文书者,杖一百。有所规避者,从重论。事干军机、钱粮者,绞。当该官吏知而不举,与犯人同罪。不知者不坐。误毁者各减三等。其因水、火、盗贼毁失,有显迹者,不坐。若遗失制书、圣旨、印信者,杖九十,徒二年半。若官文书,杖七十。事干军机、钱粮者,杖九十,徒二年半。俱停俸责寻,三十日得见者,免罪。若主守官物,遗失簿书,以致钱粮数目错乱者,杖八十。限内得见者,亦免罪。其各衙门吏典,役满替代者,明立案验,将原管文卷交付接管之人,违者,杖八十。首领官吏不候交割,扶同结照者,罪亦如之[8]。
可以说,制书的发展和完善,乃得益于皇权的有力维护。其名称的调整、格式的确定、行文标准的提出,以及违反制书的律条规定,无不通过国家制度得以完成和实现。制书规范性的明晰与强化,客观上也使其作为“制度之命”的文体特性得以充分地展示和凸显。
二、制书功能的发展与演变
制书旨在颁布“制度之命”,这是汉制对制书功能的明确规定。所谓“制度之命”,即国家从礼制、道德、法令等方面对人们进行引导和规约,旨在通过汉制形成群体性规范和普遍性影响。《言文》:“制,裁也。上行于下,犹匠之制器也。《说文》云:‘从刀从禾。物成有滋味,可裁断也。’《礼记》有《王制》,《家语》有《庙制》,《通典》‘八政’中诸制也。”《珊瑚钩诗话》:“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文者,故谓之制。”《文中子·读书有制》:“帝者之制,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者乎!”这几种对“王言之制”的界定,涵盖了礼制、法制等诸层含义,它们恰恰是对“制度之命”的具体阐释。《独断》:“其文曰制诏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当是汉代制书作为“制度之命”的具体体现。
在汉代制书基础上,唐代制书功能得以进一步发展、演变。《旧唐书·百官志》载:“凡王言之制有七:……二曰制书,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革旧政、赦宥降恩,则用之矣。三曰慰劳制书,褒贤赞能、劝勉勤劳,则用之。”其中,“厘革旧政、赦宥降恩”相当于汉代赦令、赎令等制度之命,而“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则当是由汉代“申下上迁”的人事任免功能发展而来。由《唐大诏令集》的记载来看,“行大赏罚、授大官爵”而称制的情况最多,制书被普遍地用于立皇太子,册封妃嫔、公主、亲王、郡县主,任命或罢免宰相、将帅等等。相比之下,制书用于“厘革旧政、赦宥降恩”的情况则少得多,在确立新法、建易州县、祭祀、大赦天下等诸多关涉政事的领域,虽然也可见到制书的使用,但其数量并未形成一定规模,只有零星几次而已。这与汉代制书的使用情况明显不同。可以说,制书在由汉至唐的发展过程中,其功能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原本作为非制度之命的人事任免功能,至唐代则在制度层面加以突出强化,成为制书的主要功能,而赦令、赎令等制度之命,其功能在使用中则呈现出弱化的趋势。此外,“慰劳制书”被单独分出,而列为“王言七制”之一,则强调了制书“褒贤赞能、劝勉勤劳”的功能。《唐大诏令集》专设“慰抚”一类,所辑诏令多谓“宣慰制”,即当归于“慰劳制书”之属。
宋承唐制,《宋史·职官志》载:“凡立后妃,封亲王,拜宰相、枢密使、三公、三少,除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加封,加检校官,并用制。”《文章辨体序说》亦云:“其曰‘制’者,用以拜三公三省等职。辞必四六,以便宣读于庭。”其时始有“制诰”之称,《铁立文起》云:“下迨唐宋,制之文四六居多矣。至以诰论,李唐无其名而独盛于宋,制有妃嫔、宗室、赠官诸类,诰有命官、貤封、贬官诸类,其用亦不一云。”《涵芬楼文谈》:“宋世,制体专委除官之用。其代言之官,谓之掌制,又有知制诰之称。”此类制书的颁布亦形成固定规制。据《宋史·嘉礼志》载,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八月,太皇太后诏:“以皇帝纳后,令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两省与太常礼官检详古今六礼沿革,参考《通礼》典故,具为成式。”在议定纳后成式时,六礼亦皆颁制书,且制文内容明显在唐代纳后制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明清时期,制书功能与唐宋相去不远,大多用于立皇太子、后妃,授命封官以及祭祀等礼节仪式。
可以说,唐宋时期乃是制书功能发生演变的重要时期。在此之前,制书一直延续着秦汉以来的传统,标榜以“制度之命”,其本核内容是将皇命视为国家制度层面的标准、规则和法度,从而对人们的行为起到普遍性的指引和规约作用。逮至唐宋,制书则突出了授命封官的人事任免功能,其他制度性功能虽然仍在发挥作用,然相比之下,则显然有弱化的趋势。《文通》云:“以‘制’命官,盖唐宋之制也。古今文体之变,则作者所深悼云。”这一感慨,恰恰折射出制书功能演变的事实。
三、制书的变体形式
制书体式在后世发展中,亦经历了一番演变过程,衍生出“德音”这种新变体。将“德音”归于制书变体之列,乃由于作为制书别称的“德音”,在发展过程中,赦宥内容不断被强化,从而演变为一种特殊的赦令体式。可以说,这种新变体凸显了制书原本用以颁布赦令的功能。
汉代时,“德音”一词的含义和使用范围颇广。《汉书·匡衡传》:“窃见圣德纯茂,专精《诗》、《书》,好乐无厌。臣衡材驽,无以辅相善义,宣扬德音。”其中,“德音”乃指合乎仁德的圣贤之言。《春秋繁露·执贽》:“畅有似于圣人者,纯仁淳粹,而有知之贵也,择于身者,尽为德音,发于事者,尽为润泽。”“德音”则有“善言”之义。《后汉书·郦炎传》:“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此处“德音”意即好名声。
当然,“德音”也时常被作为皇帝诏令的代称而使用。如《汉书·董仲舒传》:“仲舒对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汉书·刘向传》:“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这里的“德音”均泛指诏令,并非特指赦令。不过,“德音”偶尔也含有赦宥之义,如《盐铁论·诏圣》:“夏后氏不倍言,殷誓,周盟,德信弥衰。无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势,而见夺于诸侯也。故衣弊而革才,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时,天下初定,发德音,行一切之令,权也,非拨乱反正之常也。”此处“德音”,即指高祖大赦天下。总体来看,“德音”只是泛指诏令的代称,其在汉代尚未形成一种诏令体式。
汉代以后,以“德音”指代诏令的现象极为普遍。如《魏志·贾逵传》:“昔先帝东征,亦幸于此,亲发德音,褒扬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晋王操之《为中书令启琅琊王为中书监表》:“中书职掌诏命,固非轻才所能独任。自晋建国,尝命宰相参领。中兴以来,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弥徽,德音四塞者也。”[9]《陈书·周弘正传》:“是以皇上发德音,下明诏,以大王为国之储副,乃天下之本焉。”总体来看,“德音”只是泛指诏令的代称,其在汉代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尚未形成一种正式的诏令体式。
到了唐代,以“德音”泛指诏令的现象依然存在。如《唐六典·中书省集贤院史馆匦使》:“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纪时政之损益。”杜牧《论阁内延英奏对书时政记状》:“旧例宰臣每于阁内及延英奏论政事,及退归中书,知印宰臣尽书其日德音及宰臣奏事,送付史馆,名时政记。”但同时出现的新情况则是,一些诏令开始以“德音”命名,如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闰三月三日《亢旱抚恤百姓德音》、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处分幽州德音》《戒励风俗德音》《长庆四年正月一日德音》等等,这表明“德音”在唐代已逐渐形成一种独立的诏令体式。不过名之以“德音”的诏令并非完全等同赦令,诚如《文体明辨序说》所言:“后世乃有大赦之法,于是为文以告四方,而赦文兴焉。又谓之德音,盖以赦为天子布德之音也。然考之唐时,戒励风俗,亦称德音,则德音之与赦文,自是两事,不当强而合之也。”《古今文综评文》则将“赦文”归于“德音”中的一类,其称:“德音之体,起于唐代,盖天子布德之音也。体于赦文为近,然赦文止言肆赦之意,德音兼及处分之事,义有广狭,故以德音统焉。”然施行赦宥,对于天子下达“布德之音”来说,显然是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大,也最易于见效的方式。从现实情形来看,也的确如此,有学者统计,唐中后期,含有赦宥内容的“德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禹成旼《唐代德音考》将唐中后期的“德音”分为两类,其中,不含具体赦宥内容的“德音”占总数将近一半,主要内容是赏赐和蠲免,而含有赦宥内容的“德音”则占一半以上。。那么,相比于汉代“德音”偶尔含有赦宥之义而言,在唐代“德音”之体中,赦宥则被逐渐强化,从而成为“德音”的主要内容之一。
至宋代,“德音”则成为赦宥中的一类。《宋史·刑法志》载:“恩宥之制,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凡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所被广狭无常。”“德音”与“大赦”“曲赦”三类,同属于恩宥之制。
编纂《唐大诏令集》的宋敏求即为宋人,关于“德音”,其称:“本朝之制,凡霈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种,自分等差。宗衮言:‘德音非可名制书,乃臣下奉行制书之名,天子自谓德音非也。’予按唐《常衮集》,赦令一门总谓之德音,盖得之矣。”[10]常衮是唐代人,其撰有《制诏集》60卷,他所言无疑为唐代“德音”情况。其时,“德音”乃是臣下奉行制书的别称,其范围要广于赦令,故宋氏宗衮所言,将赦令一门归于“德音”。而这与宋代“德音”已被确立为赦宥形式之一的情况明显不同。这种区别恰恰反映了“德音”的演变过程:本作为制书别称的“德音”,在其发展过程中,则不断强化和凸显了制书范畴中的赦令之属,从而演化成为一种特殊的赦令体式。
[1] 范晔.后汉书[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24.
[2] 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148.
[3]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378.
[4] 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926.
[5] 仁井田升.唐令拾遗[M].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477.
[6] 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7] 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内阁[M].台北县:文海出版社,1991.
[8] 马建石,杨育裳.大清律例通考校注[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379.
[9] 严可均.全晋文:卷二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63.
[10] 宋敏求,等.春明退朝录: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0:48.
(责任编校:白丽娟)
A Study 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Zhishu
WEI X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hua University, Jilin 132013, China)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Zhishu(imperial orders) can be investig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state system and its style. As far as the state system is concerned, Zhishu, i.e. imperial orders, developed and improved unde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imperial power and the national system specification. With the standardization of Zhishu, its name, format, writing, and the procedure of its implementation came to have a clear standard and legally stipulated. As far as the style is concerned, its evolution has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the function of Zhishu changed from issuing imperial orders to the forms of reward, punishment and the appointment of official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yle of Zhishu has the variant of moral lessons.
Zhishu;style; function; variant
I207.62
A
1672-349X(2015)05-0077-04
10.16160/j.cnki.tsxyxb.2015.05.019
——论汉文帝诏令的个性色彩